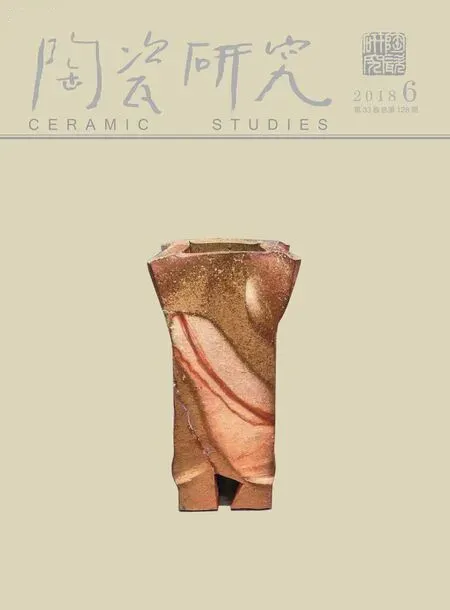中国古代陶瓷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的“误读”现象研究
何靖 杨莉萍
(江苏师范大学,徐州,221116)
1 前言
“误读”是翻译学中经常提到的概念,其所对应的英文为misreading或misprision,表示“理解错”“读错”,是指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和错误。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1975年出版了文学理论著作《误读图式》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作者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的“影响即误读”理论。该理论认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一种“缓别”的行为,实际上正确地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他提出将“误读”升华成为具有创造性和对原型具有影响的手段,是文学传承的连接方式。“误读”也是不同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错误地理解和评估是无法避免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相异的文化背景都可以是造成误读的客观原因。在中国古代陶瓷文化传播至西方的过程中,发生在西方对中国陶瓷学习和模仿的“误读”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无意或有意地“误读”是一个情节丰富的过程。
2 “误读”的存在:文化交流中的“视域”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输出的信息要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顺利解码,必然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接受者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思维方式等决定了他们的“视域”,如果以自己的角度对异文化进行解读,“误读”就会产生。人们按照自身的思维模式和“视域”去选择、解构和重构异文化,去认识和建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可见,不同文化交流之间的误读在所难免。
阐释学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从传统的阐释学思想出发,站在了生命存在的本体论高度,认为“此在”的人通过“理解”去把握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著名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观念,它有“先有”(Vorhable)“先见”(Vorsicht)和“先知”(Vorgiff)三个层面。海德格尔认为,“主体只要在阐释中进入‘理解前’,就被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所侵占,因此主体绝对不可能再是一个通体透明的文化处女,故而主体也绝对不可能在贞洁的状态下不带任何失贞的偏见追寻文本的原初意义”。①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继承了海德格尔“前理解”的观念,并且偏激地认为对于文本的解读是一种“偏见”的行为,“偏见”是文本得以顺利解读的“历史地平线”,他将这个“历史地平线”称之为“视域”(Horizont),而“视域”(Horizont)是主体阐释展开的基础。当人类带着自身的“视域”去理解历史、哲学乃至另一种文化时,我们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这是我们的“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交流的展开即是“误读”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思想和文化的“误读”史。
3 “误读”的发生:从迷恋到仿制
英国著名诗人约翰•盖伊(John Gay)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古瓷是她心中的爱好所在:一个杯子、一只盘子、一只碟子、一只碗,能够触动她肠中的火焰,给她欢乐,或叫她不得安闲。”②
诗中描绘地“她”是一位疯狂迷恋中国陶瓷的贵族夫人,这种迷恋神往的心理驱使着他们竞相购买、收藏中国陶瓷。世界各国对将中国陶瓷奉为“圣物”,上至宫廷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一例外。167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甚至为他的情妇建造了一座托里阿诺瓷器瓷宫;1700年巴姆堡和慕尼黑首先出现了瓷光辉映的“中国房间”;德国帝王奥古斯都(Augustus)收藏的中国和迈森瓷器多达57000件;欧洲的皇室和贵族们将是否拥有中国陶瓷看作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图1 18世纪英国产代尔夫特式青花花果纹盘
对中国瓷器的迷恋与嗜好,促使世界各地人争相仿效制作,尝试揭开其中奥秘。日本陶工早在唐代就模仿唐三彩烧制出了“奈良三彩”,越南和泰国已成为在中国影响下独立陶瓷生产体系的国家,他们生产的陶瓷产品和中国宋元时期的陶瓷器十分相似。从文献记载可知,中国瓷器最晚在9世纪已经运往中东地区,至10世纪,伊朗东北部、北非埃及等地都出现了类似陶瓷生产。西方各国对中国的瓷器的学习与仿制,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开始的,紧接着法国也开始试制瓷器。但直到1709年,欧洲还只能生产半陶半瓷的软瓷。西方瓷业的兴起,是从德国的麦森展开的,麦森瓷厂的创办人约翰•腓特烈•包吉尔(Johann Friedrich Boggio)经过不断地钻研,终于成功地烧制出了白瓷和蓝瓷。法国的赛夫勒瓷厂、英国的普利茅斯瓷厂也相继烧制出了硬瓷。
世界各国在学习和仿制中国瓷器的过程中,一般经历了完全模仿——部分模仿——自主创新这样的一些阶段。在最初的仿制过程中,绘彩的方法一般都将华瓷作为范本。在处理中,可以看到“误读”中国人原意的地方。例如常常绘有“拖长辫的华人,张伞成列,官吏乘舆后行;有时可见到美妙的东方景物,有大肚的弥勒佛像、亭台楼阁,配有中国或东方式花草以及各种怪兽。……又中国的桥,远瞰如曲折线条,在不习见中国式的桥梁的欧洲人眼里,结果仅成为装饰性的曲折线条”。③例如18世纪英国产代尔夫特式青花花果纹盘(图1)中的“洋葱”并不是指真正的洋葱,根据历史学家的观点,它极有可能是中国瓷器上桃子和石榴甚至是菠萝的变体。
4 “误读”的原因:差异与认识
4.1 审美文化的差异
异质审美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差异,是审美文化发展和变换中的正常现象,这也是造成陶瓷文化交流中“误读”的重要原因。在中西方绘画交流中,彼此间的误解尤其突出。例如清代画家邹一桂说道:“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小山画谱》)中国画家们往往不谙透视解剖写生,难免描虎类犬。同样,绘画观念的不同加上交流的缺乏,传统中国绘画早期并不能得到西方人的认同。英国人图古特•唐宁(Toogood Downing)曾经写到:“在我们外国人看来,这种风景画除了比较随意和自由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④
中国艺术家着墨于轮廓与体积感,令观者觉得那流动不定的场域朝向三度空间展开。中国画里的松树,松枝曲折、丛叶簇拥,垂悬地面或冲入天际,以其丰富地动态张力与自然律动展示出无穷尽的生命力。伊斯兰画家笔下呈现的松树,枝干蜿蜒、一丝不苟地细密缠绕,以扁平、对称的轮廓呈现,这种优雅的几何图案展示出秩序井然地静态之美。
“两大系统原先几乎是在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下各自发展而成,因此自然体现不同的美感价值与概念——而审美观本身,又是基于双方对现实事物迥异的观点”。⑤因此,对待同一符号不同的认知则又是中西方审美文化中的又一大区别。以“龙”的形象为例,在不同文化中,龙的特征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中国,龙是家喻户晓的祥瑞动物,在西方,龙却成为一种怪兽,《圣经》将龙描述为邪恶、魔鬼的象征,把它喻为人类的敌人。中国红象征着吉祥、喜庆,但在西方红色则象征着血腥、邪恶与暴力,赤龙更是与圣经中的“撒旦”联系在一起。中亚织工把中国龙改头换面,在织锦缎上出现原产地所无的凶恶模样,从令人敬畏的帝王象征变成吓人的喷火怪物。同样地,原本在中国象征皇后的凤凰,摇身变为好战善斗的形象。17世纪初期的蒙兀儿绘画里,凤鸟则与狮身象头的怪物扭成一团。中国工匠笔下的龙,是百虫之长,是深具动感的生物,是元气活力的表征。它们具有各种非凡的本领,或翻飞盘旋云中,或划过天际追逐火珠。埃及马穆鲁克的陶工和砖工,浑然不觉中国传统龙的意义,将龙的母题化为连续性的装饰特色,静态地安置在一系列模样相同的凤凰两侧。
中国瓷器绘画上的图案种类繁多,常见的植物有山茶、海棠、百合、木兰等;动物有狮子、麒麟、苍鹭、鹌鹑、孔雀、鹤等;象征长寿、财富、坚忍的万年青、竹、梅、葫芦、龟、金鱼、鹿等。还有华伞、宝瓶、宝珠、宝螺、莲花、法轮、宝杵、圣菌、葫芦等吉祥表征图案。这些图案内藏的寓意传递着丰富的内涵。比方“金鱼”的“鱼”,就和“丰裕”的“裕”同音,只是声高有别;“鲤”是“利”,所以鲤鱼逆流而上象征学子苦读准备科举应试;蝙蝠是“福”,“红”为“宏”,因红蝙蝠是意指“巨大福气”之意……。对深谙中国文化的文人来说,这类纹饰图案的最大吸引力正在其多重寓意。不过要理解这些装饰元素背后隐藏的意义,必须具备相当才学与艺术赏鉴品味。可是一旦这些绘瓷出门到了远地,种种中式图像脱离了原生土壤,纹饰中的多层含意自然有所损失,或变成纯粹的装饰图案,或取得当地文化脉络之下的新意涵。“八宝纹”是中国传统的器物的常见纹样,有辟邪、纳福、吉祥之意。可是在外国人眼里,它们只是一种漂亮的装饰纹样,对象征寓意不甚了解,纯粹从它们装饰性角度来考虑使用。结果就会在“八宝纹”上附上缎带等其他纹样,获得了新的审美知觉,却完全丧失了原有的装饰寓意,给人一种不中不详的感觉。
4.2 对中国缺乏认识
西方人最早主要是依靠游记信札等文字资料和传教士、商人带回去的物品认识和了解中国的,最出名的莫过于《马可波罗游记》了。其实,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在最早是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古希腊的传说开始的,旅行家阿里斯提亚斯长诗《独目篇》是西方人对中国最早的描绘。
18世纪初,欧洲大陆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热”,一大批西方学者、思想家狂热地崇拜着中国,以德国哲学大师莱布尼茨为代表,“在17世纪欧洲的伟大思想家中,莱布尼茨是对中国思想最感兴趣的一个。”⑥这位被誉为那个时代西方最早全面认识中国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文明生活的规范”上远远超出欧洲。法国学者伏尔泰曾在《风俗论》中写道,“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⑦同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英国作家笛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批评中国的学者,他们为了捍卫“西方价值”,对中国的文化与制度、国家与社会、帝王及民众等进行过严苛的批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限于交通条件,无论是赞扬或是批评中国的西方学者、工匠和艺术家亲自前往中国的机会很少,元好问诗“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论诗三十首》)形象地描述这一情景。在17世纪,由于缺乏地理知识,很多西方人们无法区分中国、印度与日本,因此常根据临摹“秦川景”——中国的绘画、陶瓷、版画、丝织品上的图案来展开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显然,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根据商品上所见的中国形象,凭想象来建构中国,他们相信,这样的中国在美丽和魅力上都胜过实际的中国”。⑧一方面,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和加工,它们来源于现实却又不同于现实。中国陶瓷工匠及艺术家在进行陶瓷创作时,从现实中获取灵感和素材,这是基于现实的第一次想象。另一方面,中国陶瓷输出至他国后,便成为外国人了解、感知中国的第一手素材——“原版”。外国人在进行陶瓷创作时,又会加以理解和变化,这是基于“原版”的二次想象。经过两次想象的陶瓷产品经过变异,离中国现实生活也越来越远。例如尼德兰北部的制陶工人能描摹景德镇瓷器图案时,边纹、花朵等都能几近乱真,设置布局都完全符合中国万历时期瓷器的标准。但描绘的中国人物形象就有点古怪可笑,是脱离原汁原味的改头换面。有时绘图者在碟盘、杯盒等器皿中央索性采用欧洲的内容主题,而四周则环绕中国万历瓷器常常采用的饰纹饰边,甚至揉进了东方其他国家瓷器图案纹饰的样式,拼凑的模仿痕迹是十分明显的。
5 从“误读”到“悟读”:迎合与需求
19世纪以后,中西方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但是反映在西方陶瓷设计及创作上的“误读”仍然大量存在,但是,这已经不是被动意义上的误读,是一种创造性误读,可称之为“悟读”。出现这种“悟读”的原因,主要有三:
5.1 迎合“以我观物”的认知惯性
从审美感知的本质层面来看,并不存在单纯的观看,观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主客二分、以我观物思维偏见。在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思维统摄下,“观看就是划分”,⑨这种思维在一开始就将东方对象置于西方主体的对立面,将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样)”⑩。为了完成西方主体规划、建构异域文化的使命,鲜活流动古代中国文化成为他们任意选择和切割的对象,这种有目的的行为是以“他者”的存在来补充自己的匮乏,是借助一个未必可靠的镜像来肯定和确立自身。他们在在表面的客观研究之下,隐含着某种想象的成分,所谓对象化思维由此形成。和西方文学中的“套话”一样,西方的“中国风”陶瓷作品大量出现了程式化的设计作品。伞盖、乐器、旗帜等一些和中国人关系特别密切的器物,它们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特定的道具。例如,中国的皇帝和官员身边必定有撑着圆伞的侍女,“谓国君威仪之物,若今繖扇之属”,⑾而普通的中国人也撑着各色的伞,虽材料、造型有异,但基本都是锥形的伞盖。由此,伞盖的圆锥形也大量出现在西方“中国风”陶瓷、织物中,如宝塔式的房屋、中国人头上的帽子等。扇子在古代中国也有很多讲究,不同的使用场合和功用也决定了扇子造型(扇柄、扇面、扇形)、材料与制作工艺的差异,当扇子传入欧洲后,也成为世纪西欧上流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道具,它和伞一样,常在描绘贵族生活场景中起到衬托威仪的作用。这些器物就是“中国风”设计的典型标志。
在欧洲人有关中国的著述与插图中,有很多关于中国宫廷生活的描绘,在欧洲人的眼中,宫廷生活的美好是他们的理想生活。在他们的描绘中,中国人宫廷生活繁文缛节甚多,其中最常见的是作揖、跪拜和磕头等。在欧洲陶瓷“中国风”设计中,画面中常见的是身穿长衫、头戴尖尖的帽子的皇宫贵族们,他们悠闲的品茶、聊天,接受官员的朝拜。因为地理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东西方的人们只能以想象的方式来构建出异邦的“他者”形象,他们不仅形貌不同于自己,而且在地理空间上是遥远的,在文化上是陌生的、奇异的,相对于“他者”来说,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并以一种封闭的状态缓慢地、较为稳定地进行着文化的发展。西方人在“中国”身上不断发现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这个他者代表的是不完善的“自我”,也有的时候“中国”是自我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可见,这种“误读”是一种自觉行为,是艺术创作的主体在自觉的基础上,通过对所参照的文化原型的主动性“误读”,有意制造具有模糊性和程式化的“误读”结果。

图2 16世纪末叙利亚生产的葡萄纹大盘和元代青花葡萄纹大盘

图3 迈森蓝色洋葱系列瓷器

图4 迈森蓝色洋葱系列瓷器
5.2 满足本国人的审美需求
“千里之外的遥远文化误读中国符码,自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虽然规模程度各有不一”。 有时异域工匠照单全收中式形状与图案,不做任何更易变动,⑿有时则极具创意地结合当地元素。他们不知中国瓷器上所绘的中国莲花属于水生植物,却将它们变成庞大的躯干和细小的叶片。在有些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的陶器表面,绘有巨龙阔步于高耸的莲花丛林之中的图案。
欧洲人笔下的“中国风”设计作品中,大量出现的中国人物形象中,几乎包括了各种阶层和职业。早期的欧洲人对东方人不熟悉,常出现穿着中国服饰的高鼻子深眼睛的白种人的面相。到洛可可时期,大多数人物形象已经改为东方面孔了,说明欧洲人对中国人有了较多的了解。但中国风陶瓷人物经常是东方人的面容、西方人的服饰,或西方人的发型、中国人的面相。有时他们还用金色绘制中国人物,称之为“金色的中国人”,颇为新奇有趣。越到后期,瓷器上中国人物的服饰、相貌上越趋于不真实,更多的是不伦不类的中西混合,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多元的、模糊的人物形象。这种审美的改造早在16世纪的波斯已经出现了,对比图2上图16世纪末叙利亚生产的钴蓝釉葡萄纹大盘和下图元代青花葡萄纹大盘,可以发现波斯青花在有选择地保留了元明青花代表纹饰的同时,新增了许多极具当地艺术特色的构图方式和图案主题,并对传统的“中国样式”进行了符合波斯审美的改造。这种改造既仿效、取法中国的古典美学,又迎合了本国人的审美需求。
“中国瓷器不仅在装饰方面,而且在造型方面,依然是欧洲的典范。像我们从麦森瓷所看到的那样,它的模特儿就来自中国”。⒀普鲁士的炼金术师约翰•弗里德里希•贝特卡于1709年成功烧制了硬质瓷器,这也就是麦森瓷器的起源。由于诞生初期就继承了中国瓷器的遗传因子,麦森瓷器著名的蓝色洋葱图案从18世纪开始生产以来,自然也就拥有了中国古代陶瓷名作的韵味,但也加入了很多西方的审美因素,这些中西混杂的麦森瓷器,一直在全世界受到热烈追捧,今天依然畅销(图3、图4)。在花纹装饰上,他们还效法中国白瓷上的浮雕,又从玻璃制作中吸收的技巧来改善这种器皿的装饰,像西方的巴洛克风格的玻璃艺术品那样雕刻着奇形怪状的纹饰、花和符号,然后将表面像玻璃那样予以磨光,并不失时机的镶嵌上贵重金属,甚至宝石。贝特卡带领着从波希米亚招收玻璃雕刻工,让麦森瓷器闪耀着巴罗克豪华艺术风格的光芒。

图5 19世纪英国青花柳纹碟
5.3 市场竞争地需要
在这方面最有名的要数非常受美国消费者欢迎的绘有柳树图案的瓷盘了,围绕这一征服西方世界的图案有很多种版本的故事、传说。19世纪稍后,一些富裕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游览,满脑子仍然西方瓷器上的山水图案和柳树图案。19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沃尔特•博尔(Walter Bole)的游客在广州观光,看到中国园林时,立即将其与瓷器上的图案联系起来:“我禁不住想起英国威基伍德公司烧制的柳树图案瓷器。”⒁在往后的游客记述中,这种偶然相似的关系却变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了。19世纪90年代的观光客弗朗西丝•克拉克(Francis Clark)游览广州的一家园林后声称:“著名的柳树图案瓷正是从这里复制的,这个图案见于我们的祖母和曾祖母的瓷器上。”⒂但是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柳树图案并非来自中国,而是18世纪70年代一位英国陶工托马斯•特纳(Thomas Turner)为什罗普郡的考利公司烧制瓷器时的创意,他显然是在模仿流行的中国山水画,那是广州瓷上的山水图案。虽然这和中国正宗的柳树图案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但瓷器商人为了扩大销路,在非正宗的柳树图案问世不久,就有许多厂家就复制它们(图5)。为了赋予这个图案以东方神秘而浪漫的情调,围绕非正宗中国瓷的英国柳树图案瓷逐渐衍生出一个伪中国故事。这是一个有关爱情、危险和冒险的故事,那是投射在中国风景上的虚构故事。故事在英国极为流行,甚至很快跨洋迁移到美国,进入了美国诗歌。诗歌这样写道:
在一个黄金成堆的国家,
有一位有钱的员外,还有美丽的孔茜,善良的张生。
他们苦苦相爱,躲进茅屋,
私奔到一座美丽的小岛上。
狠心的父亲追到那里,
要把绝望的恋人伤害。
老天救了可怜的人儿,
孔茜和张生变成美丽的小鸟。⒃
虽然瓷器鉴赏家沃伦•考克斯(Warren Cox)认为:“愚蠢地复制这一图案,缺乏中国画的任何元素,没有真正的审美追求,由此衍生的伤感故事迎合18世纪晚期感情脆弱的老太太。审美意识之贫乏,无以复加。”⒄但是柳树图案仍然在瓷器中被大量复制,成为每一个英国瓷器制作工厂必备的图案,也成为英国民众最熟知最喜爱的瓷器图案。这个虚拟的伪中国故事也随着柳树图案的复制,不断演化成各种版本的故事、诗歌甚至是歌谣传播开来。
5 结语
在 19 世纪后期以前,欧洲工匠并不在意对中国图式完全正确地仿制,况且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摆脱“正读”束缚的主动“误读”,却成为西方“中国风”产生创造性的动力。在中国古代陶瓷文化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中间流通环节越多,“误读”就越丰富,情节就越丰满。“正读”只是一个简单的传输行为,而“误读”则充满了文化,“误读”构成了一部宏大的人类陶瓷文化传播史。
注释
①梁潮:《东方丛刊》[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②约翰•盖伊:《诗集》(诗神丛书)第1卷[M].1893年版,第223页。
③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3页。
④[英]M•苏立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M].陈瑞林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⑤[美]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M].郑明宣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页。
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8页。
⑦[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7页。
⑧ Joan Kerr Facey Thill,“A Delawarean in the Celestial Empire:John Richardson Latimer and the China Trade”(MA Thesis,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73), 51.
⑨[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M]. 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⑩[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0页。
⑾《春秋左传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34页。
⑿同5,第192页。
⒀[英]迪维斯:《欧洲瓷器史》[M].熊寥译,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⒁Walter Bole,"A Day in Canton,"Appleton's Hournal of Popular Literature.Science,and Art(July 23,1865),108.
⒂Francis E.Clark(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ociety of the Christian Endeavor Our Journey Around the Worm(Hartford;A.D.Worthington&Co.,1894),172.
⒃ [美]约翰•海达德:《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9页。
⒄同16,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