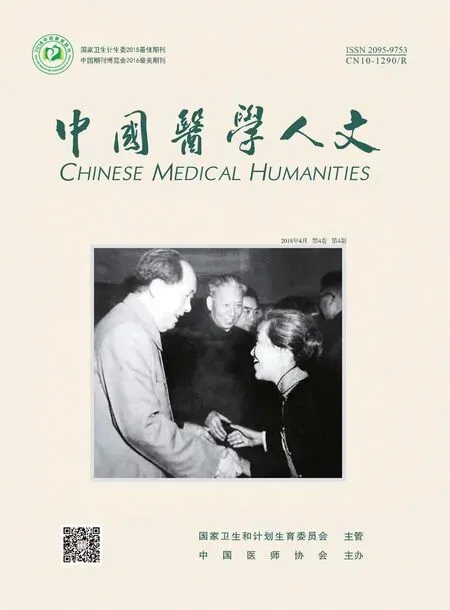一杯青稞酒
文/郭 伟

2007年,作为一名援藏医生,我来到拉萨市海拔3 800米的尼木县。尼木,藏语意为“麦穗”。在吐蕃王时期(公元七世纪),为“乌如”所辖。十三世纪,属香万户的势力范围,元世祖时代尼木既已设宗,明朝时尼木被译成“聂母”,清朝则称作“尼莫”“尼穆”“尼木”“尼冒”等,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宗。民主改革前尼木境内分设尼木宗和麻江宗。1959年二宗合并为尼木县,隶属拉萨市管辖。当地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为了让广大农牧民得到我们的医疗服务,一年的时间,我走遍了尼木8个乡镇、30多个村子。
有一次,我们到偏远的帕古村义诊,那里的山路崎岖险峻,我开着心爱的吉普车上下颠簸、左摇右晃地走了好久,才到了村委会。下车后踩在地面上有种坐船的感觉,只走了几步路,我就感到胸闷气短,双脚又像踩在棉絮上一样。随行的同志告诉我那里海拔将近4 300米,不能快步走。我停下来,扶着车子站住,让狂跳的心脏缓下来,但看到满院子有序地排着队,已经等候多时的老乡,我们立即就开始准备义诊工作。
这时,一个满脸沧桑的老汉,把一杯青稞酒捧到我面前,虔诚地请我喝。那是当地人自家酿的青稞酒,酒色有点浑,上面还飘着点点说不清的絮状物。我有点酒量、也爱喝青稞酒,但等候义诊的群众多、时间紧顾不上喝。从专业角度也有一点点畏惧,怕大肠杆菌超标,我这瘦瘦的身子骨承受不了,就向他摇摇头示意——不喝。老人失望地走开了。
义诊开始,我忙着问诊、查体、开药……冷不丁一抬头,又看到那位老汉依然端着那杯青稞酒,在人群外凝望着我,高原明媚耀眼的阳光下,他脸上那斧雕石刻般的皱纹尤为明显。我心头一动,无暇多想就向他笑笑,继续工作。老人仿佛受到了鼓舞,拨开众人再次把酒杯举到我的面前,脸上的表情或激动或怯懦。很明显,老人是真诚的或者说虔诚的,为什么呢?一个念头在我心头闪过:西藏部分偏远地区信奉萨满教,有时候信众会因为觉得对方面善有福相而投毒,目的是留下性命也就是留下了福祉。电光火石地一闪念,我同时也否定了这种可能,但还是拒绝了他,老汉又失望地走开了。
义诊结束,人群散去,唯独那个老汉还举着那杯青稞酒站在夕阳里,拖着长长的身影,显得有些孤单。我无法不为所动,赶紧走上前去,请人用藏语问他为什么,原来他是我的一个病人,曾经病情很重,家里人都准备后事了,听说县里来了北京医生,他们就走了好远的路来找我看病。
这时,才想起来2个月以前的那个傍晚,我正在吃晚饭,值班医生打来电话:“郭大夫,来了一个重病人”。我放下碗直奔病房,远远地就看到格桑医生正和几个人一起把病人从马背上托下来。我冲到近前,借着灯光观察,老汉已经昏迷,胸廓彭隆、呼吸急促,不用听诊器都可以听到肺内呼噜呼噜的痰鸣……以我的经验这是个慢阻肺、心肺功能失代偿的患者,病情很重!可是当地没条件查血气,更别说实施机械通气了,怎么办?转念又一想,几十年前没有这些现代医疗设备老一辈医生不也照样治病救人吗?我立即用身边现有的简单器械为老汉做检查,同时让护士开放静脉通道,老人的血管瘪瘪的不好扎,血压显示只有70/50mmHg——血容量不足!我急忙亲自找到一根稍粗一点的血管,一针穿刺成功,开始快速扩容;我又找人取来自己用的简易血氧监测仪,一查,老人的血氧饱和度仅仅60%——属于重度呼吸衰竭!没有呼吸机我们就低流量吸氧加呼吸兴奋剂,没有化痰药我们就频繁亲手为患者拍背排痰,每2小时测一次血压,心率血氧随时监测记录。
在我们的精心治疗下,老汉终于逃过了鬼门关。他们或许是第一次感受到,看医生比求菩萨灵验,所以一直想找机会表达谢意。看着老汉那热切、甚至乞求的眼神,我哪里还管什么大肠杆菌、萨满教,哪里还管什么高原反应和身体疲劳,按藏族的习俗“三口一杯”,将酒喝尽。顿时,老汉笑了,那笑容如孩子般纯真。我的内心也涌动起一股暖流,有欣慰,有感动,更有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