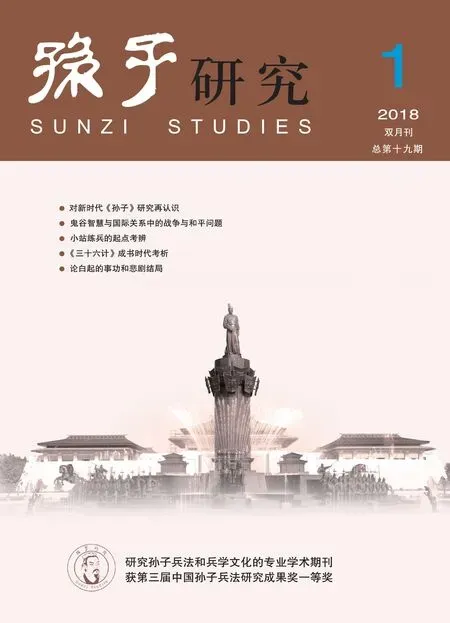以晋楚之战谈用兵之道
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页。。邲之战是春秋中期晋、楚两大强国争夺中原霸权的重要一战,战争中展现出了高超的谋略施展和超出当时古军礼②古军礼,西周时期礼乐制度规范下的战争基本礼仪,其核心理念在于推崇堂堂对阵,反对诡诈用兵。规范的战争行为,而这些灵活“悖礼”的作战原则恰恰属于后世兵家“诡道”的范畴,战争发生的时间则早于现存任何一部古代兵书的成书时间,无疑春秋乃至以前的战争理念的微妙变化对于后世兵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价值,特别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兵学文化。邲之战中高明的用兵之道则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分析邲之战的用兵之道也是认识、体会春秋时期战争理念微妙变化的重要途径!
自晋楚城濮之战后,晋国便牢牢地掌握着中原霸权,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住了楚国北进中原的势头,将楚国势力限制在南方和江淮地区。但随着晋国政坛动荡不断、卿大夫倾轧内耗严重,晋国国势日衰。相反,楚国则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特别是楚庄王在位期间,他整顿内政、扩充军备、结交与国,始终将争夺中原霸权作为楚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使得楚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富强。邲之战则是楚庄王问鼎中原的重要战略举措,此战楚军大胜晋国,使得楚国得以将势力延伸至中原诸国,宋、郑等中小国家纷纷投入楚国阵营之下,中原霸权随着邲之战的落幕而易手于楚。然而,战前楚国却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战胜对手,也曾犹疑,不敢轻启战端,那么最终楚国又是如何赢得胜利的呢?
一、战前运筹
公元前597年,楚国降服郑国不久,晋国即发兵来救,楚庄王得知晋军已至,意欲撤退,试图避免与晋国发生直接冲突,即“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③《春秋左传注》,第729页。,但楚庄王的幕僚们却劝谏他与晋一战,并从宏观上对楚晋实力作了概括性地分析。
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①《春秋左传注》,第730页。
伍参通过对晋军统帅层的详细分析,得出晋军必败的结论。他认为,晋军中军帅荀林父新任伊始,无威信可言,并且晋军三军将佐各自为政,不肯用命,从而认为楚国一定能够战胜晋国。同时,他还以楚庄王若不战而退则是惧怕晋国臣子乃是楚国的耻辱为由,激励楚庄王决心一战。这种分析看似简单,却涉及军队指挥的一大重要问题,即指挥权的分配问题,亦即军权能否集中的问题。战争胜负虽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但军队主帅却是得以盘活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关键之人。主帅的素质事关战争成败,国之存亡。故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作战篇》)诚哉,斯言!战争中,军队的指挥权统一于主将,方可令行禁止,指挥如一,而晋军中军帅荀林父新任帅位不久,在军中尚无威信,且手下又多是桀骜刚愎之将,因而实难做到军令如一,指挥三军若使一人。信,是为良将者的重要素质之一,将无威信,众将不服,政令难以有效执行,指挥必然难以集中统一,军队自然也就如散沙一般,软弱无力!
另一方面,晋军在楚军攻下郑国两个月后才发兵救郑,已错过救郑抗楚的最佳时机。同时,晋军战前诸将的分析已经预示着楚军不可敌的趋向。然而,这种理性的分析却没能转化为有效的执行力,而晋军主帅缺乏决断,战和犹疑,却对下属的莽撞举动纵容迁就。上军将士会理性地认识到,雄才大略的楚庄王“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也”②《春秋左传注》,第725页。,明言楚国在楚庄王的整顿下,政通人和,上下齐心,因而主张晋军避其锋芒,待楚军撤退后再行征伐降楚的郑国,即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武之善经也”③《春秋左传注》,第725页。。而刚愎自用的中军佐先縠却以“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④《春秋左传注》,第726页。,害怕晋国霸业丧失在自己手中,而擅自率中军部分兵力率先渡河,此时晋军亦不得不全军渡过黄河与楚军对峙,以决定下一步行动。这一过程中,晋军中军帅荀林父指挥无方、优柔寡断,任由部下摆布,从而一步步陷入对楚作战的泥潭。先縠率军渡河以后,司马韩厥说:“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⑤《春秋左传注》,第728页。劝中军帅荀林父率全军渡河。这种与其看着先縠擅自行动,不如全军一起行动有罪同担的作法,也是无奈之举。然而,晋军上下并没有意识到真正不可敌的并不是楚军,而是难以克服的内部不合。孙子曰:“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晋军知不可以战而战,上下乖张、政出多门,却一意孤行、铤而走险!
一方面是楚军的知彼知己、胸有成竹,另一方面是晋军的“明知不可而为之”。楚军战前运筹、料敌制胜,且执行有力,明显已经先胜一局!
二、楚军示弱求和, 示形动敌;晋军不睦,进退失据
孙子曰:“能而示之不能”(《计篇》)、“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行军篇》),即进攻一方为了掩饰进攻企图、进一步麻痹对手,往往采取卑辞厚礼、退却求和等战术手段造成对手的错觉和疏忽,从而出其不意地击垮对手。示弱以骄敌志,示形以怒其师,示弱的反面即是适时地以相应的战术手段调动、激怒敌人,使其失去理性,从而致其于失败之地。邲之战中,楚军通过一系列的战术手段牢牢地掌握着战争主动权,概括而言,不外乎示弱求和、示形动敌。
首先,楚国力争主动,示弱求和:
“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闻二先君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隨季对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勿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①彘子即先縠。以为馅,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②《春秋左传注》,第733-734页。
楚国少宰可谓言语谦卑,极力陈述楚国无意,也不敢冒犯晋国,辩称此行只为制服郑国而已。这虽为外交辞令,却表现出对晋国极大的恭敬,也表现了楚国的大国风范。而隨季的回答也可谓言辞谦逊,义正辞严,不仅维护了晋国的声誉和出师的合法性,也表现出对楚国的尊敬,完全使晋国占据了主动权。然而,隨季有礼有据的外交辞令却被中军佐先縠认为是谄媚楚国,竟然另派赵括骄横地告知楚使,晋国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楚国赶回去。这种强横的外交言辞不仅低估了楚国的战略意图,而且充分地显示了晋军帅并无专权,将帅不和,也为晋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楚军第一步示弱求和,虽遭到了晋国的强词回应,却进一步摸清了晋国将佐之间的矛盾,并且也达到了卑辞以骄晋军的目的。但是,开战的时机并没有到。此时,晋军内部虽军令不一,但尚未出现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分裂的迹象并不明显。于是,楚军继续向晋军抛出假信号,以迷惑举棋不定、战和不决的晋军。“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④《春秋左传注》,第734页。“求成”即求和。这虽是楚军第二次遣使于晋,但相比于第一次晋军强硬地叫嚣要与楚国开战,这一次晋军毕竟答应了和谈的请求。晋军前后两次相左的态度,并不是说明晋军决策层意见逐渐统一,而恰恰凸显了晋军将帅之间的矛盾分歧。这也表明,时至于此,晋军内部仍未就战和问题达成统一意见。大战在即,如此犹疑不决,实乃后患无穷。吴子曰:“故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⑤骈宇骞、李解民、盛冬铃等:《武经七书·吴子兵法·治兵第三》,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8页。晋军中枢指挥乏力、缺乏决断,可见一斑,失败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另外在此之前,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戌以所谓“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⑥《春秋左传》,第730页。游说晋军发兵攻楚,无论郑国此举是自留退路的考虑,还是受楚军所指使,都起到了分化、麻痹晋军高层的目的。
楚军敏锐地觉察到了晋军前后两次态度的转变和晋军内部指挥分散的问题,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激化晋军内部的矛盾,以分化晋军。于是楚军派出小股骚扰部队,挑衅晋军,“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⑦《春秋左传》,第730页。。“致师”即挑战、挑衅对方。楚军“示形动敌”这一招不可谓不高明:一为试探晋军虚实,摸清晋军的战备情况:二则在于挑起晋军内部不合,特别是迫使晋军内部如先縠等主战派的反弹。果然,晋军内部的主战派早已是蠢蠢欲动,楚军此次前来挑衅恰恰给了他们反击的借口。接下来晋军的两个举措已然将晋军推向了战争的泥潭。史载:“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弗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①《春秋左传注》,第736页。魏锜因私人恩怨,意欲陷晋军于不利,在请“致师”不许的情况下,“请使”竟得到应允,而关于请使的目的,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应不是向楚军宣战,否则不会得到同意。在这一过程中,魏锜骗得晋军高层的同意,假意求和,实则私自向楚军宣战,从而致晋军于不利境地。更为糟糕的是,晋军高层竟在同样一个问题上栽倒两次。“赵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请挑战,弗许。请召盟,许之,与魏锜皆命而往。”②《春秋左传注》,第736页。赵旃的套路跟魏锜可谓如出一辙,都是出于私人恩怨,以逞己意,欺骗晋军高层,私自与楚军开战,陷晋军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然而,《左传》《史记》等史书并没有记载晋军统帅层缘何会同意两者的要求,据史书对战争的描述推测应是晋军统帅层意见本就不统一,这些自相矛盾的事件极有可能是战、和两派妥协的产物。
实质上,军队各级军官任意妄为,不听指挥,除了说明他们各怀私心外,更加说明统帅层管理涣散、指挥乏力、令出多门,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指挥如一,以至于纵容各级军官酿成大祸。然而,指挥中枢的松散无力才是最致命的,其决策正确与否才是决定晋军成败与否的关键。如果此时晋军本部做好万全准备,以应对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那么还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正如孙子所言:“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以不可攻也。”(《九变篇》)然而,晋军非但没能做到备战以应不虞,却做出了一系列的莽撞之举。在魏锜、赵旃相继出发之后,郤克认为“二憾往矣,弗备,必败”③《春秋左传注》,第736页。,要求晋军本部加强战备。中军佐先縠却以“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④《春秋左传注》,第736页。为借口加以拒绝,先縠这种带有推卸责任的言辞,突出说明晋军统帅层的散漫无力。士会再劝,先縠仍不答应,于是晋军上军径自做好战争准备,中军一部则准备好了撤退的舟楫。另一方面,晋军担心魏锜、赵旃有失,于是派部分兵车前去接应,却未曾料到前去接应的晋军竟被楚军误认为是前来进犯的大军,而晋军统帅层也未曾料到魏锜、赵旃二人竟会擅自向楚军宣战,双方的误判致使两军提前开战,不同的是楚军已经在此前做好了万全的战争准备,而晋军各部却是各自为政,统帅层仍抱有和谈幻想,疏于战备,结果被楚军当头痛击。
三、楚军先发制敌,掌握主动;晋军指挥不力,号令不一
先发制敌是中国传统兵学中久已有之的作战原则,是抢占先机、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重要原则。强调先敌发现、先敌准备、先敌进攻、先敌制胜,是速度、时机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体现,它往往能够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从而一举制敌。先发制敌对一支军队具有很高的要求,要求能够高速机动、高效运转,能够统御全局、适时地发现对手的弱点,乘其疏忽松懈之时,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快速发起打击,并战胜对手。邲之战中,楚军始终牢固地掌握着战争主动权,强调抢占先机的重要性,从而达成了先人制敌的效果,战争中楚军先行向晋军发起集团冲锋,最终毕其功于一役,大胜晋军,将孙子的“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理论阐释的可谓淋漓尽致!
晋军赵旃部以“召盟”的名义在楚军阵地前挑战,遭到楚庄王亲自督军驱逐,即“王乘左广以逐赵旃”①《春秋左传注》,第738页。。这本属小规模军事冲突,尚未导致晋楚全面开战的地步。然而,在冲突前,晋军害怕赵旃等人此行激怒楚军,因而派兵车(数量不详)接应,即“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使 车逆之”②《春秋左传注》,第738页。,不曾想却给晋军带来灭顶之灾。楚军潘党部在武力驱逐魏锜部时,发现远方战车扬尘弥漫,即“潘党望其尘,使骋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亦惧王入晋军也,遂出阵”③《春秋左传注》,第738页。,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楚军本部,于是楚军大军尽出,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向晋军发动全面进攻。
“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遂急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④桓子即晋军中军帅荀林父。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⑤《春秋左传注》,第738-739页。大战在即,楚令尹孙叔敖虽无法侦知晋军此番前来的目的,但时间紧迫,晋军已然挑起了战争,且楚庄王尚率王兵驱逐赵旃部,晋军后援踏烟尘而来,楚王甚至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孙叔敖当机立断,决定抢占先机,率先向晋军发起攻势,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冲杀过去。虽然从史料来看孙叔敖误判了晋军的作战意图,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楚军决心一战的战争计划,反而是孙叔敖的当机立断占尽先机之利,一举制敌,打的晋军措手不及,致使晋军全线败退,溃不成军。与此同时楚军两翼左、右拒对晋军展开了全面攻势,一方面“工尹齐将右拒以逐下军”⑥《春秋左传注》,第739页。,楚大夫工尹齐应归楚右军将子反节制,这里未言子反何去,不可知;另一方面“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⑦《春秋左传注》,第140页。,楚军左军将为子重,左拒大部应是由子重统属。面对楚军全线攻势,疏于战备、互不统属的晋军或各自为战、或争相逃命,晋军溃败!《史记·楚世家》对此进行了简要叙述“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⑧(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楚世家》,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54页。。由“大败”一词可见晋军损失之惨重。

晋楚各军将帅(依据《左传》)
反观晋军,在大战的生死关口,身为全军统帅的荀林父统军不力、疏于战备、毫无作为,楚军掩杀过来却命令晋军迅速渡河撤退,且号令先渡河者有赏。此令一出晋军瞬间崩溃,争相逃命,为抢险渡河自相砍杀者不计其数,舟中断指无数,其情景令人发指!这绝非夸张性的描述,《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军败,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众。”⑨《史记·晋世家》,第2022页。晋军战前不知备战,战败后仅凭中军大夫赵婴齐事先准备的些许船只强行渡河,其结果可想而知。晋军统帅层的指挥乏力、号令不一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晋军上军和中军赵婴齐部,由于战前准备周密,基本全军而退,中军和下军可谓损失惨重。幸运的是,在古军礼的规范下,楚军未对晋军进行穷追猛打:“及昏,楚师军于邲。晋之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①《春秋左传注》,第743页。,即楚军适时停止追击,在邲地安营扎寨,任已完全丧失战斗力、溃不成军的晋军连夜渡河而去,渡河之声彻夜不息。战争中楚军甚至还帮助陷于泥淖的晋军逃跑,这就是古军礼所谓的“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②《武经七书·司马法·仁本第一》,第141页。的礼制规范。春秋时期,周天子余威尚存,各国之间往往是兄弟、甥舅之国,且古军礼的影响尚未散去,各大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则以服国、服人而已,并不在于将对手赶尽杀绝、争地杀人。因此,春秋时期的战争相较于战国乃至后世的战争着实温和得多。
四、楚军战胜修功,胜敌益强
“战胜修功”是战争进程中的最后阶段,也是能否巩固胜利果实的重要环节。它指的是战胜对手后安抚民众、论功行赏、妥善处理失败者等事宜,以巩固对占领区的控制,强化与盟友的关系等。如果战后问题处置不妥,那么战胜的效果则大打折扣,甚至是会造成功亏一篑的后果,即“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火攻篇》)。如果胜利者能够协调多方关系、妥善处理各种事宜,那么便能够达到更大的战胜效益,即所谓“胜敌而益强”(《作战篇》)。邲之战后,楚庄王拒绝潘党立京观以威诸侯的建议,一反常规,坚持以德抚慰诸侯,可谓妥善地处理了“战胜修功”问题。
“潘党曰:君盍筑武车而收晋师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武非吾功也……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③《春秋左传注》,第744-747页。
“楚庄王雄才大略还表现为战略善后的做法有利有节,头脑清醒。楚庄王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对待煌煌霸业时所反映出来的谦和心态与节制立场。”④黄朴民:《楚庄王的雄才大略》,光明日报2005年1月18日。胜敌而筑“京观”乃是春秋以前常有之事,炫耀武功,威慑诸侯,示功于后世子孙。因此,楚将潘党提出作“京观”之事乃是自然之举。然而,楚庄王并不以为然,因为他有更为长远的战略考量,这和他对当时争霸形势的把握、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当时中原郑、宋等国迫于晋楚强大的实力不得不暂时依附于他们,楚强则从楚,晋强则附晋,实施所谓的骑墙政策,即“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⑤《春秋左传注》,第627页。。晋或楚都很难完全掌控中原诸国,楚庄王认为挟战胜之威,威慑中原诸国,乃是以力服人,决难使诸国信服,唯有加上以德服人,才能换得中原诸国的真心归附。鲁宣公十一年,楚庄王征讨陈国大夫夏徵舒,先是灭陈置县,后又复陈,即足够说明楚庄王在争霸中原的过程中,注重军事打击和政治安抚相结合的策略,怀柔远人,以德服人。另一方面楚庄王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对战争的性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政治的目的是使民众安居乐业、国家和平稳定,并尽可能的制止战争,不得已而使用武力同样是为了镇压暴乱、保国安民。因此,战争只是政治的手段,武力的使用是有限度的,过度的使用和炫耀武力于国于民都绝非好事。这段话十分具有政治情怀,如果不是出于后人的杜撰,那么楚庄王对于战争的认识可谓相当深刻!楚庄王在处理“京观”问题上的自信和宽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极为少有的,所以这也进一步凸显了楚庄王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此战之后,楚庄王一跃而成为中原霸主,郑、宋等国纷纷依附于楚国,楚庄王任德不惟力、以德服人的作法,也得到了当时诸侯国的认可和尊敬。鲁宣公十五年,楚人围宋,“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乃止”①《春秋左传注》,第759页。。在对晋景公的谏劝中,伯宗认为楚国势力如日中天,乃是天命所为,晋国虽强仍不能挡,不可违背天命。晋景公接受了伯宗的劝谏,这恰从侧面说明,楚国邲之战后声威大盛,显示了晋国对楚国霸权的认可和畏惧!邲之战后,楚庄王击败楚国争霸的最大对手晋国,成功夺取了中原霸权,西联秦,东亲齐,北控郑、宋等中小国家,霸业之盛无可匹敌!
晋楚邲之战中楚军展现出了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和精湛的用兵之道。“知彼知己”的战前运筹,正确地预判了战争形势的走向,而两军相对应驻扎下来以后,楚军又积极谋势,示弱于敌以骄其志,示形动敌探查虚实,完全掌握着战争主动权,陷晋军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大战爆发之际,楚军当机立断,先敌出击,占尽先机,一举击溃晋军,大获全胜。战后楚庄王拒绝以“京观”威慑诸侯,不夸武功,宽容谦逊,以德怀诸侯,客观上将邲之战的战略意义无限放大,成功将楚军塑造成了仁义之师。反观晋军,将帅不睦,政出多门,主帅荀林父指挥乏力、将无威信、临战不备、不纳良言,缺乏决断和担当,常为其下属左右而不能制止,在关键时刻下达“先济者有赏”的命令,瞬间造成军心涣散,军队土崩瓦解,晋军将士只知奔命登船,完全不顾军队阵型和秩序,最后导致前有自相残杀,后有楚军掩杀追赶的惨状,遂使晋军遭受大败。
此战楚军指挥灵活、用兵有道,战术展开环环相扣,很多用兵原则已经突破了古军礼的限制,朝着春秋末期“诡诈”用兵的思维转变。其示弱于敌、“示形动敌”的战术运用显然已经不是古军礼约束下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②(战国)公羊高撰,(东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19页。的堂堂对阵,这已经属于春秋末期孙子“诡道”用兵思维的范畴。虽然楚为南蛮,但大部分时间其始终以西周体系内国家自居,对古军礼也往往是笃行不改,如此战中楚军追击晋军适可而止、楚军士兵帮助晋军逃跑等,皆属于古军礼规范下的正常战争行为,而对于楚军示弱、示形等战术手段的运用则属于那个时代“反常”的战争行为。虽然宋、楚弘水之战中宋军的失败已为古军礼的瓦解张目,但毕竟弘水之战中双方都未曾使用违背古军礼的战争手段。邲之战中,楚军在局部上突破古军礼的束缚,灵活地进行战争部署、战术安排,这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周天子权威的日益丧失、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的日益频繁,古军礼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
古军礼的日趋衰落,灵活多变的战争手段的频繁出现,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对某些呆板战争理论的抛弃,对战争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这也为春秋末期《孙子兵法》“诡道”用兵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参考的样本。随着时代的发展,强调灵活多变的“诡诈”用兵逐渐成为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诚如班固所言:“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③(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62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3]骈宇骞,李解民,盛冬铃等.武经七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5](战国)公羊高撰,(东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6](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7]黄朴民.楚庄王的雄才大略[N].光明日报,2005-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