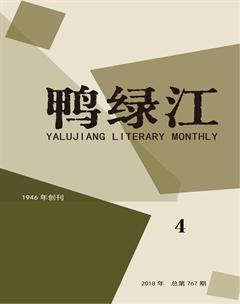相识经年,唯几言可嚼
汤世杰
交谈乃人与人相识相知的便捷方式之一。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便是。而人生诡谲,有的人,与之相识虽已几十年,总共倒只跟他说过几句话,比如于坚。早年,我们在一个院子里做事,虽说一直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碰头见面的机会说来也不算少,可细细一想,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三十多年一晃而过,我和他总共竟只说过那么几句话,很短,很有限。这事,想想还真有点怪。
上世纪80年代,正理想主义盛行。1985年3月初,我刚刚从一家企业,到云南省作协做事。那是我从没想象过的,仿佛天上掉馅饼。去后我干的头一件活,就是筹办全省青年诗人作品研讨会,初选了几个年轻诗人,名单交给当年的主席、诗人晓雪,说可以,便着手准备。其中一位就是于坚。其时于坚以口语入诗见长,由此显出了与另一些诗人的区别。那是诗歌铺天盖地大行其道的年代,老老少少都在写诗,诗如潮水,汹涌澎湃,淹没了几乎所有俗常的日子——曾经的神祇应声塌陷,转瞬便为中国腾出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空间,“诗”——包括广义的“文”——迅即作为一种空无的替代,成了新的神明。深究起来,其实,诗文从来就是这个古老国家的神,几千年来一直盘踞游荡斯土斯民。作为无神之神,诗一直存在,只是在那十来年间,除了几个伪文人的奉命之作,大多都被弄得灰头土脸,甚至被蛮横地遮蔽,看似消失,却如地火,潜行于世。这个有着几千年诗教传统的民族,诗的基因强大坚韧,一遇合适的土壤与气候,便以星火燎原之势,一呼百应,攻城掠寨,所向披靡。
那之前,我在一家企业做事,编着一份小报副刊。出于职业与喜欢,认识了许多诗人,包括不少后来成为外省和云南诗界中坚的爱诗者和写诗人,于坚是其中之一。好像——恕我记得不大准确了——那时他已在本地报刊和远在西北的《飞天》上,发表过一些诗作。我和他在一个院子里上班,倒不在一幢楼,为了那个活动,专意跑到他那里,请他把发表的作品拿给我,为研讨会做些准备。他说好,后来就拿了一沓复印的剪报给我,说,就这些。我说好。其实,那比我原先预想的要多。
那以后,我们偶尔在院子里碰到,也就点个头。我们从没有特意地,或说正儿八经地聊过天。忽有一天,我竟和于坚在院子的一个巷道里狭路相逢。那个院子,旧时是个公馆,变成文联的院子后,到处乱盖房子,房间距离很小,巷道丛生,如迷魂阵。我就在一个只能让单车、行人通过的小巷道里,与于坚迎面相遇。于坚忽然站住,靠着墙,神秘地问我,你说,我该不该要娃娃了?那个询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脑子飞转,寻思那会是一句诗吗?往常,我们见面也就点个头,笑笑而已。可那天他说:“我该不该要娃娃了?”如果那真是一句诗,我就该用诗的语言回答他。但他说话的口气,完全不像在那个研讨会上讨论诗的调子,于是我断然否定了我的惊异与胡思乱想。随即我就想大笑,怎么可能呢?一个诗人,怎么会突然跟我这个只是偶尔见见面,见了也只是点个头的人,打探虽是人生必经却如此私密的问题呢?顿时,他从我想象中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之骄子,还原成了一个也要考虑人生百事的人,如果不说是个江湖俗人的话。心想,他不会是在开玩笑吧?不像,看样子不是开玩笑,他满脸满眼的期待神色,让我静了下来。我的目光透过巷道,看着院子里那个小小花坛。阳光清亮,不太灿烂,花木扶苏,疏朗有致。我极力忍住刚才那股想笑的劲头,说,此时不要,更待何时?尽管我极力压低嗓门,但声音可能还是有些大。他怔怔地看看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扬长而去。剩下我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才走出巷道。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背影宽阔而厚实——我想,他会不会把我的回答当成开玩笑啊?我可是认真的。一个当过几年工人,又读了几年大学,上了几年班的人,结婚,生个娃娃,是人生游戏的一套规定动作,顺理成章的事,还用问吗?特别是,还用去问一个跟他原来的日子几乎毫不相干的人吗?但事实证明他没有误解,他向我询问这事,也完全正常——毕竟,我比他年长了十多岁。
于坚询问那事真正的隐喻在于,在那样一个几乎全民为诗疯狂的年代,诗人那时自身遇到的,并不是,或说至少不完全是一个个纯粹又纯粹的诗学问题,而是一个人生的日常问题。他们发现,比诗学更现实的,是生活,甚至生存。其实,那是一个较之本义的“诗学”博大得多也深邃得多的、更大的“诗学”问题。意识到于坚所问问题这一隐喻的内涵,深感其间意味深长。作为一个曾经的锻工,曾经的大学生诗人,整日整夜埋头于诗的日子,已经过去。于坚已开始思索生命自身的生存问题。生命的延续恰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他对此,对要回到生命的日常,或許有些迷惑,甚至没有足够的准备。后来,于坚的许多作品写到过他的日常,幼时的,成年的,林林总总。但对结婚生子这个日常不过的问题,那时他还没有准备,或说还没做好准备。其实他的困惑,远不止于他个人的困惑。那是诗的困惑。事实上,与他同时期的另外一些年轻诗人,遇到的也是形式尽管不同但性质完全一样的问题:生存。许多自以为是为诗而生的人,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如何才能立足于世焦虑万分。一些人转行去经商了,去教书了。他们彻底地置他们曾经奉为圭臬的缪斯于不顾,投身到尘世之中,还原为一个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俗人。传说中有某诗人在菜市场为跟小贩讨价还价直至亮出“我是诗人”的故事,虽乃笑话,倒在某种程度上显出了生活的真实。诗情的燃烧毕竟也是燃烧。燃烧即消耗。不久,我们就能见到燃烧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满眼灰烬——这个世界,永远都严格遵守着能量守恒定律。
还好,于坚没有沦陷。
不久,我听说于坚当父亲了,孩子叫于果,我想,于坚这家伙,心里想的肯定是“雨果”吧?幸运的是,就像我后来看到的那样,于坚并没有像许多抛别缪斯的人那样寡情,从此跌进生活的旋涡而难以自拔——初初听到“于果”那样一个名字,我已从中嗅出了于坚的某种志向,甚或说是野心——诗还在。还在他心里。他还要向前走。怎么走,往哪里走,我不知道。但随即,于坚的那些写昆明写昆明日常生活的诗文陆续问世。诗不再高蹈凌虚,从半空中落下尘世,发现了俗常之美。他把人对日常生活的尊重、怀念和不可分离,变成了他的文字,诗,摄影,以及散文。
又一次,记不清年份了,反正,那是一段有些艰难的日子,无形的、看不见的,却又让你分明能感受得到的艰难。在另外一个同样狭窄的巷道——那些巷道让那个院子有如迷宫——于坚碰到我,突然说,你还是要写。呵呵,我们似乎总是相逢在路上。我一时有些惊愕,不知他那话从何说起。我想我没有听错,他就是那样说的。他又说,有的人写得远不如你,你怎么不写了?我仍不知他那话从何说起,愣着,没有吭声。时间流逝,分分秒秒。那一刻的寂静分量千钧。日子突然变得严峻,更加严峻,不仅是生存的压力,还有一些来自不明方向的压力。我没吭气。我在想是怎么回事。
——许久之后,我听说,就在那条巷道,于坚干过一件很江湖的事,豪迈无比:他恰好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在背后说他坏话、近乎于向克格勃告密一类的人,他把那人堵在巷道里,厉声告诉那人说,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把你的另一条腿打断。这个真实性存疑的故事,曾在那个院子里添油加醋地广为流传。又过了许多年,我见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公众号链接,把于坚和那个疑似告密者的人并列在一起,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那些人肯定不知道,巷道曾经发生过的那精彩一幕。
那时,于坚又说,你要写!我知道,你的名气比有些人大多了。我说,我会写啊。我想,他是在恭维我吗?恭维我有什么必要?我断然否定了那个念头。他不是要恭维我,他从不恭维什么人。我很想问问他,怎么会突然跟我说起这个话题,是听到了什么吗?何况,我也从没说过我不再写作了,只是因了一些事,有些伤心,有些感慨,如此而已。后来我听说,那次他是刚刚从外地,也许是北京之类的地方回来,不知是不是偶尔听说了什么。而我们共同生活的小地方,不时会有些比那些大地方更大的风浪。我至今不大明白,那天他所指究竟为何。但我愿意相信,他那句近乎没头没脑的话,全然是出于好意。好意出于他的在意,对一个人的在意,对一个同事的在意,对一种写作的在意,而无其他。我想我没听错他的话中之话。我当然会继续写作。但我没有那样跟他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依旧,平淡如昨。许多时候,我们见了面,连话也不说,只是相互点个头。不说话,不等于无话可说。人在世间,有许多话,是不必挂在嘴上的。在谎言流行的时候,不妨把嘴巴换成眼神。对一个诗人,尤其如此。诗,思也。而思者,心田也。岂非诗即心耶?你读他的作品,好的作品,即见其人,明其心。阅读就是交谈,以心对心。有些人,你读了他的作品,就是读不到心,读到的尽皆语词的洪流,铺天盖地,华丽多彩,唯不见心;或充满机巧,小聪明,炫技,看上去睿智如哲人,如大师,就是见不到心。心躲在很远很深很暗的地方,看上去在写作,其实是在干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不说别人也知道,但都装作不知道,看他做。于坚的诗文,其实我所读不多,但每读都可读出心来。读出他在干什么,想什么,至少大体知道。就那样,我们不说话,或很少说话,偶尔说两句,都是短语,见了照样点点头,相安无事。
但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实在忍不住了,直接打上门去,找他。我说,于坚,你能不能不再半夜三更地打印啊?那时电脑刚刚兴起,所用打印机还是针式的。那种打印机的打印速度很慢,打一份几千字的文稿,需要很长时间。我记得我曾为打印一部长篇小说,花了整整五天时间。我与于坚的窗户中间,只隔着不到三米的距离。有时,他会在零点之后开动打印机,滋啦滋啦地打印新成的文稿,而那时,我刚刚要进入梦乡。我被那种让整个身体发酸的声音弄得无法入睡。他说他是赶个稿子。他说他会注意的。我听了,转身就走了——你还能怎么着?
长诗《0档案》发表后,表面平静的大院,一时议论蜂起,说什么的都有。我特意找来读了,先是有些不习惯,再读,有味道了,心想,很好啊,很有意思啊!一个隐蔽的伤疤,被扒了开来,里面是一团荒谬与荒唐。也有人不那么高兴了,说东的说东,说西的说西。见仁见智,你可以不高兴,不喜欢,不理会,公开评论,却无须也不该藏在暗處,施用文学以外的手段。压力会很大吗?看样子有点大。偶尔看见,于坚在院子里匆匆而行,一脸的凝重。我很想跟他说几句什么,到了也没说。我在想,当事人如果是我,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任别人说去吧!一个人,到了那样的年龄,总是要经受些什么的。借此想想自己的来路去路,未必不是好事。
一晃多年。新世纪之初,一次我们一起到铁路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末了,请大家都发发言,最后我也讲了几句,其中说到,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从来都是以山河湖海为中心的。我举例说,古人有句话,叫“孔子过泰山侧”,而不是说孔子从曲阜边走过。我说,那不仅仅是个修辞。曲阜无非一座人造的城,泰山才是大自然生成的庞然大物。大块。大块假我以文章。城可一朝毁败,山却万世不朽。一句“孔子过泰山侧”,把孔子和大千世界,和一座巍然大山联在了一起。说孔子过曲阜,只点明了方位,说“孔子过泰山侧”,不仅点明了方位,还把孔子和泰山联在了一起,那是个宏大的、能给予人无限想象空间的画面,意象磅礴,其味深远。散会时于坚边走边对我说,讲得好,“孔子过泰山侧”,可以好好写篇大文章!我说是吗?我说我正在写。那之前,我读于坚的作品,总有些“现代”“解构”的印象,如《0档案》。我没想到他会赞同我的说法。我想他不会轻易赞同谁的说法。许久之后,我发现于坚文风有变——那当然与我无关——他好像迷上了谈经论道,文中随时随地会出现“大块假我以文章”“道法自然”之类的古典名句。他在向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致敬。那种致敬并不空洞。古典里的中国日常,以及日常里的古典中国,成了他的在意。那与他对故乡或说乡土的追索,一并成了他诗文的两翼。他的追索固执到让人心疼心颤。过往的一切都成了美好回忆。他哀滇池。哀旧时昆明。哀他的亲人。哀他曾大汗淋漓的厂房。哀那一切俗常而有味道的日子。
初,我以为那已近偏执:昆明,未尝都好,昆明往昔,亦非尽可怀念。而他继续铺排,动辄万言,洋洋洒洒,如乡土文学,如鲁迅所谓:“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细想不然,深味,或道存于中。先前的鲁迅、沈从文,如今的莫言、贾平凹,都乡土过。而鲁迅的乡土不是沈从文的乡土,“鲁镇”也绝不是“湘西”。各人借用乡土的一角,意在各自心里的一个中国寓言。网上见有人为《建水记》站台,谓该书在歌颂建水的美好生活,该文读来仿佛在营销一本旅游读物,所言不唯非关宏旨,甚或相去万千里。我发微信给他:“我还没看到书,但微信上一些人的评说简直没摸到门,让我笑死!这肯定不是在告诉人们建水好在好玩,说那里尚存一种古老生活,哪跟哪啊?你是在对这个时代做出诗人的应答,这是责任,即西川所谓处理这个时代。”一个诗人、作家,不“处理时代”,不对时代发声、定位,亦白当了。于坚亦发出声明:“此书非关旅游。是关于那些被粗暴而轻蔑地拆迁掉的是什么?老中国在空间上已经彼岸化了。唯新是从,猎奇式怀旧,骨子里崇拜未来主义的旅游加速了这种彼岸化。所幸者时间还在汉语中幸存,也仅将碎片连缀起来。这是一种朝向废墟的、穷途末路的写作。”
诚是。我更喜欢他的散文。说到他新出的《挪动》,他说,那是“我近年的中篇散文合集。上一本是十年前出版《相遇了几分钟》。汉语写作的不朽道统是散文(我更喜欢随笔这个及物的词),小说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西人很少或不译散文可证,散文深植汉语中,译不过去。白话一百年后,能穿越时间,可传者依然是散文。鲁迅、周作人之重都在散文上。散文自古影响着汉文明。《赤壁赋》鼎立如《圣经》。如果文明复兴,小说必日渐黯然。小说只是散文中的细节,《红楼梦》是个典范。20世纪西方先锋派的写作趋势其实是走向散文化。当代,散文、随笔已经被汪洋大海的花边文学搞成了雕虫小技。《左传》乃重器,具有歌德、普鲁斯特、乔伊斯、托尔斯泰式的重量,影响到政治、国本、语速、材质、文明进程。”足见在中国,散文一以贯之,可记史、抒怀,可言志、明理,可发而为檄文,可系之于幽情,而当下小清新、小浪漫一类,无《史记》之恢宏,无《左传》之凝重,无《水经注》之俯察山川,无《世说新语》之济世悯人……已全然败坏国人胃口。那么,诗呢?诗依然在,在它自己,也在好的散文之中,化而为魂。
日前,我刚写完一篇非虚构文字,看来看去,总像少了点什么,兴未尽,意未结。正踌躇中,偶尔看到于坚微信上的两句话,“时间啊,请严加拷打,我全部如实招供”。正好,想用作引语,电话问他可以吧,他的回答仍只有两字:当然。
——与一个人,相识多年,寻寻常常,平平淡淡,唯几言可嚼,幸耶?不幸耶?唯吾自知耳。
【责任编辑】 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