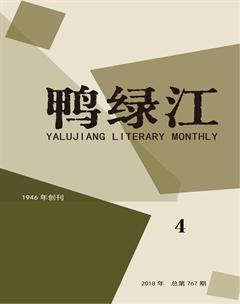死之将至
王彪
他们告诉他,他母亲就要死了。这话当然不是直截了当说的,他还是个孩子,他们说得比较隐晦。
他放学回家走在街上,有认识他的人跟他打招呼,问长问短,多是些学习和生活上的鸡毛蒜皮,不过表示一下关心而已。待他走过,他们看着他的背影,目光里贮满了同情,然后一声叹息,“唉,可怜的孩子!”也有人会突然塞给他一只橘子、几颗糖果,非要他收下。他被这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的礼物弄得尴尬万分,他们已拍拍他的肩,也是一声叹息,摇头而去。
家门口,邻居们都比以往殷勤,他不小心碰翻了他们的小凳子,不会有人责备他,相反,他们都说对不起对不起,好像是他们的不是,拿小凳子挡了他的道。隔壁的大嫂、对门的老奶奶也是热情得不得了,都来拉他的手,叮嘱他好好照顾自己,听上去似乎他遭遇了什么不幸。
走进家门,外婆正烧晚饭,叫他帮着洗把菜,顺便把阳台的衣服收了。大约他洗的菜不干净,衣服收下来也没折好,外婆叹气说:“你这孩子,你以后怎么办啊?”他不明白菜没洗干净衣服没折好与以后怎么办有啥关系,便转脸去看外婆,却见外婆背着身抹眼泪,好像他这两个微不足道的错误着实伤透了她的心。
他终于紧张起来,他的生活出了问题,他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所以有这么多人要来同情他,怜悯他,为他忧愁,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有一个病入膏肓、即将死去的母亲。
这个世界的人都在宣告,他母亲快死了,他成了一个最可怜的孩子。他最需要同情、怜悯,最需要他们向他表达善心。
他先是茫然无措,等他明白过来后,他突然感到愤怒。
他每天都要去看她——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女人,他的母亲,他是怀着一种奇怪的羞辱感去的,心里有隐隐的刺痛。
按理不该这样,她是他的亲生母亲啊,她多爱他。每次他去,她都会捏着他的手问长问短。他打个哈欠,她心疼他没睡好;他的手臂擦破点皮,她担心他与同学打架了,非得问个一清二楚,待到确信他一点事都没有,她便让他躺到自己身边,依然怕他缺了点什么似的,搂着他的小脑袋,东摸摸,西摸摸,恨不得连他的每根头发都数一遍。
他闻到她身上浓烈的来苏水气味,被单上也是。病床过于狭小,他被这股气味埋没了,晕晕乎乎的,似乎他也成了一个病人。其实,他是多么讨厌这股气味,每次他从病房回去,走过他那些漂亮女同学身边,惹得她们蹙起尖尖的好看的眉毛,拿手掌扇着鼻尖,仿佛要把他与他身上的那股味道一并赶走。
因而他总是尽力躲避她的亲热,把脑袋扭过来扭过去,用臂肘顶她。他表现得像个小小男子汉,自尊,要面子。她先是吃惊,他怎么一下子长大了?早早进入叛逆期,碰都不要她碰?继而吃吃笑起来,笑着笑着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你个小屁孩!”她说着扑上来,执拗地抱住他,用了最大的劲,鸡啄米一样亲他,口水糊了他一脸。
要是黑皮知道他满脸都是他母亲的口水那就完了,黑皮会把这事传遍校园,他便成了一桩丑闻的主角,这则丑闻经过发酵,不出三天,保准变成他还在吃他妈的奶这样的大笑话。黑皮父亲是这家医院的勤杂工,黑皮常来帮父亲干活,哪天冷不丁叫他撞见,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
可他母亲才不管这些,这会儿,她把他抱得更紧了,似乎害怕她一松手,他便跑得无影无踪。“你都听清楚了吗?妈妈那张雕花大床以后是你的了。”母亲盯着他的眼睛,翻来覆去说。
为了那张雕花大床,母亲已跟他说了无数遍,还和父亲吵了一架。这张床是母亲的嫁妆,床架四周有精美雕饰,文人雅趣的梅兰竹菊,民间吉祥喜庆的石榴灵芝蟠桃喜鹊蝙蝠之类,应有尽有,彼此交相辉映;最有趣的是戏文里的男女人物,雕刻得栩栩如生,睡在床上如同看戏一般,那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母亲从小就是在这张床上听外婆讲戏文里的故事,开启了她的文化教育。因此也可以说,这张床是母亲家族的传家宝。
很奇怪,在他所处的年代,“文革”破四旧没把这张散发着封建余孽气息的奢侈品给破掉,家里别的东西都砸烂了,这张看上去最触目惊心的雕花大床却幸免于难。据母亲说,红卫兵闯进来的时候,她正躺在床上陷入弥留,那是她第一次病危。红卫兵想把她从床上抬下来,却发现她口吐白沫,气息奄奄,模样异常怕人。一个紅卫兵叫起来:“哎呀,她快死了!”按理这些红卫兵是不怕死人的,他们连坟墓都敢挖,挖出来的尸骨散了一地,骷髅当球踢。但将要死去、马上要变成尸体的人他们却没碰过,眼看着一具活生生的尸体在他们面前躺着,他们都有点发瘆,一个个畏缩不前。“等她死了我们再来!”红卫兵们扔下一句话,转身蜂拥而去。“他们没想到我到现在都没死,嘿嘿。”母亲笑着跟他说,不知是替雕花大床躲过一劫高兴,还是为她自己同样死里逃生而庆幸。
母亲的意思,这是她拿命保下来的,她把最宝贵的东西传给了他。面对这份厚礼,他却惶然不知所措,“我死后这张床给你睡。”母亲抓着他的手,急切地说,“答应我,这也是妈给你的婚床,别让你爸睡。”
母亲把雕花大床早早传给他,还有另一层意思。母亲害怕她死后父亲再婚,别的女人睡到这张床上,这是母亲无法容忍的。“我死了你要娶哪个女人?”有一天他听见母亲问父亲。父亲很尴尬,说:“你这是什么话?”“我问你你要娶哪个女人?”母亲固执地重复着,不依不饶。父亲躲不过了,说:“你活得好好的,我娶谁啊?我谁也不娶……”母亲不信,说:“没女人你能活吗?你们男人都这德性!”母亲说着突然哭了,“我受不了,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发狂,你会跟别的女人上我的床。”父亲赶紧安慰母亲,赌咒发誓说:“不会的,我只在乎你,我不会有别的女人的。”
可是母亲不信,她的爱情保卫战演化为雕花大床保卫战,并且更新换代,打这场保卫战的已不是她自己,而是她儿子。只要她儿子保住这张床,没有哪个女人在她死后能占据她的位置了。于是,他被推到了前线,夹在母亲和父亲中间,其结果是,因着他畏缩而孱弱的态度,母亲怀疑他会叛变,只等她一死便站到父亲那边。父亲则认定他早被母亲洗脑,是母亲安插在他日后生活中的奸细。所以,父亲看到他总是讪讪的,闪避着他的目光,好像他总想发现自己的什么秘密。
他很难过,不知道说什么好,母亲再跟他说雕花大床,再抱住他亲他,他会突然充满羞辱。他狠狠擦去母亲留在他脸上的口水,叫嚷着说:“不要不要,我不要!”母亲怒容满面,同样,她也充满了羞辱,为了他的拒绝。
他吓坏了,不等他逃走,她拉住他的胳膊,狠狠咬一口。他疼得快叫出来,却忍住了,眼泪不争气地冒出来。她松了口,骂他:“你这小没良心的!”他的手臂上有一圈牙印,一枚枚牙齿像钉子钉进去一样,留下惨白的凹坑,周围的皮肉红彤彤肿起来。红白对照如此鲜明,看上去令人惊心动魄。
他带着没褪尽的齿印去学校,好像带着一个难言的秘密。果然,这秘密很快揭穿了,全班同学都知道他妈咬了他。想想看,一个十岁的男孩还让他妈咬!那有多可笑啊。“哎哟,疼死了疼死了!”几个爱捣蛋的男同学模仿他的口气,捂着胳膊,龇牙咧嘴的,在女同学面前走来走去,惹起一场又一场的哄堂大笑。黑皮头上扎了块白手帕,扮演他病怏怏的母亲,东倒西歪追逐那几个男同学,可怜巴巴叫唤道:“我儿,你来啊,让妈再咬你一口!”
被追的同学狂笑着逃散,黑皮奔到门口,一头撞在工宣队李师傅身上。李师傅五大三粗的,钳工出身,最喜欢用武力教训老师和学生,也最讨厌老师和学生瞧不起他,黑皮这一下真是自投罗网。李师傅劈手揪住黑皮,不由分说给了他一巴掌,“妈的,你叫谁儿子!啊?”
黑皮头上的白手帕掉在地上,半边脸红了,留下五只清晰的指印,与他胳膊上的齿印相映成趣,叫同学们乐了好几天。这一巴掌也使得黑皮与他结了仇,那以后,黑皮常在教室里散布他母亲的传言,那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等死的女人,如何丑态百出。比如,她小便失禁,把尿撒在床上,同病房的病人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尿壶”;她不敢喝水,又得了便秘,难受起来哭个没完,半夜里寻死觅活,把整个医院都吵醒了;护士硬按着她给她灌肠,她起先拼命挣扎,等扒下裤子,她突然无所谓了,一动不动露出光屁股,给所有的人都看见。黑皮渲染了半天,要说的重点就是这个——他的意思是,他也看到了他母亲的光屁股,白白的光屁股,一小块三角形的卷曲的毛毛……果然是爆炸性新闻,黑皮把他母亲最私密的地方都看去了,这是多大的事啊!全班的男同学震惊异常,又亢奋万分,一个个涨红了脸,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仿佛他们也都跟着黑皮目睹了一把最难以启齿的秘密。女同学则羞惭难当,对他充满怨愤和轻蔑,好像他母亲的裸露把她们身体的隐秘也给出卖了。
他知道母亲可怜,病痛剥夺了她最后一丝尊严,将一切软弱、不堪与隐私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羞辱却是他经受的,这样的情景,跟母亲当众被强奸又有什么差别?不仅如此,母亲的政治隐私也曝光了。有一天,母亲单位来了一个人,陪同邻省的两名外调人员,向母亲调查一桩反革命案件。案件的主犯死不认罪,但从他家里抄出一些证据,其中有写给母亲的信,母亲曾是他从前的恋人。黑皮在医院病房的窗外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她是个破鞋,她搞别的男人,还是个反革命。”黑皮向全班同学宣布说。
母亲什么也不肯交代,她躺在病床上装死。鉴于母亲的死硬态度,外调人员勒令母亲起来,跪在地上接受批判。这场特别的批斗会最后以母亲昏倒而告終。这一次,母亲的丑态是她松开的病号服里露出的大半个乳房,母亲病成这样了,乳房依然饱满。外调人员叫正在走廊打扫卫生的黑皮父亲过来,把母亲拉起来,母亲不肯起来,黑皮父亲就在母亲的乳房上抓了一把,他这一招真的灵验,母亲一个激灵爬了起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黑皮得意地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替他父亲的流氓行为拍手叫好。
他的心一阵刺痛,眼泪不争气地冒出来。每逢这时候他只有跑开,同学们在他身后发出怪笑,“嘎嘎嘎”,那才是真正快乐的笑声,仿佛之前的所有嘲笑都有了合理根据,他们不是欺辱一个有病的女人,而是这个与反革命同穿一条裤子的臭女人自找的,他们做对了。
当然也有同情他的,想过来安慰他,但莫名其妙的,他更害怕也更恨这些好心人。他们目光里的怜悯会像刀子一样割疼他,使得他血流不止,又必须装出感恩的样子谢谢这些人。他转身逃离,逃得越远越好。
无论逃多远,他还是要回到母亲身边。满腔的委屈顿时变作愤怒,他注视着她辗转病床的痛苦的脸,脑子飞快掠过一个念头:她什么时候死?
这个念头是如此猝不及防,如同一声霹雳,一下子照亮了他纠结如麻的神经,然后是石破天惊一般,他意识到自己对母亲发出了一道诅咒——她什么时候死?他居然盼她死!他完全震撼了,这怎么可能?他是她儿子啊!当他这样战战兢兢地责问自己,一个更强烈的念头又如一道电光劈下:要是她死了就好了!
是的,她死了就好了,一切都结束了,包括她与他所有的羞辱!
这真是从他脑子里出来的吗?他吓坏了,僵立在母亲面前,像雷电劈中的一棵树,浑身焦毛,感觉头发都在冒烟。母亲并未留意到他奇怪的表情,从床上坐起来,她要吃药,叫他把药丸拿过来。他递过水杯,母亲不满地重复了一遍,她要的是药丸。他满心羞愧,拿回水杯,把药瓶送上。母亲又说你拿走水杯干吗?我没水怎么吃药?他简直无地自容,恨不得马上就哭出来。母亲却笑了一笑,说:“好了,你哪会照顾人,我自己来吧。”
母亲欠身倒水,她手抖,水洒在床头柜上,吃药的时候,又洒到衣襟上,下巴上也是,亮光光的挂下来,不知是杯里洒出的水还是口水。他记得他小时第一次吃药,不会吞咽,也弄得下巴全是水。母亲试了许多办法,浪费了好几颗药丸,全以失败告终,他总觉得有东西鲠在喉咙而不肯下咽。母亲黔驴技穷,想起他喜欢吃橘子,便把药丸塞进橘瓤里叫他吞下去,这样的主意也只有母亲想得出。他一吞又卡住了,咬破了橘瓤,满嘴苦味,他哇一声将药丸吐出来。母亲终于失去耐心,打了他一巴掌,骂他说:“我生你有什么用,吃药都不会!”
这是母亲第一次打他,他哭了,母亲看他哭,自己也哭起来。她把他搂在怀里,哭得比他还伤心。
忽然之间,他也很想哭。母亲终于注意到他的异样,问他怎么啦。他眼眶潮润,喉咙发涩,整个身体黏糊糊的,仿佛搁置在阳光下的冰块,只要母亲轻轻一碰,他就彻底融化,变成一摊水。但他的心底却又生出一种拒绝,冷硬的不近情理的拒绝。母亲拉住了他的胳膊,她的手凉丝丝的,有一种浸泡过福尔马林的感觉,这个意念如此恐怖,会令他联想到实验室浸泡在药水里的某种器官。近乎本能的生理反应,他把心一横,推开母亲,转身奔出了病房。
跑到街上,他想他可以哭了,等了好久,他没有一点悲伤,泪水已从他身体里退走了,他一摸眼眶,眼角干干的,他整个人也是干的,像沙漠一样。
我恨不得她死,他想,我还是人吗?他原本是要逃避她给他带来的羞辱,结果他为自己带来了更大的羞辱。这以后,他特别害怕见到她,他发现她看他时眼珠瞪得大大的,目光清亮,似乎要看透他的五脏六腑,令他无法直视。他开始躲避她,放学了也不去医院,但她不放过他,有时叫父亲找他,有时叫外婆。父亲非常粗暴,找到他拎起他的胳膊就走。外婆要温柔多了,她迈着一双小脚,一路走一路数落他不懂事,不会孝顺,不知道珍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亲生母亲,“宁要讨饭娘,不要当官爹。等你晓得这个道理就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外婆漫长的唠叨使他觉得,父亲的粗暴是可以原谅的。
到了病房,母亲并非有什么事要见他,她就是想见到他而已。他今天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想她?他回答不想,会惹她生气,有一次她冲动之下,把挂盐水的针头扯了,一股殷红的血从静脉飙出来,溅得墙上到处都是,那场景仿佛她要自杀。他回答想,她当然开心,拉过他来,没完没了地亲他,又追问他都想她什么。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尴尬地沉默。她的情绪一落千丈,说起他生过的几次病,她如何带他去看医生,有一回他得了肺炎,发着高烧,她抱着他冒雪去医院,天黑路滑,她摔下河沟,差点淹死,他却在她怀里睡着了,睡得真香。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她盯着他问,越说越伤心,而他脑子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起来她说的这些事情,恨不得马上就找个地洞钻进去。
他慢慢明白她的意思,她是害怕她在他的记忆里消失。“那我就都没有了,连我的儿子都不记得我了,我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留下的?”这让她有很深的恐慌,她夜里常做噩梦,梦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她在寻找他,经历千辛万苦,她找到了他,可他却不认识她了,与她形同路人。她吓出一身冷汗,从噩梦中惊叫着醒来。这时候如果他来看她,她会迫不及待把他搂进怀里,搂得紧紧的,翻来覆去问他一些只有她俩知道的事情,仿佛要证实一下他确实是她儿子。然后,她把这些细碎的往事打捞起来,敲钉子似的钉进他的脑袋,最终钉成一串词语:你妈是最爱你的人!她疯狂地亲他,咬他,留下一圈齿印,直到他疼得受不了而挣开她逃走。
他知道她留在他背影里的目光一定是痛苦而迷茫的,记忆像那圈齿印一样靠不住,第一天红肿而痛彻心肺,第二天变成淡漠的乌青,第三天第四天就消失不见了。她需要有一种东西可以一直陪伴他,与他今后的生活形影不离,把雕花大床传给他大约是她所能做的最后努力。“你以后睡在这张床上,会想起妈妈的,对不对?”他当时没听懂这句话的深意,以为母亲在与父亲赌气,她最嫉恨的是将来有个女人代替她的位置而成为这张床的主人。
她一定想得很远,他在这张雕花大床上结婚生子,“我在这张床上怀的你养的你,你也一样,在这张床上有了你的孩子……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她像做了个美梦似的微笑着,他却突然打了个寒噤,有一种恐惧从他内心蔓延开来。很久以后,他都不明白他为何恐惧,他只是在跑出病房时意识到自己的抗拒,“她都快死了还揪着我不放,她到底想把我怎么样啊?”
他受不了了,他必须摆脱她。班级里又召开批判会,黑皮揭发他天天去医院看望反革命分子,工宣队李师傅要他拿出实际行动来划清界限。他低头站在讲台前,鬼使神差地,想到了那张雕花大床。他的脑子于是亮了一下,是啊,他为什么不领着同学们去砸了它呢?
他有钥匙,打开了父母的卧房,同学们蜂拥而入。母亲住院,父亲在外地工作,他住外婆家,这个房间弃之不用,里面弥漫着一股霉味。黑皮和几个同学冲上前去拆这张床,但床太结实了,怎么拆也拆不下来。后来大家索性在床上蹦跳,玩起了体操。雕花大床的棕绷好极了,弹性十足,男女同学都上去蹦跶,玩得不亦乐乎。他也被黑皮拉上去跳。如果不是因为头上的天花板,他感觉自己可以飞到天上去,与母亲在这张床上睡了这么多年,他从没想到过,雕花大床上还藏着这样的快乐。
雕花大床到最后都没能拆下,钳工出身的李师傅找了把斧子,三下两下把它给劈了,他和同学们每人拿了块劈下来的床板,当作胜利成果回到学校。他拿回的那块雕着一个男人和半个女人,他记得母亲跟他讲过他们的故事,是《牡丹亭》里的柳梦梅与杜丽娘。母亲会唱《游园惊梦》的一小段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母亲唱得凄切婉转,给他留下不祥之感。
母亲是如何得知雕花大床被毁的?他不清楚。母亲是否知道他在其中的作用?他更不清楚。他心里不是没有一点担忧,要是母亲知道了她视同性命的传家宝毁于他之手,会是什么结果?也许她对他由爱生恨,继而彻底绝望。这样也好,他就可以解脱了。
经过两天平静又心惊肉跳的等待,要来的终于来了。不过临了还是超出他的预料——竟然是他外婆出现在教室门口,外婆眼泪汪汪的,一把将他从教室里拖出来,撒开小脚就跑。外婆跑得像飞一样快,他都跟不上。“外婆,我们要去哪儿啊?”外婆这才哭出来,“去看你妈啊,晚了就看不到了!”
他一下子明白了“晚了就看不到了”的意思,是他母親快死了,他的心怦怦狂跳起来,却不知道是悲痛还是害怕。按理说他应该高兴,他不是盼她死吗?他终于得逞了!
他与外婆等在抢救室外面,从外婆的哭诉里,他听到事情的真相,果然与他有关。雕花大床的毁灭,对母亲的刺激真是致命的,她不知哪来的力气,从病床上爬起来,偷偷跑出医院。她要去找回她的雕花大床,但她的床已给劈碎砸烂了,结果她一路找到废品收购站,爬上收购站仓库小山一样的废品堆,她找到了雕花大床的一条腿。她抱着那条腿号啕大哭,哭到昏厥,从废品堆重重摔下来。要不是工作人员发现了她,把她送回医院,她早没命了。
那一刻他想逃走,外婆却揪着他不放,哭着问他说:“她这是干吗呀?她不是去送命吗?”外婆想要他回答吗?可他怎么回答得了?要是外婆知道他就是罪魁祸首,会不会给他一个耳光?
正在胡思乱想,母亲从抢救室里推出来了,没有一点气息,苍白如纸,看上去跟死了差不多。外婆推了他一把,催他说:“叫啊,叫一声妈。”他没叫出来,喉咙哽住了,非常难受。
然后,突如其来的,他流泪了。准确地说,他是吓哭的。但这一哭却救了他,外婆发现了他的孝心,感动得抱住他也哭个不停。
她足足昏迷了三天三夜,他留下陪夜,有好几次,他从瞌睡中醒来,怀疑她真的已经死了。这时候他心里涌起强烈的歉疚,如巨浪一样吞没他,“是你害死了她!”他听见有个声音在他里面说话,那声音非常尖细,像刀刺他一样。
他不敢凑近看她,害怕她醒过来,她醒了他如何面对?但害怕的同时又盼望她醒过来,她醒了他凶手的罪名就洗脱了……他纠结不休,反反复复,整个人像犯热病一样发抖。
果然,他真的病倒了,感冒发烧,不能在医院陪夜,于是他回家躺了两天。他是暗暗感激这场病的,给了他一个台阶,使他可以暂时躲开。等两天后他再次走进病房,危机已过去了。
她安静地躺在床上,依然苍白如纸,但生命是真实存在的,在她的细如游丝的呼吸,她的半开半闭的眼睛,当他挨近她,她散开的目光慢慢聚拢来,在他脸上聚成一个焦点,她的嘴角跟着牵动了一下,发出比哭还难看的笑。
她认出他来了,看上去她似乎并没表达出对他的憎厌或愤怒,相反,她显得很高兴。他努力叫了声:“妈——”她点点头,已经用完了力气,虚弱地闭上眼睛。这个可怜的女人,她原谅了他的一切,而他居然盼她死,“要是她死了就好了。”当时他的确动过这种坏念头的。
他应该跟她说声对不起,向她认错,请求她原谅。于是他又結结巴巴叫了声:“妈——”她吃力地睁开眼,很奇怪,这一回她不知哪来的精神,眼珠子一眨不眨地看着他,听他说话。他却说不出来,舌头打结,面皮发烫,重新陷入愧疚而难以自拔。
他懊悔万分,要是前两天她昏迷时,他守在病床边,开口向她说出自己的道歉就好了,那时候他已话到嘴边,只要说出来,他心里就会好受些的。但现在不行,他胆怯了,他在她的目光下无地自容,他的自尊好像被剥光一样一文不值。
他竟然想到了自尊,他是她儿子,他在她面前有这个必要吗?可事实就是如此,哪怕最简单的三个字,他也说不出口。
他决定天天来陪她。宁愿逃学,宁愿被黑皮挖苦嘲弄,宁愿挨李师傅的臭骂,他都要待在她身边。他替她递茶端水,扶她上厕所,帮她削水果,他觉得他做得越多,心里的愧疚就越少,他是爱她的,他可不希望她死。
他赢得了孝顺的美名,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和病人都夸他,她也开心得很,胃口大开,精神一下子好了许多。她看他的目光总是笑盈盈的,充满幸福感,这让他觉得,这是他们母子俩最甜美的时光,居然是在医院里得到的。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一点不适感,有一次她换衣服,叫他帮她拉一下袖子,他看见了她从衣襟里滑出的大半个乳房,他突然尴尬万分,并且兀自羞红了脸,因为他想到了黑皮父亲,那个流氓男人堂而皇之地把他的脏手伸到她怀里。他赶紧把她的衣襟拉回去。但她对此似乎不以为然,或者说,她毫无察觉,她在医生护士病人面前,包括在黑皮父亲这样的勤杂工面前,她对待她的身体都是坦然的。每天查房,像她这样的胸腹部病患,多少有点小私密,她通常不等医生吩咐,已熟练地把衣裤解开了,好像那是别人的一具肉体,她不需要为之掩饰。
他记得她刚住院那会儿不是这样的,有陌生人在跟前,她连臀部注射都很排斥,脸涨得通红,护士总要拍拍她的屁股,说:“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我针都扎不进去,放松一点。”她还是紧张,肌肉绷得像石头似的,结果护士的针扎断了,这是这家医院破天荒的事情,院方当作医疗事故来处理,但并没起到严肃效果,反而在病人中传为笑话。她的屁股也得了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美名,叫作“石头屁股”。
她肯定感觉到了他的尴尬或不快,但她却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因为她过于麻木,或者说是过于习惯地裸露身体。她以为是别的什么原因,比如,他害怕她死,他一想到她死就忍不住难过。
她开始巴结他了,他待她的所有行为她都报以讨好的笑。哪怕倒一杯水,拿一张草纸,穿一下袜子,她都像得了额外的好处似的,忙不迭地表示她有多开心,多享受。她当然没说谢谢,她神情里的意思却就是这个,小心翼翼的,满脸堆笑的,刻意保持几秒钟,让他也可以开心起来。
而当他偶尔一回头,会发现她脸上的笑立刻僵住了,是鲜花盛开后刹那凋零的肃杀,荒凉而愁苦——是的,她其实早知道事情的真相,她的心里也并没原谅他,她只是不想戳穿他而已。
他极度震惊,原来不光是他想表现得好一点,她也是的。他们都在彼此遮掩。这个发现使得他无法再待下去,他不知自己是怎样离开的。他足有一个礼拜没去医院,因为刚好有个机会,他跟着同学下乡学农去了。一到外面的世界,他就像鸟儿飞出笼子,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虽然农活很苦,他却干得挺欢的,身上所有的力气都掏空了,累得像一根木头倒下便睡,夜里也不会做噩梦。一个礼拜结束,他都很少想起她。原来,没有她的日子是这样的。
他像找到了一个讳莫如深的秘密,不敢轻易触碰,藏着掖着,胆战心惊地回到家。外婆正哭得一塌糊涂,见了他,跟他说,这一次,他母亲真的走了。
他愣了一下,问外婆,为什么不早点叫他回来?
外婆说,你妈不让,她说她知道你想出去,难得自由几天……
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她是故意放任他离开的,蒙在鼓里的却是他。外婆还在哭诉,“真可怜啊,她熬了这么久,走的时候还是没见着你,你可是她的老疙瘩……”
在他家乡,老疙瘩是指过了足月好久才生下的孩子,差不多一条街的人都知道,他的出生是个传奇。他足足在母亲肚子里多待了两个月才生下来,别的孩子是十月怀胎,他却是十二个月,这实在不可思议。母亲一提起这事,总是羞红了脸,因为医生说她算错了孕期,一个女人,连自己怀孕的日期都搞不清,你当什么母亲!这是当年医生的斥责,弄得她再也没脸待在待产的病房,私自跑了出来。那会儿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街上没一个行人,树皮都啃光了,她跑到野外,看见一个得了浮肿病的女人抱着皮包骨头的死婴坐在一只坟坑前,旁边立着条野狗。这条野狗有一双血红的眼睛,像吃过死人一样,吐着长长的舌头瞪着那个死婴。她吓得又跑回医院里来。
这场惊吓彻底改变了她的生理机能,她肚子里的婴儿也仿佛被吓着,突然停止了生长,待在里面不动了。“千万别出来孩子,还是妈妈肚子里最安全。”她发着烧,每天捧着大肚子,跪在地上向天祈祷。别人以为她神经错乱,胡言乱语,结果却是真的,他在她肚子里多待了两个月。“这样多好啊,妈妈有吃的你也有吃的,妈妈开心你也开心,妈妈难过你也难过,你最听妈妈的话,跟妈妈最亲。”她拍着肚子夸他,一脸的陶醉。
据说他生出来的情形有点可怕,他满脸皱纹,完全像个老头儿。她看着看着泪流满面,“你真是个老疙瘩!妈妈的老疙瘩!”她把他抱在怀里,像猫一样舔干净落在他脸上的泪水,“对不起,妈让你住在世上最好的地方,你怎么都住老了呢?”
现在,她连同她那个曾经的世上最好的地方都消失了,永远消失了。他跟着外婆匆匆赶往殡仪馆,外婆拉长的哭声像唱歌似的,在风中有不绝如缕的回音,仿佛天地都在共鸣。这时候他也应该哭出来才对,但他哭不出来。好像他身体里面同样存在着的一个曾经最好的地方,已经壅塞,干涸一片,再也滴不出一滴水。
【责任编辑】 于晓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