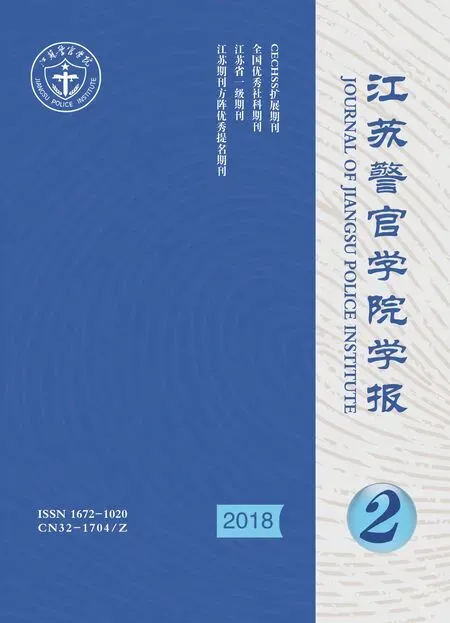对女子扒动车门事件的若干思考
——以警察行政强制为视角
李 铭
一、案件基本事实及处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8年1月5日16时44分,G1747次列车在合肥站准备开车时,旅客罗某(女)以等丈夫为由,用身体强行扒阻车门关闭,不听劝阻,造成该次列车延迟发车。公安机关对此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1月10日上午,罗某到合肥火车站派出所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罗某的行为涉嫌“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输”,扰乱了铁路车站、列车正常运营秩序,违反了《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77条之规定。按照该条例第9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责令罗某认错改正,对罗某处以2000元罚款。①安徽铁路公安:《“用身体强行扒阻车门”女子处以2千元罚款》,http://news.eastday.com/s/20180110/u1a13575855_K26861.html.在该起事件的现场处置及后续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三方面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第一,违法嫌疑人罗某扒动车车门的第一时间,仅有两名男性铁路工作人员在场(一位站在车站站台上靠近被扒车门,另一名站在车门内侧)进行反复劝说、说服、拉劝工作,前后长达数分钟之久,直到动车启动警报铃声响起、才有一名乘警从车厢里一路小跑,赶到现场。整个处置过程,铁路公安民警未在第一时间,即时到场处置。按照《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63条之规定,维护车站、列车等铁路场所和铁路沿线的治安秩序,应由公安机关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质言之,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火车站警力配置不尽科学合理,列(动)车上有乘警、候车室(大厅)内、进出站口均有巡逻民警值守,但站台上、车辆进出站上下客时段却往往难觅警察的身影。无独有偶,2015年5月2日,震惊全国的庆安火车站枪击案中同样暴露出先期处置警力不足、当班民警田泽明不到岗尽责履职的严重问题。②《央视全程还原庆安枪击案 开枪民警很委屈》,http://news2.jschina.com.cn/system/2015/05/31/024926657_03.shtml.因此,必须加大对火车站进出站口安检通道、车站上下客站台等关键部位的治安查控力度,尤其是进出站高峰时段、车辆上下客敏感时段应保证有充足的巡逻警力,加强巡逻、盘查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有效预防和遏制案件的发生。常态情况下,既要保证固定警力驻点值守,同时配备充足的机动警力。加大对关键部位的视频监控,即时发现隐患、在第一时间有效处置各种突发警情。
第二,事后,合肥站派出所对罗某扒动车门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条款的具体内容值得商榷。认定罗某的行为涉嫌“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输”,已考虑到罗某扒车门是为了等丈夫的目的性。而扒车的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上的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了扒车行为,出于什么目的、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则在所不问。我们认为,罗某实施了“用身体强行扒阻车门关闭,且不听劝阻”的具体违法,与《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77条第12项“扒车”的行为特征更为契合。从文义上讲,扒车通常是指攀上行驶的火车、汽车等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页。这里如果将扒动车的违法行为,简单机械地理解为“扒”正处于行驶状态中的动车,不符合常识常情与常理。众所周知,火车行驶速度较慢,每小时数十公里(快速列车的最高限速是120KM/每小时),可能还扒得上去;而动车正常行驶速度高达200KM至300KM/每小时,此时正常人要徒手“扒”上高速行驶的动车不可能轻易做到。合肥铁路公安或许是基于上述考量,在主要违法事实之认定上未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扒乘”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之规定(拘留并处罚款),而选择了《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77条第1项“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输”之规定单处罚款,顶格处理。
我们不同意该观点,本案处罚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4项“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作为法律依据。理由如下,动车靠站上、下客的车辆虽不是正在行驶的行驶状态,但与不在行驶(运营)的车辆(到达终点站或检修车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类似于道路上等红灯状态的汽车)。这种行驶过程中的特殊状态,仅是为上下客而临时短暂停靠(通常只有数分钟),随时准备发车、继续行驶开往下一个站点。动车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的广义“扒车”行为所指称的客体之一。而车门作为动车之重要组成部分,扒车门的行为应属于扒车之具体行为内容之一种,实践中还可能具体表现为扒车头、扒车尾、扒车窗、扒车身、扒车顶等各种姿势和扒法。罗某行为客观上已经造成了“造成该次列车延迟发车”的严重后果。有鉴于此,基层铁路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对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的“扒乘”),没有法定解释权力(没有法律规定和授权)。有权解释机关(公安部)应当适时以行政解释的方式,对上述类似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外延进行目的性扩张的方式加以解释②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并以《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的形式公布实施,以有效地指导基层警务实践之所需。否则,相关条款无法关照类似情形的处理,该条款的部分内容将形同具文,法律空转现象势必无法避免、成为常态。
第三,针对违法嫌疑人为女性等特殊情况,在事先的处置预案里明确规定,现场处置人员的组成中,应当配备相应的女性工作人员。今后铁路公安机关应当为基层一线实战单位配备一定比例的女民警、女情报信息人员等女性工作人员,便于相关盘问、检查、查缉、控制等现场处置工作的实时开展和有效实施。
二、警察行政强制行为的因应与优选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调整,公共福利也必须加以保护以使其免受反社会的破坏性行为的侵损。”③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本案中,对于女子用身体强行扒阻车门关闭且不听劝阻的违法行为,如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该如何应对并有效处置呢?经过细致的梳理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警察法律规范提供了三种备选方案。
(一)行政约束——现行法律依据不足,亟待健全完善,不可适用
《人民警察法》第14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行政管束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管束在学理上,按照目的不同可分为:对精神病人(《人民警察法》第14条)和醉酒者(《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46条)的保护性管束;对饥饿、寒冷、疾病、受伤、即将临产而濒临死亡或有生命危险的人进行的救护性管束(《人民警察法》第21条救助和帮助义务);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目的,实施的预防性和制止性管束。①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88页。现行《人民警察法》中,对于预防性和制止性管束未有明文规定。导致警务实践中,基层一线民警的执法行为要么因没有明确法律依据或法律授权,陷于无法可依的窘境(如本案中,就不能简单、机械地将行政管束条款作为现场执法的依据);要么按照《人民警察法》第6条概括式授权,极易导致滥用职权的尴尬。
有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第28条专门规定了保护性约束措施:人民警察对实施危害公共安全、他人人身、财产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可能自伤、自残的疑似醉酒人、吸毒人、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其他丧失辨认或者行为控制能力的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送至医疗机构、救助机构,或者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领回。需要送往指定的医疗机构、救助机构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除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及时通知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②公安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http://www.mps.gov.cn/n2254536/n4904355/c5561673/content.html.上述立法的健全完善,无疑将填补现行警察法上的漏洞,为基层执法提供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遗憾的是该条款在体例安排和内容表述上存在先天不足,有待商榷。第一保护性约束措施显然未能穷尽行政管束的各种情形。如上文所述,未在学理上按照行政目的和警务实践之所需对行政管束进行类型化区分。我们认为,具体条款应当分为保护性约束和预防性、制止性约束两种类型,而救护性管束已被第13条危难救助所涵盖,在此无需赘述。第二既然作类型化的区分,从立法技术上讲,应当按照执法目的,分作两款分别予以单列规定为好。而不能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地取其一种情形,合为一款,这样于理(法理)不通、于法无据,也不符合上下文义、前后逻辑。第三建议将保护性约束作为第一款居前,预防性、制止性约束作为第二款垫后。以起到防止基层民警滥用预防性、制止性约束措施,真正实现服务群众、规范警权、保护人权之立法目的。
(二)强行带离现场——依据明确可适用,但后续措施必须及时跟上
《人民警察法》第8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者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现场立即实施强行带离现场的行政强制措施之目的,是为制止违法行为(继续扒动车车门)、避免危害发生(罗某自身人身安全)、控制危险扩大(导致动车停驶、晚点、沿线动车准点率受影响)等危害后果的发生,依法对罗某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如前文所述,本案中从实体上看,罗女“用身体强行扒阻车门关闭,不听劝阻,造成该次列车延迟发车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之规定,是一种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已经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且即将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此时依法对其实施强行带离现场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人民警察法》第8条之规定,法律依据明确具体。从程序上看,这属于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之紧急情况。按照《行政强制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之规定,一般情况下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第 18条第 1项);紧急情况下,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24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第19条);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返回行政机关后,立即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第20条第3项)。所以,对于此类极少数紧急情形下,“先实施,后报批”的特殊情况。事后,应当依法立即补齐相关法律手续。
其他后续处置措施也应及时跟进。否则,如本案中开始仅对罗某作教育处理(1月5日),随着舆情不断深入发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月10日,才给予罗某罚款的行政处罚,虽未出现违反办案程序和法定期限的情况,但办案节奏较慢、拖泥带水确是不争的事实。就结果看,行政处罚明显违悖了过罚相当及比例原则。对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稿)》①公安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修订草案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http://www.mps.gov.cn/n2254536/n4904355/c5604357/content.html.分别提高了罚款的上限(一般违法行为由200元以下罚款提高到500元以下;情节较重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由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提高到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对于情节较重的情形,拘留期限未有变化。我们认为,上述处罚设定明显较轻,不足以对扒车的违法行为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高速动车日渐普及,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类似扒车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属于情节较重的情形。②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http://www.66law.cn/domainblog/12182.aspx.如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苏公厅[2006]394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在铁路非法拦截、强登、扒乘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属于情节较重的情形之一。2017年9月,江苏省公安厅法制总队编撰的《公安执法实务问答——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页也采纳上述观点。据此,我们建议将拘留期限延长至15日,以充分发挥法律对该严重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和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作用。虽然,上述江苏省公安厅的规范性文件对合肥火车站发生的案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但对类似案件办理时的事实认定、性质甄别、情节判断和打击处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行政传唤——万能条款,可适用
行政传唤是通知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嫌疑人到指定地点接受询问的调查措施。由于该调查方法缺少罚则作担保,仍应理解为任意调查,在实施中要尽量取得行政相对人自愿主动地协助,否则,调查将难以完成。③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规定了行政传唤的三种方式:口头传唤、书面传唤和强制传唤。对于当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可以口头传唤。口头传唤时,公安人员应当出示有关证件表明身份并告知传唤的原因和依据(有随身佩戴的执法记录仪记录在案、备查)。实践中,为了便于公安机关更好地查破案件,对于“当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人”中的“当场”,应当包括“案发现场”和事后“当面发现”这两种情形,而不应只局限于“案发现场”。本案中,处警民警可以依法当场对违法行为人罗女进行口头传唤。如罗女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民警可以强制传唤。如认为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来不及全部履行完口头传唤的所有义务内容或对方明确表示不予配合的,直接适用强制传唤亦无不可。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42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强制传唤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措施,在使用时必须特别慎重:—是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即必须是“无正当理由”。若行为人有正当理由,如因亲属病危或处理与己相关、非办不可、特别紧急事务等方面原因而逃避传唤的,则不得适用强制传唤措施。二是必须事先进行告诫。三是措施必须得当。对于强制传唤中使用警械的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53条第3款规定:强制传唤时,可以依法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至于行政传唤的性质,我国台湾地区在类型化行为中,将传唤归为行政命令的做法使得其关系显得更为顺畅。对于证人和关系人,“通知”应该是事实行为;而对于嫌疑人,“通知”是一种混合性的行为,具有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的双重属性,包含了一般“通知行为”和命令行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口头传唤和强制传唤往往是连动发生、“一气呵成”的,其间可能没有多少的时间间隔。据此,余凌云教授更倾向于认为行政传唤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①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270页。笼统地定义行政传唤的性质显然不够科学,我们主张将行政传唤程序分为两个阶段加以分析,第一个阶段口头传唤类型化的区分:绝大多数情况下,相对人配合的属于事实行为(不产生法律效果、不影响相对人权利,相对人负有容忍、协助义务),极少数不配合的情形是一种法律行为(大多数情形转化为强制传唤)。书面传唤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调查行为。第二个阶段强制传唤则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已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42条第1款第2项所确认。
铁路公安处警民警因无明确法律依据,不能适用行政管束;可以依法采取强行带离现场或行政传唤的处置措施。理论上,上述三种行政强制措施,都是对人身及人身自由的强制。行政约束是预防性强制措施②张建良、马泽红:《公安行政执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强制带离现场是制止性强制措施,强制传唤是保障性或辅助性行政强制措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都是临时性的,都是为保障行政决定所载明的义务能得以最终实现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至于行政强制措施性质,恰如学者所言:“行政强制措施既不是执行性措施,更不是惩罚性措施,而是一种强制和教育措施。”③湛中乐、杨君佐:《行政强制措施制度研究》,《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因此,不能将行政强制措施错误地理解为对行政相对人的一种制裁办法和惩罚手段,来替代其依法应受的行政处罚。
三、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
(一)行政强制必须有实体法的明确授权
韩国宪法规定,为维护秩序,对国民自由与权利的限制只能通过法律进行,警察权的发动要有法律依据,这时的法律应当是作为警察作用根据的警察作用法。法律的授权应当是个别的、具体的,原则上是不允许概括性、一般性授权的。所以,单纯组织法性质的警察任务条款不能成为警察权发动的概括性授权的根据。④金东熙:《行政法Ⅱ》,赵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因和人身自由及财产权息息相关,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对即时强制措施的行使要件和程序也有严格规定。即必须明确地、具体地,并且限定性地加以规定。在没有充裕时间下令的紧迫情况下可以采取即时强制措施,但必须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只有在因强制措施的采取而消除的障碍形态、程度以及消除的紧迫性进行对比权衡后在必要的限度内,才可以授权采取即时强制措施。⑤市橋克哉、榊原秀訓、本多滝夫、平田和一:《日本现行行政法》,田林、钱蓓蓓、李龙贤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207页。
诚如余凌云教授所言:行政管束、强行带离现场、强制传唤等即时强制、直接强制行为对公民权利自由的干预力度较大,特别是其实施过程的合成性、不间断性,使得任何事中的救济都不大可能;目前事后救济(国家赔偿)又是不充分赔偿,不足以切实保障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所以,在实体上坚持即时强制必须具有具体、明确的警察行为法上的法律依据⑥余凌云:《警察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而非警察组织法上概括性授权(《人民警察法》第6条)的科学论断,无疑为警察法中行政管束制度的建立健全、强行带离现场制度的完善指明了科学立法的正确方向。
(二)行政强制程序上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强制法》实施
抚今追昔,让人略感惆怅的是,从早期的“孙志刚案”、“西安夫妻看黄碟案”,再到近期的“乘警没收涉黄手机案”、“网警受贿删帖案”,这些案件无不反映了警察强制处分的随意化。本应该由立法规范、司法制衡的失范行为,大多数以事后追责的方式收场。其中的程序要件问题、裁量基准问题都未得到有效的制度确立。①蒋勇:《警察权“强”“弱”之辨:结构失衡与有效治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3期。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应当预先制订各种紧急行动方案,规定紧急集合和执行任务的联络方式和要求,并按照规定报经上级批准,组织必要的演习和训练。针对扒动车这种严重危害铁路运营治安秩序的重大警情,事先亦应制定相应的处置预案,并据此认真贯彻、严格实施。值得欣慰的是,随着《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在程序上对规范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该法第18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的法定程序:如: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等。尤其是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予以特别规定,如第20条依照法律规定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除应当履行本法第18条规定的程序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当场告知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在紧急情况下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在返回行政机关后,立即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法律规定的其他程序。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得超过法定期限。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条件已经消失,应当立即解除。可见,紧急情况下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只是“先实施、后批准”之极少数特殊情况,且事后仍应依法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并且不是百分之百会得到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如2017年9月发生的“上海交警粗暴执法事”,上海公安机关即时启动了调查问责程序并于第一时间对社会公布案件的具体处理结果,即是对朱警官等二人执法行为在法律上、实体上作出的否定性评价,也是公安机关内部自我纠错机制的有效运作和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公安机关的处理及时且有必要,体现了知错就改、绝不护短,雷厉风行、严厉问责的工作作风,值得肯定、褒扬。质言之,行政强制程序上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强制法》实施,现场执法人员(执行者)和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者)必须依法审慎对待,不能恣意、任性、滥权。以保证警察强制权的正确行使,从而使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行文至此,惊闻2018年1月11日中午,从兰州西发往上海的G1972次列车到达宝鸡南站后,再次上演类似女子拦高铁门等夫归的荒唐闹剧。②《女子宝鸡南站拦高铁门等夫归》,http://news.sina.com.cn/c/2018-01-12/doc-ifyqptqv8035919.shtml.为了使类似事件不再重演,立法机关亟待健全立法、公安部应当出台相应的行政解释,让民警有法可依;同时,基层铁路公安部门应当严格执法,并做好舆情的宣传引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