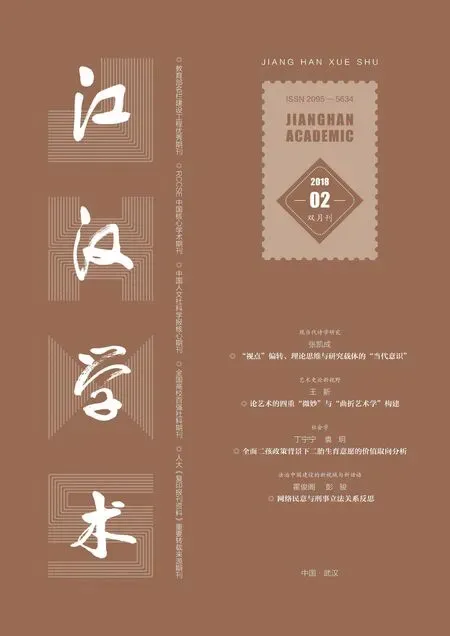论艺术的四重“微妙”与“曲折艺术学”构建
王 新
(云南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昆明 650091)
一个基本事实是,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中的“心”是复杂的,世界中的“物”是复杂的,“心”“物”相生,更是复杂的,所以任何试图对世界进行触摸、把握乃至阐释的理论,不可能不复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出,好诗应“随物以婉转”“与心而徘徊”,这虽然说的是艺术创造,但亦可用来形容好的理论。好的理论一定是体贴着世界的“物”与“心”,随之婉转徘徊,从而获得生发力、穿透力和阐释力,这就是我所谓的理论的“曲折性”。
明晰性,固然是一切理论所固有的本性,然而,纵览人文科学一切有生发力与阐释力的理论,往往都极富“曲折性”。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既要具体,又能抽象,极其“曲折”。实际上,这是黑格尔从康德的“知性直观”概念而来。在黑格尔这里,概念是能动的,是有生命和涌发力的,概念通过“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恢复到单纯的自身(即“一”),这个自身蕴含着丰富性(即“多”),所以直观中可以有知性,抽象中可以有具体[1],他的“绝对理念”应作如是观。
又比如,佛教唯识学里,讲人对世界的认识,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第六识意识的思虑与分辨表层底下,还有一个第七识“末那识”,即恒思虑与恒我执,是人自利的根源。而这七识,皆会断灭,皆由不灭的第八识“阿赖耶识”所生起,但这七识,皆可熏习“阿赖耶识”,在“阿赖耶识”中落下种子,为“阿赖耶识”摄藏,世世轮回,续续积累,形成业果之“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赖耶识”与前七识相互相生的“曲折”,尤其是“熏习”的氛围场域性与“种子”的续续生发性,都无法彻底概念化与现成化,都极其微妙。所以这一理论,对我们人类认知能力的把握,远远比理性、知性、感知或前意识、潜意识诸概念,来得深刻,来得有包孕力。
再如,早期尼采讲悲剧精神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两厢摩荡,海德格尔讲真理在大地与天空之永恒争执中现身,都深富曲折性。
因此,理论应该是曲折的,动态的、生发的,乃至富有些微的模糊性。当然,曲折并不是故意晦涩、故意叠床架屋。
由于关联世界中最丰富、最复杂的“心”“物”关系,艺术无疑最微妙、最需要曲折的“艺术学”来体贴触摸。在这点上,中国古典艺术学可谓风标独树,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即立“委曲”一品,来品评含蓄婉转之诗格。顾随先生讲中国文学中韵文风致有二,一坚实,一夷犹[2],如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真是锤字坚而难移。至于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其上下摇曳的韵致,顾随先生拈出“夷犹”一词(“夷犹”为双声而起落,从发音到词义,皆具起伏摇曳的风致),用之概括品赏屈原艺术的微妙,真真可谓曲尽其妙。当然,当代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讨论梵高的《农鞋》,梅洛—庞蒂研究塞尚《静物》,福柯评论委拉斯凯兹《宫娥》,皆是流连沉吟,千回百转,曲折感十足,艺术的“微妙”与艺术学的“曲折”,于此,可见一斑。
下文即从艺术中最为微妙的四个方面,即作品形式的微妙、艺术创造状态的微妙、艺术接受的微妙及艺术史精神气脉流转的微妙,来阐发与反思艺术学所必需的“曲折”。
一、艺术作品的“分寸”
从微观形式到中观结构,再到宏观风格,艺术作品皆有很多微妙之处。比如中国书法,讲究“绵裹铁”,说的就是笔线中能刚劲内含、柔中带刚;至于“柔”几分,“刚”几分,其分寸感,很难具体计量,却是十分微妙。欧阳询用笔,劲健中透着俊秀;褚遂良用笔,劲健中跳跃着柔嫩和敏感。如果对应到西方,伦勃朗用笔,苍率中有细腻;塞尚用笔,细嫩中有老健。齐白石总结毕生绘画用笔经验“半如儿女半风云”:“工者如儿女偏锋之有情致,粗者如风云之变幻,不可捉摸。用笔前要和小儿女一样细心,要考虑是中锋还是偏锋,还要注意疾、徐、顿、挫来描绘对象,下笔时要和风云一样大胆挥毫。”[3]这里,齐白石既道明了创作状态的“小儿女”和“大风云”,也点出了自身用笔正反相成的妙处。如果不是巧合的话,我们观察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如珂勒惠支,用笔皆是席卷“风云”的迅疾与果断,但作品却有“迟拙”味,这是典型的“德国”气质;中国“德国学派”的全显光,其钟馗、山水用笔亦复如是,正是渊源有自。
自结构而观,有的艺术家作品履险如夷,在险峻中求平正,如中国的八大山人,其画面物象多取倒三角形,一方巨大的危岩,蹲伏着一只缩颈鼓腹的怪鸟,危岩下是一条形单影只的小鱼,上大下小,可谓险矣;但他有手腕,通过题款书法、印章,在相应位置平衡之,化险为夷。中国石涛、潘天寿绘画经营多如是。也有的艺术家,反其道而行之,平中见奇,在平正中藏险峻,如巴洛克大师委拉斯凯兹《宫娥》,乍看平平,具象写实,一览无余。但如果沿着福柯的考察路径,从画家、被画者、赞助者、旁观者各个视角看其转折,到画面上的画中画、镜中画,全画可谓波澜起伏、玄机重重。西方塞尚、蒙德里安的画面结构,亦似之。总之,这种中西绘画结构中平正与险峻的搭配手腕,受各自文化传统与审美趣味制约,拿捏如何,全赖艺术家自身的“分寸感”,其中微妙处,自不待言。
自宏观风格而论,中国文人画推重“熟中生”的格调。生固不足论,熟却是俗,唯有熟后生,方是中国文人艺术的最高标准。明清绘画中董其昌、八大山人、王原祁三人绘画,外在形貌差异甚大,但总体“熟中生”的格调,却一脉相承。这是一种笔墨、构图在纯熟后的自然与自由,这种自由有时还显出一种似乎功力不到的随意,这就是生味,是文人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当代黄宾虹在这个文人绘画传统里,深潜拓进,从“熟中生”,过渡到“浑厚华滋”,合范宽之浑厚与董源之华滋为一体,其题画云:“力挽万牛要健笔,所以浑厚能华滋”[4],其实浑厚华滋,也内蕴“熟中生”。同样,中西艺术通达的最高境界,亦即浑厚华滋:如浑厚,是中西艺术皆追求的大境界,然浑厚者,很多难以华滋,如中国的范宽、西方的米开朗琪罗;如果能够合“浑厚”与“华滋”为一体,则大大提升了审美层级,通达了艺术极境,王蒙、伦勃朗,皆是浑厚而能华滋的大师。
除了在绘画、书法当中,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种相反相成的微妙之美,更是触目葱茏:欧阳修“豪放中有沉着之致”,王国维深赏之;李白雄伟而能俊秀,顾随推重之;周邦彦柔婉而能浑厚,唐圭璋深誉之,并言明,词须婉,婉而须厚,厚而须亮[5],此中婉与厚、厚与亮的微妙分寸,非深谙者绝无可能把握。
显然,这些作品中相反而相成的分寸,深刻体现了艺术的微妙;另外,艺术作品恰到好处的圆满很好,有时候作品中的“不及”亦很好,“多余”[6]还很好,那么“不及”与“多余”的分寸,也就成为作品的微妙之处。
为了贴近与捕获艺术作品的如许微妙,中国古典艺术学开创了一些相应的曲折理论,比如两个内涵相反的概念并置,“沉着痛快”“乱而不乱”“浑厚华滋”是也;两个内涵相似、但程度不同概念,通过肯定方式并置,“腴而润”“丰而沃”“秀而媚”是也;两个内涵相似概念,通过否定方式,限定程度分寸,进行并置,“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也。此种独特的艺术批评语言,渗透其中的,正是中华文明中对“度”的拿捏之智慧,也是中庸哲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7]的生动体现。
二、艺术创造状态的“入韵”
伟大的艺术创造过程往往波谲云诡,难以逆料。有创造经验的人都知道,创作开始前会有一个初步构思,以绘画为例,下笔后,最先往往难以一下子上手。但是画着画着,到得意处,往往是忘乎所以,萌生“神欲止而手欲行”的高潮体验。在这样的创造的体验中,原来的构思完全被修改了,非常出彩的创造出现了,有时连自己也不清楚这样的创作状态究竟是怎样生发出来的。著名画家陆俨少先生正有此创造体验为证,“先前画了一笔,接下来忙画第二笔,如波连潮涌,笔笔紧跟,下笔不能自止,而章法之间,续续生发,虚实得当,笔畅神怡,如是血脉相通,精气相贯”[8]。一个作品,如果从一开始就能预料到它的最终完成,那么,一般来说,这个作品虽可能完美,但不会伟大。一个成功的创造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刺激、不断生发,不断“逸出”的过程,其中微妙,实在难与昧者说。
然而,经典艺术理论在阐述艺术创造时,基本是灵感、“迷狂”、潜意识、摹仿(师造化)、表现(得心源)、传统(图式限定)、“心斋”“坐忘”“澄怀味象”等理论,艺术创造的鲜活微妙状态,往往被这些简单直接的理论,筛弃得一干二净。所以为了贴着艺术创造不断生发、不断创新的过程,阐释其微妙肯綮,笔者曾借镜知觉现象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以手为先的场域化艺术创造论”[9]:一个完美的创造过程,是一个有韵律的“动作”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手的作用最为关键;一般最先的部分动作,还不那么上手,不那么“入韵”,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动作没有意义,相反,这些动作地不断反复,正是一个调整与寻找韵律的过程。它为引发下一系列“入韵”动作酝酿蓄势,它的每一步、每一笔、每一个动作,对紧接而来的下一步、下一笔、下一个动作,都有着潜在的诱发作用。最终,艺术家由凝神于画面的落笔着色,进入到凝神于落笔着色动作本身,并且动作渐入韵律,从而忘乎所以,游刃有余。正是创造中手之“动作”(动和作)逐步唤醒、引发了艺术家身体出场,如梅洛—庞蒂指出的,身体富有场域性,在身体场域中,传统(贡布里希的图式限定论、谢赫的传移模写论)—造化(摹仿论)—心源(性灵说、潜意识等)三个对创作具有决定性的要素,才会兴发起来,融冶起来,创化起来,最具创造意义的美感、羞感,才会卷舒开合,灵活动人。笔者相信,这一艺术创造理论更为“曲折”,更细贴创造的动态性、偶发性与灵活性过程,更能把握艺术创造的精义。
三、艺术接受的“入神”
如果说艺术创造的巅峰体验中,有一种“入神”状态,那么在艺术接受的巅峰体验中,同样有一种“入神”状态。这已经为阐释学理论证明,但这种“入神”状态与日常状态,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裂隙,其中出现的全新境界与经验,是以前日常经验所完全无法寻访的——如同宗教徒的神灵附体体验,一旦你有过这样的审美体验后,你的日常状态就会被刷新,你的人格完全被改变了:被一首曲子点燃,被一支舞蹈点燃,或者是被一幅画作点燃,从而改变命运的事情,并不少见。中西宗教艺术史上,因触摸或瞻视圣像,而蓦然被治愈或信靠的故事十分常见。而在艺术审美接受上,康定斯基就记载自己在观看莫奈的《干草垛》时,就蓦然在耳畔响起了音乐,自己的灵魂猛然振颤,从而接通了更辽阔的神秘之境[10]。
此种“入神”状态,在禅道的入定、基督教的神性临在,乃至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状态中,皆历历可证。那么,这有没有神经科学的依据呢?2008年《时代》杂志百大影响人物吉尔·泰勒,在其左脑受伤、手术康复后,出版《奇迹》一书,书中描述了她受伤左脑功能关闭、右脑功能开启时的状态:
我意识到自己已不再能清楚地区分自己身体的疆界,分辨不出我从哪里开始的,从哪里结束……我感到自己是液体组成的,已经和周遭的空间与流体混合在一起了。
我右脑快乐地搭上了永恒之流,我不再疏离和孤单;我的灵魂和宇宙一样宽广,在无垠地的大海里快乐嬉戏。[11]
在我看来,吉尔·泰勒的这种体验,就是“入神”体验,因为左脑主宰科学理性、固化空间,右脑主宰非理性、流体时间,所以关闭左脑、开启右脑,应该就是禅道修习入定的目的,最终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入神”境界。另一方面,既然阐释学已经认定审美接受就是“二度创造”,那么,接受的过程同样如艺术创造一样,是一个不断生发、不断逸出、渐入佳境的过程。显然,这两方面都拥有足够的微妙与丰富。
然而,现代接受美学中的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想象与审美回味诸理论,明显太过简单与坚硬,根本无法阐释整个动态绵延的接受过程。伽达默尔所谓文本视阈与读者期待视阈碰撞、对话、融合、创造的接受理论,宏观层面赋予了接受的动态感与创造性,但对个体具体而微的接受过程,尤其如“入神”状态,难以阐释得贴切,多少显得有些大而无当。因此接受理论的曲折性建构,需要建基于具体而坚实的作品接受史、趣味史研究上。
四、艺术史的“艺术意志”
艺术史的复杂与微妙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个体艺术创造充满种种偶然性与多样性,但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艺术史演变,却体现出一种统一的大势与必然;其二,艺术史内在的形式演变具有强悍的生命,但又如布克哈特所言“只有通过艺术这一媒介,一个时代最秘密的信仰和观念才能传递给后人”,即艺术史映射着一个时代的行为、知识、思想和信仰,但又明显受它们制约与影响。这一与多、内与外的两大张力,决定了艺术史气脉流转的复杂精微。
为了回应第一个问题,西方艺术史学史上,尤其是德语传统艺术史学上,充分借鉴康德的“先验范畴”思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统摄艺术史研究,以图艺术史的多样性演进中,扣住其内在的同一气脉。沃尔夫林就受康德的十二先验范畴启发,归纳出艺术史的五组基本概念(线性的与平面的、平行的与退缩的、封闭的与开放的、静止的与动态的、清晰的与模糊的),企图探索艺术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李格尔则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概念辩证演化生命中,找到“艺术意志”概念,以贯串艺术史从触觉型向视觉型的内在演进气脉。潘诺夫斯基则合康德与黑格尔、李格尔与沃尔夫林为一身,既找到五组艺术史基本概念(本体论上的内容与形式、现象论上的视觉原理与触觉原理、深度与平面原理、融合与并置原理、方法论上的时间与空间),又在图像学方法建构的第二个层面即图像志分析,向第三个层面图像学综合阐释跃迁上,深受康德启发。因为康德认为,先验范畴整合后天经验材料,形成知识时,需借助先验想象力的翅膀,究竟想象力如何承上启下的,这个地方康德保留了一定的模糊性,体现了理论的曲折性。恰如潘诺夫斯基图像学运用中,如有神助地跨越第二层面与第三层面的裂隙,即由图像志到图像学,“一超直入如来地”,豁然洞开图像内涵阐释的全新意境。有意思的是,贡布里希终生批判黑格尔哲学,但他的“传统习得图式+修正”的艺术史哲学,似乎也难逃德语哲学传统思维,“传统图式”极有康德意味,艺术史“试错性”演进中的统一性与进化性,也极有黑格尔之意味[12]。
为了回应第二个问题,布克哈特、赫伊津哈、德沃夏克、洛夫乔伊等文化史、艺术史家,将艺术史置于广阔的文化史与思想史背景中,以求勾索两者的亲密关联。布克哈特以艺术史启发文明史观,洛夫乔伊以观念史提携艺术史,德沃夏克则直接提出“作为思想史的艺术史”,当然,潘诺夫斯基也应该在这一谱系中。另外一些艺术史家,关注艺术与更具体的外在社会政治、经济、阶级、种族、性别关系,如哈斯克尔、巴克森德尔,就研究艺术与赞助人的关系,与社会风俗、时代日常知识的关系;豪泽尔、克拉克侧重研究艺术与阶级关系;芝加哥、诺克林等学者着重探究艺术与性别关系;布尔迪厄致力于研究阶层区隔与艺术品位的关系。这些学者在艺术个案与艺术断代史研究上,做出了耳目一新的贡献,但是,在艺术通史与艺术史哲学构建上,似乎缺乏抱负,或力有不逮。
中国艺术史学史上,为了回应第一个问题,滕固、梁思成等学者试图在中国艺术史中寻找到有机生长、演进的艺术生命,把握贯串中国艺术史气脉流变的内在“艺术意志”。滕固受沃尔夫林影响,尝试以风格生命演进发展,统摄唐宋艺术史演进,他在《唐宋绘画史》引论中说,“绘画的——不只绘画的——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风格,自有横在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一朝一代的皇帝易姓实不足以界限”[13]。这一“横在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换成李格尔的说法,即是“艺术意志”[14]。梁思成则受进化论影响,在其《图像中国建筑史》前言也揭明了中国建筑史内在演讲的“艺术意志”,这是一种有机的生命:“中国的建筑是一种高度‘有机’的结构。它完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孕育并发祥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发育’于汉代(约在公元开始的时候);成熟并逞其豪劲于唐代(7—8世纪);臻于完美醇和于宋代(11—12世纪);然后于明代初叶(15世纪)开始显出衰老羁直之象。”[15]如果将梁思成的建筑史与滕固的绘画史两相对照,实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
此外,美国学者罗樾受其师祖沃尔夫林影响,运用其风格分析方法,研究商周青铜器纹样风格,并勾画出其五期有机演进的历程。方闻运用库格勒的“形相连锁法”,列各时期对原作的临作与仿制,为第一序列,赝品为第二序列,创作明显有仿前辈画风的作品,如四王“仿倪瓒”作品等,为第三序列。由此,原作作为起点,几经临、模、仿,流变绵延,构成中国艺术史的内在自律序列。曹意强引用西方观念史研究方法,对“文艺复兴”“中国文艺复兴”等观念的衍义谱系,进行分梳研究,并且启发了邵宏运用此观念史方法,对中国艺术史的核心观念“气韵”及其衍义谱系进行研究。显然,这些学者都深受西方艺术史学影响,力图构建自律的中国艺术史,其卓伟抱负与筚路蓝缕之功,令人感佩。
为了回应第二个问题,中国艺术史学史上,唐代张彦远最早意识到官方与私人收藏对艺术创作有重大影响,之后,海外学者高居翰、柯律格、白谦慎,以西方艺术赞助人研究方法,研究明清美术,大大开辟了中国艺术史的视野;台湾学者石守谦,则以此方法,按时序,串联多个个案,大略勾画了中国艺术史的演进。美国学者包华石受新马克思主义影响,运用集赞助理论、公共性理认与品味区隔理论为一体的方法,对汉代画像石图像背后的阶层利益、品位与权力表达进行了研究。巫鸿关于墓葬美术及先秦物质文化艺术的研究,落脚点基本在思想史上,尝试通过物质材料与视觉图像,揭示时代观念,以沟通艺术史与思想史。范景中、曹意强多年来的一以贯之学术努力,无论是倡导“图像证史”、观念史写作,还是论证艺术与科学并行的智性认知功能,皆是致力于打通艺术史与思想史的隔阂,以提升艺术史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
总括以上,可见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寻找中国艺术史内在绵延的气脉,或者说“艺术意志”,对中国艺术史研究十分重要;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推动中国艺术史生生不息、绵延演进的“艺术意志”,究竟为何,似未深究。这就使得诸多中国艺术史通史写作、研究,统统变成“时代背景+风格流派+艺术家、艺术品”的模式,僵硬、粗疏、简单、丧失了艺术学的曲折性。而部分艺术社会学的个案研究,如万木春对明代嘉兴文人李日华八年日常生活世界的“深描”及与其艺术创作、鉴赏关系研究,已然足够曲折,但又失却了宏观纵览、通达古今的视阈。因此中国艺术史研究,还没有真正深入与承续中国思想、文化的根脉,发展出系统而深刻的中国艺术史哲学。
在此,笔者尝试提出一个中国艺术史哲学的思想构架,即推动中国艺术史内在演进的“艺术意志”为“儒道互补,与古为新”的三元动力结构。即尊儒的顺“礼仪”、重道的求“逸雅”、儒道皆重的“复古”为新,构成了中国艺术史演进的三元动力,或者说三个制约要素。对应到艺术史与艺术形式上,顺礼仪,对应谢赫六法之“经营位置”,且秦汉以前,中国艺术在平面上经营主次;魏晋开始,多元空间经营萌发自觉,唐代、两宋已然成熟,元代开始向求“逸雅”的个人性灵抒发转化。求“逸雅”,对应谢赫六法之“骨法用笔”,秦汉以前,骨法用笔,服从经营位置的礼仪装饰与象征;魏晋间,开始审美自觉,关注线条本身;唐末、五代,笔与墨结合,皴法成熟;南宋、元后,完全走向书写性的逸笔雅墨,笔墨臻于圆熟。复古对应谢赫六法之“传移模写”,即从传统师承学习与创造转化,中国古典时代的艺术,皆有强劲的追求复古的内在动力,但与古,目的是为新,这是中国艺术创造的特点,也是中国艺术史的特点。由此整个中国艺术史的宏观风格演进呈现为:秦汉及以前的气象(浑茫)→魏晋的风骨(清劲)→到唐宋的兴象(浑融)→到元的韵致(淡远)→到明清的格调(高古)。当然,每个时代,皆有一要素为主动力,其他二者辅而助之,三个要素关联推荡,续续生发。窃以为此阐释模式,更富有艺术学的曲折,也更贴近中国艺术史生发流变的气脉本身。
总之,通过前文详尽地阐析,我们会发现现在通行的“艺术理论”“艺术原理”“艺术概论”,对艺术四重“微妙处”捕捉、阐析,根本无从措手,或者说扞格难入,从而显得大而无当,因此提出“曲折艺术学”构建,就极有必要。除了前文对应艺术四重“微妙”的“曲折艺术学”四个分支的论述,“曲折艺术学”,要成为体系性的学科构建,笔者以为,其要旨有四:其一,首先要谦卑地承认“世界”是有神秘存在的,艺术中的艺术家—艺术品—欣赏者—世界四个要素,任何一个背后都有神秘存在;而且这四个要素中任何两个两厢遇合、摩荡皆有不可预料的兴发性、偶然性与模糊性,承认神秘性与模糊性,是“曲折艺术学”构建的前提。其二,要着力围绕“艺术作品”与“艺术创造”两大主体,进行学理研究构建,艺术中最为“微妙处”皆集中在这两大部位,要调动赏的、史的、论的三大块知识,对二者之“微妙”进行研究,艺术学其他部位研究应紧紧环绕着这两大主体进行。其三,要破除现行艺术学人为切分为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四大块的僵化格局,实现四者聚焦于“两大主体”前提下的深层融通。其四,实现跨艺术品类、跨学科门类的艺术研究,既着力诗歌、绘画、音乐等品类深层融通拓展,又借助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神学等学科知识或视角,对艺术“微妙处”进行交叉融通研究,这里特别强调要借鉴、转化三部分知识,即中国古典(诗学、画学、哲学)知识、西方现象学知识与后现代哲学知识,因为这三者对世界与艺术的“微妙”研究,业已积淀了深厚传统。显然,“曲折艺术学”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创作者和研究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1]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4-145.
[2]顾随.中国古典诗词感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齐白石.齐白石题画诗与画语录撷萃[M]//山西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田园匠心诗趣:齐白石书画精品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4]黄宾虹.黄宾虹谈艺录[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7:244.
[5]唐圭璋.词学胜境[M].北京:中华书局,2016:57-59.
[6]王新.艺术中的“逸出”现象研究[J].美苑,2013(4).
[7]尚书·大禹谟[M]//《线装五经》编委会.五经.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175.
[8]陆俨少.山水画刍议[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5.
[9]王新.论以手为先的场域化艺术创造[J].美苑,2007(6).
[10]曹意强.艺术与智性[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56.
[11]吉尔·泰勒.奇迹[M].杨玉龄,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9.
[12]曹意强.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13]滕固.唐宋绘画史[M].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
[14]陈平.李格尔与艺术科学[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15]梁思成.前言[M]//梁思成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7.
——《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第2版)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