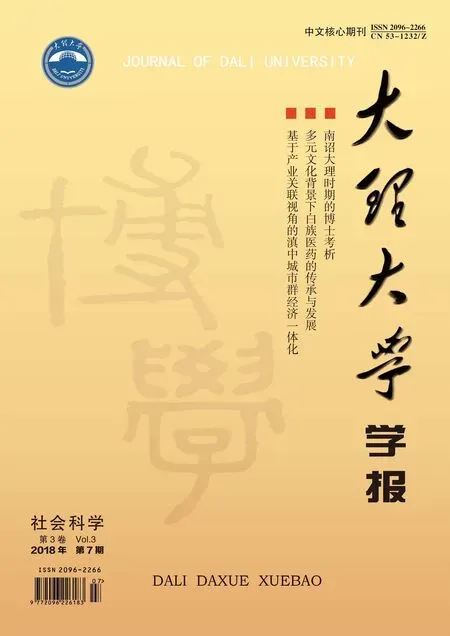空间视角下的厄秀拉成长之旅
王爱素
(黑河学院,黑龙江黑河 164300)
《虹》(The Rainbow,1915)是英国现代小说家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的名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劳伦斯及其作品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相关研究资料颇丰,但从空间视角研究劳伦斯作品的学术文献凤毛麟角。学界更多从弗洛伊德和拉康哲学或现代性等方面入手研究《虹》中的自我身份。傅光俊在其文章中,通过分析“厄秀拉从‘没落’走向新生”〔1〕,揭示《虹》的哲学意义;丁礼明的博士论文借助哲学思想,研究劳伦斯笔下的主人公在工业社会中遭受身份危机之后如何重构〔2〕;沈雁从美学角度探索劳伦斯笔下人物的人类无意识领域和心灵困境〔3〕。从空间方面入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别空间和小说整体空间形式的探讨。于娟和刘立辉曾从叙事艺术视角探讨劳伦斯短篇小说的性别空间特征,指出劳伦斯的空间书写表现了小说人物对自己身份的寻找和确定性自我的建构〔4〕。谭敏从女性地理学视角将《虹》中的地理空间、叙事空间与性别空间相结合,解读女主人公生活变迁过程中的空间隐喻〔5〕。而劳伦斯本人对空间其实有着独特的体验,他所谓“空间的精神”揭示出人类“各种奇特的潜能跟地球上的每个区域都有密切关系”〔6〕。换言之,身处不同空间的人物会有相应的特质:空间的转换,会产生各种奇特的效果。厄秀拉在现代主义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在对感知空间的实践过程中,萌生了对女性“家中天使”身份的困惑;她通过在空间的关系生产中的探索,在父权制的社会空间中突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找寻身份;她通过正视情感与肉欲的诉求,在女性身体空间中寻求灵魂的释放,重塑自我。
一、家园空间与身份困惑
现代文化批评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人类活动发生于其中的某种固定的背景,因为它并非先于那占据空间的个体及其运动而存在,却实际上为它们所构建。”〔7〕小说伊始,劳伦斯向读者展现了工业化日益加剧的时代画卷,新开发的煤矿,延伸而来的公路、铁路,城市化逐渐代替工业化成为资本增值的一种手段,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生活。城市空间在拆迁与建设中急速膨胀,空间生产散布到发达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空间的各个方面。空间的生产基于主体行为,又对主体的认知和建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厄秀拉渴望通过探索来建构自己的生活空间,但又受制于空间生产的约束。父亲布朗文是掌控物质资料生产的场主,是小厄秀拉的他者镜像之一。厄秀拉在教堂玩耍,被布朗文愤怒地指责为随意乱动东西;在田间玩耍又被呵斥为肆意踩踏。厄秀拉困惑,在大地的开放空间里倘若没有人的介入,如何发掘大地的物性;教堂作为沟通上帝与圣徒的空间,不能自由游走,如何参透宗教教义。厄秀拉作为渴求自由的现代性主体,在父亲布朗文那里只有“他者”身份,因而陷入了自我与世界的分裂之中。
厄秀拉小时候以父亲为“她赖以依靠的支柱,父亲在家,她就觉得圆满和温暖,他出门后,她就会神思恍惚,心不在焉……他是她力量的源泉和更伟大的自我”〔8〕209。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生性恬静,却充满好奇心的厄秀拉,因为探索欲望的被压抑而对冰冷的世界充满冷漠感,她“似乎在某个黑暗的神秘有力的阴影中奔跑,她感觉不到这种神秘的阴影,甚至不敢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它的魔力将她的头脑笼罩在一片黑暗中”〔8〕231。一次离开教区房间时忘记关门,弟弟妹妹们摸进去搞得乱七八糟,父亲拿着掸子啪啪朝她身上抽去,深深刺痛了她的心,怀疑和抵制的火星在她心里越烧越旺,烧掉了她与他的联系。她始终对权威感到恐惧和厌恶。“她认为她只要设法避免同权威和权势交战,就能够随心所欲。但是如果她屈服了,就会遭到失败和彻底毁灭”〔8〕261。于是,她一面崇拜着父亲,一面疏远着他的残酷、暴力,常常独自一人把自己锁在房间,“变得顽固,切断自己与外界的任何联系,以顽强的意志生活在自己独立的小天地里”〔8〕218。这种个人空间的闭塞进而使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关注女性,寻求女性主体的自我建构。
祖母莉迪亚与母亲安娜忠实顺从于家庭主妇的身份,生儿育女,扮演着社会传统思想将女性的社会角色限定为囿于一隅的“家中天使”①维多利亚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1823—1896)在其诗作《家中天使》中,称女性为“人人仰慕的完美者,头戴桂冠、犹如天使”。“家中天使”,专心家务,体贴顺从,并坚守在家庭空间的活动领域。的角色。随着孩子一个一个地出生,“她(安娜)必须待在家中,满意地放弃了向那未知世界冒险的想法……于是沉醉于盲目的满足之中”〔8〕192。厄秀拉厌恶安娜对命运的妥协和顺从,“虽然还是个孩子,却知道生活在……生儿育女中意味着什么。虽然还是个孩子,她却对母亲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她渴望某种精神上的高贵生活”〔8〕255。厄秀拉意识到“将女性局限于私人空间的行为既是一种空间控制,也是借此对女性身份进行的社会控制”〔9〕。厄秀拉的主体意识进一步萌发。厄秀拉与安娜在秉性上一脉相承,在观念上却无法认同。厄秀拉厌恶安娜对上帝的冷漠态度,而她自己试图通过“自我”探索,寻找“上帝”的现实存在。厄秀拉不认同安娜整天忙于打理家庭琐事的生活方式〔8〕265,质疑安娜没有独立灵魂,没有自我,精神极度空虚的状态。厄秀拉对“生儿育女,乱糟糟的家庭生活深恶痛绝”〔8〕266。她觉得“像她(母亲安娜)那样把一切局限在物质享受的圈子里,还自以为是地拒绝其他所有现实的存在,是十分可怕的”〔8〕341。厄秀拉反感安娜沉迷于情欲的狂热之中,缺失作为个体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沉浸在生育和抚养下一代的快乐中。“她不喜欢待在家里,在家里她感到不自在,她不情愿也无法表现得正常、自然”〔8〕209。“她恨母亲入骨……她就受够了这个家”〔8〕341。厄秀拉构想自己的女性乌托邦,正如西方女性乌托邦作家皮森所构想的:“在她的理想城市里居住的是各种年龄的优秀女性,这些女性德才兼备,为社会做贡献。”〔10〕而厄秀拉与母亲的冲突更加坚定了她寻求自我意义的道路。
厄秀拉在感知的空间的实践过程中萌生了身份困惑,从中激发出追逐真正自我的原始动力。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家庭空间是主体意识和身体的产物,通过物质生产活动而固化,并反过来支配主体的意识和身体。”〔11〕劳伦斯笔下的家庭空间既是具体的物理空间也是抽象的隐喻空间,现实感强韧的厄秀拉并未就此在迷惘与困惑中沉沦,她迎刃而上,不懈地寻求有效的空间代偿机制,去探寻自我之路。
二、空间逃离与身份找寻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将社会的维度引入空间的研究,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社会空间是政治权利与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与载体,空间的社会属性表现为深层次的社会关系的揭示。厄秀拉的自我成长之旅正是从家庭转移到学校(社会),在社会空间的理想与现实冲突中逐渐实现。这种旅程是一种空间的位移和转换,它是从一个旧世界到新世界,从熟悉的世界到陌生的世界,从自我的世界到“他者”的世界的转换,更是显著性自我塑造的过程〔12〕。厄秀拉的自我正是在空间的转换中逐渐找寻的,正如空间批评认为“空间分布、地理经验和自我身份认同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13〕,而厄秀拉积极的空间移动意识和行为推进着她身份找寻的进程。在文本中可以看到,劳伦斯用了两次相同的标题:The Widening Circle(扩大的圈子),这绝不是偶然。他在这两个章节中呈现了厄秀拉摒弃个人狭小空间,走向社会大空间的旅程。第十章,十二岁那年,母亲安娜要送厄秀拉到诺丁汉郡去读书。厄秀拉为此兴奋不已,因为她能逃离“那使人变得渺小委琐的生活环境,摆脱可鄙的嫉妒,无聊的争吵和可鄙的吝啬的地方”〔8〕254。厄秀拉年岁虽小,但对狭小空间的抵触感和对外面广阔社会空间的向往已很强烈。第十四章,厄秀拉离开圣菲利普小学,即将踏上大学生活,走向更广阔的空间,而布朗文一家也将搬离可塞西去诺丁汉郡。她梦想着将跟贵族交往,感情也变得没有牵绊。这种向往一是由于物理空间的局限与她的自由的天性格格不入,二是因为社会空间的现代权力形式的谱系与她的感知和设想的生活相去甚远。前者在上文中已阐述,后者将在下文探讨。
厄秀拉试图“到男性的神秘世界里冒险……成为社会的一分子。然而她却无端地嫉恨这一切,她渴望征服这个由男人主宰的世界”〔8〕322。虽然,厄秀拉具有一定的空间探究意识和空间的转移能力,但她对社会空间的热爱只能表明她对独立的渴望。厄秀拉怀着满腔的热情来到圣菲利普小学,以期给孩子们带来快乐,但是这所监狱般的学校,既是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又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厄秀拉很快就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强大的封闭、复杂,具有阶层的结构中”〔8〕368,并受控于监督和操纵的持续政权之下。“她不愿让学校完全征服,她不想像机器一样屈从,但是学校就像一个沉重的阴影,在控制着她的行为,时时感到挫败和威胁”〔8〕369。男校长对教师教学的干预,对学生的体罚,都构成厄秀拉极其恐惧与厌恶的噩梦。
在圣菲利普小学的监狱式空间形态中,“空间是任何形式公共生活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行使的基础”〔14〕。空间与权力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空间秩序的展现隐含着权力运作的模式。圣菲利普小学成为控制冲突的权力场,成为训诫的工具,强调统治、服从和反抗的关系,具有潜意识的神秘性和有限的可知性。厄秀拉在圣菲利普小学的两年密切交互中,不断地以各种形式与之进行互动,她与哈比先生、布伦特先生和麦琪的交互关系网络构成了她在圣菲利普小学的社会空间,呈现出一种思想同另一种思想的交锋、一个群体阶级对另一个群体阶级的压迫或反抗;从微观上看,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对于女性的压迫;从宏观上看,社会的政治权力监控体系,维护上层建筑,处处体现剥削和压迫。厄秀拉无法改变空间的存在职能,剥离其社会功能,从而实现她的社会理想。她身处其中,自我不存在了,在这个强大的男人的世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无法解脱。但她永远不会屈服,“她得了解它,为它服务只为有朝一日能摧毁它”〔8〕390,“不想成为男人世界里的囚犯”〔8〕393。但她最后对这个强大社会空间还是妥协了,直至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空间。但她的反抗精神同现代主义的社会准则的交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厄秀拉思考着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愿让世界摆布使其生活空白乏味,她那放任不羁而混乱的灵魂在探索中变得坚强而独立。厄秀拉在圣菲利普小学的冒险中变得强大,但它也同时摧毁她所拥有的、所知道的和所是的一切。
随着梦想的破灭,厄秀拉抱着对埋没人性的机械化体系、对压迫、对传统歧视的反抗态度,和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热切渴望,离开了圣菲利普小学。女性地理学指出“限制妇女在身份和空间中的移动性是维持女性隶属地位的关键”〔15〕。而厄秀拉的出走,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局限,进一步拓展空间。厄秀拉唱歌、跳舞庆祝自己离开圣菲利普小学,转移至大学空间;庆祝自己离开可赛西农舍,离开这个古老封闭的外壳,到诺丁汉郡。厄秀拉憧憬着大学生活,“前面就是大学,那是她的天空,一个陌生而广阔的天空”〔8〕400;厄秀拉梦想着诺丁汉郡的新居,和那里富有教养、情操高尚的朋友。然而,她从圣菲利普小学的逃离只是一种暂时的躲避,她的大学校园也只是知识贩卖的地方,就像一个虚假的车间,只为了物质利益而不是为了生产。她在思索“我到底是谁”,“真正的厄秀拉隐藏在黑暗中,并没有被发现,她还在找寻光亮”〔8〕417。空间的拓展并不意味着身份的建构,厄秀拉对空间的叛逃和追逐只能说明她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彻底实现主体意识的自我重构,她的自我追寻之路更加坎坷。
三、身体空间与自我重构
厄秀拉在外部世界中探索失败,继而转向自身身体经验的感受。她在与安东的性欲、情爱纠葛中,逐渐实现人物性格的完善和身份的自我重构。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身体”是最为重要的建构基石。空间通过身体的感官经验内化进入文学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中的身体空间对文学人物的塑造提供理论支撑。厄秀拉的成长之旅在与安东的身体、情感纠葛中曲线向前。初恋的纠结:一方面,厄秀拉被安东的男性自然力量吸引,渴望释放被抑制的、冰冷的、不屈不挠的激情。在安东的他者镜像中,厄秀拉看到了自己娇美的身姿,第一次爱上了自己〔8〕282,并试图在激情中了解最大限度的自我,在同男性的抗争中限定和限制自己,以期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并取得暂时性的胜利〔8〕291。另一方面,厄秀拉无法与安东在灵魂上取得共鸣。安东对教堂充满敬畏,而厄秀拉更向往精神自由;安东热衷战争,而厄秀拉痛恨所谓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军队〔8〕299。厄秀拉对安东的虚无主义思想感到害怕和无望,对安东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与信仰充满仇恨;而对他所体现的男性的自然力量又充满了渴望。正是这种对充满感性能量的身体空间的依赖,厄秀拉不能正视自己的精神需求,因而,随着安东的离去,她感到不安,“……似乎潜藏着一种深深的、恐惧的、死灰般的失望。”〔8〕338厄秀拉少女的痛苦、激情和渴望,找寻不到情欲出路的苦恼在与英格老师的身体触碰中,得以缓解。这段奇异的情感消解了厄秀拉的身体欲望,使她更深刻地理解爱情的恒久和激情的短暂。女性的身体空间在父权制中是一种繁殖空间,并非女性理想中的罗曼蒂克和温情脉脉。英格老师告诉厄秀拉男人只是把女人当成一个思想或想法,女人不能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男人实现思想的工具。这论断与祖母迪莉娅不谋而合,她曾告诉厄秀拉:“我希望那个人爱的是你本身,而不是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有权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8〕251这些思想渗透到厄秀拉的思想之中,使她的身体从父权制建构的女性身体所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厄秀拉逐渐走出了父权话语下的伦理牢笼,给自己的身体自由的空间。重逢的纠缠:厄秀拉渴望情感肉欲的释放,而身体作为欲望空间的载体,具有创造性和接纳快乐的双重属性,厄秀拉渐渐清醒,却又在与安东的重逢中慢慢沉沦。她一面“想逃向斯克列本斯基(安东)——新生活,新现实”〔8〕421,一面拒斥他在印度“凌驾于那古老的文明之上,作为贵族和主人统治一个落后的文明”〔8〕423。但因为这份爱,“她的心灵必须囚禁着,沉默着”〔8〕424。她满足于被当作斯克列本斯基夫人的虚荣,“占有着他的身体,愉悦地享受着,却完全忽视他(的精神世界)”〔8〕398。厄秀拉对情感和肉体欲望的诉求逐渐被理性统领,厄秀拉不能认同安东去印度的殖民主义行径和所谓的民主。“一想到结婚,一想到在印度同斯克列夫斯基与那些欧洲人在一起,她就不愿再考虑了,她对这种生活毫无兴趣,觉得那只是死路一条。”〔8〕453厄秀拉结束了两人的关系,成为自我身体空间的主宰,并以身体为载体实现自我主体性,通过身体空间对抗父权制,摆脱婚姻、家庭的束缚,追寻精神世界的完满。
劳伦斯笔下人物的自我重构常常在情感与肉体的欲望诉求中得以完成。正如多兹华斯试图从妻子弗兰身上探索她“究竟想要什么”的种种行径,但终究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最后他不得不从自身的欲望出发去探索这个谜底一样,厄秀拉在纠结和挣扎中正视自己的身体与情感欲求,进而试图完成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定。在发现自己可能怀孕之后,出于母性,厄秀拉试图妥协于身体的欲望,回归生儿育女的父权制婚姻家庭中去,甚至写信给安东发誓要做个贤妻良母。但最终她直面自己的情感,深刻剖析了情感、身体和世界的关系,为自己的身体要依附于他人而痛苦不堪。她在病痛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中,找到了“她和外壳之间的空间”〔8〕471,很快从自身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从没有精神、徒有肉体的爱的束缚中剥离出来。厄秀拉精神上的冷静最终使她告别过去,选择了灵魂的解放,去追求自由、永恒的理念。厄秀拉对身体的处置象征了主体的书写方式与反抗策略,颠覆了法国作家邦达(Julien Benda,1867—1956)在《于里埃尔的关系》中的断言:“男人的身体通过自身而具有意义,可以撇开女人的身体不谈,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体看来就缺乏意义……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16〕厄秀拉对身体空间的探寻使她在男性的他者身份中实现了自我的存在,彰显了她的心理成长与追寻独立自我之间的互动关系。厄秀拉正是在通过他者的镜像和自我的身体书写,在矛盾冲突中确认自我身份。
身体首先是物质的构成,其次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身体既是一种表征的空间,又体现了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小说结尾,“厄秀拉病好些了,坐起来观察那个新世界”〔8〕361。厄秀拉惊异地发现一弯淡淡的彩虹,积蓄着力量,最后矗立在大地上。彩虹在人们的血液中拱起,在精神中获得生命;旧的残破不堪的房屋和工厂都被一扫而光,光洁的新生命和真理的构架建起来的世界与自然协调一致。厄秀拉透过拱形的彩虹,找寻到人与世界和自然的交融,实现精神的回归与自我的重构。
综上,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再是纯粹的容器,它是社会生产和实践的产物。厄秀拉正是从空间生产的纬度,凭借个体的独特体验,在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中追寻和探索。劳伦斯笔下的空间给厄秀拉的身份找寻和自我建构提供了重要载体,厄秀拉的自我探索和追寻也成为空间得以延伸的途径。在空间生产中,人类“始终是一种空间存在,并积极参与着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17〕。在此过程中,厄秀拉主体空间意识得以彰显,她在家园空间的困惑中,在社会空间的反抗和挣扎中找寻自我;在身体空间的情感与肉体欲望的诉求中实现自我。这也是劳伦斯在不断地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的过程。
〔1〕傅光俊.从“没落”走向新生的厄秀拉:浅议劳伦斯《虹》的哲学意义〔J〕.外国文学研究,1992(1):23-28.
〔2〕丁礼明.劳伦斯现代主义小说中自我身份的危机与重构〔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3〕沈雁.《虹》与《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另一个自我”:劳伦斯人物美学一探〔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7(2):367-381.
〔4〕于娟,刘立辉.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性别空间叙事探究〔J〕.外国语言文学,2011(4):281-284.
〔5〕谭敏.从女性地理学视角解读《虹》的空间隐喻〔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1):100-105.
〔6〕朱通伯.劳伦斯文论精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23.
〔7〕丹尼·卡瓦罗拉.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87.
〔8〕LAWRENCE D H.虹〔M〕.韩梅,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9〕DOREN MASEY.Space,Place and Gender〔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4:179.
〔10〕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50.
〔11〕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1:139.
〔12〕张德明.从岛国到帝国: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2.
〔13〕WAGNER P L.Foreword:Culture and Geography:Thir⁃ty Years of Advance〔M〕∕∕FOOTE K E.Rereading Cultur⁃al Geography.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4:7.
〔14〕FOUCAULT M.Space,Knowledge,and Power〔M〕‖PAUL RABINOW.The Foucault Reader.New York:Pan⁃theon,1984:252.
〔15〕CRANG M.Cultural Geography〔M〕.New York:Rout⁃ledge,1998:182.
〔16〕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17〕EDWARD W S.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Malden:Wiley Blackwel,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