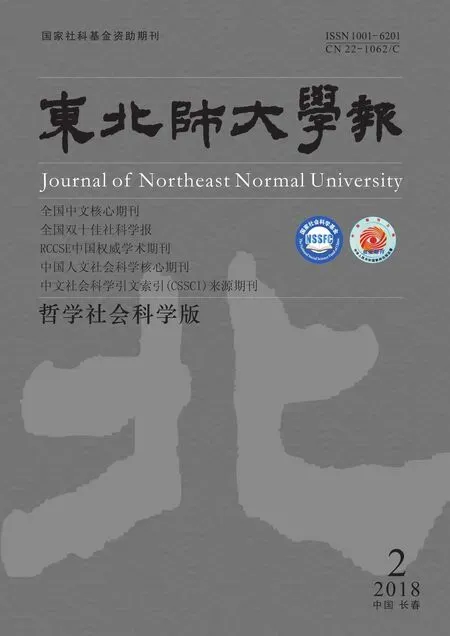接受与差异
——觉醒、救赎与超人主题在鲁迅和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变奏
冯立华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长春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日本学界研究鲁迅的学者可推竹内好、丸山升和伊藤虎丸,而日本文学界吸收鲁迅的文学理念,并将其用于文学实践,笔者认为大江健三郎应是其中之一。在王新新与大江健三郎的对谈中,大江健三郎表示“作为一个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而奋斗的斗士终此一生,是我作为文学者的理想。我正是想在这一点上靠近鲁迅。”[1]大江健三郎第五次访问中国的三次演讲主题都与鲁迅及其文学有关,并且在其第六次访华于北大演讲时,坦承他的早期小说《奇妙的工作》是在鲁迅作品直接影响下,引用《白光》中“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虚构了青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这次演讲中,大江健三郎说他23岁时在夜行的火车上读鲁迅的《野草》,身心受到巨大震撼。50年后的2009年,大江在鲁迅创作《希望》的地方默诵了《希望》全文,以表达他对鲁迅的那种感情。鲁迅对于大江健三郎的影响可谓是一生的。
关于鲁迅与大江健三郎文学的比较研究,已经有了一些论述,如霍士富在其专著《90年代以后的大江健三郎》中,专门有一章从叙事的视角比较了鲁迅的《药》与大江的《被偷换的孩子》,认为两部作品都表现了“救赎”主题。较早研究的还有王新新,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将大江健三郎的《奇妙的工作》的“监禁主题”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出的“铁屋子”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唤起危险的感觉上二者殊途同归、异曲同工[2]76。鲁迅对大江文学的影响究其根底应为思想层面的,不过也有文学形式上的,但不是简单的模仿。本文通过对大江健三郎小说《需要献祭之男吗》的考察,结合鲁迅的《狂人日记》,从觉醒意识、救赎、超人主题考量《需要献祭之男吗》在《狂人日记》后的变奏。
《需要献祭之男吗》可以说是大江的巅峰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发表之后,寻找新的创作方向的尝试之作。作为大江健三郎第一期创作结束的标志性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之后,时隔3年,大江推出了代表他作家生涯的巅峰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众所周知,大江健三郎后来凭借《个人的体验》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长篇之后,大江又回到了他所擅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从1967年到1972年,他创作的小说包括《跑、持续地跑》(1967)、《需要献祭之男吗》(1968)、《核时代森林的隐遁者》(1968)、《父亲呵,你去向何方?》(1968)、《请告诉我们在疯狂中生存下去之路》(1969)5篇短篇,以及《狩猎生活的我们的祖先》(1968)、《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1971)、《濒死鲸鱼的代理人》(1971)和《月男》(1971)4部中篇小说,主题涉及战争、天皇制以及对人类生存的关怀等方面。可以说,大江在这段时间进行了大量的尝试,而这些作品也正是为时隔6年后的长篇《洪水涌上我灵魂》做了准备。《需要献祭之男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是这一时期的尝试之作。
一、罪恶的根源
竹内好的鲁迅论中,认为鲁迅的文学有“罪的意识”,进而对鲁迅的“赎罪”是针对“什么人”的问题写道:“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对坐在这个什么人的影子面前。这个什么人肯定不是墨菲斯特,中文里的鬼或许与其很相近。”[3]328针对这一点,伊藤虎丸进一步解释说:“竹内好所说的‘罪的意识’这一用语,是为说明‘某种本源上的自觉’而做的‘比喻’”,“竹内好要比喻的当然是《狂人日记》里读出来的鲁迅的‘文学的自觉’。”[3]352-353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发觉周围都是“吃人”的人,但是那些人却并不自知,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狂人”的第一次觉醒,发现了罪恶的存在。然后“狂人”开始救助他人,结果却发现自己“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于是,“英雄”落入凡尘,“狂人”的这个第二次觉醒,即发现了自身的罪恶,可以说这正是鲁迅“文学的自觉”的显现。
“赎罪”一词是宗教用语,是指屠宰动物,将其作为牺牲奉献给神灵。鲁迅不是基督徒,当然也不会向谁赎罪。所以笔者认为,竹内好所说的那个“什么人的影子”就是罪恶,这个罪恶具有广泛的人性意义,也包括鲁迅对自身内部的一种认知。与“罪恶”“相对而坐”,即鲁迅与包括自己在内的“罪恶”对决的问题意识。鲁迅的武器是文学,在那样的社会,其对决方式便是通过文学进行绝望的抗争,拼死一搏。绝望之为希望,他的绝望的文学抗争,正如献祭的牺牲一样,非功利性,如飞蛾扑火,即使灭亡,也要驱走黑暗,追求瞬间的光明。鲁迅是非宗教的,但是他文学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
大江健三郎接受了鲁迅的“文学的自觉”方式。他说:“鲁迅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思考中国民众弱点的同时,也将知识分子划归为中国民众,并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鲁迅的自我剖析,就表现在他认为自己也是一个软弱的中国人,并对这样的自己加以批判。”[1]大江正是将这种唤醒罪恶意识、绝望抗争的“文学的自觉”方式应用在了他早期小说《需要献祭之男吗》中,《需要献祭之男吗》里同样构筑了一个如同《狂人日记》般的吃人社会。
《需要献祭之男吗》创作于1968年,正值越南战争时期,不过小说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二战后的日本社会,控诉了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及日本军国主义圣战思想对人性的扭曲。自命名为“善”的高大青年造访小说家“我”,让“我”用小说揭发“亚洲大魔王”工厂主的恶行。所谓的“亚洲大魔王”是“善”命名的,他的恶行就是要做和朝鲜战争时同样的事情,即把炸弹安装在玩具上,然后送给越南的孩子们,将他们炸死。“善”为了得到“我”的协助,告白自己还是流浪儿时,也就是二战刚结束后的日本,由于吃了照顾他们的复员兵的肉,自己已经从本质上被污染了,除了不断地揭露“恶”,他已经无法活下去。后来为了获得资金与土地,建造被弃孩子的家园,“善”与“亚洲大魔王”签订不告发协议,但是“善”最后还是揭露了“亚洲大魔王”的罪恶行径。小说的最后是“善”带领被弃孩子在街头为越南的孩子募集资金的场面,“善”绝望地喊叫“救救孩子,我们现代的大人全部都染上了‘恶’,吃人并且毫无反省的人在东京不下百万……为了给所有的孩子准备丰收季节的果实,我愿意成为被献祭的男人……”[4]85这些熟悉的语言,在《狂人日记》中的结尾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景象“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5]15两部小说如此相似的结尾,并非偶然。这是觉醒与救赎问题意识的接受与变奏。
两篇小说中罪恶产生的形式相似:人吃人。人吃人,无论在哪个文明社会都属于禁忌行为,弗洛伊德认为,“可以说禁忌和良知有关,或者说破坏禁忌与其后产生的罪恶感有关。禁忌良知也许是良知最早的表现形式。”[6]7《狂人日记》里“用馒头蘸血舐”“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这些吃人的行为是有真实史料可考的,“人吃人”将人的最基本的禁忌破坏了,这正是鲁迅要表达的问题意识的基础,因为其他社会的、伦理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吃人”禁忌破坏的基础上。当面临生存威胁时,就会打破禁忌,暴露出人性的丑恶。《需要献祭之男吗》里大江将《狂人日记》的“吃人”史料和罪恶产生的根源具象化,描绘了真实的吃人场面。二战后整个日本处于饥饿当中,复员飞行员收留了包括“善”在内的9名流浪儿,由于资源的极度匮乏,所有流浪儿面临饿死的境遇,复员兵让最大的孩子杀死自己,流浪儿们在狂欢中吃了复员兵的肉,“善”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一片,而这成为产生罪恶的根源。原始社会,为了能够迎来丰收的季节,王成为牺牲品,献给神灵。复员兵认为将自己的血肉献给饥饿的孩子,便间接地成为复兴的牺牲,流浪儿食其肉,那便继承了“复兴”思想。于是吃了复员兵肉的“善”也沾染上了“圣战思想”。如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未必没有吃了他妹子的几片肉一样,他们都成为罪恶的载体。
二、觉醒与救赎
先觉醒,然后是救赎。《狂人日记》里的觉醒和救赎是“狂人”陷入疯狂状态后实现的,那么《需要献祭之男吗》的觉醒契机在哪里呢?在这篇小说中有一处提到了《狂人日记》,“我让他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是我在中学的教材中读过的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小说,你还记得结尾处吗?‘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那是救救孩子的呼号”[4]76,笔者认为这就是“善”在童年吃了人肉后觉醒的契机,《狂人日记》为其开启了救赎之窗。
善与恶仅在一线之间,意识到自身之恶,进而进行救赎行动,那就是善,反之就是恶的延续。小说中写道“当意识到被全人类拒绝的自我时,要么选择成为‘恶’,要么选择成为‘善’,除此之外,将无法生存下去……必须慎重地让人意识到这一点。”[4]74可以说,这不是世界观意义上的,也不是人格、伦理上的思考,而是处于被抛弃的边缘之人的深刻的赎罪告白,是个人觉醒之后救赎的指导思想。《狂人日记》关于“狂人”在复原后是否要继续开展拯救行为,鲁迅没有明确的交代,关于这点小说处于失语的状态,笔者认为这是鲁迅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绝望态度的体现。相对于此的《需要献祭之男吗》中,被“恶”污染的“善”觉醒后,他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揭露“恶”上,展开了救赎行动,也就是说大江健三郎将救赎由意识发展成为现实的行动。首先就是揭露“亚洲大魔王”的恶行。朝鲜战争时,“亚洲大魔王”就欲将装有炸弹的玩具送给朝鲜儿童。越南战争时期,他又故技重演。“亚洲大魔王”要把所有日本的民众都卷入到他的“恶”中,以此获得黑色的满足。因为他的菠萝炸弹孕育着二重的恶:一重恶是肉体上的伤害;另一重恶是精神上的污染。因为这种炸弹不仅威力巨大,破坏力严重,而且他把收集到的赌博用的“爬金库”小球安装在玩具上,一旦爆炸,便是将全日本所有玩过爬金库的平民卷入到罪恶当中,都成为“吃人”的人。从复员兵的“圣战思想”对“善”的污染,到“亚洲大魔王”对全体日本民众的污染,大江与鲁迅一样,着眼的都是所处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和对由此产生的罪恶之批判。《狂人日记》所描写的“人吃人”的世界,并不只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也是鲁迅所说的“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随感录六十五·热风》),弱者见弱者,即使稍弱于自己一点,便凌辱他人,玩味他人的痛苦。二战后的日本已经是弱者,但仍然要施加苦痛于更弱的朝鲜、越南,在这个意义上,伊藤虎丸所说的“《狂人日记》不是在世界观意义上,而是人学、伦理学意义上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普遍的。”[3]165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献祭之男吗》里“吃人”的恶行还有另一番熟悉的景象。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一方面对恶行的真实性或怀疑或嘲弄,比如小说家“我”已经沦为了无动于衷的看客;另一方面有些人虽然知道“恶”的真实存在,但却表现出回避态度,甚至刻意隐瞒,比如小说里的警察当时面对吃人事件,为了自保而不敢深入追查。《狂人日记》里也是如此,以狂人兄长为代表的看客一样冷漠。重复与差异,接受与变奏,在两部作品中有了完美的展现。
三、“超人”行动的失败
鲁迅早期留学日本时,受到进化论和尼采的影响,这已经被国内外许多学者论证过,此不赘言。鲁迅将尼采的以意志超越自我的思想投入自我之中,《摩罗诗力说》里的“反抗和行动的诗人”“精神界之战士”背后,不可否认有尼采的“超人”思想之影像。《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也是一位“超人”,他同样有改变世界的愿望与行动。当然,鲁迅终究没有造出“超人”,他知道了自己“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大江健三郎在《需要献祭之男吗》里也塑造了一个名为“善”的“超人”。不过,“善”这个“超人”不同于“狂人”这个“超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江将《狂人日记》里“狂人”这个主要是精神上的“超人”具象化,从外形上塑造了一个“超人”的形象。另外一点就是,不同于鲁迅笔下“狂人”的觉醒与改革行动是处于“疯狂”状态下进行,大江的“超人”是处于完全正常的状态,以具有绝对清醒的自我意识为前提,现实主义特征非常明显。关于前者,“善”是个高大肥胖的男人,他的外表让人感到威压、畏惧,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善”符合强者的形象,但是这只是个悖论,是“这怪异的肥胖,甚至连骨头的每一个部分都那么肥胖,如此像鬼一样的身体在其他地方看见过吗?而且不能和我自身新创造的血肉相连,因为我吃了人肉没有了生殖力”[4]63的二律背反,其肥满高大的肉体仅仅是“恶”的载体。尽管《需要献祭之男吗》和《狂人日记》的创作时代不同,有国别的差异,但是结局却很相似:向“恶”宣战的“超人”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大江笔下的“善”与“恶”对决的方式如同鲁迅笔下的“狂人”般坚决,不过,大江将鲁迅对“恶”的绝对批判姿态进行了区分,并进行了批判与拯救的尝试,但是结果依然是失败,回归到鲁迅的视点。
“善”与“恶”作为矛盾的两极,具有绝对性。大江在这篇小说里,不同于自己以往作品的暧昧表达,通过“善”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恶”的坚决斗争的态度,不能混淆,不可调和。“善”以自身之恶(吃了人肉)对抗“恶”,这是绝望的无所求的抗争,疾恶如仇,正是以这样的坚决态度开始了他的行动,但并不是无区分地对待。大江将“善”对抗之“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明知恶行而故意为之,如“亚洲大恶魔”,对于这种恶,要坚决揭露斗争;第二种是做了恶,却不自知,如同《狂人日记》中的看客,又如“无辜者之家”不知情的食人肉的孩子们,因为这种“恶”具有可转化性,需要谨慎对待,故欲救“恶”从“善”,需先使其觉醒。关于前者揭露“亚洲大恶魔”之恶行,虽然其中有妥协的桥段,但是最终“善”还是果断地揭发,不过结果“善”只得到记者“表面是感伤的,在其外皮下是阴险的歪曲意图”[4]75的报道。而第二种的唤醒行动,以“我”的无动于衷、看客之麻木、警察的驱赶而告终,“善”只能进行绝望的呼号。至此,超人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不过,在这个浅层文本中却是蕴含了深层的觉醒意识。如果说“善”认识到自己食人肉的恶行是第一次觉醒,那么第二次觉醒就是从依赖他人转变为依靠自己。第二次觉醒的结果,就是救助流浪儿童,尽管为了获得建立新的流浪儿的“无辜者之家”的资金和土地,而有向“亚洲大恶魔”妥协的戏码,但是最终还是告发了他,结果导致“善”的第三次觉醒,那就是“善”这位“超人”意识到了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民众,正如同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弱小,将自己上升为民众。但是日本的大人却被“恶”污染了,所以小说的结尾只能和《狂人日记》一样,“救救孩子”,将希望寄托于将来。吃了人肉的“善”愿意被吃,成为献祭的牺牲。“善”的拯救是无功利的,其方式是拼死的,是带有基督教性质的,正如鲁迅之于文学的方式。大江心中的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的“超人”思想在《需要献祭之男吗》中崩塌了,在这段时间的尝试之后,大江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越发明显。
大江文学进入80年代以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引用,其作品不仅大量引用了他人的作品,对自己以往的小说也广泛地引用,例如《致令人怀念之年的一封信》中,引用了《圣经》、但丁的《神曲》、拉伯雷《在活火山下》、柳田国男《美丽村庄》等,引用的自作从初期的《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然后是《十七岁》《叫喊声》《个人的体验》,直至《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等,将自己作为作家的创作活动充分地吸取并引用进去。大江关于自作的引用曾明言“将过去不同时间点作品的文体和形象,与现行的作品进行比较,就会产生差异。”[7]245无论是引用自作还是他作,都会制造出多样化的文体,而且,正如菅野昭正评价的那样,“沉淀于古今中外以及历史之中的庞大作品群的共识的交错存在,在作家的意识与视线中活动的不仅是引用的方法,而是要扩展到作品人物精神生活的领域。”[8]所以,可以说大江的这个“重复中存在差异”的文学理念,不仅使得小说的文体富于多样化,更是小说人物精神层面的关照。纵观大江的文学创作,这种非常明显的引用或称之为重复,可以说最初就是出现在《需要献祭之男吗》这个短篇中,在这里,大江主动吸收了鲁迅的表现手法,并在人物精神层面的塑造与形式上也无限接近鲁迅,而且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对《狂人日记》进行了褒扬与引用,这正是80年代以后大江在小说中常用的方式。可以说大江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开辟了引用手法或者称为互文的先河。
《狂人日记》是鲁迅由“超人”上升为民众的“回心”之作,中国学界也一直将其看作“启蒙主义的第一声”。大江健三郎小说《需要献祭之男吗》,从开始就是已经觉醒的“善”回归社会后的救赎行动,整部作品都是“善”如何去除“恶”以及如何拯救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小说是否可以看成是“狂人”回归后的实践?尽管这个社会参与实践带有“超人”性质,并以失败告终。
从大江健三郎整个创作生涯来看,这篇小说写了人吃人的社会,是带有异质的尝试,但是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我”=作者(尽管“我”=作者会让小说的理解变得复杂,但不可否认“我”确实可以认为与作者有关)虽然是看客的位置,但不能不说“我”受到了“善”的狂人般行动的触动,认识到了“恶”的存在。在这之后的作品,“我”无法摆脱各种阴暗的东西,也无力改变现状,这样的“我”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如《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请告诉我们在疯狂中生存下去之路》中,“我”逐渐陷入到抑郁的、疯狂的状态中,而这其中的原因,是否可以认为与这部作品有重要关系?即由“善”发现“恶”,进而被看成疯人的行动。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将这部小说看成是大江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承接性作品。
从吃人社会的设置到“超人”的拯救行动,再到“回心”脚步的追随,到处可以看到《狂人日记》的影子。不得不说,鲁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1] 王新新.大江健三郎心中的鲁迅[N].文艺报,2001-10-13(001).
[2] 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早期文学世界一从战后启蒙到文化批评[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2.
[3]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灭论[M].李冬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4] [日]大江健三郎.生け贅男は必要か[M].東京:新潮社,1977.
[5]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6] 赵文书.重复与修正:性别、种族、阶级主题在《看不见的人》和《最蓝的眼睛》中的变奏[J].当代外国文学,2015(3).
[7] [日]榎本正樹.大江健三郎の八十年代[M].東京:彩流社,1995.
[8] [日]菅野昭正.根拠地思想 — 大江健三郎『懐かしい年への手紙』[J].群像,198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