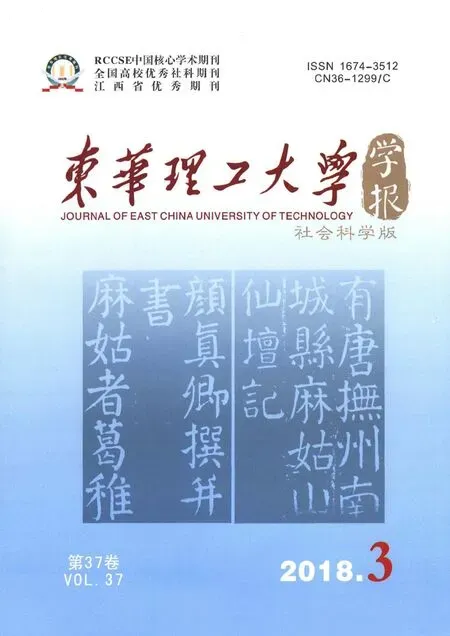陶渊明的佛学思辨与儒道内核
陈 方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新世纪以来,不少学者从文本结构分析、地域文化影响、语言词汇渊源、思想文化过滤等角度与层次,对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深度的研究。以下,对陶渊明作品中的佛教因素作一整理,探析其中蕴含的原因与特点,对陶渊明与佛教思想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1 陶渊明与佛教的渊源
在论述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时,许多学者会追溯其曾祖陶侃得文殊像之典[1]。另有侃之子陶范交好庐山僧人慧永的记录,其从父太常夔与佛教亦有因缘[2]。但即便家族先辈与佛教结缘甚深,也不能作为陶渊明与佛教有关的直接证据。
就目前现存陶渊明诗文,可知与其相关的信佛友人有刘遗民、周续之、张野、颜延之,或者还有慧远法师。陶渊明与刘遗民、周续之之交往,可见于《酬刘柴桑》《和刘柴桑》《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三诗。张野与陶渊明关系非同一般,现存陶集中有《岁暮和张常侍》一诗,二人不仅有诗文往来,还是姻亲关系[3]。颜延之亦是虔诚佛教信徒,不仅与当时名僧慧静、慧亮等人均有往来,并有多篇佛学论著存世。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自尔介居,及我多睱”[4],可见二人交往颇密。从现存陶集与史料来看,他对崇佛之人并无排斥。陶渊明与崇佛人士多有接触,对佛教义理就不会陌生;对崇佛之人不排斥,就有接受佛教义理的可能。
但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文人思想中的儒佛道内涵并不能截然分清,时常呈现出交融杂糅的情况。陶渊明是模糊了儒释道区别,还是“取熔经意,自铸伟辞”,当作具体分析。
2 陶渊明诗文中的佛理哲思
2.1 佛教语汇的引用与演绎
渊明对佛教概念的演绎自有特色,或是运用佛教词汇表情达意,或是运用佛道相通之理阐述思想。就其中所表达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2.1.1 人生无常,盛年难再
哀叹人生苦短,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当生命渐近暮年,大多数人都会有青春不再的感慨,陶渊明也不例外。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这些“人无再少年”之慨有了更多消极的意味。如《杂诗》其一: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前四句论述,人生而无根,飘流转徙如陌上之尘,随风流转,无恒久不变之身。其中所表达的漂泊无依、人生无常之感细缕入微;在盛年难再的哀叹后,诗人勉励自己当及时行乐。此意在陶诗中多有体现,如: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
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
……
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杂诗》其三)
这些诗文中的思想,除受中国传统惜生观念影响外,与佛教“诸行无常”“诸受皆苦”思想的流布不无关系。《大般涅槃经》云:“一切有为法,皆悉归无常。”[5]又如在当时对士大夫影响较大的《维摩诘经》:“是身如幻,转受报应;是身如梦,其现恍惚;是身如影,行照而现”[6],这些概念、思想随着佛教的传入,作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内容,早已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2.1.2 世事空幻、虚妄不实
陶诗中直接引用的佛教概念,大多是佛教的基本词汇与主张,如“幻”“梦”“空”“无”等词。如: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还旧居》)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八)
这些词语常见于大乘般若经典。如西晋罗无叉译《放光般若经》:“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于大众中所念具足,于无数劫堪任教化,所说如幻、如梦、如响、如光、如影、如化、如水中泡、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水中月,常以此法用悟一切。”[7]
2.1.3 无住无我,无心随化
世事无常,诸受皆苦,凡事不可执著,于是有无住、无我、无心之论。佛经中多有阐说,如:《增一阿含经》:“色者无常,无常者即是苦,苦者是无我,无我者即是空,空者非有、非不有,亦复无我。”[8]陶渊明不仅对“苦”有较充分的论述[9],并有不少作品表达了与此意相通之思想,如:
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杂诗》其五)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
“壑舟”一词当是出自《庄子·大宗师》:“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10]喻大化默然潜运,非人力可改变,后喻自然万物变化莫测,这与佛经中所论“现在不住”相通。对于陶诗中所用“壑舟”之意,何剑平有详细论述,并得出结论:“佛经‘现在不住’的时间观念也是陶诗‘引我不得住’一语遣词的来源。”[11]不论陶诗之“不住”是否来源于佛经,但佛道思想在此处的相通之处显而易见。
2.2 与佛教哲学思想的矛盾之处
在渊明直接引用的佛教概念中,可见其两种态度。一是肯定,一是否定。前者如上文所论,肯定了人世空幻等佛教思想。但并非所有引用了佛教概念的诗文均是对佛教思想的认可,以下例举陶潜作品中与佛教哲学思想相牾之处。
2.2.1 形尽神散
《形影神》组诗历来是学者研究陶渊明形神观的重点篇目。《神释》之中委运任化的观点,明显是作家倾向的更高级的人生境界。诗中对“神”的推崇,使不少研究者将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同佛学观念结合起来,并认为此组诗是针对慧远法师的形神观而作。但仔细比对二人的观点,便可发现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慧远法师于《形尽神不灭》[12]中提出“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魂神如火,神传于不同形体正如火传于不同薪木,神并不因形之灭而聚散。在陶作之中,有不少形尽神散之论,最典型的如: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知?枯形寄空木。
……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拟挽歌辞三首》其一)
其它几首亦有此思想。可见渊明并不否认甚至是希望魂神的存在,但他所谓的“神”,是依附肉体存在,形体销亡则魂神无依,此正是陶渊明的形神观与佛教思想的不同之处。有不少学者认为《形影神》中有浓郁的道教因子,如钱志熙认为“《形影神》诗也涉及魏晋时流行的神仙家思想”[13],李小荣则提出形、影、神三分且以“神”统合的思想在道教古灵宝经中早已出现[14]。因此,仅凭陶渊明诗文中出现形神概念便断定其受佛教思想影响并不客观。
2.2.2 质疑报应
东晋时期,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已十分普遍,陶诗《乞食》中亦有“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二句,但不少学者认为此“冥报”与佛教并无关系。如逯钦立注此诗时,认为此是“死后报恩于幽冥”,并引丁福保注“如韩厥之梦杜回之踬是也”,表明此“冥报”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之报恩[15]。《左传》中,实已有结草衔环之典,并不能确定陶诗中之“冥报”是佛教之意。且《饮酒》其三中又云:“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这是明显对所谓善恶有报观点的质疑。即便是直接使用佛教术语的诗作,也有评论认为此与佛教并不关系,如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句,真可谓知天地之化育者,与远公白莲社人见识相去何啻霄壤!”[16]
2.2.3 追求欢乐
世事的烦恼与痛苦并没有让陶渊明厌弃尘世、遁入空门,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向自己心中的理想生活迈进。如: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并序)
饮酒是渊明所爱,或浇心中块垒,或是田园简朴生活的乐事。他的及时行乐,并非荒诞纵欲,而是在有限的人生期限之中,在修养道德的前提之下,去过自己想要的自由生活。他对归隐后的田园隐居热切深爱,即便饥馁穷困也甘之如饴。这便与佛教所谓四大皆空、应无所住有本质区别。另,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因避秦乱而聚居的绝境,其中民风纯朴,幽蔽闲逸。可见他向往的人间圣地并非虚无飘渺的宗教净土,而是虽虚构却在现世的世外桃源,在桃花源中是世俗安乐平稳的生活,并无超自然的存在。
3 佛理外衣下的精神实质
从上述陶潜具有佛教思想的作品中可看出,诗中的思想虽与佛家理念颇为相似,但除对人生无常、物我为一的认同外,诗人还在思考在自然万化之中,人与宇宙的相处方式。他的内在心理可分为两个层次。
3.1 顺其自然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
一方面是对自我本性的顺应。陶渊明早年官场的经历让他备感受束与不适,时常向往隐居田园。“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于是,诗人于义熙元年(405)辞官彭泽令,欣然归林泽,其中之欢跃之情时露笔端,这一切,均来自于他对本性的顺应。田园的生活也并非一切尽如人意,农业生产的辛苦且不说,穑稼无获、困顿难存却真正是渊明无能为力的境地。陶渊明晚年所作《乞食》,表现其晚年穷困饥馁,至于乞讨,但“明夷利坚贞”,诗人没有对当初远离官场的选择感到懊悔,而是在困顿之中举觞倾杯、言咏赋诗。此种随遇而安即是对己之亲近自然之心的体认与顺应。另一方面,陶渊明又以哲学家的思维思考自然宇宙中的真谛。在陶潜的诗文中,极为显著的现象之一,即是对“化迁”思想的展现。如: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所谓“化迁”,指顺应自然而变化。其思想实质当来源于老庄。从上举诗例来看,陶诗中所述顺应自然者,除己身之形体外(虽然他也哀叹是身无常,老之将至),还包括精神情感。此种身心自然而然地随天地万物而化,“任真”而存,是以道家思想来应对佛教的“无常”观念。顺任造化,摆脱物役,由此造成的结果即是与自然融合为一。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嘉,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作为浔阳三隐之一,陶渊明与那些假隐欲仕之士不同,虽未隐深林,却心净无碍。山林、日月、飞鸟与自我,均是宇宙自然中的一物,物我为一,不作分别观。这是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相通之处,亦是陶潜于庐山脚下静谧的田园生活中,体悟出的万物之道。
3.2 追求自由的最大化
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渊明选择自由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安贫乐道、体道亲仁,追求道德的升华,如: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前一首化用《论语·里仁第四》中“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后一首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之典。在陶诗文中,记录其勤勉儒学的例子不少,《咏贫士》《读史述九章》等篇章皆可见陶潜思想中深扎的儒家思想。但陶潜追求自由的方式,更多的是归去田园,纵迹林野,不负光阴,饮酒享乐。在诗文中,有两类意象能明确体现出陶渊明的这一思想,一是酒,二是云鸟。
据逯钦立统计,“凡说到酒的共五十六篇,约占全部作品的百分四十四”。[15]在阐述作家日常生活时,文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性之所爱,是消烦解忧之良药,更是纵志享乐的抒情方式。除酒之外,云鸟二意象在陶作中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云与鸟,在陶作中所代表的情感类型与意义有多种,有孤独无依的落寞,有纵志凌云的旷达,有对世事变幻的感叹,更有闲适自由的情怀,如:
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与殷晋安别》并序)
山气日夕嘉,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
游云与飞鸟常给人孤独无依、无迹可追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无拘无束、不为尘累也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对田园自由的追寻,又包含着对功名与肉体的淡然,如《和刘柴桑》中所咏“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顺应自然、离形去智、物我为一是老庄思想的核心。《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7]认为自然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庄子·大宗师》则提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10]这是消除贪欲与伪诈的方法,去除对肉体与物质的执著,才能在心灵上与自然同通。陶作中对老庄典故的引用不在少数,此不赘述。诗人对田园生活的渴望、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最终达到与自然合而为一之境。由此可看出,陶渊明在运用佛教概念与思想的背后,却是对儒道精神的阐扬。
3.3 外释而内道儒
就陶渊明思想中的儒道二家而论,陈寅恪曾提出著名的“新自然说”:“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18]陈寅恪先生所论“外儒”实有其理,所谓“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当更多指渊明出仕之时,以及其对儒家道德思想的认同。另一方面,“内道”之说则应明辨。在“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的表象下,陶渊明的诗文既有对老庄思想的认可,又有对佛教思想的运用,实是委运任化与空幻虚无思想的结合。
魏晋时期,是玄学大盛之时,佛教思想尚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其传播尚需依附玄学展开,故有“玄学化佛学”之说。佛玄二家在出世遁隐、体道大化、空无思想等方面颇有相通之处,因此,在佛教传播的大背景下,心中深扎儒道思想的陶渊明在作品中偶用佛教词汇与流露佛家思想也可理解。但陶渊明诗文中所论佛教概念,很难说是对佛教思想的全盘接受。从上文可知,佛学思想的展现是在陶渊明人生的中晚期才出现,而儒道的内核却贯穿了他的一生。可以说,陶渊明作品中的佛教思想,当是“外释而内道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