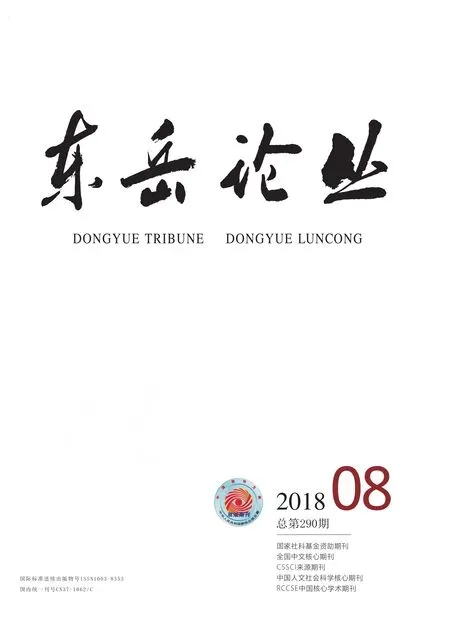当人文研究遭遇“听觉”课题:开拓中的学术话语
王 敦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本文尝试为听觉文化研究话语的发展动态绘制一幅地形图,旨在发现、勾勒和阐述该领域前沿的问题意识、学术增长点和概念端口,并对该领域在国内的进一步话语开拓与建构发表意见。但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还要对听觉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发展做一番回顾、界定和审视。
对听觉(声音)文化的思考逐渐成为人文学界的新课题。要想搞清楚新课题为何“新”,莫如先思考它在先前何以被忽略。设想如果有人要取消电脑里的声卡,那么不管“读图时代”的说法如何深入人心,你我也不会答应。这样细想一下会发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类似于“声卡”的文化装置无处不在。从地铁站、机场等公共场所的声音提示到服务于私人听觉的耳机和手机app,各自所发挥的文化功能都值得考察。广场舞不仅是被看到的,也是被听到的。看不见的声卡为何重要?又如何被意识所遮蔽?这些不为眼睛所见的声音(听觉)感知、装置、文化机理,虽然从来都不是人文研究学者所刻意要回避的,但却在现代知识建构体系中,在视觉性知识框架占据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在事实上处于人文科学术主脉络之外的边缘地带,被封存在音乐学研究、建筑声学、电磁声学、录音学等孤立的专门领域中,或者成为学者阐述其他问题所启用的转喻、借喻性修辞。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听觉(声音)现象的思考,事实上自有史以来不绝如缕。在中西方的思想谱系里,从毕达哥拉斯的“比例”、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我国的《乐记》《乐论》到《毛诗大序》,都能发现有关听觉感受的丰富话语和深层脉络。当全球各地次第经历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时候,听觉性问题成为一些重要学者思考议程里面的成分。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不仅论及视觉性问题,也对于声音复制的文化工业产品如唱片、留声机十分关注。阿多诺在分析现代文化工业时往往从音乐入手,其《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觉的退化》一文就是范例*“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 in 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al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NY:Routledge,2001.。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皮埃尔·舍费尔(Pierre Schaeffer)在以实验性电子音乐为特征的“具体音乐”(musique concrète)方面的成就与表述,为日后的听觉(声音)话语发展开辟了道路*Pierre Schaeffer,Traité des Objets Musicaux,ina-GRM,1966.。在传媒学领域,加拿大的麦克卢汉则在六十年代提出了“听觉空间”概念*参见Marshall McLuhan and Edmund Carpenter,“Acoustic Space”, in 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An Anthology,ed.Edmund Carpenter and Marshall McLuhan,Boston:Beacon,1960.该概念反复出现于麦克卢汉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各种著述和访谈中(参见埃里克·麦克卢汉等编《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在七、八十年代,加拿大的雷蒙德·默里·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做出了“声音景观”“声学生态”阐述*Raymond Murray Schafer,The Turning of the World:Toward a Theory of Soundscape Desig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0.。同时期在法国则有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关于视听差异、听觉机制的研究*[法]米歇尔·希翁:《视听:幻觉的构建》,黄英侠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声音》,张艾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提出的“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参见[法]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思路,在美国有唐·伊德(Don Ihde)对于声音现象学的开拓*Don Ihde,Listening and Voice:a Phenomenology of Sound,Ohio University Press,1979.和沃尔特·翁(Walter Ong)(《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对于声音的文化功能的论述*[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限于篇幅,仅举出比较重要的几个例子。所有这些都为二十一世纪初西方学界听觉文化研究的兴起做了准备。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听觉(声音)性文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正式浮出水面。以英文学界为例,这类研究被冠以“Sound Studies”“the Study of Sound Culture”“Sonic Culture”“Auditory Culture”“Aural Culture”等名字,其中“Sound Studies”居于主导地位。在欧美一些大学里也出现了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机构。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等一些国家的相关学者已经初步集合为专门的学术共同体*在笔者正在选编的《听觉文化读本(译文卷)》(厦门大学出版社将出版)里,收录了此类研究的多样化具体形态。。在国内,除了笔者从2011年起开始发表话语建构性的研究论文之外,有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涉足听觉性议题,渐成星火燎原之势。在“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历史”这几个一级学科可选择举例如下:傅修延从2013年起开始撰文探讨“听觉叙事研究”;耿幼壮研究西方哲学里面与视觉性“凝视”相对应的听觉性“倾听”的话语;在符号学领域,陆正兰展开“音乐符号学”研究;周志强在文化批评领域对当代大众音乐进行“声音的政治”分析;徐敏将文化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探索百年来流行音乐和大众音乐的嬗变;上海社科院的葛涛研究二十世纪初上海留声机文化与现代化转型;浙江大学青年学者王婧对新兴的“声音艺术”(Sound Art)理论和本土化实践予以了系统介绍。以上仅仅是几个例子,遑论音乐学领域里面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等方向的突破了。
如何在中文学术语境里命名和界定这一听觉(声音)研究领域?笔者认为不妨比照“视觉文化研究”把它叫做“听觉文化研究”。这是具备多重叠加含义的“听觉文化研究”,一是指与“视觉文化研究”相对应的一片跨学科领域,二是指能与国外学界新兴的“Sound Studies”相对应的研究,三是指比狭义的文化研究既有套路更多元的,在人文诸学科里面具备听觉性议题的研究。这一“听觉文化研究”亦可进一步细判为“听觉文化的研究”和“听觉的文化研究”两端。前者“听觉文化的研究”以“听觉文化”的内部机制作为内核。后者“听觉的文化研究”以“文化研究”为主词,更像是具备文化社会学式介入使命的“文化研究”家族的成员。以成果和泡沫都已经蔚为大观的视觉文化研究为鉴来开展“将来时”的听觉文化研究话语建构,这个“时差”本身就具备范式反思和创新的意义,从而带出一系列具备特殊性的话语节点来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人文研究范围内的共相问题对接。
下面进入正题,勾勒和阐述笔者所认为的该领域一些前沿问题面向和话语增长点,并对该领域话语开拓与建构的进一步发展发表意见。
一、跨学科知识坐标和知识网格的搭建
“听觉文化研究”作为宣称以跨学科为基本存在方式的“文化研究”家族新成员,跨学科是其基本存在方式。它考察散布于各学科关注之下,比音乐艺术的范围更加广阔的听觉(声音)文化课题,其相关知识和求索方法分布在错综复杂的知识脉络和思想史之中。从国内听觉文化研究起步标志之一的“听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2017.11.11-12)70多篇论文分组设置就可见一斑。其中“中外听觉文化理论及其延展”分会场里面分为“听觉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听觉或声音史研究”“关键词研究——‘声音’、‘听觉’、‘噪音’、‘寂静’”“中外听觉文化理论与相关作品研究”等组。“媒介与听觉文化研究”分会场分为“技术与听觉文化研究”“音乐理论与音乐作品研究”“听觉研究与文化产业”等组。“文艺作品与文化现象中的声音研究”分会场分为“听觉研究与现代社会”“声音美学与声音政治”“电影中的声音研究”数组*会议由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上海美学学会、天津美学学会主办,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声音艺术工作委员会、中国录音师协会电影录制专业委员会协办。。 当来自各学科的学者们聚到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听觉性议题时,其思维方式和所受的学术训练之不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事实上,“听觉文化研究”出现得如此之晚近,也说明构建相应的公共知识坐标并不容易。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这也许意味着,当话语建构能力较强的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界(也包括文学研究领域之内的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美学等分支领域)在介入到听觉文化研究话语构建任务中的时候,不宜过度在自身资源里面进行改头换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话语能力强大未必意味着话语资源也丰饶。所以要特别注意真正“跨”出去。这意味着除了要吸收邻近学科如传媒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符号学、叙事学、哲学、思想史、技术史、文化史、影视学、民俗学、图像学、神学、宗教学等等的资源之外,还要了解、尊重、消化、吸收音乐学诸学科(特别是民族音乐学、音乐史、乐器学、音乐人类学等)和声学诸学科(电磁声学、环境声学、建筑声学)、录音学、播音学,以及“声音艺术”“具体音乐”与多媒体教学研发等实践门类的基本知识前提和规范。
这也牵涉到对关键词的概念梳理和辨析。关键词如同知识网格上的话语节点,是搭建公共议题的关键。这里面既有偏重于形而上思辨的如“倾听”,也有牵涉物质文化和媒体、科技、身体诸问题的如“耳朵”“回声”“广播”“噪音”,也有与文艺表征、跨艺术理论共相问题接壤的如“形象”“符号”“再现”“音乐”“空间”“符码”“灵韵”,也有极具听觉(声音)文化研究特殊内涵、兼备形而上和形而下广阔纵深的“寂静”“声音”“听觉”,还有极具延展性,既通达视觉性类比又通达现代性转型问题的核心概念“声音景观”。在每个关键词的后面,都牵涉到复杂错综的知识脉络和思想史。词与词处于互动的相对关系之中。比如,“声音”和“听觉”是不是可以互换的概念?与声音概念对应的,是“噪音”还是“寂静”?声音的本体,与语言修辞的“声音”“口吻”“声口”的关系如何?国外学界近年也出版了这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提供参考。如《声音关键词》一书*David Novak and Matt Sakakeeny eds.,Keywords in Sound,Duke University Press,2015.,里面列举听觉文化研究者们所撰写的包括“语言”“身体”“回声”“音乐”“无线电”等在内的二十个关键词词条,折射了在西方学术语境之下的相关建构动态。被关键词所编织的知识网格处于开放的动态关系之中,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界定,并随时邀请不同语境之下的更多分析阐释来激活并更新对知识框架整体和局部的理解与应用。
二、对哲学和思想史里面听觉性知识源流的发掘与再叙事
身体、形象、语言、符号表意、修辞、时间、空间等,如何在声音、听觉里得到展现?听觉认知和文化表意具备怎样的先验结构或特质?与精神分析以及现象学等等现代主要的人文科学思考路径,有怎样关系?不管我们对哲学认识论和思想史之中的听觉性话语脉络是否了解,前人对听觉和声音的认知和思考都已经嵌入在认识论、思想史和认知科学发展的肌理内。我们今天思考听觉问题,也是对认识论和思想史脉络本身被视觉性垄断所遮蔽的一些部分的再认识。
“启蒙”一词在英文里面是“enlightenment”,其字面意义大致是“被光照亮”。它在欧洲各主要语言里基本都是如此。“启蒙”这一命名,可以被解读为对《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四节经文“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所做的隐喻,即现代知识理性之光洞穿愚昧的黑暗,带来观看万事万物的明晰。这一隐喻在语词和想象层面显然是建立在视觉性基础上的,无形中喻示了视觉性知识在现代知识路径的中心地位。毋庸置疑,启蒙运动以降的人文学术以及日常语言的确充满了以光、视线来隐喻真理和启悟的修辞。但是即便如此,依然不能以为这样就能够将现代性的问题描绘得全面,也并不意味着听觉性知识脉络应该缺席。
美国听觉文化研究学者乔纳森·斯泰恩(Jonathan Sterne)发现听觉性知识在启蒙事业和现代化知识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他甚至自铸新词“声音启蒙”(Ensoniment)与“enlightenment”对应,以命名听觉性知识源流的存在。斯泰恩发现听觉现象和感知被近代逐渐萌发的一系列学科所注意,成为生理、物理、精神性探索的对象。与视觉技术发展(光学透镜、仪器、摄影术)平行,人们借助不断增进的听觉性知识和聆听技术,加深对声音、听觉的理解和驾驭。例如十九世纪的医生从聆听病人的自述转向对病人身体的倾听,使得听诊器与视觉性的显微镜等一起成为医疗职业的象征。在福柯的知识谱系学意义上,此间所发展出来的一些听觉知识和技术范式在后来的电话、留声机和收音机技术中得到间接的传承*Jonathan Sterne,The Audible Past: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
如上所述,乔纳森·斯特恩将听觉性问题意识放置到学术史和思想史中,从而在学界所熟知的视觉性认知范式之外发掘出西方知识传统中所平行的另一套听觉性知识脉络和资源。他的一段话值得引用:
如果对声音史、声音文化或声音研究的成分缺少某种整体性的、共享的感知力,要想从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演讲、音乐、技术和其他声音实践的故事中拼凑出一部声音的历史,简直无异于在拼凑一块破碎的玻璃。我们只知道这些碎片会以某种方式排列,我们知道它们可以彼此拼接,但我们不确定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将它们彼此整合。我们已经获得了关于音乐会听众、电话、演讲、有声电影、声音景观以及听觉理论的历史。但只有仅少数的声音史的写作者能够说出他们的工作是如何与其他研究成果或更大的知识领域建立关联的。因为围绕声音的学术研究从未持续地针对更具基础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文化和历史问题展开工作,这使得声音研究无法引入更广阔的哲学问题来勾连它所身处的不同知识领域。于是,挑战就在于如何将声音想象为一个超越近便的经验性语境的问题。声音的历史已经与更大的人类科学的问题建立了关联,而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将这些关联具体化。*Ibid,5.
这是一件非常复杂但却能将听觉文化研究推向人文科学深水区的工作,能够使听觉(声音)局部性知识获得总体性拼图,且这样的拼图不应仅是斯泰恩的个人版本,甚至也不是以欧洲思想脉络为唯一脉络的版本。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同样会有自身的听觉知识源流以及在现代化转型时期发生在西方范式以外的碰撞与融合,这些都能够在听觉性资源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研究中带来广阔的发现、整合。
三、听觉文化史对现代化转型研究、媒介文化史、物质文化史的利用
对留声机、电话、麦克风、录音机、KTV、广场舞等不同的声学技术和日常文化活动予以考察,能否帮助回答人文社会科学有关现代和后现代转型、社区分化等大问题?这是对媒介文化史、物质文化史等学科的发问。在视觉现代性之外同样存在着“听觉现代性”,赋予现代人与以往所不同的现代、后现代审美和文化感受。媒介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如果忽略了对声音的录制、传输、扩放,和听觉现代性形态对文化艺术的塑造等问题,也就不是完整的媒介文化史、物质文化史研究。听觉文化史则需要对现代化转型研究、媒介文化史、物质文化史研究里面所出现的听觉性考察加以凸显和利用。
美国的听觉文化史学者理查德·库仑·拉斯(Richard Cullen Rath)在其尚未出版的新作手稿《对历史的倾听/关于倾听的历史》(Hearing History/History of Hearing)中提出了“对历史的倾听”和“关于倾听的历史”这样一对概念*在去年召开的“听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2017.11.11-12)上,拉斯教授也到会并做了同题报告。。“对历史的倾听”的重心放在历史学学科本体,是为历史学学科增添“倾听”历史的新范式。相比之下,“关于倾听的历史”,则在于研究关于“倾听”的感官专门史。这两个路径都要求研究者激活自身的听觉性问题意识并运用到历史想象、叙事中去,而且在研究实践中也难于截然分开。拉斯自己也说,这两个路径在并肩而行的时候效果最好。
关于国外的听觉文化史专著成果,笔者在之前的一些论文里面介绍过一些。比如文化史家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揭示了听觉生活变迁之下的社会变迁。布鲁斯·R·史密斯(Bruce R.Smith)《近代英格兰的声学世界》还原英格兰早期现代社会的声音景观和口传文化向文字文化的转型。马克·M·史密斯(Mark M.Smith)的《倾听十九世纪美国》对历史上美国南方社会的日常声响文化状况进行了还原。拉斯的《美洲多早开始发出声响》发现了清教意识形态对北美殖民地听觉的支配作用。约翰·M·匹克(John M.Picker)《维多利亚时代声音景观》则通过对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文学描写来发掘该时期对于声音景观的文学表征。卡林·比吉斯特威德(Karin Bijsterveld)《机械之音:二十世纪的技术、文化和噪音的公共问题》研究了都市噪音的历史。艾米莉·汤普森(Emily Thompson)《现代性的声音风景:美国1900-1933年的建筑声学及听觉文化》描述“现代声音”技术产品是如何由现代社会意识所决定的。乔纳森·斯特恩在《可听见的过去:声音复制的文化源头》将听觉技术史整合到现代的认识论和思想史里面*参见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王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Bruce R.Smith,The Acoustic World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Mark M.Smith,Listening to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Richard Cullen Rath,How Early America Sounded,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John M.Picker,Victorian Soundscapes,Oxford Univ Press,2003.Karin Bijsterveld,Mechanical Sound:Technology,Culture,and Public Problems of No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IT Press,2008.Emily Ann Thompson,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MIT Press,2002.Jonathan Sterne,The Audible Past: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
还有一些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海外学者如安德鲁·琼斯(Andrew F.Jones)、唐小兵、黄心村、陈小眉等,用听觉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百年来音乐、都市文化的发展进行研究,包括我国二三十年代上海留声机文化,延安左翼文化,建国之后的舞台表演,以及大陆、台湾当代流行文化。国内也出现了葛涛、徐敏等从物质文化史、媒介文化史方面来展开的多元研究。
四、与音乐学诸学科话语的关系
音乐学与听觉文化研究的关系,与美术学和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有些类似但又不同,因为听觉文化研究较视觉文化研究更为年轻,话语资源也更为零散。音乐学在听觉文化研究乃至于文化研究出现之前一百年就已经建立。把历史悠久的音乐学诸学科与新兴的听觉文化研究放在一句话里面并置,巨大的张力立刻呈现。如果音乐学认为听觉文化研究业余和多余,听觉文化研究觉得音乐学远离人文研究话语主流,固步自封,则都是可以理解的“歧见”。笔者的任务不是解决分歧,只是指明情况,引发思考。从过去通过音乐学传统诸学科讨论音乐艺术形态,到后来发展生成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来讨论更宽广的问题,再到现在经由听觉文化研究来探讨声音、听觉,有没有可能在话语和知识网格方面做到兼容和沟通?音乐做为人类最重要的听觉艺术形式,理所当然是听觉文化研究需要正视的内容,所以需要对音乐学予以足够的尊重。但听觉文化研究也认为,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听觉科技因素对人类的声音感知、听觉艺术形式变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因素虽然外在于对音乐形态的研究本身,但却是音乐形态变迁的必要条件。
已故的民族音乐学大师黄翔鹏在探讨中国古人的音律辨识问题时说道,“我们对于人类听觉能力的认识,至今仍然知之甚少;如在艺术与科学的接壤之处,前来研究音乐听觉问题,恐怕就更将暴露出其间有关知识的贫弱了。”*黄翔鹏:《“悟性”与人类对音调的辨识能力——炎黄文化中几则有关辨音事例的提问》,见于《黄翔鹏文存(上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41页。他这里所提出的“听觉能力”问题,是处在音乐学科体系的边缘,却居于听觉文化所研究的中心。听觉感知能力是人能够对音乐形态进行体验和分析的经验类基础,而恰恰对听觉感知和能力问题,音乐学做不出正面解答。“听觉能力”,正如同黄翔鹏所说,“处在艺术和科学的接壤之处”。这里的“艺术”一词,其特定含义比音乐艺术自身要宽广,包含了塑造审美感官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这里的“科学”一词,指的是在具体科学技术条件下人们对感官的认识程度和对感官的人为延伸。而这个“接壤之处”,是个随着具体的社会状况而变迁的历史与当下语境变量。从我国国内来看,音乐学各学科和听觉文化研究诸领域相互关注、借鉴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但如何能够获得更有效的交集,还需要在今后的动态发展中来思考。
五、听觉文化研究的“视听二元对立”框架陷阱问题
笔者认为“视听二元对立”是听觉性人文研究发展初期一些学者开始专注于此领域时经常会掉入的思维陷阱。由于东西方各国的学术语境和进入此领域的时机、路径各不相同,所以具体呈现出来的症候也千差万别。涉足此领域的一些先驱人物如雷蒙德·默里·谢弗、麦克卢汉、沃尔特·翁,都曾陷于此。当我们初步意识到听觉问题的重要性,思考它为什么被忽略,并且苦于没有思维参照系来界定听觉性特质的时候,如果将听觉与视觉的各个方面逐一对比关照,往往会获得“豁然开朗”的感觉,并且不自觉地将潜意识里面的二元对立文化观一一激活,赋予听觉以拯救视觉性文化弊端甚至文化救赎的价值。如果进入到我国的学术语境,则还可能会把视听两者的对立叠加到将中国与西方文化审美、古典与现代文化审美、中国与西方叙事等等对立的一系列二元对立里面。
笔者发现从2003到2008年,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路文彬比较早地在国内提出听觉性议题,发表论文《凝视与倾听——试论中国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视听审美范式问题》(《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视觉生活与听觉生活》(《创作评谭》2005年第2期)《论中国文化的听觉审美特质》(《中国文化研究》2006 年秋之卷)及专著《视觉时代的听觉细语:20世纪中国文学伦理问题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路文彬力图界定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某种听觉“特质”,并借此来诊断他所认为的当代中国文学文化某些症候性缺失。在一系列类似于转喻修辞的概念跳跃中,将听觉附着在老庄哲学、感性、东方文艺形态等作者所认同的价值层面,对立于视觉、古希腊形而上学哲学、理性、西方文艺样式等该作者所不认同的取向。该作者判断“听觉是一种将我们领入和谐关系的能力,……而视觉则是一种容易破坏我们同对象间关系的能力”*路文彬:《视觉生活与听觉生活》,《创作评谭》,2005年第2期。。“视觉偏重于理性,听觉偏重于感性。古希腊哲学所确立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以视觉为本位,而中国老庄哲学则以截然相反的听觉为本位。两种传统,促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艺样式。”作者还延展出通达当下叙事线条:“但五四运动的兴起,对西方范式的挪用,消除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听觉范式的品格,引向了视觉中心的道路”,以至于“通达当代”之后愈演愈烈,转向“欲望的无节制膨胀”,铸成了“读图时代”对艺术本真的剥夺。在所指衍异的滑动斜坡上,该作者展开了相当宏大的视听二元对立叙事,将中国古典文化与听觉文化划等号,认为“听觉认知范式熏陶出独特中国文化气质”“听觉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确有给予语音以特权的诸种可能”“汉语文化于初始之时表现出的听觉迷恋,在本质上属于对生命根基的坚守,是始终为归属感所牵挂的心灵回眸。”*路文彬:《论中国文化的听觉审美特质》,《中国文化研究》,2006 年秋之卷。这样近乎抒情的话语是建立在不完善的归纳和演绎思维之上的,让人不禁想问:中国独特的视觉表意感强烈的文字系统,难道不属于“独特中国文化气质”?
从国外听觉文化研究发展几十年历史来看,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在听觉性文化议题开始讨论的初期比较流行,并在学科领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后逐渐消失。为了说明此,乔纳森·斯泰恩提供了一份曾经被沃尔特·翁、麦克卢汉等广为关注的,用简短语词形式所固定下来的视听二元对立性描述。斯泰恩称其为“视听连祷文”(audiovisual litany),发现其与天主教圣礼仪式中的连祷文吟诵有异曲同工之妙:
——听觉是球状环绕的,视觉则是方向性的;
——听觉将主体浸泡,视觉则提供视点;
——声音是向着我们而来的,但视觉则是向着它的对象而去的;
——听觉关注内部,视觉关注表层;
——听觉包含着与外界的物理接触,视觉则要求与之保持距离;
——听觉将我们置于事件之中,视觉则提供关于事件的视点;
——听觉趋向主观性,视觉趋向客观性;
——听觉带我们进入生命世界,视觉则将我们引向衰败和死亡;
——听觉与情感相关,视觉与理智相关;
——听觉主要是一种时间感官,视觉则主要是一种空间感官;
——听觉是一种令我们沉浸在这个世界中的感官,视觉则是这一种将我们与世界分离的感官。*The Audible Past: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p.15.斯特恩指出,这个列表在沃尔特·翁的The Presence of the Word: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1)中有清晰的阐释。另外可参考Ong,Orality and Literacy,pp.30-72;Attali,Noise;Lowe,History of Bourgeois Perception;Marshall McLuhan and Edmund Carpenter,“Acoustic Space”,in 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An Anthology,ed.Edmund Carpenter and Marshall McLuhan(Boston:Beacon,1960).
这份“视听连祷文”从试图进行听觉、视觉属性的客观描述始,以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终。对于斯特恩来说,它“并没有提供一个进入感官史的入口”,恰恰相反,“它将历史假定为发生在两种感官之间的存在。随着主导文化的感官从一种转向另外一种,历史也随之改变。视听连祷文将感官史变为了一场零和游戏,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感官必然会压抑另一种感官*Sterne,The Audible Past: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p.16.。
六、其他的重要前沿问题
因篇幅和研究所限,笔者难以对听觉文化研究话语建构问题全面铺陈,下面仅对另外几个重要问题做简要慨述。
(一)听觉(声音)符号的表意以及跨符号跨媒介意义指涉问题
对听觉(声音)符号性表意机制的探索,本身就是挑战符号学既有范式和有效性的难题。从结构主义符号学高潮时期以降,音乐符号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折射出符号学各流派与音乐学的互动。在音乐符号学之外,音乐或听觉的符号性问题也被西方比较重要的一些人文学者作为局部性问题来分析,例如出现于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和艺术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以及罗兰·巴特的随笔中。但至今为止,关于符号、表征、艺术创造等的机制如何通过声音得以运作,并如何通过听觉感知来表意,仍然众说纷纭。在“符号转向”退潮,“文化转向”方兴未艾的当下,如何让这样一种符号论立场之下的研究在广义“文化符号学”中发展出稳定有效的范式,也仍然是一个挑战。另外,如何用文字符号来解释关于声音/听觉的种种?语言文字符号、视觉符号、声音(听觉)符号相互之间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文字文献、图像文献,与声音文献的关系如何,各自的意义指涉如何被媒介形式所设定?这些多样性的探索已经在国内展开,比如陆正兰对于音乐符号学、歌词与音乐的关系等一系列论述和译著,正在该领域获得进展。
(二)语言、文学、修辞、叙事层面的声音与听觉
以语言符号为载体的文学文本具有两重性,即作为视觉符号的文字和作为听觉符号的语音,那么后者(作为听觉符号的语音)在文学本体中的功能如何?另外,讨论文学修辞和文学叙事的声音、听觉,能够与讨论实际的声音、听觉在怎样的学理层次发生关联?声音、听觉在文学修辞和叙事结构上的表征、延展,如何塑造了文学修辞、叙事结构乃至于社会想象力本身?在这一方面,国内外国文学和叙事学领域傅修延及其团队做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三)声音政治
尽管福柯对权力关系最脍炙人口的图解是视觉监视性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他在《性经验史》(第一卷)也用听觉感官意义上的天主教的忏悔活动(神父与忏悔者之间阻断了视觉,只剩下听觉)来阐释权力运作的机制。听觉感官与权力、声音与政治,这些问题也被听觉文化研究者所关注。在国内,周志强借鉴并阐发了法国阿达利《噪音:声音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话语,开辟了声音政治批评的路径,在对我国当代声音文化现象的微观分析中示范了文化社会学洞察力、政治乌托邦想象力,和当代历史文化语境“深描”这三者的结合。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文化批评模式之下展开对改革开放以来流行音乐文化机制、声音政治的研判。
(四)视觉性研究和听觉性研究的打通与综合
现代人凭借技术手段很容易让音轨与视像拼装,也可以借助耳机和随身听来将眼前与耳中的不同环境拼贴为复合式体验。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也应该包括声音之“像”。如何让视与听两种知识话语体系在研究中实现沟通、盘点,这构成了审美与文化修辞研究的一片深水区。电影学、媒体学以及视觉、听觉理论都在此大有可为。
(五)对听觉技术应用及其听觉性实践领域的考察
考察的对象包括声学诸学科(电磁声学、环境声学、建筑声学)、录音学、播音学,以及声音艺术、“具体音乐”、多媒体教学研发的理论与实践。另外,民俗学、人类学的一些研究和田野实践与听觉性手段的利用和对听觉性问题的考察(歌舞、口述等等)一直有不解之缘。这也可以成为听觉性研究的考察对象。考察的方法可借助技术文化史的方法,也可借助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深描”甚至田野考察。考察的价值在于:这些学科深谙听觉(声音)一些极为鲜活、具体、独到的现象,有着自己的“行话”,具备可资利用的经验性资源和理论资源。
(六)听觉与个人、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
关于记忆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目前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牵涉到心理学、哲学、文化理论、感知理论、感官研究以及媒介技术研究。听觉作为记忆构成因素的重要性不可低估。现代媒介技术在听觉上的应用,对性别、种族、身份、阶级等身份认同的塑造也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对听觉文化研究话语在国内进一步的开拓和建构提出三点想法:
一是尊重此话语领域本身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这需要注意避免在先入为主的问题预设和框架中去臆造,也要避免简单地将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二元对立起来,突出听觉贬低视觉,还要避免以偏概全,从哲学、美学、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的论述中片面撷取某些片段,遮蔽听觉性问题的复杂性、深度、广度。还要真正将听觉本体的问题,与发生在语言里面的听觉性修辞、隐喻问题,做到有所区分。
二是“实践性”优先。听觉文化研究模式有别于对文字、图像的研读范式。既然是要构建听觉性文化研究的话语场域,在研究方法上需要以“实践性”“有效性”为先。构建出来的话语概念场域要为对听觉文化的跨文本分析提供有效的切入工具。
三是营造中国语境。要以外来的“Sound Studies”和国内近年来的听觉性人文学科论述为资源,开拓出一个开放、有机的知识话语场域。不仅要接榫到国内学术语境既有的文艺学、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等的话语里面,还要与各种相关学科充分交流,构建在我国学术具体语境下的听觉文化研究学术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