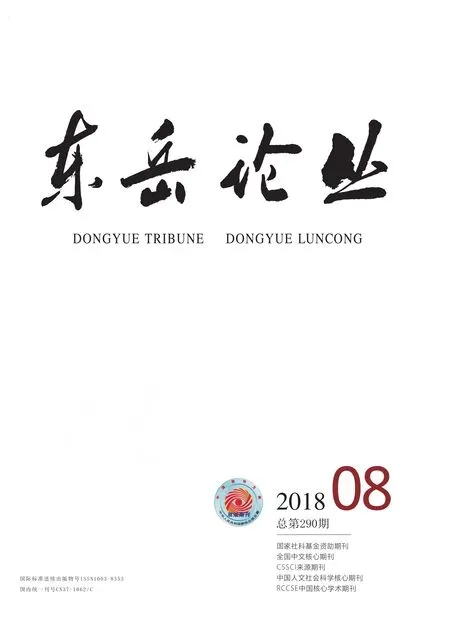网络场域:网络语言、符号暴力与话语权掌控
周 彬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马克思曾提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在以Internet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支撑下,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即网络社会阶段(Network society & Cyber society)。网络社会作为一个虚拟社会(Virtual society),是一种现实社会的延伸。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场域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由各种相互竞争的“场域”构成,而个人的心智结构则呈现为更具有形成性的“惯习”②[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互联网已经发展的如此迅猛,形成了一个强大场域,即“网络场域(netdoms)”。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从人们现实社会生活来看,网络依赖症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网络控”“手机控”成为左右人们心智结构的“惯习”。互联网的发展为资源匮乏的社会组织提供了自我呈现、网络建设、公众动员以及建构另类话语的工具,具有赋权功能③Sima,Yangzi,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The Internet:Constructing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Asian Studies Review,2011,35(4):pp.477-479.。习近平指出:“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④《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网络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基于场域理论研究网络语言的符号暴力和话语权掌控,对“建设良好网络生态”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场域理论及网络场域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往往是较为狭隘的,因为受到自然空间的限制,而人与自然界的同一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受到自然界狭隘关系的制约。马克思说:“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可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狭隘的关系被完全打破,成为一个无边界的场域(field)。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这些位置是客观存在的,占据特定位置的行为者或者机构,被这种网络或架构所决定,从而界定了这些位置,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权利和资本,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包括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缘关系等。他将场域理论融入到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深受各个学科的重视并得到广泛应用。他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存在,亦可以理解为一种关系网络。社会大“场域”又包含各种“子场域”,“子场域”受制于大场域,也是大场域的内在组成部分。“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场域是一个包含着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持续竞争场所。场域按照一个为了自己自主性的竞争历程,可以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有自身逻辑的发展,成为支配着场域中一切行为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也就是说,场域是一个有一定边界并可以相对独立实践活动的逻辑空间,这种空间可以自成生态而相对独立运转。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布迪厄所提出的场域具有以下特性:其一,客观存在性,场域是客观存在的关系架构;其二,普遍存在性,社会世界普遍存在场域;其三,多层次性,大场域下有小场域;其四,相对独立性,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的逻辑和空间;其五,支配性,场域逻辑支配着其中的行为者。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我们可以把互联网社会看作是一个“网络场域”,这个场域具有以上所言的五大特征。引入“场域”这个社会学概念,将信息网络放置在“信息网络场域”这个中观范畴之中进行考察,使其既成为现实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因其与传统社会相区别的特征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郭鹏,郑华萍:《论信息网络场域中主体间的道德学习》,《学术交流》,2014年第12期。。互联网中的行为者(网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网络构成一个网络场域,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场域作为网民的言论空间,不仅具有虚拟性、交互性和匿名性特点,还具有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碎片化(Fragmentation)、流动性、互动性和非线性等特征,其中的行为者(网民)的关系网络超越了传统社会的任何网络。在这个网络场域中分布着无数个具有高度自治特征的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自由链接,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成为及时化的中心,但又不具备中心控制功能的强制性,与传统社会场域中的中心节点完全不同。节点之间通过平等的、开放的网络行为者的互相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因此,网络场域是一个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网络架构(configuration)。
网络场域不是没有中心,中心的随机性是由行为者(网民)自由选择、自主决定的,不是由某一个权威机构或权力机构决定的中心,不是传统社会场域意义上的中心来决定节点或节点依赖中心,而是节点决定中心或中心依赖于节点,也就是说在网络场域里,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中心,但是每一个中心又不是稳定的中心,而是随机流动性的中心,哪一个节点成为中心是由网络场域的众多行为者(网民)一致性行动或者共同认可的,且任何一个中心对节点也不具有强制性,节点对随机产生的中心都是自主自愿地服从或者说是推崇。任何参与行为者(网民),均可提交或者分享自己获得或创作的内容,网络场域的内容是所有参与行为者(网民)协同创作或贡献出来的,所以网络场域是扁平的、内容生产也更加多元化。网络场域、海量的社交数据与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学研究者分析在线文化、社会关系网络、行为者的地位和角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Evans,James A.and Pedro Aceves.Machine translation:mining text for social theory,Molecular Microbiology,2016,42(1):pp.539-547.。将互联网看作是一个场域,即网络场域作为分析的背景和空间,对于认识其中的内在逻辑和规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背景意义。
二、网络语言的符号暴力倾向
语言是人们用来交流的工具或符号。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惊人的符号体系”,是一种在各方面都符合符号本质规定的“纯粹符号”*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传播情感和交流互动的符号工具。马克思认为,“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网络场域中行为者的实践重要形式就是交流,在这一实践中创造了网络语言,部分地依赖网络语言实现交流的功能,其特殊性在于不完全是现实社会的语言,很多是行为者(网民)自己创造的语言,运用这样的语言构筑起新的网络场域里的社会关系,从实现社会场域中转化到网络场域,实现了新的社会意义。“在线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不同的网络场域,而用户所表达的话语符号在特定网络场域内以及不同网络场域的转换中获得具象的社会意义。”*黄荣贵:《网络场域、文化认同与劳工关注社群》,《社会》,2017年第2期。布迪厄质疑结构主义语言观,并认为不应把语言仅仅看作一种沟通的手段,不应忽视语言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也就是说,语言背后是有权力关系的,谁的语言,对谁说的语言,这是涉及到说话者的权力和接受者的地位。不仅如此,语言的内容体现着权力关系,不是纯粹的沟通手段。
布迪厄可以看作是唯物主义人类学家,关注语言问题,不是仅仅关注概念化符号系统的语言,更主要的是关注语言的社会学意义,关注实际语境中作为特殊符号象征性系统的话语,关注语言的象征性权力,提出了“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概念,探究了符号暴力的各种形式是如何发挥特有的作用,并影响支配结构的再生产及其转换的过程。“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形形式(transfigured form)表现出来。”*[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符号暴力理论认为,符号权力通过言语构建已知事物的能力,是人们看得见、听得到且可信的一种权利,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白纸黑字”“当面说清楚”之类的表达。这不仅仅是沟通的功能,还有言说者与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他之所以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因为结构主义者认为有一个共同语言规则,大家在自觉遵守的前提下实现沟通交流目的,因而忽视了语言的生成过程,没有从语言形成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或者个人是如何共同使用这些语言的社会历史过程。是约定俗成,还是权力关系支配,这里面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Bourdieu P,Thompson JB.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1991,71(4):pp.466-468.。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统一文字,新中国推广普通话,都包含着一定社会将它的主导价值赋予这些语言并建构它,从而成为标准语言符号。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中符号所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具有心理性质的语音形象和概念内容,即“能指”和“所指”,两者统一了就是语言的“约定俗成”,但不一定是客观本来*夏登山,蓝纯:《索绪尔语言价值理论源考》,《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在这一点上,布迪厄是认可的,也是他进一步研究的知识基础。布迪厄认为,“符号系统‘只有通过那些并不想知道他们臣属于符号权力甚至他们自己就在实施符号权力的人的合谋’,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符号暴力,意在强调被施用者的不知情,因此,也被布迪厄称为‘温和的暴力(The gentle violence)’。”*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Cambridge:Harversity Press,1991:p.164.根据布迪厄的“符号暴力”理论,在网络场域里,网络中的“符号暴力”,是在每一个行为者(网民)都是参与合谋的基础上,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这是网络场域所决定的,虽然网络行为者也有认知能力,但是,他们受制于网络场域决定机制。每一个行为者既参与塑造这一网络场域的决定机制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又受这个网络场域机制所决定。网络的符号暴力施加于网络场域社会行为者,自己却不能够领会这是一种暴力,甚至自觉地认可了这种暴力。实施符号暴力的过程,是由暴力对象以他者的自我异化来施行的,参与行为者协助施暴者施以符号暴力。现有的文献中,国内不少学者提出语言暴力,究其所指来说,与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有学者认为,“‘语言暴力’是指用诋毁、谩骂、讽刺等歧视性语言,使他人精神层面遭到侵犯,它属于一种精神伤害。”*辛学伟:《教师语言暴力的成因及对策浅析》,《当代教育科学》,2010年第23期。网络语言暴力行为从性质上讲属于大规模网络集体宣扬隐私、贬损名誉的侵权行为,具有规模巨大、影响力强、涉及范围广、后果严重的特征,应当以法律对其进行有效规制*邱业伟,纪丽娟:《网络语言暴力概念认知及其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符号暴力理论认为,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人们的语言表达是一种权力行为,服务于社会中特定成员的利益,又称为“符号权力”。这种暴力行为是“无形的”或者“隐蔽的”的权力的施加与被施加行为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歧视性语言或者谩骂性的用词。
网络语言(主要是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创造并得到广泛认可而传播扩散使用的语言。网络语言的生成是在网络场域里网民在键盘上敲打出来的包括文字、符号或者图片在内的能够表达思想或沟通内容的而逐渐被网络大众认可、使用和扩散的过程。从语言经济学角度解读了网络语言,认为网络语言所遵循的语言经济学原则,网络语言的产生、动态发展,以及其构词法和泛洪(Flooding)传播特性恰恰体现了语言网络效应,均衡和省力的语言经济学原则,其发展符合一般语言的发展规律*刘念:《网络流行语的语言经济学原则》,《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网络语言的符号暴力,是在网络社会的行为者(网民)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而网络社会行动者(网民)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事实上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网络场域现象,网络场域的关系架构成为决定行为者(网民)的机制,网络语言暴力有一种特殊的工具理性,其实施过程是由暴力对象以“他者”(others)的自我异化方式进行的。也就是网络语言(符号)的被施暴者协助了施暴者对自己的符号施暴,网络语言(符号)已经广泛渗透到参与网络行为者意识深层次,并享受着网络用语的“便利”,成为网络场域里每一位行为者(网民)所特有的“实践无意识”,布迪厄称这种现象称为“误识(misrecognized)”,即由于各种旨在掩盖社会不平等的符号权力的存在,行动者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符号的这种不为人知的强制作用,通过“误识”在网络场域的实践中悄然且持续地发挥作用。马克思认为:“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表现,而不管此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网络语言的符号暴力倾向逼迫网络场域行为者(网民)必须接受这些网络语言,方可以识别或认知这些被特殊符号表达的社会事件、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在网络场域中才能够正常交流或沟通。这些网络语言不仅在网络场域里起作用,还会渗透到现实社会,人们在现实社会里广泛使用网络语言尤其是网络流行语,甚至在大学的课堂、政府文件、官方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偶尔使用网络语言,充分表明网络语言在实践中悄然且持续地发挥作用的力量和符号暴力倾向。
三、网络场域的话语权掌控及策略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福柯话语论认为,话语不仅仅是涉及到内容或表征(representation)的符号,更主要的是被视为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话语权是指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福柯的话语论影响很大,话语论一方面强调话语对主体及其现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又力图揭示话语后面的权力与知识共生关系*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此后,话语论的理论观念和方法广泛运用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等领域,更有甚者认为,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话语转向(the discursive turn),意思是话语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更是深藏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姚文放:《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与福柯的话语理论》,《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3期。。福柯将话语内部的秩序划分为三个原则,即外部力量话语的控制原则、话语内部的控制原则和对话语主体的控制原则*黄华:《论“话语的秩序”——福柯话语理论的一次重要转折》,《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他说:“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说我们喜欢的东西,谁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p.57.也就是说,从外部约束来看,话语是受到外部体制和历史的约束,受到真理对谬误的约束和排斥;受到理性和疯癫之间的区分和对立。从话语内部控制来看,有话语就必然受到评论的评论秩序,作者组织话语的秩序,以及话语对象领域的学科秩序。从对话主体来看,必须遵循四个秩序,说话者能够在对话和评论中使用某种形式陈述的仪式秩序,话语者是有话语圈的话语团体秩序,话语与话语者相互作用的学说秩序,为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进入话语的社会占有秩序。
在福柯看来,话语与语言是不同的,话语分析不是分析语言逻辑,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具体说明话语规则,所关注的是“机构的、社会的话语秩序”。话语权是意识形态运行的技术或者形式。意识形态产生于权力,但不是凌驾于话语之外的,而是与话语者群体形成一个关系链条,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共存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已经不是传统的政治法律强制,经济压迫或心理压抑,而是借助于话语进入非上层建筑领域*张秀琴,孔伟:《福柯的意识形态论:“话语—权力”及其“身体—主体”》,《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7期。。福柯指出:“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立刻受到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M·Shapiro.Language and Politic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4,p.109.也就是说,话语总是受到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性等社会实在的约束,而不仅仅是涉及到物的存在,任何言谈者都有发出话语的出发点,是由社会关系(含社会阶层)、观察的立场和既得的制度性约束,各种社会不平等和权力关系融入在话语之中。他强调话语既是思维符号又是交际工具,对主体和现实世界具有建构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张传泉,路克利:《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的内涵与引申》,《重庆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权力(symbolic power)关系并不完全是由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力量所单独决定的:通过所讲的各种语言,通过运用这些语言的人,通过根据占有相应能力而得到确定的某些群体,通过所有这些,整个社会结构在互动中得以呈现。”*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Cambridge: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74.语言是由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形成的一整套复杂的体系。在这一点上,与福柯的话语权力论是基本一致的。布迪厄探究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特别是考察权力是如何渗透到语言符号之中的。语言有一个语言市场,有的语言价值高一些,有些语言价值低一些,在给定的语言市场上,有的语言被很多人需求,就成为价值高的语言。说话人的语言实践是在于他们知道相关语言市场什么是有价值的语言表达,怎样产生有价值的语言表达。他还认为说话人的语言资本(linguistic capital)是不一样的,语言资本是控制语言价值形成机制的权力,语言资本要依赖于说话者个人在社会地位、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就是说社会地位不同、经济实力不同、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环境不同,其语言资本也是不同的。“符号权力”与其说特指某种权力,不如说是指代社会生活中不断施展的、形式多样的权力的某个方面*傅敬民:《布迪厄符号权力理论评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符号权力是一种隐形的权力,有一种特殊的动员手段,强加于行为参与者,参与者不仅相信权力的合法性,还相信实施权力的人也是合法的,是理所当然的权力。
在网络场域里,网络语言是网络中的行为者(网民)创造的语言,具有草根性、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特点,话语权控制成为网络时代的一个新课题。福柯认为:“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法]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转引自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网络场域是仅次于现实社会场域的最大场域,而且具有强大的舆论传播性质,谁掌握了舆论,谁就掌握了主动性,“话语权”的本质是控制舆论的权力。应该承认网络语言就像社会语言一样,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不能够一概批评,也不应该一概禁止,毕竟是越来越多社会网民大众参与的一种技术带来的便利场域,但是,任其自由发展,必然鱼龙混杂,嘈杂不堪,混淆视听,扰乱网络场域社会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那必然会影响社会网民大众在其中健康地生存。因此,网络场域的话语权掌控策略必须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
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形成了话语权的辩证法。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网络场域的行为者在网络生活实践中,必然产生自己的语言、思想,进行语言交流、思想沟通和精神交往,这是由这一时代的物质关系决定的新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物质力量或关系决定了人们的精神活动,虽然网络场域是一个虚拟社会,但是其在人们网络交流中超越了现实社会的人际交流空间和范围,其中网民的语言乃至思想超越了传统的任何交流方式和传播方式,所以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做出反应。因此,观念和意识形态、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数亿人参与的网络场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去占领,那就会失去意识形态的掌控,就难以掌握网民群众,甚至会酿成“意识形态风险”。“当下(网络)流行语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其迅猛发展对我国话语传播模式和政策议程设置产生了革命性的挑战,话语体系的传播同样面临考验。”*黑晓卉,尹洁:《从当下流行语看我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传播与创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因此,对网络场域的实施有效话语权掌控策略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义。
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19日。网络场域是网民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迫切需要进行意识形态治理和话语权掌控。“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现实关系中把握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之间的关联网络”*莫伟民:《福柯与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从话语权掌控策略来看,主要有六个策略。其一是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时刻不忘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的领导权,要善于在网络时代,借助于网络技术,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其二是主流媒体引导策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党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其三是教育体系教导策略。福柯指出:“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法]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转引自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因此,学校教育和社会各种类型的教育都必须坚持对网络参与者的教导。其四是社会组织开导策略。网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失控,大多因为偶发或者突发社会事件,因此,社会各类组织要本着开导原则,及时消除意识形态隐患。其五是网民情绪疏导。网民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总是会有情绪的,而网络场域集聚着大量的行为者(网民),虚拟社会往往没有现实社会的各种约束,容易情绪激动,甚至出现情绪失控,需要及时疏导,才能够缓解因情绪失控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危机。最后是关键词语制导。网络本身是一种技术,既然是人们发明的技术,就一定为人们所掌控,从技术层面有针对性地进行关键词控制,也是必要的策略和手段。总之,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控仅仅是手段,就其根本要求是意识形态要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我党及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体现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