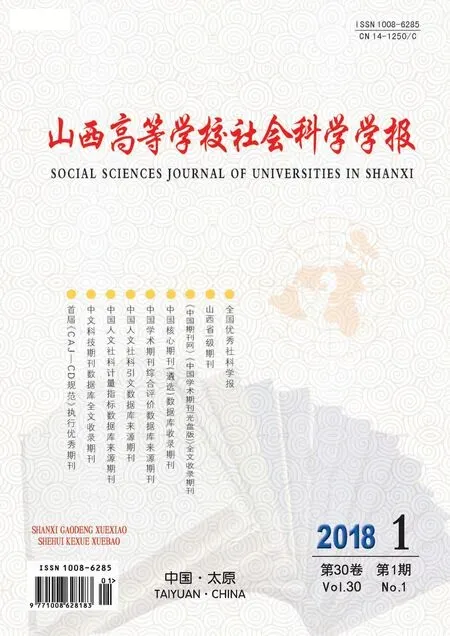五四现代小说诗性传统的续接与重建*
廖高会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五四文学革命至今已历百年,如何正确认识五四文学革命与民族文学传统特别是诗性传统之间的关系,对于消除五四文学革命“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错误认识、加强当前文学与文化传统及时代精神之间的联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晚清民初到五四时期,小说文体被推向文学中心位置,承担起“新民救国”和“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这种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小说观直接导致了现代小说对诗性传统的疏离甚至中断。但这也只是“脐带式的中断”[1]。因为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诗性传统必然与现代小说形成某种张力与对话,也必然逐渐渗透居于主体地位的现代小说,成为现代小说逐步完成诗性重建的根基。在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五四现代小说的诗性续接与重建才得以完成。
一、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文学资源
五四时期,胡适与陈独秀等人倡导文学革命之目的不仅仅是要明确什么是新文学,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如何创作新文学,而后者与文学资源的选择密切相关。五四理论家和作家们多主张借鉴外国文学资源以创建新文学。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指出,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要完备得多,特别是19世纪欧洲的散文戏本,体裁多样,有“问题戏”“心理戏”“讽刺戏”“象征戏”和“专以美术的手段”创作的“意在言外”之剧本。而西洋小说的材料、体裁、命意、描写等方面都远胜中国小说,“真是美不胜收”[2]18。胡适高屋建瓴的文学视野,对后来引进象征主义、心理描写等艺术技巧,提升现代文学诗性品质奠定了思想基础。鲁迅也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为新文学增添新的质素。周作人在《国粹与欧化》一文中表示,我们无法改变自身本性,也不能完全拒绝外来资源,两方面都需要吸收[3]121。周作人提出“抒情诗的小说”概念,明显受到库普林小说《晚间的来客》的影响。同鲁迅等人一样,五四不少作家都重视对外国文学资源的吸收,以吸收其新质来增添五四小说的审美特性。
五四现代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对国外文学的某些艺术技巧进行了创造性的应用。诸如心理描写方法、象征主义方法、浪漫主义手法和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等,在郭沫若、鲁迅、郁达夫等作家的小说中都得到了大量的应用。特别是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借鉴与吸收,极大增强了五四小说的诗性色彩。普实克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受到欧洲文学如浪漫主义影响时指出,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欧洲文学的主观抒情性和浪漫主义气质,渗透并瓦解了叙事性作品固有的传统形式[4]66。叙事性削弱和主观抒情性加强,成为当时的世界潮流。受此影响,五四作家如苏曼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创作了一批具有浓郁主观抒情色彩的小说。
外来文学资源之所以能融入民族诗性传统,关键在于中国文学中有着适宜它们生长的土壤,这土壤便是本身具有明显的主观抒情性特征的比较高雅的古代文言作品[4]66。即使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时期,启蒙者们在批判文学传统和文言文时也有所保留与肯定。比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指出自己并不反对现代文学中使用广义之“典”。傅斯年指出:“古典原非绝对不可用,所恶于古典者文学,为其专用古典而忘本也。”[5]他反对的只是堆砌典故,卖弄才学的华而不实之文风,并不反对正确恰当的用典。胡适、傅斯年等人对文学传统与文言传统留有余地的批判为现代文学吸纳古典元素留下了空间。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五四文学理论家和作家们开始对过去的激进思想和行为进行纠偏,重新反思和审视文学传统问题。鲁迅也承认自己创作受传统影响,他说:“以前我看过不少旧小说,所受的影响很深。”[6]周作人在《国粹与欧化》中表明,国语文学(新文学)完全可以向着自由方向发展,“炼成音乐与色彩的言语,只要不以词害意就好了”[3]121。他还主张把传统“融化”进现代文学中,使诗歌具有“朦胧美”,散文具有“涩味”,小说具有“意境”与“古典趣味”[7]。由此可见,周作人非常重视语言的雅化与诗化,重视语言的艺术美感。他还倡导小说创作融入诗歌,这种今古相容和文体交融观,对现代小说特别是京派小说诗性语言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周作人的文学观实际上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国际视野中以探寻民族文学发展的自我特色的,尽管他的这种意识还比较朦胧。
五四现代小说对民族诗性的认同与继承以及对外来诗性潮流的接受与吸收几乎是同步的,二者皆为五四现代小说诗性回归与重建的两大不可或缺的资源。
二、五四现代小说诗性精神的重建
文学作品的诗性必然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而隶属于内容的诗性精神是促使文学作品诗性生成的第一要素。诗性精神是一种与人的存在即本原相关的思维活动,是超越现实而想象彼岸世界以及回归永恒自然神性的生命冲动,是以更高的更理想的超验的世界重新设定并期望改造现实世界的诗意向往。传统诗性精神主要体现在“发愤抒情”“家国意识”“抗争精神”等方面。而诗性精神常常和特定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将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五四现代文学的诗性精神是对传统诗性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只是更多体现在独立民主、批判抗争与救亡图存等启蒙精神方面。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精神的主体。因而,鲁迅、沈雁冰、钱玄同、罗家伦等五四新文学家对晚清民初新小说产生的不良甚至恶劣的影响进行清除,特别对诸如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之流只顾泄私愤、泼污水、求消遣、玩游戏的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阐明新小说的破旧立新与为人生为民众的宗旨[8]。1916年前后黑幕小说泛滥成灾,鲁迅所在的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鲁迅时任主任)拟定了《劝告小说家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函稿》,严肃地揭露了黑幕派小说的恶意和恶果。沈雁冰也批判旧派小说把文学当成消遣、游戏与载道工具,同时指出新派小说借以表现人生,扩大人们的同情[9]75-76。五四新文学家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要求其承担启蒙使命。在对旧小说思想内容与创作态度等进行清理之后,五四先进的知识分子便着手为新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内涵。李大钊写下了《〈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青春》《今》等一系列文字,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和青春的诗性气魄呼唤人们创造“青春中华”。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讲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10]。李大钊之文表现出强烈的青春气息、战斗精神和进取精神。
五四作家和理论家张扬人性和救亡图存的启蒙精神与传统诗性精神是相一致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开创者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消除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方面的黑暗,只有靠“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而为了拥护这两位先生,哪怕是断头流血都会毫不推辞[11]。这种舍生取义、大义凛然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是传统诗性精神的现代表现。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对文学研究会作家进行评价时指出,作家们不再躲在象牙塔里,而是和时代相互呼应,深切地感受民族与国家的痛苦与灾难,倡导“血与泪的文学”,十分敏感地为苦难的社会写作。即便是创造社诸作家,其“为艺术而艺术”的面纱仍然难以掩藏他们反抗旧时代旧社会的情感冲动。郭沫若说:“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12]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人的文学”的目的在于反对非人的文学,即在文学中提倡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基于个性自由和解放的人道主义[13]。他要求在文学中注入平等、自由之精神,主张依靠个性表现自己情思,这些主张具有浓厚的反封建礼教色彩。五四启蒙运动在彰显抗争精神的同时,还表达了对个性解放、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连同对传统文学中的反叛皆与“发愤抒情”“家国意识”“抗争精神”等民族诗性精神相一致。无论是救亡图存的“家国意识”,还是追求独立自主的“抗争精神”,都要通过“发愤抒情”的形式进行自我抒发,这便使现代小说具有了浓郁的主观色彩和诗化色彩。
三、小说审美属性的重视与回归
五四知识分子在文学革命的浪潮中极力强调文学救亡图存的启蒙使命的同时,并没有忘却文学的艺术形式之美,而对艺术形式美的重视与回归,使五四小说诗性传统的续接与重建成为可能。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道如何创作新文学,他特别强调方法,其中有结构方法和描写方法,而描写方法又包括了写人、写境、写事、写情等方面,写人、写境须有个性,写情要“真精”“细腻”和“婉转”[2]17。作为社会革命家的李大钊,他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指出新文学必须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但同时也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14]。李大钊肯定了文学的写实性,也强调了文学的情感性和审美性。1918年,胡先骕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批判文学革命中把文学工具化、忽视和违背审美特性的现象,指出:“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学在达意之外还有各种修辞技巧的追求,有着字句的锤炼,不是信口开河,信笔所写[15]。他努力强调文学语言的艺术性和审美特性。陈独秀在《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中对文学进行了界定,其中包括三方面:“(一)艺术的组织。(二)能充分表现真的意思及情。(三)在人类心理上有普遍性的美感。”[2]57简言之,就是文学作品必须包括艺术技巧、真情实感和美学效果三大要素。因而陈独秀强调文学的“饰美”性,即文学的艺术形式之美,形式美表现在“意思的充足明瞭”“声韵调协”以及“趣味动人”等方面[2]54。由此可见,陈独秀对文学的审美特性即对诗性的追求是十分明了直接的。傅斯年以理性和情感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文学价值观,提出了文学评价标准,即能引入感情、启人理性、营造境界、能化别人、能忘自己的是好文学。文学的根本和职业便是“移人情”和“人化”[9]57。对白话文自身的美学特征的追求和人情人性的重视,正是现代白话小说诗化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同时,五四启蒙者们还对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指出,新文学除了承担社会历史使命外,还有文学自身的使命,即排除功利的打算而追求“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他认为,美的文学能“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 ”[2]512。成仿吾反对文学的纯功利化,因而主张有美感价值的文学创作,以培养人们优美的感情并提高精神境界。蔡元培则从思维角度反思唯科学理性主义所带来的片面性,他认为人类的思考方式,不应限于逻辑理性思维,而应该有多种,如论理学用概念思维,美学用直观思维,伦理学二者兼用[16]。蔡元培区分了科学与美学之间的思维特征,目的是要纠正当时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给文学带来的弊端,要求文学遵循自身的思维特征和审美个性,重视直觉与诗性想象。
四、五四现代小说语言的雅化和欧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语言的工具性的强调,必然影响到小说语言的诗性生成。但五四文学革命并未全然否定或放弃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特别是当白话文运动落潮后,他们开始对过去激进的反文言而独尊白话的语言观进行反思和纠偏,重新审视和评价文言,肯定其美学特性。
陈独秀指出,要实现“文言一致”,就需要在白话文中多夹入些较为通行的“文雅字眼”[17]。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表示:“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9]17这实际上为白话文融入文言或现代文学融入古代文学留下了空间。朱经农指出:“文学的国语”应该“并采兼收”文言与白话,形成“‘雅俗共赏’的‘活文学’”[18]。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提到,朱经农认为白话文应该吸收文言文的有益质素,强调新文学的语言应该是综合白话与文言的产物。任叔永和梅觐庄等人认为,无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但白话文的使用需要“美术家”之锻炼[19],“美术家”之锻炼正是语言的艺术化审美化过程。《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把白话作为小说之正宗,但白话应吸收文言“扬抑抗坠,轻重疾徐”和“提挈顿挫,烹炼垫泄”等句法特征[20]。这实际上是主张用文言的典雅性、音乐性增强现代小说语言的诗性色彩。
鲁迅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是十分激进的,在五四运动热潮过去后,对于古代文言文,明确表示给予接受与继承。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表示,在用白话文进行写作时,力求顺口,一旦“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2]244。在鲁迅的创作中,实际上一直受文言文和古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中断诗性传统的吸纳。1925年,周作人在《理想的国语》中也表示,古文已经不能适合现代人的思想,因而需要以白话口语为基础,融入古文方言及外来语,形成说理严密而又有“艺术之美”的语言[21]。
在五四作家不断借助文言雅化诗化语言的同时,语言的欧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五四现代小说诗性语言的形成。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文学语言的欧化,为中国现代文学拓展了诗性空间[22]。五四作家在借鉴欧化语言时能扬长避短地诗化语言,或在白话文中融入音乐的质素,或化长句为短句,形成相应的节奏,或短句组合成长句,形成流畅的语势。王本朝认为,其“多个短句的拼贴组合成长句,形成语言的链条,如同滚雪球,气韵贯通”[23]。而有的则对白话文的欧化句子结构进行颠倒或倒置,从而凸显某些部分,或加深受众印象或更为深沉地吟咏性情。如鲁迅的《伤逝》写道:“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这样欧化的句式带来了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在情感方面更适合浓郁绵长的感情抒发,在乐感方面增添了语言的节奏感,产生了一唱三叹的效果,所有这些都更好地营造出了诗意的抒情氛围。
五、主体意识的觉醒增强了小说诗性抒写
晚清至五四报章杂志的繁荣兴盛,推动了小说文体叙事模式的转变,即由古代白话小说的“说—听”模式转变为“写—读”模式。陈平原指出,这种叙事模式强调艺术的个性与日常生活的抒写,使小说的“意旨”倍受重视,而且普遍关注人物内心的各种感受、意识或潜意识、联想、梦境甚至幻觉,对小说的“情调”“意境”和“诗趣”比较重视,从而为五四现代小说带来了“诗化”倾向[24]。这种新的叙事模式为现代小说的主观抒情和诗性意境的营造提供了可能。
五四现代小说主观抒情性的增强,既表现在个体情感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情感方面,而个体情感与社会情感又是统一于追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五四启蒙精神。在五四作家中,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成员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具有更为浓郁的个体主观情感表现,而这些具有鲜明特性色彩的主观情感,却又是五四时代精神引发和催生的。而强调“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如沈雁冰、叶圣陶、王鲁彦等人的作品中更多重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展现或批判,因而也更多表达了社会情感。普实克说,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结合[4]4。正是这样的情感或心理倾向,使五四现代小说具有了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因此,五四小说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以讲述故事或传奇为主,而以传情表意为主,创作动机和叙事模式的改变必然削弱小说的故事性,淡化小说的情节,从而促进了五四小说诗性传统的回归与重建。
总之,五四运动前后,现代小说从其滥觞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也是诗性传统逐渐续接和重建的过程,诗性传统在不同形式小说中的回归与重建,为现代小说的艺术境界与艺术水准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现代小说过分功利而带来的抽象与粗糙的缺陷,使现代小说在关注现实与吟咏情怀之间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艺术之路,为民族诗性传统与现代小说艺术之间搭建了对话与续接的桥梁。
[1] 陈平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J].文艺研究,1985(5):68-77.
[2] 许觉民,张大明.中国现代文论: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3] 傅光明.周作人散文[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
[4] 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5] 陈平原.《新青年》文选[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111.
[6] 周令飞,葛涛.鲁迅零距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64.
[7] 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
[8]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85.
[9] 黄健.民国文论精选[M].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14.
[10] 华锺彦.中国历史文选[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271.
[11] 董丛林.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第3册民国卷二[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303.
[12] 张燕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辽金元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11.
[13] 雷达,李建军.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47-49.
[14] 王长华,崔志远.河北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评论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1.
[15] 钱基博.国学必读:上[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19.
[16] 蔡元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M]∥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3.
[17] 陈独秀.《独秀文存》选[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291.
[18] 刘勇,李春雨.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第3卷1915—1919[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123.
[19] 胡适.四十自述[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6:107.
[20] 恽铁樵.《小说家言》编辑后记[J].小说月报,1915(6):6.
[21] 周作人.集外文上集(1904—1925)[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757.
[22] 邓伟.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J].广东社会科学,2011(2):182-187.
[23] 王本朝.欧化白话文:在质疑与实验中成长[J].文学评论,2014(6).
[24] 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238-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