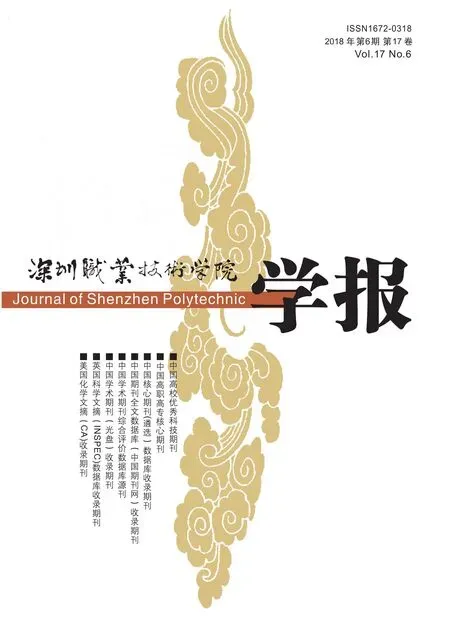威廉·福克纳的文学创作与乡土情结
李 湘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正如大多数读者习惯性地把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和英国的威赛克斯,把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和新英格兰北部,把威廉·巴特勒·叶芝(Butler Yeats 1865-1939)和爱尔兰联结在一起一样,人们也经常会将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与美国南方放在一块去联想。尽管这些作家所联系的地区和文化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它们和二十世纪世界的大城市文化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们共有的最大特点就是农业经济,农场、小村庄和小城镇的悠闲惬意,陈旧的价值观念,依旧有生命力的宗教,仍然以其基本的教义、思想和规矩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每一个地区都为它们的作家提供了一个文学乐土,从这里直接地或仅仅是暗示地批判强大的大城市文化。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之父”,他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Yoknapatawpha)①”小说大多都是以南方为背景的。他坚信文学创作的想象力来自于自己最熟悉的人民和地方,他在“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用一砖一瓦垒起了“约克纳帕塔法”艺术大厦——一个与现实的经验世界不同的艺术世界。他依恋美国南方社会的淳朴与和谐,更热衷于南方的土地和自然风光。在他的眼中,高山、河流、土地和树木都象征着南方人勇敢、坚毅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南北战争之后,南方的土地、森林和荒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福克纳对此痛心不已。他从地方的和传统的文化观点出发,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对流行的商业与都市文化对故土带来的灾难和精神痛苦进行了批判。福克纳写乡土,却不仅仅是地域性的乡土作家,他在艺术创作中更多反映的是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个体内心的孤独感和异化感(alienation)以及人类普遍的精神危机。这种深邃而有力度的乡土情结是有丰富的思想意义的。
1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乡土性之源
“约克纳帕塔法”原本是一个印第安词,意思是“河水静静地流过平原”[1]33。福克纳以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环境为依据,虚构出了一个典型的南方县城的名字,以此来象征自己的家乡。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约克纳帕塔法”县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它方圆二千四百平方英里,处于密西西比州部的丘陵和那肥沃的黑土洼地之间,人口约一万五千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主要描写了从 1800年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之后,该地区不同社会阶层几个家庭中几代人的故事,描绘了被工业文明入侵后的美国南方社会的现实。1956年在接受《巴黎杂志》(Pairs Review)记者采访时,福克纳曾表示,自从开始写作《沙多里斯》,他就喜欢上了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尽管土地并不广袤,但蕴藏着数不尽的故事;通过把真实的生活改编成故事,他可以有完全的自由用他可能有的才能到达它绝对的顶峰。它为别人开启了宝藏,于他而言,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他可以像上帝那样把这些人不仅在空间而且在时间方面到处移动[2]72。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题材“南方的历史,南方的神话和南方的现实”[3]255。
《沙多里斯》(Sartoris 1929)是一部历史感凝重的书,它写了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的故事,开启了福克纳的家系小说的先河,故而被称为是一部“在门槛上的书”。从这里开始,福克纳正式有意识地经营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福克纳曾建议想了解他全部创作的人不妨先读一读《沙多里斯》,因为它包含了他的“Apocrypha②”(世袭)的胚芽。“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南方的社会和历史,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揭示西方现代文明的普遍问题。
福克纳成就斐然,其主要原因是他把他“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变成了他精心创造的那个关于人类道德的寓言或者神话的令人信服的背景。奥克斯福、里普莱和霍利斯普林斯一次次被重新创造成杰弗生;拉斐特县和邻近的地区被用作“约克纳帕塔法”的原型;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在编纂的《福克纳袖珍文集》(The portable Faulkner 1946)前言中阐明了福克纳作品中地理和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那种在我们这个时代别的美国作家身上找不到的想象力。那种劳动他称之为双重的劳动:“第一,创造了一个神话中的王国般的密西西比州的县,但在所有细节上都完整而生动。第二,他使约克纳帕法县的故事成为全部边远的南部地区③的寓言或传奇。[4]55”这里所说的两点,即我们习惯所称的“乡土性”,通过写南方故事,福克纳表现了人类共同的喜怒哀乐,写出了他们亘古至今所面临的命运。
于乡土而言,不管文化背景如何,情结却是有所相似的。不管是怀念还是厌烦,都无法割舍作家对乡土的精神依恋。福克纳的写作与美国南方小镇的生活息息相关。他曾经表示,一个作家的创作一定要从自身背景出发。他个人曾经在密西西比的一个小镇度过了漫长的童年时光,这是他写作的一个重要的背景。他在成长过程中,不经意地将这些融入到生活中,融入到自己的情感中[5]97。一个作家只能借助于熟悉的地域场景、特定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才能更好地揭示出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和普遍性,才能取得最高的艺术成就。因为最具地方色彩的艺术才最具世界性和普遍性。
2 乡土情结——福克纳文学创作的内驱力
故土和乡情维系着作家的血脉,唯有回归故乡,才能写出真正出色的作品。福克纳从自己故乡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中获得了灵感,这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他小说中浓郁的南方文学气息的缘由。他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都是以自己故乡作为创作原型,也是他回到故乡之后的作品。福克纳真正回到了故乡,也使得自己的艺术灵感源源不断得到了充盈,进而能够合理驾驭自己的情感。故乡已经成为他的精神宝藏,也为其在美国文化中取得了独特的文化身份标签。福克纳多数的作品都源自于乡土题材,对故乡的历史习俗、地理环境和父老乡亲的深情眷恋和真挚的情感体验都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乡土情结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主要精华所在。通过描写自己的故乡,福克纳将南方文学中极具历史感和乡土性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坟墓里的旗帜》④(Flags in the Dust 1973)和《亚伯拉罕神父》(Father Abraham 1984)等一系列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都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每个故事都传达了福克纳对孕育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深刻的爱意。《坟墓里的旗帜》将时间定位于1919年的春末夏初,将一年四季里大自然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故事写进了作品中。通过描写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和自然环境,福克纳表达了自己极为赞赏的几种优秀品德:独立、坚强、果敢、宽容和忍耐。此小说是以密西西比为背景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约克纳县(在后来的小说里改为“约克纳帕塔法”)的政治经济中心——杰弗生镇。当然无论是杰弗生还是约克纳,其实都是以他家乡奥克斯福镇和拉法耶特县为蓝图的。小说通过沙多里斯家族四代人的沉浮起落把 19世纪旧南方的历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南方现实以及与这两个时代有关的几代人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反映了那个时代乡土生活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
《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 1932)中的莉娜·格鲁夫(Lena Grof),一个身怀六甲的未婚妈妈,独自一人,踏上了离开家乡的路,一定要找到那个抛弃了自己的情人。人们对她的行为并不看好,然而,她内心的平静和逆来顺受的性格,使得当地人对她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怀。在寻找情人的旅途中,有的人帮她寻找马车,提供住宿,给她食物使她能够继续上路;有的人甚至将自己很长时间卖鸡蛋为生攒下来的钱全部送给了她,让她有足够的路费。莉娜恬淡的性格,朴实无华的外在,还有村民们的善良淳朴,都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莉娜的这个故事十分普通而平常,几乎可以说是无数普通人生活场景的再现,或许有些小的曲折,但并没有大的坎坷。而整本书中描绘了一个十分复杂的世界,唯有莉娜如同人生一点亮丽的色彩,使人感觉到温暖而祥和,让人们对古希腊、斯巴达、荷马时代甚至是宗教之前的时代极为怀念。莉娜没有在偏见和世俗眼光下生活,她还没有被异化,只是简单的以真实、自然的面貌示人,这也成为她智慧和力量的来源。福克纳通过塑造莉娜这样的乡村人物形象来寄托自己回归自然的乡土情感。
恬淡的乡土人情是很让人陶醉的,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福克纳塑造了无数饱含着作者内心情感和理想寄托的人物,他们中有善良真诚、不辞辛苦的莫莉大婶(《火与壁炉》);有视家庭为生命的卢卡斯老头儿(《火与壁炉》);有战胜了洪水灾难却依然没有逃跑,一心想着要去自首的囚犯(《老人》);还有关心着爱米莉小姐的杰弗镇上的居民《献给爱米莉的一朵玫瑰》)[6]。“约克纳帕塔法”县里到处都是那些充满着乡土风情的人们,你甚至可以想象自己也生活在这里,喜欢它们,热爱它们,而不单纯就是看着它们。“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和我们今天的一般小说很少有的特点:家庭关系的和谐,兄弟姊妹间的团结,父母对孩子的疼爱——这些爱如此暖人如此祥和,就如同与世隔绝一般。
福克纳对故乡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情感进行描写已经突破了传统上的乡土文学界限,他自己构筑了全新的乡土世界,已经上升到追寻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精神的原乡的高度。他的小说世界里有很多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传统美德的泯灭、原始自然的淳朴、资本主义的掠夺、阶级和种族歧视的恶劣影响、战争的破坏与荒诞等,福克纳描绘了几乎整个当代的美国南方社会[7]41。
3 故土挽歌情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农业和乡村为主的美国南方,在宗教方面依然十分正统,由于共同的历史和神话而关系密切的各州开始努力回归到现代化的工业祖国。这大大改变了南方的面貌,在思想意识方面引起了混乱。福克纳在作品中表现了这种混乱和错位感。他扎根于家乡社区,尊重历史和传统,珍视个人主义,对工业文明、大政府和官僚主义深为怀疑,热爱南方的历史、文化和人民,对历史和记忆念念不忘。南方的文化传统、历史、社会与福克纳的文学创作的关系非常重要。霍华德·欧登姆(Howard W. Odum)认为由于南方主要是一个以关系密切、感情强烈、团结一致和彼此共享为特点的民间社会,这种民间社会和文化起源于早年开拓边疆时跟自然和印第安人斗争的殖民者和种植园贵族、农村社会在跟自然和土地的斗争中培养的坚韧的个人主义、边疆文化在山区和边远地区的残余以及既有别于白人主流社会又是其中一份子的黑人社会。这样的文化跟城市、技术、知识、理智和极权主义的文化完全不一样。这样的社会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种种冲突、沮丧和理性与感情方面的矛盾,而这正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素。福克纳生长在南方民间和地区社会文化的成长时期,目睹它们如何在同国家、种族、传统的冲突中努力为生存而奋斗。这促使他考虑历史,分析当前世界的可怕混乱,并且展望人类的未来[8]84-100。
福克纳抛弃了那些只局限于自然和风俗概念而对地方环境和乡土进行描写的做法,以强烈的南方意识,试图把自然环境、水土气候和整个社会群体的特点融合在一起,在这种人为审美观念的带动下南方特有的文化情结也得以呈现出来[9]76。福克纳的思想及作品中的“南方性”源自于他独特的南方生活经历,也使得南方叙事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标志性内容,而土地就是最突出的主题之一。扎根于大地获得的安宁感是福克纳创作的精神支柱。小说的生命来自于地域,南方叙事使福克纳获得了像大树一样深深扎根于土壤的力量。在《危机中的作家们》(Writers in Crisis 1971)一书中马克斯威尔·盖斯默(Maxwell Geismar)曾经这样评价道,福克纳不仅仅是南方腹地的代表,而且是南方腹地的化身,任何一个美国作家都无法取代他的文学地位[10]145。福克纳的作品来自南方的农业文化,这样的民间文化不给作家任何固定的地位和角色。福克纳虽然在南方诞生长大,但从他创作开始,他就必须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既作为当地人看到并感受到南方社会和文化的实质但同时又像外人那样冷静客观地看待它们。
福克纳对美国南方故土的描写,无不渗透着他独特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感受。在描写故乡的美和魅力时,他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对那些拒绝或破坏土地的人们进行了惩罚。因为在他看来,拒绝了土地就是拒绝了生活。在《八月之光》中出现的乔·克里斯默斯(Joe Christmas)就是一个典型,小说出场时,他就一脸十分傲慢且不屑的表情,“他的神态清楚地表明,他无根无基,行踪靡定”[11]22。他背离了自己的家乡,一直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种族观念,结果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他被孤立在任何社会之外,包括黑人的社会和白人的社会,他努力过,结果摒弃了两个社会。他也被女人,被大自然本身摈斥。在坚持自己独立性时,他表现出了高贵的品质;可是他的追求是一种无望的追求,人是不能够踢开自己脚底下所站的土地的。作为对照的是《八月之光》中的莉娜·格鲁夫,一个浑浑噩噩的女人,她独自步行来到杰弗生,她也有着同样可笑的追求——寻找她的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父亲。然而莉娜并没有异化,她在一个陌生的市镇里感到非常自在。她几乎没有花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保护者,虽然城里有身份的妇女对她圆睁双眼,撅起嘴唇,不过整个社会还是接受她的。《八月之光》明显地解释了时代的精神病症,这就是:背离了故土之后,人把握不住自己的身份,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
福克纳成长于美丽富饶的南方,南方的荒野、江河、森林对他来讲都是最美好的回忆。在福克纳的心中,故乡已经褪去了形而下的外衣,开始升华为人们心灵上的精神家园。随着旧制度的瓦解,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分崩离析,人类不断膨胀的个人欲望和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南方原有的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摧毁。森林被过度采伐,土地成为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牺牲品,过去被人们所珍视的尊严、道德、信仰也都渐渐地被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所代替。福克纳努力地在作品中表现这种近代文明对乡土生活的冲击,以及新旧两种文化撞击过程中普通人的命运变化。《八月之光》对人们疯狂砍伐森林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而南方人竟然以伐木作为主要谋生的手段。“这家场采伐松木,已经在这儿开采了七年,再过七年就会把周围一带的松木砍伐殆尽……萧杀肃静而又荒凉的田野,无人耕耘,无人栽种”[11]2。因为同情、谦卑、受难、忍耐等传统美德的消失,土地也开始遭受厄运。人类在结束了土地和树木的生命时,自己也只能背井离乡。只有亲近自然,摆脱文明的枷锁,复归土地,才能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安宁。福克纳在文学创作里唱的是美国南方社会的挽歌,反映了工业社会对农业文明的掠夺,表达了对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思考。
4 结 语
一个伟大作家在地域性和世界性的思考上是一致的,通过描写南方人的生活和南方社会,他实际上是想以此来表达现实人生的普遍意义。正如“新批评派”(New Criticism)⑤理论家、福克纳研究专家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所说,福克纳因为创作乡土小说而闻名。他也因此能够借助于更先进的艺术手法描述当代充满矛盾的人对现代世界的看法;然而,他也对自己内心那些古老的难以改变的真理十分坚守。借助于乡土小说,他发现他能守在家乡又能处理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12]78。
在人类日益缺乏交流、情感日益淡薄的今天,自然、乡土、人情将会成为一道照亮我们生活的“八月之光”;同时我们也会在阅读“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体味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听到冥冥中的一种声音。这声音厚重而有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它穿透了小说的形式,穿透了小说的语言,直抵你的心灵,让你在强大的生命原创力面前感到窒息——这就是与命运搏斗的声音。伴随着这种声音,是福克纳对生存、对生活、对人类从虚无中夺来的生命的关切与悲怆感。这种悲怆感源于一种执著而又朴素的乡土之情;在这悲怆里有对沧海桑田的热爱,更有对周而复始的更替和人类生生不息的敬畏。正如他在1950年12月2日在瑞典科学院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致辞时提及的,他相信人类可以存活,也一定能获取胜利;人类是不朽的生物,并不是唯独他有着永不枯竭的声音,更因为人类有自己的思想,能够施以同情、怜悯、忍耐和牺牲。而作家的特权就是,努力帮助人们坚信自己的理想,鼓励人们坚定地走下去,带着希望、勇气、自尊、同情、关怀和牺牲,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骄傲[13]154。
注释:
① 从出版《沙多里斯》(Sartoris 1929)到《掠夺者》(The Reivers, a Reminiscence 1962)为止,福克纳为创造“约克纳帕塔法世系(Yoknapatawpha)”写作了33年。
② “Apocrypha”原意是《圣经》的《经外经》,这是福克纳对他的“世系”的戏称。
③ 指美国南部的佐治亚(Georgia)、亚拉巴马(Alabama)、密西西比(Mississippi)、路易斯安那(Louisiana)诸州。
④ 《坟墓里的旗帜》(Flags in the Dust 1973)是《沙多里斯》(Sartoris 1929)未删节的原始文本。
⑤ 新批评派:这一派别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兴起,30年代在美国有了雏形,40、50年代称霸美国文坛,也反映了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进化。现代文学史上主要指20-60年活跃在英美文坛的重要文学理论流派。在美国以约翰·克罗·蓝色姆(John Crowe Ransom)、克林斯·布鲁克斯、艾伦·泰特、罗伯特·潘·沃伦、W·K维姆萨特(William Kurtz Wimsatt, Jr.)、R·P·布莱克穆尔(R. P. Blackmur)为代表。https://zh.wikipedia.org/wiki/ New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