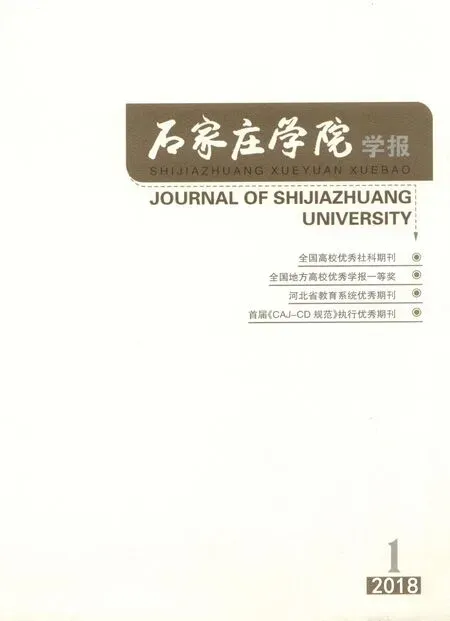论《桃花扇》民国间版本的类型与价值
王亚楠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清代孔尚任的传奇名作《桃花扇》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甫一问世,便在北京引得洛阳纸贵,最初以抄本形式辗转传抄、得到阅读,在康熙晚期刊刻后流传更加广泛,并延绵不绝。有清一代,《桃花扇》的刻本和活字印本及其翻刻本、重刻本便有十余种之多。《桃花扇》在清代的流传以刻本为主,进入民国后,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随着西方书籍形式和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引入、推广,该剧的版本形式更加多样化,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和优势,有其独特的价值意义,促进了该剧的传播、接受和对它的研究。
民国间《桃花扇》的版本多由位于上海的出版机构印行,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的出版业中心之一。这些版本多采用现代装订形式,依其出版形式,又可分为刻本和其他形式两大类。刻本即刘世珩的暖红室《汇刻传剧》本,曾先后多次校订、刻印,最早的《汇刻传剧》第23种本刻印于1914年。因笔者已另撰文对其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其他形式的版本依其印刷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石印本和铅印本,但这些版本间更本质的区别在于有无标点(圈点),所以本文主要以此为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论述。
一、《桃花扇》民国间版本概说
无标点本指剧作本文中既无传统圈点,又无现代标点,主要包括上海海左书局本、上海锦章图书局本和上海进步书局本等,以上皆石印。其中海左书局本和锦章图书局本封面题《桃花扇传奇》,进步书局本封面题《传奇小说绣像绘图桃花扇》。这三种版本皆翻印宣统元年(1909年)传奇小说社印行的《绘图桃花扇传奇》,字体、版式相同,剧作正文首页即“卷一”或“上卷”下皆署“石潭居士校正”,“卷二”或“卷下”下皆署“云亭山人编、砚云主人重校”,锦章书局还在封面特别标明“石潭居士校正本”,每出出目下刻本原有的干支年月都被删去,卷首皆有插图数幅,但各不相同。传奇小说社印行的《绘图桃花扇传奇》每页12行,行37字。海左书局本和锦章图书局本则同为每页13行,行37字。进步书局本每页20行。“石潭居士”“砚云主人”的姓名、身份均不可考,他们的“校正”“重校”在书中也没有体现。这三种版本卷首皆载录刻本中的序跋、题辞、凡例等文字,皆保留了刻本中的眉批和出批,卷首插图的每幅空白处标明对应的出名。其中海左书局本和锦章图书局本除封面、书名页和版权页外,其他部分完全相同。曲文大字,说白小字双行,曲白接排,序跋等未分段,排版不太紧密,字迹较为清晰。进步书局本卷首的插图与前两者不同,而且一页四幅,排版太过紧密,文字尤其是说白的文字过小,难以辨认,严重影响阅读。卷首另有一篇《〈桃花扇〉提要》。
标点本包括两类,一为使用旧式标点符号的版本,二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版本。前者如世界书局本,平装,全一册,竖排楷体,美观清晰,每页17行,曲白接排,以曲为主进行分段,有眉批和出批。卷首依次为顾彩序、孔尚任的《小引》、田雯等的《题辞》、孔尚任的《凡例》和侯方域的《李姬传》。世界书局本主要使用传统圈点符号中的点号来断句,具体符形为“·”,标于字之右下角,用来标示语气停顿或语意停顿,而不论语气、感情的差别和语意是否终止、完整。又如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的《国学基本丛书》本,精装,全一册,卷首文字及次序与世界书局本相同。每页10行,说白小字双行,也是曲白接排,以曲为主进行分段,有眉批和出批。顾彩序等文字和曲文中用以断句的点号“·”标于字之右下角,说白和批语中用以断句的点号“·”标于字的正下方,占一个字的位置,具体用法则和世界书局本相同。使用旧式标点符号的版本,虽然断句,但是符号单一,既不能表现词句的语气和感情,也不能表现句子内部的层次和逻辑关系。因此,这种形式不利于读者特别是一般读者对于《桃花扇》的阅读、理解和接受,也不利于《桃花扇》的流传。于是,有了新式标点本的出现。
我国的传统标点符号以句读、圈点符号为主,从殷商时期的萌芽期算起,有三千余年的历史,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和完善,为文人学者所接受,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如种类虽多,但比较繁杂,在形式上没有比较统一的规范,在使用时也比较混乱、随意;最大的缺陷即是如上文所述,基本只用来断句,而不能反映词句、文本的语气、感情和内部诸层次间的逻辑关系。因此,传统标点符号对于阅读效率、书籍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具有一定的负面限制作用。清末,西方书籍大量传入和流通,维新变革思潮涌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进行和开展,使西方的标点符号得到认识和重视,旧式标点符号的缺陷也在与其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经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陈望道、鲁迅等倡导,也因为社会生活、阅读实际所需,以我国传统的句读、圈点符号为基础,同时借鉴、移植西方标点符号的形式和用法,加之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形成了一套新式的标点符号,为广大作者和读者逐渐接受和使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改变了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阅读习惯。1919年11月,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和胡适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将之作为第53号训令公布,题为《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虽然颁布之后的推行工作并不顺利,但标点符号的使用总算有了一个比较统一、正式的规范。新式标点符号的推广、使用对于白话文运动,对于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证明和彰显新式标点符号的优势最直接的途径便是将之施用于文本中,特别是旧籍的整理上。因为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在旧籍整理中较早和大量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就是小说、戏曲,而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小说、戏曲的流行又促进了白话文运动的进行,两者相辅相成。这其中引领风潮的就是亚东图书馆的一系列标点本的小说。1920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汪原放标点的《水浒》,首开标点传统小说的先河。这与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新式标点符号和《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的颁布有一定的关系。之后,亚东图书馆又先后出版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多部标点本的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新式标点符号整理旧籍还包括分段和新的版式,如胡适提倡“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意思是包括:“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这三大要项,就是所谓‘整理过的本子’了。”[1]随着汪原放标点、整理的小说一纸风行,有不少出版社跟风、仿效,标点的文本也不再限于小说,但质量参差不齐,正如鲁迅在《望勿“纠正”》中所说的:“一班效颦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2]431
二、陶乐勤“重编”新式标点本《桃花扇》及其特点
《桃花扇》作为传统名剧,也有多种新式标点整理本出版。其中最早的、影响较大的是陶乐勤“重编”、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年初版的“中国名曲第一种”本《桃花扇》。平装两册,竖排繁体,分上下卷,将原剧的闰20出《闲话》改为插一出《闲话》、续40出《余韵》改为补一出《余韵》,删去原有的加21出《孤吟》。卷首有陶乐勤所作《新序》,主要评价了该剧的情节、人物,这倒符合胡适所说的“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的第三项要求。他尤其赞赏该剧的艺术笔法:“《桃花扇》的作者笔法,描写悲欢离合,直令人可歌可泣。其于社会的效能,在我看,实驾出近日所介绍西洋名曲如《华伦夫人职业》之上。其谓我中国的艺术不及西洋者,实未尝致力于国曲而得其奥者的盲评,不足为训。总之一出有一出的精彩,一人有一人的神情,忠勇节义,奸雄譌诈;热闹冷静,幽雅雄武,无不文中有物,纸中有人,可说:‘叹观止矣’!就中《却奁》《拒媒》《闲话》《守楼》《骂筵》《逃难》尤为出色;可令奸雄丧胆,正士壮气。”[3]4之所以称“重编”,是因为这一本子具有不同于其他标点本的几个特异之处:一是以原剧中生、旦、小生、副末等角色名所代表的人物的姓名或者身份代替这些角色名;二是在每出的出名之后有“布景”说明,主要介绍该出剧情发生的地点和场景,遇有场景转换的,则在剧中另加“布景”说明,这应是借鉴自翻译过来的西方剧作的文本形式;三是曲牌或词牌位于每首曲子或词的最后。如试一出《先声》的“布景”作:“赞礼之庭院。赞礼闲步庭中,同事自后入。”[3]1之后是“赞礼:‘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剩魄残魂无伴伙,时人指笑何须躲?旧恨填胸一笔抹,遇酒逢歌,随处留皆可;子孝臣忠万事妥,休思更吃人参果!’……”[3]1-2这一版本没有保留刻本中的批语,每出出名下删去原有的干支年月。“布景”的文字和曲文均为每句一行,说白则每句间接排,同一人物既有曲文,又有说白,曲白不接排。“布景”文字和曲白的首行与“布景”和人物的姓名、身份间有一个字大小的空格,其他行与首行平行。下场诗为一人所说的,两句一行;每人一句的,每句一行。同时,每行之间间隔一行的空间。以上所说的版式使得这一版本的页面显得疏朗美观,字迹清晰,没有其他版本特别是石印本因为排版过密所造成的缺陷。
陶乐勤在《新序》的最后对自己的整理原则和方法也作了说明:
校正这种旧名曲,手段各有不同。现所通认为是的,将独白割去,旁白删除。起初我也以为如此方合科学的作品。然细考以后,这种办法,实在未能苟同。因为各出都可独立,非有独白,断难使读者观者知其人物前后线索;这创造中国戏曲者的苦心思索得者,也是创作精神的结晶。至于旁白,尤不得删除;因为歌曲中的词句,有接旁白而成的。倘使删除了,那歌曲不免成了断简阙文,所以我完全不易。至于科目,因表现一种神情,是剧中要件,尤不可不详,所以特别留意,非可删者,万不可妄去;其有错误者,亦经添改。
旧本印品,差字脱句甚多,均经改正加入。但因中国的印刷业,程度尚属幼稚,不可为讳;所以合作精神尚欠圆满,以致难免错误。还望阅者匡政,俾便再板之时,加以订正。其中尤易错误的,则为旁白与词曲合在一气;而旧本未加分别,均用大号字表之。现今统为分别,凡词曲均加以“”号,以醒眉目;然犹不免相混。曲牌名用六号字,附记于词曲之末;这是我的创格。[3]4-5就实际而论,在传统戏曲剧作的标点整理方法和形式上,确有他自己的创造。后来,他还以这种形式“重编”、标点整理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汤显祖的《牡丹亭》。此外,陶乐勤还标点整理过《宣和遗事》《谐铎》《聊斋志异》《花月痕》《儿女英雄传》《两般秋雨庵随笔》《论衡》《文史通义》等大量书籍,因此,有人就认为:“自从汪原放标点了《红楼梦》《水浒》,为书贾大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于是一些书店掌柜及伙计们大投其机,忙着从故纸堆里搬出各色各样的书,都给它改头换面,标点出来,卖之四方,乐得名利双收。而尤以昆山陶乐勤对这玩意儿特别热心。”[4]28但整理戏曲剧本还不同于整理白话小说,在断句、标点时还需注意曲牌的规定和曲文的韵脚等,因此难度更大,对标点整理者的要求更高。而陶乐勤明显不熟悉古代戏曲文本,也不具有丰富的与戏曲相关的知识,所以他标点整理的戏曲文本中存在不少错误。刘大杰就曾经撰文指出陶乐勤整理的《董西厢》中的错误,并给予了他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有几句话要敬告陶君的,就是古书有古书的价值,实在是用不着我们后来的人来替他重编和改削。假使重编没有错误的时候,当然不能说减少了原书的价值;要是像陶君这样随便的重编古书,那就不仅是欺骗自己,确实是自欺欺人——一般的青年——了。欺骗了自己,当然不关紧要;欺骗了一般无辜的青年,那就可以说只想出风头、不要良心了。”[5]16
就陶乐勤标点整理的《桃花扇》而论,曾有人撰《示众》一文,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小错处”和“大错处”,认为“小错处”在书中“指不胜指”,并批评陶乐勤“不问自己懂不懂就乱七八糟的胡闹”。[4]28文中所举的“大错处”确实已经到了文意不通、读来拗口的地步,还可以看出某些错误是整理时疏忽大意错行造成的,其实谨慎认真、稍加注意就完全可以避免的。如第九出《抚兵》中的【北石榴花】曲:
你看中原豺虎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有何人勤王报主,肯把粮草缺乏?一阵阵拍手喧哗,一阵阵拍手喧哗,百忙中教我如何答话?好一似薨薨白昼闹旗拿;那督师无老将,选士皆娇娃,却教俺自撑达,却教俺自撑达,正腾腾杀气,这军粮又蜂衙![5]28
鲁迅在《示众》一文的“编者注”中说:“原作举例尚多,但还是因为纸张关系,删节了一点”,并指出“但即此也已经很可以看见标点本《桃花扇》之可怕了”[6]256。陶乐勤在《新序》中说:“旧本印品,差字脱句甚多,均经改正加入。但因中国的印刷业,程度尚属幼稚,不可为讳;所以合作精神尚欠圆满,以致难免错误。”[3]4但书中的很多错误明显是因为他自己不够谨慎、认真造成的,而且是越改越错。就如鲁迅曾经批评他在标点、整理上海梁溪图书馆1923年印行的《花月痕》时对小说文词的“纠正”:“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2]432
陶乐勤标点、整理的《桃花扇》尽管存在不少错误,却得到不断的印刷,包括翻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海大中书局1931年出版了《(新式标点)桃花扇》,书名下署“陶乐勤重编”,版权页也标明“句读者”为“昆山陶乐勤”。全书凡两册,内容文字除卷首删去原陶乐勤《新序》外,与梁溪图书馆本相同。这一版本后又于1933年再版,封面题“桃花扇”,版权页未列出标点者,也删去了陶乐勤的《新序》。全书共一册,将1931年版的两页合为一页,分上下栏。上海启智书局1932年10月翻印了大中书局1933年的再版本,版权页未列出标点者。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年也翻印了大中书局1933年的再版本,但版权页标明“标点者”为“鲍赓生”、“校阅者”为“鉴湖渔隐”,其实还是陶乐勤标点的整理本。
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出版时也采用了和陶乐勤标点的整理本相似的版式,也在每出前有“布景”说明,并新增了“时间”“地点”和“人物”,即本出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出场的主要人物,其实相当于将陶乐勤本的“布景”进行了细化、分列。《桃花扇注》也将原剧中的角色名改为该角色代表的人物的姓名或身份,每出下也没有干支年月,曲白也分排,曲文每句一行,曲牌名位于每支曲子的最后,说白则每句接排。但《桃花扇注》在断句时使用的还是旧式的圈点符号。梁启超在卷首的《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中引用《桃花扇》曲文时,也是每句一行,曲牌名位于每曲的末尾。《桃花扇注》的版式明显受到了当时的新式标点本的影响,但因为它的初版是1936年被列入《饮冰室合集》中、梁启超已经去世之时,在出版时又先经过了梁启超的侄子梁廷灿的整理,所以梁启超最初是在什么本子上作批注,为何在出版时选用这种版式,这是梁启超生前自己的意愿还是梁廷灿在整理时的选择,因为相关文献记录的缺失,已经很难考证了。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每出之首所列的“人物”中是先列剧中人物的姓名或身份,然后标明对应的扮演该人物的角色,如“老赞礼——副末”“侯方域——生”,在每出的正文中则只使用人物姓名和身份或者其简称。这种不同于古代戏曲文本的形式的更改方便了读者,使我们在阅读剧作时,能够将曲白、科介和人物直接对应,从而大大提高阅读效率。凤凰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梁启超批注本〈桃花扇〉》在保留了《桃花扇注》原有的每出前新增的几项说明的同时,又将剧作正文中的人物姓名、身份或其简称改回了对应的脚色名,反而不方便读者阅读。而且,该版本中错别字很多,标点也有很多不妥之处,还不如《饮冰室合集》本方便读者使用,此不赘述。
三、其他民国间新式标点本《桃花扇》
《桃花扇》的新式标点本除了陶乐勤标点、整理本的系统之外,还有其他版式的本子。如上海广益书局1933年初版的《(新式标点)桃花扇》,平装,全一册,竖排繁体,版权页标明“标点者”为“南汇朱益明”。这一标点本与陶乐勤本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卷首有多篇文字,如顾彩序、吴穆的《后序》、沈成垣的《重刊〈桃花扇〉小引》、朱太忙的《标点〈桃花扇〉序》《〈桃花扇〉考证》、田雯等的《题辞》、黄元治等的《跋语》、孔尚任的《小引》《凡例》《纲领》《砌抹》《考据》《本末》《小识》,偶见错误,如“淮南李柟”误作“淮南李相”;第二,保留了刻本中的眉批和出批,但条目不全,眉批未加标点、断句;第三,剧作正文文字除删去每出出目下的干支年月外,其他与刻本全同,曲白以字号大小区分,曲文和说白分排,多个人物、脚色的说白接排。《题辞》中除刻本原有的篇数外,最后为近人味芩和丹徒李吟白所作的几首。味芩所作原载录于《民权素》第三期,题为《读〈桃花扇传奇〉》,广益书局本收录时删去了最后一首:“几人遗臭几留芳,名节长存壮悔堂。劫后秣陵重吊古,渡江桃叶又归王。”[7]李吟白所作原载录于《春柳》,题为《题〈桃花扇〉院本》,广益书局本收录时删去了第一首:“艳说秦淮水一钩,媚香楼胜顾迷楼。诸君也自耽声色,争怕官家不解愁。”[8]《〈桃花扇〉考证》包括多种笔记、曲话类著作中评论《桃花扇》的文字,其中有几篇的原书较为罕见,故引录于下:
吴梅村《怀古吊侯朝宗》一首云:“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掇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终负侯嬴诺,欲滴椒江泪满襟。”自注:“朝宗遗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骏公自责甚是,而朝宗不足以当之。骏公之出山,初非本心,实系被逼而然。朝宗固未仕清,然贻书约隐于先,又何以应乡举于后?朝宗亦幸而早世耳!而不然者,其收局盖可知矣。张船山诗有云:“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洵是定论。孔云亭《桃花扇传奇》,叙事最称翔实,顾于朝宗之本末独否,岂其香君故,曲为讳饰与?何朝宗之幸也![9]18-19——《毗梨耶室随笔》
明季张可大,上元人也,总兵登莱。袁崇焕杀毛文龙,将卒反,执巡抚孙元化,可大死之。事闻,以其子诸生薇字瑶星,授锦衣卫千户。甲申,流贼陷京师,瑶星不屈,贼械系之,乃罄所有以予贼,得释。其妻已先死,归里后,寄居山中僧舍,不入城市,乡人称为白云先生。今以《桃花扇》演弘光朝,授薇为锦衣卫,阮大铖委鞫朝宗事,挂冠而逃,卒年八十有八。[9]21——《销夏闲记》
曲阜孔尚任作《桃花扇传奇》,无锡顾彩又作《南桃花扇》,所衍亦侯朝宗事。尚任以张薇出家白云庵,为侯李说法,二人醒悟修行,分住南北二山结局;此改朝宗挈姬北归,白头偕老。按朝宗于顺治癸卯,尚应秋试,顾氏改之,不为无见。剧中诸人姓名履历,亦真实不虚,惟关目颇多增饰,事迹尝加扭合,盖才力不逮云亭远矣。《小说丛考》云:“今坊间只有云亭之作,而《南桃花扇》不多见。盖小说收束,最忌团圆,如读《西厢记》,至崔张花烛一回,更有何趣味也?”[9]25——《见山楼丛录》
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4年翻印了广益书局版的《(新式标点)桃花扇》,封面题“言情词藻传奇说部桃花扇”,版权页上的书名为“新式标点桃花扇”,标点者为朱益明。1935年再版时,版权页上又删去了“标点者”一行。
以上所提及的版本尤其是标点本多数当时都在一年或数年内多次重印,可见《桃花扇》的受欢迎程度和读者阅读的需要。新式标点整理本后出,而版本更多,重印次数也更多,可见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大势所趋,同时又促进了《桃花扇》的传播和接受。其中有多个出版社先后印行过无标点本和新式标点本,如广益书局1920年曾印行《桃花扇》无标点、铅印、平装一册。本文所提及的《桃花扇》的民国间的版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也可说是优点:第一,多数都保留、载录了刻本卷首和卷末的文字篇章,即序跋、题辞和孔尚任所作的《小引》《凡例》《纲领》《砌抹》《考据》《本末》《小识》等;第二,绝大多数都保留、载录了刻本中的眉批和出批,虽然条目不全,但多数是为了表示该版本收录完备,用以招徕读者,促进销售。这两点使这些版本保留了原刻本的面貌,序跋等文字和批语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桃花扇》的创作过程、创作主旨和艺术构思以及更好、更细致深入地阅读、欣赏、理解剧作。王季思先生等的校注本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最为流行的《桃花扇》的整理本,这一版本为普及之用而删去了原刻本中的批语,这尚且可以理解,但删去包括吴穆《后序》在内的跋语和孔尚任的《题辞》《砌抹》,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和缺陷了。《桃花扇》民国间的版本也有缺陷,主要的就是没有收集多种刻本进行仔细、认真的校勘,有些版本标明经过了“校正”“校阅”“重校”,实际上应该都没有进行这些工作,至多只是就一种刻本改正了自己认为的不妥之处或错别字,然后印行。
总之,《桃花扇》民国间的版本尤其是标点整理本促进了《桃花扇》在当时的流传和接受,促进了当时对于该剧的评论和研究,也促进了这部蕴含“兴亡之感”、爱国情怀的名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积极的激励人心的作用。这是应该加以积极肯定的。《桃花扇》在民国时期的出版印行也是其接受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同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评论、研究的开展也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1]胡适口述自传[M].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
[2]鲁迅.热风[M]//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中国名曲第一种)桃花扇[M].陶乐勤,重编.上海:上海梁溪图书馆,1924.
[4]育熙.示众[J].语丝,1928,(16):28.
[5]刘大杰.《董西厢》上面的错误——告重编者陶君乐勤[J].现代评论,1925,(23):16.
[6]鲁迅.《示众》编者注[M]//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味芩.读《桃花扇传奇》[J].民权素,1914,(3):4.
[8]李吟白.题《桃花扇》院本[J].春柳,1919,(6):615.
[9](新式标点)桃花扇[M].朱益明,标点.上海:广益书局,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