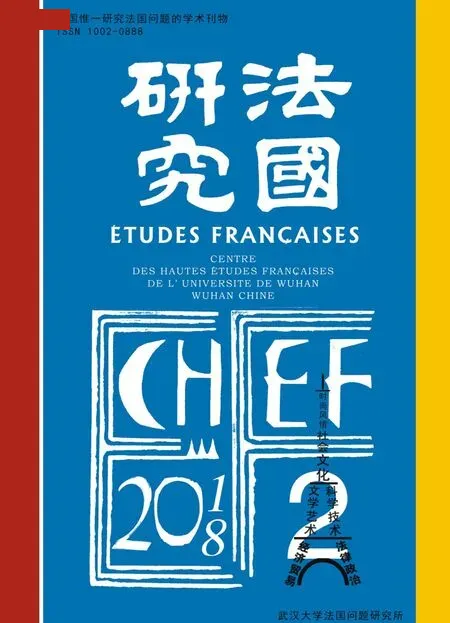孤岛求生:从社会历史语境解读魁北克法语的生存与发展
陈燕萍
孤岛求生:从社会历史语境解读魁北克法语的生存与发展
陈燕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魁北克的语言问题非常复杂和具有争议性。这种复杂性和争议性来自魁北克特殊的社会历史处境。作为民族集体身份认同核心的语言与法裔加拿大民族有着相同的遭遇和命运,魁北克法语的历史就是一部法裔加拿大民族的生存斗争史。魁北克法语经受了四百年的生存考验,克服了种种危机,它既承载了古老欧洲的历史,保留了法语的古老韵味,又汲取了新大陆的养分,体现了北美大陆的社会变迁。当今的魁北克法语一方面向标准化法语靠近,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构成了法语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Résumé]Étroitement liée à la situation socio-historique du Québec, la question de la langue a toujours été au coeur des préoccupations des Canadiens français. La langue française a connu le même destin que les Canadiens français qui ont dû lutter pour leur survie. L’histoire du Québec decide la survi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ainsi que son évolution. A travers plus de 400 ans de dures épreuves, le français continue de rayonner sur le continent de l’Amérique du Nord. Tout en conservant les charmes du vieux français et en se conformant à la norme, le français au Québec puise aussi dans les sources du Nouveau Monde, constitue ainsi un paysage à part dans le monde de la francophonie.
魁北克法语 语言问题 历史境遇 生存 身份认同
魁北克位于加拿大的东部地区, 约800万人口,占加拿大人口的将近25%,是加拿大唯一一个以法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省份,也是欧洲以外唯一一个以法语为一个民族的母语的地区。法语人口在魁北克占绝大多数,94,6%的人口都懂法语,而其中79%的人口的母语是法语。魁北克的语言问题非常复杂和具有争议性。这种复杂性和争议性来自魁北克特殊的社会历史处境。可以说魁北克的历史境遇决定了魁北克法语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特点。
一、魁北克法语的历史与境遇
1759年,在魁北克的亚伯拉罕平原(plaines d’Abraham),蒙卡勒姆①(Montcalm)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被伍尔夫②(Wolf)率领的英军打败。这场仅持续半小时的战役彻底改变了法裔加拿大人的命运:1763年,英法签署“巴黎条约”(le traité de Paris),新法兰西(La Nouvelle-France)归英国统治,成为英国在北美的第15个省——“魁北克省”。生活在加拿大的法国人由统治者变成了被征服者。法语和天主教被禁止,原先的法律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英国人的法律。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权利和地位,经济处境困难,教育处于无序状态,骨干和社会精英纷纷离去,也不再有新的移民和访客;留在北美大陆的法国人像是被母亲抛弃的孩子,被遗弃在圣-洛朗河(Saint-Laurent)沿岸,生活在英裔加拿大人的包围中,加上英国统治者施行的同化政策,法裔加拿大人面临民族消亡的危机,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一样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
从那时起,保障民族生存成了法裔加拿大人的首要任务。语言,种族, 宗教是集体身份认同的三要素。而语言更被视为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因为语言超越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其它因素,可以命名、表达和传播这些因素③;同时,相对于其它因素,语言是界定一个民族更为直观的标准:“语言是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差异性的外在和可见的标志;它是一个民族被承认生存和拥有建立自己国家和权力所依据的最为重要的标准。”④法裔加拿大人因为语言在北美大陆显得格外孤独,但也正是这一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语言赋予了法裔加拿大人区别于北美其他民族的特质。对于在英裔加拿大人的包围中艰难求生、时刻担心被同化的法裔加拿大人来说,作为民族身份认同核心的语言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可以说法裔加拿大民族的命运和他们的语言紧紧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四百多年来,作为法裔加拿大民族集体身份认同核心的魁北克法语与法裔加拿大民族承受了相同的命运和境遇。可以说,魁北克法语的历史就是一部法裔加拿大民族的生存斗争史。
1608年魁北克城建立后,法国移民陆陆续续来到圣洛朗河两岸安家。而大批法国移民来到加拿大则是1663年以后,这些移民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到1763年法国将加拿大让给英国的时候,有将近65000法裔加拿大人。这些移民中的三分之一来自诺曼底,三分之一来自法兰西岛,其余来自西南的奥依语(Langue d’oïl)地区。⑤魁北克法语的基础主要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叶的法国民间用语和口语,接近巴黎市民普通用语,与当时的标准法语即宫廷用语相差甚远。当时为给新法兰西增添人口,一批被称为“国王的女儿们”的单身女性移民来到加拿大嫁给那里的法国移民。随着她们的到来,巴黎的通俗法语就成了新法兰西的通用语。一直到了1763年大征服时期,80%以上的法国移民使用的都是一种本地标准化的法语,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法裔加拿大已经现实了语言的统一,而法国却直到1910年才正式获得了统一的语言形式。⑥
如果说法裔加拿大人由于生活在政治、经济和人口都占绝对优势的英裔加拿大人的包围中而时刻面临被同化的危险;那么作为法裔加拿大人民族身份重要象征的法语同样危机四伏,由于完全暴露在使用世界上最强大的语言的英语人群中,他们的语言环境十分脆弱。在大征服初期,为了保障民族生存,不被同化,法裔加拿大人选择远离英裔占多数的城市,退居到乡村,过着封闭的农耕生活。而这一保守的对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语,使它得以免受外界的干扰。
可以说英裔统治的第一个百年,英法两个族群接触很少,在各自的地盘上过得相安无事。但是城市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相对平静的状态。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1960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给法裔加拿大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方面,由于法裔加拿大人此前一直过着远离城市的农耕生活,加上大征服后将近半个世纪连学校都没有,⑦他们无从学习技术。到了1838年法裔加拿大人暴动⑧失败后,教育完全掌握在教会手中,教会着重培养自由职业特别是神职人员,而忽视商业和技术教育。因此,进入城市的法裔加拿大人只能在城市的最底层工作,干一些粗活,成了“挑水工”和为“一小块面包而生”的人。移居城市的法裔加拿大人的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从相对独立自由的农民变成了依附英裔加拿大人的下等人。另一方面,向城市过渡给法裔加拿大人带来心理上的强烈冲击:他们像是突然被连根拔起的植物被从乡村移植到了陌生的城市,无所适从,毫无安全感。而令法裔加拿大人的这种无产阶级化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老板—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绝对优势的英裔加拿大人属于另一种文化,说另一种语言。法裔加拿大人的身份危机也由此产生,他们不仅沦为“被统治者,无力改变自己身份的少数群体,穷人,无知者……,”而且成了“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家乡,过去,文化甚至语言。”⑨
这一民族生存状态自然反映到作为集体身份认同核心的语言中。城市化给法裔加拿大人带来集体身份危机,处于身份认同核心的语言自然不能幸免。法裔加拿大人堪忧的生存状态无疑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语言环境雪上加霜。由于进入城市后,法裔加拿大人与英裔接触日益频繁,又几乎处于英语语境的包围中,英语大量渗透到法语中,对法语造成很大冲击和破坏,语言问题开始进入法裔加拿大人的集体意识。如果说在大征服后将近百年法裔加拿大人一直为自己说的是博絮埃(Bossuet)和拉辛(Racine)的语言而感到骄傲的话,那么19世纪城市化开始,他们的语言自豪感随着语言质量的下降渐渐消失甚至变成了一种负面因素,一种对自身的否定和羞耻。
对法语状况恶化的最早担忧出现在19世纪初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主要是担心英语对法语的侵蚀。但法语危机真正出现是在19世纪后半期,当时,来加拿大旅游的外国游客,包括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现魁北克的法语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别,甚至有人认为法裔加拿大人说的不是“真正的法语”,而是一种可笑的方言。
这一语言差异主要是由法裔加拿大社会特殊的历史境遇和生活环境造成的。
1763年加拿大归英国所有后,由于法裔加拿大与法国的联系被切断,法语在魁北克和法国分别独自发展,两边都出现不同的变化,尤其是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如一些词在魁北克法语中仍然保留17世纪的发音,而在法国这种发音却早已消失。其次,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一些植物、动物名称的使用对象发生变化,同一名称的所指并不完全相同,而是经常被用在类似的动植物上。此外,在新的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法裔加拿大人需要借用许多印第安语或自己创造一些新词。另一个现象是魁北克法语中的词汇变得贫乏。由于大部分移民都很年轻,在15-25岁之间,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技术用语掌握不够;另一方面,由于法属北美殖民地17世纪生活条件的局限,许多与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奢侈相关的行业和手工业根本无用武之地,再加上教育条件有限,常常出现一词多义的现象,如工人可以被用来指锅炉工,铁匠, 枪炮匠等在法国非常专业化的职业。
但是对魁北克法语词汇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英语借用的逐步植入。大征服后,也就是从18世纪开始,魁北克与法国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无论是技术还是制度的创新都是通过英国人而后是美国人传入法裔加拿大。结果在法律, 政治机构以及经济等领域很快英语化。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之前一直聚集在乡村的法裔加拿大人涌入城市,以及与英裔居民的接触大大增加,英语的渗透加强了。而法国也从18世纪开始吸收英语词汇。但魁北克借用的英语词语与法国借用的英语词语并不相同,此外,处于英语语境包围中的魁北克法语中的英语借用也比法语中的借用多得多,这也拉大了魁北克法语与法国法语之间的差距。到了20世纪,英语在加拿大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整个北美都是英语的天下,法语成了一门可以听懂、读懂而不是大家都使用的语言。
不断受英语冲击的法语在各个层面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退化。不仅语言本身状况不断恶化,它的地位也因法裔加拿大人“二等公民”的处境不断下降。魁北克著名民族主义女诗人拉龙德(Lalonde)就以《说白人话》()⑩为标题写了一首当时被人们竞相传颂的诗来揭示当时法裔加拿大人类似白人殖民者统治下的黑人一样的处境:他们不能说自己的语言,而要说“白人话”——即他们的主人的语言——英语。生活在社会底层,干着粗活的法裔加拿大人的语言沦为了下等人的语言,而英语则成了象征权力和金钱的语言。
严重受损变质的语言状态给法裔加拿大人敲响了警种,语言危机令他们深感不安:如果他们的语言失去法语的特点成了一种方言,那么他们就等于失去了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不再属于法语文化的一份子,这将引发更加严重的集体身份危机。魁北克人意识到了语言的兴衰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魁北克平静革命(la Révolution tranquille)时期,⑪作为民族身份认同核心因素的语言问题成了魁北克社会的关注焦点。
二、儒阿尔语(joual⑫)之争
魁北克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围绕魁北克的语言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其中最著名的一场语言论战是围绕儒阿尔语展开的。1960年,魁北克作家和知识分子让-保罗·德比安(Jean-Paul Desbiens)在他的一篇题为“某兄的出言不逊”()的文章中借在学生中间大量使用的儒阿尔语现象尖锐地指出了魁北克法语的严重受损状态,他对魁北克语言状况的日益恶化象十分担忧。在他看来,“儒阿尔语”“这一语言缺失”已经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这一扭曲畸形的语言是法裔加拿大人自身生存状态的写照,是异化的法裔加拿大民族的形象:“无法自我肯定,我们对未来的拒绝,我们对过去的迷恋,所有这一切都在儒阿尔语中反映出来,这真的是我们的语言。”⑬
让-保罗·德比安的这篇抨击文章在魁北克引发了民族主义思潮,作为民族身份象征的语言问题很快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语言上的缺失被看作一种知识甚至精神的缺失。人们意识到儒阿尔语实际上象征了法裔加拿大人所拒绝的自身的东西:殖民状态(英语化的语言),文化上的落后(古语),教育的缺失(句法,法语词汇上的无知),不文雅(粗俗),文化上的孤立(外人听不懂的语言),失去根基,甚至身份认同(语言的解构,瓦解,退化,分解等)……它是魁北克语言的“殖民化版本”(version colonisée),是和社会政治异化密不可分的语言的异化,反映了魁北克社会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衰退和变质,是法裔加拿大人集体异化的一种标志。正如魁北克知识分子让-马塞尔·帕盖特(Jean-Marcel Paquette)在一篇题为“特洛伊儒阿尔”()的文章中所说:“儒阿尔语从19世纪开始小步前行,随着魁北克居民的无产阶级化飞奔前进。从这个时候起,它不再只是一只无害的小动物,也不仅仅是语言了,而是异化的整个条件反射行为,语言只是它们的载体。”⑭
围绕如何对待儒阿尔语,魁北克社会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对者认为儒阿尔语是一种萎靡颓废,贫乏的次语言,用它写作会显得滑稽可笑,没有可读性,使用这样的语言无异于玷污了自己的母语。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倡导把儒阿尔语当作一种政治武器,尝试通过用儒阿尔语写作让魁北克人意识到自身的可悲处境。米歇尔·特朗布雷(Michel Tremblay)就是第一个在魁北克文学作品中赋予儒阿尔语完整地位的作家。
1965年,特朗布雷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戏剧《妯娌们》()。这部戏剧将十五个在现实生活中被忽略、没有话语权的魁北克普通女性搬上舞台。这部戏剧最独特的地方是作者大胆运用被认为粗俗、不雅的儒阿尔语作为戏剧语言,剧中人物除了一人说的是勉勉强强的欧式法语之外,其他人都说儒阿尔语。由于使用了儒阿尔语,这部戏剧最初遭到剧院的拒绝,直到1968年,才在蒙特利尔的绿幕剧院(Théâtre du Rideau Vert)上演。这一演出在一片赞赏、惊讶、反对声中获得很大成功,成为魁北克戏剧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反对者认为这部戏简直就是一件丑闻,无论是语言还是表现的人物和主题都很粗俗,不登大雅之堂。他们担心人们会利用这部作品,“传播这种语言并将它制度化”,虽然引进巴黎法语并不可取,但他们认为使魁北克口语更加“克里奥尔化”(créolisé)同样不幸。支持者则认为这部戏对魁北克异化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必要的揭露。特朗布雷让人物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使得作品更加真实可信,大大增强了戏剧效果,是对此前魁北克既非法语亦非儒阿尔语的折中戏剧的一种突破。
特朗布雷认为儒阿尔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也是魁北克社会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反映。使用儒阿尔语或者民间用语是写出与魁北克现实相符的作品所必需的。针对《妯娌们》招致的质疑和批评,他这样为自己辩护:“在世界各国都有人用儒阿尔语写作,甚至他们最成功的作品就是用儒阿尔语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就不行。”⑮在这里,特朗布雷表达了自己对享有差异权的诉求,而这也反映了平静革命时期魁北克人对身份认同的追求。特朗布雷曾对《世界报》(的记者这样说过“我们希望以我们的不同被承认。”⑯他认为魁北克应该享有文化差异的权利,使用统一的国际化法语是可笑的:“我觉得这一法语的完全国际主义是病态的。是一种自我殖民主义。法国从来没有要求魁北克文化成为一种次法国文化。为了模仿另一种文化而忘记自己真的太可笑了……”他“想要成为世界法语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想成为一个次法国人。”⑰
然而,特朗布雷使用儒阿尔语并非为了将魁北克人禁锢在儒阿尔语的使用中,他最初的意图是唤起人们对儒阿尔语的意识:“我所做的是一种觉悟。”⑱这种语言意识的觉醒无疑得得益于平静革命给魁北克社会带来的重大变化和在此氛围中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因为正如特朗布雷所说的魁北克人“以前没有这个权力,几乎没有。”⑲
应该指出的是,平静革命时期,魁北克作家使用儒阿尔语的目的不是为了将它合法化,而是让人们通过语言意识的觉醒认识到改变这一状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是为了呼吁改变这种语言所代表的魁北克人卑微的处境,即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因此,儒阿尔语的使用只是过渡性的,正如著名魁北克诗人雅克·布罗(Jacques Brault)所说:“儒阿尔语身上背负的肯定不是我们的文化未来,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是把它从身体中除去,我们自己将这一令人窒息的坏疽连根拔掉。……如果革命(特别是文学革命)要经过它来实现,那么应该从中走出来也让我们尽早走出来。”⑳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到了1980后,随着民族问题的淡化,这一现象也逐渐淡出,作家们重新使用国际通用的法语写作,不再需要通过语言来彰显自己的文化属性。
三、语言保护措施
面对法语语言令人堪忧的现状,法裔加拿大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自己语言的生存和发展。1960年初,魁北克设立了法语语言局(Offic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成立了不同的团体机构来研究法语在魁北克的使用情况,并负责检查法语的质量。魁北克历届政府都为保护和推广法语纷纷立法。1966-1968,约翰逊政府把法语变成魁北克主要语言。 然而,由于1969年制定的63法(la Loi 63)允许家长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受教育的语言,大部分移民都选择了英语学校,面对这一现象,为了推广法语在魁北克的应用,1974年,魁北克省议会通过了《官方语言法》(la Loi 22),布拉萨(Robert Bourassa)的自由党政府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法语在魁北克的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规定法语为教育、经商、张贴告示的语言。但是由于这一法规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所以结果无论是英裔加拿大人还是法裔加拿大人双方都不满意。1977年魁北克人党执政的魁北克政府通过了《法语宪章》即101法案(la Loi 101)。魁北克人党把法语作为魁北克的唯一官方语言,规定全体魁北克公民都有权说法语,用法语工作,接受法语教育,享受法语服务。法语全面应用在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公共服务部门,劳动部门,商业活动和教育部门,规定公告必需只用法语,而对企业语言的使用也作了明确规定:50个及以上员工的企业必需使用法语,并对其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合格后颁发“法语化证书”。[21]1980年仅有7.7%的企业获得这一证书,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持续维持在70%以上。可见这一举措对确保法语在魁北克的垄断地位确实非常有效。
在教育方面,中小学阶段除少数特例,魁北克的孩子必需都上法语学校,中学以后才可以自由选择。这一举措使得原先选择英语学校的移民不得不上法语学校,这不仅保证了法语在魁北克英法裔群体中的地位,同时也促进了母语是非英语或非法语的社团的法语化。此外,法语化措施也体现在移民政策中:在选择移民身份的标准上,如“魁北克选择技术移民计分表”中,法语掌握程度的分值是0-16分,要远远大于英语掌握度0-6的分值。这样,就确保了新移民中有一定比例母语为法语的居民。[22]同时,政府还免费为新移民提供各种法语语言培训课程。所有这些举措都对保护法语语言在魁北克的权利和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魁北克政府的努力下,魁北克法语语言本身的状况也得到改善。从1960年开始之前不断扩大的英语化减退;此外,随着与法国接触的增加,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口的旅游等途径,以及在教育方面的重视,在语音和词汇方面的魁北克地方特色褪去不少,更加向标准化法语靠近。从20世纪初开始,美洲印第安语在魁北克法语中的影响部分消失了。[23]
在经历了平静革命重拾信心和尊严的魁北克人在语言上的自卑情结逐渐消失,他们积极参与定义世界各地共同的法语语言标准,一方面向标准化法语靠近,另一方面,他们追求属于自己特有的文化属性,保持选择差异的权力,在语言中保留了自身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在语音和词汇上。到了20世纪末,尽管魁北克人对自己的语言状态还不是完全满意,但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的语言特色看作是文化衰退的象征,也不再为自己的语言感到羞愧,取而代之的是自信和自豪感。
四、结语
魁北克法语经历了四百年风云变幻,经受了社会历史变迁带来的种种考验,在美洲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并在那里落地生根,顽强绽放。它既保留了法语的古老韵味,同时汲取了新大陆的养分;它承载了古老欧洲的历史,也体现了北美大陆的社会变迁,是法语世界一道不可或缺的独特的风景。
① Montcalm Saint-Véran,Louis—Joseph,(1712-1759),法国将军。1756年任新法兰西法军指挥官,率领法军多次打败英军,在1759年亚伯拉罕平保卫魁北克的战役中重伤身亡。
②Wolf, James,(1727-1759),英军指挥官,带领英军打败法军,取得亚伯拉罕平地战役的胜利,但和蒙卡尔姆一样在这次决定加拿大命运的战役中阵亡。
③参考Abou, Selim.. Paris : Anthropos, 1981, p.33.
④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58页。
⑤Bouchard,Chantal.. Montréal: Fides, 2002, p.43-44.
⑥Bouchard,Chantal.. Montréal: Fides, 2002, p.45.
⑦即使在1801年学校恢复后,这些学校是英语学校由英联邦政府资助,直到1837年暴动,学校从85所减少到5所。参见:Paquette, Jean-Marcel. “le Joual de Troie.”,Ed. Dir Heinz Weinmann et Roger. Montréal: HMH, 1996, p.201.
⑧大征服之后,法裔加拿大人虽然为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力和经济权益与英裔统治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却屡屡受挫。1837年,由于法裔加拿大代表提交给伦敦的92项争取权益的决议全部被否决,法裔加拿大人举行了武装暴动,然而终因寡不敌众再次惨败。
⑨Bouchard,Chantal.. Montréal: Fides, 2002, p.81.
⑩ “speak white”出自1889年10月12日加拿大联邦众议院的一场辩论。法裔议员亨利·布拉萨(Henri Bourassa)在发言时被英裔议员用嘘声打断,当他试图用法语解释时,下面的人叫喊:“speak white!”。从此,这句话成了二十世纪60年代以前英裔加拿大人对法裔加拿大人在公共场合说法语时说的一句侮辱性的话:即让他们不要说法语,要说白人话——英语。
⑪狭义上的平静革命是指1960-1966年间由让·勒萨日(Jean Lesage)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政府进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改革。广义上来说,用来形容新自由主义和新民族主义取得胜利,魁北克各个交接政府指导方向保持连续性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魁北克社会。
⑫“joual”这个词最先是由安德烈·洛朗多(André Laurendeau)提出来的,他把周围的青少年所说的语言称作“joual”,是法语“cheval”(马)的松垮的发音。现在的“joual”泛指蒙特利尔城市工人区说的法语,在发音、词汇、句法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的法语。
⑬Desbiens, Jean-Paul. “Les Insolences du Frère Untel.”,Ed. Dir Heinz Weinmann et Roger. Montréal: HMH, 1996, p. 204.
⑭Paquette, Jean-Marcel. “le Joual de Troie.”,Ed. Dir Heinz Weinmann et Roger. Montréal: HMH, 1996, p.201-202.
⑮Tremblay, Michel. “Mon Dieu que je les aime, ces gens-là !” Ed. Claude Gingras,. le 16 aôut 1969, p. 26.
⑯Zand, Nicole, ed. “Michel Tremblay, un Québécois défenseur de la différence.”. 9 novembre 1979.
⑰ Zand, Nicole, ed. “Michel Tremblay, un Québécois défenseur de la différence.”. 9 novembre 1979.
⑱Tremblay, Michel. “Mon Dieu que je les aime, ces gens-là !” Ed. Claude Gingras,. le 16 aôut 1969, p. 26.
⑲Tremblay, Michel. “Mon Dieu que je les aime, ces gens-là !” Ed. Claude Gingras,. le 16 aôut 1969, p. 26.
⑳Brault, Jacques. “Le joual: moment historique ou ‘l’aliénation linguistique’?”30 octobre 1965.
[21]王助:“魁北克社会的移民与法语双重属性”,载《加拿大研究》(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26页。
[22]王助:“魁北克社会的移民与法语双重属性”,载《加拿大研究》(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26页。
[23]Bouchard,Chantal.. Montréal: Fides, 2002, p.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