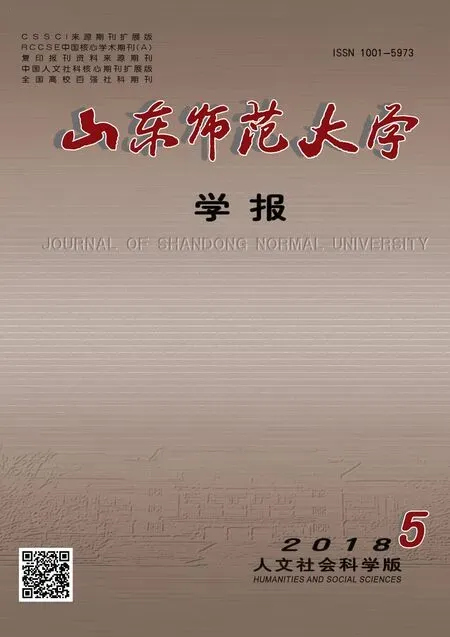“立德树人”与新时代中国美育话语的现代性营构*①
陈 剑
( 山东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中国美育话语的现代性问题是推动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20世纪上半叶异彩纷呈的中国现代美育思潮,就是在回应这一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问题依然是当代美育思想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在立足于新的时代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美育思想的现代性建设,实现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的民族化与全球化,是当下美育建设的重要任务。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大都是以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史研究为依托,从“启蒙”的角度来讨论美育的现代性问题,如金雅的《为什么重提“人生艺术化”》、徐碧辉的《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20世纪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于文杰的《现代形式与儒学精神——在比较中寻求中国美育现代性的发展与重建》、王德胜的《“以文化人”:现代美育的精神涵养功能——一种基于功能论立场的思考》*金雅:《为什么重提“人生艺术化”》,《艺术百家》2012年第6期;徐碧辉:《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20世纪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于文杰:《现代形式与儒学精神——在比较中寻求中国美育现代性的发展与重建》,《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王德胜:《“以文化人”:现代美育的精神涵养功能——一种基于功能论立场的思考》,《美育学刊》2017年第3期。,而从新时代语境与教育需求的角度来探讨美育现代性建构与发展的成果则少之又少。在此情况下,本文从“立德树人”的新时代文化教育语境出发,对当代美育理论的现代性建构进行重新审视,以期探索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美育话语的本土现代性路径,为当下美育思想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一、中国美育话语现代性发展的“启蒙”思路及其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的困境
美育的现代性是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同时也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从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美育现代性的讨论,主要是在“启蒙”的框架中进行的,着重探讨中国现代美育在“启蒙”潮流中的独特形式和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来呈现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具体来说,这种研究模式主要以中国美育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为依托,通过对中国美育现代性历史轨迹的梳理来彰显中国美育现代性的“启蒙”内涵,并将其作为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加以推广。比如杜卫曾明确指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感性启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不仅有以理智为中心的理性启蒙思想(如标举‘民主’、‘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还有一条以情感为中心的‘感性启蒙’的思路,后者是颇具中国特殊性的。”[注]杜卫:《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而这种“感性启蒙”之所以成立,主要是由于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对西方美育思想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原本以修正甚至颠覆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席勒、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美学到了中国变成了从感性情感方面重建国民性、启发国人心智、重建国人道德的重要思想资源。”[注]杜卫:《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通过艺术和审美来洗刷人心、提升人性,进而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是“感性启蒙”的基本路径,这一路径与倡导“民主”与“科学”的理性启蒙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启蒙的基本格局。杜卫认为,这种“感性启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现代性意义之所在,同时它也应该成为中国当代美育建设最直接的资源。徐碧辉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她认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进程实质上是一种“审美启蒙”,这与所谓的“社会启蒙”相对:“陈独秀、胡适等人进行的是社会启蒙,他们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正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或要素……二者都是从社会群体价值层面上进行的精神启蒙。而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的目标同样是要通过审美来改造人心,拯救社会。不同的是,他们是从对个体的心灵改造入手进行启蒙的。”[注]徐碧辉:《美学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20世纪中国的审美现代性问题》,《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与杜、徐二人对于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启蒙特征的总结不同,于文杰是在对中国美育的现代性问题史进行细致梳理之后,直截了当地将启蒙理性注入到美育现代性的营构之中,并且将其与现代儒学知性精神的重构联系起来,作为中国美育现代性发展的未来方向加以宣扬:“中国缺少西方国家的科技现代性进程,所以现代中国需要传统儒学中的知性精神,又需要现代西方的科学精神。因此,民族国家的进步期待着科学精神的张扬。尽管普通教育注重人的道德与情操等方面的人文素质,而对于整个民族教育来说,美育还必须担当起知性启蒙的使命。”[注]于文杰:《通往德性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这种明确地将科学、理性置于美育现代性发展的核心位置上的做法,是目前关于中国美育现代性建构之启蒙路径最有代表性的做法。
一方面,从“启蒙”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美育的现代性问题,将中国美育现代性的历史经验总结为“感性启蒙”或“审美启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学术呈现,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如果由此而将“启蒙”作为中国美育现代性建构的核心,并且将其延伸到新时代的美育现代性营构之中,则是有失偏颇的做法。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立足于新时代的文化语境而得出的结论。谭好哲曾指出:“任何话语行为都是生成于具体的语境之中的,语境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必然造成话语构成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美学现代性问题自然也不例外。”[注]谭好哲:《语境意识与美学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美学或美育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必须树立明确的语境意识,从具体现实的文化语境出发,来确立美学或美育现代性的本土化路径。从这个角度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启蒙性话语逐渐退守到了边缘的位置,超越性的精英文化也不再是时代文化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于执着于美育现代性建设的“启蒙”维度,则会加剧美育的边缘化地位,最终使其成为凌空高蹈的文化形式;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社会观念的变革,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道德沦丧、信仰缺失、人性分裂与堕落等现代文化弊病也逐渐蔓延开来,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以崇尚理性的“启蒙”思路来营构美育,这对很多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来说将是十分无力的;此外,也是最重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也产生了新的时代指向,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和践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在客观上要求统一决策、统一规划,要求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引导之下凝聚民族力量,要求美学、美育研究必须纳入到国家设计的层面上,与其他文化形式一道共同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所有这些问题和任务,是远非一个“启蒙”所能涵盖和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一味固守“启蒙”的单一化思路,美育建设则会难以融入到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之中,也就无法在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发挥自身应有的价值和功用。因此,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需要在吸收“启蒙”思路合理内涵的前提下,以新时代现实的文化语境为出发点,去寻求更为现实有效的现代性发展路径,这应该成为新时代美育建设的主导性方向。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敏锐地作出了反应。曾繁仁就曾指出,应该从美育在现代知识经济所需要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现代化建设以及美育对现代社会中人文精神的补缺等方面来推进审美教育的现代性建设。[注]曾繁仁:《美学之思》,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1-622页。孔新苗也认为,应该“将传统美育围绕感性/理性、个体/社会、审美/现实二元对立的审美解放论范式,置换为对‘精神生产’中的生产/消费、编码/解码、治理/自塑的文化研究范式”[注]孔新苗:《美育:现代性问题意识中的人文理想与文化治理实践》,《艺术百家》2016年第4期。,使美育在现代社会的“文化治理”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这都是明显不同于“启蒙”思路的新的美育现代性建构路径,对美育现代性的建设和研究有着重要启示。当然,以曾、孔为代表的学术观念在整体的学术语境中还是为数不多的思想之“点”,要想由“点”成“面”,进而促成对美育现代性研究“启蒙”框架的实质性跨越,还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需要大家付出更多的努力。新时代的美育研究者,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的文化语境,寻求中国美育现代性研究与建设的新突破。
二、“德性”与“民族”:“立德树人”为新时代中国美育话语现代性营构确立的两个理论生长基点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理论建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习近平同志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注]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2014年5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注]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10日。(2014年9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张烁:《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2016年12月)、《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注]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青年报》2018年5月3日。(2018年5月)等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宗旨与核心任务之所在,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重要论断,这就为新时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总体的方向,同时也为新时代美育理念的创新提供了现实的理论触发点。可以说,“立德树人”一方面是面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文化对策,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它又是立足于民族复兴的时代任务,代表了时代对中国教育的最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将美育理论建设与“立德树人”联系起来,在“立德树人”精神的引领之下营构中国美育的现代性形态,不仅能够使其切合时代语境,贴近现实,融入现实,同时也可以通过教育特性的凸显将其纳入国家制度轨道,在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发展中寻求自身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空间,这对美育现代性建设固有路径的突破及其更大发展空间的营造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
鉴于“立德树人”在新时代教育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一理念的阐释性成果,一时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有不少学者倾向于从并列或相互补充的角度来谈论其理论旨归:“‘立德树人’在构词上应该被视为联合结构。一方面,立德是树人的前提,树人是立德的归宿,立德最终是为了树人;另一方面,树人是立德的途径,立德是树人的追求,树人是为了更好地立德。所谓的立德树人实质上就是‘立育人之德’和‘树有德之人’的辩证统一,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不可分离,必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考量、统一理解。”[注]韩丽颖:《立德树人:生成逻辑精神实质实践进路》,《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这种对于“立德”与“树人”各有分工、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解释方式其实并没有抓住“立德树人”的实质性内涵,真正精髓的东西被掩盖起来。从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层面来看,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曾经明确地提出中国教育的战略主题要“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7页。。习近平同志也曾在讲话中多次提出要坚持“德育”的基础性地位:“‘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注]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青年报》2018年5月3日。所以,“立德树人”的理论旨归,其核心在于“立德”,“立德”含有更大的优先性和基础性,在整体的概念构成中具有更大的主导性。进一步来说,“立德”的基础性地位不仅仅是教育制度层面的规定,同时也是解决当下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必然要求。在当下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学生的品德问题越来越突出。从总体上看,虽然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感“总体发展正向积极,但亟待提高;道德情感下属各因子发展不均衡,其中爱国感、责任感、信用感发展良好,而正直感、公益感、奉献感状况欠佳”[注]卢家楣:《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感现状调查研究》,《教育研究》2016年第12期。。可以说,当下的教育现实状况需要强化“立德”在教育宗旨中的意义,这是解读新时代教育宗旨的重要依据。正是出于对这一现实问题的考量,我们倡导“立德”的根本性意义在于将“立德”作为核心理念加以弘扬,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注]顾明远:《德育为先 立德树人》,《中国教育报》2013年12月6日。当然,强化“立德”的首要性意义并不意味着“树人”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而是强调要在“立德优先”的前提下实现“树人”的目的,因为有了“立德”,“立德树人”才能成为一个有效能的美育活动。
就学界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于“立德树人”的阐释只是停留在观念本身的层面上,除此之外并无更深的推进。在此,我们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于“立德树人”的把握,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的内涵层次上,而应该以此为基础,从更广阔的外延层面上来把握其深层理论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教育观念与时代精神之间的深刻关联,进而触摸到其本身所包涵的更为广阔的精神实质。由此出发,从整体的时代文化语境来看,“立德树人”的观念指向并非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它是以教育为基点,将精神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国家和民族领域,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为落脚点。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注]张烁:《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2月9日。“立德树人”的最终目的,是指向外在的社会现实,民族复兴历史重任的实现是其最终的归宿,同时也是理解其深层意蕴的现实依据。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拓展和总结“立德树人”的理论旨归,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新时代教育宗旨的内容。在此,如果说“立德树人”内涵层面的核心可以用“德性”来概括的话,那么其外延层面的核心则可以概括为“民族”。与前者相比,后者是更能体现“立德树人”的时代性要素。可以说,德性的提升与民族的复兴是“立德树人”教育宗旨的精髓之所在。新时代教育观念与教育实践的建构与落实,必须在这两个基本精神要素的引导之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对于新时代美育话语的现代性建构来说,要想真正在立足于教育体系、凸显教育特性的前提下彰显自身的时代价值,也必须以“德性”与“民族”这两个理论基点为导向,沿着新时代教育宗旨的精神理路,确立起新的本土现代性建构的理论生长点。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大众文化的融入:新时代美育话语德育之维拓展的方向与路径
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观念为美育现代性话语建构的突破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和坚实的理论依据。如前所述,德性的提升是当今教育最现实的需求,同时也是教育观念的核心之所在,作为教育基本形式的美育自然也应顺应这一思想,将通过美育提升人的道德品质这一维度作为自身的关键任务加以强调。从这方面说,“立德树人”观念中“德性”要素的凸显,预示了新时代美育话语建构中“德育转向”的来临。在新时代教育宗旨的召唤下,审美与道德的融合问题应该重新作为一个显性话题占据美育话语建设的核心位置,通过对这一基础问题的时代性解读来实现对美育话语现代性建构的推进。
强调美育的德育价值和功能,一直都是中国美育理论的重要传统。杜卫在总结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本土特征时就曾明确指出:“他们(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家——笔者)都肯定地把德育作为美育的目的或者核心,把美育作为德育的基础来加以强调;而对美育功能的理解也多偏向于使情感‘高尚’、‘纯洁’,使趣味‘脱俗’、‘防卑劣’等等,其中的道德意味显而易见。”[注]杜卫:《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在此,将德育看作中国现代美育的“目的”或“核心”,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从总体上说还是以强调美育的独立性为其根本任务的。即使是探讨美育的德育功能,也是在尊重美育特性的前提下来进行的,并未将德育置于“核心”或“目的”的位置上,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一点。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现代美育理论重视美育的德育价值,强调通过审美这一中介来实现人的道德品质的构建和提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中国美育的现代性建构历史经验所呈现出的一大特色。不仅如此,注重审美与道德的融合性,同时也是以儒家观念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重要维度:“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来讲,美不仅在源发意义上成为人性向善生成的内部动因,而且也是道德外化的形式。所谓以美储善或以美导善,最终生成的仍是一种以审美作为标识的道德形象。或者说,美与德的关系,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可以表述为首先以美育德、继之以德成美的连续性过程。”[注]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善”》,《光明日报》2018年6月25日。可以说,注重美育的德育价值,强调审美与道德的融合,在中国美育的传统和现代性进程中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这是中国美育思想的特色之所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新时代美育话语对于自身德育之维的强调,与传统框架尤其是启蒙框架下美育话语对德育功能的强调有何不同呢?理清这一问题,是新时代美育话语建构的关键之点,同时也是超越启蒙框架、凸显新时代美育现代性建构特色的重要节点。
从最表面的层次来说,这几种美育话语类型最大的不同首先在于所育之“德”内涵的差异。新时代美育话语所要培育的“德”,是与新时代的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注]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教育所“立”之“德”的核心内容,而在“立德”观念引领之下大力彰显自身德育价值的美育话语建设,也应该将自身的德育建设目标锁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上,要“充分考虑到个体的生活情境和个性因素,通过制度的完善和社会道德环境的改善构筑核心价值观的系统工程,引领人们逐渐养成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高凤敏、沈大光:《全面理解道德教育本质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就这一点来说,它与传统美育话语所要树立的封建伦理道德、与启蒙的现代性美育话语所宣扬的人道主义道德都大不相同,而这也决定了新时代的美育话语现代性建设与启蒙的美育话语现代性建设及传统美育话语之间根本的不同。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从不同的美育“话语型”在“育德”之时所采用的路径和运行机制,也可以探寻到美育现代性建设的巨大差异性。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彰显自身的“育德”效果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关系”说,通过对这一命题的本土化阐释来呈现美育的“育德”路径。蔡元培曾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注]金雅:《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蔡元培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王国维也曾明确地表示:“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注]金雅:《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页。不难看出,这一立足于康德哲学的美育话语德育价值的实现机制中有着鲜明的精英化意识。按照这种模式,美育的实施必须以具有极高水准的审美或艺术产品为中介,通过高雅艺术的引领而超越世俗的“欲”或“利”,在超拔的审美境界中体悟美善合一的真谛,由此而实现德性的圆融。可以说,这一模式在当下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遵从着,很多学者都是在这一思路的规引之下进行美育理论建构和实践的。这一思路在学理上固然有着自己的合理性,但客观地说,这种精英化的美育路径已经与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产生了很大的疏离,新时代的美育现代性建设如果继续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是很难在时代文化潮流中站稳脚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美育机制在当下是完全无意义的,很多学者都对它的意义和价值作过深入探讨。我们只是立足于时代的立场对其与当代话语环境的疏离之处作出概括,同时也是在认可其历史价值的前提下,探寻更为现实有效的美育运行机制,以此来为新时代的美育现代性建构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此,我们倡导新时代美育话语的德育价值的实现,应该超越单一的启蒙思路,在具体的运行机制中引入“大众文化”这一要素,把当下文化的主流——大众文化纳入美育实施轨道之中,通过大众文化这一中介来实现美育的德育价值的彰显。
“大众文化”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很多学者都曾对大众文化的弊端与优势作过明确的梳理与总结。而对于大众文化与美育的关系,学界则倾向于从两者对立的立场上来谈论:“大众文化肤浅化、模式化、庸俗化及色情化等缺点正在腐蚀着当代审美主体的思想,造成审美主体心灵的空虚与情感的淡漠。要规避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净化审美主体的心灵,丰富审美主体的情感,提高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审美主体实施审美教育,特别是艺术审美教育。”[注]张鸿声、王晓云:《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审美教育》,《艺术百家》2012年第3期。这种将大众文化等同于低俗,将美育等同于高雅,并由此而将两者置于截然对立位置上的做法依然没有跳出固有的启蒙思路,依然是从精英化的立场上来规范美育,将美育作为疗救大众文化泛滥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这种对两者关系的看法并非是个案,而是当今学界研究的主流,至于说以大众文化为中介,由此来探讨美育的德育价值的实现问题,学界有价值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客观地说,大众文化在今天的时代环境中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中国当下的文化主流是大众文化,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靠立足于精英立场的鄙视与批评,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并且也无益于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质性进展;而对于新时代的美育来说,如果忽略“大众文化”这一要素,或者将其置于自身的对立面,则会失去一条走向大众的重要通道,也无益于自身的发展。正视大众文化,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积极性意义,将其纳入积极的文化发展轨道,是新时代美育现代性建设的正确态度。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学者作出了正面回应,陶东风就曾明确指出:“落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是让它从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进而赢得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而这种转化,如果离开了大众文化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是不可能达到的。”[注]陶东风:《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巩固着主流价值观。作为产量最高、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类型,大众文化既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也是确立文化领导权、落实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不能落实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之中的价值观必定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不可能深入人心,不可能成为主流文化。”[注]陶东风:《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所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重要任务的新时代美育话语,必须重视大众文化这一环节,从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入手,充分发挥其对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美育发挥作用的机制就不应再是建立在康德哲学基础上的“审美无利害关系”模式,而应该是在立足于大众文化本身特点基础上的“道德渗透”模式,通过碎片化的大众审美文化这一中介,将抽象的道德规则与感性的审美快感相结合,使大众在感官愉悦之中体味与认同道德理念,进而达到在娱乐性与感官性的审美享受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这也就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的具体化。以此来实现新时代美育话语的德育价值,进而推动其理论话语的现代性建构,应该成为新时代美育建设的一个着力之点。
四、新时代的美育话语建设与民族精神空间的开拓
从根本上说,启蒙的现代性美育话语的最终指向也是“民族”:“中华民族要改变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走现代化发展之路;而国家的现代化大业必须有现代化的人才来实现,现代化的人才又必须依靠现代的教育来培养。包括美育在内的中国现代教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规定性与认识逻辑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注]谭好哲、刘彦顺:《美育的意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可以说,近代以来对民族危机的拯救以及对民族独立的渴望是启蒙的现代性美育话语生成的触发点,也是其核心的落脚点,“民族”观念也因此而成为现代美育理论深层的话语建构准则。但是,启蒙美育话语所遵从的“民族”观念与新时代的“民族”观念有着本质的差异,两者属于截然不同的话语环境。具体来说,在进入21世纪以后,新时代“民族”观念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民族独立、民族生存,而是转变为以民族自豪与民族自信心的养成为主要任务的民族复兴;不仅如此,新时代的“民族”观念中也融入了明确的“国家”建设的成分,加快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人民幸福感这些更具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理念也成为新时代“民族”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新时代的“民族”观念场域中,国家的强大是实现民族复兴和民族自信的物质基础,而民族复兴与民族自信又是实现国家稳定与强盛的精神支撑,两者互为基础,共同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旗帜之下,为新时代社会文化建设树立起了新的目标和指向。所有的思想和理论建设只有沿着这一精神导向行进,才能最大限度地彰显出自身的时代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立德树人”的内涵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领域,而应该在宏阔的时代潮流中树立更为高远的精神指向;同时也正是从这个方面,我们说新时代美育话语建设,必须沿着“立德树人”所蕴涵的“民族”主题,去进行更为深邃和更具时代感的现代性营构。
以新时代“民族”观念为基点的美育话语现代性建构,有一个基本的拓展维度,那就是新时代语境下民族精神空间的开拓。从内涵上来看,这主要是指通过美育这种教育文化形式的实施与落实,丰富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构建其灵魂世界,进而塑造起既有丰富内涵又有独特旨归的民族精神品格。关于这一点,于文杰曾给出过明确的答案:“中国美育现代性缺少的正是被传统的封建理性遮蔽了的科学意识和不断流失的儒学精神。因此,追求民族精神的重建必须寻找远去的饱藏着知识理念和人本意识的儒学之魂。”[注]于文杰:《通往德性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4页。“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应当以科技事业的建设和科技教育的普及为中心问题,中国美育的现代性转换也必须体现原典儒学中的知性精神,并使之获得重建和提升。”[注]于文杰:《通往德性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在于文杰看来,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儒学精神是现代性美育民族精神建设的核心内容,只有在理性之光的烛照之下,去整合与复兴传统儒学中的知性精神,现代民族文化才有出路,中国美育的现代性发展才有方向。从最基本的学理层面上来说,这种将美育置于理性笼罩之下的做法本身就极容易构成对美育自身问题的遮蔽,虽然这里面也存在着通过理性的刺激与推动来激发感性生命活力的合理成分,但从根本上说,它对于美育自身独特价值的呈现是弊大于利。此外,从现实的层面上来看,将现代儒学的科学理性作为民族精神来规引美育话语建设,对于当代人生存状况的改变来说也是一剂不太对症的药。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的过度挤压所造成的人性扭曲与现代文明弊病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中逐渐成为突出的问题:“市场化所导致的市场本位、金钱拜物,工业化所导致的工具理性膨胀,城市化所导致的精神疾患蔓延等等。这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目前看,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这些问题也难以避免。”[注]曾繁仁:《美学之思》,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2页。在这些现代性的社会问题面前,理性的现代儒学精神所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美育要想真正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还必须寻求更为广阔和现实的思路。
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凸显的情境下,美育应该彰显的是其抚慰人心的人文精神,充分发挥审美这一文化之维在现代信仰重构和价值重塑中的意义,从个体心灵的栖息到群体信仰的营造,最终在整体的民族精神层面上构建起支撑民族心灵的灵魂大厦。潘知常曾经言辞激烈地批判过20世纪中国美学对信仰问题的漠视。他说,在“天下”“丹青”等观念暴露出它本身的虚假性之后,鲁迅、王国维直面个体的虚无,中国美学第一次发现了属于自身的问题,但在此之后的美学既未能照着讲,也未能接着讲,从而在根本上偏离了道路,西方文化中更高的存在——爱、信仰的维度,他们也未能发现。21世纪的美学必须补上爱与信仰的维度,才能比鲁迅、王国维走得更远。[注]潘知常:《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学术月刊》2003年第10期。与此同时,潘知常还指出,20世纪的中国美学对于信仰的忽视导致了它对于启蒙、革命等问题的热衷,由此将美学“视之为工具——社会改革的工具、救亡的工具、改造国民性的工具、人性启蒙的工具等等。而美学自身的本体论建构却被完全忽略了,超越性的精神维度根本就没有出现。于是,美学失美,美学之为美学,研究的竟然不是自身应该研究的问题,而是自以为是的假问题”[注]潘知常:《“以美育代宗教”: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信仰的失落是触发中国现代文化发生的大问题,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本身就是在信仰重构的时代背景中提出的,但其在后来的走向中却引入了人性、道德、社会等因素,而淡化了原初的信仰之维。从这个方面来说,潘知常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但从理论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中国现代美学在信仰之域也并非完全是无动于衷的。在美学启蒙话语这条显性的线索背后,还存在着一条呼唤审美与信仰相融的隐性线索。它以丰子恺、李叔同的美学观念为代表,最典型的命题就是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注]陈星:《丰子恺全集》(文学卷五),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第110页。这是强调审美、艺术与宗教的相通性,通过审美而通达人的信仰之域的做法。这是中国现代美学(美育)在主流话语之外所开辟出的另外一条迥异路径,它将美育的建构与个体灵魂的重塑、人生苦闷的宣泄联系起来,体现出了现代性美育话语丰富的理论可能性。在21世纪的今天,在信仰失落、人性扭曲、价值虚无的人生苦闷重新凸显的情形之下,现代美育理论中这束若隐若现的思想之光更加显示出它的珍贵。我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不断拓宽前进的道路,将其由从个体心灵的层面上升到民族心理的层面,最终将信仰的建构与时代的伟大目标相结合,构建起新时代的民族精神空间,其基本的逻辑可以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现代中华民族为自身所设定的一个外在性的预期奋斗目标,更是人们内在的自觉的情感寄托与归宿,它通过审美这一中介转化为一种信仰精神,并通过美育这一现实的手段融入国人的血液之中,慰藉着现代中国人的心灵,支撑着国人的信仰世界。”[注]陈剑、陆晓芳:《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潮中的信仰精神及其对中国梦的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当然,这个支撑民族心灵的灵魂大厦的根基,只能是建立在本民族自身的文化根基之上,在立足于民族审美特性的基础上,构建起以抚慰现代中国人灵魂为最终指向的新时代美育话语,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空间的开拓。这是新时代美育话语在“民族”观念指引之下进行现代性营构的一个维度,它既体现出美育固有的现代本性,同时也展现着美育在时代精神引领下的新拓展。在这两者的共同推进之下,新时代的美育话语建设不断走向深入。
五、结语
当下,中国美育话语的现代性建构主要还是在“启蒙”的框架中进行的。这需要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加以突破,“立德树人”的教育观念正为其提供了理论超越的契机。在这一教育宗旨的引领之下,中国美育话语应该在“德性”与“民族”这两个维度上拓展自身的理论空间:通过美育来实现人的德性提升,要利用好“大众文化”这一中介,强化大众审美文化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渗透功能;同时,新时代的美育话语也要在开拓民族精神空间与树立审美信仰方面凸显自身的“民族”维度。当然,限于篇幅,我们从最宏观的层面上对美育话语建构的精神方向作了探讨,而具体的美育实践方式和建构策略等问题——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众文化中的渗透方式、现代民族审美信仰的建构路径等——还需投入更大的篇幅和更多的精力进行探讨;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宏大的理论话题,中国美育话语的现代性建设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也并非只能遵从教育观念这一个维度,从更多的角度、更宽广的理论层面探索其理论发展路径,也是新时代美育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