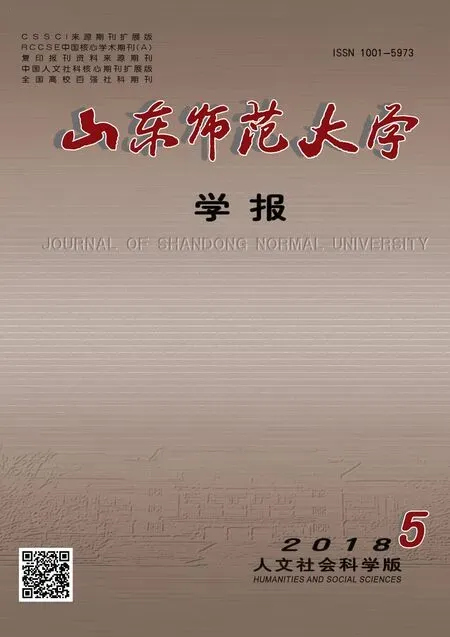实用主义美学的发明:对一个术语和命名的谱系学考察*
理查德·舒斯特曼著 胡莹译
( 1.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 身体、心灵与文化中心,美国;2.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100875 )
一
当朱丽叶催促罗密欧干脆“丢弃”或“否定”自己的姓名,却依然保持他的真实身份及他“可爱的完美”时,朱丽叶问道:“姓名有什么意义呢?”她在修辞上勇敢争辩:“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北京:文学艺术出版社,2004 年,第30页。然而,莎翁的戏剧不幸地揭示了名称(包括姓氏)的确有其意义;由于拥有不断塑造其当下指称的历史,名称通常具有持久而有效的意义与内涵。如果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仅仅说明了丢弃、否定或逃避名称的麻烦意义是多么困难,那么当代认知心理学则揭示了一个名称的诸种联想是如何影响我们基本的感知。如果发现某种芳香的气味并非玫瑰之香,而是携带了有毒浆果、化学合剂或啮齿类动物分泌物的名字,那么,这一气味将会变得不那么甜美。
广告展示了名称的说服力,它们可以吸引人们去购买某一产品或舍弃这个念头。哲学观点、理论和运动同样拥有名称,而其形式和命运很可能会受到其名称的极大影响。这些名称尽管是先前历史的产物,却会造成哲学传统的彻底重塑。名称甚至能够用于创造新的传统,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使用“实用主义”这一名词时所做的那样,他从皮尔斯(C.S. Peirce)那里借用了有关意义的实用主义原则,然后加上经验主义多元性和美国改革派的改良主义(American reformist meliorism)这些古老观念,从而大胆地发展出一个新的哲学运动。带着对行动和命名力量的明确自我意识,他将实用主义的第一本书命名为《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式的一个新名称》(Pragmatism:ANewNameforSomeOldWaysofThinking),并预言这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创造一个能够彻底转变我们文化思维的运动,其意义“就像清教徒的宗教改革一样”[注]Ignas K. Skrupskelis,Elizabeth M. Berkeley:《威廉·詹姆士书信集》卷三,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339 页。。尽管这一野心勃勃的预言尚未彻底实现,实用主义却成为过去百年文化的一个有力参与者,这不仅体现在美国哲学中,也体现在国际性的不同文化领域。
美学领域内的实用主义影响直到最近才日益强劲。美学起初在实用主义哲学中也是一个边缘化的领域。皮尔斯或詹姆斯皆未撰写过美学方面的专著或文章,而约翰·杜威仅在其事业的晚期才转向美学,1934年,在他75岁时发表了巨著《艺术即经验》[注][美]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Jo Ann Boydston:《约翰·杜威晚期作品》卷十,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尽管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此书被视为实用主义美学的奠基性文献,但事实上,杜威本人的著作并未在此称谓下推进过任何理论。杜威在这部书中不仅避免使用“实用主义美学”(或类似术语,如“实用主义的美学”或“美学实用主义”),甚至不曾使用过“实用主义”一词。正如本文将要展示的,杜威在美学领域对“实用主义”的忽略是有意的、策略性的、持续性的。我在1992年首次出版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中,试图为后杜威时代的当代文化阐述一种新的、明确的实用主义艺术理论,策略性地将杜威视为该书的主要灵感,尽管最初我意识到杜威并不喜欢“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提法,却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有意强调自己拒绝这一提法。[注][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Blackwell 出版社,1992 年;第2版,Rowman and Littlefield 出版社,2000 年。现在,20年过去了,“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概念已然十分流行,并指示出一种充分确立的思潮——这种思潮能够促进学术会议的组织、研究资金的设立以及文章和书籍的出版[注]如 Wojciech Mafecki:《具身性实用主义: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哲学和文学 理论》, Peter Lang 出版社,2010 年;Dorota Koczanowicz,Wojciech Mafecki :《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文学和身体美学之间》,Rodopi 出版社,2012 年; John Golden, Wojciech Mafecki:《当代实用主义》特辑《情感、美学和身体》2012年第3期。Sorbonne 还在 2012 年5月举办了题为“实用主义美学:20 年之后”的有关实用主义美学的国际会议。,探究这一术语的源起、流行及如何回溯到杜威(及其他早期实用主义思想家)就显得很有意义。
本文试图对实用主义美学这一名称和观念的谱系学进行探究。在下文中,我简要介绍了三位实用主义奠基人物(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美学观点,探讨他们为何从未在任何以“实用主义美学”命名的理论中阐述过这些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讨论杜威的美学理论(尽管是实用主义美学范式的先声)如何依然被指责为不充分的实用主义,以及杜威是怎样对此进行论述——他的美学理论确实从未试图成为一种特殊的实用主义美学。接下来的章节探究的是这样一个谱系学问题,即“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术语如何在后杜威时代得以确立,又如何能够将杜威视为新实用主义美学的支持者。通过回溯我是怎样以及为何最先使用此术语,本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在回顾中也觉得很吃惊),即尽管杜威很快成为了我的主要灵感,但事实上,我最初迈向实用主义美学并不是受杜威的影响。
二
除了创立实用主义,皮尔斯还创立了符号学这一领域,且在符号逻辑和解释领域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大大影响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然而,皮尔斯从未阐发过艺术理论,也未对美学领域内的其他问题作出过持续分析。他甚至说自己“并没有能力”涉足这一哲学领域,尽管他声称自己有着敏锐的美学鉴赏力,并至少以三种方式意识到了美学维度的重要性。[注]Nathan Houser ,Christian J. W. Kloesel:《皮尔士辑要:哲学作品选》卷二,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 年。皮尔斯在《形而上学的7个系统》(1903 年) 中承认:“我在美学领域还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人”且“忽视了……艺术”(189、190 页)。他在《三种标准科学》(1903 年)中指出,自己“不能胜任”“定义美学善”(201页)。通过欣赏游戏在创造性表达和思考过程中的作用(试图通过一个他称为“娱乐[amusement]”的极具启发性的概念捕捉这一点),皮尔斯还将经验的直接性(immediately felt quality)强调为他意识理论中的第一范畴,或“第一性”(Firstness )。詹姆斯在其著作《心理学原则》中也强调和发展了这一直接性。之后,这一点被杜威转化为“统一直接性”这一关键概念,以此定义审美经验和艺术。除此以外,皮尔斯还将美学确立为标准科学逻辑和伦理的最终总结,因为“逻辑上的善仅是道德善的一个特殊部分”,而“道德上的善则是美学善的特殊部分”[注]Nathan Houser ,Christian J. W. Kloesel:《皮尔士辑要:哲学作品选》卷二,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01 页。。如果“道德是承受自我控制的方法的科学”,以此获得我们所欲求之物,那么,皮尔斯论述道:“一个人应当欲求的......将是使(某个人的)生活变得美好和令人爱慕。而令人爱慕的生活的科学就是真正的美学。”[注]见皮尔斯给 Victoria Welby 女士的信,转引自 Joseph Brent:《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一生》,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9页。美学与伦理学和逻辑思考之间的这种连续性,在詹姆斯和杜威那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
尽管具有敏锐的美学鉴赏力、开阔的文化视野以及早期在绘画事业上的雄心,威廉·詹姆斯还是避免在哲学美学领域内进行任何讨论。事实上,他明确谴责这一领域,因为他认为,在捕捉对审美经验至关重要的艺术核心处那无可名状的细微感时,之前的原则和各种哲学美学定义都注定是失败的。同一个一般性定义和言语性范畴(如小说、交响乐、三联画等)既可用于天才的作品,也可用于机械性的无趣作品。他相信哲学美学所提供的一般性规则、抽象原则或言语性标准无法胜任艺术和审美经验中不可命名的特性,而正是这些特性强化了审美经验,并区分了艺术品——即便处于相同术语之下——在价值和精神层面的不同。“艺术中优秀和第二优秀的区别似乎完全逃避了言语性定义——问题的关键是某个细节、某种微妙、某些内心的震颤——这些都使艺术品产生云泥之别!绝对相同的言语性准则可用于最成功的作品,也可用于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作品,但美学却将只能给出言语性准则。”[注][美]威廉·詹姆士:《威廉·詹姆士书信集》卷八,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75-476 页。以概念系统化闻名的德国哲学家被詹姆斯特别挑选出来加以嘲弄。“为什么艺术家对所有德国哲学家的美学避之唯恐不及?”“想想德国的美学文献吧,竟荒谬到将康德这样非美学的角色置于其中心!”[注][美]威廉·詹姆士:《多重宇宙》,Bruce Kuklick:《威廉·詹姆士:1902-1910年间的作品》,Viking出版社,1987年,第638页。
虽然拒绝发展美学理论,詹姆斯不断强调(特别是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中)经验的美学维度——其特殊的感觉品质以及这种品质作用于我们的心灵和行为时产生的感染力——在我们认知和行为生活方面的关键性。美学思考塑造着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决定我们将什么筛选为该事物的真正属性;它引导我们选择理论,甚至包括我们所信奉的一般性哲学理论。他写道:“最伟大的两个美学原则,丰富性和舒适性(of richness and of ease),主导着我们的智识及感性生活。”我们需要的理论是“丰富、简单与和谐”,这听起来像是对美的传统定义——美是多样性的统一。詹姆斯说道,“丰富性”,“是由囊括图景中所有感觉事实而获得;简单性,要求从尽量少的原始实体……中推导出来”。简单性提供了舒适这一审美感觉,因为它倾向于使事物更清晰、更确切,而复杂性则榨取着我们有限的注意力和记忆力。[注][美]威廉·詹姆士:《心理学原理》,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943-944页。因此,他后来认为不同哲学或世界观之间的争论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美”的不同,或者说是气质的冲突。[注][美]威廉·詹姆士:《威廉·詹姆士书信集》卷八,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8页。
詹姆斯不仅通过论证感知和认知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学和实践基础来连接美学与实践,而且以美学为基础解释关键性的实践准则(如简单性和清晰性)。这一对审美和实践之间连续性的坚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康德式的两者对立观点——是实用主义美学的关键维度,这也反映了以下核心主题:生活和艺术的统一,承认身体性的倾向和欲望也可以是审美的,肯定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功用价值对审美价值和审美欣赏的贡献。
詹姆斯还阐发了另外四个实用主义美学的核心主题:第一,身体自然主义。这种身体自然主义承认身体性的基础,以及审美感知和愉悦的进化论根源,但也同时意识到社会文化现状及由此产生的习惯对品味的塑造。更重要的是,詹姆斯在审美经验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看到了实践连续性,艺术的交互力和愉悦感,其所带来的群体活力和兴奋感建立在社会本能——这种社会本能深植于我们具身性的、生物性本质中——之上,并使其得到满足。第二,詹姆斯定位了一个宽泛的合法化审美满足和艺术形式的范围,这一范围从较原始的到较精致的,不一而足。第三,他将包容性的多元主义与民主色彩浓厚的审美性社会改良主义(meliorism)结合起来。詹姆斯认为,我们需要克服自身品位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使得我们对他人(尤其是那些不具有我们自身文化优越性的人)的审美满足嗤之以鼻,也使得我们对其艺术和经验的审美价值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自己“根深蒂固的不宽容”(ancestral intolerances.),也同样可以享受到他们所感到的审美满足。我们需要“开阔视野”,因为我们可以“在自身中的每一处”发现美,但我们的“文化却过于死板,因此甚至无法设想这一事实”[注][美]威廉·詹姆士:《什么使生活有意义?》,《为心理学老师和学生所做的关于生活理想的演讲》,Cosimo 出版社,2008 年,第135、131页。。詹姆斯还论证了艺术想象力在设想和启发能够改进经验的新观念方面的力量,以及创造“一个理想世界,一个乌托邦”方面的力量,现实境遇“执著于相反的方向,但是我们也固执地坚持使之成真”[注][美]詹姆士:《心理学原理》,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35页。,这一论证展示了审美性社会改良论的另一个方面。
实用主义美学中第四个重要的詹姆斯式主题是,统一性在建立经验连续性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詹姆斯将其心灵哲学构筑在连续的意识流这一概念之上,其结构统一性、内在一致性、相关感和方向,取决于感受性经验的一种无名的统一性,感受性经验的“心灵暗示性”,或“感受性关系的光晕”组织并引导着我们的思维。[注][美]詹姆士:《心理学原理》,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47、249页。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解释过的,詹姆斯这一意识的无可名状的、直接感受的统一性为杜威的审美经验概念提供了理论雏形,而审美经验概念则在本质上建构起了杜威的艺术理论。因为已经在很多其他地方分析过杜威的美学,我不打算在此赘述这些分析以说明杜威怎样阐发上文所讨论的詹姆斯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主题。我在这里想简要勾勒的是杜威怎样开始写作其美学巨著《艺术即经验》。考虑到杜威开始发展其美学理论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从未将其明确地列为“实用主义美学”,甚至没有在书中提及实用主义。第一,实用主义本质上与美学相对,这在当时是一个流行已久的教条。第二,美学中并不存在已确立的实用主义传统,因为皮尔斯、詹姆斯或其他有声望的实用主义者并没有提出过美学理论。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杜威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他自己经常明确称之为“工具主义”)已因过于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而备受批评,对工具性方法和现实的关注使得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缺乏对艺术和审美经验的想象力价值及有益目的的敏感性。事实上,《艺术即经验》一书是专门为回应这一持续指控,即实用主义不能充分用于美学而撰写的,因为这种指控(由著名的纽约学派学者提出)不断困扰着杜威。
一战期间,杜威的前弟子鲁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就曾以缺乏“诗性视野” ——这使得想象力价值和理想悲哀地附属于技术——攻击过杜威的“智性控制的哲学”。刘易斯·芒福德又在19世纪20年代重新提出这一批评,他将一般意义上的詹姆斯和杜威哲学视为对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及其“功利主义特性”的“实用主义默许”。通过斥责杜威将艺术轻视为仅是另一种工具,芒福德谴责了在他看来是实用主义的 “对实践发明的片面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缺乏对“以获得更完备及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为目的的艺术性想象力”的同等关注,还缺乏理论化或实现美学价值的持续尝试。这些美学价值以其自身的利益获得享受,同时因为超越了实用工业及利益赚取等日常生活工具主义的压榨,也能使生活变得高贵。[注][美]鲁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偶像的黄昏》,Olaf Hansen: 《激进意志:鲁道夫·伯恩著作选》,Urizen Books出版社,1977年,第341-347页;[美]刘易斯·芒福德:《黄金时代》(第3版),Dover Publications,1968年,第134-137页。
杜威意识到,在经过42年的哲学著作出版生涯后,是时候对美学进行具体讨论了。所以,1929年,当他受邀到哈佛大学做首个关于威廉·詹姆斯的演讲时,杜威很快决定要将美学作为他的演讲主题,表达他“进入一个我从未系统阐释过的领域的渴望,而我所以讨论艺术和审美, [是因为]有批判说我忽视他们,也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理论的完备性”[注][美]杜威:《艺术即经验》,Jo Ann Boydston:《约翰·杜威晚期作品》卷十,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75页。。杜威当然也意识到如果将其审美理论标志为特殊的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结果会适得其反,因为与这一标签相连的反美学偏见正是他试图克服的。因此, 1931年,他做了题为“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关于詹姆斯的演讲,之后修订、扩充,并于1934年以《艺术即经验》付梓。
通过明确肯定其批评者的论点——“没有什么比对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处理更能揭示一种哲学的片面本质”[注][美]杜威:《艺术即经验》,Jo Ann Boydston:《约翰·杜威晚期作品》卷十,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8页。,杜威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策略,这一策略使他能够在辩护和深化其整体哲学核心观念的同时有效处理美学领域。这一策略的关键是经验这一强有力的多义概念,而这一概念已经是杜威实用主义的核心(也是詹姆斯和皮尔斯的)。作为一种经验哲学而非先验哲学(“经验”[empirical]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实用主义以其经验效果决定意义和价值信念,因此也忠实于构成科学方法核心的观察及实验性假设检验的经验流程。尽管杜威对经验探究和实验方法(即使是在伦理学领域)的强烈主张在中国为他赢得了“科学先生”的称号,这一点同样引起了(正如上文提到的)对其哲学是片面科学性的持续批评。[注][美]杜威作为“科学先生”这一点,见 Sor-hoon Tan:《中国的实用主义民主探索: 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杜威在中国的影响》,[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的范围和哲学界限》,Blackwell出版社,2004年,第43-62 页。然而,正如实验是革新艺术创造的关键一样,杜威聪明地意识到经验(在其本能价值的意义上)同样明确构成了审美欣赏和审美愉悦的核心。
通过使经验成为美学的核心,杜威能够游刃有余地说明其经验性的实用主义并非狭隘的科学性,而是丰富全面的、统一的,更重要的是,有能力修复艺术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分歧斗争的裂痕。艺术与科学一样,是智性经验的产物,且这两个领域(杜威强调二者的连续性)都将经验作为其成功的试金石,并将改善经验作为其关键的动机价值或目的。在意识到高雅艺术(也包括自然美、仪式等)的审美经验通常特别强烈,并能由其统一性和整全性带来极大的满足感,由此突出为“一个经验”的同时,杜威还认为审美经验最根本的形式——对将一个经验中所有元素结合起来的统一性的瞬间攫获——是将任何情景或事件组构为内在一致的、可辨识的经验的必要基础。“为了审美经验,则哲学家必须去理解什么是经验。”[注][美]杜威:《艺术即经验》,Jo Ann Boydston:《约翰·杜威晚期作品》卷十,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8页。杜威以此总结说明(也驳斥了认为他是工具主义俗物的指控)美学在其整体哲学中所占有的核心地位。
由于有着广泛的丰富性,经验这一概念能够调和许多二元论,这些二元论扭曲了我们对艺术和生活的思考。经验既可以是认知的,也可以是非认知的;既包括主体,也包括客体;既包含经验的内容,也包含经验的方式。经验是我们一般意义上很难注意到的意识生活之流,也是那些从意识生活之流中绽出为“一个经验”的高峰和特殊时刻。[注][美]杜威:《艺术即经验》,Jo Ann Boydston:《约翰·杜威晚期作品》卷十,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通过同时囊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经验既包含被保守思维拥趸的积累性的传统智慧,也象征着被进步理论所肯定的对变化的开敞和实验。人类经验遍布于历史、社会和政治语境中,所以将艺术定义为经验保证了这些领域都能得到其应有的关注,而非将美学孤立为狭隘的形式主义。在英语中,经验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经验同时表征了一个完整的事件和一个过程,并同时包含当下性和持久性。经验同时属于艺术和生活,并对艺术家和观众都是根本性的。经验既可以解释为个人的主动创造,也可以解释为其所经历的,或向其席卷而来的,正如一个人可以被审美狂喜压倒一样。经验包含的这一较为被动的方面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杜威最终选择了这一概念定义艺术,而不是或许更为实用主义的实践概念,杜威有时也调用实践概念描述艺术。
对奉准确性为圭臬的哲学来说,经验丰富的多义性也能造成困扰。这一问题造成了接受杜威美学理论的困难。分析哲学家轻视杜威的美学理论,视之为“各种矛盾方法和无序猜想的大杂烩”[注]Arnold Isenberg,“分析哲学与艺术研究”,《美学和艺术批评》1987年第46期.。这是一个十分不公正的裁定,但它表达了很多读者面对杜威的风格和经验这一多义概念时的挫败感。不久之后,杜威自己也表达了对这一术语可能引起混乱的担忧。因此,他的新实用主义拥护者,理查德·罗蒂尖锐地谴责杜威对经验这一概念的使用,认为其落入了一种经验性直接及非语言学给定的基础主义虚构。[注]关于杜威后期对于经验这一术语在当代哲学中的效用的担忧,见其《经验与自然》附录,收录于Jo Ann Boydston:《约翰·杜威晚期作品》卷一,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61-364 页;关于罗蒂的批评,见理查德·罗蒂:《杜威的形而上学》,收录于《实用主义的影响》,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72-89 页。对于经验(包括审美经验)在哲学中的影响,我自己的立场介于杜威和罗蒂之间,不仅在《实用主义美学》,也在《实践哲学: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劳特里奇出版社,1997年)中阐发过了,特别是后者的第 2、6章,以及《通过身体思考:身体美学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章。即使是欣赏杜威一般性实用主义路径及对审美经验的强调的美学家也对其艺术即经验的理论感到头疼。
三
史蒂芬·佩波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例子,因为他批评杜威的艺术经验理论不够实用主义。他在1939年为《约翰·杜威的哲学》一书所写的文章中描述到,1932年左右,自己是怎样开始以杜威的一般性实用主义视角及其在《艺术即经验》发表之前的“零散的艺术和美学论述”为基础构建一种解释,以回答“实用主义美学”会是怎样这一问题。[注][美]史蒂芬·佩波(Stephen Pepper):《杜威美学的一些问题》, Paul A. Schilpp ,Lewis E. Hahn :《杜威的哲学》(第3版),Open Court,1989年,第371页。佩波认为,《艺术即经验》这本书包含了他所期望的实用主义特性,但同时令他吃惊的是,该书肯定了一些只有美学领域的“有机理想主义者”(如克罗齐)才会拥护的观点,佩波认为这些观点与杜威所呈现的“实用主义精神相左”[注]Paul A. Schilpp ,Lewis E. Hahn:《杜威的哲学》(第3版), Open Court,1989年,第371页。。这些有问题的观点包括,杜威对有机整体性的强调,对内在一致性和统一完整性或完备性意义上解释审美经验特殊价值的强调,以及对这样一种统一经验的强调,即艺术品欣赏者需要在感知和想象力上重建与艺术家创作艺术品时性质相似的统一经验。相反,对于佩波来说,与强调经验的统一相比,“一种实用主义美学”会更强调经验特殊的直接“品质”(包括其“广度、深度和生动的程度”),会更强调经验产生于与环境互动这一途径,且会随互动情景或互动组成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作为经验的艺术品将不会具有固定的价值,而是会随着不同语境中不同人的不同经验方式而改变。[注]Paul A. Schilpp ,Lewis E. Hahn:《杜威的哲学》(第3版),Open Court,1989 年,第374-375页。佩波认为,就强调经验的互动性和直接性而言,称杜威为实用主义是令人信服的,但在将经验品质的规定性本质和功能理解为经验材料统一成的有机整体时,杜威牺牲了实用主义的旨趣。用杜威的话说,最突出的“一个经验的普遍品质在于其将所有决定性要素,所有我们集中意识到的客体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整体”[注]Paul A. Schilpp ,Lewis E. Hahn:《杜威的哲学》(第3版), Open Court,1989 年,第386页。。
为了回应佩波,杜威不仅继续表示拒绝接受一种特定的“实用主义美学”概念,还再次肯定了自己对统一性、内在一致性和完整性的热衷。[注][美]约翰·杜威:《经验、知识和价值:反驳》,Paul A. Schilpp ,Lewis E. Hahn :《杜威的哲学》(第3版),第517-608页;对佩波文章的回答在549-554 页。更重要的是,杜威还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在实用主义这面旗帜下发展其美学理论。杜威给出的原因明显是方法论的,且可以被矛盾地表述为一种真正的实用主义对待美学的方式,应当是从不致力于发展一套实用的或实用主义的美学。因为这样一个目的在经验上会是不充分的(像实用主义应当是的那样),相反,它会试图带着一种实用主义的偏见(在实用主义的范畴和原则意义上)甄选和分析相关美学主题,而不是如其所是地检验相关美学现象。“我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明确反对典型的和现今的审美哲学,即它们并非形成于对审美主题和艺术性经验的检验之上,而是形成于从先行的预想推演出后者一定是什么之上”[注][美]约翰·杜威:《经验、知识和价值:反驳》,Paul A. Schilpp ,Lewis E. Hahn :《杜威的哲学》(第3版),Open Court,1989年,第550-554页。,杜威这样解释道,这意味着提出一种明确的“实用主义美学”可能本身就会是错误的,因为这可能正是那种当其他哲学运动或学派使用这一术语时,“(他)会批判的” 推理性的、不充分的经验“程序”。而对于杜威来说,“实用的经验主义”[注][美]约翰·杜威:《经验、知识和价值:反驳》,Paul A. Schilpp ,Lewis E. Hahn:《杜威的哲学》(第3版),Open Court,1989年,第 549页。之本质似乎并不利于探求一种作为特别方案或计划的实用主义美学。如果能就“一种经验性的实用主义美学”说点什么的话,它的决定性特征应会是经验性路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实用主义原则;杜威还声称,经验性方法必须“正确处理” 审美经验关键核心处的统一性、完整性和整合性。[注][美]约翰·杜威:《经验、知识和价值:反驳》,Paul A. Schilpp ,Lewis E. Hahn :《杜威的哲学》(第3版),Open Court,1989 年,第 554 页。
杜威对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提法的拒绝一直持续到他职业生涯的末端。在他去世前4年发表的对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的回应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拒绝态度强有力的、甚至急躁的表达。克罗齐撰写了一篇文章,勾勒杜威与自己的有机理想主义美学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提到了佩波对杜威美学不够实用主义的批判。杜威带着不同以往的坏脾气作出回复,声称他无法恰当地“回应”克罗齐,因为他找不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注][美]克罗齐:《杜威的美学》,《美学和艺术批评》1948 年第6期;[美]约翰·杜威:《对前述批评的评论》,《美学和艺术批评》1948年第6期。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是,杜威认为克罗齐假定自己的目的是塑造一种关于美学的实用主义理论。但杜威自己从未将此作为目标,因为他将自己的实用主义限定在知识论的范围内,且并不认为美学主题归属于认识论的领域。“克罗齐假定我是带着将艺术带入实用主义哲学范围这一意图来讨论艺术的。……而事实却是我一直将实用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关于认识的理论来对待,且将其划定在特定认知主题的领域界限内。同时,我特别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学主题是一种知识形式,且我认为艺术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将主题如其曾是怎样地对待。”[注][美]约翰·杜威:《对前述批评的评论》,《美学和艺术批评》1948年第6期。如果这一对实用主义美学方案的拒绝还未足够清晰的话,杜威还通过坚持自己“并未将《艺术即经验》当做其实用主义的附属品或应用”这样一种观点来澄清这种拒绝,因为他认为审美的理论化不应通过“某些优先的哲学范畴”来实现,而应“由其自身并以其自身的方式”来实现。[注][美]约翰·杜威:《对前述批评的评论》,《美学和艺术批评》1948年第6期。也许可以讨论的是,杜威自己在《艺术即经验》中的论点可能会与上述观点——在知识和艺术及审美经验主题间作严格区分——相冲突,但因为已经在《实用主义美学》中解释过了,我不打算在这里展开这一讨论。
杜威在建立一种充分的“实用主义美学”上的明显失败(按照佩波和克罗齐的观点),其自身对这一术语的拒绝,其对探索相关理论这一想法的强烈排斥,本应使其他学者踟蹰于将类似“实用主义美学”的术语视为指示了一种确立了的、杜威式的理论方向。因为如果伟大的约翰·杜威,唯一一个构建实质性美学理论的实用主义者,都不断否定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提法,那么其他渺小的实用主义者们(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又怎能反对他,并提出以这一被摒弃的标签为名的理论呢?我们将会看到,从经验数据上说,这一术语一直很少被使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实用主义开始兴起。
事实上,实用主义美学(尽管无疑受杜威启发)这一提法本质上是新实用主义思想的产物,且这一术语是经由我在自己的著作《实用主义美学》(1992年)和其他文章中(从1988年开始直到现在)系统地使用和推介后,才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性的认可。现在,重新回顾起来,我起初对实用主义美学计划(并将杜威作为其奠基人)信心十足的热情,部分源于自己在实用主义学说方面还是个新手,因此较少受到限制,从而能够创造性地重新阐释杜威的观点,甚至还包括推进他自己所忽视的论点——正如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概念一样。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才开始对实用主义感兴趣。这发生在我于牛津大学接受分析哲学训练,并在分析美学领域获得特定的专业知识之后。的确,(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作为一个受分析哲学训练的年轻学者,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第一次阅读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时,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注][美]理查德·舒斯特曼:L'expérience esthétique comme forme de l'art,Revue d'esthétique,1994年第25期。我认为他的概念不清楚,风格繁冗,论证令人沮丧的松散和无序,且他的观点也过于混乱而不能为我所用。直到1988年再次阅读该书后,我才开始欣赏其价值,而这是因为我已倾向于将实用主义观点——更准确地说是新实用主义的观点——明确应用于美学问题(也许正是起初缺乏对杜威思想的敬畏,才使我能够毫无顾虑地提出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杜威自己不断坚定鄙弃的概念)。不管怎样,我对实用主义美学的初始兴趣并不源于杜威,而是源于新实用主义哲学的语言和文学理论。因此,我将用下一部分描画这一来源,以及将我引向杜威并构建实用主义美学的路径。
四
作为研究美学和语言哲学的分析哲学家,我特别关注文学理论。我最初的两本著作是《文学批评中的客体》和《T.S. 艾略特与批评哲学》。[注][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艺术批评的客体》,Rodopi,1984年;《T.S.艾略特和批判哲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文学理论中,阐释的问题构成了我的主要研究兴趣。当我欣赏的分析哲学家(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ty)和乔瑟夫·马戈里斯(Joseph Margolis)转向解释学理论和其他形式的大陆哲学,以求发展出一种关于阐释的非基础性的后分析哲学来回避固定的、物化的意义时,当他们以一种改进过的实用主义为名提出这种理论时,我受到启发追随他们的方向。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一位精通大陆解释学的文学理论大家,也开始发展一种拒绝固定的、基础性意义的阐释理论,并将其认同为实用主义。除了批判性的接受新实用主义文本外,我还开始大量阅读大陆解释学理论和解构理论,将这些理论置于与分析美学的批判性对话中,并提出这样一些方式,即一种新的实用主义路径能够在整合分析理论和大陆洞见的同时避免二者的极端所带来的问题。实用主义似乎为美国理论家提供了一种视角,这种视角足够哲学化,同时又充分的实用、灵活,并避免了模糊、深奥的思辨给理论这一概念带来的坏名声。
新实用主义在获得任何美学领域的地位之前,已经在文学理论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性的影响力。它在文学理论领域(特别是阐释这一问题方面)的显著成就可见于1985年在《反对理论:文学研究和新实用主义》这一激进标题下出版的重要文集。[注]William J.T. Mitchell:《反对理论:文学研究和新实用主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年。正如其标题所示,这一文集针对的是文学理论家而非美学理论家。包括罗蒂和费什的文章在内,这本书关注的是理论如何能够说明意义和文本阐释这一问题。不出意外,我早先撰写的实用主义和艺术方面的文章关注的也是阐释的问题,明确表达一种能够调解分析哲学的刻板和大陆哲学的过度的实用主义。这些文章既不聚焦于杜威,也不聚焦于其有关经验的关键美学概念,而是探究新实用主义介入意义,阐释和指示同一性的方式。它们会涉及由下述哲学家提出的关键议题,这些哲学家包括,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克罗齐(Benedetto Croce)、T.S. 艾略特(T.S. Eliot)、E.D. 赫希(E.D. Hirsch)、M.C. 比尔兹利(M.C. Beardsley)、G.E. 摩尔(G.E. 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约瑟夫·马格里斯(Joseph Margolis)(最后两位明确将自己认同为新实用主义者)。[注][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分析美学:回顾与展望》,《美学和艺术批评》1987年第46期;《克罗齐的阐释:解构和实用主义》,《新文学历史》1988年第20期;《有机整体:解构和分析》,Reed W. Dasenbrock:《重绘边界:分析哲学,解构和文学理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92-115 页;《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相遇:实用主义的视角》,Diane Michelfelder, Richard Palmer:《对话和解构: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相遇》,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5-222页;《阐释,意图和真理》,《美学和艺术批评》1988年第46期;《艾略特关于实践智慧的实用主义哲学》,《英语文学研究评论》1989 年第40期。
这种在文学理论方面对新实用主义策略的试探性主张促使我更广泛地研究实用主义哲学,并促使我思考实用主义哲学怎样能够在艺术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这反过来又催促我重新阅读杜威的美学。1988年与自己舞蹈博士班学生共同探索杜威思想的特别经历,使我完成了向实用主义美学的转换。在这些经历中,经验这一概念最终起到了核心作用,正如其在杜威思想中一样。这一概念在我之前的理论研究中完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管是分析哲学还是实用主义。
这样,我就决定在1988年写一本关于实用主义美学的书,通过借鉴以下5种来源中的洞见和论点来发展一种全面的理论:杜威的经验性美学和哲学的重构主义视野;新实用主义关于意义、阐释和同一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向艺术自律及精英主义倾向提出的挑战及其为这些特点所作的辩护(阿多诺和布尔迪厄的理论);对流行艺术的建构性研究(包括我自己对流行音乐进行美学分析的努力和对嘻哈音乐歌词的解读);由福柯和罗蒂提出的将伦理视为一种生活艺术的后现代视角。[注][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后现代主义的美学主义:一种新的道德哲学?》,《理论、文化与社会》1988年第5期;《美育还是美学意识形态:T.S. 艾略特的艺术到的批评》,《哲学与文学》1989年第13期。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他们曾出版过由我修订的《分析美学》——在看过我为这部书列出的简要提纲后,同意提前签订合约,出版一部从新实用主义视角讨论美学的专著。1988年8月,在第11届国际美学大会上(于诺丁汉召开),我以“分析和实用主义美学”为题介绍了该书第一章中有关杜威的主题;《新文学历史》1988年秋季刊(其中发表了我的文章《克罗齐的阐释:解构和实用主义》)已经在其作者注释栏中写明我在“撰写一部关于实用主义美学的书”;1989年我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现在谈杜威?》的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在当代文化需要一种新的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意义上重塑杜威的关键主题,试图使这些主题更具时代性。[注][美]理查德·舒斯特曼:《为什么现在谈杜威?》,《美育杂志》1989年第23期。该文章发表于杜威《艺术即经验》出版75周年座谈会。
我在1990年写了《实用主义美学》一书第一版的初稿。当时,我在布尔迪厄位于巴黎的研究中心做客座研究员,远离了实用主义历史研究所需的图书资料。不过,我这本书的明确主旨在于前瞻性的改良而非重新解释杜威和实用主义传统。正如此书第一版封底的宣传语所说,我的目的在于“为目前的后现代语境提出一种实用主义美学”,原因是“新实用主义还未在新的美学中表达自身”。这本书的评论者们普遍意识到,此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的实用主义美学,而非杜威理论的简单注释,杜威的理论仅限于此书的前两章。杰罗德·列文森(Jerrold Levinson)在《心灵》上的评论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将这本书中“艺术哲学的新方向”视为一种范例,这种范例所表达的是“英美哲学美学的新趋势,这一趋势的特点是对国内外后现代哲学所带来的挑战更强有力的参与,以及对流行艺术及其产品更为持续的关注和处理”,并认为书中杜威的部分是其中“获益”最少的。即使是杜威的追随者们,如詹姆斯·斯科特·约翰斯顿(James Scott Johnston),也认为《实用主义美学》“在一些明显的方面比杜威走得远”,因此此书“不应作为对杜威的阐述来阅读,而应作为下述思路的一个事例,即,实用主义如何为目前21世纪的美学讨论作出贡献”[注][美]杰罗德·列文森(Jerrold Levinson):《实用主义美学评论》,《心灵》1993年第102期;James S. Johnston:《现时代的 杜威美学》,《美育杂志》2001年第35期。。此外,因为本书寻求美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而非依然受限的实用主义读者群,我最初将实用主义限制在副标题里,称之为“生活之美,艺术之思:一种实用主义美学”,以突出自己的目的,即发展一种后现代美学,它能够恢复艺术之美的重要性,并重申古代思想中将伦理视为生活艺术的观点。但编辑史蒂芬·钱伯斯基(Stephan Chambers)本着敏锐的市场本能和出版知识建议我改变标题。他认为,我提出的主标题虽然具有吸引人的鼓动力,却过于模糊,这使其很难成功地在书籍市场运作的主要方式——分类目录系统和交叉上市系统——中起作用,而“实用主义美学”却定义了一种既具辨识度又新奇的新哲学流派,它源于确立了的实用主义和美学领域。而且,通过提出一种令人兴奋的新理论风格——能够挑战或充实关于艺术的分析哲学风格——的存在,如“实用主义美学”这样的类型性标题也许能够借助我最近在布莱克维尔出版的著作《分析美学》的成功。因此,钱伯斯调换了我最初对标题的提议,(经我的允许)书的英文版标题定为《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
回过头来看,出版商对书名的改动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一行为促成这本书的成功,也推动了由其所命名的流派的有效确立。今天,在拥有快速搜索引擎的互联网时代,无论何时,人们只要输入流行的术语“实用主义”和“美学”,《实用主义美学》这本书就会立即出现在搜索页面的顶端,如果用“艺术”替换“美学”,该书也会出现在前几个搜索结果中。早在1990年,互联网搜索引擎得到广泛应用之前,图书馆数据库也有着同样的分类逻辑。搜索有关实用主义和艺术的研究的人会被直接引向《实用主义美学》,这说明,确实存在一个由该书命名和处理的重要哲学运动或学术领域。令人惊讶的是,该书的最早两个译本——由法国和德国主流出版商出版的精简版本——并未采纳编录逻辑将“实用主义美学”作为主标题,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强调“生活艺术”这一概念,并将谈及实用主义的部分放在副标题。法语版的书名是L’artàl’étatvif:lapenséepragmatisteetl’esthétiquepopulaire;德语版的书名是KunstLeben:DieAesthetikdesPragmatismus。[注][美]理查德·舒斯特曼:L'art à l'état vif: la pensée pragmatiste et l'esthétique pop ulaire,Christine Nuille 译,Paris出版社,1992年;Kunst Leben: Die Aesthetik des Pragmatismus,Barbara Reiter 译,Fischer 出版社, 1994年。事实上,这本书的前四个译本都没有在主标题中使用“实用主义美学”,其中三个甚至连在副标题中都没有使用。如果这说明实用主义美学的概念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还过于陌生,那么该书的国际性成功明显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这本书之后的十个译本只有一个(以一个在语言上作调整的相关术语代替)未在主标题中使用“实用主义美学”。[注]唯一一个例外是1999年的日文译本,这个译本以德文的5章译本为基础,但是从英文直接翻译的。标题是“流行艺术的美学:从实用主义美学的观点看”。《实用主义美学》的15个译本及不同删减版的完整列表可见于我在为就此书开的座谈会上 写的文章,收于《实用主义和美国哲学欧洲杂志》,2012年第4期,这本杂志还发表了Paolo D'Angelo, Krystyna Wilkoszewska, Heidi Salaverria 和 Roberta Dreon的文章。我文章的标题是《回顾实用主义美学:历史、评论和阐释——20年之后》,第267-276页。显然,实用主义美学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认知度很高的概念,这一概念可以自信地(几乎是毫无争议的)追溯到杜威以定义杜威自己的美学,尽管杜威不断强调的是相反的方面。[注]杰出的杜威学者 Thomas Alexander,仍对将实用主义美学概念与杜威联系起来表示犹豫。他为美国哲学进步协会年会中的“实用主义美学:回顾与展望”座谈会写 过一篇文章(纽约,2012 年 3 月 17 日)。在文章中,他坚持认为“实用主义美 学”是惊人的说法,并以“伴随这一术语的不适感”开题。我引用了他演讲草稿的第1页,这些草稿是我作为回应他的文章和其他三篇座谈会上的文章的应答者身份收到的。
我相信“实用主义美学”在哲学和人文学科讨论中将会继续成为一个熟悉的术语,因为它有效地标示和促进了一个广泛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以不断拓展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为基础,这一传统的向善改良论观点通常致力于超越理论话语的界限,并改善我们的经验。这种经验不仅与艺术相关,也与日常生活和构建我们全部经验的社会政治现实相关。如果这意味着实用主义美学价值的最终证据就其自身的标准来说不能仅限于学术话语内的流行,而应包括改善非学术和非文本的现实,那么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学术话语能够有助于塑造其他现实,正如其他现实塑造学术话语一样。
——充满艺术的实用主义者Eva S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