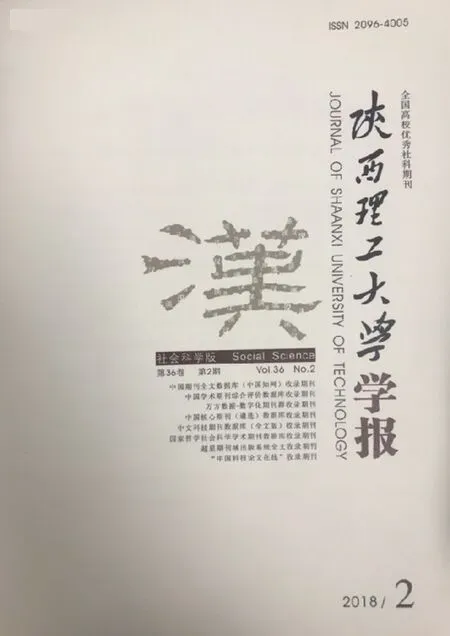学文与文学:林传甲大学堂教学观念论
火 源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一直以来,人们关心林传甲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问题,对他在京师大学堂的文学教学活动却很少涉及。原因是相关材料仅限于1910年武林谋新室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本文之所以可以讨论他在京师大学堂教学时的观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在京师大学堂使用的另一部讲义——《练习各体文字讲义》被“发现”*笔者在北京大学访学时查阅清末民初资料时偶然发现。。《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发表在1905年的《南洋官报》上,奇怪的是这个讲义至今没有被人提起过。与它一起发表在《南洋官报》上的《中国文学讲义》,即一直被讨论的《中国文学史》,也同时被发现。它是从《南洋官报》1904年第143册开始刊行的,比通行的宣统本(1910年武林谋新室版)早6年,也就是《中国文学史》成稿后不久。奇怪的是它也没有被人提到过*吴绍礼的《著名学者林传甲考》(《绥化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曾提到《中国文学史》被《江南官报》转载,不知是不是笔误。。
《练习各体文字讲义》是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和大学堂预备科的分类科第一类学科(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中国文学科目的课程。因为癸卯新学制刚刚实施,大学堂的新课程尚在建设中,其师范馆只能参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实施*“师范馆可作为优级师范学堂,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参见《奏定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391页)。。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目次》里说自己教的课有“公共科文学,每星期三小时,分类科文学,每星期六小时”,三小时的课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即他所说的“历代文章源流”(其实应该是第一学年公共科的“历代文章源流义法”[1]416),按《练习各体文字讲义》上所说,该门课每星期六学时,查《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可知,师范馆只有这门课是六学时,因此可以推知“练习各体文字”正是林传甲担当的分类科文学主课*见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目次》,武林谋新室1910年版,第23-24页。关于《中国文学史》课的情况可参阅陈国球对于林传甲《目次》的解读。。
正因为发现了第二部讲义,使初步了解林传甲的教学观念成为可能。当然林传甲的中国文学课不是真正的大学堂文学科中国文学门的课程,但是他在设计“历代文章源流义法”课程时借用了大学堂文科大学中国文学门的两门课程,一门是“文学研究法”,用其要义作为《中国文学史》的骨架,另一门是“历代文章流别”,借鉴了章程上对其科目内容的提示,参考了日本人的《中国文学史》。如果由林传甲来讲授大学课程,内容也会大体相近,也许深度会加深一些。另外,因为他讲授的是师范科目,需要兼顾中学的教学*“此日为师范馆之讲义他日即为中学堂之读本”见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序目》,《南洋官报》1905年第25册。,所以还可以从中了解他对中学教学的想法。由此,“深入解剖林著,对我们理解京师大学堂的教科书建设,以及新学制下的文学教育”[2]11,绝对非常有益。本文主要关心的是作为旧读书人的林传甲在大学进行教学实践时的想法是什么,借此了解旧知识体系与新式教育体制结合的实况。以下关注他三个有特点的方面:身份定位、趣味标准和文学教育方法及观念。
一、 身份定位
作为大学堂教师,林传甲当然是教师的身份。但是这个教师并非新式教师,而是古文家型的教师。虽然他不认为自己属于古文家,他会在评注中直呼“古文家”名号,指代他之外的某种人,但是他的教师身份却带有古文家色彩。大体上可以说,他的选择是带有古文家气味的开明旧文人。
首先,他的教学中有古文家的影子,他自愿继承了古文家传统。林传甲的大学堂教科内容以文章为主,所选课本体例参照古文家的选本。他在《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序目》中追溯了总集的源流,从《文选》到《文苑英华》,再到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直到曾国藩,其中他明确表示肯定的只有桐城派古文家。他说:“姚惜抱《古文辞类纂》分为十三类,颇得要领。曾文正则区为三类,尤为简括”[3]。他自己把要讲授的文体分为四体:治事(谕告、国书、敕书、诏书)、纪事(本纪、世家、列传、载记)、论事(论、策、议、辨)、文事(赋、颂、箴、铭)。四体正好与曾国藩的三类(著述门、告语门和记载门)对应。“治事”对应于曾氏的“告语门”,“纪事”对应于“记载门”,“论事”对应于“著述门”中的论著类和“告语门”的奏议类,“文事”对应于“著述门”的词赋类——几乎不出曾国藩的藩篱。
他的文章论也受古文家影响。如《中国文学史》的大纲虽然来自“文学研究要义”,子目却是他个人所加,代表他的个人趣味。其中谈论诗歌的内容很少,比较集中的是第七篇《三百篇兼备后世古体近体》和《淫诗辨正》,其他还有辞赋部分算是现代意义上的诗。表面上看,他的选择可能是受到“文学研究要义”中反复出现“文体”一词的影响,所以偏于文的论述*陈国球、夏晓虹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点,参见《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陈国球)和《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夏晓虹)。,但是仔细辨析也可以看出这属于桐城古文家的印记。姚鼐、曾国藩的选本中都很少涉及诗,即使涉及了也主要限于《诗经》中的篇什,特别是雅颂;还有就是屈宋的辞赋也为《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共有*其实他认为“屈宋骚赋皆骈散相合之文”(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1910年版,第195页),这个文不是广义的文,而是骈散相对的文。。此外,林传甲还把古文家著作当作自己讲义的重要参考文献。比如他只摘录了《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纪》,目的是“明其源也”,同时指出“深究者当取归方二先生评本观之可也”[4]。说明,他选文的参考文献是归有光、方苞等古文家的评本和选本。他不过是择其精要,附加自己的意见而已。
与此同时,在桐城古文家传统的两个重要角色“治化者”和“教书匠”中间,他明显倾向于前者。“治化”是治理教化之意,曾国藩、姚莹等办理实务、建功立业的人,属于桐城古文家中偏于“治化者”角色。而“教书匠”则是姚鼐、刘大櫆等人所承担的角色,虽也属于教化,却是比较边缘化的一部分人。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第四篇《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中将两者提出来,“夫政者治化也,布在方策者文也”[5]51,教书匠所教的不过是“遗文”,而林传甲心心念念的都是为国家出力。他在选文的评论中经常显示自己的远见卓识,目的大概在于求进身。他不满于清廷闭塞言路,在《后汉刘陶改铸大钱议》的评语中写道:“夫汉之太学,今之大学也。汉之初叶太学博士品位最尊,其末叶太学诸生犹能上书言事。榰柱艰危,故可贵也。今章程明禁学生干预朝政,尚何言欤!尚何言欤!”[6]他认为大学堂教师和学生应该有地位,并有义务提出建议,成为国家支柱。他又说:“学而后入政,固古今之通义,中外之公理也。”[5]51可见他的自我期许。在姚鼐和曾国藩两者之间,他明显更认同后者。背后的原因是事功的力量。后来他外放广西,大概会让他有志得意满之感吧。
虽然孔子因为正道不行,退而施教,对于热心治化的读书人具有安慰效果。但是传统中国士大夫于“三不朽”中首选立功,最后才是立言,教书当然更是等而下之,希望的是“乘舟梦日边”,哀叹的是“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古文家的特点在于他们把这种观念灌注在文学教学之中。姚莹曾明确将桐城派要义归纳为“义理、经济、多闻、辞章”。曾国藩也讲“经济”。林传甲步武前辈古文家,在《中国文学史》第十二篇的一条注中写道:“为史以时代为次。详经世之文,而略于词赋。”[5]143写史少不了一条时代变化的线,但是具体写什么,却可以加以选择,他的做法就是详论具有经世意味的文章,而论辞赋则比较简略。尽管他也从乾隆的诗文集中发现“词章亦未尝无用也”[5]51,但是治化总具有优位性。在选文中大讲经世致用的学问就是古文家实现治化理想的代替方式。
有清一代,桐城派受惠于“四祖”筚路蓝缕之功,在乾隆朝就有“京城官生半桐城”的盛况,后经曾国藩的振发,直到清末,古文家在文人中越来越有影响。1901年古文名家吴汝纶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连严复都服膺桐城古文。后有林纾、马其昶、姚氏兄弟等古文家盘踞京师。《奏定大学堂章程》也离不开桐城派推崇的“义法”、“言有物”、“言有序”等作文之法。这些细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文家在当时的笼罩性影响。林传甲既然为严复所推荐,他也不可能不与严复气味相投,取统一步调。再有,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大多为教书匠,从戴名世、姚鼐、梅曾亮到林纾、马其昶、姚氏兄弟,都曾教授作文或一辈子教人作文。因为癸卯学制时期的国文主要是作文,在现代教学法尚未占领学堂的时候,传统的教书先生们无疑成为模范。难怪林传甲论文学史不出“文章学的视野”[7],因为他继承了古文家传统,关心文章的教学。
在古文家中,因为他更接近于事功派的曾国藩,所以稍微超越了教书匠的固执。他的《中国文学史》肯定了骈文在文章中的地位,他特别在文章变迁史中辨认出骈散分离的大势,在最后一篇(十六篇)宣告了骈文产生的必然性,这使他的论述几乎涵盖所有“文”的体式。在古文家的主要选本中,《古文辞类纂》不包括骈文,《经史百家杂钞》才加以补充,你可以说他接受了曾国藩的新观念。你也可以因为“骈散古合今分之渐”本来就来自“要义”,说这是被“文学研究法要义”引导的结果。但是,他对于曾国藩事功经济能力的喜爱,使他更接近曾国藩的通达,让他从本性上视“兼顾骈散”为当然,希望调剂一般古文家对于散文的偏重。当然,他与曾国藩又有一点不同,他更加重视明清文,特别是所谓“国朝”的文字,不像曾国藩偏于秦汉文。总之,在认识到他继承了古文家传统的同时还要看到他对古文家也是有所择取的。
林传甲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至少他并不是那样明确意识到。相反,他毕竟身处清末动荡的现实中,他面前的问题与曾国藩面前的不同,是文化性质的,因此感受也更强烈,这种背景使他寻求拯救的办法。另外,他又是思想比较活跃的人,自认是比较通脱的一派,因此他的思想更为开放。他的开明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就是他适应时代需要对古文有所矫正,丰富了古文的内涵。比如他增加了古文中科学的成分。他在一条注中说:“姚姬传言:考据、义理、词章缺一不可;传甲言学术则谓:天算、地舆、人事、物理缺一不可,考据、义理、词章则四者之佐助也。曾文正公所谓经济,亦非明于此四者不可也。”[5]51-52天算、地舆、人事、物理几乎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按照他的理解,文章是科学(当然他不可能用“科学”这个词,那时“科学”还有科举的意味)的从属,而治化(约等同于曾国藩所谓“经济”)也必须借助于科学才能实现。科学为学术的冠冕,文学乃学术的从属。他甚至说过:“以文学为专门各学之鼓吹亦何不可。”[8]此处“文学”有一些文章之学的意味。
他这种观念自然是受了外患的刺激。林传甲在武昌两湖书院时关注过格致学,1896年(丙申)秋湖北改化学堂为武备学堂,他与几个老友才因此辍业[9]。后来虽然他没有再深入地研究,但因此开阔了眼界,深知科学的重要。他推崇能描写自然风物,因此方便格物的“赋”体,赞扬那些好赋“所赋不出天算、地舆、人事、物理四端,皆可益国民智识,发国民之感情者也。鸿篇巨制美不胜收,犹桂林一枝、昆山片玉耳”[10]。他的历史时代和家国经历使他给传统的古文增加了新鲜的内容。他的提法是顺应时代需要给古文指出的开新之路,希望古文能涵容新知识,获得新生命。
他自己解释过自己的立场。他在《晋江统徙戎论》中赞扬江统的《徙戎论》,当然因为江统只不过是一个小官员,而能高瞻远瞩,非常难能可贵。他说:“是论深惟至计,欲杜四夷乱华之萌,其时君相莫能用,未及十年,而五胡祸起,世人乃服气深识焉。呜呼,晚矣。”[11]更为重要的是,他同情江统命运,为国家痛惜。在《中国文学史》里也提到此篇,并痛斥前人“无识”[5]156。如此念兹在兹,不免让人感到他对江统的同情,其中含有对自己的哀悼,他对江统的赞扬,其中含有对自我的期许,希望当权者能发现他的远见卓识。就文论文,他直接表达了对《文选》和《古文辞类纂》的不满,指责它们没有选这篇关系民族命运的好文,并且认为原因是:“昭明,文士也,桐城,古文家也。”他自己与他们不同,他说“各国国文读本皆选其与国际相关之文,传甲忝以国文自认,故所著录与文士及古文家略区别焉”[11]。也就是说,他的独特眼光源于他忧国忧民、识见超卓、深通时务、思想开明、关心内政外交,是属于时代的读书人。
总之,他除了是个继承古文家教书传统的读书人,还是半觉醒的、具有开明色彩的、睁眼看世界的那群读书人之一。虽然他时而在涉及正统的时候表现出一点冬烘气,比如对女学的偏见[12],这是时代的局限,但是一旦关乎时事,他颇能执中冷静,比如《今人东三省善后策》中评论道:
甲午以来士子皆有挟策自雄之意,顾其策,不尽可用,亦未有用之而著效者。遂致侈口空谈,徒滋横议。论国文者乃欲以报章体裁悬为厉禁。呜呼,是殴党人游士以资外国矣。租界洋旗非今日国权所能及,亦何用此掩耳盗铃之举耶。报馆之策亦何不可,河岳涓埃之助。余于课余浏览,惬心者实不可多得,著录是篇,嘉其立论之不激不随也[13]。
他对于被视为革命党的人,也保留一点平心而论的态度,不满政府禁止报章,觉得那种愚蠢举动无益有害。他对于骈文的同情另有根源,他从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理解骈散分离的趋势,他说“大抵文明之国,科学程度愈高,则分科之子目亦愈多,诗文之用古体骈体,各视乎性之相近,及用之适宜耳。又何必相讥相诋乎。”[5]205他从文明发展的规律来认识骈文的发展,因此与曾国藩不是一个层次。他的开明看法说明他果然属于稳健一派,具有爱国热情,爱文化,是思想观念上已经出现变化的传统士大夫。他自己的话最可以作为证据,他在《国朝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中慨叹“魏默深之言不早用,则东南海防日亟;龚定庵之言不早用,则西北之边界日危”,并表明自己的认同,“传甲欲远师顾黄,近友龚魏”[14]。由此可见,林传甲的心中除了古文教书匠之外还有一些偶像,就是顾炎武、黄宗羲、龚自珍、魏源等这一类心兼天下、学以致用、开明通达的读书人。
二、 趣味标准
林传甲的趣味体现在他选文时的倾向上,与他的角色认同紧密相关。大体来说,他的趣味受到古文家的影响,如选择思想正统、忠君爱国、不悖于“道”的文章,兼顾“义理”、“考据”和“词章”。但是又有与古文家不同的特点,即时代性或者现实性。他的一些有个性的选择,往往是根据时代和现实的需要而做出的。
林传甲选择某些文章,是含有现实针对性的,要与现实对话。比如他选择《大清世祖章皇帝入关告谕》,该文写的是满人刚入关时顺治并未严格要求薙发,林传甲在注里进一步说明了后来的发展情况,即在福王被消灭以后,清政府改为明令全体薙发,对此他解释说,满人刚刚入关的时候,“惧殷顽弗率,将铤而走险,故黽勉羁縻,不易旧俗。既而中外一家,制度必当划一。然后革故鼎新,用昭法守。今海外华工戴我朝三百年深仁厚泽,犹不忍去其发辫,谈时务者不能深究东西之政治学术,而亟亟焉易服为事,岂足以谈时务乎”[15]。他选择该文,并加说明,潜在的读者是那些反清的谈时务者,告诉他们:世易时移,统一制度势在必行。并以海外华工不愿剪发来说明薙发的文化意义,指责谈时务的人不通历史情势。
他在选文里还表达自己的忧愤,比如在《国朝凌廷堪金宣宗迁汴论》里,他注解说:
世宗朝,女真人习染汉俗,日以文弱,虽极力整饬,不过奉行故事耳。世运相乘,蒙古继起汪古之界,垣既破,臚朐衣带岂足以限铁骑乎。野狐岭之败,蒙古人以少胜众,金人之气夺矣,况屡战屡败之后乎。吾谓世之大国与小国战,慎勿竭国之全力以自敝也[16]。
前半部分论述金朝人如何被汉族习俗影响,而日渐萎靡,后来遇到蒙古人的兴起,在野狐岭之战受到重创。后半部分虽然分析的是金人失败的原因,进而论普遍的道理,但联系当时的背景,可以感到他的潜在意思:属于金人苗裔的满族,面临同样的命运,民风日弱,不慎于甲午之战大败,再败于庚子,国本动摇,赔款割地,丧权辱国,原因都在于当国者不能慎重行事。这里虽然是评论金朝旧事,但是别有幽怀,语含讽喻。再如选《大清圣祖仁皇帝平定台湾上谕》,借机谈论台湾问题,并发出感叹:“吾闽人也,吾不敢忘我闽人之殖民地也。吾中国人也,吾不敢忘我中国之殖民地也。呜呼,台湾之中国人,犹仍我中国衣冠之旧式也。”[17]《大清宣宗成皇帝遗诏朱谕四条》希望后人体察道光皇帝的隐衷,“怀春秋复仇之志”[18]。《宋苏洵辨奸论》是论“识人”的文章,林传甲评论时也联系当时的国家环境,批评宋代应该变法自强之时,不能适当推进,变法者操切从事,而反对变法的奸臣误国[19]。从这些文章看,林传甲的深切家国之思不是很清楚的吗?
他在选文中抒发自己的家国之思,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下面再多举几例。《飞猎滨共和国布告各国书》中说:“吾置华盛顿建国之国书不录,特录此篇不仅为中国文计也,更欲策励我黄族诸小国闻风而自立也。”[20]在评论《南朝宋鲍照昭芜城赋》这种表达黍离之悲的文章时,更便于抒发自己对国家的感情。他追忆了洪杨作乱,荼毒生灵,义和拳蹂躏畿辅的惨状,他写道:“传甲登正阳门城楼,犹亲见劫火余痕,为之仰天泣血也。”[21]从这些评注的文字中可见林传甲的热血悲情。除了选文和评论以外,文学史也成为他寄托现实关怀的载体。如《中国文学史》第十三篇中有“呜呼,中国能自强,夷人虽通中国之文,不过为藩属耳。不自强则草泽不识字者揭竿起,其锋镝之祸,亦无殊于戎狄也”[5]158,表达了对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殷殷期待。统揽林传甲的各种选文、评论和史论,其中有自强的渴望,有国破的悲伤,还有中国学堂在格致学方面的落后感到的羞耻(《唐仲无颇气毬赋》)[9]等,几乎是一有机会就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关怀。
在《中国文学史》第九篇《学周秦诸子之文须辨其学术》的注解中,他反对张之洞。张在《章程》中提出,对于周秦诸子的文章,只论文,而不学其“学术”[1]357。林传甲则认为儒家以外还要学诸子的原因就在于可以补助儒家所不及,他坦承自己读诸子的文章,“必辨其学术不合于儒家,惟求其可以致用者”[5]116。奇怪的是,林传甲对张之洞起草的章程几乎是尽可能遵从的,但这里却加以抵抗了。陈国球猜想这种想法大概是维新派言论,与康梁相近[22]55,其实不尽然,他一反常态,背后的原因是他强烈的“致用”观念。
为了致用,他在研究周秦文时,不敢卖弄周秦时代的奇字,以炫耀博学,不敢宣讲诸子的不正统说法,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当时中国所不需要的。相比于外国的拼音文字,中国文字正在遭受质疑,认为“过于艰深”,于此同时,墨子、老子等先秦学者开始重新受到重视,与时代新说一起成为危及儒家正统的力量,林传甲认为这些都有害于中国,认为都是没有好作用的,容易误尽天下,无补于事。所以他不怕被讥笑为“疏陋”,不在《中国文学史》中多加涉及。他研究学术的目的就是要对社会对文化有所补益。他寄希望于“笃实致用之士”能够赞同他[5]116。他取悦的对象是那些不重虚浮、讲究实效的士人,他自己也正是这种人,具有相同的实用趣味。
还是为了致用,他对文章形式也提出特殊要求。他认为古代把“论”体分为八种过于繁琐,指出其弊端在于容易导致“空论无实”。他自己只分两种:事前之论和事后之论。前者选择的标准是看它是不是后来得到证实,后者选择的标准则看作者论文根柢是否深厚,简言之就是有根有据。事前能够提出预见,后来得到验证的,这种文字最为有用。事后才加以总结的,毕竟可以总结经验以利益后人,也算是有用的,而对于那些当时受到追捧的所谓“名论”,现在已经是“陈言”的,则因为无裨于事,所以一概不选入[23]。更不用提那些没有得到验证的空论,更是排斥在选文之外。他讲到自己对于文体讲解的原则,虽然说“凡古人文集中所有文体之名咸甄采不遗”,好像没有区别,既包括“古今皆有之文体”,也有“古有今无之文体”,还有“今有古无之文体”,但是他却不是无所偏重的,他在后面特别强调了“附以今人之程式,学归于致用”[3]。他在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原则,体现在讲授骈文的同时,更强调骈文有用的篇什,肯定“陆宣公奏议为骈体最有用者”[5]205,借以打破骈文的自我限制,引导它向有用的文体发展。
林传甲强调文章为时代服务,强调实用性,以有用为导向,这些有着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在原因是他本身是被时代惊醒的开明士人,他不满于文人脱离实际,反对文人要么只认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要么沉迷于时文八股,不涉及当时时事。他认为这些文人“临事不能治事,所记所论皆古之陈言”,于是“文事一端亦趋于空疏纤巧,无复博大昌明之钜制”,造成的结果是“文运降,世运益降”[3]。与之相反的是域外的文教。林传甲是睁眼看世界的人,在讲义中多次提到欧美的情况,隐隐以他们为效法对象。他这种识见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中国的困境引导他重视现实,反对虚文,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至于外在因素,大体有三点。首先是官方要求。皇上要求办学堂的宗旨是“博通时务,讲求实学”[1]6。学堂这种形式在西方列强那里已经被证明是有教育国民实效的工具。中国本来学术自足,而今在科举之外另开一门,目的就是为了改良中国应时人才的短缺状况。很自然地,学堂教育要把实用性看作先决条件。况且,学制变化根源于文化危机,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想法最易追求实用。皇帝的意旨也体现在学制的各章程中。《奏定学务纲要》(1904)中说:“近代文人,往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辞章之外,于时势经济,茫无所知。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诚痛乎其言之也!盖黜华崇实则可,因噎废食则不可。”[1]493-494虽然这处引文带有一点折衷的意味,但是新学制针对的到底是那种虚浮的倾向,肯定了“黜华崇实”。林传甲作为一名国文教员,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大体按照章程来设计课程内容,他在与章程设置者之间的对话过程中,认同了章程的看法。
其次,自明末清初开始,到晚清尤烈的“致用”思潮对于林传甲也有巨大影响。明末陈子龙、徐孚远等不满晚明“帖括清谈派”的脱离实际,选编《皇明经世文编》,选取关于军国、济于实用者;清初吸取明亡的经验,顾炎武联同黄宗羲、王夫之、唐甄、颜元、李塨等人,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品评时政,提出各式“匡时济民”的改革方案,使“经世致用”思想从明至清一脉相承。晚清龚自珍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再次接续此脉,影响及于魏源。魏源主张通经致用,黜虚崇实,于他参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高扬顾炎武旗帜。后人踵事增华,又有多部续编。世纪末属于这个潮流的还有谭嗣同、梁启超等。有越来越多的士人反对虚文,强调致用。林传甲自称踵武顾、黄、龚、魏,正好表露了他遵从此流脉之精神,很显然他属于这个致用的潮流。
再次,影响林传甲的还有当时的学堂教育观念。当时,教育者认为国文中有国粹。有人从万国通例的角度来认知从小学到大学设置国文专科,“以立国民爱国之宗旨”[24]的重要性。林传甲教的师范国文更要以之为题中应有之义。按照《初级师范教育章程》的观点,“师范生将来有教育国民之重任,当激发其爱国志气,使知学成以后必当勤学诲人,以尽报效国家之义务”[1]401。也就是说师范国文教育更强调新型国民的养成。林传甲明确认识到“国文为国民教育之原”,他选皇帝谕旨入文,就因为“我列祖列宗圣训”可以让边缘地方的学子“发其爱国热诚”[25]。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但图晏安,是非颠倒,民智日锢,外患日多”[26],这些都需要让后人认清现实,努力改良。他高度重视国文的功用。他选择苻洪的记述,就因为希望“论国文者”,“重国防也,料敌情也”[27]。他在序中交代他的写作原则是“不足以激发志气、范围道德、增益智识者,则弗录焉”[3]。他之所以选择这类具有时代现实意义,令人血脉贲张的故事,无非是为了发挥国文的教育作用。在《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初编的最后,他特意选了《国朝陈文述长白山铭》,并说明自己的想法:“名山大川,国之镇也。爱国者因之以发国民之感情……今编辑练习各体文字初编将成,勒此铭为之殿,藉以联国民之感情焉”[28]。这种瞄准新型国民,欲培养为国家办事人才的意图,使他的选文都不是空谈,而是有现实针对性,希望对当时人们的错误观点有所补正。
三、 文学教育方法及观念
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中国文学课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考镜源流和“文体”教学相结合,也就是以“文体”作为单元讲授写作规范,又以“文体”为基本角度梳理作家和作品的源流。讲“文体”的时候兼及源流,讲源流的时候以“文体”为关注点。他的文学教育观念是文章写作与文学知识传授相互为用的传统观念,这个观念体现在其教育方法上。
他的《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就是按照各种“文体”练习写作的意思,分为四大类,每一大类又细分几种文体。他的《中国文学史》也以“体”为主,当然这里的“体”除了“文体”(如群经文体、史文体)以外还有字体、作者的“体”——风格(如诸子文体、杜牧文体等)等内涵*只有音韵,训诂,作文法,修辞法等是例外。。林传甲的中国文学教学依赖“文体”是显而易见的。他自己似乎也把“文体”当作文学本色当行的东西。他在《尚书今古文辨体》一节中,有一句说明:“传经源流,经学王教习讲义已详,此节以文体为主”[5]82。这句话的意思是,经学门中讲这些经传文章的意义,中国文学课主要讲它们的文体。当然经传之外的诸子、史著和文集上的文章,他会兼及意义和文体。这反映了他在知识分科的背景下形成的观念,即文学科应该注重文章的形式因素,即文体是“中国文学”关注的重点(也许他不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
表面上看,按文体讲文章似乎受到古文选家的影响。诚然,他直接承受的影响来自古文家,但是连古文家的惯例也是渊源有自。在中国文论传统中,“辨体”从来是讨论文章的重要环节。《文心雕龙》以来的文论常常认为“文章以体制为先”*[宋]倪思语,转自徐师曾《文章纲领》,《文章辨体序说·文章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文章之道,贵于辨体,辨体之法,首在分类”[29]。“文体”在古代一直是文章的编排方式,也是学习写文章的辅助工具。评论和创作都从辨体开始。到林传甲讲课之时,这种传统观念也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林传甲与包括古文家在内的传统学者不同之处,在于他增加了源流追溯的意识。《练习各体文字讲义》本来是为了学习作文的,应该是非历史的,但是在同一文体中,林传甲也会注重源流。他解释自己的写作原则是:“首列古文溯其源也,详列今文广其用也。”[3]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即每种文体讲解的开头都有一段简短的源流追溯。比如“策”体,追溯源头到《帝典》,到《战国策》,到“制策”、“试策”之体,到“条对”之体,再到各国“政治艺学”。梳理流变,加以点评。这种体例在《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中都没有。说明林传甲在文体讲授的时候也兼顾源流的考镜,虽然内容不多,但发凡起例的背后是比任何一个古文家都更强烈的一种历史意识。
另一方面,在本来是追溯源流的《中国文学史》里,林传甲又兼顾文体教学,也就是注重在文学史中展现每种文体的优秀文章范本。林传甲在一条注里说:“文学史例录全文,讲义限于卷幅不能备录。”[5]143他认为文学史按例应该收录好文章的全文。这种想法反映了他心目中的文学史就是《文苑传》那种体例。《后汉书》创立《文苑传》,其中有大量引文,很多好文章借以流传。因此,自史书记载文学历史起,它就具有展现经典范本、供后人学习的性质。但是这个传统却没有得到强势的继承,后来史书的《文苑传》大多收录太多作者,罗列生平、官职,收录作品的越来越少。林传甲却认同那种文学历史书写的传统,只不过因为讲义篇幅所限,不能载录。如果在《中国文学史》中附上文章全文,势必因为这个“历代文章源流义法”课的“文体”视角,使收录的文章成为例文,并且是那种“体”——诸如群经文体、杜牧文体等——的范本。也就是说,在林传甲的构想中,《中国文学史》除了要做“文章源流义法”要求的研究和讲解以外,还应该具有展现各文体中的好文,以供学者揣摩学习的意味。
由于以上两种结合构成文体与源流的双线结构,并且相辅相成,教学方法也就成为文体与源流相互配合的形式。这背后有他文学教育观念的作用。林传甲的文学教育其实包括“学文”和“文学”两个方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林传甲的两门课程大体对应两者,“练习各体文字”课对应于文章写作教学,属于“学文”,而“历代文章源流义法”对应于学术研究,体系化地把握各种文章和作家,属于广义的“文学”。关于“学文”,林传甲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特别强调学习文体。刘勰说,“童子雕琢,必先雅制”[30]309。自古以来学写文章就要学习文体,写出来的文章首先要合体。合体就是“雅”。而古代文人风格的把握也是为了品评文章,学习先贤的风格。古代讲规范,学习是为了学得像样合式、中规中矩,然后再求独特。
关于“文学”,林传甲则是把“文体”当作储存“文”的体系和抽屉。章学诚认为目录学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后人眼里,考镜源流本身就可以作为把握文章的一种体系,在时间中建立类似家谱式的谱系。康有为和章太炎讲学采取宏观统揽的视角[2]153-161,也是这种方式的传承。因为这种心理联系,使得《中国文学史》才进入中国的时候,更容易被看作目录学的一种手段。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第一篇《传说文之统系》里说,“兹篇述变迁大意,其各家要旨,俟经学说文学专科述之”[5]9。第二篇《古今音韵之变迁》题目下有小注:“本篇子目皆用大学堂文学科之音韵学,文从简质,专述变迁大要。”[5]13这两条材料可以反映出林传甲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史”不过是“大意”和“大要”,专门的研究还有待于“经学说文学专科”和“音韵学”,具体深入的研究当参考专书。也即“中国文学史”并非研究,只不过是知识框架,让学习的人粗知梗概,体例接近于书目提要,是做学问的门径。类似的夹注遍及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全书各处,反映了林传甲这种意识。有人说林著《中国文学史》抄录四库总目提要,从这个角度看也是很好理解的。
不光林传甲如此看,就是与他同时代人以及稍后未有现代文学史意识者也大体如此认识。林传甲写《中国文学史》后不久,刘师培写了《中国文学教科书》(1906)。他在序例中写道:“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篇法,次总论古今文体,次选文。”这种体例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的安排大体类似,先讲文字、作文法,后论古今文体,只不过林传甲被讲义体例所限未选文而已。该教科书即包括古今文章源流在内。同时,刘师培也说:“此编所列为读古书之门径,实则工文词之基础也。若以深文奥义目之,岂其然哉?”[31]3刘师培在指出《中国文学教科书》具有读书目录意义的同时,也认为“深文奥义”不包括在“源流”之中。当时人都认为“中国文学史”的最大好处是简单,是很好的学术指南,是大纲和概略。当然也有人认为简略是“中国文学史”的弱点,比如江绍铨称林传甲的讲义为“中国文学史”,语气中含有轻视之意。细品1905年1月6日林传甲写的自序也可以感到他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史》并不很高级,只不过比较简便。但是他们无疑都承认《中国文学史》最大的好处在于明晰,在强调速成的现代学堂,《中国文学史》这种概论性质的体裁非常适用。1918年北大教授们讨论《文学史》教授法时仍然认为:“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日。陈国球认识到《奏定大学堂章程》的研究文学要义与日本《中国文学史》根本是两回事[22]49-50,这样一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林传甲的双线结构是中国古来考镜源流的学术方法与抽屉式知识储存的结合。以文体来帮助学习者掌握书写文字的规范,而以体来把握文的知识归属。“文学”本身作为文献整体,即书写的总结果,是个知识体系,当然可以用四库的方式分类,也可以使用源流的方法加以梳理。这种方法一方面受到“文学史”这种新兴体裁的刺激,使考镜源流的文献方法重获生机,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当时来自日本的“国文”想像。张之洞说:“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宜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全为主。”[32]林传甲的“文”也有储存知识和保存国粹的意味,因此他才违背了自己“致用”的观念,在《练习各体文字讲义》中安排了“古有今无之文体”,并且排在“今有古无”文体之前。
当然,“学文”和“文学”两者在林传甲那里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融合的,“文学”是“学文”的基础,“学文”的目的是贡献于“文学”。于是,学习文体写作时需要整体文学的意识,而整体文学的把握少不了对具体文体的体悟。林传甲的文学史是教授知识、介绍书籍的体系,为了让学习的人知道知识总体,而另一方面,《练习各体文字讲义》教学生学习写作,为了便于揣摩同类文体的特点,学得体式。既是学习者学习写作的东西,又是承载过去知识的总汇。这种结合也与当时的“国文”想像相关。“国文”在当时包括识字作文和高阶的知识储备两个部分,后者是国文作为科学之基础*《公立学堂国文练习会启并简章》,《济南报》第160号。的根据,因为科学知识都在国文之中。也就是在中国语境下,写作联系读书,写作促进读书以及认识世界。
源流与文体在实际教学中又是交缠在一起的。那时的观念比较奇怪。林传甲在师范馆讲授三小时的补习课“历代文章源流义法”(《中国文学史》),在程度上似乎比六小时的“练习各体文字”还要艰深。本来,《章程》在第一年公共科中设置了“历代文章源流义法”课,属于概论性的课程。林传甲竟然参照大学堂课程“历代文章流别”(《中国文学史》参照其要义),其实“义法”本来是有关作文的,但是讲源流,粗具文学史的体例。他把后面的概论性课程放到前面来,至少他自己没有感到这种安排的不合理。其实,如果考虑到总论性知识的必不可少,再考虑到古代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性质,那么它出现在前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癸卯学制的各《章程》,在设置课程时,就有在讲授各体文字的同时,从中学堂起开始讲授“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和“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1]320,第五年“兼讲中国历代文章,名家大略”[1]325;高等学堂于第三年“兼考究历代文章流派”[1]331。这些带概论色彩的课程与“练习各体文字”是并行的。不过,练习文体写作贯穿始终,而源流这种概论课程在低级学堂较少,而且较浅显,同时也总是在各级学堂的高年级讲授,但是对于整个现代学堂教育来说,源流课程与练习文体就有交叉的情况。当时的癸卯学制很可能暗含一种“刷墙式”的滚动“学文”模式——一种从低到高循环提高的方式。文学史(文章源流和框架性的知识)教育贯穿在学习写作的整个过程之中,从“文”向“学”发展,形成一种“学与文”、评论与写作相资为用的关系。现在的语文教学在低年级就只有作家的零碎知识,而缺乏总览性质的文学知识概述。
文学史视野的培养一直伴随着文章的阅读和练习,不是前后,而是相互辅助。从小学到大学堂都在讲授文章的写作,只是程度逐渐加深,也都在把握中国文学知识。前者就是所谓“国文”学习,到大学就成为“国学”。文为学,学为文,相互配合。林传甲的教学以“体”为主,就因为这种框架既是传统的文章写作时使用的,又是文学知识把握对象时依赖的工具。可能正因此,《中国文学史》为了配合作文教学,所以其中更多强调文,并不涵盖全部文体,也因此林传甲认为大学堂不应该讲授小说戏曲,因为大学堂不应学习写作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小说,他批评笹川种郎,自乱其例,识见污下[5]182,大概与他的文与学配合的设计有关。
以上分析了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教授中国文学时的观念,这些观念虽然在后来没有得到继承,但现在回顾它并非没有意义。首先,因为以前不了解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的整体教学观念,因此造成对他文学史观念的种种误解。比如,对他的《中国文学史》,无论是赞扬他在中国文学史写作方面着此先鞭,还是指责他不懂真正文学史体例,都不算中肯。因为不了解他和他的时代对文学史的看法,不了解他们的文学教育是把文学史与文章写作相配合,也不了解他认同的“国文”观念把“国文”当作教育国民的工具。补全对他教学观念的认识,可以客观评价林传甲文学史写作的功绩。其次,得益于找到林传甲这个“缺环”,可以更细致地了解《新青年》同人开创的新知识范式与文学传统之间的转换细节,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新文化运动中可能存在的民国新学制反拨旧学制的一面。最后,还可以借以思考学术史对国文教学的意义,提供语文教育改革可以汲取的资源,寻思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结合的其他可能性,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读写能力和文化水准。
[参考文献]
[1]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2]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序目[J].南洋官报,1905(25).
[4]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黄帝纪[J].南洋官报,1905(27).
[5]林传甲.中国文学史[M].杭州:武林谋新室,1910.
[6]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后汉刘陶改铸大钱议[J].南洋官报,1905(48).
[7]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M]//陈平原,陈国球.文学史: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8]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国朝梅文鼎拟璇玑玉衡赋[J].南洋官报,1905(32).
[9]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唐仲无颇气毬赋[J].南洋官报,1905(31).
[10]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赋[J].南洋官报,1905(31).
[11]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晋江统徙戎论[J].南洋官报,1905(29).
[12]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晋张华女史箴[J].南洋官报,1905(52).
[13]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今人东三省善后策[J].南洋官报,1905(38).
[14]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国朝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J].南洋官报,1905(50).
[15]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大清世祖章皇帝入关告谕[J].南洋官报,1905(25).
[16]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国朝凌廷堪金宣宗迁汴论[J].南洋官报,1905(30).
[17]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大清圣祖仁皇帝平定台湾上谕[J].南洋官报,1905(25).
[18]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大清宣宗成皇帝遗诏朱谕四条[J].南洋官报,1905(57).
[19]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宋苏洵辨奸论[J].南洋官报,1905(29).
[20]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飞猎滨共和国布告各国书[J].南洋官报,1905(34).
[21]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南朝宋鲍照昭芜城赋[J].南洋官报,1905(31).
[22]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3]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论体[J].南洋官报,1905(29).
[24]李钟奇.学堂宜设国文专科策[J].南洋官报,1905(17).
[25]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大清高宗春皇帝谕哈萨克瓦利苏勒坦[J].南洋官报,1905(26).
[26]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宋欧阳修唐书苏定方传[J].南洋官报,1905(46).
[27]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唐太宗御撰晋书苻洪载记[J].南洋官报,1905(57).
[28]林传甲.练习各体文字讲义·国朝陈文述长白山铭[J].南洋官报,1905(69).
[29]李仲甫.文体篇上[J].东方季刊,1926(12).
[30]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1]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下[M].江西:武宁南氏校印,1906.
[32]张之洞.鄂督南皮尚书建置存古学堂札文[J].南洋官报,1904(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