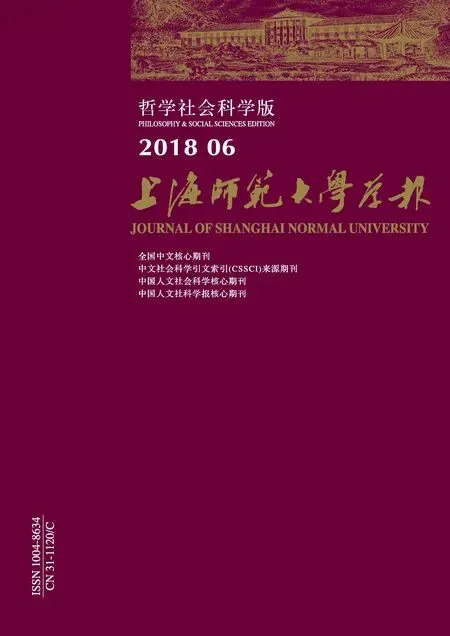建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发生学研究
李建强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研究和探讨中国电影学派的培育和养成,在建构文化自信的当下具有特别的意义,也可以而且应该有各个层面和角度的审视。本文主要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构建切入,做一点发生学的研讨。
一、历史资源
吉奥乔·阿甘本曾指出,当代问题如果不追溯到古代源头,是无法彻底厘清的,因为“开启现代之门的钥匙隐藏在远古和史前”。就此他主张,研究当下的切入点应该是采取尊重前史的考古学的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历史的过去,而是要根据当代的问题去寻找过去的历史源头,“返回到我们在当下绝对无法亲身经历的那部分过去”,[1]并善于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陈出新,改弦更张。
我以为,探讨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发生和发展,也应该有这种历史穿透的意识。
众所周知,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面世不久,与之形影相随的电影理论批评(雏形)便产生了。这一点在域外和中国几乎没有差别,而且在时间上也几近一致(世界上第一篇影评出自法国人安德烈·盖伊之手,时间定格为1895年7月11日;1896年4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英语国家中第一篇关于电影放映的文稿;而中国最早的一篇影评是发表在《游戏报》上的《观美国影戏记》,时间为1897年9月5日)。重要的是,西方人和东方人把握电影的视角和价值观念的歧异,一开始就露出了端倪:且不说1911年意大利诗人和电影先驱乔托·卡努杜发表《第七艺术宣言》,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次宣称电影是一种艺术,并把静的艺术和动的艺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造型艺术和节奏艺术包括在内进行综合比较,开创了电影艺术理论研究的先驱;就是1915年瓦契尔·林赛的《活动画面的艺术》(美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本电影批评专著)、1923年维克托·弗里伯格的《银幕上的绘画美》,其要旨也都在迎合传统的艺术观念,为电影争名分、争地位,由此产生了关于“电影的艺术性在于电影画面的构图和节奏的纯视觉艺术理论”。[2]而中国最早的电影批评理论《〈影戏杂志〉发刊词》(顾肯夫,1921)开宗明义称“影戏最是逼真,所以代表生活状态的能力,最是充分不过的”,在充分肯定电影艺术价值的同时更加看重电影的社会教育功能;[3](P6)《影戏概论——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之一》(周剑云、汪熙昌,1924)反复强调,“影戏以社会剧为最有价值,因它含有解决问题之暗示,予观众以深刻的印象,足以补助学者著述演讲之不及”,比如,“风景片可以开拓胸襟,新闻片可以增长见识,滑稽片可以笑口常开,侦探片可以益人智识,社会片可以引起研究问题之心,养成论世知人之见”,[3](P22)表现出对于电影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特别关注;郑正秋撰写的《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1922)更直接以“创造人生”“改良社会”“教化民众”作为电影及其理论批评的标识。正如罗艺军先生所说:“西方哲学重视认识论、本体论,缕析事物构成的元素、材料和实体。西方美学侧重于对自然的再现和艺术的认识价值。”[3](序言,P10)西方早期的电影观念,“可说是这种文化精神的电影显现”。而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形而上之‘道’,而对形而下之‘器’及与‘器’相联系的‘技艺’,则相对地轻视。视人格情操之完美和人际关系之和谐有序为文化之根本,而将致力于事物物理性能探究之科学技术置于文化系列之‘末’”。 这里,与之相连,“中国电影理论在形态上往往与影评合流,论评合一,以评带论;真知灼见的美学观点,旁征博引的理论阐发,与直观的随感、抒怀并行不悖”。[3](序言,P7)
中西方电影理论批评的这种形态“差异”几乎与生俱来,实际展示了两种文化的不同来路和不同走向,是和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心理联系在一起的。“物无妄然,必有其理。”西方理论追求纯知识、纯理性、纯思辨,早在古希腊已经发其端;中国文化讲究真切笃实、慎思笃行、知行合一,在华夏之初亦已肇其始。正如钱穆先生曾经指出的:“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4]可见,中西有别,文脉使然,两者并无孰优孰劣、谁高谁低的绝对区分。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科技发展和国力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巨大差距,导致民族自尊意识日渐萎缩和消解,以及对于民族文化的质询和怀疑。辐射到影像上,我们热衷于推崇那种“去中国化”“去实践化”的唯理论范式,习惯于“把中国电影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视野加以理论化考量”,[5]言必称希腊,自甘以西方理论为圭臬。这样的思维一旦形成模式,就很难摆脱自己设置的二流身份和角色认定,直接导致对自己的理论传统和样态、形式缺少应有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实际上,文化本无好坏之分,只有形状和特色之别。中国电影批评的实践理性色彩,追求经世致用的理性自觉,造就了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特别重视艺术直观和整体把握,看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讲究绘声绘影、有的放矢,在世界电影理论之林中建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价值评判体系。特别是,中国的实践哲学始终强调以社会为基础,以民生为度量,同时又特别重视修身成己的向度,亦即个人内心修齐治平、齐家治国的自我转化;强调实践智慧必须转化为实践的行动,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这就为理论的自足、开放和成长预留了空间。这一点,在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生态中同样布满印迹,无论是在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社会和生活层面,还是在感性和理性、形象和人物、技艺和手法等层面,都创造、留置了堪称丰硕的成果,并造就了一批文以载道、忧国忧民的电影理论家和实践家,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源远流长和一脉相承。李泽厚先生晚年推崇“情本体”的思想,强调情理合一、合情合理,其实就是对中国这种情理结构的重新体认。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将取决于主体和客体的情理互动结构,取决于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影像创造者和普罗大众之间的理解信任关系。这是一种共时的升华,也是一种历时的延伸,是民族文化基因长期浸润的必然归宿。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因为自成体系而妄自尊大,但也没有必要因为不同于“他者”而妄自菲薄。特定的理论话语体系一定是和特定的实践系统相联系的,一定是带有民族文化深刻印记的,因而,一定也是非舶来和强植的(我以为,近年来海外电影学者张英进等一直在强调“理论的本土化意识”——a local sense of theory,与其学贯中西、跨地视域有很大关联,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明乎于此,我们的观念就会转换一新,视野就会为之打开,目光就会由此廓大,丰富的历史资源就会摆脱“遮蔽”而浮出水面,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构建就会获得厚实的根基(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文化心理阴影也有可能为之解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毕竟,在自己的地基上建构自己的理论批评学派大厦,不仅师出有名、顺理成章,而且可能更为靠谱、更为坚实。
二、现实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P544)“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P12)毋庸置疑,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就是这种“时代的体系”提出的任务,是新时期中国电影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借助多年来电影产业改革的加速度,以超出人们想象的方式逆势上升。全面数据表明,中国电影已走出市场困境,到了收获产业化改革发展红利的新的起点。2017年,电影票房更是达到559.11亿元,城市院线观影16.2亿人次,故事片生产近800部,远远超过了世界电影市场平均增长速度,稳居世界第二。考虑到作为世界第一的北美电影市场近年一直处于稳中略降的态势,其他各国大都勉力维持现状,这种发展势能尤为难得。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电影创作的主体和客体正在互动、相伴中螺旋成长,表现出良性的、潜在的、持续的成长动能。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作为历史新时期的迅猛发展,中国电影呈现持续的市场繁荣和快速提升,创作视野不断拓宽,电影类型化、影像话语和导演个人性诠释等正逐渐形成更加多样化的理解和故事策略,电影综合产值和市场占有率、过亿票房电影数量、观影人次、海外市场票房等各项指标均不断跃进,中国电影在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更追踪时代的节拍,呈现出了多媒体的新特征。[8](P31)当下的中国电影是最生动、最多样、最具活力的,同时也是问题最多、形态最纷呈、最需要加以厘清和规范的。我们看到,新智能正在催生电影技术的突飞猛进,大数据正在重塑电影新的生态和业态。一方面,中国电影的生产力得到恢复性、爆发性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电影的结构性矛盾和发展质量问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发全社会争议、牵动朝野人心。它的现代转型和未来变化,已经远远超出甚至颠覆了传统经济学、艺术学的审视范畴,过去任何时代的电影理论都未曾面对过这样急速变幻的阵势,因此都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如果说,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当下中国丰富多彩、蒸蒸日上、新旧杂陈、问题丛生的电影实践,确实已经为理论批评建设、为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巴拉兹认为:“没有理论,任何艺术都不能成熟。”这当然是至理名言。但是,理论批评在电影产业中的地位不可能是自在的、天然的,而必须依靠入乎其内、深度参与和浸入电影的存在方式,在价值生成中一点一滴地积累和凝聚起来。从世界电影史角度考察,理论批评的发展一定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理论批评的发展促进了电影表达内容和表现手段的深化,而深化了的电影表达内容和表现手段又反过来促进和加速理论批评的发展。它们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荣、互为表里的。一旦脱开赖以生存的鲜活的创作实际,背离千变万化的当下电影生态,理论批评就会枯萎,就会窒息。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问题是实践的起点、创新的起点。读懂一个时代需要读懂这个时代的问题,改变一个时代需要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9]
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不平凡、全方位、开创性、深层次、根本性的变化: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50年将赶上甚至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以电影为龙头的文化产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急需明确理论指导下的新一轮发展跨越,亟待生发更多的理论思考和批评自觉。超越传统电影观念,重新对人类生命中娱乐的意义与价值、对电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艺术和社会整体精神文明的关系进行确认,已成为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绕不开的重大命题。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多年来我们的目光始终被西方的理论形态牵制,津津乐道于“资源来源西方化”,对自身的电影传统、电影理论批评实际缺少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始终缺乏建立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电影实践的电影话语体系的自信。再加上经过历史发掘、沉淀,能够为我们所用的现成的本土电影理论资源确实还甚为贫瘠,还不能构成齐备完整的系统,还难以担当指点江山的大任。可以说,理论形态滞后于创作实践的矛盾相当突出,已构成制约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短板和瓶颈之一。当下的矛盾焦点在于:一面是,中国的现实发展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传播好中国声音”,建构中国电影和电影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形成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而实际状况却捉襟见肘、相去甚远;另一面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攻坚拔寨,波澜起伏,我们倚重的西方电影理论话语体系又只能隔靴搔痒,难以做出准确、科学的解释和阐释。双重压力,两头踏空,相互牵制,亟待破局。从前瞻的角度考量,建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以先进开放的理论引领和指导实践,无疑已成为带动中国电影发展进程的必由之路,成为顶层设计、超前谋划、化解痼疾、应对挑战的突破口。毫不夸张地说,有没有这种清醒意识,有没有这种理论自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和价值尺度。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中国电影生产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供求两旺,市场向好,观众汇聚,产业升级,生产速率提升,发展势头不减,表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令一些传统电影大国欣羡不已(好莱坞甚至不惜“委曲求全”,同中国同行签结秦晋之好,以求分得一杯中国电影快速扩张之羹)。实际上,有利的条件还不止这一些。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思想和文化建设的高歌猛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提出,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目标方向的确立,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电影产业与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等等,合力造就和成全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最好时代”。也许,这样的“黄金机遇期”只能百年一遇,如此丰富的影像生态也不会简单重复,一切尚变幻无定,而铁定的事实是:改革的红利还在持续释放,产业的更新换代正在孕育新变。对这种全新的变化态势,不要说域外研究一时很难适应,就是国内的电影研究也有些始料未及。大卫·波德维尔谈到北欧艺术电影时曾感叹:“在革新的艺术面前,传统的阐释束手无策。”[10]
这种状态,世界电影史上曾多有发生,中国电影于今为烈。时代创造了这种风雨际会、锐不可当的条件,电影业的“未知”领域正叠加嬗变、愈益纷呈,并毫不掩饰地袒露在我们面前,难免让理论批评一时语塞,甚至张皇和难堪。真对应了那句经典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我们要真诚感谢现实的馈赠,更要善于摆脱各种有形、无形的思想观念锁定,用更加开放和淡定的心态直面现实:发展和经验当然值得总结和珍视,问题和困惑何尝不是推动发展的介质和动力?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多少发展机会可能就有多少“难点”要面对,有多少转圜可能就有多少“堡垒”要攻克,理论批评理当抓住天赐良机,因势利导,奋勇直前,加大理论思考力度,增强理论思辨自觉,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实现历史性超越。
三、合力作用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建设绝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就其普遍性意义来说,它是一个不断发生、发展的变动过程,离不开传统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团体与个体、策动与呼应等多种催生要素。这些要素在不断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以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共同推动理论研究向前发展。理论学派的建构是主体、客体、实践和价值等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不但要探究理论学派发生、发展的基本要素,而且要弄清不同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内在规律,开展追本溯源、由源及流、源流结合的考察,善于从事物发生发展的内部动态过程、整体内容与功能、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面来推进研究,进而对理论学派发生、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做出科学、合理的阐释。
综合起来,这些合力要素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与现实。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讲思想,必注意其连贯性。换言之,思想必有其传统。这一时代的思想,必在上一时代中有渊源,有线索,有条理。故凡成一种思想,必有其历史性。[4]在社会整体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代语境下,中国电影生产要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必须有前置的牵引,有传承的支撑。因此,从前瞻性的角度思考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建设,必须以后顾的方式认识和阐释传统。只有清楚地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能确切地把握我们要到哪里去;只有“化得开”过去,才可能“续得上”现在。“有效地唤醒受众内心的民族归属感,实现民族文化基因的有效传承和巩固,进而向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向不断前进,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弘扬传统文化精髓的可行路径。”[11]相对于思想观念的转换,目下同等重要的关垒是,怎样从传统与现实的衔接中找到契合处,在瞻前和顾后的联系中找到平衡点。因为只有找到既与现实相应同时也与历史资源对接的榫头,这种建构才能奠定在厚实的根基之上,才有助于形成完整包容历史、现实和未来元素的“机制性的平衡”,塑造“更高的有机体”。此前,笔者之所以单列章节慎重探讨对待历史资源的正确态度,着力坦陈对于现实条件的清醒认识和把握,用心即在于在传统和现实之间寻找交点,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架起通道。尽管对于历史资源的重新阐释可能引发分歧,但是从“文化他信”中挣脱出来,给自身传统以自主确定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在新时代的起步应当是必不可缺的。
2.国际与国内。电影理论话语体系既是对过往历史经验的集成和总结,又是对电影现实发展的系统化整合和提升,所以一刻也离不开国际视野,离不开对于世界电影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自20世纪中叶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掀起以来,世界文化日益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后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批评,既汲取了世界电影文化的充足养分,使自己的视野、面貌、形态、宽度、厚度不断提升,也具备了参与乃至引领世界电影艺术发展的多种可能。21世纪以来,中国智慧、中国创造、中国经验、中国力量正在推动世界电影发展,有力、有效地改变世界电影发展的未来版图,从这个角度说,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反过来,全球化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的建构配置了全球资源,提供了各种开放、丰富、多元的域外经验和参考,使中国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基点上融入全球电影产业新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交汇融通、互利共赢的全部要义在于,既要坚定地从国别历史和现实出发,又要勇于超越本土经验与国别实践,有更宽的视野,立更大的格局,从相互学习、开放包容、共同繁荣的高度考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电影生产与研究,用全人类的智慧来引导、开启民族影像文化的未来发展之路。比如,对于当下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实际存在的诸多问题,诸如物质主义盛行、方式方法单一、独立自在性不足、创造创意能力不强等问题,要善于从世界经验中寻求参照和解答。过去我们在国内、国际比较的方位上,习惯以“相形见绌”来解释、估价中国电影理论生态,一味放低身段,甚至自我矮化,现在看来并非完全必要和符合实际;但是,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有了些许进步就沾沾自喜、自我感觉良好,进而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又有可能坐失与世界潮流砥砺共进的难得机遇。自卑呈作茧自缚状,自足见膨胀无知态,在中国均所依有本、挥之难去,不刨根问底、痛彻心扉,便难以疗治和根除。电影人国际视野的形成,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和世界大势、国力角逐、民族认同、文化走向、个体素养、终身学习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何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格局中注入新视角、新观念、新方法,善于从全球变化和自身实践的结合中总结新经验,凝聚新认识,提出新思想,成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进学立派、走出国门、汇入世界、贡献人类绕不开的门径,也对中国电影理论批评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团体与个体。从世界电影史角度考察,电影理论学派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团体和个体共同发力的结果。比如著名的蒙太奇学派,除了库里肖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爱因汉姆、斯波蒂斯伍德、卡斯蒂这些名闻遐迩的电影艺术家个人的出色发挥,还和“团体”的凝聚、放大作用互为因果。他们有的是师承关系(如爱森斯坦、普多夫金都是库里肖夫的学生),有的是艺术观念的组合(如爱因汉姆和卡斯蒂、安德鲁形异质同的主张)。同样,著名的“《电影手册》派”也是如此,巴赞、杜卡、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杜马契和里维特,每一位都是成就卓著、个性鲜明的电影思想家(其中不少还是著名电影艺术家),但他们紧紧围绕在《电影手册》编辑部的周围,历数十年而不衰,共同营造了学派的思想大厦。还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学派、美国新电影集团学派、新德国电影学派等的生成演变,莫不如是。恰如钱理群先生曾指出的:“尽管每一个坚守学术的个人,都是孤独与寂寞的;但也总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够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挣扎着奋力前行。”[12]建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当然也回避不了这一艺术生长规律。过去我们对于“团体”和“个体”都有些忌讳,生怕“团体”演变成“俱乐部”,担心个人发展为“主义”。其实,中国传统美学历来奉行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个人之间、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差异,而且还应该欢迎和鼓励这些差异,把它们视为丰富国家艺术形态、培育思想市场的必要条件。学派并不扼杀其成员的自由研究,只要确保每个成员的才能和个性充分发挥,学派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繁荣。这是一对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也是检阅、衡量一个时期电影文化荣枯兴衰的标志性指标。我们真诚地期待和相信,伴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艺术生态的持续向好,学派团体建构和个体发展应该而且一定可以获得更宽松、更自由的催生和成长空间。
4.策动和呼应。精神生产在本质上就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它是人类全面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精神生产过程中,尤其需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它通过人的历史创造活动表现出来。[13](P118-119)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除了老一辈电影理论批评家持续活跃发力之外,一批中国自己培养的中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可以饶曙光、贾磊磊、尹鸿等为代表)。他们在理论视野、研究深度、投入程度、社会担当上,全面传承老一代的风范,潜心著述,引领全局,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下电影理论批评的主体力量。同样令人可喜的是,借助互联网的持续“升温”,新一代青年理论批评人才如虎添翼,初露锋芒。新媒体和大数据的结合,不但使他们能够轻松地越过门槛,抒发情怀,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意见领袖”。但是应该承认,由于各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现在的中青年学者还缺乏老一辈电影理论批评家那样的人格胸襟、那样的目光格局。其视野开阖不可同语,其策动效应也就望尘莫及。想当年,钟惦棐先生等前辈以电影评论学会为抓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析理论,评作品,提主张,推新人,建平台,使电影理论批评出现了少有的热烈场面,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第二个黄金期”。令人遗恨的是,天公不作美,壮心不已的钟惦棐先生突然辞世,给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建设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钟老这样的帅才可遇不可求!我们于此愈发深切地体察,领军人物是学派的灵魂,千军易得,一帅难求。缺乏学术领袖对成员的吸引力、成员对团队的向心力、成员之间的黏合力,学派的建构便无从谈起。这是一条艺术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领军者和策动者,除了功底学识的要求,更有品性、胸怀、人格的期许。学术领军,决不意味着只是名誉地位和鲜花掌声,更多是奉献和责任。相对于较易做到的“呼应”,“策动”之功筚路蓝缕、艰难备至,是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是难以计算个人得失的,有时可能还要承担一定的职责和风险。在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各种利益诱惑无所不在,做到这一点尤为艰难。但正如福柯所言,“历史是可以动摇和可以改变的,问题只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人必须具备改变事物的政治勇气”。这种勇气,既来自我们对于这份事业的无比热爱和真诚之心,更应来自我们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来自内心的强大平和,以及对于艺术人生的敬畏之心。中国古代曾留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历史佳话,今天的学者、大家能否续写这样的当代篇章?让我们翘首以待!
总之,历史资源是宝库,现实条件是基础,合力作用是路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大目标的提出,为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吹响了新的集结号。从无到有,由破土萌芽到参天立地,其艰难自不待言,唯有持之以恒、矢志不移,才会有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发生、发育、健硕成长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