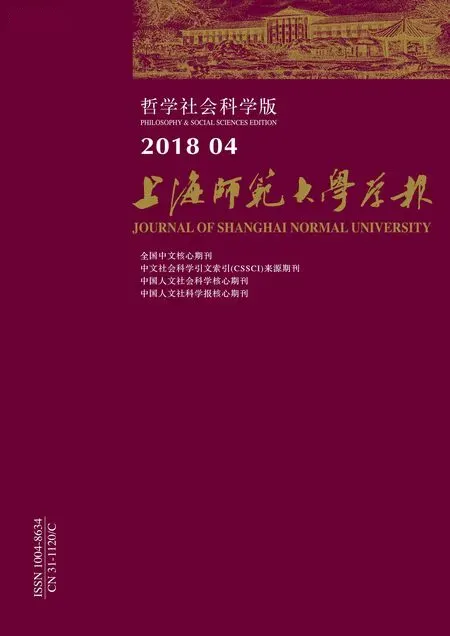比较文学变异剖析
——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在中国的变异
曹顺庆,吕雪瑞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1928年10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宣读了两篇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日后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年《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英国出版,并迅速引发了英语世界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风起云涌,伍尔夫的这部作品更是被许多女权主义者奉为圭臬,伍尔夫被视作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提出的诸多观念。在中国,《一间自己的房间》业已成为普通读者了解伍尔夫非小说类作品和女性主义观点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与伍尔夫的“生命三部曲”(《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同样广为人知的作品。在中国的学术界,《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近年来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然而这部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远非一帆风顺,其中的误读和变异现象,恰恰反映了一部文学作品在跨文明传播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异现象。本文以伍尔夫的这部饱受争议的作品为棱镜,折射出文学作品在变异学视角下的种种变异和创造性叛逆现象。
《一间自己的房间》:从第一到沉寂
与伍尔夫的其他作品在中国得到介绍的时间相比,《一间自己的房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部。根据杨莉馨的考证,①徐志摩是中国评介伍尔夫的第一人。1928年10月,伍尔夫夫妇赴剑桥发表关于妇女与小说关系的演讲;1928年12月,徐志摩便在苏州女子中学做了一场《关于女子》的演讲。在这场针对女性的讲演中,徐志摩两次提到了伍尔夫。在探讨女性的创作条件和环境时,徐志摩引用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观点:“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国一位名小说家作的,她说妇女想从事著述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这让她随时有关上或锁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华银有六千元)的进益。她说的是外国情形,当和我们的相差得远,但原则还不一样是相通的?”②
为了鼓励中国的女学生们在除旧破新的时代能够自立自强,徐志摩再次引用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所举出的英国历史上女性创作者温澈西夫人、纽卡所夫人的例子,安慰女学生说,即使是在英国,女性进行写作也面临着各种歧视,女性的创作环境无论中外同样艰辛。徐志摩认为,缺乏私人空间和财务自由,是所有女性面临的难题,然而女性在这样不利的社会条件下,依然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他热情地断言:“将来的女子自会有莎士比亚、培根、亚里士多德、卢梭,正如她们在帝王中有过依莉莎白、武则天,在诗人中有过白朗宁、罗刹蒂,在小说家中有过奥斯丁与白龙德姊妹。我们虽则不敢预言女性竟可以有完全超越男性的一天,但我们很可以放心地相信此后女性对文化的贡献比现在总可以超过无量倍数,到男子要远担心到他的权威有摇动的危险的一天。”③
从伍尔夫在剑桥发表演讲,到徐志摩在苏州女子中学的讲演中援引伍尔夫的观点,仅仅相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英国文坛的动态是十分敏感的。徐志摩敏锐地意识到伍尔夫这部作品中与女性有关的内容,并非常巧妙地拿来为中国刚刚有机会步入正规学校教育的女性学生所用(1907年女子学校被正式纳入学制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然而徐志摩对《一间自己的房间》的阐释,却是经过了文化变异所留下的符合中国女性接受状况的误读。在提及女性的创作条件和环境时,徐志摩提到了伍尔夫著名的论断:女性从事创作需要自己的房间和独立的经济保障。然而改善女性的创作条件并不是徐志摩进行这次演讲的目的,于是他把话锋一转,开始告诫女学生们,女性的地位无论古今中西都低于男性,英国的状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伍尔夫提到温澈西夫人和纽卡所夫人是出于对女性艰难写作环境的愤慨,而徐志摩引用温澈西夫人的感慨:“趁早,女人,谁敢卖弄谁活该遭殃,才学那是你们的分!一个女人拿起笔就像是在做贼,谁受得了男人们的讥笑”,④则并不是出于对女性弱势地位的不平,而是想要用温夫人的话向苏州女子中学的女学生们说明女性创作空间狭窄的事实。徐志摩列举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以及清代妇女文学取得的成果,意欲向女学生们树立的是面对逆境仍旧顽强不屈的女性形象,希望当时的女学生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写作,成为像莎士比亚一样能够写出不朽著作的女作家。这样的女作家是与伍尔夫所描述的莎士比亚的妹妹截然不同的形象,这就是变异。
在徐志摩想象中能够比肩莎士比亚的女作家应该天资聪颖、吃苦耐劳,在夹缝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却不会像伍尔夫虚构出的莎士比亚的妹妹那样,空有满腹才学却过早夭折。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描述从事创作的女性地位的悲惨,目的是想引起社会对女性不公正地位的重视,希望为女性争取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和经济地位,来保障女性创作的自由。而徐志摩借用伍尔夫的这部作品,想要传达给中国女学生的却是女性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普遍性和全球性,他并不是要号召女学生们为争取自己的创作自由而奋斗,而是让她们向历史上那些在困难中踽踽独行的女性作家学习如何在狭窄的空间中生存。同样是在女子学院的演说,伍尔夫想告诉台下女性听众的是:我们一直在不公正的环境和条件下从事写作,现在我们有必要改变这一切,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舒适和利于写作的内部与外部环境。而徐志摩想要告诉中国女学生的是:古今中外的女性在从事写作时都会面临各种困境,所以你们需要的不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而是顽强拼搏的毅力,请你们继续在艰苦的环境中争取获得更大的成就!这种文学阐述的变异,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第一次被引介到中国时,这篇文章的旨趣就因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而发生了改变。徐志摩将伍尔夫在这部作品中所描述的女性的困境作为事实介绍给了中国的年轻女性,却巧妙地过滤掉了伍尔夫列举这些例子的目的,代之以更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并鼓励当时受教育的女性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的女作家们就对救亡图存怀抱着极大的热情,丁玲就明确地表示自己卖文但不卖“女”字,杨莉馨将其称为“五四以来男女作家共赴国难的传统”,并认为这是“中国女作家能够与伍尔夫思想产生共鸣的深刻基础”。⑤事实上,从《一间自己的房间》到《三枚旧金币》,这些被国内称为女权主义的作品均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彼时战争的阴影同样笼罩在英国的上空,然而伍尔夫的这些作品并未表达过男女合作共赴国难的愿望。《一间自己的房间》表达的是女性作家对自己所处的男权社会的不满,《三枚旧金币》则明确表达了伍尔夫对于男性战争的不配合的态度。1941年E·M·福斯特在剑桥大学的讲座上谈到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时,这样说道:“在她的全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的影子,女权主义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她相信社会是由男人造成的,男人的主要职业是流血、挣钱和发号施令,还有就是穿制服,而所有这些都不能令人起敬。……她觉得发自这些人口中的喃喃自语,是在表达某种从未同女人商量过的内容,不管怎么样,这种内容是她不喜欢的。在理论上,有时也在实际行动中,她谢绝同男人配合。她拒绝参加任何委员会和在任何呼吁书上签名,因为女人不能宽恕这个由男人造成的悲惨的烂摊子。”⑥而在当时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们更希望抹去性别的差异,对自己被尊称为“先生”这件事情是相当满意的,这也是变异。
伍尔夫的确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到过女性积累生活经验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但她所希望的生活经验是交友、旅行、沉思而非与男性并肩作战,抵御外敌。正因如此,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诞生之初就遭到了英国国内一些批评家的激烈反对。阿诺德·贝内特先生认为这部作品让人摸不着头脑,伍尔夫想要为女性创作者争取的500英镑收入和一间上了锁的房间,并不是从事写作所必需的条件。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自己为例,证明受到外界干扰和贫困本身并不会阻挡一个人成为作家,“伟大的歌剧演唱家们,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却仍然是伟大的歌剧演唱家”。⑦女性作家没有成为伟大的作家绝不是外在条件惹的祸。同为女性,Q·D·利维斯夫人则在《全国的毛毛虫团结起来》一文中指出,《一间自己的房间》实在令人讨厌,伍尔夫所代表的只是她所在的那个高雅之士的群体,绝不能代表广大的受过教育的女性。⑧而这些在英国国内被攻讦的观念,徐志摩却并未察觉。此后,他也不再提及伍尔夫的这部作品,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主动模仿伍尔夫的意识流写作技巧。
为何徐志摩没有发现这部在英国国内激起愤慨的作品有种种脱离实际的弊端呢?为何徐志摩不再向国内推介《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是转向了伍尔夫更具纯粹艺术气息的意识流小说呢?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有一点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徐志摩正是贝内特和利维斯所提到的文学上的高雅之士的中国版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的家作为“太太的客厅”汇聚了一批由徐志摩、金岳霖等人组成的“以纯粹的文艺、学术探究与对话为特色的‘公共空间’”。⑨1935年11月5日,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叔华告诉我,在北平也有个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就我所了解,确实和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很相似。”⑩与徐志摩生活在同一个圈子中、受过教育的女儿们,有能力接受对当时女性来说最好的教育,对她们来讲拥有独立空间和财务自由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所以徐志摩才可以自信地说伍尔夫提出的女性创作条件对中国女性来说只是量的区别,却无质的差异。贝内特和利维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一间自己的房间》的驳斥,当然无法引起徐志摩同样的愤慨,因为虽然身处东方,徐志摩和伍尔夫同属精英阶层。只是,变异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这个东方版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徐志摩和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福斯特一样,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并不感冒,在预言女性在未来是否会赶超男性时,徐志摩下意识地使用了“竟”,说明他从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女性可能有超越男性的一天,在对女性的美好祝愿中也隐隐透露出他对女性能否担此重任的本能的不信任。同时,徐志摩也特意强调,女性对文化的贡献逐渐增加,将会动摇男性的权威,引起男性的担心,对男性造成威胁,而这种观念正是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着力批判的。徐志摩1928年在伦敦期间阅读了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对伍尔夫产生了好感,他托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罗杰·弗莱帮助自己拜访伍尔夫夫妇,虽未能成行,但伍尔夫“美艳明敏”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徐志摩向苏州女子中学的学生们介绍伍尔夫,更多是出于对伍尔夫本人和她精致的意识流小说的喜爱,而并非对她女性主义思想的赞同。徐志摩想要女学生们了解的并不是如何反抗男权社会,而是如何珍惜刚刚争取来的读书机会。
徐志摩从《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读出了伍尔夫的反叛和对传统男权社会的背离,于是在对这部作品蜻蜓点水的评介之后,迅速逃离了伍尔夫与政治有关的作品,转而从文学和审美的角度阅读、模仿伍尔夫的小说类作品。在译本产生之前,能够直接接触伍尔夫原作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除了像徐志摩这样有家学渊源的高雅之士,还有一类则是通过官费出国、想要振兴中华的留学生。而这一部分学生则把救亡图存和报效祖国树立为目标,对伍尔夫这种中上层社会女性的作品兴趣不大。伍尔夫强调女性创作中的种种不平等,对这些留学生来说也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所以,《一间自己的房间》在1928年被引介到中国之后的近20年中,始终寂寂无闻。1947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王还翻译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这部最能代表伍尔夫女权思想的作品终于拥有了完整的译介本。该译本在1989年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女性文化研究热潮的推动,获得了新的关注。然而,在面世之初的40多年内,该译本并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瞿世镜2000年增补版《论小说与小说家》的后记中,解答了沉寂背后的原因。
《一间自己的房间》与不能被侮辱的女性
1982年,当瞿世镜选编伍尔夫的文论《论小说与小说家》时,《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不在他选择的范围内。谈及原因时,他说:“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政府封闭了所有的妓院,帮助那些受迫害的阶级姊妹们治好了性病,学会了劳动技能,组织了幸福家庭。我们无比自豪地宣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又变成了人!女性进大学,当干部,人们都习以为常。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性别歧视似乎不复存在。”作为新时期国内伍尔夫研究与译介的重要学者,瞿世镜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学界对待伍尔夫女权主义的态度:男女平等在中国已经实现,中国并不存在女权主义的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打算在2000年伍尔夫的散文增补版中补译新的内容时,瞿世镜选择了《一间自己的房间》。改变他想法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不容忽视的一些次要的支流:“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包养二奶的新闻,时时见诸报端,令人触目惊心。”他以2000年9月的一篇调查报告为例,指出部分女性在当代中国依然遭受性侵害。瞿世镜愤怒地说:“女性者,母性也。我们岂能容忍这种侮辱我们母亲性别的丑恶现象长期存在下去!”他选中《一间自己的房间》来进行翻译,目的很明确:这是一篇女权主义的宣言,而当下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男女平等,所以我们需要女性的声音。
但在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时,瞿世镜面临着自身男性身份的拷问,于是他假借他人之口提问:“读者或许会发生疑问:你是男子汉,为何选中这篇女权宣言?”言下之意即男性翻译家不应该去翻译女权主义的作品,这种做法是有违男性身份和形象的。在为自己的翻译进行辩护时,他反问读者:“哪一位男子汉不是母亲十月怀胎所生?哪一位男子汉不是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成人?”接着,他用一页的篇幅来详述自己知书达理的母亲是如何为他延请名师,如何为他的学业和工作提供无私的帮助,在他罹患癌症后又是如何悉心照料,却不幸在自己儿子的第一部专著脱稿之时驾鹤西归。这饱含深情的叙述读之令人动容。瞿世镜悲叹:“她唯一的人生乐趣,就是从儿子微小的工作业绩中分享一点成功的喜悦。为什么连这么一点点欢乐都要加以剥夺?”在回顾了母亲无私奉献的一生后,他明确指出:“我翻译伍尔夫的这篇论文,正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纪念千千万万为丈夫和子女贡献了一生而默默无闻的妇女们。”于是,女性被成功地置换成母亲的形象,而女性之所以应该得到平等地对待,正是因为她们作为母亲是十分伟大的,是可以奉献牺牲自己来成就丈夫和孩子的,所以作为母亲的女性理应获得尊重。
而瞿世镜这番关于伟大女性的赞扬,不仅与他所翻译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的主张并无联系,甚至与伍尔夫本人以及她的女性主义观点背道而驰。这种变异是令人深思的。在《女人的职业》一文中,伍尔夫谈道:“当我开始写作时,发现如果要想写书评,就必须和一个幽灵展开一场斗争。幽灵是个女人,当我对她有了进一步了解后,便给她起了个名字——‘房中的天使’……她相当惹人喜爱,有无穷的魅力,一点儿也不自私,在家庭生活这门难度极高的学科中出类拔萃。每天,她都在牺牲自己。如果餐桌上有一只鸡,她拿的是脚,如果屋里有穿堂风,她准坐在那儿挡着。”伍尔夫的母亲裘丽亚就是一个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她始终牺牲自己来满足他人的需要。伍尔夫所定义的“房中天使”,便是如她母亲一般恭顺而无私的女性形象。瞿世镜的母亲或许没有获得私密的空间和足够的财政自由,或许她自愿放弃了这些,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她的前半生致力于襄助自己的丈夫管理一所私人医院,后半生则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儿子的培养上。这与伍尔夫笔下“房中天使”的形象十分相似,她们是家庭和睦的中坚力量,为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无私奉献着自己的一切。而她们所失去的,正是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想要为女性争取的能够使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想到个人的天才,去埋没它就等于死亡——才能虽小,对拥有者却弥足珍贵——它正在渐渐毁灭,随之而去的是我的自我,我的灵魂——这一切就像是一种锈菌,它吞噬了春天的花蕾,从中心把树木腐蚀掉。”
伍尔夫在她的这部作品中坦言:“我的动机,请允许我承认,有一部分是自私的。像大多数未受充分教育的英国妇女一样,我喜欢读书,……我愿意请你们去写各种各样书籍,不论题目大小都不要犹豫。不论用什么方法,我希望你们拥有足够的金钱,可以去旅行,去闲散,去深思这个世界的过去或未来,去看书梦想,去徘徊于街头巷尾,并且让思想的钓线深深地沉入生命的河流。”伍尔夫要求女性去挣钱并拥有自己的房间,引导女性去过一种生机勃勃的生活。她强调,“保持自我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最后一章中向女性转告约翰·蓝登·戴维斯先生的一番警告说:“等到完全不想要小孩子的时候,女人也就完全不需要了。”伍尔夫要自己的读者将这番话牢记于心,鼓励年轻的妇女着手自己的人生事业,向这位男性证明女性除了周旋于客厅和生儿育女外,还能读书写作,与真实世界而不仅仅是家庭的方寸之地建立联系。
伍尔夫希望女性所拥有的平等和自由,是书写和精神的自由;而瞿世镜所呼吁的男女平等,则是停留在女性不再被男性凌辱,不再成为各种性侵犯和暴力案件受害者的层面,并且通过唤起男性对自己母亲的尊重来达到尊重女性的目的,这并不是伍尔夫的女权思想所考虑的问题所在。在《论小说与小说家》的后记部分,瞿世镜客观地总结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六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并赞叹伍尔夫的文论活泼风趣、雄辩有力,读之酣畅淋漓,心生舒畅。在瞿世镜对伍尔夫作品的介绍中,提及了妇女在高等学府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男作家对女性能力的质疑、女性的诗才被埋没、女作家需寻求女性句法、妇女应强化与男性之间的区别以及雌雄同体的创作观,这体现了瞿世镜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女性被不公正的对待与女性写作应遵循的原则。而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开宗明义地点明的主旨“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对此瞿世镜却并未提及。伍氏这篇文论中所强调的女性写作需要具备的物质基础、男性的虚荣和自我膨胀等更具有伍尔夫个人特色的女权思想,悄悄地被过滤掉了。也许译文本身能够让读者自己体悟到伍尔夫关于杀死“房中天使”的种种相关论述,但这并非瞿世镜想要引导读者获得的体悟。站在传统的男性视角上,瞿世镜虽未像伍尔夫笔下的戴维斯先生那样认为女性不想要孩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却也从另一个方面迎合了他的观点,因为他毕竟也认为女性即母性,正是因为女性属于母亲的性别,我们才不能容忍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侮辱。
瞿世镜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开始进行伍尔夫作品译介与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为伍尔夫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他所翻译的伍尔夫的散文和小说,以及他主持编译的国外伍尔夫研究,至今仍是非常宝贵的参考资料。然而他对待伍尔夫女权主义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态度,却是十分值得玩味的。瞿世镜一面对伍尔夫的文笔大加赞赏,引导读者关注伍尔夫这部作品中一些表面的例证和伍尔夫的女性写作观,但却过滤掉了伍尔夫该文中十分重要的对女性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写作空间的呼吁。对中国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来说,打算写小说并不是她们的当务之急,拥有足够的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当然也并不是那么迫切的事情。伍尔夫的这种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呼唤,或许并不是瞿世镜认为的在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因为对独立自我的追寻,必然会削弱女性在家庭中所投入的时间,妨碍女性作为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奉献一切,而母性却是他所认为的女性最伟大的品质。这就是文化原因造成的变异。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最后一章中,伍尔夫自己点出了她在第一章中提出的两个物质条件的象征意义:“把每年五百英镑收入代表深思熟虑的能力,把门上的锁象征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瞿世镜希望中国女性获得的,还停留在一种可见的、身体上的平等,深思熟虑和独立思考并不是社会新闻版面的女性能够轻易获得的。瞿世镜所观察到的女性问题和伍尔夫致力于改变的女性问题,针对的是截然不同的女性群体。作为伍尔夫研究专家,瞿世镜不可能没有发现这种差异,为了使这篇被增补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了让读者们不致对男性翻译家翻译女权色彩的作品感到反感,他在自己的解说中首先过滤掉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女性物质和精神自由的呼唤,接着以母性为突破口,打出自己亲身经历的情感牌,使读者易于接受一个男性为女性鸣不平。瞿世镜笔下的母亲和伍尔夫所谈及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相似,是家庭的轴心、道德的楷模、温情的源泉;她们是“房中天使”,是伍尔夫在创作时挥之不去的阴影,是她要抄起墨水瓶砸过去的对象。而这种美好的天使形象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尊崇的女性形象。即使在今日,中国的女性已经获得了伍尔夫所提及的职业女性的身份,在各个行业崭露头角,然而呼吁女性回归家庭依然是不变的主流。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伍尔夫的这种杀死“房中天使”的思维方式无疑是自私自利和非常令人不悦的。
结语
1928年徐志摩在苏州女子中学的讲演中评介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刚刚有机会正式走进校园的女学生们内心激荡着救亡图存的理想,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这部女权主义作品中的某些部分成为激励中国年轻女性奋起的例证。徐志摩从伍尔夫的文论中截取了在历史上国外女性写作中面临的困境以及她们如何克服重重阻力而名垂青史的励志故事,使中国的年轻女学生们相信自己有无穷的潜力,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中与男性并肩作战,共赴国难。而伍尔夫举出这些例子的本意则因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被过滤掉了。可以说,当《一间自己的房间》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它并没有被当作女权主义的文本,而是被片面地解读成一个英国作家在大洋彼岸书写的鼓励女性在夹缝中发愤图强的小册子。
1947年,《一间自己的房间》诞生了第一个译本,然而这个译本却没有在当时的中国激起波澜。当中国读者有机会阅读伍尔夫的文本时,没有人能够忽视其中对男性虚荣的剖析和对女性精神自由的呼唤。而彼时的中国,女性拥有自己的房间和财产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国共两党正处在激战之时,鹿死谁手尚无定论,国家的命运和走向尚且在战争中飘摇,个体的命运和权利无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更遑论在男尊女卑思想浸淫下的女性命运。当时能够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的受过教育的女性,都在为国家的命运而担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稳定的政局,女性又怎能获得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呢?而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提升。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刊物发表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毛泽东看到此文后亲自指示,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之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随着这一口号响彻大江南北的是一种逐渐形成的观念:在中国,不存在国外所谓的女权问题,中国的女性是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现代主义小说家的排斥中,《一间自己的房间》继续沉寂着。
改革开放后,中国已持续近30年的平均分配体制被打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作为伍尔夫权威研究专家的瞿世镜,就在这股致富浪潮中看到了社会上一些侮辱女性、损害女性形象的现象。在这种现实语境下,瞿世镜重新转向了伍尔夫的女权主义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他在翻译和介绍这部作品时坦承:“我翻译伍尔夫的这篇论文,正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纪念千千万万为丈夫和子女贡献了一生而默默无闻的妇女们。”很显然,他的译介打上了自己个人经历的烙印。《一间自己的房间》既然是对母亲的献礼,在介绍的过程中,瞿氏就巧妙地回避了那些违背女性恭顺无私的品德的部分,而代之以伍尔夫对女性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列举,以此表达对中国社会那些侮辱女性行为的愤慨。同时,他引导读者关注伍尔夫在谈女性写作时所提到的论点:寻求表达女性气质的女性句法,伟大的艺术家要证明内心真实确实存在以及雌雄同体的创作观。而伍尔夫用一半的篇幅来探讨女性拥有独立空间和财产的问题,他却几乎没有提及。从瞿世镜为自己翻译的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男性为女性鸣不平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他才要以母性的名义为自己正名。站在男性立场上,他依然认为,女性牺牲自己为家庭付出是美好的品德,这样的女性才是值得被歌颂的,而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种种企图杀死“房中天使”的论述并不为他接受,于是他便以“酣畅淋漓,才气横溢”加以笼统概括。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文化传统、时代语境和民族心理对一部作品进行过滤和加以变异的痕迹。
事实上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从1928年进入中国到2000年重译的过程中,它的遇冷和近年来的回温,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现实语境和接受者的心理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变异在这部文本的传播过程中始终发生着影响。在徐志摩和瞿世镜看来,《一间自己的房间》主旨是在追求男女平等;在徐志摩的时代是男女共赴国难的平等,在瞿世镜这里则是男女人格上的平等。及至今日,当越来越多的女性研究者开始重新阐释这部女权作品的内涵与外延时,又生发出更多新的不同解读,这个文本对女性在经济和思想上地位的强调,在当下的中国获得了关注。在这些新的解读背后,同样隐藏着文化过滤、误读和变异的因素。
文学变异是在跨异质文明的语境下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这些有选择的接受和拒绝的背后隐藏着的,既有异质文明不同的内核,亦有两性认知上的差异,我们需要从这些表面的变异现象背后发现文学变异的深层原因,认识到这种由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文化传统和历史与现实语境所造成的对文本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在跨文明的文学传播中所发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才能避免抱持一己之见、固守思维定式的缺憾。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所有的阅读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误读”的批评;对文本的阐释者来说,意识到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的机制,才能更富有洞见地理解异质性的文本,更好地实践跨文明的文学文本的交流。虽然徐、瞿两人对《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解读是站在中国传统的男性视角上看待女性的问题,难免存在偏颇之处,但他们两人都在当时的语境下激励了女性争取自强自立的信心。时至今日,伍尔夫那间属于英国受教育者的女儿们的房间,对当下的中国女性也并不适合,如何在对这个文本的新解读中自觉地运用文学变异去实现文化创新,自觉地选择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意义”,吸收伍尔夫作品文学变异带给我们的启示,并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话语,理应是新时期研究者们关注的题中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杨莉馨:《20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4页。
②徐志摩:《关于女子——在苏州女子中学讲演稿》,见《徐志摩全集·第4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③同上书,第651—652页。
④同上书,第647页。
⑤杨莉馨:《20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第333页。
⑥瞿世镜编选:《伍尔夫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⑦同上书,第284页。
⑧参见Q. D. Leavis, “Caterpillars of the Commonwealth Unite!”,Scrutiny, 7, September 1938, pp. 203-214.
⑨杨莉馨:《20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中国》,第38页。
⑩凌叔华:《中国儿女——凌叔华译作·年谱》,陈学勇编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