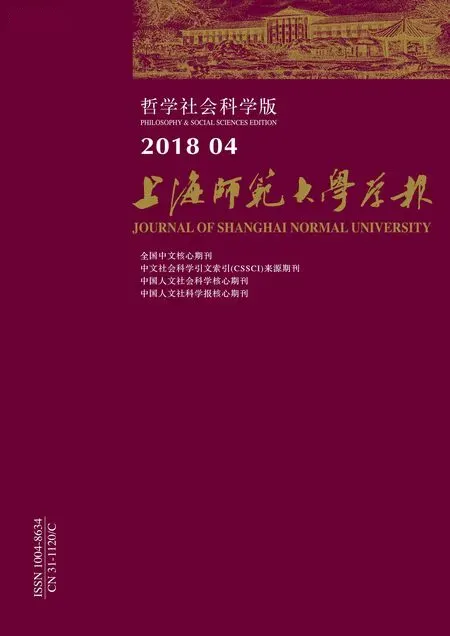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中的经济史资料及其利用
刘伟才
(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上海 200234)
中南部非洲广大地区长期未有文字,其他地区(除北非外)的文字传统也相对较为薄弱,资料缺失直接造成非洲史研究的诸多困难。虽然研究者不断探索利用考古资料、口述资料、语言资料、人类学资料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的成果,但由于这些资料本身也不充分或存在缺陷,非洲史研究的资料问题可以说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虽然非洲自身没有或少有文字记录,但外部世界关于非洲的文字记录却较为丰富。特别是在19世纪前后的百余年间,欧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在非洲扩展,欧洲人关于非洲的知识迅速积累和扩充,出现了大量文字记录。在这一时期,在非洲最为活跃的当属英国人,他们的记录相应也最为丰富。
对外部世界关于非洲的文字记录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并将其运用于非洲史研究,是一个值得开拓的领域。本文以非洲经济史为切入点,拟对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资料进行评述。
一、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的基本情况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变迁,奴隶贸易逐渐式微,而以非洲野生采集产品和农产品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合法贸易”逐渐兴起。为扩展“合法贸易”和找寻新经济机会,欧洲国家的工商业界和政府都意识到要对非洲有更多的了解,内陆探险应运而生,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传教活动的扩展,商人、猎人、旅行家、自然博物学者等也开始不断地深入非洲活动,他们留下了多种多样的关于非洲的记录。
按记录者的基本身份,大体可以把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分成探险家记录、传教士记录、商人记录、殖民军人和官员记录等几类。
1.探险家记录
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机构的支持下,一拨又一拨的人被派往非洲,在尼日尔河流域、尼罗河-大湖地区、赞比西河流域以及南部非洲广大内陆展开探查工作。
在尼日尔河河道及沿河情况探查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是蒙戈·帕克(Mungo Park)、休·克拉伯顿(Hugh Clapperton)、兰德尔兄弟(Richard Lemon Lander and John Lander)等人。帕克留下了《1795、1796、1797年在非洲内陆地区的旅行》①和《1805年非洲内陆行记》②两部记录;克拉伯顿和兰德尔兄弟的探险活动前后相继,且有重合之处,他们留下了《在中北非的旅行和发现》、③《第二次非洲内陆探险记》、④《尼日尔河河道及其终点探查记》⑤等记录。
在尼罗河源头和大湖地区探查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是约翰·斯皮克(John Speke)、萨缪尔·贝克(Samuel Baker)、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以及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和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y)。在约20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将足迹印在了包括东非沿海、东非内陆高原、东北非内陆、大湖地区、尼罗河上游在内的广大地区,留下了丰富的记录。斯皮克有《尼罗河源头发现记》,⑥贝克有《阿尔伯特湖:尼罗河大盆地和尼罗河源头探查》,⑦伯顿有《中部非洲的湖区》,⑧格兰特有《徒步穿越非洲》,⑨利文斯顿和斯坦利则分别在《在中部非洲的最后记录》⑩和《穿越黑暗大陆》中记录了与尼罗河源头、大湖地区相关的内容。
在赞比西河探查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是利文斯顿。他于1853—1856年间做横穿非洲大陆的探险,见识了奴隶贸易在这一地区造成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可以开发利用赞比西河流域的土地资源,引领发展新的经济,以取代奴隶贸易。1858—1864年间,利文斯顿再次对赞比西河中下游及支流地区进行了探查,希望能找到可供集中开发的资源并勘察通航的可行性。关于赞比西河探查的情况,一部分内容包含在利文斯顿的《在南部非洲的传教、旅行与研究》一书中,另一部分则通过《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查记》呈现。
在尼日尔河、尼罗河-大和赞比西河这三个主攻对象之外,还有在尼日尔河区所在的更广大的中西部非洲内陆、尼罗河和刚果河分水岭所在的中东部非洲、赤道地区、南部非洲以及纳米比-卡拉哈里所在的西南非洲等区域的探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南部非洲的探查,主要人物包括约翰·巴罗(John Barrow)、威廉·伯切尔(William Burchell)、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等。巴罗、伯切尔和汤普森三人分别著有《走进南部非洲内陆》、《在南部非洲内陆的旅行》和《在南部非洲的旅行和冒险》。前两本书记述了作者当时所见的开普殖民地的情况,特别是对布尔人(Boer)、有色人(Coloured)、霍屯督人(Hottentot)、布须曼人(Bushman)、茨瓦纳人(Tswana)多有记录和论述;较晚的汤普森比前两人向北走得更远,他进一步深入记录和分析了巴罗和伯切尔所涉及的方面,对一些对象和主题进行了更全面、更完善的描述,此外,他还描写了19世纪20年代初到达南非的一批早期英国移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2.传教士记录
进入19世纪后,基督教开始在非洲大范围传播。相对而言,在南部非洲和西非几内亚湾沿海地区的传教所取得的成果较为显著。
在南部非洲的传教士中,知名的有罗伯特·莫法特(Robert Maffat)、威廉·肖(William Shaw)、利文斯顿、约翰·马肯兹(John Mackenzie)以及后来进一步往北在恩德贝莱人中传教的大卫·卡内基(David Carnegie)、威廉·艾略特(W. A. Elliott)等人,他们都以不同方式留下了自己在非洲相关地区传教和生活的记录。莫法特在有色人、茨瓦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中传教,前后约半个世纪,他自己撰写了《在南部非洲的传教与见闻》一书,另外,其不同时期的信件和日志则由后人整理为《在库鲁曼的锻炼:罗伯特·莫法特和玛丽·莫法特1820—1828年日志信件集》和《罗伯特·莫法特马塔贝莱日志集》两书;威廉·肖先是在东开普的英国移民中负责教务,后在科萨人中传教,他留下了《我在东南非传教的经历》一书;利文斯顿早期作为传教士主要在茨瓦纳人地区传教,相关情况反映在他的《在南部非洲的传教、旅行与研究》一书中;约翰·马肯兹主要在茨瓦纳人的地区传教,并在开普殖民地以及奥兰治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旅行,他留下了《奥兰治河以北的十年:在南非土著族群中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在马塔贝莱兰传教的人中,大卫·卡内基留下了《在恩德贝莱人中的十年》,威廉·艾略特则有《石英中黄金》。
在西非几内亚湾沿海地区,塞拉利昂、尼日尔河河口和黄金海岸是英国人传教扩展的主要地区。由于气候等原因,在这里的传教士发生疾病或死亡的概率较高,而这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他们留下的记录比较少,一些留下的记录也往往是由他人整理的回忆录和书信集之类。在塞拉利昂工作的威廉·约翰逊(W. A. B. Johnson)有一部由他人整理的回忆录。在约鲁巴人(Yoruba)地区传教的大卫·辛德勒(David Hinderer)和安纳·辛德勒(Anna Hinderer)是一对夫妇,其中安娜的日记和信件后来被整理为一部回忆录,题为《在约鲁巴地区十七年》。在黄金海岸旅行和传教的弗里曼神父(T. B. Freeman)有一部题为《西非传教录:弗里曼阿散蒂之行》的书;而另一位在黄金海岸工作的丹尼尔·韦斯特(Daniel West)则有一部由他人辑录的信件集。
3.商人记录
进入19世纪后,西非沿海因承继奴隶贸易的余声而仍是英国商人活跃的热土,但“合法贸易”的推进需要开拓更多的原料来源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因此英国商人的足迹也持续地在非洲各个地方延伸。
在西非,英国商人在沿海的立足点主要是尼日尔河河口地区、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在内陆则主要是尼日尔河中下游一带和阿散蒂(Asante)。以尼日尔河为例,在兰德尔兄弟最终完成总体的探查后,苏格兰商人麦克格雷格·莱尔德(Macgregor Laird)即定计要开拓利用尼日尔河流域的商业机会。他装备船只溯航至尼日尔河与贝努埃河(Benue)交汇处,但这次行动因气候和疾病的原因而损失惨重。在莱尔德努力下,英国政府做出了每年派船沿河行商的安排,一些商站得以建立,尼日尔河内陆地区逐渐被英国商人打开。莱尔德本人及其合作者留下了两卷本的《循尼日尔河进入非洲内陆记》。
在东非,英国商人进入相对较晚,并且一度只是在以桑给巴尔为主的地方依托阿拉伯商人等从事代理或集散性质的业务。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商人才逐渐把目光投向东非,其中一大动作是于1888年成立英帝国东非公司(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1891年,一位名叫威廉·菲茨杰拉德(William W. A. Fitzgerald)的专业人士受英帝国东非公司委派对东非沿海地区进行调查,特别关注当地农业发展状况和潜力,后来菲茨杰拉德留下了一部题为《在英属东非海岸、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的旅行:该地区的农业资源和一般特征》的记录。
在南部非洲,白人商人持续从开普敦、伊丽莎白港赶着牛车进入内陆,从奥兰治河到林波波河,从林波波河再到赞比西河。在南部非洲行商的人中,最具特点的是一批猎商,他们通过自己狩猎和从非洲人手中收购获取动物产品,然后带回白人世界出售。猎商中比较知名的有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劳林·卡明(Roualeyn Cumming)、威廉·鲍德温(William Baldwin)、弗里德里克·塞卢斯(Frederick Selous)等。哈里斯著有《1836、1837年南部非洲行记》和《南部非洲的荒野狩猎》,卡明著有《在南部非洲的五年狩猎与冒险》,鲍德温著有《从纳塔尔到赞比西的狩猎与冒险》,塞卢斯则有《在东南非的旅行与冒险》《一个猎人在非洲的漫游》。这些记录记载了象牙等动物产品和枪支等的贸易,以及这些贸易活动对非洲经济社会的影响等内容。
4.殖民军人和官员记录
在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建立之前,英国在非洲活动的军人和官员主要是为了打击奴隶贸易。亨利·亨特利(Henry Huntley)曾参与打击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行动,他留有两卷本的《在西非奴隶海岸的七年》。苏利文(G. L. Sulivan)曾指挥军舰在东非海域巡行搜捕运奴船,后来他将相关经历写成《在桑给巴尔海域和非洲东海岸追踪运奴船:打击奴隶贸易五年的经历》。这些记录对当时“禁而不止”的东非-印度洋奴隶贸易有较多的描述和剖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开始在非洲多个地方进行殖民征服和占领,并开始殖民统治的草创工作,一些参与其中的殖民军人和官员贡献了丰富多样的记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弗里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和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两人。前者参加了征服乌干达的工作并曾担任乌干达军政长官,后又在尼日利亚任职;后者曾在大湖地区镇压掠奴武装,又在乌干达担任特派专员。卢加德著有《我们的东非帝国》,书中讲述卢加德在尼亚萨兰、乌干达与东非多个地区的军事、政治活动,以及其个人的游历和观察,对这些地区的商业发展状况和机会、奴隶贸易状况等进行了叙述。约翰斯顿则有《乌干达保护地》一书,对乌干达的地理条件、居民、历史、语言、动植物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上述由探险家、传教士、商人、殖民军人和官员等贡献的记录,或为公开出版的书籍,或可从公开渠道获得。而在这些之外,还有众多藏于机构或个人处尚未公开者,往往需要去机构或个人所在的实地,从相关人士后人的收藏室、传教会等机构的档案室、英国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各类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处搜寻。
二、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中的经济史资料
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内容涉及非洲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方面,而其中最为丰富的是经济史资料,包含非洲相关地区的土地和物产、经济活动和生产技术、内部经济体系、对外经济关系等,此外还有一些直接明了的数据和图片资料。
1.关于非洲土地和物产的资料
在非洲行走或居留的英国人往往会记录所到或所在处的土地和物产。克拉伯顿曾进入尼日尔河中游流域,称卡诺(Kano)城外有耕种状况良好的种植玉米、小米、高粱、靛青、棉花等的土地。奉命去东非调查农业投资可行性的一位专家则详细讲述了东非沿海的土壤、河流、已种植农产品和未来可种植农产品的情况,特别讲到桑给巴尔的丁香、椰子、芒果、纤维用棕榈、染料植物等已有物产,同时提议可发展种植纤维作物、可可、肉豆蔻、肉桂、甜椒、胡椒、生姜等。
利文斯顿到过濒卡拉哈里(Kalahari)的茨瓦纳人地区,说茨瓦纳人居住的地方没有多少可供贸易的东西,除了皮毯(karosses,南部非洲的一种大张皮制品,常用作披肩、裹毯)外,只有象牙,以及一些兽皮、兽角和牛。而在赞比西河流域行进时,利文斯顿却深为赞比西河谷地区的优良土地和丰富物产所吸引,他描述了赞比西河流域多处河谷地带的肥沃土地、非洲人的田园种植以及牛羊放牧,往西至安哥拉所见的葡萄牙人的咖啡和棉花,往东至莫桑比克所见的棉花和甘蔗,以及在一些地方看到的铁矿露头和煤矿露头等。在赞比西河中上游地区,利文斯顿讲当地酋长可收取的贡品包括谷物、高粱、花生、铁锄、铁矛、蜂蜜、独木舟、木桨、木器皿、烟草、野果干、皮张、象牙等。而在第二次由东海岸出发对赞比西河及其支流进行探查后,利文斯顿进一步明确了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区的土地条件和经济潜力。他指出,东南非海岸有港口和从港口到内陆宜居、宜产高地的通道;赞比西河谷地带和临近河谷的高原地带土地肥沃,适合种植靛青、棉花、烟草、油料作物、甘蔗等,也可以养牛,还有量质俱佳的林木。
2.关于非洲人经济活动和生产技术的资料
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英国人会在非洲遭遇渔猎采集者、农业种植者、牲畜养殖者、手工业者、商人等多种人群,并记录他们各不相同的经济活动和生产技术。
在西非,帕克记录曼丁哥人(Mandingo)的纺棉、织布、染布和缝纫,并很具体地描述他们用的纺织工具、染布流程和缝纫工艺;在东非沿海,伯顿记录桑给巴尔居民混合贝壳、石灰、海沙等做建筑材料;在东非内陆,格兰特记录非洲人制作树皮布和用脚踩、棒抽的方式为谷物脱粒;在南部非洲,则有众多旅行者和居留者记录非洲人牧养牛群的情况,以及记录荷兰殖民者、英国移民、有色人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讲到这些人群相对于非洲其他人群的一些长处。
利文斯顿在刚果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行走,可谓当时最见多识广者。他记录布须曼人用一种毛虫制毒箭狩猎,奥卡万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一带的叶伊人(Bayeiyi)用一种强韧的麻制网打鱼,库鲁策人(Bakurutse)则用芦苇扎制小舟捕鱼,赞比西河中上游地区的科洛洛人(Kololo)用动物脑髓、奶或油鞣制松软如布的皮张,东非内陆的尼扬姆维齐人(Nyamwezi)用蚁丘做炉炼制铜锭,大湖地区的渔民使用以芦苇劈片制成的鱼罾捕鱼。他还记录了赞比西河中下游地区颇为有效的传统农业技术:非洲人会挖洞引水,然后在洞地播种玉米,可在干旱的季节收获单株2~3个玉米棒、每棒约360粒的不错产量,还可在旱季产出豆类、南瓜等;他们还会以土覆草沤烧制作灰肥,然后在灰肥地播种,产量也比较高。
3.关于非洲内部经济体系的资料
旅行者或居留者也会在自己的记录中呈现他们所见或所在的某个区域内部的经济格局,或诸族群间的经济关系。
在中西部非洲内陆,19世纪欧洲旅行者所见的主要是豪萨城邦(Hausa States)、索科托国家(Sokoto Caliphate)、博尔努国家(Bornu)等成型的政治经济实体。克拉伯顿讲述了豪萨城邦卡诺的主要商帮、商人和商业运行的情况,他还从从事跨越撒哈拉商道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到费赞(Fezan)、的黎波里(Tripoli)和卡诺之间的贸易等相关情况。而在索科托居留时,克拉伯顿从一些商人那里了解到廷巴克图(Timbucto)的情况:廷巴克图所在的地区大体上由图阿雷格人(Tuareg)控制,廷巴克图城的黄金来自阿散蒂、贡加(Gonga)和班巴拉(Bambarra),那里的商人以黄金从图阿雷格人手中换取盐,从来自非斯(Fez)、加达麦斯(Ghadamis)和的黎波里等北非地区的商人那里换取布匹。廷巴克图并不出产黄金,却以黄金为纽带缔造了一个大市场,来自北方和东方的商品与来自南方和西方的商品在这里实现交换。
在东非,沿海—内陆一线的商队和贸易网络最引人注目,斯皮克、伯顿、格兰特以及后来的斯坦利等对此多有描述。从沿海到内陆,有阿拉伯人主导的商路和商队,还有波斯人、印度人等。斯瓦希里人和尼扬姆维齐人有的做阿拉伯人的代理,但大部分还是为阿拉伯人商队打工——特别是做搬运工。至于内陆地区的黑人,上层者供应奴隶,或坐收过路费、保护费,下层者则往往被买为奴。他们在从沿海往内陆的一路上会遭遇多种人群:有由阿拉伯人或有阿拉伯血统的混血人、土耳其人等带领的商队,他们主要掠奴、猎象以及从事各种贸易;有黑人的商帮,比如尼扬姆维齐人商帮;有大大小小从事劫掠的流动武装;还有多个组织严密、力量强大的黑人酋邦或者王国,它们可以控制商路来征收贡礼、向商队提供商品和服务,有的还自己参与到商路贸易中去。而斯皮克、伯顿这样的人也会成为商路和贸易的一分子,他们沿商路行进,通过贸易获得给养;他们会用珠子、棉布、铜丝之类的商品与沿途的人交换南瓜、小米、家畜、家禽等食物,或者在向王国或酋邦的统治者提供礼品后获取后者的“慷慨赠与”。
在中南部非洲的广大腹地,非洲人有自己的内部经济循环系统。利文斯顿讲到科洛洛人的酋长塞克莱图(Sekeletu)从多个部落收纳贡赋,而在获得这些贡品后,塞克莱图会在臣民中进行分配,他自己只会保留一小部分。象牙从名义上来讲都属于塞克莱图,但塞克莱图会根据要人的建议并在臣民的监督下公开出卖。塞克莱图可以任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还是要顾全其他人的喜好,如果他独断专行、予取予夺,那么他就可能失去臣民们的拥护。
林波波河以南区域内部经济格局或诸族群之间经济关系的资料,在汤普森、利文斯顿、劳林·卡明、塞卢斯等人的记录中多有呈现。在南部非洲,最显著的是诸种人群的等级化,它反映在经济层面就是:布须曼人、霍屯督人、茨瓦纳人都可能被布尔人收买或抢掠为仆人、劳工,而霍屯督人最有可能处于这种境地;茨瓦纳人可以在布须曼人中强征象牙和皮张,也可强迫后者做工;布尔人和有色人是布须曼人、霍屯督人、茨瓦纳人的一些基本生产、生活用品的供给者——猎商卡明记载有布尔人、有色人和茨瓦纳人之间的贸易,他讲到一些布尔人会在牛价低时装上一车货,去茨瓦纳人的地方换象牙、皮子、鸵鸟毛和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再运到格拉汉姆斯敦(Grahamstown)出卖,而茨瓦纳人要的主要是各种珠子、铜丝、刀子、衣服、火药、枪支、小奶牛、母羊。
4.关于非洲对外经济关系的资料
在19世纪,非洲内部的经济格局和族群经济关系最终还是会与外部世界连接,直接或间接地感应外部世界的影响。
帕克描绘了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一带欧洲人与非洲人的贸易:葡萄牙人最早在这里设立商站,一些葡萄牙语的词汇还被融入非洲人的语言中;随后,荷兰人、法国人、丹麦人、英国人、美国人也来到这里,但最终占主要地位的是英国人。帕克所记的那个时期,英国每年在塞内冈比亚实现的出口额达20000英镑。欧洲人带到塞内冈比亚的商品主要是枪支、弹药、铁器、酒类、烟草、棉帽,还有量较少的宽幅布、曼彻斯特出产的制造产品、印度舶来品、玻璃珠、琥珀以及各种杂货。欧洲人用这些来换非洲的奴隶、金砂、象牙、蜂蜡、毛皮,其中奴隶是大宗,他们由奴隶贩子从遥远的内陆运来。帕克还讲到,当奴隶贩子把奴隶带到海岸而一时又没有欧洲商人收购或市价不佳时,他们就会把奴隶卖给附近村庄里的商人,等条件许可时,奴隶贩子再回购。在这种出卖后再回购的模式下,有一定的投机空间,因此海岸商人也愿意做这个生意。而光靠贩卖奴隶也不行,所以这些奴隶贩子会向沿海人群贩卖土法制的铁、树胶、乳香以及一种果仁油,而沿海人群则主要用盐来进行交换。
在东非,桑给巴尔是一块国际贸易的热土。伯顿在《桑给巴尔:城市、岛屿和海岸》一书中记录了桑给巴尔的外国商人和商业公司的情况。他指出在桑给巴尔的英国商人和公司比较少,多的是来自美国、法国和汉堡等国家或地区的公司;其中法国公司最为突出,它们在桑给巴尔的一个特色业务是收购植物油原料——特别是芝麻,然后运回普罗旺斯提制。伯顿也讲到各公司之间的竞争,比如法国公司想挤走美国公司,而不同的法国公司之间也争斗不已。在另一部题为《中部非洲的湖区》的书中,伯顿则专门记录和分析了以桑给巴尔为枢纽的东非国际贸易的总体情况。他详细列举了东非进出口涉及的产品,其中进口产品主要包括多种日用品、棉坯布、珠子和铜丝等,而出口产品则主要是树脂和从广大内陆地区来的象牙。伯顿还分门别类地对一些产品进行介绍,说明其形状、尺寸、颜色、特质、价格、产地等,比如介绍多种布匹和珠子、几种不同的树脂以及来自不同区域的象牙等。
另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奴隶贸易仍是桑给巴尔及周边陆域和海域一项重要的国际性经济活动,它涉及东非内陆奴隶供应地、桑给巴尔等岛屿中转地以及亚洲南部、塞舌尔、马达加斯加等纳奴地。担任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的里格比将军(General Rigby)对围绕桑给巴尔的奴隶贸易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既记录了英国在禁止奴隶贸易方面的活动,也记载了仍在东非从事奴隶贸易的葡萄牙人、法国人、美国人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方面的情况;他特别讲述了葡萄牙人、法国人、美国人对英国管制的抵制以及英国与相关国家的交涉等,从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层面呈现了当时奴隶贸易在东非禁而不止的局面。苏利文舰长则从禁奴船指挥的视角介绍了桑给巴尔及周边海域的奴隶贸易情况,他讲了当时东非奴隶贸易的基本形式,特别是讲了奴隶走私贸易的情况。此外,从桑给巴尔出发往内陆的探险家如斯皮克、格兰特、利文斯顿,也都有关于围绕桑给巴尔的奴隶贸易的描述,特别是关于桑给巴尔奴隶市场的记录。
在南部非洲,以开普敦、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罗安达(Loanda)、克利马内(Quelimane)等为代表的港口是中南部非洲内陆广大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地点,中南部非洲广大地区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些沿海地方的影响。汤普森从商业调查者的视角分析了开普敦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潜力:开普敦居于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是欧、美与东方连接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开普敦可出产多种供应国际市场的产品,除已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酒类和谷物外,还可以在毛皮、美利奴羊毛、干果、矿物、生丝、海洋渔产品、象牙、树胶、鸵鸟毛、木材等方面进一步开拓。而除了英国本土、北美外,其他地方如南美、毛里求斯、南亚的市场也值得注意。
此外,在一些人关于非洲内部经济状况的记录中也往往能看到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比如在涉及枪支之类的非洲之外的商品、在非洲内陆与沿海外商之间沟通的非洲人商帮、非洲内陆商品的流转和出口、外部的供给和需求对非洲内部的影响等问题时,总是能披沙拣金,找出一些与非洲对外经济关系相关的信息。利文斯顿第一次在恩加米湖(Lake Ngami)地区遇见塔瓦纳人(Tawana)时,发现他们只是把象牙当作大象的“骨头”,但在与利文斯顿同行的一位商人用一把只值13先令的枪换了十根象牙后,塔瓦纳人被震撼了。此后不到两年,塔瓦纳人就开始不断提高象牙的价格。这可以说是外部需求刺激非洲内陆相关经济活动的一个显著例子。
5.数据与图像资料
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中还包含一些经济数据以及生产工具和经济活动方面的图像,它们对于非洲经济史研究具有特别而重要的意义。
汤普森于19世纪20年代在南部非洲旅行,他曾记录初到南非的英国移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特别是对移民移居和置业的成本进行了估计。汤普森说,以牛车旅行为例,如果日行夜宿三个月,那么成本约为75英镑;买地的成本则要看地区和土地本身的条件,这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可能要至少准备700英镑;基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主要包括牛车和简单家具,花费共约150英镑;然后是多种牲畜,按照当时当地的基本数量要求置办,包括奶牛70头、拉车牛12头、小牛30头、母羊100只、阉羊25只、母马10匹、骑乘马4匹,开支分别为70、24、30、100、25、40和28英镑。这是一组与移民移居和置业相关的数据,但它实际上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开普殖民地经济的状况。
利文斯顿1853—1856年旅行的相关记录中搜集了大西洋海岸的罗安达和印度洋海岸的克利马内这两个地方的对外贸易数据,其中有一份反映罗安达在1848年7月至1849年6月间出口情况的统计表,表中呈现,在罗安达出口的商品主要包括象牙、棕榈油、咖啡、皮张、树胶、蜂蜡和热带海藻,其中出口金额最高的是象牙,为48225英镑,然后是热带海藻和棕榈油,分别为23940英镑和12196英镑。利文斯顿还记录了一组罗安达1818/1819年度至1848/1849年度关税收入情况的数据,这组数据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30年间奴隶贸易所带来的关税收入最多,为108028英镑。
除了明确的数据外,一些行记还包含了作者手绘的图像。在没有摄像设备的年代,旅行者们往往需要有一定的手绘技艺,这样才能记录异域所见。
利文斯顿描绘过卡拉哈里妇女用鸵鸟蛋壳容器取水和鲁伍玛河(Rovuma)的渔民用多种渔具捕鱼等。再有,关于东南非内陆和东非内陆奴隶贸易状况的描绘,如掠奴者用树杈枷连奴隶行进图、当着其他奴隶的面用斧子砍死逃跑未遂者图以及鬣狗窥伺下被弃置路边等死的奴隶图等。斯皮克的记录中有多幅描绘东非内陆人群村庄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图,比如尼扬姆维齐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图、尼扬姆维齐人打谷、舂谷图等。斯坦利的《穿越黑暗大陆》一书也包含多幅图画,包括桑给巴尔的港口图、东非内陆的村庄图,以及大湖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器物图等。
三、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中经济史资料的利用
考察16至20世纪之间的非洲史,外部世界的文字记录非常重要。其中,19世纪能贡献的资料最多也最丰富,它们构成一个重要的资料库,特别是就非洲经济史而言。
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和大卫·伯明翰姆(David Birmingham)主编的论文集《前殖民时代非洲的贸易》是将行记资料利用于非洲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典型范例。这本论文集关注20世纪前中部和东部非洲的贸易状况,对中部和东部非洲广大地区的贸易商品、贸易人群、贸易模式、贸易影响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书中有多篇论文不同程度地利用了英国人的非洲行记,如:《尼扬姆维齐人的贸易》较多地使用了伯顿的《中部非洲的湖区》中的资料;《康巴人和北姆里马海岸》中对康巴人及其贸易活动的描述,几乎完全依赖克拉普夫的《在东非的十八年:旅行、研究与传教》;《大湖地区北部》所关注的地区与赤道、尼罗河相关联,他较多地利用了斯皮克、伯顿、格兰特等人的行记资料;《19世纪柯克韦人的贸易与征服》《卡曾伯与坦噶尼喀-尼亚萨走廊:1800—1890》以及《18世纪赞比亚地区居民与宗博的贸易》诸文所指地方多为利文斯顿旅行所见或所闻之处,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利文斯顿旅行记录中的资料。
1.呈现面貌和构建连续
从总体来看,对行记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仍有待继续探索和推进。而在探索和推进的过程中,似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呈现实在的经济面貌,二是构建连续的经济变迁。
一方面,研究者可利用行记资料来呈现非洲前殖民时代乃至史前时代经济生活的面貌。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涉及非洲大片地区和多个族群,各地区的土地和物产,各族群的生产模式、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间的经济关系,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与非洲之外世界的经济关系,这些内容都能在行记中找到资料和数据的支撑。而一些处在偏僻难入之地、发展变迁缓慢的族群,比如布须曼人,对他们经济生活的观察和记录有可能为非洲史前经济生活的还原和演绎提供一些辅助性证据或者启示。
另一方面,研究者可利用不同时期的不同人对同一对象的记录来构建非洲经济变迁的连续。从19世纪英国人的非洲行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来自不同时期、不同作者关于特定地区、特定族群、酋邦或王国等方面的多种资料。立足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线性地呈现一个地区、一个族群、一个酋邦或一个王国的经济变迁。
以南部非洲为例: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接管开普殖民地后,白人北上的步伐加快;19世纪20年代第一批成规模的英国移民抵达后,走向南部非洲内陆的白人越来越多,除了旅行家外,还出现了传教士、被野生动物产品贸易利益吸引的商人和狩猎者,他们的足迹开始越过林波波河,进入赞比西河地区;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探矿寻金者加入,紧随其后的是意在瓜分非洲的殖民者。在百余年间,每一个十年都能找到一些有代表性的在南部非洲不同地方活动的人物,也能找到一些有分量或者有特殊价值的记录。通过综合利用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开普殖民地、茨瓦纳人地区、林波波河—赞比西河间地区的经济变化,可以呈现荷兰殖民者、英国移民、有色人、霍屯督人、科萨人、茨瓦纳人等族群的生产、生活变迁,可以看到祖鲁王国、恩德贝莱王国等的发展起伏。
2.比较、互证和结合利用其他类型资料
在做呈现面貌和构建连续这两项工作时,需要注意比较和互证,还要注意尽可能地与其他类型的资料相结合。
以行记资料为基础呈现面貌和构建连续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更是一个比较和互证的过程。一个人的记录不可避免地会因浸染个人因素而难称客观,这就需要把尽可能多的记录放在一起对照。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资料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内包含多种、多层的局部,按照选定的对象和模式进行排列组合,可在同一时期不同人的不同记录之间进行比较、互证,可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不同记录之间进行比较、互证。
除了能在自身内部比较、互证之外,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资料还可以与之前、之后时代的资料进行比较、互证。
19世纪英国人的诸多记录可以与19世纪之前的葡萄牙人、瑞典人、法国人的记录进行比较、互证。19世纪的记录者们可能会证伪前人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得出与前人不同的见解,但这并不能否定前人记录的参考价值。
19世纪英国人的诸多记录还可以与19世纪之后的民族调查记录和人类学调研成果进行比较、互证。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统治逐渐确立之后,英国及其在非洲各地的殖民当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其所统辖地区的自然条件、居民、历史和文化等进行调查,以及进行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包括委托专业的人类学家对特定地区或特定族群进行跟踪观察和研究等,由此贡献了多种多样具有科学规范性和权威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就可以与19世纪的行记资料放在一起利用。
利文斯顿四次旅行到达了东南部非洲的多个地区,接触了中南部非洲的众多族群如茨瓦纳人、洛兹人(Lozi)、通加人(Tonga)、奔巴人(Bemba)、隆达人(Lunda)、恩戈尼人(Ngoni)、姚人(Yao)等。后世以北罗得西亚为基地的罗得斯-利文斯顿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则专门组织人类学家对涉及今赞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坦桑尼亚等国的多个族群如洛兹人、通加人、奔巴人、姚人等进行了调查研究。人类学家在回顾自己所关注族群的过去时,往往会借助利文斯顿的相关记录,同时又会对利文斯顿的记录做一些深化、扩展乃至纠正。比如利文斯顿曾进入今赞比亚东北部一带,这里河湖众多,渔业资源丰富。利文斯顿描述了这里的鱼类、渔民、捕鱼、食鱼、渔产品加工和贸易等方面的情况。他讲到在一处湖边发现被弃的渔村,当时利文斯顿一行还选了几座茅屋栖身。而后来罗得斯-利文斯顿研究所有一位叫伊恩·卡尼森(Ian Cunnison)的人类学家也在这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他对这里的自然条件与居民生产生活进行了描述,系统地介绍了这里的渔民和渔业经济,这些都可以与利文斯顿的记录进行对照。这位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利文斯顿所说的“被弃的渔村”其实是渔民根据水位涨退或者渔捞实际需要而季节性地空置或占用的情况,并不是真正的“被弃”。
最后还要注意的是,强调文字性的行记资料的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情况下的不可或缺,并不是为了贬低其他类型资料。尽管考古资料严重不足、口述资料可靠性堪疑是非洲史研究中客观存在的问题,语言学资料搜集和利用仍有待开拓,人类学资料“以今证古”也需谨慎,但有用则用,可用则用,这些类型的资料仍然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发挥自己的功能。当19世纪英国人在非洲各地行走和居留时,他们也少有文字的记录可得、可看,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也无非是看和听。从实际内容来看,一些行记资料恰恰是非洲的旧物遗存、口述资料、语言的记录者,而行走、居留者历见并记录的经济、社会、风土人情也并不逊色于后世人类学家的研究。行记资料绝不排斥其他类型的资料,而是要尽可能地与它们结合。
四、结语
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记资料的多样性也意味着它们的利用价值和利用方式的多样性,但是需要注意两点:首先,行记资料的丰富和重要价值并不意味着它是“万灵药”,即便可以从中撷取各种论据,可以基于其呈现细节深入的面貌和在不同层面上可称完整的连续,也仍要注意综合比较,互证求真;其次,说行记资料的优异性和说考古、口述、语言、人类学诸种资料的局限性,并不是二元对立,更不是要贬低后者,而只是说现在前者的可用性要强一些,后者则需要进一步努力发掘、开拓。有用则用之,无则求于他处,多种类型的资料可以比较,可以互证,也可以互相借助,交织糅合,这样,反而更能凸显行记资料的价值,也更有助于非洲经济史乃至整个非洲史的研究。
注释:
①Mungo Park,TravelsintheinteriordistrictsofAfrica,performedintheyears1795, 1796and1797, John Murray, 1816.
②Mungo Park,ThejournalofamissiontotheInteriorofAfrica,intheyear1805, John Murray, 1815.
③Dixon Denham, Hugh Clapperton and Walter Oudney,NarrativeofTravelsandDiscoveriesinNorthernandCentralAfrica,intheYears1822, 1823,and1824, 2 volumes, John Murray, 1826.
④Hugh Clapperton, Richard Lander,TheJournalofaSecondExpeditionintotheInteriorofAfrica,fromtheBightofBenintoSoccatoobytheLateCommanderClappertonoftheRoyalNavytowhichisaddedtheJournalofRichardLanderFromKanototheSea-Coast,partlybyamoreEasternRoute, John Murray, 1829.
⑤Richard and John Lander,JournalofanExpeditiontoExploretheCourseandTerminationoftheNiger,withaNarrativeofaVoyagedownthatRivertoItsTermination, 2 volumes, J. & J. Harper, 1832.
⑥John Hanning Speke,JournaloftheDiscoveryoftheSourceoftheNile,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63.
⑦Samuel W. Baker,AlbertN’Yanza,GreatBasinoftheNileandExplorationsoftheNileSources, Macmillan & Co., 1868.
⑧Richard F. Burton,TheLakeRegionsofCentralAfrica, Harper & Brothers, 1860.
⑨James A. Grant,AWalkAcrossAfrica,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64.
⑩Horace Waller,TheLastJournalofDavidLivingstoneinCentralAfrica:From1865toHisDeath, John Murray, 1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