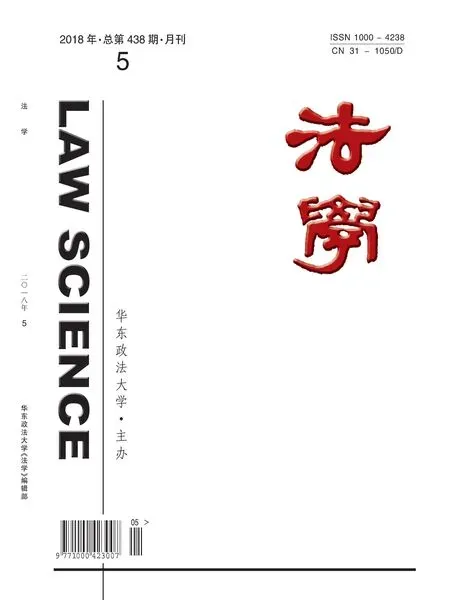日本临终期医疗的相关刑事法问题
●[日]佐伯仁志 文 孙文 译
一、前言
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10月1日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龄化率)为27.3%。〔1〕参见日本内阁府《平成29年版高齢社会白書》(2017年)。临终期,换一个更广泛的词汇可以称为“人生的最终阶段”。最近,临终期的医疗与护理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成了一个大问题。与之相伴,安乐死、尊严死这些刑事法上的问题也越来越受重视。与临终期医疗及其关联刑事法问题相关的日本的情况,想必在中国也已经存在相关介绍,今天,笔者想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谈一谈临终期医疗及其关联刑事法问题中司法、立法与行政三者的关系。
在此先就相关用语进行解释。“安乐死(euthanasia)”是指,为了将濒临死亡并承受着剧烈痛苦的患者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终结其生命的行为。一般来说可以进行如下分类:不继续或者中止延命治疗的“消极安乐死”;以去除、缓和患者痛苦为目的的措施在间接上会导致患者死期提前的“间接安乐死”;为了将患者从痛苦中解脱而终结其生命的“积极安乐死”。另一方面,不以缓和痛苦为主要目的,停止对已经没有康复希望且濒临死亡的患者的无效延命措施,让其自然死亡的情况被称作“尊严死”。现在,尊严死和消极安乐死大多数时候被作为“治疗的中止”来探讨。再者,安乐死和尊严死的问题受国外影响,将其作为“临终协助”(Sterbehilfe, assistance in dying)来探讨的情况也在增加。
二、日本安乐死的起源:森鸥外的《高濑舟》
在日本,对安乐死问题的关注起源于196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的判决。当然,安乐死的问题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
例如,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小说家森鸥外在1916年发表的小说《高濑舟》。日本江户时期,在京都遭受流放的罪犯会乘坐一种叫高濑舟的小舟,前往有大港口的大阪。某日,有一名因杀弟之罪而遭受流放的名叫喜助的男子来到舟上。喜助所犯之罪如下:某日,外出工作的喜助回到家里,发现其弟因难忍病痛企图自杀,已将剃刀深深地刺入了喉管。尚未断气的弟弟向喜助恳求,请把我喉管上的剃刀拔出来,让我能早些轻松离世。喜助虽然犹豫了一阵,但最终还是拔出了剃刀夺走了弟弟的生命。喜助也因此背负杀弟之罪而遭受流放。负责押送喜助的官差听闻此事遂产生了“这真的是杀人吗?”的疑问。“就算放任不管,弟弟无论如何也活不长了。之所以想要早些死去,也是因为难忍病痛。为了让其脱离苦海而动手终结其生命,这真的是犯罪吗?”官差心里疑云难释。
森鸥外的《高濑舟》作为描写安乐死的小说而出名,其背景是,在他的儿子因病进入濒死状态之际,为了让遭受病痛的孩子能少受些罪,而决定让其子安乐死,并委托来家里出诊的医生实施。但此事因知晓原委的岳父强烈反对而作罢。最终孩子却奇迹般地康复了。
在过去,想必私底下偷偷进行安乐死的情况不在少数。当时和现在最大的不同点是,过去人们在自己家里去世的情况占多数,而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医院去世。安乐死在过去主要被作为家庭内的问题来看待,被作为杀人罪而遭受起诉的事件,在1991年东海大学附属医院事件发生之前,全部都是子女杀害父母或者丈夫杀害妻子的事件。〔2〕参见东京地判昭和25年(1950年)5月10日裁时58号4页;名古屋高判昭和37年(1962年)12月22日《高刑集》15卷9号674页;鹿儿岛地判昭和50年(1975年)10月1日判时808号112页;神户地判昭和50年(1975年)10月29日判时808号112页;大阪地判昭和52年(1977年)11月30日判时879号158页;高知地判平成2年(1990年)9月17日判时1363号160页。与之相对,在1991年之后发生的案件全部都是发生在医疗机构,这也反映出了医疗状况的变迁。
三、日本的判例
在此先向各位介绍一下日本有关安乐死的代表性判例。
(一)名古屋高等法院1962年12月22日判决
名古屋高等法院1962年12月22日判决〔3〕参见《高刑集》15卷9号674页。对如下案件,即儿子在遭受病痛的父亲的委托之下,给父亲喂食杀虫剂而致其死亡,关于其中安乐死的成立要件做出了如下解释,即以下6个要件:①患者在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范畴内已属不治之症,且已濒临死亡;②患者的痛苦非常剧烈,已经达到了任何人都不忍见其继续受苦的程度;③以缓和患者的死亡痛苦为主要目的;④在患者尚有明确意识且能进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需要存在患者本人真挚的委托或者承诺;⑤原则上只能由医生来着手实施,如果不能由医生实施时,则需要存在足够认定不能由医生来实施的特别情况;⑥其方法必须是在伦理范围内妥当之法。由于本案中的情况并不符合要件⑤和⑥,因此被告人被判成立受嘱托杀人罪,并被处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的轻刑。
因为这个判决,日本作为早期承认安乐死的国家被介绍到其他各国。但在实际实施了安乐死的案件中,一件无罪判决都不存在,因此笔者对于日本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承认了安乐死尚存疑问。
(二)东海大学医院事件横滨地方法院1995年3月28日判决
如前文所述,以前的安乐死刑事事件全都是由被害人的家属来实施的案件,因此也就都不符合名古屋高等法院所要求的安乐死六要件中的“原则上只能由医生来着手实施,如果不能由医生实施时,则需要存在足够认定不能由医生来实施的特别情况”这一要件。但是,1991年东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生,因对住院中的患者实施了安乐死,作为杀人罪的被告人而被起诉。被告人作为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担任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疗,因被患者家属强烈要求中止治疗行为,最初仅是拔掉了输液和排尿用的导管,之后为了抑制鼾声,注射了具有抑制呼吸副作用的镇静剂,最后抱有杀意,注射了具有停止心跳作用的药物,使患者死亡。该医生因最后注射具有停止心跳作用的药物的行为作为杀人罪的被告人而被起诉。横滨地方法院1995年3月28日的判决〔4〕参见《判例时报》1530号28页。认定,该医生构成杀人罪,处以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该判决内容如下:首先,关于中止治疗行为,在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且没有康复希望,已经进入不可避免死亡的临终状态时,如果要求中止治疗行为的患者的意思表示在实行中止时存在,则可以被允许。并且,在患者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时,也可以根据患者的推定的意思表示来认定;如果不存在患者在事前的意思表示时,也可以通过家属的意思表示来推定患者的意思。接下来,关于安乐死,可以将不作为型的消极安乐死视为治疗的中止,而间接安乐死需要以下要件才能被允许,即能够将该行为视为具有医学正当性的治疗行为范围内的行为,以及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此时患者的意思仅要求有推定的意思就足够。再者,关于积极安乐死的根据,有紧急避难的法理,即为了去除痛苦已经没有其他替代手段时牺牲生命的选择也可以被允许;以及自我决定权的理论,即将此类选择交由患者自己决定。与名古屋高院不同,该判决提出的成立要件如下:①患者被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所折磨;②患者已经无法避免死亡,濒临死亡;③已经尝试了所有其他去除、缓和患者肉体痛苦的方法,不存在其他代替手段;④存在承诺缩短寿命的患者的明确意思表示。关于本案,并不能认定存在患者的推定的意思,最后的积极安乐死行为自不必说,最开始的消极安乐死以及第二步的间接安乐死行为也不能被认为合法。
该判决的第一个意义在于,修正了名古屋高院关于积极安乐死的六要件。特别是将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作为正当化理由的基础,要求患者对于积极安乐死存在明确的意思表示,这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该判决要求在医生已经尝试了所有代替手段之后的最终阶段中存在患者的现实的意思表示,因此也被评价为“事实上封杀了临终医疗中的安乐死”。因为在最终阶段中患者通常都已经失去了意识或者已经失去了能够进行有效的意思表示的能力。并且,对于医生来说,通常都存在通过深度镇静(deep sedation)使得患者失去意识从而去除痛苦的替代手段,在此意义上,该判决要求的要件已经封死了积极安乐死的回旋余地。
该判决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对于没有作为起诉对象的中止治疗行为以及间接安乐死也做了详细论述,并明示了其允许要件。这样的要件由法院来明示在当时尚属首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部分属于该案件的“旁论”,也就是对于得出本案有罪的结论并不必要的论述,对于这样的“旁论”作为司法的作用是否合适的问题也存在一些批判的声音。
(三)川崎协同医院事件判决
1998年,被告人作为川崎协同医院医生,对因喘息型支气管炎的重度发作而造成缺氧性脑损伤进而陷入昏迷状态的患者,拔除了为确保患者呼吸而插入其气管内的软管,并静脉注射了肌肉弛缓剂导致患者窒息死亡,因此被起诉杀人罪。横滨地方法院2005年3月15日判决〔5〕参见《判例时报》1909号130页。认定,该医生杀人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该判决认为,关于中止治疗行为的根据,包含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和医生的治疗义务的界限两方面。判决原文较长,引用如下:
“在讨论临终医疗中与患者的死亡有直接联系的中止治疗的可接受性时,这种中止治疗行为的根据可以认为是尊重患者的自我决定以及以医学判断为基础的治疗义务的界限。……这种有关死亡方式的决定,必须是患者本人的决定这一点自不必说,且该自我决定的前提必须是在获得了充分的情报(病情、可考虑的治疗与对应方法、对死期的预见等)的情况下,接受了关于该事项的充分说明,患者在此基础上基于自己自由且真心实意的意思表示来做出决定。本来,关于临终医疗中的中止治疗行为,在决定时,由于病情的进展、病体的恶化等原因,导致不能直接确定患者本人的自由的自我决定和意思表示的真意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尽量沿袭前文中提到的自我决定的宗旨,为了充分尊重患者的自我决定,去探求患者的真实意愿。关于这一点,如果直接采用只要不能跟患者本人确认就不能认可中止治疗的观点,的确能使解决问题的标准变得明确。但是,其结果可能导致违反患者意愿的治疗一直持续,最终导致事态的发展被委任给医生进行判断,这样反倒招致了与尊重患者的自我决定背道而驰的结果。因此,应该沿袭尊重患者本人的自我决定的宗旨,为了准确的追寻患者意愿的方向性,去探求患者的真实意愿。在探求患者的真实意愿时,患者本人事前的意思表示的记录(生前预留遗嘱living will等)以及与其一同生活的家人等对患者的生活和想法十分了解的熟识者所做出的对患者意愿的推测等,都是对其进行确认的有力根据。此时,如果依然难以探明患者的真实意愿,那么根据‘存疑时生命利益优先’的原则,医生应优先考虑保护患者的生命,继续采取在医学上适当的各种措施。
关于治疗义务的界限,如前所述,医生在可能的范围内采取了适当的治疗且已经达到了在医学上有效治疗的界限,即使患者依然希望持续治疗,但从医学上看该治疗已经有害或者无意义,那么对于医生来说已经不存在继续治疗的义务,或者可以认为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该义务,在此情况下在该限度内的中止治疗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实际上,也存在医生为了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理解依旧持续治疗的情况,但此时应该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义务)。但此时医生的判断也只限定在医学上治疗的有效性等方面。”
将以上要件适用到本案的事实时,判决认定,在本案中,并不能认为患者已处在“没有康复希望且濒临死亡的状况”,也不存在能够推测出患者本人有中止治疗的意愿的事实,且该行为是在尚未达到治疗义务的界限时所采取的违法的中止治疗行为,该行为与违法注射肌肉弛缓剂的积极安乐死一并构成杀人罪。
东京高等法院在受理获罪医生的上诉后,于2007年2月28日的判决〔6〕参见《高刑集》60卷1号3页。中,驳回了上诉,对于中止治疗的要件做出了如下判断:
“1.关于所谓的尊严死……中止治疗的合法根据应该是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与医生的治疗义务的界限。
2.首先,从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来分析时存在一个基本问题,即患者自身对于临终期的治疗方案的决定是否属于宪法上所保障的自我决定权。在常规治疗行为中应最大限度地尊重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因此,也可以认为在临终期同样需要考虑到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但是,一旦患者做出了中止治疗的决定,医生是否就直接应该受到该决定的约束,尚存疑问。再者,即使该行为的权利性质在实体法上得到了解释,但是由于不存在允许尊严死的法律(以下简称‘尊严死法’),在认可中止治疗的合法性时,也需要做出与《日本刑法》第202条的参与自杀行为以及同意杀人行为不相矛盾的解释。因此,以下理解不过是形式论而已,并没有给出实质的答案,即认为中止治疗的相关自我决定权并不是选择死亡的权利,而是指拒绝治疗的权利,医生仅仅是中止了治疗行为而已,并没有对患者的死亡本身做出允许。更进一步来说,根据自我决定权说,如同本案中的患者那样突然失去意识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做出自我决定,只能由家属代替实行自我决定或者根据家属的意见来推测患者的意愿。关于前者,一般并不认可这种类型的代替实行,即使不是代替实行,仅指代替承诺,也不认为存在实质上的差异。并且,即使需要重视家属的意愿,但这样一来,可能存在与患者本人所希望的,减轻在临终期给家属带来的经济以及精神上的负担的意愿背道而驰的风险。……关于后者,即使认为是现实意愿(当下推定的意愿)的确认也不过是一种虚拟而已。……因此,仅靠自我决定权来解释中止治疗的合法性尚存局限。
3.其次,从治疗义务的界限这个角度来解释时,对医生来说不存在进行无意义的治疗或者无价值的治疗的义务,这是非常清晰明了的理论。但是,只能在深度临终期时才能适用这个理论,仅适用于失去了医疗意义的限定性的情况,这在解释论上也不可能得到广泛的运用。并且,在什么阶段可以认为治疗是无意义的也存在问题。只要尚存一丝得救的希望,对医生来说也就存在继续治疗的义务吗?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解决。
4.如此看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都存在解释上的局限。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尊严死的问题,只能依靠制定尊严死法或者替代性的指导意见。即,关于尊严死的问题,在广义上来看,是需要形成国民合意的事情,并将此合意的结果形成法律或者替代性的指导意见。因此,不但要广泛听取国民的认识和意见,也要听取与临终医疗相关的医生以及护士等医疗工作者的意见,并且重视对社会舆论负有责任的媒体的作用。与此相对,法院仅能对该刑事事件中所记录的内容进行有限的探讨。当然,法院可以参考与尊严死相关的一般文献以及鉴定性的学术意见等,但是无论如何也存在力有不逮之虞。并且,要将尊严死合法化,不仅需要实体上的要件,程序上的要件也必不可少。例如,如果将家属的同意作为要件之一,那么是否需要签署同意书、同意书的格式等也自然进入了需要考虑的范畴。医生方面的判断程序以及其主体应该如何划定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不从整体的程序上进行构建,就难以实现适当的尊严死。在此意义上来说,制定法律或者替代性的指导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举国讨论、探讨,并不是仅依靠司法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
5.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在认定该中止治疗的行为是杀人行为的基础上,必然要给出合理的理由。此时,首先要确立一般性的要件,即不仅给出适用于具体案件的结论,且在必要的范围内还应该允许讨论解决具体案件所需的假定的要件。即,从前文的两个视角,也就是从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与治疗义务的界限这两个观点出发,该中止治疗的行为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都不能认为合法,因此不得不认定成立杀人罪。需要强调的是,此时并没有以某个观点是合适的、适当的为前提来分析,仅仅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只有根据以上的某一观点,或者依据以上两个观点来看,已经是属于有合法可能性的案件,法院才应该对其要件的适当性做出判断。关于本案,如下文所述,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都不合法。如此一来,即使假定性地确立了尊严死的要件,其结果也不过就是做出了一个对本案的结论推导来说并非不可或缺的要件的‘旁论’,作为旁论来解释以上问题并不合适。”
如上所述,本案的判决在一般论的基础上,并没有给出哪一主张可以阻却违法性的明示。但是,该判决认可了在一审判决中被否定的家属的委托,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该医生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缓刑3年。
在二审中依然获罪的医生再次上诉,最高法院在2009年12月7日的决定〔7〕参见《刑集》63卷11号1899页。中认为,“(鉴于本案的事实经过)从被害人因喘息型支气管炎的重度发作住院后,到拔出软管为止,并没有采取过判断该患者剩余寿命所需的脑电波等检查,且不过是在病发后仅2周的时候,本院认为并不足以得出关于其康复可能性与剩余寿命的明确判断。且被害人在案发时处于昏迷状态,案件中拔出气管内的软管的行为虽然是根据已经对被害人的康复不抱希望的家属的请求所做出,但该请求……并非是在对被害人的病情等情况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所做出,因此上述拔管行为并不能认定是基于被害人的推定的意愿的行为。基于以上理由,应该认为上述行为并不符合法律上所允许的中止治疗行为。综上所述,原审认为本案中拔出气管内软管的拔管行为与投用肌肉弛缓剂的行为一并构成杀人行为的判断正当合理。”
笔者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中曾提到,关于临终患者的中止治疗,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与医生的治疗义务的界限可分别独立成为相关根据,由于许多临终期的患者不能进行现实的意思表示,因此此时患者的意愿根据推定的意愿就足够,其判断的依据可以是患者事前的意思表示或者根据家属的意愿来推定患者的意愿。〔8〕参见[日]佐伯仁志:《末期医療と患者の意思·家族の意思》,《ジュリスト》1251号(2003年)第104页。另收录于[日]樋口範雄編:《ケース·スタディ生命倫理と法(第2版)》2012年第69~74页。2005年横滨地方法院判决的见解与笔者的见解类似,因此有人评价是采用了笔者的见解。但是,高等法院认为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与医生的治疗义务的界限两方面都尚存应该讨论的问题,不应仅靠法院的判决,还应从立法或者指导意见的方面来解决问题。接下来,将阐述通过立法和指导意见来解决问题的相关尝试。
四、立法的尝试
(一)议员联盟的法律草案
在日本,关于积极安乐死的合法化的立法动向尚未形成,主要存在关于尊严死、中止治疗的相关立法动向。作为最近的动向,2012年超党派的国会议员组成的“尊严死法制化议员联盟”提出了“尊严死法律草案”(即《关于在临终期医疗中尊重患者意愿的法律草案(暂定)》)。该草案中的主要规定如下:法律草案第7条规定,“在患者通过书面或者其他厚生劳动省〔9〕负责日本医疗卫生和劳动保障的主要部门。—译者注命令所规定的方式表达了希望中止延命措施的意愿时(该意思表示仅限于行为人满15岁之后),且该患者已经接受相关临终期的判定,则医生可以根据厚生劳动省命令的相关规定,采取中止延命措施等行为”;第9条规定,“第7条中所规定的中止延命措施等行为不负有民事、刑事以及行政上的责任(包括过料〔10〕一种非刑罚的罚款,一般由日本地方行政机构或者法院做出处罚决定。—译者注)。”
并且,第5条中设置了下列相关定义规定。
第5条:“①本法中的‘临终期’是指,在接受了关于其伤病的所有可以实施的适当医疗措施(包括营养补给措施以及其他维持生命所需措施,下同。)的情况下,患者依旧没有康复可能性且被判断为濒临死亡状态的时期。
②本法中的‘延命措施’是指,并不能治愈临终期患者的伤病或者缓和其痛苦,单纯的只是为了延长该患者的生存时间而采取的医疗上的措施。
③本法中的‘中止延命措施等’是指,中止临终期患者正在接受的相关延命措施,或者当临终期患者处于需要现行延命措施以外的新的延命措施的状态下时,担任治疗该患者的医生没有开始实施所需的新的延命措施。”
该法案因为受到了强烈反对,到现在为止,也尚未提交给国会。反对意见中,既有对法案中所规定的中止延命措施本身进行反对的意见,也有基本上赞成,但认为没有必要作为法律来规定或者将其作为法律来规定并不恰当的意见。
(二)关于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的意识调查
2017年12月厚生劳动省面向一般大众以及医疗从业者展开了“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的意识调查”。有七成的一般大众赞成,在自己不能进行判断的情况下,医疗从业者能依据其事前填写好的、关于愿意接受何种程度的治疗或者不愿意接受治疗的事前指示书来决定医疗方案,并且基本不存在反对意见。但是,对于是否应该将这样的观点作为法律来规定这一问题,认为应该的意见,只占一般大众的22.4%,认为没有必要制定法律的意见占35.1%,不应该制定相关法律的意见占10.2%,各项相加之后持有消极意见的民众占45.3%。由于现在不存在国民对法制化的强力支持,因此笔者认为在近一段时间内该问题被法制化的可能性较小。
五、行政机关的指导意见与通知
(一)厚生劳动省的程序指导意见
行政方面的动向如下:在制作法案的动向的前后,政府方面也试图通过指导意见来解决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2006年发生在富山县射水市市民医院的事件,该事件中医生摘除了7位意识不明的末期患者的人工呼吸机导致患者死亡(但引起该事件的医生在事后却并没有被检察院起诉)。以此事件为开端,厚生劳动省开展了“临终期医疗相关决定程序的研讨会”(会议议长是樋口范雄教授,笔者本人也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了会议),通过多次审议,于2007年5月出台了《关于临终期医疗决定程序的指导意见》。虽然该指导意见在2015年3月更名为《关于在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决定程序的指导意见》,但其基本内容没有改变。指导意见的内容如下:
“1.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以及护理的方式
①最重要的原则是,由医生等相关医疗从业者提供恰当的情报与说明,在此基础上患者与医疗从业者进行沟通,并在患者本人的决定的基础上,进行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
②在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中,相关医疗行为的开展与不开展、医疗内容的变更、医疗行为的中止等,都应该由通过多专业职种的医疗从业者所构成的医疗·护理团队来慎重地进行医学上的妥当性与适当性的判断。
③医疗·护理团队需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减轻患者的疼痛或者其他不适症状,展开包含对患者及其家属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援助在内的综合性医疗及护理。
④以缩短生命为意图的积极安乐死不是本指导意见的规制对象。
2.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及其护理方案的决定程序
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及其护理方案的决定应参照以下事项:
(1)在能确定患者的意愿的情况下
①在经过专业的医学探讨后,在患者基于知情同意所做出的意思决定的基础上,由通过多专业职种的医疗从业者所构成的医疗·护理团队来执行。
②在决定治疗方案时,患者需要与医疗从业者进行充分的沟通,患者进行意思决定后,需要将合意内容制作成书面文件保存。
在上述情况中,需根据时间的经过、病状的变化、医学评价的变化,留意患者意愿可能发生变化,在每次情况改变时都需进行说明并对患者的意愿进行再次确认。
③关于以上程序,在患者不拒绝的情况下,应该将决定内容告知其家属。
(2)在不能确定患者的意愿的情况下
在不能确定患者的意愿的情况下,应遵循以下手续,由医疗·护理团队进行慎重的判断:
①家属能够推定出患者的意愿时,应尊重该推定意愿,以采取对患者最合适的治疗方案为基本原则。
②家属不能推定出患者的意愿时,应该就对患者最合适的治疗方案与家属进行充分的沟通,以采取对患者最合适的治疗方案为基本原则。
③家属不在场以及家属委托医疗·护理团队进行判断时,以采取对患者最合适的治疗方案为基本原则。
(3)需设置由多名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委员会
上述(1)和(2)的情况下,在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医疗·护理团队因病状等原因难以决定医疗内容时、患者与医疗从业者沟通过程中就妥当且合适的医疗内容难以达成合意时、家属意见不统一时、家属与医疗从业者沟通过程中就妥当且合适的医疗内容难以达成合意时,应另外设置由多名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委员会,就治疗方案等进行讨论和建议。”
厚生劳动省将出台的指导意见向全国的医疗相关机构进行了通知,并委托医院进行宣传。该指导意见有鉴于过去发生的东海大学医院事件、川崎协同医院事件等都是由于1名医生的自行判断所引起的问题,所以要求由医疗团队进行商讨并慎重地制定治疗方案。该指导意见如其名字中所表达的那样,仅规定了决定程序的方式,并未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应中止治疗的实体要件,并且也未规定在遵循指导意见的情况下的法律效果。但是,该指导意见是在遵循了该指导意见进行判断时可免除刑事责任的构想下出台的政策,事实上,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医疗从业者因中止治疗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件。
(二)通过行政机关的指导意见以及通知来应对的事例
在新问题发生之后,不依靠修改法律或者法院的解释,由对法律的实施负有权限·责任的行政机关来设置研讨会并进行审议,在此之上出台指导意见或者法律的解释,实务照此执行的例子在日本也较为常见。由于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也参与了研讨会的相关讨论,因此可以认为研讨会上出台的指导意见或者法律解释受到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可。其优点是,与立法和司法解释相比能够更加机动灵活地应对问题。
笔者因为个人的工作关系,除了医疗领域的事例以外,还参与过有关电讯通信业者应对网络攻击的相关对策问题的讨论。日本的电讯通信事业法规定“不得侵犯电讯通信业者所掌握的相关通信秘密”,并对相关违反行为规定了罚则(《电讯通信事业法》第4条1项、第179条)。那么电讯通信业者为了防范网络攻击而对用户的通信进行解析时,是否属于可以被允许的侵害秘密呢?关于这个问题,总务省设置了“有关恰当应对电讯通信业中的网络攻击方式的研讨会”进行讨论,出台的报告书认为遭受网络攻击的电讯通信业者为了进行防御,在必要且适当的范围内对通信的秘密产生侵害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其违法性受到阻却,因此属于被允许的范畴。在此基础上,通信从业者团体“网络安定运营协会”也修改了相关指导意见,并且通信从业者依此采取了应对网络攻击的相关对策(《电讯通信事业法》第4条1项、第179条)。由于网络攻击的问题仍在不断恶化,所以该研讨会的讨论至今仍在持续。
比通过研讨会的报告书来制定指导意见更加正式的应对之法是行政机关通过“通知”所做出的法解释。
比如,日本的《医生法》规定,“非医生者,不得从事医疗事业”,禁止了相关医疗从业行为(第17条),对违反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1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第31条)。该制度规定,只有在大学学习医学并在国家资格考试中合格、取得了国家颁发的资格证书的医生才能从事医疗事业。但是最近随着居家医疗的扩展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在该制度的运用上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当下较受关注的问题是,护理从业者以及教育相关人士是否可以进行引痰行为。ALS〔11〕肌萎缩侧索硬化(ALS)也叫运动神经元病(MND)。—译者注等神经疑难病患者需要依靠第三者将体内的痰牵引出来,而引痰行为属于医疗行为。此时,居家看护或者护理机构的护理从业者进行引痰,是否是医生法所允许的行为也就成了问题。厚生劳动省针对此事,在机构内设置了研讨会进行了审议和报告,在2003年通过“医政局长通知”,仅限对于ALS患者作为“当前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的条件下认可了护理从业者的引痰行为。并且,这也成为了刑法上的实质违法性阻却的根据。之后,在2011年对《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进行了修正,在护理福祉士的业务中增加了“牵引咳痰及其他日常生活中所必要的行为,应在医生的指示之下进行”,如此一来不光是对ASL患者,在以接受特定教育·训练以及获得国家相关从业资格认定为前提下,护理福祉士的引痰行为以及从胃造瘘注射营养液的行为获得了法律认可。
在对残障儿童进行教育的特殊援助学校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厚生劳动省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拨款开展了相关研讨班的研究与报告,并在2004年10月20日通过“医政局长通知”的形式进行了以下公告,即以需要长期驻守看护师且必须接受过相关训练等为条件,基于刑法上的实质违法性阻却的考量,认可特殊援助学校中的教员进行引痰及营养输液属于“不得不采取”的行为。之后,根据前述《社会福祉士及护理福祉士法》的修正,特殊援助学校的教员也作为“护理职员等”的一种,而获得了认可。
像这样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依旧可以阻却违法性的情况,亦即依据所谓的实质违法性阻却的理论,先通过行政机关的通知来进行许可,待相关运用稳定后再通过法律来进行正式确认的方式也较为常见。
(三)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研讨会所做出的解释被法院否决的情况
如前文所述,通过行政机关的研讨会所出台的指导意见或者行政机关的通知来解决问题的优点在于能够灵活应对。而其缺点则是,由于指导意见或者通知并不具有正式的法约束力,因此基于指导意见或者通知的解释,之后被法院否决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但是,一般来说法院会尊重对法律执行负有责任的行政机关的解释,因此进行否决的可能性非常低,且即使真的发生了此种状况,在遵循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的研讨会所出台的解释,相信自己的行为合法而采取了行动的情况下,应以违法性错误为由,对其进行免责。日本过去发生过以下案件:1972年石油业界的相关干部成员遵循行政机关(当时的通商产业省)的行政指导对石油的生产进行了调整,而该行为被认为是触犯了反垄断法而遭到起诉。法院认为,被告人等的行为虽然符合反垄断法中所规定的犯罪的构成要件,且不能作为正当行为来阻却其违法性,但因被告人等误信自己的行为的违法性会被阻却,因此缺乏违法性意识,且关于欠缺违法性意识具有正当理由,因此对行为人等并不能进行刑法的非难也不能对其进行归责,基于欠缺犯罪故意,法院宣告无罪。〔12〕参见东京高等法院1980年9月26日判决·《高刑集》33卷5号359页。
六、司法与立法的相互作用
川崎协同医院事件中的高院判决认为,解决安乐死·尊严死的问题在司法上存在其局限性,法院仅能对该刑事事件中所记录的内容进行有限的探讨,并且,不仅需要实体上的要件,不从整体的程序上进行构建,就难以实现适当的尊严死。在此意义上来说,制定法律或者替代性的指导意见是十分重要的,这并不是仅依靠司法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并且法院也不应该对立法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积极干预。但是,如果这是与宪法所保障的人权相关的问题,即,如果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是宪法所保障的人权,那么作为法院的任务,就不能对该侵害置之不理。
既要恪守司法的界限,又要发挥坚守宪法所保障的人权的司法作用,作为其操作方法可以参考外国的事例。在此简单阐述加拿大的事例。
《加拿大刑法》第224条(b)规定“帮助他人自杀者,处以14年以下的拘禁刑”,但加拿大最高法院2015年2月6日的判决〔13〕Carter v. Canada (Attorney General),2015 SCC 5.认为,以上刑法规定与《加拿大权利与自由的宪章(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第7条相抵触,即与“所有人,在不存在符合各项基本正义原则的情况下,享有生命、自由以及身体的安全性不被剥夺的权利”的规定相抵触而违宪。在此之上,加拿大最高法院并没有直接认定刑法第224条(b)违宪无效,而是给予了议会1年的改正缓冲期。在此之后缓冲期又被延长了4个月,议会通过审议最终在2016年6月对刑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刑法》第224.1条规定,18岁以上对自己的健康具有决定能力的人在罹患“严重且不可能康复的病症”时,基于患者对死亡的“合理的预见可能”,可允许医生或者护士对其进行医疗性临终协助(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刑法所允许的医疗性临终协助中,不光包含递给患者药物由患者自己服用之后导致死亡,还包含由医生或者护士直接投用药物导致患者死亡,也就是说,不光包含帮助自杀还包含同意杀人的类型。
对于以上刑法规定中所提到的对象仅限于对死亡“有合理的预见可能”的人这一点,正在进行更进一步的违宪诉讼。
上述情况中,即使法院做出了违宪判决,但并不直接认定刑法的规定无效,而是给予议会一定的立法缓冲期,并且在此之后的立法是否妥当再由法院进行审理。这种程序在笔者看来是为了产生更加完善的法制度而让司法与立法相互对话的制度,其意义深远值得参考。
七、现状
如上所述是对到目前为止的状况的介绍,就现阶段来说,近期内实现立法的可能性应该较低。但另一方面,关于程序指导意见,厚生劳动省现在正在开展研讨会进行修改,笔者也作为其中的一员参加了讨论,虽然还不是最终确定版本,但在此笔者想介绍一下修订案中的内容。〔14〕在笔者的演讲会结束后不久,《关于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护理决定程序的指导意见》经过部分用语修改,已经正式出台,并向社会公布。参见厚生劳动省网页http://www.mhlw.go.jp/stf/shingi2/0000199004.html。
修订的目的在于,第一,不仅是医疗还要将看护护理也纳入指导意见的范畴内。第二,要将临终关怀计划(Advanced Care Planning, ACP)的理念纳入指导意见之中。名称也变更为《关于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护理决定程序的指导意见》。关于ACP的内容虽然存在许多定义,在新的指导意见(草案)的解说中是指,关于人生最终阶段的医疗护理,由患者本人与家属等人或者医疗护理团队的人进行事前反复沟通的过程。并且,指导意见的修订案规定,“医疗护理团队需注意,患者本人的意愿可能发生变化,每当患者本人的意愿发生变化,都需要对患者的需求进行援助,重点在于与患者本人进行反复沟通。基于此种沟通,理想状况是由患者本人指定某位特定家属作为其意愿推定人。”关于意愿确认的方法,修订案中规定,“医疗护理团队需注意,根据时间的经过、身心状态的变化、医学评价的变化等患者意愿也可能发生变化,此时需要提供合适的情报并进行说明,并对患者的需求进行援助。此时,患者本人可能已经处于自己不能进行意思表示的状态,必须与家属等人进行反复沟通。”
如前文所述,在指导意见出台后,医疗从业者因中止治疗而被起诉的事件一例也没有发生过。在刑法的学说中,有观点认为可以将通过除去生命维持装置来实行医疗中止视为不作为,通过否定医生的作为义务来说明其不可罚性。但是,笔者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第一,不能将一般性的除去生命维持装置的行为等同于不作为。例如,第三者擅自去除他人的人工呼吸机导致患者死亡,自然应该视为作为的杀人问题来处理。第二,给患者安装了生命维持装置的医生去除该装置的行为也并非都能视为不作为来处理。例如,并非患者主治医生的医生擅自去除了人工呼吸机,与第三者时的情况相同,应该视为作为来处理。第三,即使是患者的主治医生去除装置的情况,如果不是被允许的中止治疗的行为,那么也应该将其视为作为来处理。最终,基于不作为说,将去除行为视为不作为来处理,仅限于去除行为属于被允许的中止治疗的情况,并不是因为是不作为所以被允许。也就是所谓的预先设定结论。如此一来,比起通过技巧偷换概念将明显的作为视为不作为来处理,不如直接将符合中止治疗允许要件的去除生命维持装置的行为视为正当业务行为,进而阻却其违法性。这样的理解更加清晰明了。关于其理论根据在前文中也有论述,即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与医生的治疗义务的界限。
以上对于与临终期医疗及关联刑事法问题相关的日本的最新情况,以司法、立法与行政三者的关系为中心进行了简单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