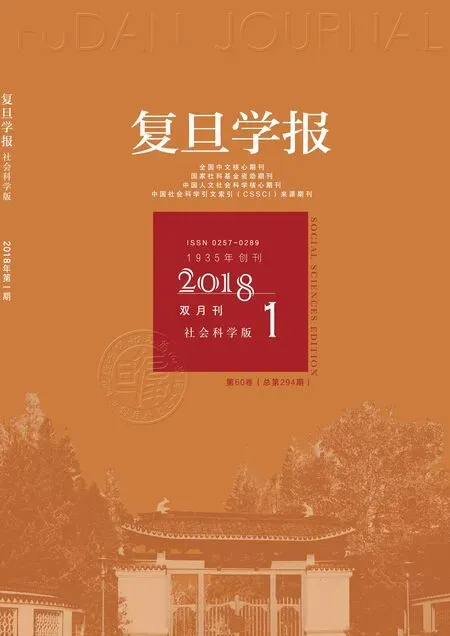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为什么我们这个“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专栏,要发表奥斯特哈默教授这篇关于全球史研究的演讲辞?
这是因为讨论历史中国的“内”和“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回应目前全球史研究潮流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是因为当全球史研究提倡历史叙述超越传统国境,不再强调传统帝国或现代国家的疆域或边界,这使得“内”和“外”又一次变得模糊不清。在那个叫做“全球史”的全方位宏大视界下,超越国境的气候、贸易、移民、战争等,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而“国”之内、外,在历史叙述中,似乎变得有点儿无关宏旨,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作一个回应。
毫无疑问,全球史是近来历史学界日益热门的一个领域,它不同于把区域或国家历史组合起来的传统的世界史,而是通过网络、联系和影响,把全球描述成为一个整体,借用奥斯特哈默教授的话说,全球史“对同时性和同步性感兴趣,青睐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因此,我们看现在若干全球史著作,包括奥斯特哈默教授本人的大作,主要历史叙述中,“定居与迁徙”、“生活与物质”、“城市与乡村”、“战争与革命”、“等级与文明”等主题,取代了过去的王朝更迭、政治人物与事件等主题,给传统的历史学理论、方法和写作,带来了很多新的启示和挑战,这种变化是我们必须举双手欢迎的。但我也一直觉得,当全球史关注弥漫于整体的“网络”、“联系”和“影响”的时候,也需要关注过去国别史叙述中呈现的“变化”、“断裂”和“区隔”,我很赞赏一部关于全球史的通识教材WorldTogetherWorldApart。事实上,世界历史进程中,既有“合”也有“分”,有时候,“分”也许恰恰是更深刻的“合”。而国别史如果可以超越国境,把全球史或区域史作为观察背景,也许正好可以看到,由于帝国/国家的力量,在历史中逐渐区分“内”与“外”,催生了近代的各个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崛起的近代,也催生了全球进一步的融合。其实,16世纪以来现代国际秩序和现代民族国家,不也正是这种区分与融合的结果?
所以,我特别赞成奥斯特哈默教授这次演讲中所说的,“国别史和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不应混为一谈”,也特别赞同“全球史与这种国别史绝对兼容”,这是一个真正研究了全球史的学者的通达见解。我还想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全球史往往比较容易处理文化史上的联系、比较和影响,使得气候、环境、疾病、移民、宗教的传播,以及技术与知识的转移等,比较容易纳入历史学的视野,那么,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国家历史,则相对容易处理政治史。特别是中国,当传统帝国和现代国家同样以政治权力划分“尓疆我界”,从而形塑了华夷/胡汉,也就是“我者”和“他者”的时候,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的“内”与“外”,就还是必要的。
奥斯特哈默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少有的从研究中国(以及英国)起步的全球史家,他的三卷本《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不仅如同各界评论所说,厚重、有趣,令人印象深刻,描绘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十九世纪图景,而且他不断地把“中国”带入“全球”,把“中国”放入“全球”,使得过去中国往往缺席的全球史,开始有了较多的中国故事,也使得中国故事较多地有了全球背景。9月份,他在复旦大学的这一演讲,谈到他对有关全球史和时间的思考,也一样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