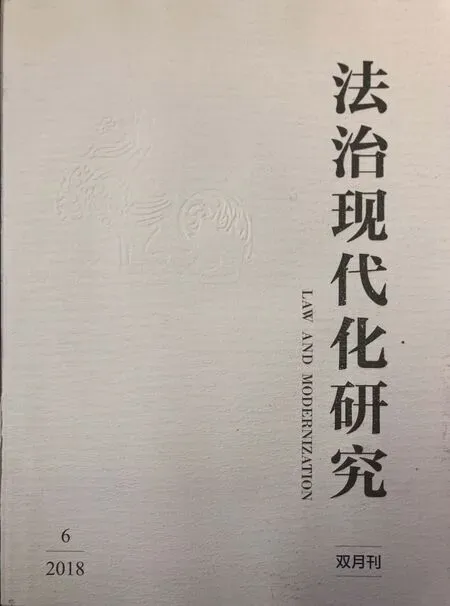美国税收法治生成的历史之维及启示
陈兵 程前
一、背景与问题
没有哪个现代革命像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革命那样深深扎根于税收。殖民地的税收问题不仅导致了独立,更重要的是它在殖民地中形成了统一的力量。曾经分散自治的殖民地为“同税同权”和“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诉求聚集在一起,共同抗争母国的税收暴政,最终形成了如今的美利坚合众国。
作为一个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国家,美国所塑造的税制在当前世界范围内是相当成熟和完备的。①负责起草中国“税收基本法”的李炜光教授认为,美国的税收法治要素是比较完善和成熟的。第一,现代税收的基本要素比较齐备,如政府征税的权力来自人民,须同意才能征税在美国贯彻得最为彻底;第二,法治化的预算编制、审议和拨款制度,国会设有专门委员会与专职国会议员携手设计公共预算法案;第三,治税权在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之间的配置也比较科学,讲究公平和效率。参见李炜光:《权力的边界;税、革命与改革》,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92-93页。纵观美国建国至今200余年的历史,税收一直伴随着美国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波士顿倾茶事件”是独立战争的导火索,南北方因关税矛盾激发了美国内战,20世纪里根总统以“美国第二次革命核心”的《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一扫经济滞胀颓势。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秉持“重塑伟大美国”的施政理念,力推大规模减税计划以期提振持续低迷的美国经济。上述现象的反复呈现已很难被归因于历史因素的巧合,反而共同彰显了税收以及围绕税收进行的法治活动对美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效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我国在各项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下行压力紧迫的新情势下,财税体制改革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抓手。②自1994年分级分税财税体制建立后,我国于2014年的新节点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4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明确强调推进依法治税。与此前若干轮改革类似,财税改革再次成为研讨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切入点。参见贾康等:《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之路:分税制的攻坚克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8页。但令人遗憾的是,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在税收方面建立起严格而缜密的法律约束机制,相关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也远没有结局,这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③为此,我国在2016年至2020年的新一轮财税改革中,将税收方面的立制、立法和修法作为主要内容来进行,具体涉及:完成消费性增值税改革并完成立法,改革和完善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制度,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以及个人所得税制进一步向综合税制过渡。按照预设目标,到2020年前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将基本构建完成,在此基础上促进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理顺和完善。参见前引①,李炜光文,第2页。
对于普遍意义上的法律改革而言,比较的历史研究能细致探讨不同国家在相关领域特定阶段所适用的规则,并检视这些规则是否表达了良好的政策,以及政策制定者在决定应为本国制定那些规则时会如何行动。通过对各国实践的研究来了解新的可能的途径,通过例证来确信这种可能性,并避免从头做起。④Zweigert,Konard&Hein Kotz,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3 rd,trans.by Tony Weir,1998,pp.4-5.对于目前中国税收法治面临的问题,比较地考察美国经验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王立新教授在《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一文指出,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原因,美国成为中国人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领域的政策走向以及美国国内各方面发生的变化,都应该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⑤参见王立新:《六卷本<美国通史笔谈>: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具体到本文所研究的“美国税收法治”⑥张守文教授认为,对“税收法治”的理解,尽管各国具体税制不尽相同,但只要是现代国家,就都会在税收法治方面强调公平、效率、秩序等基本价值,并会将其贯穿于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与守法的各个环节。故中美两国的税收法治的基本价值层面具有相同的内涵与特征。而本文所讨论的“税收法治”以现代国家为主体,独立后的美国具备以下三个现代国家的基本特点:其一,以现代社会为基础,公民拥有政治平等的历史和逻辑前提;其二,以现代国家主权为核心,公民共享并获得发展保障的国家制度体系;其三,以公民权的保障为机制,将社会成员聚会成有公共政治纽带的共同体。故对美国建国之初的税收法治进行探讨之于当代中国的税收法治化进程,其比对主体和基本价值是相对一致的。参见张守文:《税制变迁与税收法治现代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这一宏大命题,考虑到篇幅、史料及比较考察后能够归纳总结出可资借鉴的普遍原则与基本路径,在历史时期上选取了美国税制的“起源时期”,即英属殖民地时期。而考察的切入点则集中于制度形成的基本要素,即法文化思想传统、宪法性权利与实践两个维度。毕竟,比较中美两国税法浩如烟海的具体规定,会使人望而生畏且实效有限。但关注税收法治的基本路径、结构性特征以及基本的法律传统,这些“深深地根植、历史地形成的关于法律的本质,法律在社会和政治国家中的功能,法律制度如何合理构建并运行,以及有关法律如何或应该怎样去制定、实施、研究、完善的观点”。⑦John Henry Merryman,The Civil Law Tradition2,1985,p271.这无疑更值得我们回望历史的具体情境,俯察其详实的制度机理。
二、美国税收法治的传统继受与思想革新
正如伯尔曼所言,“绝大多数法律是某种产生于社会共同体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产生于它的社会习俗和社会传统的东西”。⑧[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7页。17世纪来到北美的移民以英国人为主,在社会行为上继受了大量母国习俗,“法在王上”的自由传统便是其中之一。⑨“法在王上”是对盎格鲁-萨克逊时代英国自由传统的继承,在诺曼公爵统一英格兰领土后经由1215年《大宪章》以成文法律文件形式固定下来。尽管《大宪章》具有历史局限性,仍有效巩固了英格兰传统封建民主秩序,弘扬了“法律至上”的契约自由精神。爱德华·柯克爵士认为,是《大宪章》将英国从专制暴政里解放出来,基本的政治权利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并萌发了英国宪政政府。参见Bryce Lyon,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2nd Edition),New York,1980,pp.310-311.诺曼征服后的英国虽然领土统一,但中央权威因战乱不断而难以集中。国王无法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一般性全国法律,只能将古代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奉为规范国民行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准则。因此,由社会习俗演化而来的习惯法便成为英国及其殖民地早期法律的主要来源。习惯法文化之于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即使国王也受其约束。⑩程汉大:《政治与法律的良性互动——英国法治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在税收问题上,“法在王上”的习惯具体体现为“征税须获纳税人同意”及“国王靠自己收入生活”两项税收传统,并通过君主与臣属的合意与协商,最终达成同意征收的“税收契约”。[11]李建人:《英国税收法律主义的历史源流》,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9页。因而“税权”与“契约”在英国及英属殖民地人民心中是约定俗成的法律信仰,神圣且不容置疑。
在北美殖民地日益壮大的17世纪,英国正经历一场对近代民主宪政发展意义非凡的革命运动,且革命的根源恰恰是君主与议会对于征税权力的争夺。最终,英国内战爆发与《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颁布,使得英国议会在削弱君主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税法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主义”。[12]《权利法案》规定:“第1条,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利,为非法权力;第4条,凡未经议会允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征税,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间或方式皆为非法”。其中第1条关于国王无权废止任何法律的规定,开宗明义地保证了议会的立法权(当然也包括税收立法权);第4条不得随意征税的规定,则保证了议会在税收上处于主导地位。其确立的“议会、法律至上”与“税收法定”以最高原则的形式成为英国宪政民主的制度基石与法律习惯。参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同时,“法在王上”的习惯理念得以延续,在税收领域习惯法所体现的“征税须获纳税人同意”的契约精神,经由《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等法律文件确认,成为“税收法定”的应有之义。英国议会逐渐在税收等重要国家政策上取代君主权威,对殖民地施加直接的影响。因此,前往北美殖民地的英国移民顺理成章地以《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为基础,以英国议会保证其享有“英国人所享有的所有权利、特权以及豁免”的殖民地宪章为依据,达成了“同母国人享有同样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新契约”。这意味着他们在殖民地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力;他们应当遵守普通法;他们不能被任意监禁;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向他们征税。
光荣革命后,“无代表不征税”作为英国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先进文化的象征被进一步推介到英属北美殖民地。尽管英国政府考虑对殖民地征税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但英国第一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Walpole)考虑到对殖民地的保护与承诺而拒绝了议会的要求。至18世纪中叶,英国与法国的“七年战争”(1756—1763)在北美愈演愈烈。战争对税收的需要急剧增长,让北美人民承担一些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军费开支并不是不公平的。母国试图以正当理由开征新税:所征税款全部用于保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这些税款从来不运回英国。殖民地应当为保护他们土地安全的军事力量承担一些费用,毕竟殖民地人民是当时军事胜利的受益者,这一军事胜利消除了法兰西的威胁并开辟了新英格兰西部的土地。客观上,在这之前,如果他们帮助英国国内分担了一些战争负担,英国的土地税确实可以降到和平时期的水平,一些消费税也可以取消。而且,在英国也开始流传,北美的商人从免费使用英国的士兵、战争合同以及走私中牟取了暴利。对于很多英国人而言,北美是一块财富丰沛的土地,可他们的费用还要由英国纳税人来承担。[13][美]查尔斯·亚当斯:《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翟继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15页。
然而,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看来,母国后续的政治措施于新世界而言却违背了议会与移民达成的“契约”,即“殖民地人民同英国人享有同样的税收权利”。英国议会在没有殖民地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于1764年通过了《白糖法》(Sugar Act),[14]这部法律采取了不同于以往普通法精神的“有罪推定”。在新英格兰的审判中,宣告无罪是很常见的,因为根据普通法,如果陪审团的成员认为法律或者惩罚是非正义的,陪审团便会宣告无罪。而宣告无罪就会为向征税官和告密者提起损害赔偿创造条件。故在《白糖法》中,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也被明文禁止,甚至告密者可以获得被没收财产的1/3作为奖励。参见Thomas Andrew Green,Verdict According to Conscience,Chicago,1985,pp.ⅹ-ⅷ.并于1765年征收印花税,[15]1765年,英国法律遵循已经确立的实践,对于报纸、法律文件、商业许可、执照以及一些其他项目开征印花税。印花税在当时整个欧洲大陆是十分流行的税种。来自印花税的资金将专门用于支付驻扎在北美军队的费用。为了使税收更容易执行,当地的公民将被授予销售和发行印花税票的专有权利。参见何芊:《反<印花税法>风波与北美殖民地“爱国”话语的初步转变》,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9期。以回应国内日益激烈的舆论压力。殖民地的立法者为此举行紧急会议,乡镇集会、演讲和宣传册都在谴责英国的税收政策。马萨诸塞州呼吁建立各个殖民地的议会,组建“印花税国会”请求英国议会取消印花税。他们的依据是印花税是“国内税”,需要经过殖民地的同意,未经他们同意不能向他们征税。为此,印花税国会派了几位著名的市民到伦敦游说英国议会取消印花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便是当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被邀请到议会下院发表演讲。以下是富兰克林在议会下院被提问时的回答:
问:“在1763年之前,美洲人对大英帝国的态度是怎样的?”
答:“世界上最好的。他们自愿服从君主的政府,遵守议会的法律……”
问:“那么,现在他们的态度是怎样的?”
答:“已经改变了很多。”
问:“你是否听说过最近才提出的议会对美洲人制定法律的权力?”
答:“议会对于所有的法律都有令人信服的权力,但是征收国内税的权力除外。使用关税来规制贸易的权力从来没有引起争论。”[16]L.W.Labaree,ed,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vol.13New Haven,Conn.,1969,pp.129-158.
富兰克林的证言表明,在提及取消印花税等国内税时,他的态度十分温和。同时,他也清楚地表明了关税(涉外税)是不能反对的。最终,印花税虽然被取消了但却增加了一个附录,即议会在必要时有权征税。议会想让殖民地人们清楚,他们并未以任何方式放弃对殖民地的权力,特别是征税权。当殖民地关于印花税法的抗议结束后,英国议会遵循富兰克林的建议单方面对北美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开征了称为汤森(Townshend)关税的“涉外税”。[17]根据汤森法关税的内容,对于来自英国的纸张、染料、玻璃和茶叶征收关税。其中有一个驻扎条款,要求殖民地支持在北美的英国军队,这一条款可以间接实现印花税没有实现的目的。参见前引[13],亚当斯文,第316页。富兰克林单纯地认为涉外税和国内税是不同的,而结果却是议会提供了殖民地所需要的税收种类。从内容上看,汤森关税与印花税没有实质区别,母国强硬的姿态使得殖民地逐渐滋生出反抗情绪。到1773年,税收矛盾已经无比尖锐,战争开始成为殖民地舆论不断渲染的词汇。
殖民地人民逐渐认识到,此时的母国已经公然违背了“同税同权”的习惯法契约传统,“无代表不征税”的权利制度并不是为远在美洲的殖民地人民所设计,相反,殖民地被推向了“无代表不纳税”的义务抗争之中。然而,从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轨迹来看,这似乎又是一种必然的循环与趋势。英王在光荣革命前为实现对专制王权与财权日益强烈的意愿,不顾习惯法“法在王上”“征税须经同意”的契约传统,最终在同议会的政治斗争中失去了权威。而光荣革命后,母国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为转嫁军事开支、缓和国内矛盾,生硬甚至狡黠地违背与北美殖民地间“同税同权”的税收契约,同样只会招致殖民地人民激烈的反抗。究其原因,习惯法文化自身的固有弊端较为明显:习俗作为调整契约双方的规则工具有着巨大缺陷——权利义务界限模糊,实力强大的一方在法律解释和适用时自由空间过大,毕竟这种风俗的具体内容通常不是成文的。但同时,习惯传统所形成的制度惯性无疑是巨大的,尽管实践中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边界经常被逾越甚至篡改,但断然摒弃或者公然违背法制习惯与风俗传统的制度措施,将很难被有效实施,甚至引发民众心理的强烈反弹,特别是在税收这一同私人权益休戚相关的敏感领域。
三、美国税收法治的权利本位与宪法确认
当习惯法的契约精神被践踏,而母国对殖民地税收权利的侵害又缺乏成文法律依据予以批驳时,美国革命先驱者们将目光投向了洛克的自然法理论。[18]在1776年前主要的26家殖民地图书馆中,足足有一半的图书馆收集了《政府论两篇》《人类理解论》等洛克作品,其中6家甚至藏有1714年编辑的原版书籍。英国法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Raz)认为,在1760到1775年间的“美国政治作品中,洛克是被最频繁引证的作者,其他作者与之相比差距十分巨大”。参见[美]迈克尔·扎科特:《自然权利与新共和主义》,王岽兴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7-28页。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西欧大陆的自然法思想就已经广泛传播到北美殖民地。美洲人从那个时代思想的根本前提——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找到了弥补习惯法不足的依据,最终在历史的选择下成为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有力武器。[19]18世纪有关自然和自然法的哲学,可通过许多渠道在北美殖民地传播。大量的殖民者在英国大学接受教育,牛顿和洛克的著作在那里随处可见。而在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上学的殖民地精英们,从18世纪中期就开始认真阅读洛克的原著或借助解释说明的书籍了解其思想。至少早在1773年时,哈佛图书馆就已收藏了洛克和牛顿的全集;普林斯顿1760年的图书目录里收有洛克的著作;耶鲁图书馆在1755年就有了牛顿的《原理》和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洛克的政治著作为革命领袖们常常说起并顶礼膜拜。参见[美]卡尔·贝克尔:《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彭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6页。
自然法思想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在殖民地独立前后的各种法律文献和名人著作中可以得到体现。在诸多运用“天赋人权、人民主权”理论反抗母国压迫的先驱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20]陈兵:《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生成的历史基础考察——写在“依宪治国”之际》,载《兰州学刊》2016年第1期。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从其早期论文《英属美洲权利概观》开始,便依据自然法理论,否定了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权力,批判了英国国王对殖民地所实行的税收政策。[21]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352页。杰斐逊在《英属美洲权利概观》开篇开宗明义地表明这是一篇“陈诉怨情”的请愿,是因“对上帝与法律平等地、独立地赋予一切人的那些权利进行多次侵犯和剥夺所引起的”,并进一步强调“王在法下、人民主权”的观点,认为“国王是按照法律委派的、权力受限制的、协助庞大政府机器运转的人民的主要官员,而政府机器是为了人民使用而建立起来的,从而受他们的监督”。对于引发殖民地税权危机的《白糖法》《印花税法》《汤森税法》等一系列法案,杰斐逊进行了如下描述:
“我们刚从英国议会给我们的打击所造成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另一个更为沉重的、更为令人惊慌的打击就落在我们身上。单独的暴虐行动可以归咎于偶然的想法;但历届内阁加以推行的一系列压迫政策,明显地证明有一个奴役我们的处心积虑的计划:
陛下在位第4年通过的标题为‘一项许可在美利坚的英属殖民地征税的法案’的法案;
陛下在位第5年通过的标题为‘在美利坚的英属殖民地认可实行某些印花税及其赋税的法案’的另一项法案;
陛下在位第6年通过的标题为‘关于更好地保证陛下在美利坚的殖民地对于英国国王及议会的依附的法案’的另一个法案;
陛下在位第7年通过的标题为‘对纸、茶等征税的一个法案’的另一个法案。
这些构成议会篡权的互相关连的链条,它们已经是屡次向陛下及英国的上下两院请愿的主题,而其中任何一次请愿都没有得到答复,我们将不重复它们的内容,以免打搅陛下。”[22][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7页。
当明确列举了英国议会在税收问题上对殖民地造成的恐慌与专制后,杰斐逊援用自然法理论反驳道:
“难道凭他们(殖民地人民)从未见过,从未加以信赖,而且从未对之行使惩罚或免职权的一个机构(英国议会)发出一句专横傲慢的话,这些政府(殖民地各州政府)就必须被解散,他们的财产就必须被消灭,他们的人民就必须被降低到自然状态吗?大不列颠岛上的16万选民为美利坚诸州的400万居民制订法律,而美利坚的每一个人在道德上、理解力上及体力上都与英国的每个人相等,难道这有理可喻吗?”[23]前引[22],杰斐逊文,第148页。
杰斐逊坚持认为在英国议会向殖民地征税的问题上,只有得到殖民地人民或他们代表的同意才能征税,这是人人享有的自然权利,也是英属殖民地应有的宪政权利。如果,真如英国议会一贯声称的所谓英议会“实质上”代表殖民地人民,那么其必须受包括殖民地在内的人民的制约,上帝和自然法以及英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绝不应受到议会权力的侵害。“在任何情况下,必有更高的权威,即上帝。倘若议会的法律背离上帝和自然法……则这些法令就是违背永恒的真理、平等和正义,因此是无效的。”[24]参见陆镜生:《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2页。
然而,母国此时已不会再过多顾及殖民地的陈诉,当波士顿倾茶事件[25]波士顿茶叶事件在当时是十分严肃的事件,殖民地实际上并不接受这种对私有财产进行肆无忌惮破坏的行为,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大部分美洲人提议应当立即给茶叶的所有者全额赔偿。但不幸的是,英国战船和军队以此为由侵入了殖民地,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前引[13],亚当斯文,第318-319页。发生时,英国议会终于寻得了借口,派出了军队。对于杰斐逊等革命者们而言,温和的“权利请愿”已经不足以鼓舞殖民地各州进行抗争,一份具有纲领性质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应运而生。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起来被管辖者同意的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根据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幸福。”
上述文字作为《独立宣言》的开篇,闪烁着洛克自然法思想的光芒。“托马斯·杰斐逊尽管是这个文献的主要作者,但从不声称他有任何思想上的独创性。”[26][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许季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96页。事实上,《独立宣言》同洛克《政府论》(下篇)的核心思想基本一致。但杰斐逊的独到之处在于能够清醒地根据美国革命形势,在《独立宣言》中将自然权利内容予以明确,将自然法思想予以推理,将自然统治秩序予以论证,从而在理论上为北美反英斗争及殖民地宣布独立表达出重大历史时刻所应有的革命精神和社会反响。具体而言,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运用了18世纪科学论证惯用的三段论逻辑法,将《独立宣言》从结构上分为:大前提,即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人民天赋的自然权利,如果政府侵犯这些权利就应被推翻;小前提,即英国一直侵犯北美人民的权利,并且怀有把暴政强加于北美人民身上的意图;结论,所以北美人民推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而实现独立是理所当然的。[27]参见史彤彪:《自然法思想对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从《英属美洲权利概观》到《独立宣言》,杰斐逊对自然法理论的运用更加娴熟和精辟——在习惯法契约精神的基础上,以“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人人生而平等”理论构造出融合代议制原则、权利制衡原则、法治原则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框架。作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杰斐逊以明确而坚定的语言将近代以来西方权利政治观的主要内容以正式文件形式表达出来,深刻地影响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杰斐逊创造性地将“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积极性权利融入到自然权利理论体系当中,在人民“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与政府“经同意可以征税”创设了关联并达成了契约:政府能够征税须以人民权利的主动让与为基础和前提,若政府在征税后不能保卫其权利,人民便有权将其推翻。这一由《独立宣言》所确立的税权理念,在革命胜利后的1787年被写入《美利坚合众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并直接规定在第1条至第7条第10款,即“掌控立法权”的国会章节部分。[28]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部分原文如下:“All bills for raising revenue shall origina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but the Senate may propose or concur with amendments as on other Bills;-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lay and collect taxes,duties,imposts and excises,to pay the debts and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and general welfare of the United States;but all duties,imposts and excises shall be uniform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No tax or duty shall be laid on articles exported from any state;-No state shall,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Congress,lay any imposts or duties on imports or exports,except what may be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executing it' inspection laws:and the net produce of all duties and imposts,laid by any state on imports or exports,shall be for the use of the treasury of the U nited States;and all such law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evis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ngress.”由于笔者在此仅讨论征税问题,故只对相关内容进行引证。因联邦宪法关涉税收的条款集中于第1条,上述原文可理解为税权被完全赋予代表人民意志和立法权威的国会,行政权和司法权均不得越权干涉。可以说,由征税问题所引发的美国革命,其实质虽是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为各自权益所作的斗争,但以杰斐逊为代表的革命先驱者们显然更加准确地把握了政治形势,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本位的思想旗帜下,母国违背习惯法契约、侵犯自然法权利的税收暴政昭然若揭,其对北美殖民地的统属关系被彻底动摇。[29]1778年,在革命战争开始后的两年,英国议会制定了一部法律,国王乔治三世批准了这部法律,它宣布:“大英帝国国王和议会永远不会为了筹集财政收入而在任何殖民地、省和新开垦地征收任何税收、关税或者其他规费。”不幸的是,这部明智的立法来得太晚了。在接下来的150年里,英国议会不断宣称其对它的殖民地拥有绝对主权,但是在征税问题上,地方的议会,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要表达它们的同意。参见Page.Smith,A New Age Now Begins:A Peopl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Penguin Books(Volume 1)August 1,1989,pp.282-283.
从另一角度而言,自然法的“天赋人权”思想在获得宪法承认前仍然存在着过于原则和抽象化的缺陷,为此,在殖民地鲜有的税务纠纷中,经典的司法判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援用先例。因此,当尚不存在可以代表北美殖民地统一权威的立法机关与行政机构时,法院对母国与殖民地间税务案件如何行使司法裁判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美国宪法文本所依托的实定法体系。
依照美国学者的一般观点,在独立前的殖民地时期,美洲社会自身的法体系仍处于萌芽和孕育状态。[30]英属殖民地时期的法律虽然呈现出早期现代化的一些趋势或特点,尽管它们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在当时还十分有限,而且与19世纪的美国法律相比,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法律还只是一个初生的婴儿,但是从美国现代法律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殖民地时期绝不是美国法律史上的“黑暗时代”。参见Lawrence M.Friedman,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Simon and Schuster,1973,p.29.13个殖民地间风俗习惯差异明显,“普通法”作为英国法最鲜明的特色和传统,在北美殖民地初建的纠纷解决机制真空期,在没有制定法的情况下,“英格兰的普通法就是规则”,是当时移民不可避免的选择。[31]参见[美]莫顿·J.霍维茨:《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谢鸿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尽管来自英国的清教徒起初更愿意依靠习俗和宗教来维持社区秩序,但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由殖民地所演化形成的自治社区间经济关系日益紧密,与此相关联,法律在处理人们之间的诉讼纠纷时也不再仅仅着眼于个别社区内人与人的具体关系,而开始具有超出社区的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和一般性。北美殖民地出现了法律现代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陪审团作用的弱化、事实性答辩向法律性答辩的转变、普通法令状制度的逐步健全、专业律师队伍的出现和扩大等特征。[32]参见韩铁:《美国宪政民主下的司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0页。不难发现,这种“现代化”使得殖民地司法体系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上愈发倾向英国普通法制度,但在理念上又深受当时“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故依据现有文献所记载的一个典型税务案件中,辩护方依据自然权利向法院的普通法权威发起了挑战:
案件起因是英国普通法中特有的令状制度。[33]令状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是由国王发布的一种书面命令,其主要内容为命令接受令状的人去作或不作某事。诺曼公爵征服英国之后,继承和发展了令状制度,使其成为应诉、胜诉的必备要件。至亨利二世时期,国王通过令状制度将司法管辖权从地方法院集中到中央王室法庭。王室法院则通过审理案件发展出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律,即普通法。故作为英国法治的基石,其确立的“严格程序”与“法律至上”原则,经由英国的殖民活动,深刻影响着采用普通法国家的司法实践。参见郑云瑞:《英国普通法的令状制度》,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6期;项焱、张烁:《英国法治的基石——令状制度》,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1期。在克伦威尔时期,原本应由国王签署的一种援助令状(Writ of Assistance),因封建制被短暂废除而转由英国财务法院颁发。通过获得援助令状授权,海关税务官员可有权搜查在英国的走私货物。签发这种独特令状的条件是,税务官员必须在法官面前宣誓走私的财物就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如果能够出示适当的证据,法官就会签发令状,税务官员从而在当地治安官员的协助下进行搜查。
这种独特的令状在1755年来到了殖民地,但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直至1761年,当塞勒姆的一位税务官员要求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继续颁发“援助令状”(乔治二世刚刚逝世,令状需要新王的重新认可才能生效),授权他搜查涉嫌走私的进出口货物时,却引起了马萨诸塞州商人的强烈反对。在波士顿,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身为英国皇家附属海事法庭的总辩护律师却辞去了公职,转而代表当地商人申辩到:
“这种令状是任意权力最坏的工具,是对可以在英国法律文本中找到的对自由等基本权利的最大破坏…当专断暴虐的法庭权力终止以后,这种令状已经无法在我们的法律文本中找到,它只存在于任意权力的鼎盛时期。”[34]Charles Francis Adams,The Works of John Adams,Boston,1850,p525.
即使存在殖民地州法院向海关征税官颁发援助令状的先例,奥蒂斯强调,他所反对的并非援助令状所载的实质内容和形式程序,他警惕的是这种令状会放大法院的任意权力,并通过授权让母国税务官手执援助令状在任何时候闯入任何地方进行搜查。这种做法无疑是对殖民地人民财产权利的肆意践踏,是对自然法根本原则的严重违背,因而理性和英国宪法两者都是反对这种令状的。他借机阐述了自己的自然权利观:人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都是无可争辩的。[35]参见前引[27],史彤彪文。然而马萨诸塞州法院的法官考虑到普通法的先例原则以及母国的政治压力,当庭并没有支持奥蒂斯的诉请。但是它吸引了殖民地人民广泛的关注,使得法官和律师少有地达成共识并一同阻止海关税务官实际获得援助令状。
对此,美国著名税法学者查尔斯·亚当斯认为,这次有关援助令状的税务诉讼在美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案件表达着这样一种威胁:若法院以任意性的司法裁判侵犯公民私人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应如何被救济。显然,殖民地法院的法官也感受到了司法权力扩张所带来的政治隐患与社会压力,英国普通法虽是司法运行的基础,但正如奥蒂斯所言,违背理性和宪法精神的法律体系是不会为人民所接受的。相较于英国法官们的因循守旧,殖民地法院采取了富有勇气和足智多谋的做法:虽然表明上没有支持奥蒂斯的主张,援助令状可以遵循先例颁发,但需要经过法院认可的符合殖民地情势的司法程序。最终援助令状的颁发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大部分令状被法院搜集在一起,无限期等待殖民地法官办公室签署。
为避免此类司法问题的出现,美国建国之父们在联邦宪法中增加了第四修正案。[36]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原文如下:“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houses,papers,and effects,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shall not be violated,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but upon probable cause,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参与了“援助令状“的庭审并印象深刻,在后来由其起草的马萨诸塞州《权利宣言》明确增加“所有搜查必须合理”的条文,其他各州宪法相继效仿,并成为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重要来源之一。尽管这一修正案现在的用途已非常广泛,但最初在采纳它时确是为了限制可能会获得类似援助令状授权的征税官员。这一修正案明确禁止“不合理的查收和查封”,这就意味着包括税务稽查在内的行政权即使有法院授权,也无法单凭可能的证据便肆意窥探。[37]参见前引[13],亚当斯文,第311-312页。
通过“援助令状”引发的税务判决,殖民地法院及其继受自英国的普通法司法体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包容性和创造性,正如丹尼尔·杜拉尼(Daniel Dulany)所说:“普通法纳入了自然法则,理性法则和上帝启示的律法;这些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有同样的拘束力。”美洲人对此坚信不已。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因为司法权对契约习惯传统的尊重,对自然法则权利的尊崇,才使得殖民地的实定法获得了不同于英国普通法的独特品格。殖民地人民不会担心依据美利坚普通法裁决案件时的司法自由裁量权问题。因为这些规则被认为是“建立在诸多永恒的、统一的和普遍原则的基础上的”、普通法和自然法都被定义为“植根于每个人内心的公平与正义”。[38]参见前引[31],霍维茨文,第10-11页。正是基于这一推理,鼓励了殖民地与建国先驱们继续选择普通法作为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法治基石,在联邦宪法的统摄之下,尊重先例与衡平正义的美国普通法体系为制约国会征税立法权和政府纳税执法权创设了有利条件。
四、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启示
仔细观察美国税收法治源起的始末,不难发现如下历史脉络: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国人因在议会中没有代表自己权利的代表而不可能“同意”法律和征税。“同税同权”的缺失状态归根结底在于习惯法文化传统的不成文性与不确定性。在保证该权利的政治形式和实践尚未出现时,自然法权利思想成了殖民地税收抗争的必然选择。而殖民地法院虽然可以按照普通法来审理税收案件,但因为缺少一部制约司法权力的殖民地宪法而大多无效,特别是他们可以为税收而辩论或者同意征税的途径。所以,美国革命的本质可从税收法治的角度解释为:18世纪北美英属殖民地的法律实践与“英国人税收权利”不和谐,而美国独立便是这种不和谐最终呈现的历史结果。
回归到比较研究美国历史的“中国现实”,我们应通过前述对美国税收法治的历史考察,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面临的财税体制改革与法治化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并加深对今天美国税收政策及制度的理解,即经由美国关涉税收的历史文献和司法判决,明确不同国家的人如何看待税收法治,以及不同法律制度中的参与者是如何付诸行动的,从而“应答现实、教育民众、影响政策”。[39]李剑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国史研究》,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当前中国税收法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在立规建制的过程中尚未完全接受“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尚未完全落实“外部政治控制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税收的控制权力是有限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只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纳税的义务,并未涉及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纳税权利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宪法,对于税收立法权的归属并不明确,国务院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权力界限十分模糊。相较之下,美国宪法则在税收法定、税收分权和税收司法三个方面都有涉及,征税权则统一归属国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权利和法律的来源,公民纳税的具体问题可通过下位法解决,但税收立法权的归属至少要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经由美国税收法治经验起源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国上述现实问题显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我国税收法治发育所需要的传统、思想与制度土壤还十分贫瘠。因此,在今后的税收法治化与财税体制改革中,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对此进行以下两个基本维度的根本性关照。
(一)注重培育中国税收和谐文化
在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观念中,从社会契约论出发,税法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协定。政府征税与民众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自愿互换”,税收是人们为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付出的代价。[40]参见蔡昌:《论税收契约的源流嬗变:类型、效力及实施机制》,载《税务研究》2012年第6期。相较之下,中国历史上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契约精神”在我国缺少平等和自愿的法文化传统,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至少在税收领域中应当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这一点是我们从美国经验中可以得出的基础性结论。在现实中,每当我国税收公权和公民纳税私权发生冲突时,公民常处于弱势地位,这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无疑在根本上体现了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发育欠缺思想传统与文化环境。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中严重缺失以税收为核心的价值文化体系,使得大量纳税人丧失税收诚信、寻求法外空间,进而在偷逃税行为中报以思想轻视与心理侥幸,税收法治化进程亦因此遇到了自下而上的现实阻力。张文显教授曾指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和谐是中国法律价值体系的元价值之一。作为法的终极价值与绝对精神,和谐是道德、宗教、法律的共通原则、最高原则、至善原则,是人类的普世文化。因此,和谐对税收法治而言,具有凝练法价值、规范法价值、引领与平衡法价值、反思和追问法价值的作用,是能够催生和推动良法善治的关键要素。故在税收法治这一具体领域,以和谐精神为要旨的税收和谐文化构建,是税法与税制革新的社会性基础与必要性前提。[41]参见张文显:《和谐精神的导入与中国法治的转型——从以法而治到良法善治》,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期。
具体而言,作为保障纳税人权利,推动法治思维代替行政强制监管的思想前提,可从以下三方面予以着眼和布局。
第一,围绕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和谐精神,在进行立制、立法、修法基础上,通过税法教育与社会宣传在企业纳税人与普通公民层面强调“税收法定”与“税收契约”观念。经由对《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宪法》中税收基本权利义务的社会宣介,以保障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税务部门与纳税人在权利义务获悉与运用层面的相对一致,避免税务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权力寻租与自力救济。
第二,提升税收征管部门自身素质,弘扬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核心价值理念。税收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单是对纳税人而言的,对于税收征管部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倡导以爱岗敬业、公正执法、诚信服务、廉洁奉公为基本内容的税务干部职业道德规范,积极探索税收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广泛开展纳税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加强税务部门教育培训和自我学习,推进税收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全面发展。[42]参见胡金木:《着力化解影响税收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载《中国税务》2007年第1期。
第三,在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与转移支付添加“代议监督”的外部控制程序,从而摆脱传统单一的政府内部审计监督体系,拓宽纳税人参与社会公共税收事务的合法渠道,实现税收法治中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互动。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须定期向社会公开财政信息,从而降低事权履行过程中的财力隐形损耗,将纳税人通过权利让与所形成的公共财产真正落实到关键用处,最大限度提升税收社会公开与公众监督水平,为税收法治营造坚实的制度运行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参与氛围。
(二)申明纳税权利的宪法意义及其司法救济途径
首先,明确公民纳税权在宪法上的意义。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掩盖了体制积弊与法治滞后的负效应。反观美国等发达国家,其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与对私权的保障和法治功能的强调成正比,体现为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对行政公权与个人私权间的价值协调,借此充分调动个人创造性,提升社会整体福利。因此,我国税收法治模式的优化,需要以社会主义税收和谐文化为认知基础,通过培育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与纳税权利意识,纠正义务优先权利缓行、绝对经济自由、行政执法泛化等错误观念及做法,通过“税收法定”与“纳税权利”入宪树立正确的税收法治主导价值。公民税收权利法律地位的提升在现实中应主要着眼于:其一,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应明文写入宪法;其二,在宪法基础上,纳税人具体权利配套以下位法明确规定;其三,行政机关税收征管理念与方式予以宪法性规范,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人民代表大会可授权包括税务机关在内的国家行政机关按照税收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依法收集社会公共财产、调整财富收入分配,并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国家征税权加以控制,避免税收异化为侵害人民财产和自由权利的工具。[43]前引①,李炜光文,第13页。最终经由宪法对人民权利进行有力保障,维护法治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其次,释放税务纠纷司法救济效能。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发展有特殊性:其一,整体经济处于转型期,市场化程度有限;其二,国有经济体量庞大,新兴产业虽然发展迅猛但比例有限;其三,治理机构缺乏约束,税收征管政策偏离客观实际。在此背景下,法律尤其是司法活动之于税收的积极作用应得到充分发挥。比对前文美国经验中的司法实践对社会能量的释放作用,我国税收司法活动应具体着眼于保障经营者财产权益的安全与有效、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制约行政征管权限三方面,以实现纳税人权利的法律救济。然而,我国目前税务纠纷诉讼案件总量畸少。[44]目前,税务纠纷的司法解决途径主要通过税务行政诉讼,即纳税人及其他税务争议人因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起的诉讼。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聚法案例”“无讼案例”“北大法宝”等公开途径,2016年度可以收集到的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共368件,以全国3100余个基层法院计算,年平均八个法院才有一起税务纠纷诉讼案件,仅占我国整个行政诉讼案件受理数(331549件)的1.1%。参见靳昊、梁熙明:《2016年最高法行政案件受理数创历史最高》,载“光明网”,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7-06/14/nw.D110000gmrb_20170614_3-04.htm?div=-1,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8月16日。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因“双重前置”规定[45]根据已上网公开的司法文书统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1款关于“清税前置、复议前置”规定的援用率高达31.25%,而其余93个法条的援用率无一超过7%。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上述“双重前置”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其限制了纳税人申请权利救济的渠道,是造成法院受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少,司法人员缺乏税务诉讼实践经验的主要原因。参见杨志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税收法治建设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付大学:《比例原则视角下税务诉讼“双重前置”之审视》,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1期。导致税务诉讼成本过高,降低了司法救济的可能,提升了司法审判的风险,形成了权利价值冲突取舍的困局。故建议司法机关在裁判过程中应有意识有计划地摆脱对“双重前置”的过度依赖,逐渐降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的援用比率,或仅强调复议前置的程序必要性,以同新的行政诉讼法中的复议规定保持协调一致。[46]中国纳税人基数庞大而税收案件总量畸少的矛盾不仅不会节约司法资源,反而会因司法资源利用不足加剧人民法院“思维僵化”“发育不良”的税务诉讼困局。从可行性角度而言,现有国家财政的公信力远高于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加之《行政诉讼法》中诉讼不停止执行的规定,即使没有税收征管法第88条的“清税前置”,国家税收也不会因司法活动受到损失。单独规定“双重前置”反而引发法律冲突,提升裁判难度。参见刘剑文、陈立诚:《迈向税收治理现代化——<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之评议》,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王霞、陈辉:《税收救济“双重前置”规则的法律经济学解读》,载《税务研究》2015年第3期。经由司法活动将“双重前置”弱化为“单一前置”,为解决税务纠纷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救济的渠道。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能型政府在“简政放权”的趋势之下,逐渐将社会治理功能让位于法治。在税收领域,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我国长久以来经济政治改革的着力点,在法治化进程上仍然亟待提升。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际,以税收方面的立制、立法和修法为内容,逐步建立法治化语境下的现代财政制度、严格而缜密的税收法律约束机制,日益成为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47]前引⑥,张守文文。经由对美国税收法治起源的历史基础考察,法文化的税收契约传统、自然法的税收权利理论、普通法的税务纠纷判例对殖民地革命运动影响巨大,并为美国税收法制与税收法律的生成、发展与成熟创设了历史条件与法治基石。因此,有必要辩证地看待美国税收法治起源的历史经验,针对我国财税改革与税收法治步调的脱节,深挖立规建制现实困境背后的机理,从“培育中国税收和谐文化”“明确公民税权宪法性权利”“释放税务纠纷司法救济效能”三个方面出发,夯实我国税收法治发育的传统、思想与制度土壤,以实现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与税收法治化建设的协调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