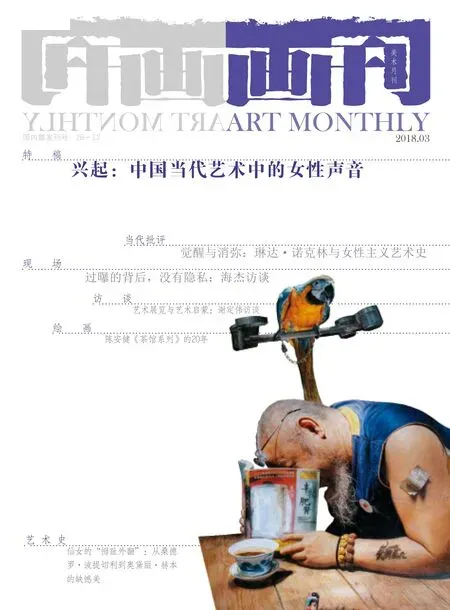仙女的“拇趾外翻”:从桑德罗·波提切利到奥黛丽·赫本的缺憾美
[意]马尔齐亚·法耶蒂(Marzia Faietti)
按: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第十九分会的主题是“审美与艺术史”,主要关注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之外的审美活动之间的关系。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最早在19世纪的德语国家被建立起来,其建立过程与美学紧密相关。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加通(Alexander Baumgarten)最早提出了美学 (Ästhetik)概念,美学一直被视为哲学研究感觉认知的一个分支,同时也被视为“艺术理论”或者“审美理论”。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艺术观念的变化,美学因长期陷入诸如“美的本质”这类形而上问题的研究而招致批判。新兴的学者认为除了美学之外,还应该设立一门艺术科学(Kunstwissenschaft),对艺术作品作出科学、客观的描述和研究,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由此诞生,是一门人文科学内的经验学科。但是随着艺术史学科的日益精细和分工,现在也要对艺术史和审美的关系重新探讨。
然而,艺术史侧重的艺术和广义的审美并不完全是同样的东西,审美的关系跟艺术可以没有关联,却包含了对自然、人以及对于一些对象的感觉和品评。因此这一个特别主题的分会场委托给南京的刘伟冬教授和罗马大学的克劳迪娅·切里·维亚(Claudia Cieri Via)教授来主持,还有另一层深意,是想要依据江南和罗马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审美观念胜地展现出来。当然本分会场所组织的稿件不仅限于此,但是由于他们基于这样的形胜和风貌展开,一个是中国的江南,六朝风月,一个是西方的罗马,铁血长风,各自的艺术和艺术史文化根基,两相对比,差异频现。审美上的差异并不仅仅是感觉问题,而涉及如何来看待事物的方法,由此而引发的问题扩展到历史、生态和政治。尤其是在新媒体发生之后,这样的扩展为新媒体所扩大,而又为新媒体所“损害”。因此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不同的文化中,对于人类所遭遇的共同的问题的反思。
来自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的马尔齐亚·法耶蒂(Marzia Faietti)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在极致女性优雅的甜美图像中描绘出一种令人不快的畸形,这说明个别艺术家以及他们曾进行创作的历史年代对于美的感知都是主观且变化无常的。为此,法耶蒂介绍了一部分15、16世纪的意大利绘画,除了各种各样的美的概念,还要关注反常事物,并将其看作艺术家的灵感和他自我挑战的主要部分。在15、16世纪的意大利绘画中,轻微缺陷是衡量完美的标准,古代也是一样(维纳斯的缺陷),一些生理细节的异常(波提切利描绘的仙女的拇趾外翻)没有影响整体美感;美的新概念的发展,震惊了标准的比例(帕米贾尼诺的人物形象)。(朱青生 戴丹)

《宙克西斯为画海伦选模特》 维克多·莫泰 137cm×102cm 1789年

《春》 波提切利 木板蛋彩 314cm×203cm 1476-1480年
画家和史学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生于阿雷佐,著有《艺苑名人传》。当他在佛罗伦萨家中的艺术和艺术家大厅(Sala delle Arti)里描绘古希腊画家宙克西斯(Zeuxis)创作一幅为克罗托内的朱诺神庙所绘的海伦像时,他旨在证实对自然的艺术选择原则——宙克西斯为了绘制海伦像而挑选了城中最美的女人作为模特,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同的外形特征。此外,在那幅油画中,瓦萨里想赞美“赋形”(design)在调和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上所起的作用,后者是在古人的支持下出现的。
还是在佛罗伦萨,15世纪80年代,Alessandro di Mariano Filipepi,即桑德罗·波提切利,给迷人的女性形象赋予了生命——无论是维纳斯、仙女或真实的女性。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仙女的特殊魅力(对于了解这位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它们是典范式的创造,早在19世纪后期就吸引了年轻的阿比·瓦尔堡的关注),这位佛罗伦萨画家发展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在他熟悉的文化圈中广为流传——在那里,过去和现在优雅而轻易地彼此交汇。然而,他并没有在意要描画出看得见的缺陷;我指的不是不完全正确的比例,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时有关古代的概念还与18世纪60年代温克尔曼所提出的新古典主义美学理论相去甚远。相反地,我想要讨论的是惹眼的异常之处,比如仙女的“拇趾外翻”,这当然无法与维纳斯的缺陷相提并论;姑且不谈为了强化女神凝视的特殊之美而设计的斜视——后者不能归因于病理学,但波提切利确实描绘了脚的病变——即便是处于初级阶段。这些细节是一种艺术的重要标志——这种艺术遵循古典风格,在概念上又是现代的。
这位佛罗伦萨画家毫不犹豫地在精致的女性优雅的甜美图像中描绘一种在审美上令人不快的生理畸形,这使我开始思考在这位艺术家的眼中,以及他进行创作的时代对于美的主观的、不断变化的感知。为此我将介绍15世纪和16世纪意大利绘画的一些例子;通过这些例子,我们能够领会到,除了不断变化的美的概念,对反常性的关注是艺术家的灵感和他自我挑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另一方面,20世纪电影业提供了一些对明显的缺陷持接纳态度的惊人的例子——这些缺陷是专门用来吸引人的;但是我们同样也能找到与此相反的一些现象,即利用替身来掩盖生理缺陷或不完美之处。这种两极对立的行为提出了两个具体的问题:利用替身是否创造了一种非自然的美——这种非自然的美现在已然成了一种甚嚣尘上的大众现象?对生理缺陷的逐渐强化的排斥是否会带来一种理想的美——这种理想的美通常求诸于整容手术,而且无论怎样都与宙克西斯的选择完全不同(他的审美理想并不无视自然的东西)。这些问题很复杂,所以需要各学科的专家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持开放态度,我将只简单提及一个接受个人生理缺陷并将之升华的重要例子,即奥黛丽·赫本——她是代表女性优雅的著名偶像,一个20世纪真正的女神。
让我们回到波提切利来集中关注一些神话人物身上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这些神话人物出现在现藏于乌菲齐美术馆的《春》《帕拉斯和半人马》和《维纳斯的诞生》等作品中,这些作品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主题,近年来这样的研究变得更强化了。我不想在这里提及别处已经写到过的内容,而是希望在视觉上关注一下四肢,尤其是这些优雅女性的脚部。在《春》这幅画里,对脚部的局部畸形的关注集中在维纳斯的形象上,特别是旁边的那位女性人物。在《帕拉斯和半人马》中的女神也显示了类似的缺陷(有人将其称为历史上的卡米拉,她是沃尔西人部族的纯洁的公主,戴安娜的信奉者),除此之外还有手指中间部分环形的肿胀。最后,在《维纳斯的诞生》中,虽然爱神没有显示出类似的病理特征,但是它们出现在左侧与泽费罗斯一起飞翔的风神人格化的女性形象身上——尽管在这里不那么明显(这个形象被解读为奥斯特或克洛里)。我们讨论的是体现了理想的女性优雅和美丽的人物:这些人物被洛伦佐·德·美第奇和美第奇家族广为推广,被诸如阿尼奥罗·波利齐亚诺和玛律西利奥·费西诺这样的诗人和哲学家加以颂扬。然而,正是这些常常被忽视的次要细节,将理想与现实、神话人物和波提切利时代的仙女联系起来了——只要后者采取合适的姿态,并穿上古代的服装。
此外,在15至16世纪之间,肖像艺术也毫不回避地仔细关注最明显的生理缺陷或最令人厌恶的畸形,将肖像画体裁提升为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艺术形式,画家们被要求尝试表现最极致的自然主义的逼真效果,以下作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所绘的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的肖像(乌菲齐美术馆),多梅尼哥·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所绘的一个祖父和他的孙子(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以及拉斐尔画的红衣主教托马索·因吉拉米的肖像(乌菲齐美术馆,帕拉丁画廊)。因此,并非所有画家都遵循宙克西斯的榜样,至少不是在一以贯之地这么做,但是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原因通常与画作的体裁和赞助人有关。

《帕拉斯和半人马》 波提切利 木板蛋彩 148cm×207cm 1482-1483年

《凸镜中的自画像》 弗兰西斯科·帕米贾尼诺 油画 直径24.4cm 1524年
将注意力从15世纪最后20年的佛罗伦萨转移到1524年年末的罗马,我们发现以凸面镜代替平面镜在莱昂纳多·达·芬奇的时代仍然很流行,并被推荐给画家用来纠正错误。一位来自帕尔玛的艺术家以一种试验性的方法将其用来创作一幅自画像。这位艺术家是弗兰西斯科·帕米贾尼诺(Girolamo Francesco Maria Mazzola);当他在1524年夏末抵达罗马时,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传奇的中心——据瓦萨里记载,他身上体现着拉斐尔的精神品质,与他同样地谦恭有礼,同样地外表优雅而令人愉悦。很有可能,这位来自帕尔玛的年轻艺术家在刚抵达罗马之后就开始绘制《凸镜中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现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凸镜的使用,以其不可避免的扭曲(身体和头部可能部分被校正过,似乎不如手部的畸变严重),导致了“一种夸张和跳脱的视觉修辞,与所有镜子相关的那种诡辩的一个尤其典型的例子。”(克兰斯顿,2000)事实上,如果帕米贾尼诺想获得对自然的完美模拟,他会选择使用平面镜,但他的实验性的研究把他导向了另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并不想与自然相媲美,而是能够创生出另一种自然,与最直接的视觉体验的那种艺术有所不同。事实上,帕米贾尼诺似乎继承了这样一种艺术观,即把艺术看作对自然的模仿而非一种仿真;从某些方面来讲,他继承了在他之前的安德烈亚·曼泰尼亚所体现的思想。
这张《凸镜中的自画像》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以至于我们对眼前所见感到困惑:它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幅画?这位艺术家的意图并不是要借助镜子来创作一幅自画像,而是要创造一种错觉,即这幅画就是一面镜子。为此,帕米贾尼诺赋予了它一个凸面的形状,模拟理发店的镜子。令人惊讶的是,在一幅相当早期的作品中,帕米贾尼诺就展示了他未来艺术的基本的先决条件,并且这是通过一面歪曲形象的镜子所反映的他自己的形象来得以实现的。事实上,在这幅自画像中,背景以及描绘元素的改变有助于拆解一个依照中心视角的标准安排而成的结构。
帕米贾尼诺毫无顾忌地接受凸面镜创造的扭曲效果,这暗示着随着时代的推移,艺术逐渐需要一种另类的美,这种美不是基于模仿经过挑选并去除了所有不完美之处的自然现象的单个方面(如在宙克西斯的例子中那样),也不遵循自然世界更具普遍性的那些方面。
对自画像这一体裁尤为关注的帕米贾尼诺似乎在炫耀他意识到了他自身的形体美和作品的美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其为斯泰卡塔圣母圣殿(Santa Maria della Steccata)所绘的自画像(现藏于查茨沃斯庄园)中,位于前景部位的艺术家脸部的刻画所显示出的自我意识丝毫不逊色于拉斐尔和丢勒在他们的自画像中所显示的。有人正确地指出了这幅自画像与纽伦堡的大师所绘的自画像以及基督形象之间的相似性,因此,帕米贾尼诺旨在肯定他的艺术是一种神启的创作就得以强调了。自画像在这幅画所描绘的大背景中被加以强调处理,这有效地说明了创新方法如何在帕米贾尼诺的脑中跃然而出,是一种强烈的、甚至是知性的精致化的结果。在藏于查茨沃斯的这幅画中,艺术家及其自画像几乎提供给我们一种自我告解:这里的顶篮少女看上去要从帕米贾尼诺的头部跃出,正如弥涅耳瓦从朱庇特的头部生成那样。它们与那张脸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达成了一种概念上的统一。此外,在1584年吉安·保罗·洛马奏发布的《绘画艺术、雕塑与建筑的专题研究》中的“概念中形式的构成”部分里,帕米贾尼诺被列于一批画家名单中——在开始创作前,这些画家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以实现创新,这个酝酿过程可与诗人的酝酿过程作类比。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如此美丽的形式只能出自像来自帕尔玛的这位画家——与拉斐尔一样,他在生前以英俊著称。像拉斐尔和帕米贾尼诺这样的例子是瓦萨里思想的发展的起因——按照他的思想,有魅力的艺术家可以将其自身作为艺术中理想美的比喻。
虽然帕米贾尼诺是在拉斐尔及其典型范式和对古代的表现模式的联合支持下探寻一种理想美——他以充满激情的关注来探寻这种理想美,但是他深刻的独创性和对拉斐尔式的标准的背离都正是在他最接近拉斐尔的时候趋于成熟的,由此生成了非常不同的有关 “优雅”、“魅力”和“妩媚”的理念(引用拉斐尔所用的词)——这样的理念或许不仅与原有的理念非常不同,而且能替代原有的理念。在涉及到美的地方,帕米贾尼诺的紧张状态与他所处的文学背景不是毫无关联的——包括古典文学和14世纪的文学(后者特别派生自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正是这样的文学潜流使得帕米贾尼诺可以对“诗如画”(ut pictura poēsis)作出他自己个人的阐释;在这种阐释中,前者的优越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立在后者之上——虽然他的这种阐释是建立在之前的艺术家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莱昂纳多·达·芬奇和安德烈亚·曼特尼亚。
《长颈圣母》是受艾琳娜·芭雅蒂的委托,为她位于帕尔玛的圣母教堂中的礼拜堂创作的,在这位艺术家去世时还未完成(乌菲齐美术馆)。据说这幅画吸收了各种文学作品作为灵感来源,有些比其他更直接。其中,以下参照尤其值得注意,包括对安德里亚·芭雅蒂的诗歌的引用。另一方面,圣母脖子的比例反常而优雅,似乎是在帕米贾尼诺自发自主的艺术想象中独立生成的,源于诗歌和文学文本中可能的参照物。

《长颈圣母》 帕米贾尼诺 油画 132cm×216cm 1535-1540年
在对应于16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半期和第二个10年末这两个不同的时刻,拉斐尔致力于年轻女性的肖像,为人所知的是《La Muta》(乌尔比诺,马尔凯国家美术馆)和《La Fornarina》(罗马,巴贝里尼宫的国立古代艺术美术馆);他创作时眼前有真实的女性形象,他能够将对诸如服装这样的细节细致描绘,与脸部和身体的纯粹且理想的形式结合起来(在《La Muta》中是这样),也能够强调一个女人外貌的迷人的天然感——这样一个女人体现了古典时期与他所处的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在《La Fornarina》中是这样)。此外,被认为在描绘优雅和魅力方面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大师,拉斐尔有时以自然主义的逼真手法来描绘一个男性或女性那些不太吸引人的面部特征,同时依照他对超越庸常的普遍和谐的理解来升华自然主义的细节,意在将偶然性纳入到永恒当中。在帕米贾尼诺的创作中,对一种几乎是破坏性和前卫的另类美的探寻使其变得更加令人着迷,直到它变成了对前所未有的审美标准的探寻,越来越远离古典时期的作品所体现的那些标准。
20世纪的电影业成功地利用了一些具有另类美的女性形象,有时带有模棱两可的魅力和轻微雌雄同体的特征,如葛丽泰·嘉宝。但是,至少在我看来,上世纪代表优雅的偶像仍然是奥黛丽·赫本,趣味精致的喜剧中无与伦比的主角——在这些喜剧中,她清新的优雅感似乎延续了波提切利的仙女们超然脱俗的气质。赫本战胜了那些她看作是自己突出缺陷的特征:消瘦的外表,扁平的乳房,大鼻子和大脚。我们会说这些是轻微的瑕疵;在如此迷人的一个造物身上,它们就好比波提切利的仙女的拇趾外翻,事实上从来没有影响其优雅的外表。

《La Muta》 拉斐尔 木板油画 48cm×64cm 1507年
但是在电影业却通常是另外的情况,例如,不仅在必要时使用替身,还会去掩盖一些生理缺陷。渐渐地,明星体制的要求最终压倒了性质更复杂的艺术创作,人为地加以改变形象,而不是优化那些更有趣的人物形象的魅力——即使他们的美是有缺陷的。
简而言之,选择真实女性做模特儿的宙克西斯,他的画笔已经被整容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所替代。整容已经在各个社会和文化层面变成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做法,重复的面部拉皮手术和矫正手术,徒劳无功地追逐一种完美无缺的美或是延缓衰老,它们导致了程式化的呆板形象,总是比时间的自然推移显得怪异。
在15、16世纪的意大利绘画中,美带有一种轻度的不完美性,是衡量其完美的一个标准——正如在古典时期那样(请记住维纳斯的缺陷),它流连于一些生理细节的异常(波提切利的仙女的拇趾外翻)而没有让它们影响到整体的美;或者说一种新的美的理念由此生成,动摇了各种标准比例(帕米贾尼诺的人物形象)。
如今,整容外科医生的工作似乎奠定了一种美学概念的基础——虽然方法简单粗暴,也没有理论的伪装。由社会上的盲从推波助澜的,以外科手术矫正生理缺陷的做法,导致了一种不再把艺术当作镜子来加以参照的美(艺术被理解为审美价值的储存库,既是主观的,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相反地,它把脸部和身体上(因此也是在整容后的形态的重复序列中)外科手术过程留下的可辨识性当作本身很吸引人的东西。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审美的转折点吗?还是我们只是正目睹la grande bellezza的丧失?(译:白正玲 校:戴丹 金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