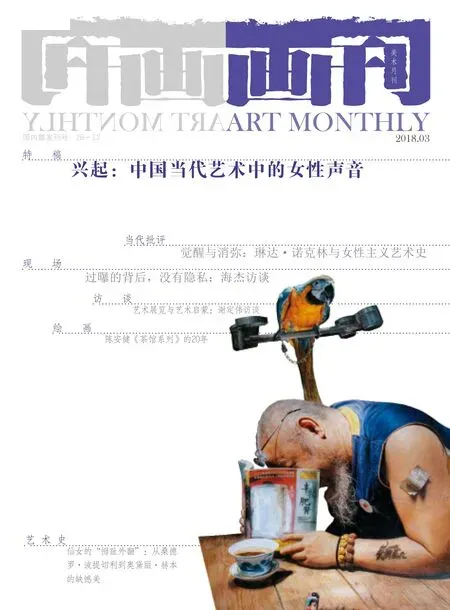觉醒与消弥:琳达·诺克林与女性主义艺术史
杨冰莹(Yang Bingying)
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1931-2017)无疑是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开创性人物。早在20世纪70年代,她的论文《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1971)就轰动了整个艺术批评与艺术史界。这篇著述首次将女性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观照,并且揭示了女性艺术在艺术史中长期被边缘化、被遮蔽的现象。在文中,诺克林分析了学院训练、人体模特写生、沙龙评奖制度对于女性艺术家的种种限制,从而指出女性从事艺术创作所面临的困难绝非传统艺术史所认为的是“天赋缺乏”造成的,而是来自于男权主导的社会体制。
从历史背景来看,诺克林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的横空出世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量男性奔赴前线,导致国内男性劳动力严重紧缺,才使得女性得以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拥有了受教育与就业的权利。经济的独立是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的必要前提,也是推动20世纪60、7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的原因。因此,女权运动在风起云涌的60年代出现并非偶然,与此同时爆发的还有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等等,并催生了70、80年代的女性艺术、同性恋艺术、酷儿艺术、黑人艺术、涂鸦艺术以及青年亚文化,诺克林的女性主义艺术史便是应着这样的时代潮流产生的。
作为一种方法论,诺克林的女性主义艺术理论是建立在对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广泛观照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她早年对于新马克思主义(或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息息相关。从她早期对于库尔贝的研究之中,即可体现出她明确的左翼立场,库尔贝笔下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妇女一度成为她关注的对象。此外,她对于印象派画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的研究同样注重结合19世纪法国的文化社会史,如《莫里索的<奶妈>:印象派绘画中的工作与休闲》。新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的学说给了她极大启发,无论是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抑或法兰克福学派,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化在权力意志之下对于人的建构作用,其中以阿尔都塞对她的影响最大。在法国“五月风暴”中,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最前卫的学说,并在大学取得了胜利。在《女性、艺术与权力》一书中,诺克林承认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的文章是其研究工作的基础,但她“绝非忠诚的阿尔都塞的追随者”。因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探讨的对象主要停留于阶级文化的冲突和协商的层面,而诺克林则将范围扩展至性别领域,指出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白人男性”所主导的社会体制,“也特别关注意识形态在视觉艺术上扮演的角色”[1]。在诺克林之后,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紧密结合成为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及艺术史研究的普遍特点。正是借助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方法论,诺克林所开创的女性主义打破了传统艺术史书写的惯例,充分质疑了有关艺术家的“天才论”,通过一系列颇具解构性的方法,达到了为艺术史祛魅的目的。

琳达·诺克林

《晚宴》 朱迪·芝加哥 装置

《妇女之屋》之一 朱迪·芝加哥等多名女艺术家
此外,诺克林对于女性心理的研究也促成了女性主义与心理学之间的结合。她指出:女性要成为艺术家,不仅需要冲破社会体制所设置的重重阻碍,还必须拥有一个足够强大、勇敢和独立的性格,来摆脱“社会赞同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2]。而大部分的女性无法从事艺术创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于社会指定给她们的单一身份的屈从。因此,诺克林对于艺术史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她揭示了被遮蔽的女性艺术的历史,更在于她使女性主义成为了一种新的艺术史方法论。
同时,诺克林开创的女性主义艺术史是与女性主义艺术实践相辅相成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的大型装置作品《晚宴》(The Dinner Party)以史诗性的方式为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女性正名。在巨大的三角形餐桌上,摆放有39个暗示女性生殖器官的陶瓷餐碟;每个餐碟下面垫着一块手工刺绣餐巾,上面绣着历史上杰出女性的名字;餐桌中央的地板上,还书写着另外999个女性的名字。整个作品既体现了强烈的女性特征,又以极其私密而个人化的方式参与到了历史书写之中。1972年创作的《妇女之屋》(Woman House)同样是由朱迪·芝加哥组织多名女艺术家集体完成的作品。这件作品之所以叫做《妇女之屋》,是因为它展现了充满女性经验的生活空间,如浴室、厨房、花园、衣柜、女孩的玩具屋等等。这件作品在反映女性的私密生活经验的同时,也暗示了社会对于女性身份的固有观念以及女性形象的定型化。女性艺术团体“游击队女孩”则戴上面目狰狞的猩猩面具,以极为激进的方式反对男性对于女性的欲望投射。正如她们在颇具戏谑的海报上写的那样:“难道女人只有变成裸体才能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吗?在现代艺术部分,女艺术家不到5%,但85%的裸体都是女性。”摄影艺术家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则通过扮演不同角色来反对本质主义的单一身份,她或装扮成初到大都市的乡村女孩,或化身为时髦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以此来揭示女性社会身份的多样化。更加具有解构意义的是雪莉·莱文(Sherrie Levine)的装置作品《杜尚的小便器》,她将杜尚的小便池镀上一层金色,以滑稽而戏谑的方式讽刺了现代主义艺术中自鸣得意的男性主义。至20世纪80、90年代,越来越多的杰出的女性艺术家涌现出来,如伊朗艺术家席琳·奈沙特(Shirin Neshat)、印度艺术家芭尔蒂·科尔(Bharti Kher)、美国黑人艺术家卡拉·沃克(Kara Walker)等。她们的作品涉及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主题,显示了当代女性艺术家的广阔视野与洞察力。可以说,女性主义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对于当代女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诺克林在其著作中所显示的富有解构意味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不仅成为女性主义艺术史的主要特征,也深深启发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艺术。

《杜尚的小便器》 雪莉·莱文 装置

辛迪·舍曼摄影作品

《妇女之屋》之二 朱迪·芝加哥等多名女艺术家
这种影响不仅仅限于西方艺术世界,中国当代女性艺术亦受到了有益的启发。虽然诺克林的理论与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并未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艺术思潮涌入国门以来,诺克林所开创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的诸多观念也随之对国内的女性艺术及艺术批评产生了影响。陶咏白、廖雯等学者对于中国女性艺术史的书写无疑可以纳入到女性主义艺术史的整体谱系之中,而喻红、向京、尹秀珍等艺术家的作品亦显示了在经历了女性主义思潮之后的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的发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琳达·诺克林所开创的女性主义艺术史是20世纪70年代的时代产物,是长期以来备受歧视的女性在最初奋起抗争时的理论结晶,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但是,随着女性生存状况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在教育、就业、从政以及性等方面逐渐获得了几乎与男性平等的权利[3],此时再度强调女性的身份特征与生理经验便有了打“身份牌”的嫌疑。因此,当今的大多数女性艺术家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以避免再度被标签化、定型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女性主义”即是这种反身份论的范例。同时,在70、80年代还出现了若干从事“男性主义”创作的艺术家,他们有意强调男性的身份、身体、欲望及私密经验,反映男性在社会生活中所承受的不同于女性的精神压力,形成了一种对于女性主义的反扑。例如艾伦·琼斯(Allen Jones)创作的臭名昭著的雕塑作品《椅子、帽架、桌子》(1969)就引发了包括女性主义者在内的广大观众的强烈不满,以至于作品在数十年间的几次展出中总是遭到破坏。在这件作品中,琼斯制作了三个等身大的女性形象,她们穿着带有性虐意味的内衣,用自己的身体充当着椅子、帽架和桌子。这三件雕塑看似是对于女性的极大侮辱,是一种变态的厌女症(misogyny)的体现;但事实恰恰相反,对于女性身体的控制、虐待、厌恶或侮辱,不过是源于男性潜意识中对女性的恐惧。正如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杂志《多余的肋骨》(Spare Rib)中所说的那样,这件作品的灵感也许来自于男性内心潜在的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再如美国画家艾瑞克·费舍尔(Eric Fischl)的绘画作品,采用了与女性主义艺术相似的角度来进行创作,只是他所强调的是男性的身体经验,如《坏男孩》(Badboy,1980)、《梦游》(Sleepwalker,1980)、《床、椅子、舞蹈、注视》(The Bed,the Chair,Dancing,Watching,2000)等。在《床、椅子、舞蹈、注视》中,费舍尔塑造了一个身心俱疲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他全身赤裸地坐在沙发上,对面脱衣舞女的影子投射到了他背后的墙上,但这似乎丝毫无法让他激动起来。不同于以往男性在女性面前所展示的自高自大和支配性力量,费舍尔笔下的男性形象总是充满了精神焦虑和空虚的性幻想,与被观看的性欲旺盛的女性相比,他们显得虚弱而无力。
无论是后女性主义,还是并未形成强大浪潮的“男性主义”(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都反映了女性主义二元论的局限。其实,在诺克林最初建立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时候,她希望打破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文明与原始、西方与东方、进步与落后、主体与客体、男性与女性、理性与欲望、灵魂与身体等等——将女性主义艺术史引向了更为深层的领域,即传统的知识划分的问题。但在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过程中,女性身份似乎又陷入到了另一种定型化的趋势之中,或者说再一次强化了传统的性别对立,即男性作为支配者和征服者,而女性总是受压抑的欲望对象。与其他研究社会边缘人群的方法论相同(如后殖民主义、青年亚文化研究等),一旦这些边缘人群走向主流,其对应的方法论也就会逐渐失去有效性,因为身份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差别。当女性逐步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能够自由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并获得声望之时,“男性”或“男权”这块靶子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因此,这似乎可以解释今天的女性主义艺术史为什么适用的范畴越来越狭窄,甚至越来越走向消弭。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诺克林就已经指出:不存在一种普遍的“女性气质”或“女性风格”,“女性艺术史是必须加以建构的”。其实,搜集作为集体身份的女性艺术家是她批判和解构主流艺术史的途径而非目的,因为对于女性自身特质的强化只会演变为另一种本质主义;只有消除身份的差异性,才能走向真正的平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主义艺术史的自身消解(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也许是其自身价值——或者说诺克林本人的愿望——的最终实现。

《床、椅子、舞蹈、注视》 艾瑞克·费舍尔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那个特殊时期,诺克林所开创的女性主义艺术史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它与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关联,具有多元化和跨学科的特点,并且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性别视角;它对于女性艺术史的重新发掘,对于男权话语的剖析和解构,对于女性艺术作品价值的界定,均对当今女性艺术乃至整个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1] 琳达·诺克林,《女性、艺术与权力》,游惠贞译,远流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页。
[2] 琳达·诺克林,《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李建群译,《世界美术》2003年第2期。
[3] 这里使用“几乎”,意思是不排除某些不发达地区仍存在男女严重不平等现象;同时,也承认就业方面的性别歧视和对于女性的性侵犯至今仍未彻底消除。
注:本文作者供职于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
——《艺术史导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