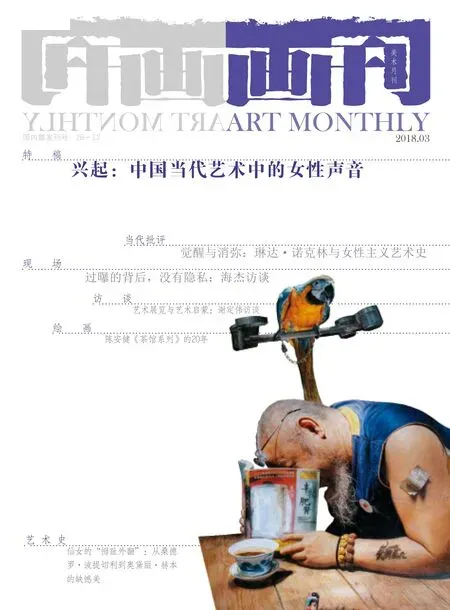你认为自己是女性艺术家吗?
胡祎祺(Hu Yiqi)
2018年2月22日下午,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一场以“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性别问题”(Gender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为主题的研讨会,作为中英交流展“兴起: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女性声音”的学术活动。该研讨会由“批评架构”(Critical Framework)和“当下的声音”(Voices of Now)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通过两名英国学者的发言,从西方艺术史学者的角度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女性艺术家及其作品展开了深入研究及梳理;后半部分则以艺术家自我叙事的方式,让西方观众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更直观的了解。由于参展艺术家皆为女性,因此“女性主义”一词也成为了当场居高不下的话题。在研讨会即将进入尾声时,主持人面对着台上参与研讨会的三名艺术家代表(娜布其、马秋莎、叶甫纳),提出了一个观众普遍好奇的问题:“对于三位同样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的、女艺术家,各位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女性艺术家?”。
三人的答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点,即:“没有,并不会刻意考虑用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去创作。”她们解释说,尽管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女性的身体,或者作品会表现为女性化的特质,但是她们认为,这都是一种基于自身所熟悉的、或所感兴趣的东西而创作的,作品内容更多是一种个人的经验的表达。事实上,我们从她们的作品中也看到了各自关注的焦点:娜布其的装置作品试图以参与式的方式进入空间,通过自然的环境、人为的场域和二维的空间试探人对不同空间的感知;马秋莎的作品,从早期寻找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到后来将兴趣点转移到身体内部,自始至终,个体的生存状态是她一直讨论的话题;叶甫纳最新的作品《指甲计划》,通过指甲完成一件件艺术作品,同时将人的指尖作为一个可移动的展览空间,从而使美术馆不再作为展示艺术作品的唯一场所。三位艺术家都有明确的艺术方向,但因为这是一个以“性别问题”为议题的现场,所以她们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
为什么讨论女艺术家时,非得首先讨论她们的女性身份?

《展示癖套装钻石指甲宝盒》 叶甫纳 10 套指甲、铝合金、施华洛世奇水钻和其他综合材料 50cm×40cm×15cm 2015年

《从平渊里4 号到天桥北里4号》 马秋莎 单频录像 7分54秒 2007年
在这次的展览中,马秋莎展出了一件名为《从平渊里4 号到天桥北里4号》的单频录像。从平渊里4 号到天桥北里4号,从此处搬到别处的两个不同住址,串联了马秋莎所有儿时的回忆——一个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北京女孩的经历:出生于普通的中国家庭,承受上一代期望的独生子女,从小周末就只能被辅导班排满。而被发现画画的天赋,走上艺术道路之后,父母更是花光了所有积蓄供她出国留学。忙乱的生活,让她在偶然间才发现母亲的一缕白发。“妈妈老了”,艺术家平铺直叙又略显含糊地自白,直到最后她从口中拿出了藏在舌头上带血的刀片,一切才归于平静。观众看到这里时,往往都会深吸口气,而具有相似成长经历的中国80后、90后,更是在这里能看到自己的缩影,对这份痛苦也更加感同身受。作品其实是对中国社会生存状态的剖析和解读,这是伴随着城市的喧嚣声崛起的一代,是被称为“最幸福的一代”,却也是伴随着各种压力和痛苦成长起来的独生一代。然而,这件作品在西方观众的讨论下却“变质”了。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研讨会宣传册页上,被截取并放在醒目位置作为海报的是这句:“因为我不是他们期望中的男孩。”这是马秋莎在谈到自己的出生时,提及的她父母当时的想法。中国重男轻女的观点根深蒂固,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也适时削弱了这种影响。但在西方,这可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这句话代表着一种男权化的价值取向?又或者是因为性别问题作为一个先锋性的艺术观点,值得深入探讨?不管怎样,透过美术馆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他们给出的答案。并且,通过这个小小的宣传册和海报,女性主义概念被愈发放大和扭曲,并桎梏了其他内容。以至于当观众再次看到录像时,“因为我不是他们期望中的男孩”成为了影片焦点,于是作品的主题被弱化,女性对家庭、对自己地位的不满,对成长的抱怨占据了上风,使得女性主义的维度成为观众思考这件作品的关键线索。
另一件叶甫纳的作品也面临着这种局限,当她的作品剧照被放上诺丁汉当代艺术馆在社交网络Facebook的官方平台时,不到一下午,评论区就已经热火朝天地吵起来了。因为在这张剧照中,两个身着厨师服的白人男子,在一个类似厨房的环境内,对身着演出服平躺在桌子上的女孩泼倒牛奶。这是叶甫纳参展作品《直播计划:宅之书》中的一个小片段,整部作品都是以“网红”化的日常举动为内容制作的。就连艺术家自己也没有想到,泼牛奶这一戏剧般的一幕被截取后,作品第一时间就被网友添上了性别差异和种族歧视的色彩,围观的群众纷纷留言称“这不算艺术”。他们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件作品是通过在线互动直播的形式完成的,观众在线参与本身变成了艺术作品的一部分,而作品主题更是体现了艺术家对中国“直播热”这一现象本身的反思。对此艺术家也只能说:“观众需要去理解艺术家的观点。”难道在研究女艺术家作品的时候,只能通过性别问题去了解她们的作品吗?
性别的确是无法被抹灭的一层身份,它必然会在艺术作品中透过某些细节表露出来,但性别问题并不是解读所有女艺术家作品的关键所在。就像从达·芬奇、毕加索到达明赫斯特,批评家在分析他们作品的时候,不会首先研究他们作为一个男性所代表的艺术语言,不会用男性主义文化来概括他们的创作。那么当对象变成女艺术家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应该优先讨论其中的性别问题,用女性主义涵括所有艺术家的创作特点呢?女性主义艺术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在当代艺术中确有其地位和影响,甚至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曾掀起一阵热潮,这种观念影响下的艺术家更是不在少数,这点不可否认。但若将所有女艺术家都放到女性主义艺术下标榜并无限地强调,让性别走在艺术观念的前面,那么何时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消除性别等级差异的目的呢?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个体经验和背景,解读一件作品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创作者的原生语境去探讨。
为什么现在中国青年女艺术家,更想和女性艺术保持距离?
当我再次问及其他艺术家同样的问题时,回答都是“不会刻意考虑用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去创作”。这个回答其实是模棱两可的,她们并不想承认自己女性身份,同时又不想被女性艺术这个潮流圈抛弃。前者是艺术家下意识地对自身创作形态多样化表现出的态度,后者则更多是对一种处境的默许,允许批评家在女性艺术范围进行讨论,所以她们不愿意正面回答。为什么女艺术家都在小心翼翼地逃避这个问题?女性艺术因何成为令人进退两难的话题?当对欧美的女艺术家提问:你认为自己是女性艺术家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果断的肯定或是否定,她们有的会大方地说:“是,我是一名女性主义艺术家。”但同一问题上,中国艺术家的态度会变得暧昧——“我是吗 ?”
“女性艺术”这一概念,在中国是一个一直发展着的、尚未被完全厘清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西方的女性主义艺术传入中国,当时学者认为,就本地语境来说,中国不存在“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因此将其改称为“女性艺术”,并认为这种概念上的“女性”,在新时期的中国早已出现。当时曾宣扬的“男女都一样”,其实是男权社会下试图呼唤女性作为与男性同等的生产力而出现的一种“无性”意识形态。女子被要求从事与男子相同的岗位,要显示出男人般的刚强和魄力,“铁娘子”变成了女性的标榜。这种“一刀切”的男女平等,使得女性特质和风格在这过程中被湮灭,人成为无性别的生产工具。因而,用“女性”一词代替所谓的“妇女”,就是替当时被社会政治高压下的无性化的人找回女性身份。直至80年代,“女性意识”在艺术中觉醒。这是以中国文化土壤为引,加以西方先锋的女性主义艺术理论调和出来的中西“女性艺术”论。中国生出了“女性艺术”,但这种在地的转化,却使得“女性艺术”的定义模糊了。对于女艺术家和作品,应该如何定义其为“女性艺术”?是按性别统一归类,还是按思想概念逐一划分?标准如何?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明确。
严格地说,中国到底有没有“女性主义”或“女性艺术”?中国艺术无法用西方的理论并解,尽管二者曾经存在相类似的女性处境,但不同的历史语境是差异的基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女性主义艺术,是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产生的。从争取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到对父权制的社会体制的挑战,从人权到女权,这是西方女权主义浪潮的一条主线,女性主义艺术更是女性艺术家主动争取权利的运动。不同的是,社会背景注定了中国女性的妥协,从五四运动时期伴随着“移风易俗”及“民主科学”一同出现的“妇女解放”,从新时期的“妇女顶起半边天”到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生男生女一样好”,中国的女性都是在革命的浪潮中被裹挟着向前,是潜在的、不自觉的、被动的、丧失话语权的女性独立史。至“八五”新潮时期,西方的女性主义艺术在中国爆发,但这更多的是一种跟风,一种对新兴艺术观的兴趣取向,新鲜期过去后,女性主义的艺术作品又再次归于沉寂。女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是一次次被冲撞后的回应。中西艺术家的不同回答,其实也是女性艺术在中西不同语境发展下必然的结果。
为什么中国当代女艺术家小心翼翼地和“女性艺术”保持距离?如果你向女艺术家们提出这个问题,她们十有八九会反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女性艺术”的称谓?为什么一定要用女性主义理论去讨论她们的作品?事实上,她们对女性艺术是不认可的。向京说:“每次要谈到女性艺术都会让我有种本能的不情愿,聪明的女性艺术家都应该拒绝关于性别的讨论。”艺术家林天苗也曾立场鲜明地声明:“艺术就是艺术,没有男性艺术和女性艺术之分。我就看作品,不看性别,所以我挺反感参加女性团体性的展览,非常反感,跟我所有的想法是相左的。”她们拒绝女性这个身份,并不意味着她们就不具有女性意识,不存在一种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气质。只不过女性的身份对她们更多是一种限制。女艺术家不愿被当做女性艺术家讨论,因为当她们获得女性艺术家这一层身份时,她们将会失去作为艺术家被解读的权利。
反思当下,现在80一代的年轻艺术家,模棱两可地说着不会刻意去使用女性身份进行创作,她们明显对女性这个身份是逃避的。有人认为,这种忽视性别问题、试图回归传统的倾向不符合现代化进程中的女性的个体独白和自觉意识增强的目标,反而有向男权中心主义妥协的趋势。其实并不尽然,性别观念的弱化,正是女性和男性平等对话的基础。性别阶级差异观对于80后、90后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同在一个班级学习艺术的女生早已多于男生,甚至在理论专业可以达到1∶8的比例,女生不再处于弱势和失落的地位。近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更多地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自由表达权利和观点的机会。当“新新一代”的焦点正逐步从社会塑造的“我”走向真正的“自我”,此时需要重点讨论的不是社会给她们的“第二性”条件下生产的艺术,不是一位女性艺术家的艺术,而是一位艺术家对自我及个体经验的探索的艺术。
廖雯说:“人最终是人,不是男人和女人。”就意识形态和主观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我们也正不断消解着性别的差异,这样女性才能得到和男性同等对话的机会。但是,男人和女人又是不同的,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上帝创造人的宗教角度,物理形态上的男人和女人的差异是不可取消的。如果男人和女人真的具有共性,那么这个问题也不需要消解,消解的姿态就在于这是一个事实。在今天,事实是我们更要强化、强调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在性别、政治话语的理论研究中,在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艺术中,突出女性性别立场的差异。尽管这不需要刻意地在作品中展现出来,但是女性艺术家本身需要具有这种立场。拒绝趋同于和男性一样的性别特征,拒绝抹平所有的性别差异,恰恰是证明女性独立价值的所在。
你认为自己是女性艺术家吗?真正持有的答案是不需要迟疑的。是女性艺术家就需要敢于承认。在今天这个强调男女平等的时代,恰恰是说明自己是女性艺术家的时候,才更具有男女平等性,才证明女性自我的独立意识,而不是通过和男性的趋同,消解和掩饰自己的女性主义诉求。
[1]陶咏白 贾方舟主编.中国女性艺术.香港:四季出版社,2016年6月.见序言。
[2]向京.为什么要谈女性艺术?. Hi艺术 专栏. 2016年8月23日
[3]刘倩. M4系列之林天苗:“我就看作品,不看性别!”雅昌艺术网专稿.2012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