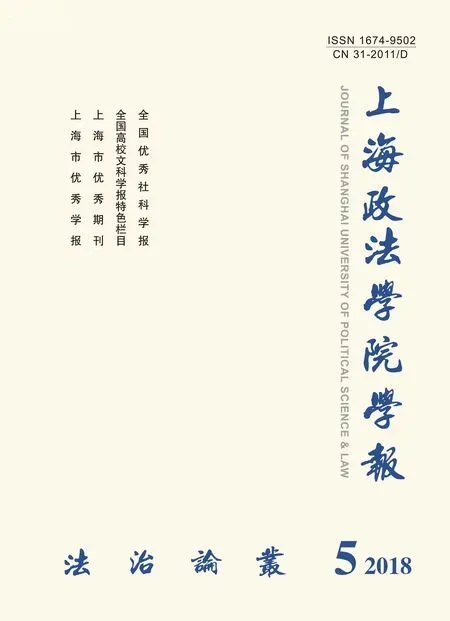论国际商事仲裁中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冲突与协调
——以快速仲裁程序中强制条款的适用为视角
刘晓红 冯 硕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际仲裁的效率问题愈发得到各方重视,希望通过规则革新提高国际仲裁效率的呼声也愈发强烈。①根据伦敦玛丽皇后大学国际仲裁学院和White & Case律师事务所联合发布的2018年国际仲裁调查报告(以下注释均称《QMUL报告》)显示,提高效率是国际仲裁未来改革的首要任务,而这也得到了超过60%的受访者的认同。参见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White & Case, 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38.在提高仲裁效率上,世界主要仲裁机构均作出了诸多尝试,国际商会仲裁院(IC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以及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等推出的快速仲裁程序(Expedited Procedure)便是其中的代表。但在仲裁实践中,快速仲裁程序也暴露出某些问题并引发各方探讨。尤其是在ICC和SIAC最新版仲裁规则中,均以强制条款的方式规定当事人只要选择快速仲裁程序,即使仲裁协议存在不同规定也应按照快速程序的规则进行仲裁。②2017年版ICC仲裁规则规定“By agreeing to arbitration under the Rules,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is Article 30 and the Expedited Procedure Rules set forth in Appendix VI (collectively the “Expedited Procedure Provisions”) shall take precedence over any contrary terms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2016年版SIAC仲裁规则规定“By agreeing to arbitration under these Rules, the parties agree that,where arbitral proceedings a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pedited Procedure under this Rule 5,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set forth in Rule 5.2 shall apply even in cases where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contains contrary terms” 。然而,仲裁协议作为意思自治的表现,其既是仲裁机构获得管辖权的来源,也是仲裁规则得以适用的前提。仲裁规则否定作为其前提的仲裁协议是否具有法理基础需要探讨,其会不会导致意思自治的减损也需明确。笔者认为,上述问题本质上反映了国际商事仲裁中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冲突,而如何协调好两者关系事关国际商事仲裁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我们要认清国际商事仲裁发展中机构管理权扩张的趋势,探究其扩张原因并明确其扩张的界限。另一方面,我们更应明确意思自治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价值本位和内涵扩展,从而探寻化解冲突、实现协调的可行路径。因此,本文将从仲裁机构管理权扩张和仲裁意思自治两个方面挖掘两者冲突背后的原因,并在明确原因的基础上探寻不同层面上协调两者关系的可行路径。从而得出相关结论,推动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协调下国际商事仲裁的良性发展。
二、国际商事仲裁中机构管理权的扩张与因应
在当今国际商事仲裁体系中,仲裁机构居于重要地位,其既是保证仲裁体系正常运转的必要枢纽,也是推动仲裁制度不断改革的主要力量。从仲裁近年来的发展来看,由仲裁规则所反映出的仲裁机构管理权不断扩张已渐成趋势。而在这一趋势背后,主要反映的是各方对仲裁效率这一价值取向的追求。当然,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对公正的坚持仍是仲裁发展的必然要求,更应是机构管理权扩张的基本遵循。
(一)机构管理权扩张是仲裁发展的趋势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逐步规则化的过程,人的社会生活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渐成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发展成更为抽象且具有一般性的陈述。①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4页。而仲裁作为根植于市民社会并以意思自治为前提的社会化争议解决方式,其自身发展历程也体现了逐步规则化的过程。仲裁产生之初,争议多是通过当事人选择共同信任之人依公允善良之原则等方式加以解决。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集中化组织形式的社会形成,人们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意愿越发强烈。因此,以仲裁为代表的社会化争议解决方式也肩负起对社会秩序维护的责任。②See Simon Roberts, Order and Dispute: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Anthropology (2nd ed.), New York : Quid Pro LLC, 2013, pp.1-3.在社会秩序逐步建构的大背景下,仲裁也通过机构化和规则化实现了对争议的有序解决,而在这其中仲裁机构发挥着案件管理、规则制定等多重功能。可以认为,机构管理权的产生与扩张,本质上是秩序建构与维护背景下仲裁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从机构管理权扩张的路径看,通过强制条款的制定和适用来疏导当事人意思自治已成趋势,这一点从ICC等机构在快速仲裁程序的发展历程中便可有所窥见。
ICC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仲裁机构,其始终在引领国际仲裁行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21世纪初,ICC便开始关注快速仲裁程序,ICC秘书处曾于2002年针对1998年版ICC仲裁规则第32条作出说明,强调了当事人拥有基于规则缩短仲裁时限的权利。③13(1) ICC ICArb. Bull. 29 (2002).该文件主要是对仲裁规则中当事人权利的阐释,强调在提高仲裁效率方面仍然要依靠当事人的选择。然而,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之间想要达成合意本身便具有难度,仅通过当事人合意来提高仲裁效率并不现实。因此,面对各方对仲裁效率提高的渴求,ICC于2007年再次发布报告,呼吁仲裁参与各方在仲裁庭组成等方面通过多种方式来控制仲裁的时间及花费。①See ICC Commission on Arbitration, Techniques for Controlling Time and Costs in Arbitration, ICC Publication No. 843 (2007).尽管该份报告仍强调当事人选择对仲裁效率提高的重要性,但其已然开始关注仲裁员及仲裁机构在该问题上的作用。而在2012年版ICC仲裁规则的制定中,其以增加案件推进力度(第22条)、强化案件管理会议(第24条)等方式提高仲裁效率,并通过出台相关指引来引导当事人。②See ICC Commission,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Arbitration :A Guide for In-House Counsel and Other Party Representatives, ICC Publication No. 866 (2014).该规则尽管已显现出在提高仲裁效率上需要仲裁机构通过规则修订作出努力这一基本认识,但仍强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并力图通过对当事人的有效引导提高效率。而在该规则颁布后,国际仲裁界对仲裁效率的渴求依旧强烈,相关数据也显示出通过增设强制条款来推进仲裁程序以提高效率的意愿。③在2015年《QMUL报告》中有94%的受访者希望通过仲裁规则的修订引入快速程序以提高仲裁效率,其中59%的人认为这种规则修订是为当事人提供一种选项,在当事人选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但同时也有33%受访者认为应当以强制条款的方式推进快速程序。参见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White & Case, 2015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Improvements and Innovatio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26。面对这一现实,2017年ICC正式将快速程序引入仲裁规则,并通过强制条款的方式加以适用。这种对快速程序的直接引入,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仲裁效率。但其同时也对仲裁的运作提出了挑战,尤其会引发仲裁败诉方基于正当程序而提出质疑从而可能影响裁决的执行。④See Michael W. Bühler, Pierre R. Heitzmann, “The 2017 ICC Expedited Rules: From Softball to Hardball ? ”, 3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21, 145-148(2017).与ICC相比,SIAC在快速程序的运用上更为直接。其早在2010年版仲裁规则中便将快速程序引入,并且在2013年仍旧坚持这一规定。然而,在面对AQZ v. ARA⑤AQZ v. ARA[2015] SGHC 49.案中暴露出仲裁协议与快速程序之间冲突的问题时,尽管新加坡法院支持了快速程序的优先适用,但这仅是就个案作出的决定。因此,SIAC在2016年版仲裁规则中不得不进一步明确快速程序条款一经选择便强制适用的立场。
因此,从快速仲裁程序的产生与发展看,其在适用上经历了从间接影响到直接引入、从选择适用到强制适用的过程,这反映的是在提升仲裁效率的要求下机构管理权的不断扩张。而这背后更暗合了在法秩序建构下,仲裁机构主导争议解决并推动其有序化发展的趋势。
(二)效率是机构管理权扩张的现实需求
如前所述,快速程序条款的强制适用反映了仲裁机构管理权的不断扩张,而这种扩张背后体现了在效率与公正两大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国际仲裁机构以效率为先的倾向。可以说仲裁机构管理权扩张是对提高仲裁效率这一呼声的回应,其既是仲裁自身发展的“内需”,也是来自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发展的“外迫”。
从仲裁自身发展看,作为服务于商业的争议解决机制,仲裁在价值取向上也体现了商人对利益的追求。一方面,仲裁强调程序效率。其以一裁终局的方式避免了繁琐的诉讼程序,在实现争议有效解决的前提下能够保证商事交易的连续性和利益产生的稳定性,从而实现对商业关系的维护。⑥参见刘晓红:《仲裁“一裁终局”制度之困境及本位回归》,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另一方面,仲裁也强调规则效率。仲裁裁决和“先例”既通过影响争议双方及潜在争议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来实现最优化的制度安排,也会影响仲裁员作出能够得到当事人认可和法院承认的裁决。⑦参见晏玲菊:《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97-198页。尽管仲裁从诞生之初便强调对效率的追求,但近年来仲裁效率的提高却不尽人意,其原因主要在于仲裁程序在灵活性特征下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所引发的负面效应。第一,随着现代商事交易的不断发展,仲裁因多方主体的参与和专业律师的介入而日趋复杂,越来越多的诉讼程序被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引入仲裁当中。这种仲裁的诉讼化倾向,使得效率这一仲裁区别于诉讼的重要特征被逐渐消弭。①参见丛雪莲、罗楚湘:《仲裁诉讼化若干问题探讨》,《法学评论》2007年第6期。第二,一裁终局的方式一方面的确是提高效率的制度设计,但其也增大了争议解决败诉的风险。而多数的仲裁程序并不像诉讼一样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其往往是依靠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确定争议解决的时限。②See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2nd ed.) ,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6,pp.13-14.因此,为降低一裁终局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为赢得时间会选择以各种方式拖延程序,可以说仲裁效率的低下与当事人的刻意拖延有着很大关系。第三,因为日趋诉讼化的仲裁规则赋予了当事人诸多程序性权利,而当事人也会据此提出诸多不必要的程序性要求来拖延。若仲裁员基于仲裁效率而拒绝,则极有可能招致败诉方以违反正当程序的理由请求法院予以矫正。因此,以维护正当程序为要旨的司法监督便也成为了悬在仲裁员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为了裁决的有效执行,仲裁员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③See Klaus Peter Berger ; J. Ole Jensen, Due process paranoia and the procedural judgment rule: a safe harbor for procedural management decisions by international arbitrators, 32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415, 421-429(2016).所以,在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想要快速解决争议的同时,也恰因意思自治使得仲裁规则越发复杂、程序性权利花样百出,从而成为拖延仲裁的原因。因此,想要提升仲裁效率就需要平衡意思自治在仲裁中的作用,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便需要仲裁机构通过强化其管理权加以实现,这也是提高仲裁效率的“内需”所在。
从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看,首先,国际商事仲裁依托《纽约公约》所构筑的仲裁裁决全球执行体系是目前多数人选择仲裁的原因。④根据2018年《QMUL报告》显示,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是多数人(64%)选择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首要因素。参见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White & Case, 201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7.然而,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民商事新秩序的不断形成,民商事判决和调解文书的跨国执行性日渐提高。一方面,随着国际法制与国内法制的双向互动和融合,诸多国家基于互惠认可他国商事判决或调解文书的倾向已越发明朗。⑤参见徐伟功:《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的构建路径——兼论我国认定互惠关系态度的转变》,《法商研究》2018年第2期。另一方面,随着《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生效以及《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公约(草案)》的逐步形成,仲裁之于诉讼和调解的执行便利优势正在弱化。其次,近年来多元化争议解决的融合式发展使得诉讼和调解也在不断地借鉴仲裁的长处。例如在私密性上,诉讼和调解也越发重视商事主体对商业秘密的关切,强调通过制度设计协调私密性和争议解决透明度的关系。⑥See Susan Oberman, “Conf i dentiality in Media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Right to Privacy,” 27 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 539, 540-589 (2012).因此,在面对诉讼和调解不断发展的“外迫”下,仲裁想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找寻新的突破口。而从多方的意见看,提高仲裁效率是仲裁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通过扩张仲裁机构管理权来实现仲裁效率的提高也是仲裁继续发展的现实需求。
(三)公正是机构管理权扩张的基本遵循
任何争议解决方式中都存在着法律的两大基本价值——公正与效率的矛盾与冲突,仲裁也不例外。①参见刘晓红:《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理与实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38页。然而,仲裁制度理性构建的初衷是公平和效率兼顾,当不能两全其美时,追求仲裁的公正必须是摆在第一位的,而追求仲裁的效率则是相对的。否则,仲裁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作为现代法治的核心观念,公正已然成为法律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而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通常当事人同意仲裁并非是因为仲裁是最优选择,而是因为它是当事人能够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解决争议中其不利因素最少的选择。②参见[美]加里·B·博恩:《国际仲裁法律与实践》,白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4页。仲裁长久以来更是将公正作为最基本的运作准绳和价值追求。因此,在仲裁机构通过扩张管理权提高仲裁效率的同时,对仲裁公正的坚持与维护仍是仲裁发展的基本遵循。从仲裁内部看,对仲裁公正的保证既是仲裁参与者的普遍愿望,也是仲裁机构行使管理权的底线。通观仲裁的发展,无论是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员始终重视对公正的坚持,仲裁机构总是试图通过完善的规则设计,实现对普遍公正的维护。同时其也通过对友好仲裁等制度的保留为个案公正的实现打开通道,从而兼顾普遍公正与个案公正。另外,仲裁机构也通过内部监督、行业自律等方式防止仲裁员在具体案件中行为越轨,以保证仲裁的公正性。而聚焦仲裁机构管理权扩张问题,在快速程序的适用上,诸多仲裁机构也基于公正认识到扩张管理权不能忽视对仲裁公正的维护。例如SCC在引入快速程序的过程中,决策者从一开始便强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仲裁协议的尊重,尽量避免规则与协议之间产生冲突而影响仲裁公正。③安妮特·麦格纳森(Annette Magnusson)女士作为时任SCC副秘书长曾在200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仲裁研讨会上明确表示了SCC在推动仲裁效率提高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和重视。参见 Annette Magnusson, Fast Track Arbitration-The SCC Experience, http://sccinstitute.com/media/56055/fast_track_arbitration.pdf, visited on June 14, 2018。所以,从仲裁的自身看,无论是宏观上的制度设计还是微观上的具体操作,保证仲裁公正一直是仲裁所坚持的,而这当然也是仲裁机构管理权扩张的基本遵循。
从外部看,仲裁公正是司法监督的重点。因为仲裁的程序尤其是仲裁结果,既关乎当事人利益也维系着社会公正,司法需要对仲裁实施必要的审查和控制。④参见赵健:《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而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往往通过撤销、承认与执行两个程序实现。纵观《纽约公约》和《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等文本可以发现,其在前述两个程序上的规定都渗透着对仲裁公正的维护。换言之,要是仲裁裁决失去应有的公正性,对其进行撤销或拒绝承认与执行是法院应尽的义务。因此,快速程序强制条款与仲裁协议的冲突之所以引发多方担忧,是因为其极易被各国法院所否定。而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冲突,也极有可能触动了各国司法监督的底线即对意思自治的维护。因为仲裁公正包含了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而这种保护也往往通过意思自治所体现,因此机构管理权的扩张应当坚持对意思自治的尊重,否则便可能侵蚀当事人利益从而影响公正。所以,无论是仲裁的自身发展还是司法监督,对公正的追求贯穿了仲裁的始终。机构管理权扩张反映了对仲裁效率的追求,而效率与公正的二元对立却也一直是仲裁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在管理权扩张的道路上,仲裁机构不能也不应忽视对仲裁公正的维护,否则便可能彻底摧毁仲裁制度的立命之基。
三、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源流与价值
在解决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冲突上,除了厘清机构管理权扩张的原因及方向外,更要认清意思自治这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基石的源流与价值。这既需要对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生成路径加以检视,也需要正确认识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新发展。
(一)仲裁意思自治的生成路径
仲裁制度的发展本质上来自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后前者对后者的妥协,①参见郭树理:《民商事仲裁制度: 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之妥协》,《学术界》2000年第6期。而也就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中,意思自治逐渐形成并成为了仲裁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首先,欧洲中世纪社会等级差异明显,而这种等级是横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因为此时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有机原则。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5-335页。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逐渐分离,社会等级被打破从而实现了人的独立。人们开始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与他人签订契约,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整体利益。③参见刘旺洪:《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身份的独立推动人的觉醒,人在自我觉醒的情况下产生自我意志,人的意志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源渊而且是其发生根据,④参见尹田:《论意思自治原则》,《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3期。由此令意思自治渐成市民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其次,在私有财产扩充与个人主义张扬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基于对利益的追求令多元利益冲突的格局逐渐形成。基于意思自治,以仲裁为代表的民间纠纷解决方式应运而生。这既是国家司法权向社会的“归还”与“下落”,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方社会法治产生的深层原因。⑤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7页。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妥协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而是面对历史趋势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一方面,市民社会的底层逻辑是意思自治,政治国家想要排除意思自治解决争议既缺乏正当性也无力面对如此多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使得人在获取自由并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趋于理性,而基于意思自治的争议解决起于个人意志也遵从于个人意志,无需国家权力的介入便可实现有效的自我执行令成本收益最大化。因此,以仲裁为代表的社会化争议解决方式的产生,既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意思自治的逻辑延伸。也正是在意思自治这一市民社会最高主义的旗帜下,仲裁获得了区别于诉讼制度的基石,拥有了向诉讼夺权与竞争的一套说辞。
最后,仲裁在通过意思自治实现独立后,如何保证争议的长效解决则需要法秩序的保障。因为意思自治尽管是根据个人意思自由形成的法律关系,但在没有得到法律秩序承认之前,私主体行为的这种自由只不过是个人自主性的体现,而其只有在法律秩序存在后才能转变为私法自治。⑥参见李军:《私法自治的基本内涵》,《法学论坛》2004年第6期。其实,在市民社会形成的初期,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仲裁制度处在一种绝对自治的状态。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政治国家基于法秩序的统一开始对仲裁进行全方位干预,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纷纷确立“法院管辖权不容剥夺”等原则,力图限制包括仲裁在内的无限度的意思自治对法秩序的突破。直至资产阶级夺权后,这种对仲裁的压制才得以缓和。从表面上看,仲裁的解放应归功于资产阶级的胜利,但当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后,其仍要强调对法秩序的建构与维护。因此,在深层次上,随着法治的成熟与完善,意思自治也逐渐被法秩序所规劝,那些原始且凌乱的意思表示被逐渐体系化,并在时代的拉扯中并入了国家法秩序当中。从而令自由与秩序两大价值相互融合,让我们在获得自由价值的同时必然也相应地获得秩序价值。①参见龙文懋:《“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冲突”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所以,纵观西方仲裁制度从政治国家绝对不干预到绝对干预再到有限干预的路径,其背后除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与妥协外,意思自治与法秩序的对立与融合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给了意思自治滋生的空间并使其成为市民社会的底层逻辑。而面对市民社会日趋复杂的利益冲突,以仲裁为代表的社会化争议解决方式被意思自治所孕育并依靠意思自治与诉讼形成竞争。但肆意的意思自治并非是法治国家所需要的,也就是在代表国家意志的法秩序面前意思自治被逐渐规劝,从而形成了蕴含着秩序的意思自治和洋溢着意思自治的现代法秩序。
(二)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价值本位
仲裁意思自治的生成路径为我们揭示了仲裁产生与发展的深层逻辑,从中也让我们看到了意思自治之于仲裁的价值所在,而这些价值也同样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得以继承。笔者认为,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价值本位有以下两点。
1.意思自治是仲裁区别于诉讼的界限
纵观仲裁意思自治的生成路径,其首要价值在于将仲裁与诉讼进行分离,并划定了各自的疆界。首先,在管辖权上,基于意思自治的仲裁协议是仲裁获取管辖权并排除法院管辖的依据。一方面,仲裁庭因仲裁协议获取管辖权是基于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意思自治作为市民社会的底层逻辑,其在强调私主体依据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的同时,更强调选择后的义务自主与责任自负。所以,当事人有权利通过仲裁解决争议也有义务履行仲裁裁决。另一方面,仲裁协议排除了法院管辖是政治国家对意思自治应有的尊重。《纽约公约》第2条规定存在仲裁协议的前提下仲裁具有优先管辖的地位,但这种优位并不来自仲裁庭而是来自法院的礼让,因为最终仲裁是否具有管辖权仍然由法院决定。例如一方当事人对仲裁管辖权提出质疑时,之所以自裁管辖权原则被普遍遵守,是因为法院基于对意思自治的尊重所作出的礼让。而这种礼让并不否定法院具有最终决定权,因为无论是从维护国家法秩序的角度,还是保证裁决可执行性上法院都具备这一职能,这也是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必需。②参见刘晓红:《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理与实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3-105页。
其次,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监督仍以意思自治为标准。法院基于对意思自治的尊重所作出的礼让赋予了仲裁庭解决争议的权力,而当这种礼让成为常态后便被固定为国家法并以国家授权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仲裁庭的权力既来自当事人意思自治下的授权,也来自政治国家尊重意思自治的法律授权。③参见汪祖兴:《仲裁监督之逻辑生成与逻辑体系——仲裁与诉讼关系之优化为基点的渐进展开》,《当代法学》2015年第6期。仲裁需要司法加以适当监督,而司法监督的界限为何则是需要明确的。在规范上,《纽约公约》与《示范法》均将保证意思自治作为司法监督的重要抓手。例如在裁决撤销上,《示范法》第34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有效性关乎意思自治是否存在、仲裁超裁关乎意思自治的授权范围、仲裁程序与约定一致性关乎对意思自治的遵守。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上,《纽约公约》第5条和《示范法》第36条的规定均与前述撤销事由基本一致。而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司法应抱着“违法必究”的态度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与程序的全面监督;另有学者则认为将司法对实体争议进行监督无异于将仲裁变为诉讼的附属并影响效率,因此司法监督应限于程序。④参见陈安:《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评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肖永平:《内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之我见——对〈中国涉外仲裁监督机制评析〉一文的商榷》,《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以上两种观点看似对立,但实际上主张全面监督者也认可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排除法院监督的权利;而主张程序监督者也认为如果当事人同意,法院进行实体监督也无可厚非。因此,以意思自治为标准划定司法对仲裁监督的范围,是平衡司法监督与仲裁自治的最佳选择。①参见万鄂湘、于喜富:《再论司法与仲裁的关系——关于法院应否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立法与实践模式及理论思考》,《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2.意思自治推动仲裁融入多元法秩序
如前所述,仲裁意思自治的生成离不开对法秩序的保障,而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中也依旧强调意思自治对法秩序的维护。这其中既有对一国法秩序的维护,也有对多国法秩序的维护,更有对国际民商事秩序的维护。
首先,仲裁中的意思自治寓于一国法秩序当中。诉讼作为维护国家法秩序的争议解决方式,其具有“解决争议—维护统一法秩序—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合法性”3个渐进的功能。②参见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4页。但仲裁缺乏对后两者关照的可能,故需要法院在对仲裁协助时为其赋予相关功能。而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其需要对仲裁地法秩序进行维护。国际商事仲裁尽管处理跨国争议,看似并不属于任何一国,但实质上无论是仲裁庭的组成还是仲裁程序的推进都与特定的法律体系相联系。③See Mauro Rubino-Sammartan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3rd ed),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Inc., 2003, p.9.所以,仲裁当然要遵从仲裁地法秩序,仲裁意思自治也应维护仲裁地法秩序,否则其将面临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风险。
其次,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意思自治寓于多国法秩序当中。随着仲裁日渐成为解决跨国争议的主要方式,其也需要在维护一国法秩序的同时兼顾多国法秩序。仲裁裁决的全球可执行性离不开被请求承认和执行裁决国支持,这就需要仲裁裁决符合相关国家公共政策以融入多国法秩序。而随着跨国民商事活动日趋复杂,一份裁决的执行有时需要多国予以协助,从而也要求仲裁裁决必须兼顾多国法秩序并加以遵照。所幸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越发看到国际合作的利益所在,并基于国际礼让原则逐步对公共政策进行自我限制。④参见何其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但笔者认为,公共政策的范围界定权仍在各国手中,各国的自我限制并不意味着仲裁可以凭借意思自治肆意妄为。因此,仲裁要牢记对各国法秩序的遵从,意思自治更要强调对各国法秩序的维护,只有如履薄冰才能如鱼得水。
最后,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意思自治推动构建和维护国际民商新秩序的形成。传统民商秩序是建立在强化主权思想上无序、封闭且僵化的一种不公平秩序。⑤参见李双元、郑远民、吕国民:《关于建立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法律思考——国际私法基本功能的深层考察》,《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而国际民商新秩序更关注人本身,所以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以构筑超越国别与种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整个民商事新秩序的构建上,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便要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因此这一秩序的构建本质上是在私主体推动下市民社会的跨域融合,是作为市民社会底层逻辑的意思自治去国别性而求国际性的过程。从国际商事仲裁自身来看,长久以来的发展使得国际商事仲裁已然形成了跨国别的仲裁法律秩序,而其也在发展中得到了国家法律秩序的接受并与之融合。⑥参见[法]伊曼纽尔·盖拉德:《国际仲裁的法理思考和实践指导》,黄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8页。这种接受与融合无不是基于对意思自治的尊重和发展,实际上是从过去单个政治国家的礼让转变成了整个国际社会的礼让。
(三)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内涵扩展
在明确了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价值本位后,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意思自治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本位价值上内涵的扩展。
1.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国际化”扩展
伴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仲裁的国际化日渐提高,而寓于其中的意思自治也深受国际化的影响。首先,国际化使得仲裁意思自治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要面临更复杂的情况,内涵趋于开放。当仲裁解决跨国争议时,由于当事人来自不同法域或争议标的具有国际性,使得在仲裁中当事人不仅有权决定受哪国法律的约束,也有权决定不受哪国法律的约束;当事人有权决定是依照国家法提供的制度规则保障或实现自己的权利,还是依照自己的或者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习惯和规则保障或实践自己的权利。①林一:《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原则论纲》,华东政法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7页。此时,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从某一法域变成多个法域,其选择空间得以扩大。但选择空间扩大的同时当事人所要面临的选项也更为复杂,因为在同一法域,无论是法律概念的内涵还是法律关系的判定等都是一致的。但随着争议的跨国,使得某些相同的法律概念产生了不同的内涵,同一法律关系也可能被划入不同部门法中,从而令意思自治在行使的过程中面临更多障碍,故需要意思自治的内涵更加开放。
其次,仲裁的国际性使得司法监督需要将国际仲裁与国内仲裁相区别,并对国际商事仲裁采取更为礼让和包容的态度。现代国际仲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国际仲裁与国内仲裁作出区分。特别是商事仲裁,要求适用不同于解决国内争议的仲裁规则,国际仲裁规则应比国内仲裁规则更加自由。②参见[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7页。一方面,国际仲裁远没有国内仲裁与本国法秩序的联系紧密,因而国际商事仲裁的意思自治突破本国法秩序的影响也不及国内仲裁。所以,采取更为包容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代表了一国对仲裁的基本态度,对国际仲裁过多地干预极可能会被认为干涉仲裁自治,从而影响该国国际声誉且不利于打造面向国际的营商环境。故在对国际商事仲裁进行司法监督时,采用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最低干预是一国较为明智的选择。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便开始将国际仲裁与国内仲裁分而治之,以更少的干预和更多的协助来展现对国际仲裁的支持。③See Guido Carducci, “The Arbitration Reform in Franc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28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125, 147-157(2012).而1985年制定的《示范法》更是倡导限制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干预,这一理念被1994年新加坡《国际仲裁法》所吸收,从而推动了新加坡在国际仲裁业的迅速崛起。④See Mohan R. Pillay, The Singapore Arbitration Regime and the UNCITRAL Model Law, 20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355, 370-386(2004).
2.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商事化”扩展
在市民社会发展之初,民商事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仲裁在处理私人争议时也少有民、商之分。但随着交易的复杂,民事与商事的差异也日趋凸显。相较于民事活动,仲裁的低成本、高效率更加符合商事活动的特征,仲裁的商事化也令仲裁意思自治从过去的民商混合开始产生商事倾向。商法与民法在法理基础上便具有差异性,一方面,在法律行为成立与否的判断上,尽管两者都强调意思自治但商法更关注于法律行为的外观及形式,而民法则强调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在意思自治的适用上,商法侧重于考虑交易的效率及安全,更多顾及行业习惯和交易惯例,而民法却强调如何通过意思自治保证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公平。①参见宋晓:《国际私法与民法典的分与合》,《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
首先,商事化令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逐步类型化。从商业角度看,生产要素的全球分布使得现代商业交易日趋复杂,往往在同一交易中会涉及多方主体并联通多个法域。而交易中的意思自治也逐步从双方合意变为了多方合意,从而增加了合意形成的难度。因此,为保证交易的顺利,大量的国际商事惯例得以形成。例如在国际贸易上,自1936年起国际商会便开始制定统一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供交易方进行选择,使得意思自治趋于类型化。而从国际商事仲裁看,效率始终被认为是现代商事仲裁的重要价值取向,从而也影响了意思自治的发展。如前所述,仲裁经历了逐步规则化,而仲裁规则本质上便是对意思自治的类型化。当事人可以通过意思自治选择现有规则,从而免去了自己设计规则的低效。也因此,使得新加坡法院在AQZ v.ARA案中选择站在商业效率的立场上指出选择后的仲裁规则也是意思自治的体现。
其次,商事化要求司法监督着重把握意思自治的外观与形式。如前所述,在私法领域尊重和实现意思自治便是保证公正的有效方式,而当事人在仲裁中的意思自治可以归纳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选择自由。在实体上,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准据法在各国国际私法及众多国际公约中得到了普遍认可。②参见许军珂:《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因此,当仲裁协议明确选择了某一准据法,除所选法律有违反仲裁地强行法等情况外,即使仲裁庭认为选择其他法更为合适也应遵循双方的选择。而在司法监督中,法院基于对仲裁的支持,也仅需对仲裁适用法与协议选择法进行形式上的比对即可,即使法院认为实体出现问题也不能轻易撤销或拒绝承认执行。③参见宋连斌:《论中国仲裁监督机制及其完善》,《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在程序上,正当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所必需,而在仲裁中正当程序也与意思自治产生了关联。因为仲裁庭的权力来自意思自治的授予,这一来自当事方的权力理应保障当事方的程序性权利,从而实现正当程序。而从商事角度出发,保证程序公正应达到形式上的相关标准而无需锱铢必较而消耗效率。因此,在面对一方当事人以意思自治之名行拖延程序之实时,仲裁员应当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敢于驳回某些无理请求。法院也应以形式上的程序公正作为审查标准,不必过分追究某些程序性要求的本意为何。
四、国际商事仲裁中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协调
通过前述对仲裁机构管理权和意思自治的分别考察,笔者试图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基于对仲裁效率的追求,机构管理权扩张已成趋势,而在扩张的过程中保证仲裁公正仍是基本遵循。其二,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具有区别诉讼与仲裁并推动仲裁融入多元法秩序的本位价值。同时在发展中“国际化”推动意思自治内涵更开放,理解更包容;“商事化”推动意思自治趋于类型化并强调对外观和形式的把握。因此,在协调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过程中,不同主体应当依据上述结论进行操作,这也体现在快速仲裁程序中强制条款的适用上。
(一)当事人应正确认识意思自治并慎重选择
仲裁作为一种社会化争议解决方式,其始于当事人的自我选择,终于当事人的自我约束。可以说,仲裁机制的运作主要是围绕当事人展开的。因此,在协调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关系上,当事人有着重要地位。
首先,当事人应正确认识意思自治,具备应有的国际视野和商业思维。一方面,当事人应认识到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意思自治除了赋予当事人自由行使争议解决的权利外,其仍强调义务自主与责任自负。所以,在确定争议解决方式上,当事人应当基于自身情况、交易目的和利益诉求等多方因素,在仲裁与诉讼、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仲裁地等多方面进行慎重选择。因为合意达成便成法锁,当事人就应承担该选择背后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当事人一旦选择通过国际商事仲裁解决争议,便要把握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国际化和商事化要求。要在运用意思自治时具备国际视野,以更为开放的视角看待交易相对方在法律概念、交易习惯上的差异,求同存异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当事人也要看到国际商事仲裁服务于商业的功能,要以商业的思维理解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类型化,从而提高争议解决的效率。
其次,当事人应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尊重机构管理权,正确把握其与仲裁机构及仲裁员的关系。机构管理权的扩张是基于对仲裁效率的追求,而这一追求本质上也是来自当事人希望减少成本提高效率的愿望。一旦当事人选择将争议交由某机构管理,则代表着其承认了相关机构的管理权,因此应当从态度上加以尊重,这本身也是尊重自己和对方意思自治的表现。另外,当事人也应认清其与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关系。一方面,当事人选择将争议交由某机构进行仲裁,实际上机构及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而该合同当中包括了当事人仲裁协议与相应的仲裁规则,所以仲裁规则并非是被排除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外的。①See Kinga Timár,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e Arbitral Institution, 2013 ELTE Law Journal 103, 121-122(2013).另一方面,机构及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除了以提供仲裁服务为标的的合同法律关系外,还具有以作出仲裁裁决为标的、以法律规定为准绳的身份法律关系。②参见范铭超:《仲裁员与仲裁当事人法律关系模型的困境及其解决》,《北方法学》2014年第6期。因此,在仲裁程序推进的过程中,仲裁员和机构除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外,还应兼顾蕴含于法律、仲裁规则甚至商业惯例当中的其他因素。如果当事人基于意思自治而令仲裁程序扭曲并脱离了法律规定下其应然的走向,仲裁机构与仲裁员当然有权予以纠正并使其沿着正轨解决争议。基此,针对当事人,其应正确理解仲裁意思自治的内涵,看清意思自治的价值本位与内涵扩展,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慎重选择。而选择之后,无论是从意思自治的内涵出发还是从当事人与机构或仲裁员的关系入手,当事人都应尊重机构管理权与仲裁规则,履行合同及法律义务,实现争议的有效化解。
(二)仲裁机构与仲裁员应完善规则的设计与运用
无论是快速程序强制条款的适用还是机构管理权的扩张,其都与仲裁机构的规则设计和仲裁员的规则运用密不可分。因此,在协调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问题上,仲裁机构理应通过完善规则来避免冲突,仲裁员也应通过适当的规则运用来化解矛盾。
首先,仲裁机构应通过妥善的规则设计来避免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冲突。2017年我国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SIAC 2015年005号仲裁裁决案引发各方关注,而从分析来看该案之所以被拒绝,本质上并非是由于快速程序不被接受,而是因为2013年SIAC仲裁规则在快速程序的规定上存在漏洞。因为2013年《SIAC仲裁规则》规定“案件应当由独任仲裁员审理,但主席另有决定除外”其并没有排除快速程序中适用其他仲裁庭组成方式。而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仲裁制度运作的基石理应被尊重,主席在作出决定时应当根据当事人合意决定以3人仲裁的方式进行。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沪01协外认1号。因此,这一表态传递出我国法院并不反对机构管理权扩张且支持快速程序的适用,但在机构管理权扩张的同时也应明确其界限所在,而这一界限便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因为这既是《纽约公约》的规定,也事关仲裁的公正性。①See Mohamad Salahudine Abdel Wahab, Expedited Institutional Arbitral Proceedings Between Autonomy and Regulation, in Expedited Procedur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42-151(ICC ed., 2017).所以,在明确当事人选择的规则可以被涵摄进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的前提下,仲裁机构应通过妥善的规则设计引导当事人作出正确的选择并释明选择的后果,在规则设计之时尽量避开可能的冲突,从而防止侵蚀意思自治以影响仲裁公正。
其次,仲裁员推进仲裁程序应把握规则精神并协调当事人合意,从而兼顾效率与公正。仲裁员作为仲裁程序的具体推动者,其肩负着推进仲裁并解决争议的职责,更掌握着解释和运用仲裁规则及相关法律的权力。因此,其是解决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冲突的主要责任人。在快速程序强制条款的适用上,一方面,仲裁员应当理解该条款背后所反映的机构管理权扩张本质上体现的是对仲裁效率的追求。因此,在程序的推进和规则的解释上仲裁员不能仅因机构管理权扩张而任意地行使仲裁权,而应以追求效率作为规范解释的目标。另一方面,仲裁的首要功能仍在于解决争议,其要求仲裁员能够在明晰当事人诉求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并促成双方达成合意以解决争议。如前所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保证仲裁公正的重要标准。因此,在诸如快速程序的推进上如果仲裁规则出现漏洞,仲裁员便应当通过向当事人适当的释明和合理的引导促成双方形成明确的合意,以避免对意思自治的突破。
所以,针对仲裁机构,其应通过妥善的规则设计避免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冲突。而针对仲裁员,其也应当明确机构管理权扩张背景下的规则设计本质上是在追求仲裁效率,而这一价值目标也应成为其解释规则的依据。同时,在面对规则漏洞时仲裁员也要充分履行职权促进当事人形成合意,实现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对规则的正确适用,从而维护仲裁公正。
(三)司法监督应认识到意思自治的价值本位和内涵扩展
首先,价值本位要求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意思自治只要不突破国家法秩序,司法监督就应尽量保持克制。笔者认为,意思自治并非是司法监督的工具而是维护仲裁自治的盾牌。其一,意思自治是仲裁区别于诉讼的界限,其要求国家司法权对仲裁持有礼让和尊重的态度。其二,意思自治也并非偏执地保护仲裁自治,其同样要求仲裁自治应归顺于国家法秩序。因此,从意思自治的价值本位出发,司法监督应因意思自治而保持克制,最大限度地尊重和听取仲裁庭在个案中的意见,去试图理解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处理方式,从而实现仲裁自治。
其次,内涵扩展要求对意思自治的理解更加开放,对类型化的意思自治理应认可,对意思自治的审查要侧重外观。笔者认为,其一,国际化令意思自治内涵进一步扩充,对其的理解应当尽量开放。在不同法系背景下,当事人对意思自治有着不同的理解,而这种不同的理解本质上并没有正误优劣之分,至少法院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试图理解各种观点。同时,国际化也要求法院对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进行区别对待,针对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具体问题更应当采取包容的态度去尽量尊重仲裁庭的观点。其二,商事化让我们看到了意思自治类型化的优势,而仲裁规则本质上也是意思自治类型化的表现。其作为选项被当事人选中以后便归入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范畴,所以其与仲裁协议一样代表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商事化还强调司法监督尽量限于意思自治的外观,故在司法监督中法院应侧重于形式和程序审查,而减少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干预。
因此,在仲裁快速程序的适用上,理论上在当事人选择适用该程序时,仲裁规则的相关条款也构成了当事人的合意,体现了意思自治。仲裁庭以此推进仲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本质上并不存在快速程序侵蚀意思自治的情况。目前规则的修改,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而做出的明示,是在尊重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对当事人作进一步的提醒和引导。其所呈现给法院的意思自治外观是当事人选择快速程序解决争议,并愿意接受快速程序对协议中相反内容的否定,这是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后通过意思自治的否定。根据这一外观,法院应当予以认可而不必探究当事人是否是出于本意而放弃仲裁协议中的意思表示。
五、结 语
综上,本文以快速仲裁程序条款趋于强制化为切入点,点明了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机构通过修改仲裁规则等方式扩张管理权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出现本质上体现了对仲裁效率的追求。然而,机构管理权的扩张并非是任意的,其仍然要以保障仲裁公正为基本遵循。具言之,仲裁公正强调对当事人利益的维护,而维护当事人利益则离不开对意思自治的尊重。因此,仲裁机构管理权扩张应当尊重意思自治,通过完善的规则设计与灵活的实践操作来避免可能的冲突。
而在明确机构管理权扩张理应关照意思自治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对国际商事仲裁中意思自治的理解应着重关注以下几点。其一,意思自治既强调当事人之间私法自治,也强调仲裁机构自治与仲裁庭自治。尽管机构自治与仲裁庭自治是来自并服务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但法院在司法监督时不能仅仅关注当事人而忽略机构和仲裁庭自治。①参见董连和:《论我国仲裁制度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因此,在具体案件上要尽量相信仲裁机构与仲裁庭的公正与专业,避免想要通过司法监督矫正仲裁的思维惯性,从而给予仲裁机构与仲裁庭自治空间。其二,对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的理解要尽量开放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注人并发展人的理念,而不同环境下人的思维与行为千差万别。要试图去理解,并在理解中去包容,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其三,对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的理解要坚持商事思维,国际商事仲裁是处理商事主体之间争议的,其前提便是默认参与者都是成熟的商事主体,其通晓商业规则并具有商业思维。即使某些商事主体因不成熟而产生利益损失,这种损失也并不需要法院本着法律家长主义来加以救济,因为责任自负也是意思自治的内涵所在。总之,面对国际商事仲裁中机构管理权与意思自治的冲突,我们需要凝聚各方智慧并汇集多方力量。要树立正确的理论认识,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运用可行的操作方式。从而实现两者的协调,推动仲裁事业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