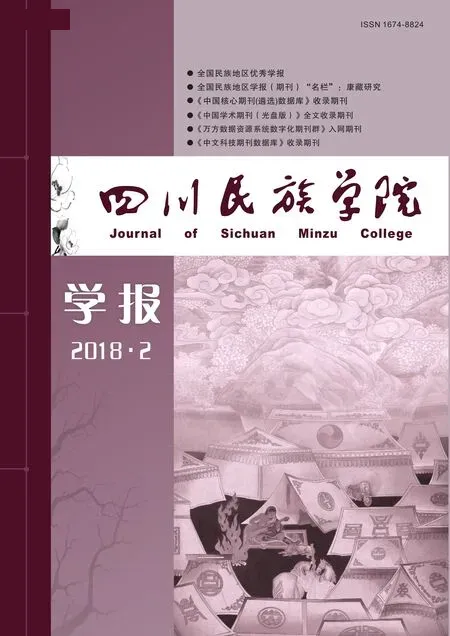关于“康藏纠纷”称谓问题的几点思考
南俊昂杰
一、三次“康藏纠纷”简述
20世纪前期,川军和藏军在川西康巴境内发生三次武装冲突,历史上将其共同列入“康藏纠纷”这一争端中。 第一次“康藏纠纷”发生在民国建立初年,在四川保路运动和拉萨“驱汉事件”*1912年在拉萨发生的驱逐驻藏大臣及入藏川军的事件。的影响下,自1912年2月开始,康区乡城,昌都,波密,理塘等县纷纷开始同驻康汉军发生冲突,复辟土司占领西部各县。 5月9日北洋政府电令川督尹昌衡等人前往川边镇压,在尹昌衡为主的川军的进攻下,到9月3日道孚、昌都、理塘等诸要地又重新被川军占领。当尹昌衡被授予“川西镇边史”后,大力开始整顿康区事物,其中包括重设康区各县的县知事,更署地名[1]*记载“将硕般多改为硕督府,拉里改为嘉黎府,江达定名为太昭府,分别派遣知事前往就职”。,划定川藏疆界等。其做法大体沿用了赵尔丰*赵尔丰(1845-1911)1905年起开始处理川藏地区事务,先后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驻藏大臣等职,在川康一带以武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以夏变夷”措施。此类做法遭到乍丫、江卡、盐井等康区民众的反抗,在1913年底他们连同西藏军队向川军发动进攻,经多次较量,川,藏两军最终在瓦合山、澜沧江一线形成了对峙。不久为解决汉藏边界问题,英藏汉三方在印度召开了西姆拉会议。
第二次“康藏纠纷”始于1917年7月,当时“边军彭日升部驻类乌齐炮队余全海在恩达县地方捕获两名越界割草的藏兵,并将之解送昌都”[1],此后彭不顾藏方的交涉处死两名越界藏人,并将其首级送还,以致激怒藏人,最后彭部边军同藏军在类乌齐发生了武装冲突。1918年2月恩达,察雅,宁静等县被藏军攻克,同年4月藏军占领昌都,彭等官兵被押解至拉萨,随后藏军以破竹之势连续占领了德格、石渠、邓科等地。8月11日,藏川两方在英国的调和下在昌都举行正式会谈,“8月19日,刘赞延与”多麦基巧“噶伦强巴丹达签订了由台克满所独拟之停战条约13条…………10月10日藏方代表堪穷洛桑顿珠,藏军代本穷让巴哲通巴等与韩光钧等人在甘孜绒坝岔签订了停战条约,条约规定汉军退守甘孜,藏军退守德格,自1918年10月17日起,双方停战一年,听候民国总统与达赖喇嘛和平解决[1]。
第三次“康藏纠纷”发生于1930至1932年间,其导火线是史上所谓的“大白纠纷”。1930年6月大金寺同白利乡亚拉寺因庙产发生争端,从而攻占了白利村,百利一方受到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支持,1930年7月8日刘文辉部下马骕占据了雅拉寺,围攻大金寺,大金寺见此遂求援于西藏,藏军正式介入。由此,大金白利之庙产争端升级为川,藏两方的军事冲突。1931年国民政府同西藏地方一同议定解决大白事件的八项条件,遭到刘文辉当局的反对。1932年2月29日,国民政府将大白事件的决定权全权交于刘文辉处置,开始了川军对藏军的猛烈反攻阶段。到1932年5月川军迅速攻克朱倭、甘孜、德格等地,藏军被迫撤回到金沙江西岸。1932年10月8日,汉藏双方代表邓骧与穷让共同订立岗托协定,暂时结束了因大白事件引起的汉藏边界纠纷问题。
二、“康藏纠纷”之名称问题
(一)“康藏”一词溯源
““康藏纠纷”作为历史名词,就笔者所查阅,《申报》是较早的出处之一。1930年12月11日《申报》的新闻报道,标题为《康藏纠纷即可解决》。”[2]随后“康藏”一词便在国内各类报刊杂志上频频刊登,以“康藏纠纷”,“康藏战争”“康藏冲突”等名称出现[2]。在此前的资料中既未见到“康藏战争”或“康藏纠纷”这类名称,也未发现称川军一方为“康军”的记载。以任乃强先生的《康藏史地纲要》一书为例,在记载前两次纠纷事件时,其书中都以“边军”或“川军”的称谓出现,记载第三次纠纷事件时首次出现了如“藏军乘康军懈弛,协同大金寺,于民20年(1931年)之夜,猛袭康军”[3]等句子。在记载第一次纠纷时载有“改组边军”“边军困守在康者”“达赖闻川滇军西征”“川边军政”[3]等称法。第二次纠纷时也载为“边军初胜”“边军失败”“被俘边军”[3]。在第二次纠纷过后,边军分统刘赞廷与西藏噶伦降巴登达签订的停战条约13条中则明文出现“汉军退守甘孜,藏军退守德格”“汉藏各军,于停战后一年间”[3]等句。同样在第三次纠纷事件中,刘赞延和琼让代本于1931年11月6日拟定的暂时停站条约八项中也明文载有“被掠川军一概放回”[3]一句。再者1932年琼让代本与邓骧在冈拖签订的停战协定中载有:“汉藏暂定停站条件:……所有汉藏历年悬案,侯听中央与达赖佛解决………汉军以金沙江上下游西岸为最前防线,藏军以金沙江上下游最西岸为最前防线”[3]等句。
就藏文方面而言,民国时期的藏文资料本就缺乏,加之仅有的资料中对三次纠纷事件的记载更是零星一点,故想从藏文史料的角度对当时事件进行整体还原可谓是海底捞针。纵然如此,从目前仅有的藏文资料中,还是能够管窥到作为当时涉事一方的西藏方面对三次纠纷事件的认识以及对双方军队名称问题的看法。 《甘孜绒坝岔历史与现状研究》一书载有“藏历十五饶囧之火龙年(1916年)汉军在昌都被藏军所击退,火蛇年(1917年)藏军来到甘孜绒坝岔地区。”[4]《藏族史·齐乐明镜》 载有“百利土司携汉军发生藏汉战争,藏军初胜。铁羊(1931)年四川汉军再度归来打败藏军,陷炉霍于汉人手中,汉军彻毁大金寺,失霍尔阔及瞻对两地,因藏军大败而不得不于水猴年(1932年)二月立定条约……水猴(1932)年3月四川汉军进入邓科,藏军落败而归。”[5]《西藏政治史》一书载有“……百利土司受到四川总督刘文辉的支持派遣汉军……四川总督刘文辉在继将军张团长之后复派遣了两路大军……汉军彻底瓦解了大金寺”[6]等内容。可见在少数可见的藏文史料中对双方军队的身份及名称的界定十分明确,对西藏军队简称“藏军”,对川军或川滇军则称“四川汉军”或直接称为“汉军”。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断定,三次纠纷事件中的涉事双方在正式场合中都分别以“藏军”和“汉军”或“川军”彼此相称,前两次纠纷事件中的汉族军队以“边军”或“川军”自称,第一次出现 “康军”和“康藏纠纷”的称法始于第三次纠纷事件发生时国内对外的报道中。以此为始,后期的大部分汉文资料中都以“康藏”或“康藏纠纷”的名称出现,而在藏文资料中则一直沿用纠纷发生时就业已存在的“汉藏”或“汉藏纠纷”的称谓,这与双方代表在三次纠纷事件中明文签订的书面停战协定内容不谋而合。故从“康军”或“康藏纠纷”称法的源头分析,这种称谓最先出自后期国内媒体单方面的对外报道,既有违当时涉事双方正式明文签订的书面名称,也不符合作为涉事者之一的西藏方面对此事件名称的界定。
(二)从纠纷的实质分析
“康藏纠纷”这一名称的应用同中央政府对此事件的定性相关。“康藏纠纷发生后,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为准绳,依据国民党”三大“的精神来处理康藏纠纷。………南京国明政府根据上述决议,将康藏纠纷定性为国内性的冲突事件,与内地各地方势力派之间的战争相同,因此国民政府反对外国插手和干涉康藏纠纷,以免事态扩大和复杂化。”[7]从中可以得知,中央政府将纠纷事件定性为地方性的冲突事件,实为避免事态扩大化,防止外国以此事件为突破口进行分裂祖国的行径而采取的一种战略性的举措,实乃一种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实行的政治手段。因此后期学者以此来判定三次纠纷事件性质的做法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
所谓的“康藏纠纷”事件系20世纪初发生在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对于金沙江两岸康巴区域归属问题所引发的争端,它源于西藏地方政府于民国建立初年在卫藏取得相对短暂的“独立地位”后,两者之间就如何划归西藏以东之川滇藏区和甘青藏区版图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也是《西姆拉会议》悬而未决的有关内藏(除卫藏以外的康巴和安多藏区)归属问题的核心。“自清末川边改流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康,藏划界问题上均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出发,试图把对方纳入自己的体系中进行解释……双方在康,藏界务问题上的迥异看法,成了康藏地区长期纷争的重要原因。”[1]
早在1934年,西藏地方政府驻京代表贡觉仲尼就指出“藏事问题,在川而不在康,外间称康藏纠纷,实系错误,实可称为川藏纠纷也。”[1]贡觉仲尼从纠纷的实质出发,一语道破“康藏纠纷”名称上存在的问题,其“藏事问题在川而不在康”一句更是合乎实际。因为就三次纠纷事件中交战双方军队的身份而言,西藏方面所派之军队都系藏人,而四川方面的军队都是四川及云南等地的汉人。而且三次纠纷中都有康区土司与民众对四川汉官的反抗运动,这些反抗运动又都与三次纠纷事件相联系[3]*载有:“宣统三年(1911)秋……察雅,宁静,德荣蕃民皆叛应达赖。昌都被围,全康大乱。……达赖既得英人援助,再?康地僧民反攻,各县叛乱纷起……电胡景尹调川军来边助剿。” 张云侠编,王辅仁校注:《康藏大事记年》,重庆出版社出版 1986年5月,P374载有:“公元一九一九年(民国七年)川边藏族掀起抗粮抗税斗争。” 刘国武: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分析,史学集刊 2004年4月 第二期载有:“因近世汉官贪污无理……该寺轻汉官而侮辱汉官……汉官过寺皆需下马,否则群僧争以土石击之。”,成为纠纷发生的导火线。从这一层面上讲,谓三次纠纷事件为“康藏纠纷”大有互相颠倒涉事主体之嫌。 更进一步而言,藏事问题在川更在中央,事关中央对川滇边区的管辖权。国内多数声音以当时中央政府并未实际参与纠纷事件为由,认定三次纠纷事件纯粹系西藏地方政府和川康当局间的地方性事件。如此便一味否定了当时中央对四川的控制与管辖权,虽然当时军阀割据现象普遍存在,但中央对川地的控制权和管辖权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三次纠纷事件中在川康当局背后起指挥和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中央政府[1]*记载:“就在西征军迅速平息康区乱局并进一步准备入藏平乱的关键时刻,北洋政府却电令尹昌衡………西征行动”。P119记载:“2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大白事件交由刘文辉负责,刘文辉拥有康藏纠纷处理权后……..”。。 在琼让与刘赞廷于1931年共同拟定暂时停站条约八项后,刘文辉对此答复有“此案要点,全在藏军退出甘瞻,乃有交涉可言………事关国防,并为中央威信所系。”[3]1932年蒋介石就纠纷问题致电达赖喇嘛“申明汉藏问题纯属内部事物……并希望达赖务使维护祖国统一,不允外人插手,内部事务可经内部协商而逐步解决”。从中可以看出,三次纠纷事件的性质不仅远远超出“康藏”地区的狭小范围,最主要的是它同中央对西南边区的控制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国防事宜密切相关,因此决不能因战事之规模大小来评判其性质之大小。
所以从整体而言“康藏纠纷”的实质归根究底应为民国中央领导下的四川省和西藏地方间关于川康地域归属权的争端,事关祖国边防事宜,故其事件性质远非“康藏”两地之狭小范围所能容纳。于这点而言,称三次纠纷事件为“康藏纠纷”与事件性质实为不符,应当称其为“川藏纠纷”为宜。
(三)从“康”“藏”两词的概念分析
历史上常将整个藏族集聚区按地域划分为三大区域(卫藏,康区,安多),自西部阿里至东部甘青藏族居住区依次分为“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死茹,下部多康六岗或下部多康三岗”[8]。“康”“藏”两地的名称,是由彼此间在地缘上的相对位置而来,“康”是藏语的音译,即指相对于藏区腹地(卫)而言在地缘上处于边缘的地区,这里的“康”不仅包括现今的康区,而且还包括卫藏东北部的安多藏区,只是后来这一名称才被惯用到康区的称谓上而已。诚如《白史》所载:“地处东部的康区和安多都称为“康”,“康”是指边缘地带,如称边缘政权为康之政权”[9]。“藏”是藏语“蕃”的直译,“藏族原来并不自称“藏”,而自称“蕃”,“藏”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对他们的泛称,这个民称概念大约出现于元代。据推断,大概是由“藏曲”,即雅鲁藏布江的“藏”而得名。”[10]由此可知,“藏”一词是汉语中对三大藏区(蕃)的集体泛称,不应仅仅局限在现今“西藏”地理概念的狭小范围内,“康”一词源于藏文对整个藏区边缘地带的具体表达,成为单指现今“康区”的地理概念。所以“康”“藏”两词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康”应当隶属于“藏”之范围,不应将两者等量齐观。
从这点来看“康藏纠纷”这一提法存在很大的问题及隐患,如果将两者放置一处论之,则容易形成两种极端的谬论。对于明确“康”“藏”概念者而言,康本身作为藏的一支,其“康藏纠纷”的提法将涉事双方身份一体化,使纠纷成为藏族内部间的纠纷,以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三次纠纷的性质。对于不解“康”“藏”概念者而言,“康藏纠纷”的提法割裂了“康”和“藏”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一种“康不属藏,康藏有异”的认识。如若对三次纠纷事件的始末缺乏了解,光以“康藏纠纷”这一名称,便能在开头部分形成一种完全错误的认识,即三次纠纷为“康巴跟藏族间的纠纷,既如此康巴并非藏族”。这种扭曲的认识不仅有违三次纠纷的性质,更甚者直接造成康巴脱离于藏民族,自成一族,乃至于后期国内学术著作及公共场合中频频出现“康巴族”,“康族”或“康巴藏族”这类千奇百怪的称谓。 再者,汉文资料中对“康藏”这一提法极不规范和严谨,有时单指居于川边和滇边的整个藏民族,即“康巴藏族”,有时又分别指向西藏和康巴两地(如“康藏纠纷”),且不谈这类用语是否严谨,单从两者之混淆情况而言,就已然成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结 语
“康藏纠纷”这一名称,从其最初的来源,到民国中央政府事后对它的定性,再到名称产生后相继出现的问题,都有其不适之处,因而将这一提法用于三次纠纷事件则多有不符。在战后涉事双方明文签订的停战协议中正式称双方军队为“藏军”和“四川汉军”(或直称汉军),这同藏文史料中所载的提法完全一致,而且从三次纠纷事件的实质来看,其纠纷性质远非“康藏”两地狭小范围所能容纳。再者,从其名称引申出来的问题来看,“康藏纠纷”混淆了康和藏的概念及关系,易于形成“康不属藏,康藏有异”的认识。凡此种种,笔者认为三次纠纷事件应称“川藏纠纷”为宜。
[1]王海兵.康藏地区的纷争与角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p13、p70 、p80-81、 p65 、p13 、p27
[2]朱晓舟.第三次康藏纠纷研究(1930-1940)[D].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p21、 p71
[3]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M].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p145 、p118、p119、p122 、p131、 p132 、p146 、p148 、p118 、p120 、p147
[4]泽仁翁加.甘孜绒坝岔历史与现状研究[M].藏文,民族出版社 ,2008年,p372
[5]毛尔盖·桑木旦著,阿旺措成,余万治译.藏族史·奇乐明镜[M].藏汉对照本,民族出版社,2010年,p185
[6]夏格巴.西藏政治史[M].藏文手抄本下册,p300
[7]刘国武.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分析[J].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
[8]智贡巴·贡去乎丹巴饶布杰.安多政教史[M].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p1
[9]根敦群培.白史[M].藏文,民族出版社,2002年,p9
[10]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6年,p58
——林俊华
——记中国共产党在川军出川抗日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