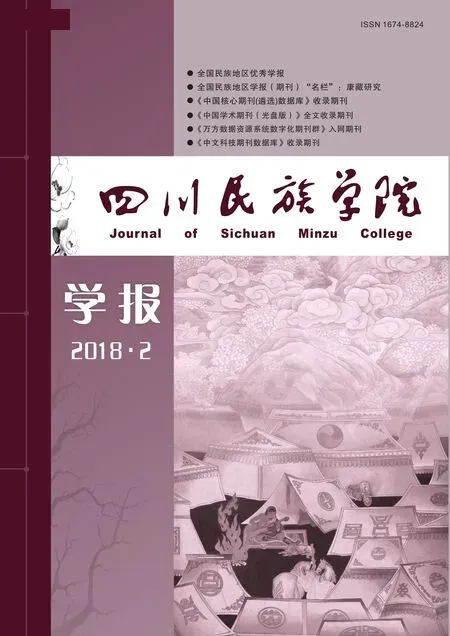浅析那彦成对青海藏区的治理
周先吉
那彦成(1764~1833),字韶九,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阿桂之孙,号绎堂,晚号更生,谥文毅。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为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三督陕甘,两督直隶,一督两广,两署巡抚,是清中期一位重臣和著名疆臣,在他受命出任西宁办事大臣及陕甘总督期间,基于当时青海地区复杂的情势,尤其在处理蒙藏民族问题方面,有效地实施了一些管理举措,值得后人在相关问题上引起重视。
一
清朝是我国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封建政权。清王朝在建立初期非常重视包括甘宁青地区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一方面沿袭元、明两代有效的治边政策;一方面根据“因俗而治”和“分而治之”的基本方针,采取和制定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多元化行政管理体制。尤其在清朝初期,调整其统治策略,在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藏区推行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民族宗教政策,对藏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及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明末清初,西藏地方的政治形势处于从政治多元走向地方统一的局面。是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并迅速发展,呈后来者居上之势,这引起了西藏其他地方政教势力的排斥和打击,为此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权和教派之争。明万历四十年(1612),藏巴汗统治了前藏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当时西藏历史上一个较大的地方政权。到17世纪30年代,藏巴汗政权与占据青海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以及康区白利土司三方因共同反对格鲁派而结为联盟,从东、北、西三面包围格鲁派,格鲁派的形势岌岌可危。此时,驻牧于天山南麓的蒙古硕特部汗王固始汗,受到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援请,率兵进入青海、康区、西藏,最终消灭了却图汗、白利土司、藏巴汗的势力。在固始汗的支持下,格鲁派在西藏社会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并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至此,固始汗统一了西藏地区,将军政大权掌控于自己麾下,为其后清朝管理当地提供了前提条件。
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偕四世班禅抵达北京朝觐。翌年在返回西藏途中,清廷赐五世达赖喇嘛金册金印,确认了他在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随后,清朝派遣使臣前往西藏,对固始汗进行了册封。事实上,清朝在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册封了固始汗,既支持五世达赖喇嘛在宗教领域弘传佛法,又敕封固始汗“作朕屏辅”,间接对青海、西藏地区进行行政管理。清政府对达赖喇嘛、固始汗的敕封强化了对西藏治理。在其后过程中,清廷继续推崇藏传佛教、优礼格鲁派高僧大德,以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即“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1]不仅如此,清朝在中央设立了“专管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在地方建立了治理西藏的机构和制度,首先是在蒙古汗王掌管的地方政权下,由第巴·桑吉嘉措管理地方政治事务;其后于康熙五十九年(1721)废除汗王和第巴制度,同时决定设立由四位噶伦联合掌政的噶厦政府,共同管理西藏事务。由此表明,清朝不再封授和硕特汗王,也不再承认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转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噶厦地方政府,这使得罗卜藏丹津重新统治西藏的幻想破灭。罗卜藏丹津是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之子,他一心冀希恢复祖先在西藏、青海等藏区的“霸业”,最终酿成两年后(1723)在青海公开发动叛乱。这次叛乱历时不足八月,很快就被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率兵戡定,但其影响极其深远:“及雍正元年,王师平罗卜藏丹津之叛,于是令土尔扈特旗、绰罗斯特旗、辉特旗、喀尔喀旗、察罕诺门剌麻[喇嘛]旗各自为部,不得复为和硕特,以分厄鲁特之势,又不设盟长,以西宁办事大臣涖盟。自后青海始同内地,渐削弱矣。”[2]它直接导致了清政府治藏政策的变化,对青海藏区的治理也在此时出现了转折。
17世纪40年代,蒙古和硕特部汗王曾于西藏、青海建立统治,是时,青海各藏族部落“惟知有蒙古,不知有厅卫营武官员”[3],大都纳于和硕特蒙古的统治之下。鉴于蒙古族在青海的强大势力,清初中央政府对当地蒙藏民族采取“抑蒙扶藏”的基本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蒙古势力。雍正二年(1724),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清廷当即实施善后措施,制定并颁行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禁约青海十二事》等。翌年(1725),又在西宁特设“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青海办事大臣”(后统称为“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政治、军事、各部会盟和茶马互市等事务,成为清代主管青海蒙藏事务的最高军政机构。从此,结束了蒙古汗王对青海的统治。
二
清政府为加强对青海的治理施行了一系列办法和措施,加强了对蒙古诸部的管理,设立盟旗制度:“分其旗分,编为佐领。各管各属,定有分界,”[4]每百户设一佐领,并严格划定各旗游牧边界。此后,又设祭海会盟制度,规定各旗每年会盟一次,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紧接着将原归蒙古汗王管辖的青海藏族部落收归清廷直接管辖。第一任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在青海藏族地区清查户口,设立千百户制度,分别给各部落首领授以土千户长、土百户长等职,加强对青海藏族社会的管辖力度。不仅如此,清廷唯恐蒙藏杂处再生事端,明确规定了两族游牧生活的地界,将藏族大部分限制在黄河以南区域,由千户长统一管理;而将蒙古划分到黄河以北以及环青海湖的地区游牧定居。后来由于河南藏族人众地狭、河北牧场水草丰美,于是,河南诸多藏族部落迫于生计渡河畜牧,导致了本文将探讨的那彦成处理藏族部落北渡黄河、驻牧河北事宜。此外,清廷通过罗卜藏丹津事件,充分认识到藏传佛教的巨大影响,于是下令限制佛教上层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发展,整顿和管理藏传佛教寺院。为改变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朝廷还将西宁卫改为西宁府,隶属甘肃省,下设西宁、碾伯两县和大通卫。由此说明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朝将治藏目光转移到青海地区,加强了对该地区蒙藏各部落及社会的掌控和管理。不仅如此,有鉴于青海藏族各部落“今日番中一族有千余户,则其势浸大,万一有枭雄纠合数族,则万众之聚,实为地方隐忧。”[5]清朝规定将他们全部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按照上述新近颁布的两条法律条款的规定,清廷于各部落中确立了千百户长负责制。为确保该制度的顺利实施,那彦成再将其细化:“将旧设千百户,饵以领易粮茶之利,而于所管番人立之限制,令千户管三百户,百户管一百户,什长管十户,是千户之族有三头人,二千户之族有七头人,各领接管,上邀天朝茶粮互市之恩,其势不肯相下,自必倍加恭顺,为我藩篱。”[5]从嘉庆九年(1804)那彦成首次出任陕甘总督,三年后(1807)任西宁办事大臣,十五年(1820)复任陕甘总督,到道光二年(1822)再以刑部尚书身份任陕甘总督三年有余,在任职期间他针对青海具体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一,请将隶属兰州府之循化厅改隶为西宁府,便于清廷进一步直接管理青海藏族部落。循化厅成立之初隶属于兰州府,由陕甘总督统辖。嘉庆十二年(1807),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会同宁夏将军兴公奎、陕甘总督长龄上奏朝廷,应不拘一格、不限民族成分重用人才:“循、贵两厅同知,应请不拘[泥]旗、汉人员,以便易于得人也。查嘉庆八年(1803)贡楚克札布等《奏定章程》‘循、贵两厅同知应用旗员’等语。特以旗员通晓清语,办理蒙、番事件较为熟谙。第通省旗员无多,此内或人地不宜,或碍于处分,一时不能得人,每至出缺,深费周章。窃以文员办理地方,但能实心任事,即可措置得宜。如从前贵德同知姜有望系属汉员,查办番案出力,曾经赏戴花翎,原不必定用旗员始能练达边务。嗣后应请循、贵两厅缺出,但择人地两宜之员酌量升调,不必专用旗员。庶易于为地择人,不致为成例所拘矣!”[6]
此外,道光三年(1823)以前,循化厅和贵德厅分别隶属于兰州府与西宁府,管理黄河以南的蒙古族和藏族,自西宁办事大臣设立之后均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凡遇到蒙藏民族事务问题,贵德厅同知就近转与西宁办事大臣衙门处理,便捷且迅速。而循化厅则不然,凡事需从兰州府经转,耗时耗力十分不便。那彦成再次出任陕甘总督后,为了便于监督、约束和处理蒙藏两族事务,奏请将兰州府之循化厅改隶西宁府:“窃查甘肃循化、贵德两厅,均系理番同知,向归青海大臣管辖。该两同知分管黄河迤南番族,凡有蒙、番事件,贵德同知即由该管之西宁府就近核转青海大臣衙门办理,甚为便捷。惟循化同知远隶兰州府属,青海大臣檄办事件,须由兰州府转行。西宁距兰州六百里,兰州距循化又五百余里,文报往返,已属需时。而兰州府又不归青海大臣统辖,遇事又多掣肘。现在河北番族,全数驱过河南,改设立千户、百户、百总,层层钳制,则以后之稽查约束,更关紧要。该两同知地界毗连,必须会同办理,而分隶两府,势难期于画[划]一。应请将循化同知改隶西宁府属,一切公事,均由该府就近移转青海衙门办理,以免歧异。该厅距西宁郡城仅止二百余里,文移往返,亦可无虞延缓,实于边务番情,悉臻妥速。”[7]至此,嗣后循化厅一切公事均由西宁府就近移交西宁办事大臣衙门办理,循化厅始改隶西宁府,既提高了办事效率,又为清廷管理循化厅所属各藏族部落事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二,清厘黄河以南藏族部落,编查户口,重申千百户制度,严格管束各藏族部落。以罗卜藏丹津事件为契机,由于青海蒙古族势力的强大,清廷为了削弱其力量采取“分而治之”、“扶番抑蒙”政策,通过扶持藏族部落来巩固清朝在该地的统治。根据藏族封建化进程的快慢,清廷将其分为“熟番”、“生番”和“野番”,设千百户、总千户进行管制,统统划归于清政府管辖。将蒙古分为二十九旗,划定地界,规定不许私自扩大领地、越界游牧。以黄河为界,实行蒙藏分治,黄河以北及环湖地区为青海蒙古二十四旗的驻牧地,黄河以南除五旗蒙古外,为循化、贵德两厅所属藏族各部落的游牧地。如此导致后期青海蒙古族人口锐减,力量衰微。相反,青海藏族部落在脱离蒙古族统治后,经休养生息势力逐渐发展,从蒙强藏弱变为藏强蒙弱。因初期划分蒙藏地界的不合理性,藏族部落随着人丁增长而缺少足够的牧地,开始徙牧黄河以北地区,蒙藏间矛盾纷争不断。早在乾隆时期,河南蒙旗经常遭到循化、贵德两厅以及果洛藏族部落的攻掠。嘉庆年间藏族部落仍频频渡河北移,大批蒙古牧民纷纷避入内地。此时,清廷改变最初的“扶番抑蒙”转而采取“扶蒙抑番”政策,驱逐北迁的藏族部落,引起了青海蒙藏社会的动荡不安。而这仅仅是河南藏族部落迁徙之始,其后大规模徙牧河北发生在道光年间。道光元年(1821),汪什代海等河南二十三族藏族部落全部北渡,于青海湖周围驻牧。此前朝廷虽屡次派遣西宁办事大臣查办,但并无明显成效。道光二年(1822),清廷再命治理民族问题颇富经验的那彦成“查办番案”。他决定“先治河南”,着手清查河南各部户口,照内地保甲一律编查,加强千百户制度。清查户口结果为“贵德厅有生、熟、野番三种,熟番五十四族,向来种地纳粮,均能谋食生番十九族,住居贵德之东南,畜牧为生,惟野番八族,户口强盛,内有汪什代亥一族,近已全数移居河北,其余七族,现俱插帐河滨,远难控制。循化厅有生、熟二种,熟番十八族,生番五十二族,大半皆有粮地。”[8]在此基础上,那彦成禀旨进一步推行千百户制度,“分其户口,每三百户设千户长一人。千户长之下设百户长、百总、什总。凡百户长一人每管百户,三百户归一千户长管理。百总一人每管五十户,两百总归一百户管理;什总一人每管十户,五十户归一百总管理。”[5]将藏族各部落更进一步纳入清廷的直接管辖下。
第三,规定藏族易买粮茶章程,整顿贸易。青海藏族部落本无类似章程,由此,那彦成首先规定藏族依照蒙古之例请票易买粮茶,由户口多少分食,请票均由各族千户长在循化、贵德两厅代领后,才能购买粮茶,照票每年准买两次。“若有不遵法度之人,即不准领票。至所必须之布、线 、靴帽、木碗之类,亦于票内注明,一同换买”[8],在事关牧民的粮茶贸易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其次,开设歇家,制定相关制度。歇家在民族贸易中既充当着商务代理人的角色,还为官府督收差税。清中后期,歇家积弊日益增多,那彦成等不仅封禁各地私人歇家,还将西宁、大通、循化、贵德、丹噶尔等地的官方和私歇全部造具花名册,由官经管,并且“另立循环印簿,每歇家两本,将逐日来店住宿之蒙、番询明何事进口,所来何货,所换何物,详细填注簿内,”[5]并规定每月呈报衙门。再次,规定固定贸易点与交易期。清代,商民前往青海蒙藏地区易买羊只货品的称“羊客”。为进一步规范羊客与蒙藏部落间的交易,那彦成等将贸易点定于“应请嗣后毋论何州、县羊客与河北蒙古买羊易货,止[只]准在于西宁县属日月山卡以内东科尔寺、丹噶尔及大通县属之乌什沟、察汉俄博等处,互相交易。其河南蒙古、番子羊只、货物均在贵德厅属之西河滩售卖,该羊客不许经赴蒙、番游牧处所牧买,致滋流弊”[5],并规定每年四至九月为交易期。
第四,规定玉树藏族马贡折银请仍循旧例交纳,取消主事、通丁征收贡马银。清朝建立之初,青海各藏族部落仍受蒙古族统治。长期以来,蒙古贵族对藏族部落收贡“并无定数,任其增减,索取无休,以至众心不服”。[9]罗卜藏丹津事件被平定后,清廷册封各千百户,开始向玉树各部落征收赋税,实行贡马银制度。清廷规定,每百户需要缴纳马1匹,每匹马折征白银8两,不足百户者,每户征银8分。原议该部落首领自赴西宁交纳。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政府改派通丁每年到玉树等地各藏族部落催收,或由当年会盟之主事征收。但“通丁出口往返数千里”,并“任意携带货物并私带买卖客商……计其往返之期,总在半年以外”。[5]主事者也同样弊端种种,他们“私备布匹等物致送番族,名为土仪,因得受番族馈送,薄往厚来。是正供不过六百余两,而蒙番所费,实十倍正供不止”。[5]道光二年(1822),那彦成三任陕甘总督之时,鉴于上述弊端上奏建议“所有此项贡马折银应请仍循旧例,责令该总管千、百户等如数凑齐,于每岁九月间交该处贸易番目自赴西宁交纳”。[5]从此,“其主事、通丁之例,永行停止”,切断了通丁与主事盘剥黎民,从中牟利的敲诈欺压行径,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玉树藏族部落及当地藏胞的经济负担。
三
清朝对青海藏区的管辖从最初的无暇顾及到雍正年平定叛乱为转折,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饬治理,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清中央政府凭倚着振兴格鲁教派的政策,与青海各部藩属建立关系;为削弱和硕特势力,长期采取了“扶番抑蒙”政策。其后又加大了对西部藏区的治理管控力度,于雍正三年(1725)设置西宁办事大臣,专管青海蒙藏事务。为此,在藏族部落中分封千百户等职,笼络部落头人,支持藏族部落的发展,千百户制度的正式确立维系了清中央政府与藏族各部落间的关系。有清一代,对青海地区的藏族部落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法,根据部落情况相应地从行政、法律等方面对青海藏族部落进行管辖,整体来说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那彦成曾经三任西宁办事大臣及陕甘总督,他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在施政、经贸、人口管理等几个方面制定和完善了章程,维护了清王朝在当地的实际统治。总体来说,那彦成管理青海藏族部落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也有弊。第一,在河南藏族部落徙牧北迁之时,通过统计人口并实行了千百户制度,将青海藏族部落纳入到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控之下。这一制度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效,在一段时间内巩固了清朝对青海藏区乃至西北地区的统治,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以南藏族部众人多地小的问题,导致他们近一个世纪持续的北移活动,最终于咸丰年间形成了今天所谓的“环湖八族”。在这次徙牧河北的过程中,清廷与藏族部落可谓两败俱伤,朝廷多次委派大臣“查办番案”,但均无成效,且劳师伤财,而北移的藏族也多次遭到清军的武力镇压,损失惨重。不仅如此,徙牧河北也使蒙藏两族间关系变得更紧张,甚至形成了长期对立状态,不利于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第二,加强千百户制度,青海藏族部落脱离蒙古部族的统治由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一方面有利于清朝的治理,达到分而治之、平衡蒙藏力量,稳定了青海地方社会的目的;而另一方面,朝廷削弱和分化了当地藏族的力量,从而使千百户们各自为政,彼此纷争,对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作用。第三,歇家的出现以及青海蒙藏贸易制度章程的制定和完善,不仅为藏族商人的贸易来往提供了便利,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藏族人民的权益,减轻了其经济负担,还使清廷对民族经济贸易的管理加以强化。尤其通过那彦成的整顿吏治,使青海民族经济贸易进入有清以来的繁荣时期。但因严格限制藏族牧区经商活动,章程规定仅可以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内互相以物易物的等等禁令,在一定程度内,妨碍了各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往来,阻碍了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那彦成是嘉道时期的一位重要的疆臣,他对青海地区的民族事务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调研,也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管理,这在清代蒙藏史上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评价其青海施政举措,需要我们客观地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考量,作为清王朝顾命西北的一位封疆大臣,他的所作所为受阶级利益和历史环境所限。一方面,他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的负担,客观上促进了当时青海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是,其奉行的还有一些措施,是清王朝为巩固封建统治而进行民族压迫的表现形式,这些源于阶级的本性和立场,对此本人不能苟同,应予以否定。
[1]清实录·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转引自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
[2][清]魏源.圣武记.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p112
[3]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p26-30
[4][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十八,武备志·青海[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p531
[5][清]那彦成.平番奏议.卷四.上绛堂尚书论番事书[Z].台北:广文书局,1978年,p395、p395-396、p160、p45、p221、p173
[6][清]那彦成.那彦成青海奏议[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p69
[7]邓承伟等.西宁府续志.卷九.艺文志·陕甘总督那彦成请将理番同知改隶近番府属疏[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410-411
[8][清]邓承伟等.西宁府续志.卷九.艺文志·陕甘总督那彦成清厘河南番族编查户口疏[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403、p406
[9]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十六.田赋志·塞外番贡[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p406
——以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创办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