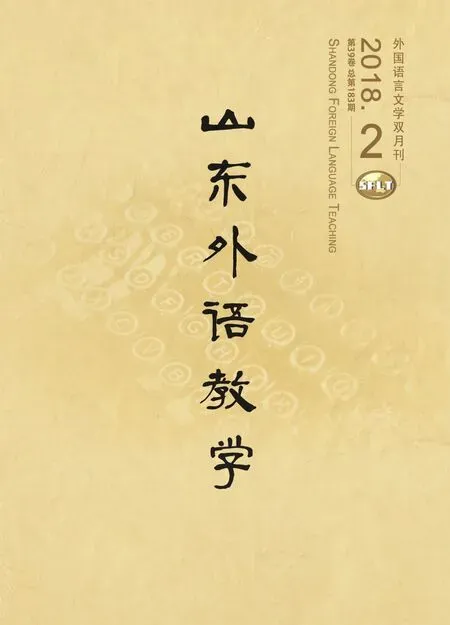库切作品书名寓意与汉译研究
王敬慧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1.0 引言
库切作品的书名会让人想起人生的不同阶段,比如他的《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小学时代》《男孩》《青春》《夏日》和《慢人》,会让人想到莎翁所说的人的七幕人生。读者也可以换个角度,将他的小说体自传《男孩》《青春》和《夏日》看作是亚里斯多德式样的人生三段展现法。这三本书有相同的副标题—— 外省人生活场景(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该标题的选择,体现着库切内心的一种强烈的“外省人”情节。“外省人”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缘起于巴黎,最初指的是居住在巴黎市区之外的人。那感觉就如同一些以上海为自豪的上海人说“阿拉上海人”,外省人都是有些“戆憨憨”的乡巴佬。在库切看来,与占有文化主导地位的西欧以及北美大都市相比,南非是外省,南非的文学是外省文学,所以他用此来界定和标记自己的作品。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敏锐优秀的作家,他摆脱了外省人的自卑,正如坎尼米耶《库切传》中所介绍的,库切认识到“外省文学不一定就是渺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就是外省的,但同样是重要的。外省主义还有许多其它可以发扬的地方”(Kannemeyer,2013:356-357)。也正是如此,库切在后期的作品中逐渐超脱了国家与民族的界限,着眼于普遍的、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本源思考。《耶稣的童年》与《耶稣的小学时代》是非常有效的例证,它们启发读者思考出生与教育这两大基本问题。如果细细考量,耶稣也是移民:他儿时被父母带着到处迁徙,成年后也是在终生迁徙中感化信徒。在目前全球化的时代,“外省人”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大都市,无数的“外来人口”是“外省人”,对于美澳加等移民国家,无数的移民是“外省人”, 对于当下的欧洲,众多的难民是“外省人”。外省人如何摆脱自卑与耻辱的烙印,恰当应对自身的流散情节,这将是未来世界文学所涉及的重要内容。
库切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英语语言学专业博士,同时还是文论家与翻译家。这样的资历让库切对文字的运用敏感而细腻。作为世界知名作者与译者,他也深知文本向异国的传输需要借助翻译,而不同的语言出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土壤,在被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会出现意义的改变或缺失。因为这样的原因,他的文字总是力求简洁,结构上也清晰可辨。曾经有阿拉伯语文化季刊记者通过邮件提出了关于他对翻译的期望问题:“对想翻译您小说的译者,特别是阿拉伯语译者,您有什么建议吗?”他的回答言简意赅,但是其中显示了他对翻译的理解:“注意纸上的文字和句子的结构”(Kannemeyer,2013:583)。除此之外,他对译者不再提其他任何要求。
相比较而言,库切的作品文本本身容易翻译,但是作品书名翻译对译者而言颇具挑战性。很多情况下,库切喜欢用寓意深刻的词汇,特别是一词多义或双关语,这让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面对多种可能,而不得不退而选其一。译者将其作品书名翻译出来之时,即是意义出现缺失的时刻。本文从库切作品中选出五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书名来分析,尝试总结有关库切书名寓意与翻译原则。
2.0 《等待野蛮人》与《等待戈多》
1980年《等待野蛮人》的出版为库切赢得了世界声誉,就如同1951年《等待戈多》的问世让贝克特蜚声世界文坛。这两部作品的渊源不仅如此。从某个角度上说,《等待野蛮人》是库切对贝克特的致敬,同时《等待野蛮人》也与《等待戈多》进行着互文。库切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致敬” 的文章来向那些影响过他写作的作家表示敬意,这篇文章实际是他199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稿。该文章开篇第一句是:“这篇文章是关于一些作家的,没有这些作家,我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些作家,我可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①在该篇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在英国如何广泛的阅读,以及在诗歌、散文和小说方面他所读过的作家。诗歌方面,他提及自己读过贝克特翻译成英语的《墨西哥诗歌集》。库切对贝克特的研究不仅出于学术目的,他自称是贝克特的 “迷恋者”(aficionado),快乐地将时间花在贝克特上面。他认为从贝克特的散文中所学到的内容要比从诗歌里学到的内容具有更高一个层次的抽象度。贝克特让他知道应该侧重的不仅仅是语言的节奏和句法,还应该是思想的节奏和句法。库切是世界公认的贝克特研究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即是《关于贝克特初期作品的语言学研究》。2006年在贝克特百年诞辰之际,纽约格罗夫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共16卷的《贝克特百年纪念文集》(SamuelBeckettTheGroveCentenaryEdition:Poems,ShortFiction,Criticism)。在这套书中库切负责介绍贝克特的诗歌、短篇小说和文学批评。
对贝克特的研究影响着库切的创作风格,以至于从作品的名字上,读者都可以找到贝克特的影子。《等待野蛮人》是库切版本的《等待戈多》。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在一棵枯树下相遇,开始了他们“等待戈多”的行为。他们等到了晚上,等来一个男孩告诉他们:“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准来。”于是两人又继续等待,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人物,只是枯树上长新叶子了。但是等待的结果只是再次被同样的人物告知:“戈多今晚不来了,明晚准来。”他们想到了自杀,但是上吊用的皮带扯断了,自杀未果。最终两个流浪汉说出了他们的台词:戈多来了,我们就得救了。库切在《等待野蛮人》中继续运用了“等待”这一主题:帝国边境的居民原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突然来了一个来自帝国中心的官员,声称帝国的敌人是野蛮人,然后发动起对野蛮人的征讨。结果整个小镇居民处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不时有传言说野蛮人要来进攻了,而到小说最终,野蛮人也没有来。在《等待野蛮人》中,《等待戈多》中枯树的场景被改编为一个历史和地理背景都被淡化的帝国边境小镇,通过一个老行政长官的具体经历激发读者对文明和野蛮的探讨。所以,可以说库切的这部小说是对“等待”主题更深层次的挖掘。
3.0 《福》与《鲁滨逊漂流记》
《福》的英文书名Foe来源于《鲁滨逊飘流记》作者的名字——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这位十八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之父本来就姓Foe,在40多岁时,为表示自己有贵族头衔,刻意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了一个贵族头衔:De,改姓为Defoe。而库切则在他创作的小说中从解构《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他要让其恢复本来真实的姓氏。对于库切而言,对经典的戏拟与重写是为了凸显过去曾经被埋没的信息,或者修正错误的信息。所以库切在自己的这部小说中,让男性人物鲁滨逊退到后面,女性人物苏珊·巴顿成了故事的主体叙述者。按照她的记述,当时被营救的船难者有三人——她本人、鲁滨逊,还有星期五。鲁滨逊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病死在船上,是苏珊·巴顿带着星期五回到欧洲大陆,她希望找到一个名字叫福的作家,因为这个作家是会讲故事的人。她请求福将她的故事整理、创作和出版。在《福》这部小说中,作家福的头上并没有“现实主义小说之父”的光环,他只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受雇文字写手。他生活窘迫,要躲避法官和债权人,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原则,为取悦读者而任意篡改苏珊·巴顿讲述的内容。那么,从解构经典作品创作者身份和还原历史真相的角度,将该小说的书名翻译为《福》是一种可选择的方法。但是这种翻译也消解了作品中包含的各种对立关系,比如: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作品,真实与虚构,女性人物与男性人物,言说者与失语者,新作与旧作,主人与仆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等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英文书名Foe的另一个含义:“仇敌”。
在书名翻译中,尽管《福》与《仇敌》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译者只能选择其中的之一。这个选择的过程对于译者而言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译者知道,在选择开始的时候,即是意义缺失的开始。所以作为该书的译者,笔者一直惴惴不安,也曾经亲自与库切本人探讨,用其他的形式来弥补这种缺失,比如建议中文出版方在图书封面上将“福”字倒着印刷,寓意 “福到”,或者用中国剪纸:红色的365个福字来弥补缺失的含义,探求展现新意的可能。尽管最后因出版常规要求的原因,比如书名不能倒印,否则会在未来书目管理中出现无法检索的情况,这些想法未能实现,但是从这个过程和译者反应可以看出,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意义的部分缺失对译者会造成一种创伤,并导致其他的可能。库切本人对此深表理解,所以他对笔者提出的弥补方案也表示出接受的态度。实际上,作为译者,他理解并能接受译者在理解作品之上的创意。比如在《异乡人的国度》中,他写过一篇关于荷兰小说家、旅行家齐斯·努特布姆的文章,其中他谈到该书名《在荷兰的大山里》的翻译。其实,该书的荷兰语原文是《在荷兰》,译者之所以在译文中加入大山,是因为根据故事情节,这个地方被分裂为南、北两半的国家里,南方来的移民聚居在北方城市周边搭建的临时棚户区里。北方人瞧不起南方人,因为他们肮脏、狡猾,因此,用他们作廉价劳动力;南方人则称北方人为“严厉冷酷的人”。主人公提布隆内在心里觉得自己是个南方人,不喜欢北方人,“因为北方人自尊自大、贪得无厌,又虚伪得总想设法加以掩饰”。一提到北方,提布隆心里就感到怕,“德文中大写的怕”(库切,2016:71)。而南方多山,所以译者在英译本书名加入了山的意象,库切认为这是对原文准确把握基础上的创意性添加。书名翻译是Foe,它需要将英语中有双关含义的词汇翻译入汉语,而汉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此类一语双关语的词汇,英语原文中的双关含义表示完全无法等效译入汉语。在书名翻译实践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局限:从宏观范畴说,翻译受到语境、语体以及文化思维差异的直接制约,所以就有了不可译性的客观存在;而从微观上看,译者的翻译水平,对文本的总体把握以及对文字的具体处理都直接影响译作的质量,所以文学作品在经过了语言转换之后,就已经或多或少失去了作品的原汁原味。那么如果某些评奖者只是根据自己能阅读的语言来对某一文学作品译本进行评判,就很难做到完全公平。库切曾说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诺贝尔不设立一个音乐奖,他认为音乐更具有普适性,而文学要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语言(Kannemeyer,2013:564)。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音乐语言完全不同于文字语言, 人类有不同的语言,却有相通的音乐。库切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翻译卡夫卡”的文章,在该文中,他详细指出了译者在将卡夫卡作品翻译成英文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他指出翻译的水平决定着一部作品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的被接受。在对穆齐尔的阅读中,他曾经切实感觉到同样的一个作品,帕特里克·布里基沃特(Patrick Bridgewater)翻译的版本就要比雷斯曼(Leishman)翻译的版本更容易理解和欣赏。翻译能译出“词”(word),但有时并不能译出“意”(meaning)。
4.0 小说《耻》与“仁慈”的缺失
小说《耻》的英文是disgrace,翻译为“耻”确实是该词汇的含义之一,但是,与Foe的书名翻译类似,当一个含义被选择为书名之时,就意味着其他可能含义的缺失。库切研究专家德里克认为该词与“耻辱”有关:“‘disgrace’一词的对立词是‘荣誉’(honor),因为《牛津英语字典》关于disgrace一词的解释总会和dishonor相联系。换句话说,公众目睹的耻辱与公众的尊敬相对、也只能由公众的尊敬来抵销;通过荣誉挽回耻辱”(Attridge,2005:178)。从小说基本情节来考虑,这种理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disgrace”还可能包括4种可能的内涵。
首先,对于小说中主人公卢里的女儿露西来说,Disgrace 可以表示一个名叫Grace的女孩的不在场,因为在卢里前妻的记忆里露西同性恋前女友的名字似乎是Grace。这样来梳理,这部小说的名字可以是“格蕾丝不在场”。
其次,还有一种可能,是“屈辱”。这可以从主人公卢里的角度考量,对于他和女儿在南非的生存状态的总结。这父女二人在南非的境遇可以用“屈辱”来描述。卢里是文学教授,却要在功利化的大学里教授交流技巧类的课程;他对于女性,不论是妓女还是女学生,都希望表达自己的真诚,但是并不被人理解;他与女学生关系的问题,卢里在登门拜访女学生梅兰妮的家长时说的话显示了他所处的状态:
“我不信上帝,所以我得把您的上帝及上帝的语言转化为我的说法。用我自己的话说,我在为发生在您女儿和我本人之间的事情受到惩罚。我陷入一种disgrace的状态不能自拔。这不是一种我要拒绝接受的惩罚,我对其没有任何怨言。而且,恰恰相反的是:我一直以来日复一日就是这样生活着,接受生活中的disgrace状态。您认为,对于上帝来说,我这样永无止境地生活在disgrace之中,惩罚是否已经足够了?”(Coetzee,1999:172)
卢里的女儿露西被黑人强暴,成为种族仇恨的牺牲品。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白人成为被欺凌的对象。白人曾经用来侵犯黑人的手段被重新夺权的黑人再次使用。当卢里教授看着女儿被三名暴徒侵犯、财产被洗劫一空,本人也几乎被烧死时,他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警察也帮不了他们。此时的状态用“屈辱”二字形容主人公是完全合乎作品主题的。
第三,该书名也可以翻译为“仁慈的缺失”。在南非这块土地上,尽管黑人与白人相处日久,但是祖先的错误使他们之间只有对彼此的仇恨而毫无仁慈与爱意。作为语言专家的库切很善于使用词汇来表达抽象的含义。disgrace从构词法上看由两部分组成——dis和grace。“dis” 表示 “没有”,而“grace”除了表示“优雅”以外,还有一个文化渊源深远的含义——“仁慈”,比如人们用英语表述仁慈的行为,“an act of grace”。所以,笔者认为从寓言角度来读这部小说,《耻》(Disgrace)是在描述一个通往仁慈(grace)的道路。小说在世俗道德上的无力,恰恰是为了建构起一个更为有力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仁慈与爱心,有存在的喜悦和悲哀,也有更高的平等和超然。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该词可以被翻译为“混沌”。库切在《双重视角》里曾经这样定义“grace”:“‘ Grace’是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之下,真理可以被清楚、且不盲目地讲出来”(Coetzee,1992:392)。那么从这个角度,disgrace就是一种没有真理的七窍未开的混沌状态。《耻》中的主人公卢里本人就认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之中。
5.0 《异乡人的国度》与《蓬莱仙境》
《异乡人的国度》英文是“Stranger Shores”。在该书名中,“Stranger”表示陌生人,异乡人;“shores”可以指海滨,海岸;也可以国家,尤指濒海国家。在英文书籍中,用这两个词汇为书名的书籍很多,比如StrangeShores,StrangersontheShore,StrangeBodiesonaStrangeShore等等。2016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将其翻译为《异乡人的国度》,是一个优美且深邃的翻译。但是,从构词法上分析,stranger除了表示陌生人、外乡人,还有一个可能,它可以是形容词strange的比较级;shores可以从海岸引申为大海的边缘处,对于内陆人而言很遥远的地方,那么此书名可以翻译成“蓬莱仙境”。这种可能性也可以从文集中各篇文论的内容加以佐证。仔细阅读该文集中收集的库切从1986—1999年间所写的文论文章,除了部分英美经典作家,如艾略特、笛福等,更多的来自欧洲、中东与非洲国家,比如荷兰、俄罗斯、德国、南非等国。库切可以通过这些来自遥远异域的作家与作品来理解自己的生活与时代。不论在哪个国家居住,库切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或外省人,与周围的世界没有任何亲密感。他的研究也多注重那些对于中心区域而言属于外围的作家。在研究里尔克的文评中,库切开篇提到一家英国的著名的读书俱乐部列出的20世纪最受欢迎的五首诗,其中有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相比较其他四首诗的作者:叶芝、艾略特、奥登和普拉斯,库切要研究为什么这位对英国一向无好感的来自异乡的德国人能被英文读者接受。他敏锐地指出,该诗所具有的异域的思辨方式,比如德国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使得这种来自遥远陌生区域的文字,对于英文读者有迷人的吸引力。
库切也在从遥远的国度寻找能让其找到共鸣的作家与作品。马塞卢斯·艾芒兹是荷兰作家、诗人,库切曾经翻译了他的《死后的忏悔》(APosthumousConfession,1976)。从该文集中,库切所写的关于艾芒兹的文评中,可以看出他试图透过异域作家的文字与人生,来思考与感悟自己的生活。库切在广泛阅读之后,指出艾芒兹论文中所产生的观点与其小说的映照:“艾芒兹这一说法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了人类在自己无意识内心冲动面前的无助感;二是强调了人在成长过程中痛苦的幻灭感。《死后的忏悔》中的叙述人名叫威廉·泰米尔。在他身上,这两点都可以找到:他在激情恐惧和嫉妒所造成的苦海中,无助地漂泊着,痛苦地挣扎着;最后一逃了之,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生活轨迹向其揭示的所谓真正的自我,因而变得瘦弱、怯懦而可笑”(库切,2016:51)。库切深刻感受到主人公泰米尔想成为作家又被出版社的退稿打击的痛苦,“作家梦的破灭,可以说是泰米尔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既然没有某种替代方式可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就只好采取直接的行动了。由于内心自我(不管这自我有多么怪异,多么可怜)的表达不足以使他成名,他只得创造一点外在于自己的东西,把这东西拿给社会看,以实现自我”(库切,2016:51)。译者库切本人当时也正处在文学创作的初期,泰米尔的作家梦中也包含着他的作家梦。所以他对主人公泰米尔的观点非常赞赏:“泰米尔声称没法保守得住他那令人可怕的秘密,把自己的忏悔写了下来,作为一座丰碑留给后人,因而使自己一钱不值的生活成了艺术”(库切,2016:53)。库切说在泰米尔身上有作者艾芒兹的影子,我们也可以说,在泰米尔身上也有着译者库切的影子。这部文集既包含库切所需需要的来自蓬莱之处的安慰与灵感,也有库切对各种可能被文论界忽视的异域作家的详细研读。
6.0 文论集Doubling the Point与库切的思辨观
文论集Doubling the Point英文版出版于1992年,是一本形式颇具新意的文论集。文集中既包括库切从1970年到1989年的文学评论文章,还包括大卫·阿特维尔对他的采访。该书出版于文集《白人写作》之后,当时,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他出版一本与南非无关的语言学研究的论文集。库切已经不再打算专门从事语言学研究,所以他并不想出版这样的一本文集。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从他的文评中选出八个主题的论文,请大卫·阿特维尔阅读,并提出一些问题,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他学术文章的进一步的对话。这八个主题分别是:贝克特、互惠诗学、大众文化、句法、卡夫卡、自传与告白、淫秽与文字审查制度、南非作家。该书目前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正式汉译版出现,在有的学术论文中它被翻译为《双角》,但是笔者认为《双重视角》更能表现出库切对该书设计的初衷。库切强调对话的重要性,而这本论文集的优势在于,它通过对话,让库切再次反思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较理想状态。库切在该书访谈部分谈到他的作品与文论关系时,说不论他创作的作品还是所写的文论都是在“讲实话/真理(telling the truth)”②,“因为从广义上讲,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自传:不论是文评还是小说,你写的每一样东西在被你书写的同时也在书写着你本人”(Coetzee,1992:17)。
在库切看来,阅读或创作的本质都是一种无形的翻译,而每种翻译最终就是一种文学批评。尽管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本质给翻译带来问题,“找到这些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部分的解决方案则包含了批评的行为” (Coetzee,1992:88)。库切认为翻译文学文本,只是了解源语言是不够的,译者还必须要了解作者及其作品。用库切作品中所虚构的人物,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话说, “文字研究首先意味着重新复苏真实的文字,然后做出真实的翻译:真实的翻译离不开对文本所产生的真正的文化与历史矩阵的真实理解。我们要理解的是历史文化的基础,文本就来自那样的基础。就这样,语言研究、文献研究(解释方面的研究)、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所有这些研究构成了所谓的人文学科的核心——它们渐渐地相互结合起来了”(Coetzee,2003:121)。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八堂课》中,伊丽莎白对她姐姐说,“各种不同的《圣经》文本一方面很容易会被抄错,另一方面很容易会被译错,因为翻译总是不能十全十美。假如教会还能承认,对文本的解释是一个综合工程,极为复杂,而不是像某些人自己所宣称的,他们能垄断解释权。假如真是那样,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争辩”(Coetzee,2003:122)。
7.0 结语
作为译者,库切认为如果要让译作与原作本身的行文整体风格一致,要与内容保持一致,这就需要译者对整本书的内容透彻理解,知晓原文作者对原文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熟悉,才可能在书名翻译中抓住精华,等效翻译成英文。但他也不反对译者的创造性翻译,以弥补翻译中所出现的缺失。同时,他多年的创意写作成果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翻译,一种他对生活的翻译。跟随着他的文学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他的童年,到青年,再到老年,看他是如何在双语的南非小学求学、去文化宗主国英国寻根,到当时还敞开胸怀的美国寻找自由,游荡于欧美各文化同源国进行精神追索,最后来到他大学时代导师的母国澳大利亚,一个同南非一样处于南半球的国家。此时的库切已经不是那个南非乡间少年,他已经成为一位世界知识分子,用他的文字探究人生的真谛。作为自己人生的导演,他已经在《夏日》中让自己的人生大幕落下,“死而后生”的每一天,都是借来的,他仍然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每日伴着黎明笔耕不辍。世界各地的库切读者在猜测,继《耶稣的童年》与《耶稣的小学时代》之后,“耶稣三部曲”第三部的书名会是什么?
注释:
① 关于库切小说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的翻译也有类似问题。其中“life”一词的含义既可以说“生活”也可以说“生命”这两个意思,所以中文译者只能在两种翻译中取舍。
② truth 是一个难以翻译的词汇,行文中笔者不得不用汉语词汇来表示,但是建议读者不要参考这个汉语翻译,只要思考“truth”本身的多重含义:事实;真相;真理;真实;实话;真实性。
[1] Attridge, D. J. M.CoetzeeandtheEthicsofReading:LiteratureintheEvent[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2] Coetzee, J. M.DoublingthePoint:EssaysandInterview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Coetzee, J. M.Disgrace[M].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99.
[4] Coetzee, J. M.ElizabethCostello[M]. London: Secker & Warburg, 2003.
[5] Kannemeyer, J. C, J. M. Coetzee.ALifeinWriting[M]. London: Scribe Publications, 2013.
[6] 库切. 异乡人的国度[M]. 汪洪章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