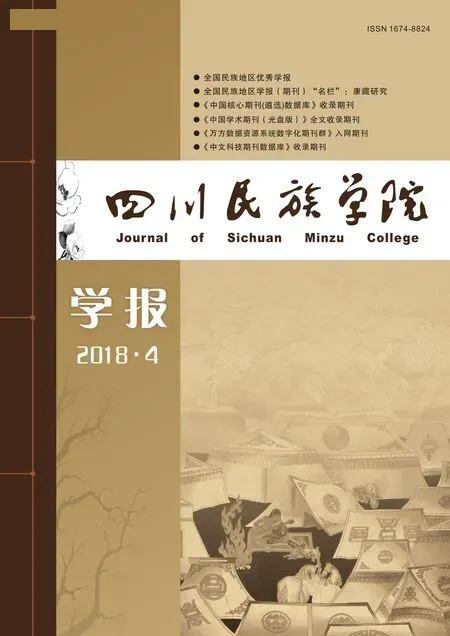21世纪国内藏戏面具艺术研究述评
张丽影
藏戏是我国民族艺术发展中独特的民族剧种,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和传统性的观赏价值。“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反映了藏族人民的能歌善舞,也成为藏族戏剧灿烂繁荣的原因之一,而藏戏面具作为“脸上的艺术”,和藏戏服饰一起成为藏戏发展的重要构成因素,成为藏戏研究中继藏戏历史源流、藏戏剧目、藏戏分类、藏戏传承后又一重要的研究方向。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外对藏戏艺术的关注,藏戏面具的研究更加多样化,下面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藏戏面具的研究成果进行划分。
一、藏戏面具的整体概述
这部分的研究主要是对藏戏面具基础概念性的解读,系统地介绍藏戏面具的历史渊源、面具类别、角色象征等内容。从著作方面看,刘志群的《中国藏戏史》[1]详细地介绍了西藏的面具艺术。书中将藏戏的面具艺术看成是藏戏发展起源和构成因素的重要部分,结合藏族早期原始的图腾崇拜,追溯藏戏历史发展的脉络,将面具分成各种傩面具和宗教面具进行系统介绍。在这之前,由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编,刘志群主编的《中国藏戏艺术》[2]完整的叙述了藏戏的历史源流、剧目流派、面具服饰、非遗传承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将藏戏面具按照样式材质分成平板式软塑面具、半立体软塑面具、立体硬塑面具和立体写实的动物精灵面具。李云在《藏戏》[3]中同样展现藏戏面具的发展脉络、分类和具体的象征意义。张鹰在《藏戏歌舞》[4]中从人物形象入手,介绍人物角色与面具的关系,并以大量图片介绍展示了宾顿巴白面具和温巴蓝面具。李宜、辛雷乾的《西藏藏戏形态研究》[5]从藏戏舞台艺术形态角度重点介绍西藏民间的演变轨迹、分类和象征意蕴,同时别具一格地加入藏戏戴面具演出的优点和不足。她在书中总结了面具的优点:第一,帮助演员进行角色转换;第二,促使观众迅速融入剧情;第三,增加藏戏广场演出效果。同时点出不足:第一,影响演员场上场下交流;第二,影响演员舞蹈动作视觉范围。在学术论文上看,刘勇强的《藏戏》[6]是对藏族藏戏艺术的整体性介绍研究,其中简明的提到了面具作为藏戏艺术最大特色所具有的代表性、类别、材质以及色彩。邢海珍、尕桑卓玛的《藏族面具艺术初探》[7]从历史渊源、分类和艺术特点进行了简要系统的论述。刘志群在《藏戏及其面具艺术辉彩》[8]中细述面具艺术的历史、类别和特点。赵名君的《浅谈藏面具之瑰丽的藏戏面具》[9]同样就藏戏面具的起源、类型、艺术特点和价值逐一阐述。高城的《藏戏的魅力》[10]与刘志群的《中国藏戏艺术》一致,将藏戏面具分成平板式软塑面具、半立体软塑面具、立体硬塑面具和立体写实的动物精灵面具四类,介绍不同颜色的角色象征性,总结出“面具运用象征、夸张的手法,使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和性格更为鲜明突出”是藏戏面具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华热·索南才让的《略论藏戏的面具艺术》[11]提到“面具的出现,正是宗教仪式向藏戏过渡的标志之一,为藏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文中将藏戏面具分成原始祭祀面具、民间表演艺术面具、宗教面具和平板式软塑面具等,并介绍了每个面具颜色的象征意义。陈怡琳的硕士论文《藏戏近几十年来的变迁》[12]中谈到藏戏面具来源于拟兽图腾,并介绍了藏戏面具的分类。林凡的《藏戏的面具》[13]从历史的角度谈到藏戏面具的渊源主要是西藏的击鼓舞,同时将藏戏面具分成温巴面具、人物面具、神怪面具和动物面具。杨嘉铭、杨环的《藏戏及其面具新探》[14]在藏戏发展的基础上整理总结了藏戏面具的形成、类型和艺术特征,并新颖的提出对藏戏平面软塑面具新认识。这阶段的研究,大多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利用纪实照片、手绘图案和表格的形式,大篇幅的展示藏戏面具的样式、人物形象、材质和颜色。
二、藏戏面具的宗教色彩
无论是追溯藏戏面具的历史发展,还是分析藏戏面具中动物面具所蕴含的图腾崇拜,这方面的研究都可以联系到藏戏面具与原始宗教祭祀的关系。对宗教方面的研究,在藏戏面具研究中开始形成一定的独立体系。范文的《藏面具的宗教内涵与美学意向》[15]提到阿坝、西藏地区藏面具的两大主题——人祖和神力,从藏戏面具与宗教神鬼雕塑关系入手,介绍了藏戏面具的类别,并具体的对每种面具进行宗教祭祀色彩的解读。陈霓的《浅说宗教对藏戏的影响》[16]提到藏戏面具中的动物面具,其动物形象就是受宗教中的苯教的影响,是一种图腾崇拜。李昊远的《藏戏面具中的狞厉美与藏族神话的关系》[17]从藏戏面具与藏族神话以及宗教的关系入手,分析藏戏面具所受的影响。冯作辉的《论藏戏的审美精神》[18]中提到了藏戏面具的宗教性质以及藏族面具在祭祀仪式中的作用。王晓莉的《藏族戏剧舞蹈文化中的面具艺术——兼谈藏传佛教与藏戏的关系》[19]一文,以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的《面具的艺术》和京剧脸谱为引子,探讨藏戏面具与京剧脸谱在表现形式、艺术特点等方面的关系,同时介绍面具艺术中的藏传佛教因素。普布仓决的《论藏戏表现形态的独特性》[20]中对藏戏面具的原始形态进行解读,“面具最早是宗教徒用来祭神祀祖、镇鬼镶定的重要道具之一,在祭祀仪式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藏戏不仅沿用了宗教仪式中的面具,而且部分面具保留了其原型意味。”以上研究基本是在藏戏面具本身类别的基础上,探究其与宗教的联系。
三、藏戏面具的艺术价值研究
随着21世纪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起,学界开始对藏戏面具的美学艺术进行大范围的研究。从著作方面看,刘志群在《西藏艺术》[21]中单独从面具发展过程和面具种类及特色中介绍了面具艺术。在对藏戏面具的艺术特色论述时提到:第一,超物象的形式美;第二,“物我两忘、主客融一”;第三,宗教之美;第四,朴拙随意性和怪诞殊胜性。李云、周泉根所著《藏戏》[22]一书重点提及藏戏面具的艺术价值,从面具艺术特点、面具分类、面具人物形象、面具发展渊源和面具存活原因介绍藏戏面具的古老稚拙、瑰丽精致、夸张变形、装饰优美、虚实结合、形神俱现的艺术特点,藏戏面具艺术以其丰富的色彩和大胆的形象设计展现了藏族艺术的审美意识。在面具的分类上按照开场戏面具、正戏面具和动物面具的形式进行介绍。本书新颖地加入对藏戏面具存活原因的探究,结合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分析羌姆跳神面具、牦牛舞面具、卓舞面具、折嘎面具和吉达吉姆面具的现状。从论文研究来看,王宗雪在《藏族装饰艺术的色彩研究》[23]中从藏族整体的色彩艺术入手,提到藏戏面具充满神秘气氛的宗教色彩,系统介绍了面具不同颜色的象征代表性,例如蓝色是勇敢和正义的象征,适合表现勇士;红色象征国王的权力,表示文韬武略、智勇双全;仙翁和忠臣通常戴黄色的面具,它象征忠实,表示功德广大、知识渊博、具足利益众生之心;绿色则是女性的代表,可扮演菩萨的化身;白色是善良的同义词,表示纯洁、温和与慈悲,外道国王、仙人等多戴此种颜色的面具;半黑半白的面具俗称“阴阳脸”,多为阴险狡诈、口是心非的角色所戴。通过色彩的象征性,藏戏面具不但表现了宗教世界的神秘诡异,也表现了人间的喜怒哀乐以及真善美丑,属于21世纪初较早的对藏戏面具色彩研究的文章。张虎生在《西藏文化中面具艺术的色彩象征》[24]中从色彩代表性及象征崇拜性入手, 以西藏文化特别是面具艺术中的色彩象征为例, 剖析了色彩象征思维中存在的两类主要文化逻辑方式, 即对色彩自然属性的归纳法及其将色彩象征进一步社会化和多义化的演绎法。陈映婕、张虎生的《再探西藏面具艺术活态生存的本质》[25],从整个西藏面具的大背景下,谈到面具艺术在寺院和民间两大系统中活态生存的因素,并以雪顿节为个例,介绍了藏戏面具的分类及表演形式。范杨文灿的《藏戏面具前后的两种对话》[26]从独特的视角探寻藏戏面具与信众观众和演员的关系,探究其内在的美学特性:第一,狞厉的造型美;第二,明晰的情感美;第三,蕴籍的宗教美。孔霞的《藏戏面具中视觉语言的诠释》[27]从藏戏面具的历史文化、视觉艺术和应用传承三个方面谈及面具在藏戏文化中的鲜活性,并着重地指出了藏戏面具的宗教性和审美特色中的力度美、世俗美。这类研究以藏戏面具的色彩艺术为重点,结合藏戏面具的分类对角色的象征颜色进行艺术再加工。
四、藏戏面具的比较研究
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产生风格迥异的艺术文化。中国戏曲、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被誉为世界三大戏剧文化瑰宝。中国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泛指,其中国粹京剧和藏戏成为两种比较的剧种形式,如此延伸而来的京剧脸谱和藏戏面具的比较成为了目前学界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谢真元所著的《藏戏文化与汉族戏曲文化之比较研究》[28]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对藏戏面具和汉族脸谱进行了化妆艺术特征的比较,同时分析藏戏面具和羌姆面具的异同。运用比较研究的手法,同时详细论述了藏戏面具的历史源流、分类方式和角色特点,分析藏戏面具经久不衰的原因,在藏戏研究发展中十分新颖。周贵的《藏戏面具与傩堂戏面具之比较》[29]一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手法对两种面具的历史起源、造型以及内涵进行系统的研究。王娟的《藏戏和羌姆中的面具》[30]在介绍四川大学博物馆中收藏的藏族面具基础上简明扼要的分析藏戏面具和羌姆面具的历史和关系,分析藏戏面具中所保留的汉文化。另外还有关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张翼的《藏戏与西方戏剧的比较研究》[31]因藏戏起源早,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传统文化保存完好,遂从文化模式、艺术思维、戏剧结构和美学及审美原则上与西方戏剧进行对比研究,试图为藏戏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参考。
五、藏戏面具的个例研究
我国藏文化分布广泛,除了西藏地区,还有云南、甘肃、青海、四川的藏区盛行着传统的藏文化,因此学界也对单个地区的藏戏面具进行研究。曹娅丽重点关注青海藏戏,在所著的《青海黄南藏戏》[32]中着重从黄南地区的藏戏文化来研究藏戏面具,并提到了面具和涂面这两种藏戏化妆艺术,通过对面具比涂面更古老的认识,追溯到藏戏面具的历史。黄南藏戏面具有自己的特点,按其形态、样式和特点看,具体分成藏族原始祭祀面具、民间艺术面具和宗教面具三种;从形制上看可以分成平板式软绣面具、立体软塑面具、立体硬塑套头面具和立体写实的精灵面具。在面具分类上,较其他著作更为全面。马达学在《青海民间藏戏面具文化之印象》[33]中总结自己之前对藏戏的研究成果,同时指出藏戏面具在青海地区的研究影响尚处空白。文中重点介绍了青海民间藏戏面具的形式及制作工艺,青海藏戏面具文化以藏传佛教为文化载体,因此还论述了青海民间藏戏面具的内涵及其宗教精神。钱钰华的《略论贵州地戏面具和藏戏面具的异同性》[34],将藏戏面具和贵州安顺地戏面具进行比较研究,探究其文化内涵的异同性,从审美特征、艺术手法、民族特征等方面具体比较。岳岚的《青海藏戏面具的审美探析——以德钦寺的<公保多吉听法>为例》[35]从羌姆与藏戏的渊源关系上,探析青海藏戏面具的色彩审美性和面相审美性,阐述藏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审美理念。值得一提的是,袁碌玉在《安多藏戏的艺术处理措施研究》[36]中对于安多藏戏面具一笔带过,称面具在安多藏戏的表演中已经不常见了,只是在进行神话剧的时候对人物的面部进行简单的化妆。除了以地区为个例,还有按照藏戏剧目进行研究,强巴曲杰、次仁郎杰所著《西藏传统戏剧——阿吉拉姆艺术研究》[37]以传统藏戏阿吉拉姆为研究个案,具体介绍了阿吉拉姆戏剧中国王、皇后、魔女等形象所戴的面具,进一步分析了每个人物形象特点和面具样式、色彩的契合度,以小见大的体现整个藏戏面具的代表性。
六、藏戏面具的传承发展研究
藏戏面具的继承、发展和改革是我们现阶段必须思考的课题,结合文化产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下实现对藏戏面具发展的保护研究,是本世纪研究的一个亮点。张如画在《民间艺术中“脸”的表现形式》[38]中,将“脸”比作中国原始艺术的表现语言,列举了传统京剧脸谱、贵州傩戏、藏戏面具的形态表现,具体介绍了藏戏面具的羌姆面具、悬挂面具和藏戏面具三大类型,同时提到了藏戏面具艺术所肩负的宗教功能。文末创新地加入对所有传统民间文化中的“脸”的传承保护模式。王嘉在《藏戏面具的产业发展》[39]中关注藏戏面具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在阐释藏戏面具的发展、类型、制作工艺、艺术特色基础上,探寻面具艺术文化产业的两个支撑点:第一,面具艺术定位的转变和对艺人的保护;第二,政府的文化政策的有力支撑。闫社霞、杨瑞洪的《藏戏面具艺术特征与旅游纪念品开发策略》[40]从传统文化向现代产业转变的视野,深度挖掘藏戏面具的文化意义,重视传统面具文化的艺术特征传承性,提高藏戏面具的创新点。
余 论
综上所述,随着大众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视,同时藏戏被列入国务院、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1世纪国内学者对藏戏面具艺术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全面,除了大部分对藏戏面具整体情况的研究介绍,还涉及到宗教学、艺术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文化产业学等领域,利用多种视角为藏戏面具甚至整个藏戏艺术的研究扩展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藏戏面具的艺术特征、色彩象征性的研究较为丰富,且有相关著作类成果。文化产业方向的研究还刚刚兴起,在日后的研究中还应该多加大力度联系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领域,使藏戏面具研究做到产学结合,有利于未来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