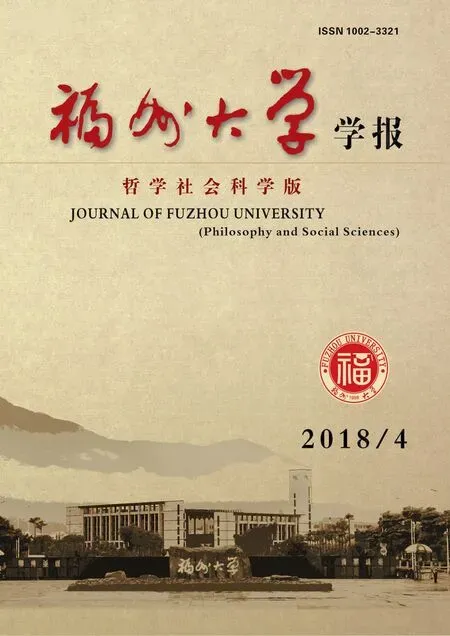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主义哲学看《天主实义》英译本几个重要术语的翻译
胡翠娥 冯婷婷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一部护教性著作,该书首次印刷于1604年,一直到1938年都不断再版,是所有基督教中文著作中读者最多的一部。[1]虽然是一本中文著作,但是正如谢和耐所说,该书“几乎每一页中都使用了繁琐哲学的范畴和推理。动力因、形式因、质料因和目的因,植物的、感觉的和理性的三种生命、恩培多克勒的四大元素、三种内涵、七种同一形式等,所有这一套哲学用语都可以推断和呈现宇宙的一种合理的、结构严密的和最终的形象”[2]。显然,利玛窦在撰写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如何用中文表达西方经院主义哲学的概念、术语和思想,也就是翻译的问题。目前国内从翻译角度对《天主实义》所做的研究,仅限于如何用中文翻译西方术语,也就是翻译名义问题,而讨论最多的是用“上帝”一词对译基督天主教中唯一的人格神。[3][4][5][6]《天主实义》曾先后被翻译成满文、韩文、越南语、法语(1811)和日语(1971)。1985年,台北利氏学社出版了由Douglas Lancashire和胡国桢(Peter Hu Guo-Chen)翻译、马爱德(Edward J. Malatesta)编辑的汉英对照全译本TheTrueMeaningoftheLordofHeaven,这也是第一个英译本。目前还没有出现对英译本的专门研究。本文愿抛砖引玉,就《天主实义》英译本中的重要哲学和宗教词汇的翻译和理解做一个比较文化学上的分析与探讨。
一、原书和英译本简介
《天主实义》共八篇,第一篇论天主,第二篇批驳各家的“万物之原”说,第三篇论灵魂,主张人的灵魂不灭,第四篇论人的灵魂与鬼神不同,万物与天主并非一体,第五篇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论述天地万物的创造是为给人用,不必戒杀生,并述斋戒的目的,第六篇论为善避恶要有“意志”,并论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第七篇论人性本善,区分性善和习善,做人修德需下功夫,第八篇介绍西方世界组织状况,说明耶稣会士终身不娶的理由, 简述天主救援史,说明入教手续。
《天主实义》自1604年初版以来的四百多年里,出现了很多版本和重印本。重印本大多或依据初版,或依据1607年的杭州燕贻堂本。英译本TheTrueMeaningoftheLordofHeaven根据的中文原本是1604年的初版,并参考了燕贻堂本。英译本由以下内容构成(依序):(1)出版前言;(2)译者序言;(3)缩略语;(4)译者的概述;(5)《天主实义》汉英对照全文以及注释(包括原本中既有的利玛窦的引言);(6)附录(利玛窦用拉丁文撰写的《天主实义》摘要);(7)书目;(8)中国古代典籍索引;(9)插图。
如果用中国佛经翻译中的术语来概括《天主实义》英译本的总体风格,那就是“敬顺圣言,了不加饰”的直译,忠实、严谨、流利。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哲学和宗教词汇和术语,翻译和理解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下面专从经院主义哲学出发,试论一二。
二、上帝的“性”“情”和“形”
《天主实义》篇篇是独立的,可是整体看来,利玛窦有其编辑方针。这方针可以用今天的整个神学思想结构来说:首论天主,后论人。[7]之所以把论证天主的存在放在首篇,是因为利玛窦秉承了托马斯自然神学传统。因为在托马斯看来,关于神学问题的理性真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关于上帝自身的问题,例如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属性(诸如现实性、单纯性、完满性、善、独一性、无限性)、上帝的理智、上帝的知识、上帝的意志、上帝的德行和真福等。其次是创造问题。再次是天道问题。[8]可见,第一篇关于天主存在与属性的问题是理解整个《天主实义》内容和主旨的基础,更是西方教会论证天主存在的哲学基础。
在《天主实义》第一篇“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中,利玛窦自觉运用了托马斯的否定排除方式来论述上帝的属性:
盖物之列于类者,吾因其类,考其异同,则知其性也;有形声者,吾视其容色,聆其音响,则知其情也。有限制者,吾度量自此界至彼界,则可知其体也。若天主者,非类之属,超越众类,比之于谁类乎?既无形声,岂有迹可入而达乎?其体无穷,六合不能为边际,何以测其高大之倪乎?庶几乎举其情性,则莫若以“非”者、“无”者举之;苟以“是”以“有”,则愈远矣。[9]
译文:
Because things fall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I can determine their dissimilarities and similar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se categories, and thereby know thenatures of things. I can see the forms and hear the sounds of those things which possess form or sound, and thereby know their natures. Things which are limited can be measured from one boundary to another, and one can thereby come to know their physical size. The Lord of Heaven, however, transcends all categories, and does not belong to any common category. To what category, then, can He be compared? Since the Lord of Heaven has no form or sound, by what traces can He be apprehended? His substance is inexhaustible and the material universe cannot contain Him within its boundaries. How then can one discover a clue as to how great He is? If one wishes to give some indication as to His nature, one can find no better way to do so than by employing words like “not” and “lack”, because, if one uses words like “is” and “has” one will err by too great a margin.[10]
利子说,属于某一类的事物,可以通过比较与它类事物的异同,而了解其属性。同为有形有声的一类事物,可以通过分辨它们的容色和声音,而了解各自的差异。有边界的物体,可以通过度量边界而了解它们的形体大小。但是天主不属于任何类,无迹可循,也无法通过比较同其他事物的差异而认识它。因此,只能通过否定和排除的方法,以示它同万物的区别。关于否定认识法,托马斯·阿奎那曾提出,研究上帝的实体主要应该运用排除法。因为上帝的实体是无边无际的,超越了我们理智所接触的一切形式,所以运用思考我们不可能认识上帝“是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些关于他“不是什么”的知识。关于他“不是什么”,我们的理智能排除得越多,我们就越接近认识他。我们在认识事物的定义时,首先把它们归入一个属(genus)中,认识它们的共性是什么,然后列举种差(differentia),一一加以区分。这样就对事物的实体有了完美的认识。然而,在研究上帝的实体中,我们不可能知道他是什么,例如他属于什么属。我们也不可能用肯定的种差来说明他同其他事物的区别,我们必须用否定的种差去认识他。例如我们说,“上帝不是偶性”,则把上帝同一切偶性区别开来了。然后,我们又加上一句,“上帝不是有形物体”,我们便把上帝同某些实体区别开来了。这样,按照各式各样的区分,即通过诸如此类的否定方法,认识到他有别于所有的一切,对于他的实体就有了独特的认识。[11]由此可知,利玛窦先说“吾因其类,考其异同,则知其性也”的“性”,就是托马斯所谓同类事物的共性,或者说“类属”,拉丁原文是“genus”;而利玛窦后说的“有形声者,吾视其容色,聆其音响,则知其情也”之“情”,就是托马斯所说同类中各事物的“种差”,拉丁原文是“differentia”。英译没有区分性与情的外延,不加区分地都翻译成“nature”(性质),失去了利玛窦原著中的严谨。考虑到经院主义哲学中对于上帝的大量论述,不妨把“性”翻译成“generic nature”,把“情”直接译成“difference”。
利子原著中的“形声”之“形”顺应了中文语境和传统,意指可感知可看见的物体之外形。英译本译为“form”,粗粗一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在自柏拉图以来到中世纪的哲学传统中,“form”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意义。在柏拉图哲学里,“form”(形式)又称为“idea”(理念),是与可感知可变化的事物相对立的永恒存在,只能通过理性才能把握。亚里士多德在修改柏拉图的“理念”论时,引入了“质料与形式”说,认为正是凭借形式,质料才成为某种确定的东西;形式赋予质料或物体以存在意义。例如,他告诉我们,灵魂是身体的形式,这里的“形式”并不意味着“形状”。[12]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有专题讨论过上帝的性质问题,例如在第一集第1卷第3题第2条“上帝是否由形式与质料组合而成”中,“质料”与“形式”分别用拉丁语“materia”和“forma”表示。阿奎那认为,在由质料与形式组合的事物中,形式决定了该事物的本质,但该事物还包括本质之外的东西。例如,定义人之为人的本质东西是人性,也即,人性意味着人之所以为人。但是,除此之外,人还包括人性之外的其他偶性,诸如肉体、骨头、皮肤黑或白等。在这里,人性意味着人的形式部分,对个体化的质料来说,它就是定义的原则。因此,人自身还包含着“人性”所不包含的东西,因而人同人性不是完全同一的。但是,上帝不是由质料与形式组合的,只有形式,没有质料,可见上帝就是他的本质。[13]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利玛窦此处所说的“形声”之“形”,绝非经院主义哲学中规定一事物的本质和作为事物定义原则的“形式”,恰恰相反,它是可感知可测量的“形体”。而在《神学大全》第一集第1卷第3题第1条“上帝是否是一个形体”中,阿奎那的回答是:“上帝绝对不是一个有形体,”因为“形体是那种具有三维的东西。”[14]在这里,“形体”的拉丁文是“corpus”。了解了“form”在经院哲学中的形上学内涵和传统,以及“形式”“质料”和“形体”的确切意义之后,则可以断定,《天主实义》中的“形声”之“形”,当为有形的物体,译为“corpus”更加准确。
三、一“理”多义: 不同的人性论
《天主实义》第七篇“论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门士正学”论述了什么是人性和人性本善:“夫吾儒之学,以率性为修道。设使性善,则率之无错。若或非尽善,性固不足恃也,奈何?”[15]显然,中士的提问借用了《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但是,他对于人性是善是恶,并没有定论,从提问的方式上看,似乎人性有善有恶,人性本善,则可以率性,人性若本不善,率性就不妥。对此,西士给予了详尽的解答。西士认为,要了解人性是否本善,须先了解什么是性、什么是善恶、什么是人性,之后才能回答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什么是性?利玛窦的回答是:“夫性也者非他,乃各物类之本体耳。曰各物类也,则同类同性,异类异性。曰‘本’也,则凡在别类理中,即非兹类本性;曰‘体’也,则凡不在其物之体界内,亦非性也。但物有自立者,而性亦为自立;有依赖者,而性兼为依赖。”[16]利玛窦同样运用了阿奎那对于“性”的类本质规定。托马斯认为,在由形式和质料组成的事物中,本性或本质必定区别于这个个体,因为本质或本性本身仅仅由关于那个种相的定义中所包含的东西构成。[17]利子所说人性之“性”,乃形上学中一个存在者的本性和本质存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利玛窦的论述也秉承了经院主义哲学思想,即不是从道德上界定,而是从本体论和实在论上界定:“可爱可欲谓善,可恶可疾谓恶也。”[18]对于“爱、欲”在这里的含义,有论者从传统儒家人性道德体系中寻找对应的解释,例如张晓林就认为利子的善恶观与告子的人性论相接近:告子以“生之谓性”,以“食色”为性,所谓“食色”即人之基本生理欲望,人之饮食男女之爱欲。[19]显然,张晓林把利玛窦所论的“爱欲”理解为人的基本生理欲望。也有的把“爱、欲”等同于儒家的“喜怒哀乐好恶”等“情”。然而,托马斯的经院主义哲学思想有关于“善”的一整套不同话语。善是一种存在,“善和存在从实在方面看是一回事。”善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可意欲性,即“可爱可欲”。“善的本质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意欲的(appetibile)……因此,哲学家在《伦理学》第一卷中说:善的事物乃为所有的人所意欲的东西。”[20]“万物,既然意欲它们自己的完满性,也就意欲上帝本身,因为万物的完满性同上帝的存在有非常多的相像。”[21]在回答“是否每一个存在都是善的”这一问题时,托马斯认为:“每个存在,作为存在,都是善的。因为,每个存在,作为存在,都是现实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完满的,而完满性则蕴涵着值得意欲性和善。”“存在之被说成是恶,并不是就其为存在而言的,而只是就其缺乏存在而言的。因此,一个人之被说成是恶,乃是由于他缺乏高尚的存在。而一只眼睛之被说成是恶的,乃是因为他缺乏看清楚事物的能力。”[22]而且,上帝是至尊至善的。上帝作为第一活动主体,他的目的仅仅在于传达他的作为善的完满性,而每一个受造物都致力于去获得它自己的完满性,这种完满性只不过是上帝的完满性和善的类似物。所以,上帝的善是万物的目的。[23]
在清楚了何谓“性”,何谓“善、恶”之后,利子对何谓人性,做出了明确的答复:
西儒说“人”云,是乃生觉者、能推论理也:曰生,以别于金石;曰觉,以异于草木;曰能论理,以殊乎鸟兽;曰推论不直曰明达,又以分之乎鬼神。……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后,以其险验其隐,以其既晓及其所未晓也。故曰能推论理者立人于本类,而别其体于他物,乃所谓人性也。仁义礼智,在推理之后也。[24]
译文:
Western scholars define “man”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He is [a creature] who has life and awareness, and who is also capable ofreason. …When man is said to be capable of reason but not of immediate comprehension, he is distinguished from spiritual beings, because spirits have a thorough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things. …[Western scholars] therefore say that the capacity to reason established man in his own category; that it distinguishes man from all other things, and that it is that which is called human nature. Humanity, righteousness, decorum, and wisdom are subsequent to the capacity to reason.[25]
利玛窦从人与金石、草木、鸟兽以及天使的类的区别中规定人性,把人性定义为人的理性推理能力。利子的人性定义,充分反映了托马斯主义的人性观。根据托马斯的观点,人性本身即仅仅由人的定义中所包含的所有东西构成,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此;而人性所意指的,也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个体性的质料,连同所有个体化的偶性(accidentibus),并不包含在这个种相的定义之中,例如特殊的肉、骨头、黑色或白色等等偶然性质,均没有囊括进人的定义中。不过,虽然它们没有包含到人性之中,却属于构成一个人的东西。因此,构成一个人的东西要比人性中所具有的东西多些。因此,人性与一个人不是一回事,人性被用来意指人的形式方面。[26]
既然规定了“人性”的本质规定是“能推论理”,也就是“理智”,那么为何“理智”是善的呢?利玛窦的回答是:“释此,庶可答子所问人性善否欤?若论厥性之体及情,均为天主所化生。而以理为主,则俱可爱可欲,而本善无恶矣。”[27]学界有不少人指出,利玛窦此处援引的是“天主赋性论”。例如张晓林认为,根据基督教创世论,人的灵魂及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人的好恶情感等,都是由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时赋予人的。创造者是绝对的善,所以,被造者的性情也应当是本善无恶的。[28]同时,根据托马斯的观点,人的终极幸福在于他的最高活动,亦即理智活动,如果受造理智永远不可能见到上帝,那就会要么永远得不到幸福,要么其幸福将在于某种上帝之外的事物,而这却是反乎信仰的。从基督教神学的目的论来看,万物都意欲自己的完满性,也即上帝本身。人凭借理智而见到上帝的本质符合对完满性的追求,因而是善的。[29]
紧接着,利玛窦批评了程朱理学中以理为性的学说,认为理学中的理,不能成为规定人性的形式方面:
“理”也,乃依赖之品,不得为人性也。古有歧人性之善否,谁有疑“理”为有弗善者乎?孟子曰:“人性与牛犬性不同。”解者曰:“人得性之正,禽兽得性之偏也。”[30]
译文:
“Reason” itself is accident and cannot be said to be human nature.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were divided ov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human nature is good or not; but who would doubt the goodness of reason? Mencius asserted that man’s na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natures of oxen and dogs. Some have explained this by saying that man received nature in all its uprightness, whereas animals received it in its obliqueness.[31]
应该注意的是,此处作为依赖之品、非自立之品的“理”,与利玛窦规定人性本质的“能推论理”之“理”不是同一个概念,分别代表程朱理学和天主教对人性的不同规定,它们互相排斥。“理学”之“理”是仁义礼智之性理。利子明确说出“仁义礼智,在推理之后”,也就是,仁义礼智至少不是对人性的第一规定,更由于“仁义礼智”之“理”,不能独立存在,因此不能作为人性的根本。事实上,在《天主实义》第二篇“解释世人错认天主”中,利子对于新儒家把太极作为万物之原的说法就予以驳斥。新儒家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32]但是利子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万物分成自立体和依赖体:“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赖者。”[33]不依赖别体而能自立的,是自立者,例如天地、鬼神、草木、金石、四行等;依托他体而存在的是依赖者,例如五常、五色、七情等。自立者先于依赖者,也比依赖者更尊贵。利子得出结论:“若太极者,止解之以所谓理,则不能为天地万物之原矣。盖理亦依赖之类,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34]太极之理,属于依赖者,不能自立,如何为万物之原?利玛窦把“太极之理”划入不能独立存在的“依赖体”范畴,也就合乎情理地否定了程朱理学把太极作为万物之原的思想。英译本在此处译为“principle”,合乎利玛窦的论辩逻辑:
When we come to the Supreme Ultimate we find that it is only explained in terms of principle. It cannot therefore be the source of heaven, earth, and all things because principle also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accidents.[35]
在第425段论述“能推论理”的时候,“理”就是“推理”和“论理”,译者都正确地翻译成“reason”,但是在第426段反驳作为依赖之品的程朱理学之“理”时,此“理”已不再是“推理”和“论理”了,而是“太极之理”,利玛窦把它视为非本质规定的属性,应当译为“principle”,译者却翻译成“reason”,是对概念的混淆,也与第84段的翻译自相矛盾。
《天主实义》虽然用中文撰写,但是由于其中主要运用论述了西方中世纪流行的神哲学思想和概念,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已经是在进行一种“文化翻译”。据此而翻译的英译本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回译。既然是回译,则必然要回到西方中世纪的神哲学背景,力求在整个经院主义哲学话语和术语表达传统中,准确传达原著的思想内容。不过,瑕不掩瑜,《天主实义》英译本在思想和风格上仍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善译和佳作。
注释:
[1][2]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15,409页。
[3] 朱志瑜:《〈天主实义〉:利玛窦天主教词汇的翻译策略》,《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
[4] 冯天瑜:《利玛窦创译西洋术语及其引发的文化论争》,《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5] 戚印平:《“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6] 雍正江:《天崇拜传统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3期。
[7] 胡国桢:《简介〈天主实义〉》,《辅仁大学神学论集》2012年第56号。
[8][14][17][20][21][22][26][29]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第1卷,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译者序言,第40,46,72,88,77-78,46-47,160页。
[9][15][16][18][24][27][30][33][34] 梅谦立:《天主实义今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5,421,423,424,425,428,426,83,84页。
[10][25][31][35] Ricci, Matteo,TheTrueMeaningoftheLordofHeaven, trans, 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Hu Guo-Chen, St. Loui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with the Ricci Institute Taipei, Taiwan, 1985, pp. 55, 425, 426, 84.
[11][13] 赵敦华、傅乐安主编:《中世纪哲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479-1480,1333-1334页。
[12] 罗 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6页。
[19][28] 张晓林:《〈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135-136,137页。
[23]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集第3卷,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75页。
[32] 朱 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