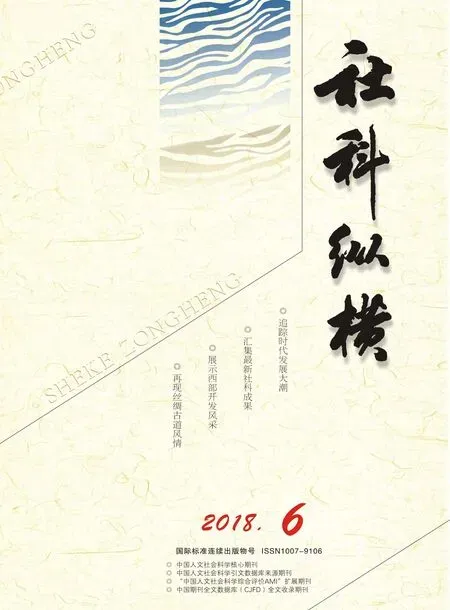论魏晋南北朝诗歌“正变”批评的审美化转向
胡吉星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68;泰州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正变”批评是古代诗歌批评的重要原则。“正变”批评主要通过论述诗歌的产生时代、诗歌创作技法、诗歌的发展史观、诗歌创作主体的身份、诗歌的体裁、诗歌的流派归属等,来辨析诗歌的正体与变体,从而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接受提供某种价值尺度。先秦两汉诗歌正变批评主要以伦理批评为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正变批评则呈现向审美转化的倾向,这种转向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在诗歌形态方面,改变以往以四言诗为正的观念,开始肯定五言诗的创作;二在诗歌本质方面,从言志转向缘情;三在诗歌语言上,由推崇实用转为主张绮靡,加强了对诗歌形式美的研究和实践;四在诗歌发展观念上,由崇正转向崇变。导致审美转化的主要原因是儒家经学思想的式微;玄学、儒家思想兴盛,从而导致了审美意识的自觉。
一
魏晋南北朝的“正变”批评呈现出审美化倾向,其表现之一即体现在对诗歌形态的认识上。先秦两汉时期是古代诗体变化的重要时期,两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杂言、骚体诗等诗歌形态都出现了。四言诗在先秦两汉时期被认为是“正体”,其原因:一是由于其诗体本身特征使然,即四言诗在章法结构上讲究反复咏叹、回环复沓,在用语上则是文辞从容、含蓄典雅等。叶嘉莹先生就指出了一点,她在《中国诗体之演进》中说“一句中字数若少于四字,其音节则不免会劲直迫促,不像四言那样有从容顿挫的韵致。”[1](P1)二是因为四言是《诗经》的语言形式,《诗经》又是儒家经典,宗经意识也导致了先秦两汉时期“以四言为正”。正因为以上原因,四言诗常被汉代士人用作讽谏颂美、宣扬道德教化的诗体。如西汉时期四皓的《紫芝歌》、《采芝操》,韦孟《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自劾诗》、《戒子孙诗》以及司马相如的《封禅颂》、焦延寿《焦氏易林》中的四言韵语等;东汉班固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东平王刘苍的《武德舞歌诗》,傅毅的《迪志诗》,刘珍《赞贾逵诗》,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桓麟《答客诗》及客之《客示桓麟诗》等诗作,都采用了四言诗体,这些诗作内容是儒家政治伦理教化思想的反映,或祭祀神灵,或歌颂祥瑞,或自勉答赠,或程述圣德,总之离“雅正”不远。
不仅先秦两汉时期在诗歌创作上以四言诗为“正体”,而且在诗学观念上也以四言为正。汉代的《毛诗序》和《诗谱序》就提出了“风雅正变”说。“风雅正变”说基于诗教目的,以时代盛衰和美刺来划分“诗三百”,将《诗经》中产生于盛世的颂美之称为“正”诗,并将“正”诗视为“正经”。受汉代诗歌正变观的影响,汉代四言诗的写作呈现程序化倾向,以颂美和说教为主,诗歌艺术性较弱。如《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等都是庙堂颂歌或祭祀的乐歌。总之,四言诗在汉代已经开始僵化,所谓“四言在汉,渐呈没泊”,到南朝时则迅速衰落下去。其衰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能满足人们抒情的需要了。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卷二十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世道日降,文句难古,苟非辞意深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而汉末时五言诗已经产生并开始运用在诗歌创作中。尽管五言诗体源自民间乐府,但它甚少教化色彩,也更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更能表现更复杂的情感,故在创作中以不可遏制之势蓬勃发展,如《文心雕龙·明诗》言:“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且出现了“自五言兴,而四言遂少”的局面[2](P2),五言诗也最终成为诗坛的主流。
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文论家在评价五言诗时,已认识到五言诗的长处,认为五言诗是新的发展趋势,纷纷给予积极评价。钟嵘是南朝杰出文学批评家,他在《诗品》中充分肯定了五言这种形式,也突破了那种认为五言为“流调”,四言为“正宗”的保守观念。钟嵘高度评价了五言诗,其《诗品序》言:“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钟嵘认为五言诗的描写景物生动形象,又富有情感,是所有诗作中最富有诗味的。钟嵘还把五言诗盛行原因归结为有滋味,并对“淡乎寡味”的四言诗进行了批评,体现了魏晋南北朝的正变批评审美化的转向。萧子显的观点与钟嵘有共通之处,他认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习玩为理,事久则读,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3]萧子显强调文学的变革性,认为体裁应该推陈出新。刘勰虽也因为五言为流调,但他能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五言诗,提出“清丽”的标准,这与汉儒的角度是不同,所以罗宗强先生认为刘勰“是非常大胆的提法。”[4](P300)他能从审美的角度来评价五言诗,已有以“五言诗”为正体的意味了。
第二,在诗歌本质上从“诗言志”向“诗缘情”转变。“诗言志”始于先秦,被认为是诗学的“开山纲领”,后世儒者假托的《尚书·尧典》中“诗言志”,就是出于此类典型提法,其中的“志”虽然也有情感的成分,但基本指人的志向、理想和政治态度。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赵孟请郑国七子赋诗时说:“武亦观七子之志”,就是要看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孔子论诗的“温柔敦厚”说,荀子阐明诗是“圣道之归”的观点,都是“诗言志”的具体呈现,其目的就是强化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5](P9)。汉代诗论继承了先秦论诗“诗言志”的传统,将诗歌与政治抱负、社会功用等联系起来,认为诗歌是经学的附庸。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强调以诗为教的“诗言志”更成为论诗的主流,也被认为是正统诗学观念。而“诗缘情”则是在魏晋时期出现的有关诗歌本质的另一重要命题。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这一观念的滥觞。虽然“诗言志”的“志”中也有情感因素,但陆机的“诗缘情”之情是诗人个体的审美情感,而非“止乎礼义”之情,强调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成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观点。其后钟嵘所论述的“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主张表现内心的真实情感;而萧纲所谓的“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更是强调写作时可放纵自己的情感,这与儒家传统诗学所主张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不同的。魏晋南北朝还有很多文论家都强调诗歌的根基是人的感情,如挚虞的“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沈约的“以情纬文”,刘勰的“为情而造文”等,“诗缘情”成为该时期对诗歌本质的普遍认识,用朱自清先生话来说,是“用了一个新的尺度”也开创一代之风气,也说明了时人对诗歌本质的新认识。
第三,在诗歌语言形式上,魏晋南北朝诗歌“正变”批评以绮靡为正,而先秦两汉文论则以实用为正,从而加深了魏晋南北朝的“正变”批评审美化特征。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注重语言的实用功能,主张“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辞达”即透彻地表达出思想。基于这样的实用态度,孔子不提倡采用华丽文采,认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以仁”(论语·卫灵公)。孔子虽然也主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但文采其实只是一种手段,是为实用服务的。汉代诗歌语言批评大体沿袭了先秦立场。如西汉扬雄、班固都曾批评汉大赋淫靡华丽的文风;东汉王充更主张语言的质朴与直露,反对“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强调文章为“劝善惩恶”而作,突出文章的实用性。与先秦两汉不同,魏晋南北朝诗论则以语言华丽为正,体现在文学语言的审美诉求。比如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绮靡就是指诗歌语言美丽。而《文心雕龙》中几乎每篇都能见到文、采等字眼,并著有《丽辞》专篇来论述文采。此外,沈约、萧纲、萧统、萧子显等人都从各方面探讨了诗歌绮靡语言的重要性,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着对美丽辞藻追求的倾向,也含有以绮靡为正的意味。
第四,在诗歌发展观念上由崇古、崇正转向崇变,这也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正变批评的审美特征。崇古、崇正是先秦两汉诗歌“正变”批评的重要内容。先秦很多文论家都强调以古人的作品为“正”,认为愈是古代的愈雅正,愈今则愈卑俗。比如孔子一心向往“三代”,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恢复“周礼”。其崇古思想表现在诗论上,即推崇韶武之类的古乐,排斥当下流行的郑卫之声。两汉时期“风雅正变”说则基于政治的治乱、时代的盛衰来划分诗歌的正变,以治世之诗为“正”;以乱世、衰世之诗为“变”。郑玄在《诗谱序》中推崇《周南》、《召南》、《鹿鸣》等周朝早起的诗歌作品,而对周懿王、周哀公时期的周朝晚期的作品则认为是“变风”、“变雅”,具有鲜明的崇正斥变的倾向。与先秦两汉崇古崇正的正变批评观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追求新变,重独创、重新奇也成为了该时期正变批评的主流。相当多的文学批评家认为今胜于昔。如曹丕就批评“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陆机也主张“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崇变”也成为诗歌发展观念的核心内容。萧子显主张“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统认为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强调文学要“随时变改”。在《诗品》中,钟嵘也提到了“变”。钟嵘认为南朝诗人任昉的诗歌为“文亦遒变”,是《诗品》中唯一擢举为中品的诗人。萧纲反对当时以复古为主旨的“京师文体”。他认为作文应该贵变化,重创造,“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梁书·庾肩吾传)刘勰还专门著有《通变》一篇,主张文章应“随时而变”。在这种崇变的风气下,这时期的诗歌体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合理地运用诗歌的音节,追求和谐流畅的音韵美的永明体,也出现了“弥尚丽靡”与“转拘声韵”的宫体诗。
二
导致魏晋南北朝诗歌“正变”批评理论审美化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现实与哲学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在社会现实上,东汉末年发生了“党锢之祸”、黄巾起义等严重的社会动荡事件,这些事件动摇了政治权威,也动摇了儒家思想权威。而魏晋到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不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社会上层争权夺利。其二,在哲学思想上,该时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6](P177)“汉代以来的维护国家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载体的经学被冷落了。”[7](P9)该时期哲学思想表现为儒学的“式微”和玄学、佛学的兴盛。玄学与佛教思想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形态,指导人们以新的观念重新思考人生自然,这既开阔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促进了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同时也促成了“正变”批评的审美倾向形成。
以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正变”批评的影响为例。魏晋南北朝“正变”批评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缘情。而“性情说”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不少玄学家都提及“性情说”,如王弼的“性其情”、嵇康的“任其情”、向秀的“称情自然”等,他们强调追求内在人格、性情的超越和自由,不注重仁义道德、外在事功与社会群体秩序等,个体的自我意识增强了。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审美化转向有重要影响,如在玄学性情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个体的情感空前丰富、自由、活跃,悲情、艳情、闲情等成为情感表现的主要内容,取代了以群体利益作为出发点的颂、赞、美、刺之情,并产生了众多“以缘情为勋绩”的文学作品,如陶渊明就写了被批评为“白璧微瑕”的《闲情赋》,还导致了文学缘情观念的兴起。如钟嵘就认为诗的本质与作用是“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刘勰的《文心雕龙》也强调:“情者,文之经”。
又以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正变”批评的影响为例。该时期正变批评的重要内容是崇变,这又与佛家的传播与兴起有关。清人刘熙载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产生了一些新的佛教观念如“悟性”、“求新”、“遣荡”等。这从哲学的角度开阔了人们的思维想象空间,使得当时士人群体中逐渐形成“每至新异,悕仰奇闻”[8](P271)的心态。范泰曾在书中描述了当时求新的风气:“外国风俗,还自不同……有闻辄变,譬之于射,后破夺先。”[9](P139)正如高文强先生所指出的“面对文化新潮的大量涌入,士人在接受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有闻辄变”、“后破夺先”态度,正是趋新求变文化心态的具体体现。“正是在这一趋新求变的文化大背景下,文学也开始了新变的探索历程,并最终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发展与嬗变。”[10]比如梁简文帝《率尔成咏》:“约黄出意巧,缠弦用法新。”萧子显《南齐书》就认为文学“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认为只有“新”才能扬名于世,而萧纲更是旗帜鲜明地主张作文应该贵变化,其曰“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11]在求新求变的思潮影响下,当时的作家如徐摛、王僧孺的作品是以“新”著称的。又如鲍泉《和湘东王春日》是一首十八句的五言诗,竟用了共三十个“新”字,时人求新求变意识之强烈可见一斑。
佛教影响不仅体现在崇变的思维方式上,还推动了崇丽文学观念的发展,对宫体诗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这一时期佛家兴盛。印度佛经语言华丽,音韵流靡,早期译者常以“失其藻蔚”为憾,如鸠摩罗什曰:“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12](P2405)所以在翻译佛教经典时就以“丽”作为标准。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曰:“(支)越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13](P270)其实从佛教翻译的“绮靡”到文论的“绮靡”主张是一致的。汪春泓先生就认为“很多浸淫于佛教的梁代宫体诗作家,欣赏佛经文字之‘丽’与其属文尚‘丽’,二者是二而一的。信佛的梁代文人作文大多有尚丽的追求。”[14]这也导致了该时期诗歌正变批评崇丽的倾向。同时随着佛教的流传,佛教的讲唱形式和梵文梵呗经声,也影响到时人对四声说的认识,使人们注重诗歌的藻丽音韵,加深了论诗者对诗歌形式美认识。另外“弥尚丽靡”与“转拘声韵”的宫体诗的形成也与佛教关系密切。如《佛本行经》的佛教经典就有很多对女子形态的刻画,如“与众婇女游居品”(第二卷其八)曰:“于是众女,昼夜作乐,嘲调戏笑,过数年已。或娱乐之,更造新术,或现已身,或时书颂,或图庙画,或有刻镂。或有以泥,为若干像。或有结华,以为敷饰,或在面目,或有涂香,或以镜照,或栉梳头,或黛黑眉,或丹口唇。或复有女,华相打掷,或戏笑者,或悲叹泣,或口咏歌。可听可乐,犹如华中,众蜜蜂鸣。”“往到太子前,各进种种术:歌舞或言笑,扬眉露白齿,美目相眄睐,轻衣见素身,妖摇而徐步。”[15](P42)书中描绘了众多神色各异的女性,有的女子搔首弄姿,有的女子妖娆徐步,有的女子伤悲,有的女子喜悦等,这是描绘了佛陀出家前诸宫女诱惑他的情景,各种神情描绘得非常逼真,这为宫体诗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模板。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的时代。尽管“正变”批评的审美化倾向是这一时期正变批评的主流。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诗歌理论领域,仍还有一些坚持儒家正统观念的诗论家。如西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就道:“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挚虞强调四言诗乃“诗之正体”,多用于郊庙歌辞这样的庄重场合,故最为庄重典雅。而认为五言和六言,主要是供乐府演唱使用,至于七言,地位更为低下,是俳谐倡乐供人君取乐的。挚虞这种以四言为正体的正变思想与儒家诗教观有直接的关系,强调诗歌形式与儒家述圣设教的内容相统一。又如裴子野在《雕虫论》中,从儒家诗教说的角度,反对当时绮靡诗风,极力表现出对江左诗风的不满,主张诗歌应为伦理道德服务,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用。另外,刘勰、萧统等人也都在诗论中反对骈俪和华艳,也有崇尚雅正的倾向。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在政治、民族、宗教、哲学和思想上,表面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但在表面之下,其审美文化的发展却有内在的演变趋势。正变作为审美范畴之一,在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是有主流倾向的,这就是朝着审美化的方向发展。
[1]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C].北京:中华书局,1984.
[2]赵翼.陔余丛考(卷 23)[M].台北世界书局,1960.
[3]萧子显.南齐书·列传第三十三[M].中华书局,1972.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中华书局,1996.
[5]朱自清.诗言志辨[M].凤凰出版社,2008.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张立文.玄学思潮的人文语境[J].中州学刊,2013.
[8]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中华书局,1992.
[9]全宋文[M].商务印书馆,1999.
[10]高文强.佛学东渐与宋齐文学观念的雅俗嬗变[J].文艺研究,2013(6).
[11]《梁书·庾肩吾传》,又略见《艺文类聚》七十七.
[12]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3]释僧佑.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汪春泓.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J].文学评论,1991(5).
[15]中国古代文化全阅读:佛本行经[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