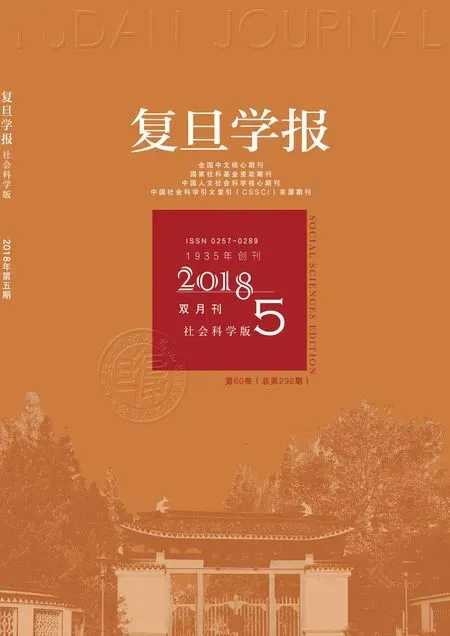暧昧的联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与研究系
马建标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寻常所说的“五四”,一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简称。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又包含两个层面,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中,五四运动是与新文化运动有别的“政治运动”,但新文化运动是促使五四运动的“原动力”。正如梁启超所说,五四运动“本不过是一种局部的政治运动,……则以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故机缘发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此实因果律必至之符”。*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1版。长期以来,五四运动一直是作为一门“显学”而存在的。但是,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倾向。也就是太侧重“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而对五四的“政治运动”研究很少措意。在此种研究风气的影响之下,人们对北洋时期的政治派系与五四运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了解的仍是非常有限。即使以关注比较多的研究系而言,史学界仍是倾向于探讨梁启超的研究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而忽略这一派与五四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相关论述,参见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五四时期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交织在一起,彼此难以区分。今人为了研究方便,才人为地把五四时期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后来者的区分会或多或少地限制我们对五四时期某些关键问题的认识,或者视而不见。如五四时期的研究系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就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在五四运动前后,因时局的变化而导致个体心态的变化,以及他们的历史言说的悄悄转变。
五四时期,蔡元培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并利用这一身份地位积极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达到其教育救国和学术救国的夙愿。然而,五四学潮发生之后,蔡元培即成为众矢之的,这是蔡元培本人始料未及的。很快,蔡元培离职出走,引发北京大学的挽蔡运动。五四运动之后,学生不安心读书,热衷于政治运动,这令蔡元培很痛心。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蔡元培撰文表达了他对学生界的希望:“学生对于政治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1版。五四时期,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和研究系在发动学生运动上,也曾有过一段“暧昧”的合作。这段历史在五四运动之后,由于时局的变化,研究系与北京大学都含糊其辞,故而成为一段被当事人有意遮蔽的历史,延续至今。
一、 暧昧的交集:五四前夕的研究系与北京大学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以1915年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为标志。不过,新文化运动力量的集结却是开始于1917年蔡元培履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同年陈独秀主掌北京大学文科。蔡元培和陈独秀是推动北京大学文科学术思想革新的领袖人物,并由北大文科学风的转变而带动北京大学整体学术思想的转变,从而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风靡全国。
谈及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人们自然想到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实际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有所侧重的,也就是重在“援引思想先进、用心改革文化教育和致力整顿社会风气的志士”。*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3页。虽然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扬言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大学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的机关,似乎与政治无涉。*《复吴敬恒函》(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2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10页。实际上,这不过是蔡元培掩人耳目的说辞,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整顿教育来刷新中国的政治风气,美其名曰“教育救国”。换言之,此时的蔡元培有明暗两种身份认同:公开的教育家和心底的革命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北大新文化学人,如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一样,在发动新文化运动时都怀抱一个“群体性的自我意识”,也即“政治”。*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85页。简言之,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学者群的政治关怀使他们与梁启超所领导的研究系成为潜在的盟友。
如果说北大新文化运动学者群是“在学言政”,而来自政界的梁启超研究系则是“在政言学”,由此构成了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学者群与研究系的交集。梁启超是研究系的精神领袖,这一系的核心成员还有张东荪、林长民、蓝公武等人。作为两方阵营的领袖,蔡元培与梁启超同属戊戌维新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拥有科举功名,共同的知识文化结构和时代经历增强了蔡元培与梁启超的相互认同感。至于略晚他们一辈的北大新派学者,如陈独秀、鲁迅、沈尹默等人早年也深受梁启超文章的影响。尽管研究系诸人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政治活动,但他们也著书立说,属于政界中的文人。研究系群体的学者气质也使他们与北京大学新派学者惺惺相惜。研究系一派不同于皖系、交通系、安福系等纯粹的军阀政治派系,他们在搞政治的同时,也高谈社会改造,使其成为中国政界中的另类。故而在时人的记忆中,梁启超的研究系即使在积极从政的时候,也给人一种“抛弃政治,只谈社会改造”的错误判断。如五四亲历者常乃悳所言,“民四、民五,正是政治上黑暗的时代,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已主张抛弃政治,专从社会改造入手”。*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4页。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梁启超一派在1915和1916年非但没有远离政治,而且在密谋发动护国运动,堪称影响时局的关键人物。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五四前夕的北京大学师生与国内政界实际上在刻意保持一段距离,其原因是那时的政界风气败坏,尤其是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所奉行的亲日政策更是引起学界的不满。当时的北大学生张国焘批评说:“当前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4年,第43~44页。北大师生这种与党派自我区分的心理,也恰好反映了北京大学“自成势力”的集团意识的觉醒。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作为一种“集团势力”异军突起,更是增强了北京大学师生的集体认同感。*北京大学自成集团的意识,是相较于其他社会各界而言,然就北京大学教师群体内部而言,其派系分野依然是存在的,如北京大学民国初年就有桐城派和余杭派之争。关于北京大学的内部派系问题,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5~716页。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致胡适》(1921年),《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1页。李大钊这句话写于1921年,其时他已经对梁启超的研究系表现得非常不满。但是,时光倒退到五四爆发前一年,李大钊所属于的北京大学新文化派学者群的确与研究系的关系很密切。
五四运动前,研究系之所以能为北京大学师生所接纳,一个主要原因是研究系自1917年年底被皖系军阀排挤出北京政府之后,暂时停止政治活动。研究系的两大领袖,梁启超专心“著书”活动,汤化龙则是“出洋考察”。*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12页。无心插柳柳成荫,此时政治上失意的研究系却无意中发现北京大学新文化派是一个政治潜力无穷的集团。而研究系表面上的“弃政从文”自然也拉近了他们与北大新派人物的距离。虽然胡适内心鄙视研究系蓝公武、林长民等人的活动,认为那不过是“政客行为”,但他却很敬重梁启超,经常与梁氏讨论学术问题,还把他本人和梁氏都归为“几个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240、472、544、676、775页。总体上看,在北大师生眼中,当时的政治派系都是一团的黑暗。如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所言:“当这个乱昏昏的中国,法律既无效力,政治又复黑暗,一般卖国贼,宅门口站满了卫兵,出来坐着飞也似的汽车,车旁边也站着卫兵。市民见了,敢怒不敢言,反觉得他们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毅(罗家伦):《什么叫做“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1919年5月26日,第23号,第1版。相较而言,研究系多少算得上是政界中的一股清流。胡适就认为,研究系的林长民和汪大燮等人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开明的政治家”。*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1935年5月5日,第149号,第7、7页。而且,胡适还曾对北京学生界宣扬,他与研究系“有些老交情”。*《张梵致胡适》(1922年7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8页。这一切都说明了研究系与北京大学的关系非同一般,是其他政治派系望尘莫及的。
在五四前夕,研究系与北京大学新派师生愈走愈近,客观上还由于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首先,北京大学新派师生和研究系都把掌权的北洋军阀政客如皖系、安福系和交通系视为共同的政治对手。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发表公开演说,劝诫皖系军阀为代表的强权派们改邪归正,他说:“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其次,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大学新派学者与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此时都信奉威尔逊主义,共同的信仰让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与研究系在五四前夕结成了政治盟友。如胡适所说:“蔡先生和当日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1935年5月5日,第149号,第7、7页。
除了双方志趣的相投之外,五四前夕,北京大学与研究系的结合,也是一种有组织观念的“集团势力”养成的结果。梁启超的研究系不过是顺水推舟,巧妙地借助了北京大学的现成势力。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北京大学校园已经出现“组织化”、“媒介化”的端倪。在教师群体中,有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派;在学生中,有新潮社、国民社等学生组织,并且还有自己的出版物,表示其主张。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校园生活的组织化和媒介化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现象,乃至引起胡适的注意,他说:“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而且胡适本人在1919年内就“收到各种学生刊物400余份之多”。*《五四运动:胡适之在光华大学之演词》,《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8年5月10日。学校里既然有了如此普遍的社团组织,客观上自然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像研究系这样嗅觉灵敏的政治团体自然也会注意到。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是一位资深的政治活动家,他认为组织学生势力从事政治运动是一种政治常理,没有什么愧疚感。即使到了1925年,此时梁启超已经淡出政界多年,他仍然毫不迟疑地认为:“人类是政治动物,参与政治是人类普遍的职责,学生也是人类,为什么不应参与?”*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第132页。在此种观念的指导下,研究系在五四运动前是在有意识地拉拢北大学生。胡适就注意到,“进步党人(研究系),特为青年学生,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辟立副刊,请学生们自由发表意见”。*《五四运动(续):胡适之在光华大学之演词》,《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8年5月11日。
研究系与北京大学的交集,还表现在组织的建立上,此即蔡元培校长与研究系共同发起的“和平期成会”。*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和平期成会的前身是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组织的“和平促进会”,由于该会被安福系所攻击,于是研究系的徐佛苏提议改为“和平期成会”,研究系的熊希龄和北大蔡元培担任正副会长。*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574页。此外,研究系还与蔡元培发起了“国民协会”,核心人物是研究系的汪大燮、熊希龄,而背后的支持者则是大总统徐世昌。*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4574页。这些联合组织的建立,说明研究系与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已经实现了跨界的组织联合。
二、 有远见者:研究系、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欧战行将结束之际,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威尔逊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和平运动的思想武器。当徐世昌在1918年9月11日通电就任总统之后,*《专电》,《申报》1918年9月13日,第2版。梁启超立即上书给徐世昌献计,建议徐世昌“旗帜鲜明地宣誓裁兵,外交重心应由日本转向欧美诸国”。*《梁启超上徐世昌签呈并函》(1918年9月15日),郭长久主编:《梁启超与饮冰室》,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67页。威尔逊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影响,就是威尔逊总统特意选择在191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致电中国总统徐世昌,劝告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To Hsu Shih-Ch’ang”, October 10, 1918, in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1(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292- 293.根据威尔逊总统的建议,徐世昌在当月25日发表了和平命令。*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1918年11月22日,北京公使馆的英美法日意等国代表召开外交团会议,支持徐世昌的停战决定;美国公使芮恩施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主张“只有重新统一的中国才能得到列强的支援”。*芮恩施著,李抱宏等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8~249页。
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原先宣称绝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参与了和平运动,他与研究系的熊希龄一同发起了和平期成会。*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8卷,第286页。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其中有言:“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第138页。蔡元培这一天的演说,也被胡适视为“北京大学走上干涉政治的路子”的开端。*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1935年5月5日,第149号,第7页。在反对垄断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问题上,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师生与研究系的目标是一致的。简言之,反对皖系军阀领袖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是学界领袖蔡元培与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进行合作的政治基础。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研究系洞察国际时势,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们重返政治舞台的千载良机。他们认为:“此次欧洲和平会议及将来国际联盟会关于国际间一切处分均以民族自决为前提,我国民亟应组织团体,合全国人民悉心研究,表示真正民意态度,与国际间足为政府之后援并以增进我国国际间之地位。”*《国民外交协会纪事》,《晨报》1919年3月1日,第6版。此时,研究系以“国民外交”的名义,干预政治。1919年初,梁启超在国际税法平等会发表演说,鼓吹:“当此国民外交之时代,凡事之行,固在政府,而所以独裁政府者,则在国民审查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政府后盾。”*《梁任公在国际税法平等会之演说词》,《东方杂志》1919年2月,第16卷第2号,第166页。
国民外交协会是研究系主导下的在其他社团基础上的再联合。1918年12月,研究系下属的国民外交后援会与和平期成会、财政金融学会及兰社等集会讨论时表示,“各愿负始终不懈联络各团体共同组织之责”。研究系首领梁启超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发表公开演说,进行鼓吹。*许冠亭:《试论五四前后的国民外交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一〇年代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29页。1919年1月26日,上述团体中的核心人物如蓝公武、梁秋水、邵飘萍等开会决定,以“国民外交协会”作为正式名称,并决定自2月2日以后,每周一三五日上午开常会。*《国民外交协会纪事》,《晨报》1919年3月1日,第6版。2月16日,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外界宣布成立。成立后的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是张謇、熊希龄、王宠惠、严修、林长民、范源濂、庄蕴宽等七人。*《国民外交协会纪事》,《晨报》1919年3月1日,第6版。
一战之后新的国际形势,是刺激研究系成立国民外交协会的重要国际因素。所谓“天相中国,既予以千载一时之机,则求振国权,时不可失”,而成立国民外交协会则是把握此千载良机的重要手段。研究系也坦然承认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是为了“博采舆论,集合众议”,就是说国民外交协会的职责是为了进行舆论动员,凝聚力量。由此可见,研究系是把国民外交协会视为一种重要的参政手段,只不过是借助国民外交的旗号,而行参政之实而已。国民外交协会经常摆出 “只问外交,不涉内政”的超然姿态,实则这是研究系混淆视听、干预内政的幌子而已。林长民是国民外交协会的干事长,亦是研究系的干将。五四运动之后,林长民有一段自白,从中可以窥探研究系利用国民外交协会的参政意图。林说:“长民政治生涯从此焕然一新,此实国民外交协会之赐。”*《国民外交协会饯别会》,《晨报》1920年3月13日,第3版。这话是林氏1920年3月对研究系自五四运动以来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重要回顾。此时,原来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的亲日派曹汝霖诸人已经离去,五四政治风波早已烟消云散。
国民外交协会是研究系的大众组织,该会与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实为一体。研究系要人熊希龄、林长民、范源濂等人同时兼任两会的职务。研究系与大总统徐世昌在政见上比较一致,都是“文治派”,与皖系军阀段祺瑞所代表的“武力派”针锋相对。研究系与徐世昌的联合是相互利用:研究系是在借助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来寻求庇护,而徐世昌则要利用研究系的影响力来制衡皖系及其御用势力。关于外交委员会的成立动机,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干事叶景莘说得很明白:“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1页。研究系既然反对北京政府的“亲日倾向”,那么曹汝霖为首的亲日派自然是研究系的打击目标。
研究系介入学生运动的渠道主要是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外交协会的会员中有不少是“大学生代表”。*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1页。国民外交协会的理事、报界代表梁秋水与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往来密切,并通过罗氏对学潮表示支持。5月5日,罗家伦在学生会议上说,“北京报界希望学界组织总机关,电报不能外发,报界可以为力”。*《学生团对外之怒潮》,《时报》1919年5月8日,第1张。由于国民外交协会与北京大学学生往来密切,致使亲日派曹汝霖等人指责其中“大有政治臭味”。*彬彬:《京潮再志》,《时报》1919年5月8日,第1张。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研究系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特别活跃,俨然执舆论界之牛耳。一方面,研究系利用国民外交协会充当民意代表,并向北京政府提出“国民的外交主张”;另一方面,研究系积极地为徐世昌出谋划策,充当谋士。据时人透露,4月30日,徐世昌在延庆楼传见研究系的范源廉、熊希龄、丁乃扬等人,“密谈和局问题达2小时之久”。*《大总统倚重之三要人》,《时报》1919年5月3日,第1张。
五四运动爆发前半个月,研究系最为活跃。研究系这期间的政治活动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直接的关联。此处,仅对研究系在这期间的国民外交活动略作考察。4月22日,研究系的熊希龄、林长民等人以国民外交协会代表的名义面见总统徐世昌。熊希龄向徐世昌提出国民外交协会的基本主张,也就是要求政府“非把山东问题提交巴黎和会不可”。*《徐总统之外交谈话》,《时报》1919年4月25日,第1张。徐世昌的回答也很圆滑,他说:“国民爱国,政府亦爱国,正宜互相提携。”接着,徐世昌话题一转,指出中国外交问题的失败在于国内分裂,他说:“南北今尚未统一,外交即大大吃亏。”*《徐总统之外交谈话》,《时报》1919年4月25日,第1张。徐世昌如此说来,是在希望国民外交协会援助其和平统一政策。此次谈话揭示了研究系与徐世昌所关切的政治利益有所不同。国民外交协会着眼于山东问题的交涉成败,而徐世昌关心的是南北统一问题,此问题牵涉到总统的政治地位。4月24日,外交委员会将《外交意见书》提交给大总统徐世昌,请徐氏“即日电令专使查照前令,乘机提出山东问题”。*《外交委员会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94页。
4月底,梁启超在巴黎得知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后,立即电告国内的研究系干将林长民,请其“警告政府及国民,严查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紧要新闻》,《晨报》1919年5月2日,第2版。研究系应声而动,其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发动请愿之举。5月1日上午,国民外交协会代表赴总统府见徐世昌,请其致电巴黎和会代表“据理力争,万勿退让”,徐世昌“允照办”;同时,国民外交协会又致电巴黎的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和中国专使,表达同样意愿。*《国民外交之奋起》,《晨报》1919年5月2日,第2版。这样,大总统徐世昌、研究系及其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之间形成了一个民意沟通系统,由此产生一个能够制约政府外交的公众舆论压力。为了广泛动员民众,国民外交协会又在5月3日下午开会,研究系的熊希龄、林长民等出席,会议决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外交之决心》,《晨报》1919年5月4日,第2版。随后,国民外交协会向北京各界发出召开国民大会的通知,又向全国各省商会、省议会、教育会等团体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82页。
研究系的喉舌《晨报》持续报道山东问题的交涉情况,引导公众舆论的关注,促使山东问题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如五四学生马骅所言,“倘使和会不议到山东问题,学生决不会运动的。那时间,北京的学生界掀起了一种打卖国贼的运动,登高一呼,四方响应”。*马骅:《十年来学生活动之回顾》,《学生杂志》1923年1月,第10卷第1号,第2页。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耸人听闻地写道:“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晨报》1919年5月2日,第2版。林氏此文成功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救亡意识。隔日之后,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上演“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历史一幕,是为著名的“五四事件”。事后,北京政府逮捕涉嫌肇事的学生三十余名。研究系自知有愧,故为营救被捕学生不遗余力。5月5日,汪大燮致函大总统徐世昌,言称“学生非释放不可”;同日晚,汪大燮、林长民等领衔向京师警察厅保释学生。*《学生界事件昨闻》,《晨报》1919年5月6日,第2版。
除努力援救被捕学生之外,研究系还试图将五四运动引向深入,其表现是力争在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五四事件发生之后,研究系的政治态度更加激进,而总统徐世昌则日趋保守。总统徐世昌原本是支持研究系及其国民外交协会的,此时徐则担心五四运动扩大而不可收拾,致使其总统位置不稳。因此,徐世昌反对研究系召集国民大会。5月5日早上,总统府秘书长吴世湘电约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传达总统之意:“五月七号之国民大会暂作罢论”,但是徐世昌的请求遭到林长民的拒绝。*《京警厅阻止外交协会开会》,《申报》1919年5月8日,第7版。5月6日晚,国民外交协会开会决定国民大会照常举行,同时熊希龄、林长民等联名致函国务总理钱能训,拒绝政府的请求。
随后,北京政府采取行动,阻止国民大会的召开。5月5日,北京各校学生“相约罢课”,并准备参加5月7日的国民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69、170、171页。与此同时,北京各界团体也向政府施加压力,请求释放被捕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69、170、171页。在此形势下,北京政府若能提前释放被捕学生,便能起到一箭双雕之效:既可博取社会舆论之同情,又能离间学生界与研究系的联合。于是,释放被捕学生是北京政府的必然之举。5月6日晚,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两个交换条件:其一是不许学生参加5月7日的国民大会;其二是各校在5月7日一律复课。蔡元培完全接受上述两个条件。*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5月7日上午,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32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69、170、171页。同时,北京政府严加戒备,阻止研究系召开国民大会。7日早晨,中央公园周围高度戒严,士兵“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耻纪念日之国民大会》,《晨报》1919年5月8日,第2版。就这样,研究系计划召集的国民大会胎死腹中。5月15日,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已经不见汪大燮、熊希龄和林长民等人的身影。*《北京国民外交协会代表会议纪》,《晨报》1919年5月18日,第7版。这意味着研究系开始回避学生运动。
三、 学潮中的谣言:研究系与学界的不欢而散
在五四运动前夕,研究系引导舆论关注山东问题,并以“国民外交”的名义进行政治动员,对北京政府特别是亲日派曹汝霖等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五四运动爆发后,曹汝霖辈断定这一切都是研究系在幕后主使。5月5日上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到北京同仁医院看望曹汝霖,曹氏愤慨地说道:“昨日的学生骚动,有林长民一派政客在背后煽动。”*《小幡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2册下卷,东京:日本外务省,1969年,“大正八年”,第1044号,第1146、1147~1148页。5月7日,天津日本总领事船津辰一郎拜访皖系干将、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询问五四事件起因,段说:“梁启超、林长民等鼓吹排日舆论,然后称呼他们的政敌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为卖国贼,极尽谴责之能事。不过,梁启超、林长民的背后有汪大燮、熊希龄,而且更有冯国璋的遥控。”*《小幡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2册下卷,东京:日本外务省,1969年,“大正八年”,第1044号,第1146、1147~1148页。由此可知,亲日派认为五四事件绝非单纯的学生爱国运动,其背后甚至有直皖两系的角力: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与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之间的政治较量。
随后,日本在华媒体《顺天时报》发表时评,指出五四事件的发生与研究系的“煽动”有关。5月6日,《顺天时报》发表金崎生的社评,将五四事件的发生首先归咎于中国媒体对山东问题的“歪曲报道”。金氏写道:“中国各报关于山东问题登载煽动的记事,遂引起学生之暴行,吾人深为遗憾。”*金崎生:《山东问题之研究》,《顺天时报》1919年5月6日,第2版。金氏所论中国媒体对山东问题的报道是否“歪曲事实”,姑且不论,但他认为中国媒体对五四事件的发生应负“言论之责”,确属事实。5月7日的《顺天时报》社论进一步将五四事件的发生归因于中国内部“政争”,是某派“煽动”所致。*《学生之暴行》,《顺天时报》1919年5月7日,第2版。两日后,《顺天时报》揭露研究系“政客”林长民等人是五四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该报还特别指出,林长民在5月2日《晨报》发表的文章宣扬“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致使读者以为“胶州主权有不还中国之虞”,强烈谴责林长民“用此暧昧且有力之语句,故意激动人心”。*《学生暴行与政客之煽动》,《顺天时报》1919年5月9日,第2版。至于研究系“煽动”学潮的动机,《顺天时报》认为他们是借此谋取政治资本。研究系别称进步党,《顺天时报》在5月10日披露研究系的参政隐衷,“目下(南北)方在议和,而进步党诸氏于南北两方面均无立足地。若南北妥协成立,则彼等无所容身,于是彼等发起国民外交协会,以自造其立足地”。*《学生暴行与政客之煽动(二)》,《顺天时报》1919年5月10日,第2版。此外,《顺天时报》还指出研究系利用外交问题煽动学潮是为了实现其“倒阁阴谋”,并由其取而代之。*《顺天时报》还列出了研究系的组阁名单:总理兼财政熊希龄,司法林长民,内务张一麐,教育范源濂或蔡元培,外交缺,交通汪大燮,陆军王廷桢,海军刘冠雄,农商徐佛苏或刘揆一,参谋张绍曾,大理院长王宠惠。详见《内阁辞职观之五光十色》,《顺天时报》1919年5月10日,第2版。
研究系“倒阁阴谋”说一经披露,不胫而走,甚至上海媒体也宣扬此说。5月15日,上海《时报》沿袭《顺天时报》的报道,批评研究系“事前演说鼓吹,临事暗中赞助。颇思借此机会倒阁,乘时取得阁员地位”。*《揭北京学潮之内幕》,《时报》1919年5月15日,第2张。不过,上海《时报》为显示其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将研究系与亲日派都视为“一丘之貉”,认为两者都是“自私的政党”,绝无“国家观念”。*彬彬:《外交风云之因果》,《时报》1919年5月16日,第1张。
随着研究系与亲日派的政争内幕曝光,这两派人士为洗刷自身,开始相互攻讦。安福系议员光云锦要求惩办研究系汪大燮、林长民、熊希龄、梁启超等所谓的“无责任的官僚政客”,并罗列其“罪状”若干条;另一安福系议员艾庆镛则呼吁撤销研究系的大本营“外交委员会”。另一方面,研究系则攻击亲日派陆宗舆与日本人所订借款条约为“卖国之据”。*《京潮四志》,《时报》1919年5月13日,第1张。这两派旗帜鲜明的辩驳引起国内媒体的热议,上海《时报》讥讽他们“俨如小儿斗口,相互揭发,内蕴毕宣,斯真可浩叹”。*彬彬:《外交风云之因果》,《时报》1919年5月16日,第1张。接着,著名记者包天笑也发表时评,呼吁各党派消弭党争而一致对外。*笑:《党派鲜明之色彩》,《时报》1919年5月18日,第1张。
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舆论局面,重组之后的国民外交协会于5月15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试图与声名败坏的研究系划清界限。会上,留日学生代表陈定远发表演说,指出“我国此次外交问题发生后,反因而牵动各派倾轧之机。并有谓学生风潮之发生,系受某派之指使,而为倒阁之计者。惟阁之倒不倒,与我辈学生无丝毫关系”。*《国民代表外交会议之详情》,《时报》1919年5月18日,第2张。真可谓众口铄金,研究系的处境日益尴尬。为避风头,一向活跃的林长民只好销声匿迹,不再出席总统府外交委员会。*《林宗孟屏居匿迹》,《顺天时报》1919年5月14日,第2版。这时,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也向北京政府抗议,进一步给研究系施加压力。5月20日,小幡酉吉向代理外交总长陈箓提出抗议,指责林长民发表在5月2日《晨报》的文章“似有故意煽动之嫌”。*《小幡致内田电》,1919年5月24日,《日本外交文书》,第1192页。日方要求北京政府“警告林长民”,并“限期答复”。*《日本公使之正式公文》,《时报》1919年5月25日,第2张。随后,总统徐世昌派人转告林长民,“对外言论稍加谨慎”。*桂生:《北京通信》,《申报》1919年5月29日,第7版。5月25日,林长民被迫辞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职务。如《顺天时报》所言:“既蒙日本公使之指摘,林氏固已有不得不辞之势。”*《读林长民氏之辞呈》,《顺天时报》1919年5月29日,第2版。在此期间,研究系另一要人熊希龄也偃旗息鼓,“携眷赴津”,并被舆论讥讽为“大有一去不返之势”。*《熊秉三之悻悻》,《顺天时报》1919年5月24日,第2版。
6月10日,北京政府罢免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三名亲日派高官。为替这三位亲日派“出气”,日本喉舌《顺天时报》连续发表评论,竭力抹杀学生运动的爱国面相,一味夸大研究系对学潮的“煽动”因素。6月16日,《顺天时报》称:“据知其黑幕者谈起谓,学生是一派,教员是一派,阴谋政客又是一派。表面挂的幌子是爱国,是要争回青岛,入手的方法即在攻击曹章陆,此学生唯一的目的。”*《同床异梦》,《顺天时报》1919年6月16日,第3版。这里所谓的“阴谋政客”就是研究系。 6月17日,《顺天时报》又刊文批评研究系利用学生运动“以扩张自派势力”,“其卑鄙污浊寡廉鲜耻,固无责备之价值”。*《论说:学生政治运动为政治家之耻辱》,《顺天时报》1919年6月17日,第2版。不久前,研究系还曾经是大总统徐世昌的座上宾,“五四事件”之后研究系成为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因此徐世昌也连带受其不利之影响。为摆脱困境,徐世昌在6月11日提出辞职,以退为进。对此,深谙北洋政局内幕的白坚武评论说:“徐世昌以日来风潮,向新国会辞职,作一度操纵,新会挽留。”*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坚武日记》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9页。随着研究系煽动学潮以图党争的内幕曝光之后,学生界也开始远离研究系。据报道,某省学界联合会发表宣言,请求“惩办卖国贼林长民、汪大燮、熊希龄等人”。*《汪大燮之运动忙》,《时报》1919年6月16日,第2张。报道又说,“梁士诒赠学生2000金,梁启勋赠学生1000金,俱却不受”。*《国内专电》,《时报》1919年6月11日,第1张。梁士诒是旧交通系魁首,政治声誉败坏,而梁启勋则是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之弟。6月9日,研究系召集国民大会并请学生到会,遭到学生“全体拒绝,以表示离绝政客”。*《中央公园之国民大会》,《时报》1919年6月10日,第2张。
学生界与研究系的关系本尚密切。北京学生界的活跃分子如北京大学的罗家伦、徐彦之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经常在研究系《晨报》上发表文章,而《晨报》也积极报道学生运动情况,积极声援学生运动。但是,到了6月10日三位亲日派高官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被罢免以后,研究系与学生界的密切关系也基本结束。尽管研究系无法继续参与学生运动,但是其他派系力量依然试图拉拢学生界,以便为其所用。如时论所嘲讽的那样:“中国共有三种人:甲与乙争,而丙则为甲乙所利用而已。甲之势力盛,手腕辣,金钱足,则丙为甲所用。反之亦然。总之,国一日不灭,甲乙之争无已时,而丙之为所利用,亦无已时。安福派也,新交通系也,研究系也,旧交通系也,官僚也,名流也,商人也,均作如是观。”*笑:《甲乙丙》,《时报》1919年6月15日,第1张。简言之,在国内政治派系林立的环境下,学生运动要保持其独立性,确实困难重重。
四、 余 论
五四学潮爆发之后,研究系的名声一败涂地。不过,研究系与北大新文化派师生关系的疏远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双方的“友好关系”至少维持到1920年。同年5月4日,正值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这一日,研究系的《晨报》特意刊登了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以及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罗家伦等北大师生纪念“五四”的文章,这难免给局外人造成一种双方“一团和气”的表面印象。*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以及罗家伦等人的文章,详见《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1版、第2版。实际上,研究系与北大新文化派师生之间在“五四”问题上已经暗生芥蒂。尽管五四运动过去了一年有余,但是研究系与五四运动的“谣言”仍然困扰着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师生。1921年初,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提议共同致信陈独秀,“去辨明此事”。*《致胡适》(1921年),《李大钊文集》,第951页。
到了1922年,北京学生张梵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研究系坏的不能说,《晨报》有时常给该系护短,终究是有个替代的——清白无派的——出来,我们就要和他断绝来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58页。外界对研究系的批评,也促使研究系内部的瓦解。在五四运动前夕一度非常活跃的研究系要人熊希龄就是一位典型。当研究系暗中煽动学潮的谣言四起之时,良知未泯的熊希龄就决定激流勇退,不再参与研究系的政治活动。其后,熊氏致信总统府秘书长吴世湘,极力辩解其痛恶“党争恶习”,并且与研究系毫不相干。熊函称:“不图五月四日之变,出诸意外,种种谣传,甚疑弟等为指使,为党争,为倒阁,实非始愿所及。……现既为人不谅,惟有仍本初衷,缄口结舌,置理乱于不闻,可省无穷烦恼,质之我公,当以为然也。”*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5册,第4573~4575、4574页。
吴世湘是大总统徐世昌的心腹幕僚,熊氏这封辩解书显然也是写给徐世昌看的。在五四运动前,研究系依靠徐世昌的支持,成立国民外交协会,集会呐喊,引导公众,一时风光无限。*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5册,第4573~4575、4574页。不料,五四学潮起来后,皖系、安福系及其政敌研究系却随之陷入政争的漩涡,其政争内幕曝光后,成为舆论的笑柄。唯独大总统徐世昌凭借其八面玲珑的政治智慧,坐收五四运动的渔翁之利。正是在此情境下,政争失利的熊希龄此时致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世湘,既是在诉说委屈,也是在间接地对徐世昌表达不满。
五四学潮平息之后,北京大学新派学者与研究系的关系再也不如之前那样和睦了。尽管研究系一再努力与北京大学新派学者和好,结果都是枉然。1922年5月14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领衔,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16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16人中有11位是署名北京大学教授,其余5位是汤尔和(医学博士、蔡元培的好友)、陶行知(东南大学)、王伯秋(东南大学)、王征(美国新银行团秘书)和丁文江(胡适的朋友、前地址调查所所长)。*《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1922年5月14日,第1版和第2版。就在这份宣言发表的当日,研究系干将林长民邀请北京大学胡适等人聚餐。席间,研究系的梁启超和林长民等人对蔡元培领衔发表“政治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而把研究系排斥在外,表示不满。梁启超赌气说:“我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劝慰梁氏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666页。考虑到蔡元培校长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曾经与研究系一道组织各种团体,指导民众运动,此时蔡元培也疏远研究系,这确实让研究系颇感纳闷。但是,研究系无法明白的是,蔡元培校长其实深受其害,方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对研究系敬而远之。
蔡元培毕竟是一位有良知的教育家,他不希望中国的教育事业被研究系这般政客给毁掉。五四之后,蔡元培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著名口号就是对已经政治化了的学界风气的补救之策。其后,中国的学潮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每念及此,蔡元培都懊悔无穷,他说:“百世之后,虽起吾辈白骨而鞭之,亦不足以□其辜也。”*萧一山:《新文化运动与蔡孑民先生》,《时代精神》第6卷第4期,1942年6月。怀抱此种心境,蔡元培还会接近研究系吗?
虽然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行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五四运动最初是在北京这样一个派系斗争异常复杂的情境下发生的,其中的派系因素不容忽视。然而,正是由于各种派系力量的介入并形成一股合力,才使得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避免团体为党派利用,已经引起当时某些社团的警惕。1919年3月4日,苏州总商会旅沪会董王介安在致苏州总商会的信中,就是否加入全国和平联合会一事,指出“惟倘内有党派利用性质等情,本会不宜与闻,免作私人傀儡”;全国和平联合会虽有多数代表“能本良心做事”,实际上仍有“少数代表欲利用此会以随[遂]私便,而达破坏目的,甚至私下运动别代表”。*《王介安复苏州总商会函》(1919年3月4日),马敏、祖苏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12~1919)第2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63~664页。
五四运动结束后不久,武汉学生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就严厉批评学联代表在运动中总是利用“已成的势力”,并将学联代表与政客、军阀、南北议员视为“一丘之貉”。*《致王光祈信》(1919年9月9日),《恽代英文集》,第106~107页。五四时期的学潮与政争乃是一对孪生的姊妹。北京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在客观上营造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空间,从而为学潮的爆发与持续提供了可能性。如若没有学潮,在野的政治派系便少了一个对敌斗争的筹码。不管怎样,五四运动确实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精神,并刷新了中国的政治面貌。也正是在此情境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而早已走投无路的国民党也因此焕发新的生机。胡适说过,五四运动“使国民党得着全国新势力的同情”,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的青年”。*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收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