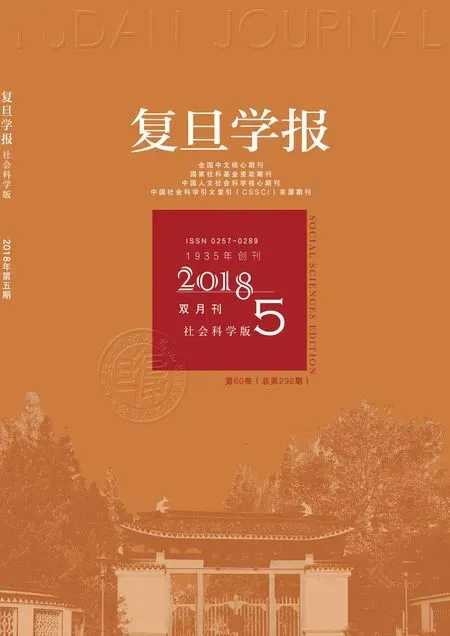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与佛教、中国文学之关系
张 煜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上海 200083)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是一部无所不包的奇书。正如此书最后终篇所言:“有关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这里有,别处也有,这里没有,别处也没有。”*[印度]毗耶娑著,黄宝生、葛维钧、郭良鋆等译:《摩诃婆罗多》第六册第十八《升天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42页。有关此书的一般性的介绍,可以参看黄宝生先生中译本的前言;奥地利学者(Maurice Winternitz)所著HistoryofIndianLiterature一书中,也有专章详尽介绍。*Maurice Winternitz,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 1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27), Mrs S. Ketkar英译。此书作者一般认为是毗耶娑(Vyāsa),意译为广博仙人。“这位毗耶娑,按照印度人的传统说法,还是四大吠陀的编订者,《往世书》《梵经》的编写者。这些著作成书时间前后相距上千年,由某一个人完成是不可能的。所以毗耶娑实际是群体编订者的代称或专名。”*郁龙余、孟昭毅主编:《东方文学史》,第一卷《古代东方文学》第四章《古代印度文学》第三节《两大史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3页。其成书年代也是众说纷纭,“奥地利梵文学者温特尼茨(M. Winternitz)曾经提出《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尽管时间跨度八百年,长期以来反倒为多数学者所接受”。*黄宝生等译:《摩诃婆罗多·前言》(下同),第一册,第9页。至于《摩诃婆罗多》的手抄本则版本复杂,主要有南北两大体系。“印本中有影响的是根据北方传本编写的加尔各答版(1834~1839)、孟买版(1963)和根据南方传本编写的马德拉斯版(1931)。为了有一个公认的可靠版本,印度从1919年开始,编订《摩诃婆罗多》的精校本,至1933年出第1卷,1966年19卷全部出齐,前后历时近半年世纪。”*郁龙余、孟昭毅主编:《东方文学史》,第65页。黄宝生先生等译的中译本,主要是以这个精校本为依据。
该书卷帙浩繁,号称十万颂,精校本的篇幅总量近八万颂,中译本有四百多万字。全书共分十八篇,主体部分讲述的是婆罗多族王国内部般度五子与持国百子为了争夺王位,而展开的一场历时十八天的在俱卢之野(现在德里附近)的自相残杀。最后以坚战为首的般度族打败了以难敌为首的俱卢族,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参加战斗的全部成员只有九人活了下来。终篇成为天神的两族终于消泯了仇恨。在大战开始之前,还有五兄弟流亡森林、合娶黑公主、难敌定计用掷骰子骗局胜了坚战、五兄弟与黑公主流放森林十二年、双方备战与谈判等故事。除了主干故事外,全书还包括200多个插话,其中包含有像《沙恭达罗》《那罗与达摩衍蒂》《莎维德丽》《罗摩传》这样的文学精品*参金克木编选:《〈摩诃婆罗多〉插话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以及关涉哲学、宗教、政治、道德、法律、风俗等的说教文字,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宗教哲学长诗《薄伽梵歌》*Winternitz认为《薄伽梵歌》从语言、风格和诗律上,都属于《摩诃婆罗多》一书中较早的部分。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Vol 1,第438页。,被称为《摩诃婆罗多》精华中的精华。
《摩诃婆罗多》在印度地位至为重要,被认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但在中国的传入却很晚。*参王汝良:《〈摩诃婆罗多〉在中国》,《东方论坛》2015年第4期。因为古代中国的翻译大部分是佛经的翻译,仅马鸣《大庄严论经》卷五提到“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又《婆罗他书》。说阵战死者,命终生天;投火死者,亦生天上。又说天上种种快乐”。*[印度]马鸣著,[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经论》,《大正藏》第4册。但事实上,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西方与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这部书对于理解印度文化的重要意义。而且事实上,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佛教,离开印度教也是不可能的。本文拟就此书与佛教教义、佛经故事以及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略作探讨。
一、 《摩诃婆罗多》与佛教
关于《摩诃婆罗多》与佛教的关系,Witnernitz在HistoryofIndianLiterature中其实已有所涉及,值得引起我们重视。温氏认为《摩诃婆罗多》不可能是出于一人或一时,而是有一个长期的创作与改编的过程。在巴利文三藏中,没有提到《摩诃婆罗多》,但是一些本生故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摩诃婆罗多》书中出现的神或人物如黑天。“所以产生于公元前四到三世纪的巴利文佛典,对于《摩诃婆罗多》的了解还相当肤浅,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佛教产生的东部,对于此书还所知甚少。”*Maurice Winternitz,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 1,第473、314、463页。而且基本可以断定在《吠陀》时代,《摩诃婆罗多》还不存在。“如果公元前六到四世纪存在《摩诃婆罗多》的话,那么本土的佛教世界对此也是所知甚少。”《摩诃婆罗多》虽然作为整体什么时候产生难以断定,但各个组成部分还是可以根据各种情况予以确定的。“It is certain, moreover, that as early as the time of Buddha there was in existence an inexhaustible store of prose and verse narratives—khyānas故事, Itihāsas古老传说, Purāas 史诗and Gāthās偈颂—, forming as it were literary public property which was drawn upon by the Buddhists and the Jains, as well as by the epic poets.”*Maurice Winternitz,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 1,第473、314、463页。也就是说,如果佛教与《摩诃婆罗多》中出现相似的故事或描写,那有可能他们都继承了更早的源头,而不是互相抄袭。另外还有论者认为,《摩诃婆罗多》在后来的流传中(十至十二世纪),受到了佛教徒的改编,则一些佛经故事也有可能是后来流入进去的。*Maurice Winternitz,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 1,第473、314、463页。
意大利佛教学者Giovanni Verardi(1947~ )在他的HardshipandDownfallofBuddhisminIndia一书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也许会争辩说,如果不顾佛教去写一部印度史是可能的话,那么不顾印度婆罗门教,去写一部更小的印度佛教史会更艰难。”*Giovanni Verardi, Hardship and Downfall of Buddhism in India (New Delhi: Monahar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11) 第14页。婆罗门教的资料、著作、神话传说中,包含了多得让人吃惊的佛教信息。宗教史家应该提供更现实的婆罗门教的图景。而在第一章Historical Paradigms,他回顾了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学术贡献。其中包括Monier-Williams的BuddhisminitsConnectionswithBrāhmanismandHindūism,andinitsContrastwithChristianity。*Monier-Williams, Buddhism in its Connections with Brāhmanism and Hindūism, and in its Contrast with Christianity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90).“Buddhism, originated within Brahmanism, reverted peacefully to it. Buddhism becomes an episode of Brahmanism.”*Giovanni Verardi, Hardship and Downfall of Buddhism in India,第40、47~48、51~52、53页。进入20世纪,Ananda K. Coomaraswamy在他的EssaysinNationalIdealism中,也提出了所有的佛教作者,都面临着如何区分佛陀与婆罗门教思想的困难。他并且认为越深入研究佛教,会越发现和婆罗门教区别不大,并无根本对立。大乘佛教和密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婆罗门教的外在压力。*Giovanni Verardi, Hardship and Downfall of Buddhism in India,第40、47~48、51~52、53页。而一些民族主义学者,如Kashi Prasad Jayaswa甚至认为佛教是一种异端的系统与反民族的运动,在巽伽与别的许多王朝受到抵制。印度的民族性应该是梵,而不是别的具有包容性的概念。*Giovanni Verardi, Hardship and Downfall of Buddhism in India,第40、47~48、51~52、53页。Babasaheb R. Ambedkar认为,穆斯林入侵时,印度社会掌握在婆罗门,而不是佛教手中。*Giovanni Verardi, Hardship and Downfall of Buddhism in India,第40、47~48、51~52、53页。以上这些观点,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来理解佛教、印度教与整个印度文化。
《摩诃婆罗多》全书的哲学思想,有一处最精彩集中的呈现,即第六《毗湿摩篇》中的第23至40章《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史诗作者将此篇视作《摩诃婆罗多》的思想核心。“薄伽梵”是对黑天的尊称,黑天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所以《梵伽梵歌》也可译作《神歌》。大战在即,双方十八支军队摆开阵形,恒河女神之子毗湿摩担任俱卢族大军的统帅,般度五子之一、最骁勇善战的阿周那却突然对战争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想要放弃战斗。自愿担任阿周那车夫的黑天,在阵前对他进行勉励。俱卢国王持国因为天生是个盲人,所以请大臣持胜为他讲述战场上发生的一切。这里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血肉横飞,而是陷入了纯粹的人生与哲理的思索,印度民族善于思考的民族性,在阿周那与黑天的对话中显露无遗。阿周那感到手足相残,争个你死我活,即使取得胜利也毫无意义。而黑天则鼓励他战斗,因为战斗是刹帝利种姓的天职。另外还笑着辅以一番非常抽象的说理:

吉祥薄伽梵说:你说着理智的话,为不必忧伤者忧伤,无论死去或活着,智者都不为之忧伤。(11)*黄宝生编著:《梵语文学读本》,《薄伽梵歌》第二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36页。以下所引梵文的解读,感谢2015年在哈佛大学梵文系基础班上Tyler Neill老师的指导,以及复旦大学Eberhard Guhe教授的帮助。
它从不生下,也从不死去,也不过去存在,今后不存在,它不生、永恒、持久、古老,身体被杀时,它也不被杀。(20)
如果知道,它不灭、永恒、不生、不变,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杀什么或教人杀什么?(21)
正如抛弃一些破衣裳,换上另一些新衣裳,灵魂抛弃衰亡的身体,进入另外新生的身体。(22)
刀劈不开它,火烧不着它,水浇不湿它,风吹不干它。(23)
生者必定死去,死者必定再生,对不可避免的事,你不应该忧伤。(27)
黑天教导阿周那:“你的职责就是行动,永远不必考虑结果;不要为结果而行动,也不固执地不行动。(47)”这真是世界一切战争文学中最奇妙的文字!这种源自雅利安民族的尚武与沉思精神,与爱好和平与思辨的佛教在精神气质上既相距甚远又消息相通。这里同时又强调瑜伽的智慧,要对万物一视同仁,虽然采取行动,又要并不执着于结果。世间万物最终难逃毁灭,时间才是真正的杀死一切者。作为个体,并不可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职责,唯有战斗到底,完成使命。所以徐梵澄先生在所译室利·阿罗颇多《薄伽梵歌论·1957年海外初版序言》中云:“《薄伽梵歌》行世,远在大乘发扬之前,淳源未漓,坦途无碍。既不以空破有,亦不以有破空,但使双超上臻,初未旋说旋扫,固曰无始无上之大梵,非有非非有是名也。”*[印度]室利·阿罗颇多著,徐梵澄译:《薄伽梵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73、475页。又云:“大致古婆门之颓废,佛教皆可匡正之。小乘之不足,大乘足以博充之;末法之罅漏,新起印度教可以弥缝之。”*[印度]室利·阿罗颇多著,徐梵澄译:《薄伽梵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73、475页。皆足发人深省。
作为一部印度教的圣典,《摩诃婆罗多》的核心思想,都是围绕着法、利、欲与解脱这些最重要的概念展开的。这样的一种教诲,贯穿了整个的故事情节与文本。其中法、利、欲三要,是传统印度教为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这些“再生者”所制定的三个人生目标。法指正确的行为,包括社会要求人履行的各种责任、义务、规矩和宗教礼仪;利指可以享受的手段,如财物、权力、名声等;欲首指情爱,也包括各种耳目之娱和权力带来的享受。*《摩诃婆罗多》第九《沙利耶篇》,第四册,第676、840页。而尤其集中在全书第十二《和平篇》中。大战结束,面对战后的悲惨后果,坚战在众人劝说下登基。黑天陪同坚战五兄弟前往战场,请躺在“箭床”上的毗湿摩传授国王的职责。这就是充满宗教哲学意味的《和平篇》及《教诫篇》。法、利、欲三者是什么关系呢?毗湿摩说:“如果世上的人们怀着善意决定事情,这三者就会在时间、原因和行动诸方面互相结合。利益是身体,以正法为根基,爱欲是利益的果实。三者又以意念为根基,而意念以感官对象为核心。所以感官对象用于满足需求。这是三者的根基。摆脱这一切,称作解脱。”*《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225、321、117、98、103、124、132、180、138页。这也正是第五《斡旋篇》中黑天对难敌的好言相劝:“智者们追求三大目的(法、利和欲),婆罗多族雄牛啊!在三者不能兼得时,人们坚持法和利。而只能取其一时,上者求法,中者求利,下者求欲。”*《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225、321、117、98、103、124、132、180、138页。以及第九《沙利耶篇》中罗摩所言:“正法受两种东西的牵制,那就是贪得无厌者的利得和执迷不悟者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不忽视法和利,或法和欲,或欲和利,而同时实现法、利、欲三者,他就能获得全面的幸福。”*《摩诃婆罗多》第九《沙利耶篇》,第四册,第676、840页。。
《和平篇》强调“一切正法以王法为首要;一切正法受王法保护。”*《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225、321、117、98、103、124、132、180、138页。“因为王法是一切生命世界的庇护。人生三要(正法、爱欲和利益)都依据王法,俱卢族后裔啊!解脱法显然也完全依据它。”*《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225、321、117、98、103、124、132、180、138页。“一个人首先要选择国王,然后才会有妻子和财产。世上没有国王,哪里会有妻子和财产?”*《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225、321、117、98、103、124、132、180、138页。“古代经典说,选择国王就是选择因陀罗。因此,盼望繁荣的人应该像崇敬因陀罗那样崇敬国王。”*《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225、321、117、98、103、124、132、180、138页。“是时代造就国王,还是国王造就时代?毋庸置疑,国王造就时代。一旦国王正确实施全部刑杖学,就出现最好的时代,名为圆满时代。”可以看出,《摩诃婆罗多》把世俗王权刹帝利的地位放到了极高的位置,这部史诗最初的写作原因,极有可能就是为了颂扬刹帝利的战争功绩。但是后来在婆罗门祭司的传播过程中, 又增加进了很多颂扬婆罗门的内容。所以其中既有宣扬刹帝利的尚武精神,如:“流出痰液和胆汁,哀求怜悯,死在床上,这不符合刹帝利正法。”“刹帝利死在战场,这是古代立法者确立的永恒法则。”*《摩诃婆罗多》第七《德罗纳篇》,第四册,第108页。“人们说,自古以来,在战斗中被武器杀死,这是刹帝利的最高归宿。”*《摩诃婆罗多》第十一《妇女篇》,第四册,第914页。又有标榜婆罗门神圣不可侵犯、婆罗门与刹帝利应该互相联合的内容,如:“刹帝利是婆罗门之源,婆罗门是刹帝利之源。他们永远互相依靠,达到荣华富贵。如果这种古老的联合破裂,就会造成一切混乱。”中国古代《高僧传》中,释道安也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说法。*[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卷第五《义解二·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77页。这不禁促使我们去思考佛教最后在印度消亡的原因是否与此有关?即使是历史上最支持佛教的阿育王与巽伽王朝,一些印度学家们也认为他们其实同时支持佛教与婆罗门教。*Giovanni Verardi, Hardship and Downfall of Buddhism in India,第56页,第97页。另可参Étienne Lamotte之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Sara Webb-Boin英译,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Louvain-la-Neuve, 1988,第三章《孔雀王朝》之“阿育王”部分。这与中国唐代的唐太宗颇为相像,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平衡术。*参[美]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之《太宗统治时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正法有时又是很微妙的。毗湿摩说:“国王想要取得成功,就要兼用正法和非正法两种手段。”*《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150、61、291~292、352、370、373、452、515、34页。在《危机法篇》中,更是详尽讨论了种种非常和意外情况下,迫使采取的狡诈的谋略。在坚战与难敌的大战中,黑天多次出计谋,让般度族通过诡计获胜,并认为这是合理的。当最后难敌与怖军决斗,黑天再度暗示怖军击打难敌腰以下部位,这在正式决斗中是被禁止的。当难敌因为跳起时被击中大腿,躺在血泊中时,他愤怒地咒骂黑天:“你将束发置于前方,造成祖父(毗湿摩)的死亡。居心险恶的人啊,杀死了一头与马嘶同名的大象,从而促使师父放下武器,你当我不知道这件事吗?当凶残的猛光就要杀死那位英雄的时候,你看到了,却不去阻止他。为了消灭般度之子(阿周那)而求得的标枪,你设法让它用于瓶首而作废。……在战场上,人中豪杰迦尔纳的战车车轮下陷,一时不知所措,处境危险,又是你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你们肯同我,同加尔纳、毗湿摩和德罗纳公平交战,胜者必定不是你们。”*《摩诃婆罗多》第九《沙利耶篇》,第四册,第843~844、845页。但黑天向难敌指出,他当初毒害怖军、火烧紫胶宫、让沙恭尼掷骰子在赌局中战胜坚战并在大会堂污辱黑公主,也一样是使用了诡计,所以是罪有因得。他并安慰般度族人:“你们的心里不应该认为国王难敌是靠诡计杀死的。如果敌人明显势众,就不妨采取各种手段杀死他们。当初众天神诛灭阿修罗,走的就是这条路。善者走过的道路,所有人都可以跟着走。”*《摩诃婆罗多》第九《沙利耶篇》,第四册,第843~844、845页。总之,正法微妙,有时非常人可以理解,“如果杀死一个人,可以保全家族;如果杀死一个家族,可以保全王国,那么,这种杀戮不违规。因为,有时正法以非正法的面貌出现,有时非正法以正法的面貌出现,智者能够识别。”*《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150、61、291~292、352、370、373、452、515、34页。但其要旨在于行善。
而人生最高的价值在于获得解脱。为了获得解脱,必须控制感官,摒除欲望,懂得自制以及满足。光看这些说教,与佛教是极其相似的。*有关佛教与印度教的比较,国内比较系统的研究,参姚卫群:《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如第三《森林篇》中,借婆罗门之口对坚战说:“众所周知,心灵痛苦的根源是爱。人由于爱而执著,也就产生痛苦。一切痛苦的根源是爱,一切恐惧也由爱产生,忧愁、喜悦和辛劳也由爱引起。爱产生激情,并产生对感官对象的追求。这两者都是有害的,但又以前者的害处为大。”*《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第二册,第7、407~408页。又借猎人之口说:“谁坚定地控制自己永不安分的感官缰绳,他就是优秀的车夫。谁坚定地控制放纵的感官,犹如车夫坚定地控制奔马,他肯定会战胜感官。如果思想屈从噪动的感官,就会夫去智慧,就像狂风吹走水中的船。”*《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第二册,第7、407~408页。在《和平篇》中,毗湿摩这样告诫坚战:“最高归依是自制。思想坚定的长者们说,自制是至高幸福。尤其对于婆罗门,自制是永恒的正法。一个人不自制,他的事业不会获得成功。自制胜于布施、祭祀和诵习吠陀。自制增强威力。自制是最高的净化手段。……自制的人愉快地入睡,愉快地醒来,愉快地周游世界,精神安详。不自制的人经常遇到麻烦,由自己的错误造成许多罪孽。”*《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150、61、291~292、352、370、373、452、515、34页。
而控制感官的本质在于控制内心。“智者控制动荡不定、无所依傍的五种感官和内心,这是禅定的第一步。”*《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150、61、291~292、352、370、373、452、515、34页。“感官之上是心,心之上是智慧,智慧之上是知识,知识之上是至高者(灵魂)。”“通过知识净化智慧,通过智慧净化思想,通过思想净化感官群,就能到达无限者。”“在这世上,欲望是唯一的束缚,没有其他的束缚。摆脱欲望,就能与梵同一。”“在这世上,解脱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而世人拥有谷物和财富,执著儿子和牲畜,不懂得解脱。”“凡善于抑制欲望的人,在任何地方都知足常乐,因为他们无处不能征服自己的欲求。抑制了欲望的人想去哪里都能到达。他们能够击跨任何敌人。毫无疑问,他们想要什么,便能得到什么。”*《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241、293页。“自我克制的真正实现才是最高的苦行。”“智者收缩一切欲望,犹如乌龟收缩肢体。”*《摩诃婆罗多》第十四《马祭篇》,第六册,第553页。“满意是最高天国,满意是最高幸福,没有什么比满意更重要,满意至高无上。”
佛教戒杀、戒淫,提倡施舍、忍让,觉得这个世界是苦、空的,这些在《摩诃婆罗多》中,同样都可以找到。戒杀则如第十二《和平篇》:“人们出于贪婪才在祭祀中杀生。因此,明白人应该严格履行微妙的正法。不杀生被认为高于一切正法。”*《摩诃婆罗多》第十四《马祭篇》,第六册,第472、476~477页。“不善之人有时也会从善。善人也会生出坏后代,不善之人也会生出好后代。不应该连根铲除,这不是永恒的正法。不采取杀戳的办法,而采取赎罪的方法。”*《摩诃婆罗多》第十四《马祭篇》,第六册,第472、476~477页。“自在之神摩奴曾经说过,那种不吃肉、不杀生,也不怂恿他人杀生的人,就是众生的朋友。所有的贤者都认为,一个永远拒绝肉食的人,是没有谁可以战胜他的。世上的一切人也无不对他表示信任。”*《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379、204页。《大般涅槃经》、《楞伽经》、《楞严经》这些佛教经典也都反对食肉。
佛教戒律中都有对于戒淫的三令五申,如《摩诃僧祗律》。《摩诃婆罗多》中这样的教诫也随处可见,如第十二《和平篇》:“聪明的男性特别注意回避女性。可怕的女性施计迷惑不聪明的男性。她们隐藏在忧性中,永远是感官的化身。”*《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385、386、416、209、215、216、219、281、321页。站在男性的立场,把女性视作产生欲望的祸端,基本和佛教是同一立场。*详参张煜:《佛教故事群中的女性——以〈经律异相〉之记载为中心》,《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婆罗门应该及时抑制淫心。不应听取妇女谈话,不应观看妇女裸体。意志薄弱的人一看到妇女,就会动情。一旦产生欲念,就应该修习苦行,在水中浸泡三天。如果在梦中产生欲念,就应该默诵涤罪祷词三次。正是这样,聪明的人富有知识,思想博大,焚毁内在的忧性罪恶。”*《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385、386、416、209、215、216、219、281、321页。“不勾引他人妻,……决不向虚空、牲畜或非阴户,也不在月变之日排泄精液。”*《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385、386、416、209、215、216、219、281、321页。
佛教中有法布施、财布施、身布施等,第十三《教诫篇》中,更是有着各种关于布施功德的记载。“苦行、祭祀、学习吠陀、行为端正、戒除贪欲、坚持真理、尊重师长和崇拜神明,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施舍土地好。”*《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379、204页。“在过去的年代里,诸天神和众仙人都曾高度评价过食物的重要。世界的发展和智慧的存在都离不开食物。可以同施食相比的施舍过去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有。所以,人们特别愿意施舍食物。”*《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385、386、416、209、215、216、219、281、321页。“谁施舍了黄金,他就等于施舍了世上一切人们想要的东西。”“一孔水源充足的水井,能不断地召来众生啜饮。凿井人的罪业会有一半因此而被涤除。常有婆罗门、善者和牛群前来饮水的水源,它的开辟者整家都会获得救度,从而免遭地狱之灾。”“在所有的施舍中,车辆的施舍是最了不起的。”“对于一切苦行者来说,牛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大自在天这位神明总是愿意在有牛的地方修习苦行。”“在所有食品中,芝麻属最上一等。”甚至还包括到讨论施舍鲜花、香、灯的功德等:“有益于健康的植物能够给人带来福祉,有毒的植物能够给人带来灾难。一切草本植物都是有益于健康的,有毒的植物则来源于火焰的能量。鲜花能够使人身心愉快,为人带来福惠,行为高尚的人称它们‘悦心之物’。”
佛教六度中包含忍辱,《摩诃婆罗多》中也有,如:“受到辱骂的人倘若不回骂,他忍耐住的怒火将焚烧骂人者,自己的善行也得到彰显。……言语的利箭从口中射出,受其伤害者会昼夜伤心;那落在他人敏感部位的言语利箭,智者绝不会将它射向别人。”*《摩诃婆罗多》第一《初篇》,第一册,第212页。“在争论中,口出恶言的是下等人,予以回击的是中等人,不予回击的是上等人。无论别人是不是说了对自己不利的粗言恶语,决不予以理睬,这是意志坚定的上等人。”*《摩诃婆罗多》第二《大会篇》,第一册,第626页。“做了不值得夸耀的事,还要厚颜无耻地夸耀。自我克制的人不必理会这种卑劣的人。永远应该容忍愚者的言谈,无论他们赞扬或谴责,能起什么作用?犹如无知的乌鸦在林中聒噪。”*《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210、535页。“受到侮辱、打击或谩骂,都能容忍,无论对方是低贱者、高贵者或与自己地位相当者,这样的人获得成功。”
甚至包括无常、苦、空等,这些佛教的基本思想,也贯穿了整个《摩诃婆罗多》故事全书。这种阴郁的人生观是印度文化的一大特色,可能并不存在佛教、婆罗门教谁影响了谁,它们与那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无缘,在近代甚至影响到叔本华、尼采等欧洲哲学家。《摩诃婆罗多》中如大战结束后,维杜罗安慰持国,人终有一死:“正如泥制的陶罐,有的在陶工的转轮上就破裂,有的半成形就破裂,有的刚成形就破裂。有的移动时破裂,有的移动后破裂,有的潮湿时破裂,有的干燥时破裂,有的烘烤时破裂。有的取下时破裂,有的烧煮时破裂,有的用餐时破裂,人有身体也是这样。有的在胎中就死去,有的刚生下就死去,有的一天后死去,有的半月死去,有的满月死去。有的周岁死去,有的两岁死去,有的青年死去,有的中年死去,有的老年死去。由于以前的业,众生或生或死。世界就是这样运转,你何必忧愁烦恼?”*《摩诃婆罗多》第十一《妇女篇》,第四册,第906~907页。第十二《和平篇》:“这个世界如同水的泡沫,充满毗湿奴的幻影,如同壁画,如同空心芦苇。如同黑暗的深渊,如同水泡,缺少快乐,最终毁灭,归入虚无。”*《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542、193、320、413、435、450、574~95页。这与《维摩诘所说经》中的“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可久立;是身如焰,从渴爱生;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为虚妄见;是身如影,从业缘现;是身如响,属诸因缘;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后秦鸠摩罗什译,僧肇等注:《注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第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和平篇》中,毗湿摩借牟尼黑树之口道:“你要知道自己以为存在的一切,实际上都不存在。这样,智者即使陷入困境,也不感到痛苦。过去和未来的一切都肯定会消失,你知道了这种应该知道的道理,你就会摆脱非法。从前的人以及更早的人获得的一切都已不存在,明白了这一点,谁还会烦恼?存在变成不存在,不存在也变成存在。但忧愁并没有这种能力,因此,人何必忧愁?……我和你,你的敌人和朋友,注定会消失,国王啊!一切都会消失。那些现在二三十岁的人,在今后一百年内肯定都会死去。”*《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542、193、320、413、435、450、574~95页。又借儿子与父亲的对答讲道:“死神带走一心迷恋儿子和牲口的人,犹如洪水卷走沉睡的老虎。死神带走正在采集的人或欲望尚未满足的人,犹如老虎叼走牲口。死神控制那些充满渴求的人,他们总是想着‘这事已经完成,这事需要完成,这事正在完成。’死神带走执著田地、买卖或家庭的人,他们或者尚未获得工作成果,或者执著工作成果。”*《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542、193、320、413、435、450、574~95页。又借因陀罗之口道:“时间不受控制,毫不松懈,始终烘烤众生,永不停止。一旦进入时间的领地,就无法解脱。众生懈怠,而时间保持清醒,从不懈怠。从未见过有谁能超越时间,即使他勤奋努力。……时间如同高利贷盘剥我们的财富,每日每夜每月,每分每秒每刹那。一个人正在说着‘今天我要做这件事,明天我要做那件事’,时间却已达到,带走了他,犹如急流卷走小船。”*《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542、193、320、413、435、450、574~95页。
在解脱论方面,佛教讲涅槃,印度教讲“梵我合一”,虽旨归不同,但也不是毫无联系。*参姚卫群:《佛教的“涅槃”和婆罗门教的“解脱”》,《南亚研究季刊》1997年第2期。如同《薄伽梵歌》中所唱的那样:“他们的心安于平等,在这世就征服造化;梵无缺陷,等同一切,所以他们立足梵中。不因可爱而高兴,不因可憎而沮丧,智慧坚定不迷惑,知梵者立足梵中。”*《摩诃婆罗多》第六《毗湿摩篇》,第三册,第500页。“一旦在一切众生中看到灵魂,在灵魂中看到一切众生,他就达到梵。一旦知道自己的灵魂与别人的灵魂一样,知道灵魂遍及一切,他就达到不朽。”*《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542、193、320、413、435、450、574~95页。“自我(灵魂)就是圣地,你不必外出朝拜。遵行这样的正法,而不向往世俗的正法,就能到达光辉的世界。”“光不在别处,就在自我中,凝思静虑,自己就能看到。……对所见所闻和一切众生一视同仁,摆脱对立,这样的人达到梵。对褒扬和贬斥等量齐观,对金子和铁石、快乐和痛苦也是如此。对冷和热、得和失、爱和恨、生和死也是如此,这样的人达到梵。”
和佛教一样,《摩诃婆罗多》还强调果报的作用。“人体原本是大神创造的。一个人用它做了大量的善业和恶业,一旦寿命结束,他抛弃衰亡的身体,立即转生,中间没有间隙。他自己所做的业,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他,产生果报,或者享福,或者受苦。”*《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第二册,第355、414页。种姓的差别固然重要,但行为更加重要。“如果一个婆罗门行为不端,走向堕落,桀骜不驯,专做坏事,那他就跟首陀罗一样。如果一个首陀罗始终奉行自制、真理和正法,我认为他就是婆罗门,因为婆罗门由行为决定。”“有的人大富大贵,有的人命途多舛;有的人降生即高门大户,有的人睁眼即贫贱人家。有的人丑陋不堪,形同朽木;有的人面容喜庆,人见人爱。有的人才疏智浅,有的人博学多识;还有人学问宏富,兼容并蓄,形上形下,无所不晓。有的人顺顺当当,有的人坎坎坷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行为的果报。*《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426、211、184页。甚至还勾勒出了行善者死后所去的天国的样子,和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极为相似。*《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426、211、184页。
二、 《摩诃婆罗多》与中国文学
《摩诃婆罗多》中的很多著名故事、神祗以及神异描写,甚至重复咏叹,都可以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找到它们的影子。虽然要找到直接的证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这可以开阔我们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以下略论其要者。同类故事如第三《森林篇》中“鹰与国王”*《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第二册,第258~260、211页。的故事,其实就是佛教中的“割肉贸鸽”。 这个故事很有名,见于《贤愚经》卷一第一则故事*[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大正藏》第4册。,以及如《大智度论》等其他很多佛经之中。*参梁丽玲:《〈贤愚经〉研究》,第五章《〈贤愚经〉故事与相关佛教故事之比较》,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18~219页。另据陈引驰《佛教故事口传方式的存在:〈大唐西域记〉佛教传说考述》,此故事还见于《六度集经》、《菩萨本生鬘论》、巴利文本生经等。*陈引驰:《文学传统与中古道家佛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4页。《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亦云:“古时候,尸毗王为解救鸽子而献出自己生命所达到的目的,通过施舍食物也能达到。”*《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第二册,第258~260、211页。《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中,投山仙人喝光海水的故事,也与佛经中的“大意抒海”故事类似。此故事见于《佛说大意经》、《贤愚经》、《摩诃僧祗律》等,并对中国元代尚仲贤、李好古撰《张生煮海》戏曲产生影响。陈明《抒海、竭海与拟海——佛教抒海神话的源流》,对此有详尽的考辨。*陈明:《印度佛教神话:书写与流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149页。《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讲大苦行者优多帖为了要回妻子,将水固化,然后调动能量,把它统统吸干,第六册,第452页。另可参陈开勇:《宋元俗文学叙事与佛教》,“张生煮海”,有较为详尽的考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而第十三《教诫篇》中的行落仙人的故事*《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426、211、184页。,则与《太子须大拏经》中的情节极为相似。*[西秦]圣坚译:《太子须大拏经》,《大正藏》第3册。

我们来看一下《摩诃婆罗多》中,对于一些主要神灵的描述。如写湿婆有四张脸、因陀罗有千只眼:“因为非常想看她(狄罗德玛),当她转到湿婆大神的右边时,他的右边就长出了一个脸,那脸上的眼睛紧紧盯住她。当她转到他的后面时,他的后面又生出一个脸;当她转到他的左面时,他的左面也长出一个脸!”*《摩诃婆罗多》第一《初篇》,第一册,第450页。而在第三《森林篇》中,描写阿周那与湿婆相遇,则把湿婆描写成一位三只眼的大神。*《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第二册,第78、84、93页。第五《斡旋篇》中写黑天:“螺号、飞轮、铁杵、长矛、角弓、犁头和刀剑,还能看到其他各种高举的武器,闪闪发光,出现在黑天的许多手臂上。”*《摩诃婆罗多》第五《斡旋篇》,第三册,第334页。第七《德罗纳篇》中,称湿婆“他有千头、千眼、千臂和千脚”,*《摩诃婆罗多》第七《德罗纳篇》,第四册,第428、431页。“他有千眼,万眼,周身都由眼睛组成,保护大宇宙,所以,他被称作大神。”*《摩诃婆罗多》第七《德罗纳篇》,第四册,第428、431页。第十二《和平篇》:“三眼神湿婆是从智慧的四面神(梵天)的额头生出的儿子。”*《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666页。而因陀罗因为勾引乔答摩的妻子阿诃罗耶,受诅咒身上长出千个印记,状如女阴,后来变成了眼睛,因此而得“千眼”称号。*《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138页,第449、459页。“创造了整个古代宇宙的,就是黑天。一朵莲花从他的肚脐中生出,莲花中又生出精气无限的大梵天。”*《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138页,第449、459页。中国古代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中有三眼杨戬,应该是受到了密教的影响,而密教归根结底,受到的是印度教影响。以色列学者夏维明(Meir Shahar)也有关于马王爷三只眼的研究,他把影响追溯到印度教的湿婆神。中国文学中的多头多手形象,主要是受到了密教影响,但最终也是受到了印度教诸神的影响,如《西游记》中的哪吒,而最著名的当然是千手千眼观音。英国学者杜德桥(Glen Dudbridge)著有《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英]杜德桥著,李文彬等译:《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年。,对此问题进行考察。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也有专章《大悲忏仪与千手千眼观音在宋代的本土化》,展开讨论。*[美]于君方著,陈怀宇、姚崇新、林佩莹等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第七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而除了佛教外,了解其印度教起源,可以帮助我们对此问题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
《摩诃婆罗多》中值得一提的神祗还有阎摩(Yama)。《梨俱吠陀》第十卷中已有《阎摩赞》,但这里面的阎摩王国,是一处天界乐园,而非痛苦的地狱。*参巫白慧:《〈梨俱吠陀〉神曲选》第135曲(作者为驹摩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7页。而《梨俱吠陀》第十卷第14曲的《阎摩赞》中,则描写了阎摩王有两条天狗作为助手兼保镖,它们天生各有四双眼睛,昼夜游弋人间,捕捉死人亡灵,并负责看守关卡,对前来的鬼魂进行严厉的盘问。*巫白慧:《〈梨俱吠陀〉神曲选》,第278、300、192页。而同卷的第10曲《孪生兄妹两神恋曲》,更是描写了一段乱伦的恋情,妹妹阎美(Yam)爱上了鬼魂王国的大君哥哥阎摩,希望能和他结成夫妇,同床共枕,以使人类后代能够不断繁衍:“阎摩爱欲情,打动我阎美。我愿同一榻,与他共缠绵。我愿如妻子,将身献夫子。合卺齐欢乐,如车之二轮。”但被严辞拒绝:“汝身与我身,不能相结合。私通己姐妹,称为有罪者。做爱寻他人,勿来骚扰我。汝兄善吉祥,无斯情欲想。”阎摩和阎美是人类最初由其产生的第一对孪生兄妹,而后者又完全同于《阿维斯特》所说的Yima和Yimeh(伊摩和伊妹)。
《摩诃婆罗多》中,多次提到阎摩,《教诫篇》中还讲述了一个阎王抓错人而把人放回的故事。*《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223、369页。那开吉陀去阎王处,又见同册第285页,阎摩向他说的话,后来成为《迦塔奥义书》。“出生以后,生命受苦和死亡之类的大事,全取决于阎摩王的使者。陷入轮回,受苦受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某个生命始终履行正法,而间有背离,那么他在来世就会先享福而后受苦。如果尽做违犯正法的事,那么他就会去往阎摩掌管的地方,在那里大受萁苦。他在来世也只能进入畜生的子宫。”阎王形象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影响巨大。美国太史文先生(Stephen Teiser)《〈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以及《幽灵的节日》,对此有专门的研究。*[美]太史文著,张煜译:《〈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美]太史文著,侯旭东译:《幽灵的节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有关地狱的研究,另可参陈龙:《地狱观念与中古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三《森林篇》中,提到一个专门偷取妇女胎儿的女鬼布多那,应该与后来佛教中的鬼子母有关。*《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第二册,第436页。关于鬼子母,请参张煜:《佛教故事群中的女性——以〈经律异相〉之记载为中心》,载《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佛教传入中国时,经常借助一些神异,以增强吸引力。*参丁敏:《中国佛教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主题与叙事》中之《汉译阿含广律中佛陀成道历程“禅定与神通”的叙事分析》及《佛教经典中神通故事的作用及其语言特色》,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以及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第六章《〈梁传〉中的神异与法术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摩诃婆罗多》中也有很多神异的描写,有的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似曾相识,有的增强了整部作品的神秘色彩与感染力,体现了古代印度人民惊人的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西游记》中孙悟空钻到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明]吴承恩著:《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摩诃婆罗多》第一《初篇》中,云发被阿修罗杀死后,焚烧成灰捣成粉末,被老师太白大仙吃到肚子里,得到老师传授的法术之后,破裂师父右侧肚皮走了出来;*《摩诃婆罗多》第一《初篇》,第一册,第190、385页。名叫何为的罗刹,潜入了斑足王的身体,让他备受折磨;*《摩诃婆罗多》第一《初篇》,第一册,第190、385页。第三《森林篇》中,迦利钻进了国王那罗的身体;*《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第二册,第111页。第五《斡旋篇》中,则有帝释天被弗栗多吞下后,众天神慌忙创造哈欠,让因陀罗紧缩自己的身体,从张开的口中逃了出来;*《摩诃婆罗多》第五《斡旋篇》,第三册,第121、435页。第十三《教诫篇》中,毗补罗为了保护导师的妻子不受因陀罗的侵犯,钻进了她的身体:“我将凭借瑜伽之力进入师母的身体,并像呆在空气里一般四面不靠。这样我就不会有什么冒犯的过失了。就像一个旅行者在旅途中寄宿空宅,今天我也不过在师母的身体里暂栖一时。我将自身置于她的体内,不沾骨肉,就像莲叶上滚动的露珠不沾叶子一般”。*《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149页。而第十五《林居篇》则描写了奴婢子维杜罗运用大瑜伽力,在死后进入了坚战的体内。*《摩诃婆罗多》第十五《林居篇》,第六册,第684页。
佛教文学中有不少神魔战斗与变幻的描写,如《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写舍利弗与劳度差斗法,甚至影响到《西游记》中孙悟空七十二变大战二郎神。《摩诃婆罗多》中也多这类描写,如第六《毗湿摩篇》写阿周那的儿子宴丰与罗刹斗法:“宴丰也能随意变形,熟谙一切要害,难以对付;他也腾入空中,用幻术迷惑罗刹,用箭射碎他的肢体。这位优秀的罗刹一次又一次被箭射碎,大王啊!但又恢复青春。这种幻术是天生的,他们能随意选择年龄和形象,因此,罗刹的肢体一次次破碎,又一次次恢复。”*《摩诃婆罗多》第六《毗湿摩篇》,第三册,第637页。第七《德罗纳篇》写怖军的儿子瓶首大战迦尔纳:“人们看见他很快又以各种新的身形出现在各个方向。接着,他变得身躯高大,有一百个头和一百张肚皮。只见这位大臂者高耸如同美那迦山。忽而这罗刹又变作大拇指般大小,像海浪似地猛地落下后,又斜向升起。他使大地裂开后又沉入水中,然而,很快就见他又从另一个地方浮出水面。”*《摩诃婆罗多》第七《德罗纳篇》,第四册,第358页。
神异的描写则如贡蒂生迦尔纳,贡蒂年少时,因为服侍仙人,而得到了能够召唤天神的咒语。她试着唤来了太阳神,后者令她生出了一个自带铠甲和耳环的男孩迦尔纳。但生完孩子后,她又回复了处女。因为贡蒂还没有结婚,她只好哭着把这个孩子放在篮子里,随流飘荡。这个故事和佛教《杂宝藏经》卷一中的莲花夫人生五百卵的故事相仿,后来甚至影响到中国包公戏中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摩诃婆罗多》第三《森林篇》,第二册,第566页。参李小荣:《〈狸猫换太子〉的来历》,《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以及[清]石玉昆述:《三侠五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一回“设阴谋临生换太子”。又如第五《斡旋篇》,木柱王的女儿束发为了不让希望得到儿子的父亲痛苦,向夜叉借男性生殖器官。而因为毗湿摩曾有誓言:“妇女,前生是妇女,有妇女的名字,有妇女的形体,我不会向这些人射箭。”后来在战斗中,坚战一方利用毗湿摩这个誓言,让束发驾驶战车,由阿周那射死了毗湿摩。第九《沙利耶》中,“罗摩割下了一个罗刹的头颅,将它远远抛出。这巨大的头颅正好落在仙人巨腹的腿上,粘在了那里。”*《摩诃婆罗多》第九《沙利耶篇》,第四册,第781页。头颅可以割下再装,不禁让人想起《封神演义》中的歪头申公豹的故事。*[明]许仲琳编著:《封神演义》,第三十七回“姜子牙一上昆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十二《和平篇》写两位具有“大人相”的古老而优秀的神仙:“胸前饰有吉祥卍字,头顶盘有发髻。他俩手臂上有天鹅标志,脚底有轮状标志,肩膀宽阔,手臂修长,有四个睾丸。有六十颗牙齿,八颗犬牙,面庞俊美,额头宽阔,双颊丰满,眉毛和鼻梁端正。”*《摩诃婆罗多》第十二《和平篇》,第五册,第647页。这样的描写,与佛教中关于佛陀的三十二相,颇为相近。*参张煜:《〈长阿含经〉中的譬喻、故事及其他》,《暨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2期。
在表现形式方面,饶宗颐先生《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认为《南山诗》连用或字五十余,是受到了来自佛经的影响。*饶宗颐:《梵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13页。而这样用“有的……有的……”来铺陈的句式,在《摩诃婆罗多》中也甚多见,可能是口头文学的某种特征。即通过重复和罗列,来加深听众的印象,有时即使漏掉一些内容,也并不影响对于整体意思的把握。如第十三《教诫篇》中,写因陀罗善于变化:“他一会儿是这个样子,一会儿又是另一个样子,多得难以胜数。有时他会佩戴顶冠,手持金刚杵;有时他会佩戴王冠,吊着耳环;有时他摇身一变,分明成了个旃荼罗。有时他会高束发髻,有时他会编起发辫,树皮遮身,当作外衣。孩子啊,有时他身高体宽,有时又瘦弱不堪。有时他面皮白皙,有时他肤色黧黯,有时他浑身黝黑。有时他丑陋无比,有时他貌美非常。有时他年轻英俊,有时他老迈蹒跚。……”*《摩诃婆罗多》第十三《教诫篇》,第六册,第148页。
又《摩诃婆罗多》中多喜用反复咏叹来增强感染力,中国曲艺多喜用这种形式。如苏州评弹《珍珠塔》中,陈翠娥小姐“下扶梯”,一方面心中急于想见到分别多年的方卿,一方面又有官家小姐的种种顾虑,所以每下一层扶梯就又踌躇不前,“站定娇躯不肯行”,而丫鬟采萍则以种种妙语来为小姐宽解,通过这种反复,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矛盾心理。*朱雪琴弹唱:《珍珠塔选回·下扶梯》,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发行。一般认为这种有说有唱的形式是受到了唐代变文以及佛经的影响。如《法华经》卷二十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以“应以……身得度者,即现……身而为说法”,罗列了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三种化身。*[后秦]鸠摩罗什译,[隋]智顗疏:《妙法莲华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这样的形式在《摩诃婆罗多》中,俯拾皆是,一般都是出现在情节最紧张与精彩的部分。例如第八《迦尔纳篇》,当坚战看到黑天与阿周那战罢归来,知道迦尔纳已被杀死,微笑着欢迎他们:“车夫之子(迦尔纳)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在战场上到处找你挑战,今天与你遭遇后,真的被你在战斗中杀死了吗?这个罪人为了探明你的下落,向众人悬赏一辆由最好的大象驾驶的金车,总是在战场上向你叫阵,贤弟啊!真的被你在战斗中杀死了吗?这个罪人是难敌的心腹好友,总是在俱卢族人集会上自吹自擂,自恃英勇,目空一切,今天真的被你杀死了吗?……”*《摩诃婆罗多》第八《迦尔纳篇》,第四册,第586页。文繁不作多引。再来看评弹大家蒋月泉先生弹唱的《宝玉夜探》:“妹妹啊,想你有什么心事尽管说,我与你两人共一心。我劝你么,一日三餐多饮食,我劝你么,衣衫宜添要留神。我劝你,养神先养心,你何苦自己把烦恼寻?我劝你,姊妹的语言不能听,因为她们似假又似真。我劝你么,早早安歇莫宜深,可晓得,你病中人,再不宜磨黄昏。我劝你把一切心事都丢却,更不要想起扬州这旧墙门。”一唱三叹之中,真是让人感觉何其相似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