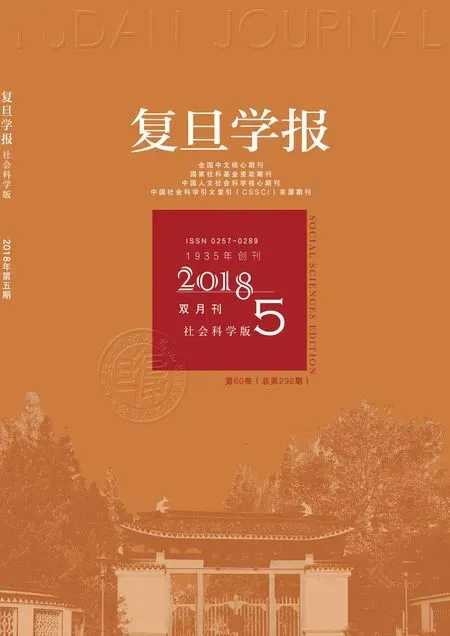朝贡制度转变的契机
——基于1873~1876年间《燕行录》的考察
王元周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在朝鲜半岛进入近代的前夜,掌权的兴宣大院君推行斥邪政策。经历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之后,更是执行严格的锁国政策,不愿与西洋各国缔约通商,甚至在全国各地竖立“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的斥和碑。面对西洋各国和日本的缔约通商、传教及和好要求,朝鲜朝野上下几乎只能以战守为大义。但是在1873年高宗亲政以后,朝鲜对外政策迅速发生转变,并在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岛条约》,朝鲜从此纳入近代国际体系,也被作为朝鲜半岛近代史的开端。
从1873年转变对外政策到1876年开港只有短短的两三年时间,由于此前大院君的极端锁国政策,导致朝鲜对外知识准备严重不足,所以在1873年以后急切希望了解日本、俄国和其他西洋各国的情况。而这时朝鲜了解外部世界的通道几乎只有中国。上述情况在1870年代前期的《燕行录》中也有反映。从18世纪开始,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日益扩大,且中国士大夫在鸦片战争以后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海国图志》等新书也很快通过燕行使传到朝鲜。那么,在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士大夫实际交往的层面,他们在时局认识与对策上是否存在深层次的交流?本文以《燕行录》为主要材料,通过考察朝鲜使行人员与张世准、万青藜和李鸿章三人交往的情况,对这一问题作了简略的回答。虽然考察的人物有限,但这三人具有代表性,一个是普通官员,一个是经常要接待朝鲜使臣的礼部尚书,一个是后来负责朝鲜事务的洋务大臣。通过1876年前这三人与朝鲜使行人员交往情况的考察,不仅有助于了解开港前朝鲜朝野的国际知识储备情况,亦可借以分析宗藩关系应对世界整体局势变化的灵敏程度,为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后来清韩宗藩关系的演变提供一个有用的角度。
一、 张世准
张世准,字叔平,号五溪,又号梅史,道光六年(1826)生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任内阁中书,后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龚方纬《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说张世准“善画墨梅,山水枯劲而淹润。住京久,与山阴周少白齐名。书法亦苍劲”。*龚方纬著,宗瑞冰整理:《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4、217页。
周少白即周棠,与朝鲜使行人员多有交往,“朝鲜人朝京师者,每乞其画归”。*龚方纬著,宗瑞冰整理:《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4、217页。张世准也是如此。同治二年(1862)以冬至兼谢恩副使身份到北京的朴永辅最早与张世准订交,此后即不断有朝鲜使行人员与其来往。张世准家住琉璃厂附近,与王士祯旧居相邻,朝鲜使行人员到了北京后都要去琉璃厂游览,而王士祯为海内诗宗,亦为朝鲜文人所推崇,所以去他家拜访也很方便。同治十二年(1873)到北京的朝鲜冬至使郑健朝等人即“因访阮亭旧宅遂造其第”。*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28、328、356页。
不过与周棠不同,张世准受朝鲜人推崇的主要是书法和诗,称赞他工书善诗。如后来代表朝鲜与日本签订《江华岛条约》的申櫶是有名的儒将,亦工书善诗,酷爱张世准的书法,曾将自己的数十幅作品求人带给张世准批评,并希望得到张世准的作品,于是张世准也以数十幅作品相送。所以后来姜玮在《奉呈张五溪世准员外为别》诗中说:“法书一纸,神交万里,渺若追仙三岛。也曾寄去也曾来,想了了才怜了了。”*姜玮:《奉呈张五溪世准员外为别》,《古欢堂收草·诗稿》卷十七,“诗余”。
朴永辅在朝鲜以诗文名于世,在北京也是与董文焕等人诗文唱和,并刊有唱和集。*赵冕镐:《秋怀八首,和寄天游》,《玉垂先生集》卷十,“诗”。他与张世准的交往应亦以诗文唱和为主。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二十四日朝鲜冬至使一行启程时,李建昌将他与郑基雨、洪岐周、李重夏四人的唱和集《韩四客诗选》交给姜玮,让他带到北京,请中国文人批评,姜玮即请张世准点评。*姜玮:《北游日记》,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第175页。姜玮也将自己的诗稿拿给张世准批评。*姜玮:《奉谢张叔平世准先生拙稿赐批后见赠之作,次韵》,《古欢堂收草·诗稿》卷十二,“北游草”。
然而,张世准与周棠最大的不同,是他在朝鲜人中还以“兼长策论”而闻名,郑健朝、姜玮等人在入燕前耳闻已久。*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28、328、356页。由此可知,张世准与朝鲜使行人员的交往并不仅限于书法和诗,也包括对时局的看法。鸦片战争以后,朝鲜使行人员在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中偶尔涉及洋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如道光十年(1859)冬至使行权大肯、金德喜、闵致庠、权时亨等人在与黄爵兹、钱江、杨熙和倪印垣等人笔谈时,不仅涉及黄爵兹、钱江等人个人经历和鸦片战争当时中英形势,也论及朝鲜军备问题。*权时亨:《石湍燕记·人》,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1,第222页。权百涵在《石湍燕记序》中肯定了权时亨在其燕行录中“多记与中国士大夫谈论文章”的做法,并说:“读至树斋翁九州八历、五岳四登之句语,顿觉禽尚寥寥,东平子伊江杂感又何其雄愤慷慨也。每于其精悍之眉睫,轮囷之腔血,未尝不掩卷嘘唏,而亦将大有望于来后尔!”*权有海:《石湍燕记序》,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0,第330页。
但是,曾经在咸丰十一年(1861)和同治十一年(1872)先后两次入燕的朴珪寿注意到,这期间北京士风已有很大变化,“老成者皆无甚兴况,且其有志者多如王顾斋之归里家食也。年少新进,皆不过词翰笔墨,而亦无甚超群者。所交虽多,而只是酒食相招邀,诙笑相乐而已”。*朴珪寿:《与温卿》,《瓛斋集》卷八,“书牍”。同治五年到北京的朝鲜谢恩兼冬至副使南一祐也觉得中国士大夫不愿意与朝鲜使行人员接触。他说:“汉人每多存嫌,不肯过从,满人则原不纳交,故结识未易,或于朝班谈话矣。”*南一祐:《燕记·回辕走草》,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第468页。
朴珪寿、南一祐等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自然有中国士风变化的因素,也有来自朝鲜方面的原因。张世准虽然在朝鲜人中亦以策论见长,但是他自称不愿意轻易与朝鲜人谈论时务,原因在于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已经基本接受了与西洋各国缔约通商的局面,而朝鲜人多年来始终一味主张战守,因此“情有所格,枢密之地,莫肯告也”。张世准在与郑健朝等人的谈话中,也提到他前后结交朝鲜名士有十数人,但是很少谈及自己的真实想法,虽或涉及也只是一些中国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斥和之论,如果稍微涉及议和通商之类的内容,朝鲜人就不愿意听。“弟之荒言无从而出。独遇尊兄,胸有定识,所虑者远,倾盖之地,处以肝胆,不施华采,笔笔悃愫,不识贵朝有如兄者几辈,与闻时议,何虑此事,此弟所以不揆谬妄,乐告而不倦也。”*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7、330~331、328~329、329~330、330~332、336、340页。
这次张世准之所以愿意向朝鲜人详细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是因为郑健朝等人因其“兼长策论”而主动以日本是否会侵略朝鲜问题向其请教。这样的谈话内容在《燕行录》中绝少见到,因此对了解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张世准这次愿意倾心相谈,但并非全无禁忌,每当“行文肯紧处与得意处,皆自下圈批而投诸火”。*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7、330~331、328~329、329~330、330~332、336、340页。
根据姜玮《北游日记》推测,《北楂谈草》所记郑健朝等人与张世准的笔谈时间应为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十三日,次日姜玮再次持郑健朝书信往访,笔谈内容即《北楂谈草》附录《古欢谈草》。在这前后郑健朝、姜玮等人与张世准还有多次交往,但是并不涉及时务。正月十三日的笔谈是郑健朝、姜玮早饭后从玉河馆去拜访张世准,在张世准的双鱼罂斋进行的,郑健朝和姜玮日暮始归,双方谈了整整一天时间。
郑健朝和姜玮之所以向张世准打听日本的情况,是因为听说同治十二年(1873)到中国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的日本使臣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在觐见中国皇帝时有侵伐朝鲜之语,想打听日本使臣与中国皇帝和总理衙门等谈话的内容。*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7、330~331、328~329、329~330、330~332、336、340页。其实副岛种臣等在与李鸿章会谈时谈到征韩问题,觐见同治皇帝只是一种仪式,不可能有如此深入的谈话。而朝鲜之所以重视日本使臣觐见同治皇帝一事,是因为同时觐见的还有英、法、俄、美和荷兰五国公使,朝鲜担心日本会与他国联合侵伐朝鲜。对于郑健朝和姜玮的问题,张世准只是说:“此是总理衙门慎密办理勾当,有非外廷臣人人预闻者。则虽或有耳目所及,无异乎途听途说,徒乱人意,而究无益于事。然天下之事,据理以断,不中不远。兄若无问其事,只问其理,则亦有可言者,未知兄意,以为如何耶?”*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7、330~331、328~329、329~330、330~332、336、340页。此后张世准的论述都是以这种基调展开的。
张世准从当时中国的情况说起。虽然中国全国上下都痛恨洋人,但是皇上并没有号召驱逐洋人,是因为认识到“今天下大势迥异前古”,不得不包容外夷,采取“以我之礼义治夷”的政策,强调“是乃天子理天下之理也”。*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7、330~331、328~329、329~330、330~332、336、340页。他指出朝鲜现在面临俄国和日本两大威胁,亦当量力度势,只能“修我礼义以示不可逾之形”,切不可舍长取短,轻易言战。这是张世准的基本主张,与当时朝鲜国内一味主战斥和正好相反,所以郑健朝和姜玮虽然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也提到回国后无法向国人阐述这种主张,“轻发此论,将得罪于国人矣”。
对于张世准以俄国和日本均为朝鲜之大患的看法,郑健朝和姜玮问道:“倭人寻衅,已是敝邦梦不到之事,而至于俄人则尤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情形何如而亦虑为患?”*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7、330~331、328~329、329~330、330~332、336、340页。张世准强调俄国与日本关系密切,有可能联合起来侵略朝鲜。这也正是朝鲜所担心的,所以郑健朝又问起日本使臣觐见同治皇帝,以及与李鸿章会谈的情况,张世准仍以此系军门机务密语推脱,最后郑健朝只得请他“以所闻,酌之以理”,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于是张世准说,日本虽然与英法等国关系也比较密切,但对于是否会联合起来侵略朝鲜,不可单凭猜测。对于朝鲜来说,重要的不是日本会不会侵韩,会不会联合他国来侵,而在于早图自强,所以他说:“我苟有备,以战以款,其权在我,我苟无备而听于人,则以中国之大尚不堪其苦。所望于贵邦者,幸以中国为鉴,早图有以自强也。”*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7、330~331、328~329、329~330、330~332、336、340页。张世准对这句话也加了圈批,也是他想格外强调的主张。
但是,当时朝鲜朝野上下尚未认识到韩日纠纷的严重性,必须等到战争爆发才会改弦易辙,所以郑健朝想知道日本何时会发动战争。这当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张世准只是推测俄、英、法等国不会马上与日本联合侵略朝鲜,朝鲜应该还有谋求自强的时间。郑健朝又提到,朝鲜自丙寅洋扰以后也在整顿军备,但是因不了解外国情况,所以无必胜之信念,因此希望张世准“详述彼我长短之形”。张世准也强调了解外国情形的重要性。他谈了中国人对西洋认识的变化,强调中国人自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之后,与洋夷相处十余年,彼此相安,说明与历史上少数民族内迁引起战乱情况不同,而且“夷之技巧,类皆前古之所未闻,如火轮舟车之运驶,电机寄信之神捷,铁路土路之便利,火枪火炮之精良,夷不自秘,乐以示人,至为设厂制造,以资贸迁,是则夷之愿欲,不在于土地人民,而专以开通异域为念,此又我人之所不料也。各国之人,并集群处,乐闻公议,不主己见,以英夷之桀骜不驯,听断于人,再次让疆,见称诸夷,是知道理之当先,而不专恃其强悍,此弟所谓仍可以我礼义治夷者也”。*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1~352、354~355、358、365、367页。张世准所说的天下之大变局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所以,处于这样的一个大变局之中,防夷之策亦不能不发生变化,因此他建议朝鲜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不仅可以了解外国情形,亦可让外国人了解朝鲜,“因是以通两国之好,互释从前之憾,理之宜然者十之七”。*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1~352、354~355、358、365、367页。
然而郑健朝承认朝鲜国内舆论“势若至于战而后已”,而他作为当事重臣则不可不有所筹措,所以他还是更关心从战守的角度来说,朝鲜有何良策。*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1~352、354~355、358、365、367页。对此,张世准不愿多言,只是说:“势苟至于战而后已,是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然而“事固有不在天而在人者”,从人可为的角度来说,朝鲜或可坚壁清野,据险固守,但是此策或可用来对付俄国,但是朝鲜的威胁并不止俄国一国而已,“夷苟兴师,必联俄倭,万一倭蹈南境,俄蹑北界,西夷冲其腹心,则蹂躏一国而有余矣”。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无论有何良策皆无济于事,所以张世准强调还是要了解外国,设法排解纠纷。张世准还提到,当年李舜臣也是通过茅元仪所著《武备志》知道日本人不习水战,所以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强调:“今西夷各国情形之书,咸萃京师,就使有远虑者观之,知所择矣。此弟所以乐为吾兄道也,贵在悉彼我之情,决机善用,未必别有奇计异筹之可求者也。”*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1~352、354~355、358、365、367页。
双方谈到这里,郑健朝说:“尊兄此论,可谓彼此两尽,无复余蕴。”但是郑健朝依然强调朝鲜国内舆论一味主战,他也是“舍战而外,断不敢措一辞效一策”,所以张世准说的这些对朝鲜来说暂时无用,朝鲜只能寄托于中国自强之后有廓清之功,朝鲜也因此得以自保;所以他又向张世准请教中国内修之策,实际上是想探讨一下中国是否有能力保邦御敌,而张世准对此更不愿多言,推脱说非他这样十年不调之郎官所能及,宜与枢密机务大臣讨论此事。*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51~352、354~355、358、365、367页。双方的谈话到此结束。
显然,郑健朝、姜玮兴犹未尽,所以第二天姜玮又带着郑健朝的信再去拜访张世准。见到张世准后,姜玮首先就问:“昨日之谈,止于此而已乎?”张世准也承认:“此只做到半截之文也。”姜玮追问是否还可以继续做下半截文,张世准说:“究不合于时,则昨谈已冗。且上半截文尚可做,下半截文不可做,上半截事尚可做,下半截事尤不可做。”张世准之所以认为“下半截文不可做”,是因为他担心“言苟泄也,则非徒无益于事,而或至于反败其事”。姜玮表示他们决不敢泄露出去,而在张世准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非敢然也,然兄欲闻此者,意在裨于国事万一耳,岂肯自秘,止观成败,以验愚言之中否而止哉?然则不得不以示人,且闻于朝而待举国之有成论,虽欲勿泄,可得也耶?”*郑健朝:《北楂谈草》附《古客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68~369页。事实上亦正如张世准之所料。李建昌提到,姜玮回国之后即将他与中国士大夫的笔谈内容整理出来给他看,内容“皆旧所禁讳,使人骇怖”,而姜玮“且读且噫且笑,意气流动”,李建昌则默然无语。*李建昌:《姜古欢墓志铭》,《明美堂集》卷十九,“墓志铭”。不仅李建昌等友人见过,而且在朝鲜应广有流传。光绪六年(1880)十月金平默所作《策略小辨》,在怀疑《朝鲜策略》为朝鲜人假托黄遵宪之名所作时,也提到《北楂谈草》。金平默说:“姜紫杞燕楂谈草,亦恐类此,未必皆张世准之言也。”*金平默:《策略小辨》,《重菴集》卷三十七,“杂著”。
显然,张世准对郑健朝反复强调朝鲜国内舆论一味主战、他也无能为力的说辞感到失望,觉得他与以前所交往的朝鲜士大夫并非截然不同。确实,张世准的一番宏论对郑健朝也许影响不大。虽然郑健朝与姜玮两人关系密切,且皆留心时务,然而姜玮为在野儒生,而郑健朝则为朝中重臣,所以郑健朝不能不更加谨慎。郑健朝回国后,在向高宗复命时,虽然对于同治皇帝接见日本和西洋五国公使起因的解释与张世准的说法类似,但是更强调有御史上疏反对而意见未被采纳,以致高宗因此产生中国“纪纲比前委靡,示弱于外国甚矣”的认识。郑健朝顺着高宗的意思,进一步强调这是中国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对外夷采取抚绥策略的结果,并对中国前途表示担忧。当高宗问到中国是否会驱逐洋夷时,郑健朝回答说:“中国物情,莫不有此心,而洋夷之留接已久,猝难驱出云,必是事势所拘矣。”*《承政院日记》第2799册(脱草本第130册),“高宗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壬申”,第117b、119a页。对于张世准的核心观点,郑健朝只字未提。即使到光绪元年(1875)五月初二日高宗召见时原任大臣、议政府堂上官商议是否接受日本书契问题时,郑健朝对自己的主张也只作了模棱两可的表述:“今若严辞责退,则交邻之谊,虑有失和。然揆以事体,遽难捧入,惟愿博询而裁处焉。”*《承政院日记》第2813册(脱草本第131册),“高宗十二年五月初十日丙午”,第29a页。此后在讨论洋扰和海防问题时,他更沉默不语。
而姜玮本来就“三教九流,无不贯穿,而尤致力于四子书,间出入孙、吴形势之言,好论天下大事,视世俗不达变者,闷焉若己之疾也”。*李重夏:《本传》,姜玮:《古欢堂收草·文稿》。他在北京“遍交名士大夫”,“尽探中西近事而归”大概也是因其有备而来。也正因为这次赴燕有很大收获,所以次年又随冬至兼谢恩使书状官李建昌再次赴燕。这次燕行时,姜玮也带有郑健朝给张世准的信函,途中姜玮在给郑健朝的信中说道:“菽侯、罂斋两处,俱当在意,信致盛函。”*姜玮:《上郑蓉山尚书健朝书》,《古欢堂收草·文稿》卷二,“书”。李建昌不仅是姜玮的诗友,而且也“颇留心明史外夷名目,及近日中国战和之迹”*李建昌:《姜古欢墓志铭》,《明美堂集》卷十九,“墓志铭”。,他到北京后与张世准也有交往。这次冬至兼谢恩副使沈履泽的《燕行录》记载,他因李建昌而接见了张世准,同治十四年(1875)正月二十六日三使同游琉璃厂时,也顺便去拜访了张世准。*沈履泽:《燕行录》,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第238页。但是,李建昌和姜玮这次与张世准的交往似乎并不密切,李建昌的《北游诗草》和姜玮的《北游续草》中皆没有与张世准的唱和诗。李建昌交往较深的是黄钰、张家骧、徐郙等。*李建昌:《明美堂诗文集叙传》,《明美堂集》卷十六,“传”。姜玮《古欢堂收草》中收有一篇与黄钰的谈草。因当时清朝礼部转咨朝鲜,日本从台湾撤兵之后可能会出兵朝鲜,姜玮想打听详细情况,并想向黄钰请教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洋各国交往中的几个问题。*姜玮:《谈草与黄孝侯钰侍郎(甲戌)》,《古欢堂收草·文稿》卷三,“补遗”。可惜只能看到姜玮起草的问题,而没有黄钰的回答,是否与黄钰进行过关于这些问题的笔谈亦未可知。
不管怎样,姜玮在此次回国之后,因朝鲜国内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则稍摅发其所蕴,遂益有名”,*李建昌:《姜古欢墓志铭》,《明美堂集》卷十九,“墓志铭”。并作为幕僚辅佐申櫶与日本签订了《江华岛条约》,然而此后姜玮仍郁郁不得志,且穷困益甚。而张世准则弃官离京,游历川黔一带名山大川,光绪七年(1881)才回到沅陵定居。
二、 万青藜
万青藜自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调任礼部尚书后,担任此职十余年,与朝鲜使臣常有接触。同治五年(1866)到北京的朝鲜冬至使李兴敏在结识万青藜后,第二年即在给万青藜的信中提及丙寅洋扰。虽然内容与朝鲜国王给清朝礼部的咨文大体相同,万青藜在收到信后还是觉得于私人信件中讨论此事有违体制,于是将李兴敏的信附在朝鲜咨文的后面一同上奏,并随礼部给朝鲜国王的咨文发回朝鲜。朝鲜朝廷也认为陪臣不应私自写信给清朝大臣,对李兴敏加以处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45、165页。同治十年(1871)正月,美国公使镂斐迪请总理衙门通过朝鲜公使代寄信函给朝鲜,总理衙门明里拒绝,暗中还是奏准通过礼部代递。礼部虽然于二月初二日将信函交给兵部,由驿站转递朝鲜,但是对总理衙门的做法有意见,所以在转递的同时上奏称:“臣部于朝贡各邦,向皆按例咨行,从无转递书函事情,良以体统所系,不得不恪守旧章。此次美国封函一件,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由臣部转递朝鲜,自是一时权宜之计,故臣部未敢拘泥。第恐各外国纷纷援照申请,将来必有窒碍难行之处,应请嗣后如有各国书函,臣部仍遵旧例,不为代递,以全体制。”
上述两事,足以说明万青藜作为礼部尚书,固守朝贡体制,但是并不能说明万青藜个人不关心朝鲜的情况。相反,他对朝鲜国内的斥邪卫正运动颇为关注。当总理衙门奏请通过礼部代递美国致朝鲜书信时,朝鲜冬至使正在北京,对事情始末应该有所耳闻。所以正使姜回国后,四月十七日入侍时说:“今番咨文,自礼部再三阻却,而亦恭亲王力劝出送之。今则天下皆知我国之必不通商,若一许和,则当为天下笑矣。”万青藜因此在朝鲜博得好名声。而且他对大院君的锁国政策持赞同态度,甚至与大院君也有联系。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初二日万青藜在与朝鲜冬至使郑健朝等人的谈话中提到,年前大院君曾送给他一个刻有“斥邪卫正”四字的墨笏。万青藜赞同朝鲜的“斥邪卫正”政策,但是他在与人交往中从来不公开提及,甚至连大院君送给他的墨笏也秘不示人,恐泄露出去,为其他国家所知。*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22、318~319、320~321、321、322、322、322页。
在此期间,万青藜与朝鲜使臣一直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而且也包括后来在对日政策上与大院君意见相左者。同治十一年(1872)朴珪寿以进贺正使赴燕,即与万青藜交往密切,万青藜还坚持以兄弟相称,所以朴珪寿后来在给万青藜的信中以“庸叟尚书老弟大人阁下”相称。朴珪寿曾到万青藜的咫村书屋与其私谈。朴珪寿回国后,曾在给万青藜的信中说:“向在都下,不过一再私觌,半是商量使事,若夫学术经济,久欲质诸大雅者,却不及倾倒囷廩。”*朴珪寿:《与万庸叟青藜(之一)》,《瓛斋集》卷十,“书牍”。那么,朴珪寿与万青藜所谈“学术经济”应该也涉及时务,朴珪寿在给万青藜的另一封信中说道: “即者部咨到国,亦关系忧虑,不比寻常。曾在咫村对话,亦尝虑及于此,何尝少弛于中耶!”*朴珪寿:《与万庸叟青藜(之二)》,《瓛斋集》卷十,“书牍”。
同治十二年(1873)朝鲜冬至使郑健朝等人到北京后,也希望有与万青藜私谈的机会。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初七日郑健朝派首译送信给万青藜,请求见面,而万青藜托以有事,说等有空自当通知朝鲜使臣,不需要频繁来问。*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22、318~319、320~321、321、322、322、322页。直到正月底仍然没有消息,郑健朝等人等不及,又派首译去打听,万青藜才答应于二月初二日与朝鲜三使会面。到了这一天,朝鲜三使来到万青藜家,万青藜也在咫村书屋接待了他们。此次谈话的内容也载于《北楂谈草》。
《北楂谈草》中特注明,因此次谈话“辞涉番情,随书随毁,防语泄也。归馆后,三使会坐,追记辞意,无以尽诵本文,故不类中朝人笔墨,览者谅之”。可见万青藜对这次谈话是相当谨慎的,此前一再推辞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在这次谈话中,万青藜十分关心朝鲜的兵备,并提到中国设神机营的好处。郑健朝等人说明朝鲜自丙寅洋扰以来也重视兵备,更强调“石坡君侯十载苦心,颛用于诘戎一事,凡系选炼之方,靡不用极”,然而“究竟当用与否,何能预图?专仰天朝,以必胜之道,指授方略”。*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22、318~319、320~321、321、322、322、322页。
像张世准一样,万青藜也认为朝鲜之大患在于俄国和日本。他说:“贵国似有二患,东之倭,北之俄也。俄人近来骤强,虎视眈眈,侵占邻壤,尤宜预备严防也。”*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22、318~319、320~321、321、322、322、322页。郑健朝等人说朝鲜对日本无端寻衅已是万万没想到,对于俄国更是一无所知,所以朝鲜特别想了解俄国和日本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万青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彼以礼来,我以礼答之,不以礼来,以礼拒之,慎勿生衅也。”*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22、318~319、320~321、321、322、322、322页。可见,万青藜虽然赞同朝鲜的“斥邪卫正”政策,并建议朝鲜加强兵备,但是也希望朝鲜不要轻易与外国发生冲突。也许郑健朝等人也感受到了万青藜在主张上的自我矛盾,所以不明白万青藜说此话的用意,正要进一步追问,万青藜又在另一张纸上写道:“洋夷之至今敬惮贵国者,即由石坡坚守斥邪之功也。”*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22、318~319、320~321、321、322、322、322页。他听说大院君患了眼疾,不能正常处理政务,因此担心外国会乘机强迫朝鲜缔约通商。*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22、318~319、320~321、321、322、322、322页。随后又谈及日本的情况,万青藜也认为日本“便是新造洋国也”,与朝鲜国内斥邪卫正派的倭洋一体论认识相近。郑健朝等人也问及西洋各国的情况,万青藜提到法国正与越南交兵,大概也是同张世准一样,由此判断西洋各国暂时不会与日本联合侵略朝鲜。
朝鲜之所以不愿意与西洋各国缔约通商,一是担心鸦片会流入朝鲜。郑健朝等人在赴燕途中听说清朝禁烟不甚严格,万青藜也承认禁烟只限于近畿而已,外省则不加过问,而且说:“道光间,禁律太严,驯致洋变,此林文忠公则徐不能深长虑之过也。”*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26、327页。天主教传播是朝鲜担心的另一问题,所以郑健朝等人又问:“中土既广,包藏渊薮,譬如大地之无所不容,然今容异学参错于首善之地,能无渐染之虑也否?”万青藜回答说:“中土则读书士大夫无一染迹邪教者,彼染邪之类,不过自起自灭而已。”可见,在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上,万青藜也相当保守。
最后,万青藜提到他与朝鲜使臣私下接触的顾虑。他说:“敝职适忝礼部,故得与贵国使臣交接,若移他部,则不必相接者。朝廷亦有议论,所以尤所不敢也。”郑健朝等人说:“中朝之于小邦,恩眸覆焘,阁下之于石坡,义同友于,何可以不在其位而越规耶。”*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26、327页。虽然郑健朝等人这样说,但当他们再次约见万青藜时,万青藜还是以没空为由推脱了,直到二月初十日三使到礼部领下马宴时才再次见到押宴的万青藜,此后再也没有私下见过面。
实际上,在郑健朝等人与万青藜私下笔谈之前,大院君已经称病下野,高宗亲政,闵氏一族掌握了政权。此事对与大院君关系密切的万青藜有何影响,尚不得而知。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因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预测日本在从台湾退兵后可能联合法国和美国攻伐朝鲜,总理衙门再次奏请通过礼部密咨朝鲜,礼部仍然照做。六月二十九日,担任右议政的朴珪寿通过朝鲜因此派往北京的咨官带给万青藜一封信,在信中也提到此事,说明朝鲜朝廷正在商议对策,并派咨官到北京请示机宜。*朴珪寿:《与万庸叟青藜(之二)》,《瓛斋集》卷十,“书牍”。朴珪寿在信中强调:“东国不娴兵事,况升平恬嬉,其所云缮甲治兵,徒大言耳,都不识伐谋消兵为何等语,只自贾勇夸胜,是岂知彼知己者耶?”*朴珪寿:《与万庸叟青藜(之二)》,《瓛斋集》卷十,“书牍”。朴珪寿希望万青藜能帮助斡旋,由中国援引《中日修好条规》中有关双方所属邦土不得侵犯条款来劝阻日本。他说:“排难解纷,虽中朝亦无如何,固已知之。然曾闻日本约条,有不侵中国属国等语,今彼之来京立馆者有之,则其必有管事人一如洋人之为矣。据其约条而诘责之,劝谕之,不患无辞。朝廷若念及于此,实排难解纷之一道矣,此非老弟礼部堂官之职也?然为中朝诸大人诵及此语,则不无其道,幸留心周旋,如何如何?”*朴珪寿:《与万庸叟青藜(之二)》,《瓛斋集》卷十,“书牍”。
咨官带回了万青藜的回信,“纚纚千百言,情挚意笃”。可惜没有见到原文,不知万青藜具体谈了些什么。而这时朴珪寿已辞去右议政一职,改任判中枢府事这样的闲职。这年朝鲜冬至使赴燕时,朴珪寿虽然也托人给万青藜带去书信,但是没有提及朝日交涉等时务。*朴珪寿:《与万庸叟青藜(之三)》,《瓛斋集》卷十,“书牍”。朝鲜冬至正使李会正、副使沈履泽和书状官李建昌,以及跟随李建昌到北京的姜玮等人也没有与万青藜私下笔谈的记载。万青藜给朴珪寿的回信也只是一些问候之辞。而到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朝鲜朝廷终于决定接收日本书契。可见,万青藜在大院君下台之后对私下接触朝鲜人更加谨慎,在朝鲜政策转变的关键时期,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三、 李鸿章
同治十一年(1872)朴珪寿以进贺正使到北京时认识了吴大澂,吴大澂送给他一套《曾文正文钞》。他后来在给吴大澂的信中说:“归而读之,景仰钦服,恨不得及门于在世之日,以尽天下之观也。文章勋业,学术经济,兼全备具,求之前代,未有盛焉。盖天于圣代,生此伟人,为儒者吐气耳。此书只是文钞,未知全集可有剞劂完本否,一睹为快,而恐未易得也。曾公卒于壬申,而岳降在于何年,其寿几何,幸示之如何?”*朴珪寿:《与吴清卿大澂》,《瓛斋集》卷十,“书牍”。由此可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虽然当时在中国已经是权倾朝野,誉满天下,但像朴珪寿这样关心时事的朝鲜士大夫对他们仍然知之甚少。
其实,同治十一年(1872)总理衙门奏请通过礼部代递美国公使镂斐迪给朝鲜的书信后,二月初一日又函知南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和李鸿章,让他们防备日本暗中帮助美国公使镂斐迪前往高丽寻衅。*“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 第165页。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从这时期一直关注朝鲜防务,在朝鲜问题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郑健朝、姜玮在与张世准的笔谈中,也提到李鸿章。郑健朝说道:“闻倭使回到天津,见李相,又发侵伐敝邦之语,李相复以言辞痛斥云。”*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37、338、338页。但是郑健朝这时尚不知“李相”的姓名,也不知他官居何职,更不知日本使臣为何要到天津去找李鸿章谈朝鲜问题。张世准解释说:“李相,名鸿章,屡树战功,勋庸茂著,位至台司,而以畿辅多事,屈为直隶总督。曾文正公殇后,代膺此任,朝廷倚为长城,外番亦所信服,不信晋楚之盟,而要季路一言,李相殆或近之,因此弭患,何幸如之!”*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37、338、338页。郑健朝等人想知道日使副岛种臣与李鸿章会谈的具体内容,因有关内容已经传到朝鲜,所以郑健朝等人认为此事应不慎密,张世准应该能据实详告,而张世准仍以此“系军门机务密语”为由不愿回答,并劝郑健朝等人不可轻信闾巷传言。*郑健朝:《北楂谈草》,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78,第337、338、338页。
同治十三年(1874)到北京的朝鲜进贺兼谢恩使对李鸿章也颇为关注,不过所得消息也多闾巷传闻。回国后,当高宗问北京是否有很多西洋人和日本人时,副使李淳翼回答说:“洋人不过几名,倭则比诸洋愈少。而九月,洋人近万名来泊天津,有求爵通婚,及通州、天津收税等难从之请,直隶总督李鸿章有智略,阵于天津以拒之,而洋人若有侵扰,则直当剿灭之意,告于朝廷云。此非文迹之得见,而传闻盖如此矣。”*《承政院日记》第2819册(脱草本第131册),“高宗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己巳”,第70a~70b页。
光绪元年(1875)八月“云扬号事件”发生后,日本派森有礼出使中国,也曾到保定与李鸿章会谈,朝鲜方面也非常关注此次会谈的内容。这一年的朝鲜奏请使李裕元在其《蓟槎日录》中收录了《天津保定府李中堂与倭使森有礼问答记》,但标明为“都京礼部咨文马上飞递”,可见是抄录礼部咨文中的内容。*李裕元:《蓟槎日录》,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第310、295页。不过在后来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提到李裕元在北京时曾与继格等人密商和战两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63、363、373~374页。也正因如此,所以李裕元在回国途中经过永平府时,主动向游智开提出愿意结交李鸿章。在游智开询问缘由时,李裕元也表示希望与李鸿章讨论时务。他在《蓟槎日录》中记载说:“余遂道日本相关事如我有国事之可议,非此中堂莫可为之。”*李裕元:《蓟槎日录》,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第310、295页。后来李裕元在解释此时的意图时也说,因李鸿章“乃中原首阁老也,或有相资之力”。*《承政院日记》第2890册(脱草本第133册),“高宗十八年闰七月初八日戊戌”,第14b页。
在李裕元的再三请求下,游智开答应为其转递书信,从此李裕元与李鸿章之间建立了书信往来。而李鸿章也许正因为听说李裕元在与继格等人的交往中表现出了胜于一般朝鲜人的见识和谋略,觉得他“老成宿望,亦颇晓畅时事”,所以才愿意跟他通信,并想以此影响朝鲜的对外政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63、363、373~374页。然而,直到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朝鲜冬至使南廷顺等人复命时,高宗仍在问“李鸿章何人?何如也?”的问题,可见高宗仍不了解李鸿章。对于高宗的问题,南廷顺回答说:“方以直隶,出住天津,威望所注,洋倭慴伏,人心赖以镇压云矣。”书状官尹致聃补充说:“概概有所载于闻见录矣。”*《承政院日记》第2823册(脱草本第131册),“高宗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癸丑”,第72b页。可见了解李鸿章的情况,已成为朝鲜燕行使觇国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朝鲜对李鸿章的了解越来越多,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八日回还告讣使入侍时,高宗曾问道:“今则恭亲王不预朝政,而李鸿章为主管乎?”书状官洪在瓒说:“然矣。”*《承政院日记》第2856册(脱草本第132册),“高宗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癸酉”,第68b页。可见高宗业已掌握清朝政局的变化。
然而,李鸿章对朝鲜国内情况仍几乎一无所知。光绪五年(1879)七月四日,总理衙门奏请通过李鸿章与李裕元的书信往来,将五月间丁日昌所陈各条作为李鸿章个人的意思转给朝鲜,劝朝鲜与西洋各国缔约通商。而直到这时,李鸿章对李裕元的情况仍不十分了解,在奏折中称:“查李裕元现虽致仕,据称系国王之叔,久任元辅,尚得主持大政,亦颇晓畅时务,如能因此广咨博议,未雨绸缪,庶于大局有裨。”当时总理衙门虽然认为“泰西各国欲与朝鲜通商,事关大局”,但是拘泥于宗藩体制,顾及“惟该国政教禁令亦难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鲜,而愿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问”,于是不得已而采取此下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61页。但是不仅李鸿章与李裕元的私交不可靠,而且对李裕元的为人以及其在朝鲜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都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李裕元虽曾任领议政,光绪元年出使中国前已经辞职,而任领中枢府事的闲职。他也自动疏离权力中心,常居乡第,不仅请辞各种兼职,也陈疏乞求退休。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上旬因参加初十日的朝会而暂时上京,朝会一结束即欲回乡第。*《承政院日记》第2869册(脱草本第132册),“高宗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己卯”,第26b页。
这年(1879)九月,李鸿章劝朝鲜和洋御倭的书信飞报李裕元。因李裕元在乡第养病,耽误了一个多月。李裕元回到汉阳后,遂与诸大臣共同商议,正面拒绝了李鸿章的建议。*《承政院日记》第2890册(脱草本第133册),“高宗十八年闰七月初八日戊戌”,第14b页。十一月十二日李裕元写了答书,交给尚在义州的谢恩兼冬至使带到中国,让他们仍通过游智开转给李鸿章。当他们抵达永平府时,因游智开不在,只好将信函带到了北京。十二月二十六日,首译卞元圭听说游智开在北京城外,五鼓潜往传递了信函。*南一祐:《燕记·玉河随笔》,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第394、415~416页。次年(1880)正月十七日,卞元圭要去保定与李鸿章面议军务,为衙门提督所阻,正式向礼部提出请求,也没有得到批准。*南一祐:《燕记·玉河随笔》,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第394、415~416页。后来有朝鲜别咨官到天津,回来告诉李裕元,李鸿章对此事未奏效也有所惋惜。此后李鸿章再致书李裕元,李裕元竟不再回信。*《承政院日记》第2890册(脱草本第133册),“高宗十八年闰七月初八日戊戌”,第14b页。光绪七年(1881)辛巳斥邪运动中,李裕元因与李鸿章私自通信而受到攻击,被施以窜配之典。
李鸿章与李裕元书信往来的非正式联系渠道,虽然因总理衙门奏请利用这一渠道劝朝鲜与西洋各国缔约通商而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但是并没有带来宗藩体制的根本变化,更没有在近代清韩交往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朝鲜方面虽然拒绝了李鸿章的建议,但是对李鸿章处处维护朝鲜还是心存感激。光绪六年(1880)四月初二日谢恩兼冬至使复命时,高宗即说:“李鸿章为我国事随处曲念,诚非偶然矣。”正使韩敬源也说:“其用心甚感服矣。”*南一祐:《燕记·回辕走草》,林基中、夫马进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第468页。
然而朝鲜人对李鸿章的认识也有差异。李建昌就对李鸿章劝朝鲜与西洋各国缔约通商有相当负面的评价,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他说:“李鸿章贻书于我,啖以通和之利,时人皆谓鸿章,中国名臣,其言可信。建昌独曰:鸿章,大侩也。侩惟时势之从而已,我无以自恃而恃鸿章,则后必为所卖。”*李建昌:《明美堂诗文集叙传》,《明美堂集》卷十六,“传”。李建昌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大概与燕行给他留下的负面印象有关。李建昌在其所撰《姜古欢墓志铭》中说:“明岁余又赴燕,君又从,既至,余所见闻,或与君同异,然固不以君为无徵也。及归,事遽悉改,纵衡驰骛之士,公道天下事,莫可防制。余自忖愚不足预,遂悉谢遣胸中所往来以日趋愦愦,而君则稍摅发其所蕴,遂益有名。”*李建昌:《姜古欢墓志铭》,《明美堂集》卷十九,“墓志铭”。可见,李建昌与姜玮在中国的见闻不同,并导致他们回国后对朝鲜对外政策转变的反应也有所不同。李建昌充分感受到中国之衰弱,并为朝鲜的前途担忧。他在《明美堂诗文集叙传》中说:“初朝廷斥倭洋主战守,然实不得其要领,建昌以为忧。尝曰:‘中国者,外国之枢也,如入中国而善觇之,则可以知外国之情。’既入中国,则叹曰:‘吾犹不知中国之至于此也。中国如此,吾邦必随之而已。’”光绪三年(1877)四月初四日朝鲜谢恩兼冬至使复命时,正使沈承泽对中国的评价也很低,对高宗描述说:“大抵主少国疑,人心涣散,朝廷未有主张,民业只趋末利,已具于书状官闻见事件。而以臣所见,亦多慨叹之事矣。”*李容学:《燕蓟纪略》,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98,第99页。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初七日谢恩兼冬至使三使臣辞陛时,高宗也说道:“向见皇历赍咨官手本,则琉球国王为倭所执,而至有请救于李鸿章与礼部之举,而终不能救,大国之柔弱,亦可知矣。”*《承政院日记》第2869册(脱草本第132册),“高宗十六年十一月初七日丙子”,第17b页。高宗因此要求三使臣详探其实情以报,可见高宗这时对中国能否保护朝鲜也存有高度怀疑。
四、 结 论
自18世纪后期以来,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逐渐扩大,从诗文唱和到学术探讨,并进而谈及时务,最终到近代从朴珪寿、郑健朝、李裕元等人身上可以看出有从“人臣无外交”到“人臣做外交”的转变。但是两国之人在交往过程中始终有所顾虑,由此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中国已与各国缔约通商,并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而朝鲜仍固守锁国政策,国内舆论也一味主张斥邪、战守,使中国士大夫不愿意与朝鲜使行人员多谈洋务;朝鲜使行人员中虽或有人愿意了解外国事情,但是拘于国内舆论,亦不能发挥很大作用。两国人的交往始终不能突破传统宗藩体制的制约。而此时长期担任礼部尚书的万青藜本身就比较保守,赞同大院君的锁国政策,甚至在总理衙门奏请暗中转递美国公使致朝鲜书信时,从维护传统宗藩体制出发,提出下不为例。最终导致朝鲜在没有充分知识储备的情况下与日本签订《江华岛条约》。中国作为此前朝鲜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并没有主动为朝鲜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朝鲜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中国对朝日交涉的冷漠,不仅导致朝鲜对《江华岛条约》有些条款的认识不足,而且将清韩宗藩关系从此置于被动地位。
此后,又同样在没有充分沟通和制度准备的情况下,在通过李鸿章与李裕元的书信劝朝鲜与西洋各国缔约通商失败后,再以《朝鲜策略》推动此事,然而也加剧了朝鲜国内文明开化和斥邪卫正两大势力的分裂。而日本成为朝鲜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派遣绅士游览团到日本考察,文明开化派因此与日本结下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仅派留学生到天津学习机械制造。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明显跟不上朝鲜半岛内外形势的变化,反而把自己越来越置于进退维谷的困境。而清政府又无主动打破宗藩体制的决心,只能穷于应付,最后坐视清韩宗藩体制被日、俄、美等国人肢解,以致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