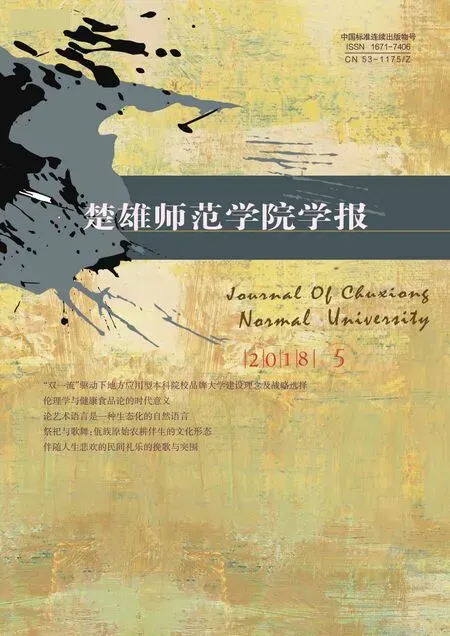伦理学与健康食品论的时代意义*
——兼及迈克尔·波伦与彼得·辛格的食学思想
赵荣光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8)
20世纪中叶以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历史标志,世界加快工业化的步伐,科技改变生产、生活的观念与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时代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合成了近70年来的环球工业——产业化特征。科技渗透与产业化彻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食生产与食生活模式。科技干预、工业化生产造就的产业化食物链颠覆了自原始农业以来,人类历经万年形成的和谐自然食物链。人类利用自然食材烹饪的习惯、食物养生的传统,被产业化制造的不可胜计名目的可食之物所取代。而就在人们深深陷入并重重困扰应接不暇、手足无措迷失状态之际,产业化食物链所造成的负效应开始雪崩似的涌现,每个进食者和整体人类社会陷入了从来没有过的“吃的危机”之中。
一、人类的确陷入了“吃的危机”之中
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的确一步步加速地陷入了“吃的危机”之中。这危机就是旨在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的逐渐扩大的产业化农业和不断掘深的产业化食物的陷阱,陷阱中的食物标志就是“西方饮食”,身陷其中则患“产业化食物链病”。“产业化食物链病”是笔者的概念界定,通俗的理解就是时下流行的“西方饮食病”,但泛泛地统称为“西方饮食病”又似有不妥。首先,“西方饮食病”已经不仅仅是西方;其次,“西方饮食病”应当有其特定的时效性;第三,“西方饮食病”的本质是饮食理念与理论、食材选择与食物制作、饮食目的与进食方式的一系列问题而无严格的地域或政治界限,因此称其为“产业化食物链病”更为准确恰当,尽管它也应有其时效性限制。我们对“产业化食物链病”的理解是:“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广泛流行的、片面追求产量和利润的工业化食材生产与食物制造导致食者所罹患的各种疾病。”
谈到“西方饮食”,研究者一般都强调其快速、廉价、方便的特点,无疑问这概括得很准确,这种产业化食物——“快餐食物”适合“快节奏生活”,与工业社会人生活方式节律谐调,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仅仅是这些特点吗?这种美国式“西方饮食”席卷全球的效应,仅仅依凭的是快速、廉价、方便三大特点吗?应当还有其他。当我们不仅仅将其视为一袋袋肯德基、一份份麦当劳、一块块炸鸡、一瓶瓶可口可乐的具体食物,而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和新型生活方式来审视时,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要素。各种传统的饮食文化几乎无一不节节退让直至失去最后生存之地,岌岌可危悬挂式存在的只是那些久有历史的品牌食物——它们也基本被“现代化”改造过了。
为了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单一品种大规模的工业种植、养殖,致使食材、食物营养素严重缺陷的同时携带严重危害进食者健康的农药、抗生素、病毒等,于是,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群被感染了产业化食物链病。为了不断增多的利润的需要,产业化食物制造商、营销商真的是绞尽了脑汁。食物产品的形态、味道、口感以及包装设计、推销语言等,都极尽炫目、撩情之能事。他们将超市的食品区营造成了充满快乐视觉和神奇联想的伊甸园,对产品“有机”“绿色”“自然”“营养”“安全”品质、功能等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宣传,造成了“超市田园诗”文化景观,甚至也形成了“超市食物品质推介文题与文化”。炫目、撩情,本来是产品市场营销的商业文化,但达到“超市田园诗”境界则堪称叹为观止。超市精心设计出购物者“文学体验”的效果,“经过有机认证”“人工栽培”“自由放牧”成为统一标签;用词竞相委婉含蓄:牛排出自“住在美丽地方”的牛,那里“各种植物、高山牧草地以及浓密的白杨树,还有布满野蒿的草地数千米”;牛奶则来自“远离不必要恐惧与压力”“全年都在绿色草地上嚼草”的牛体;蛋则来自“散养素食母鸡”;同时配以美妙的图片甚至声像,刻意“提升为一种让人迷醉的经验,这种经验混合了美学、情感甚至政治,让食物变得与众不同。”[1](P145―147)然而,事实则大相径庭。在中国,因为营销商对产业化食物的“超市田园诗”渲染性介绍,发挥到了文字与文学炫撩功能的极致,撩情与痛快而又毫无快乐用品的羞涩隐晦。人类“食色性也”的两大需求与功能,在中国“超市田园诗”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升华:高价的“处女蛋”;“绿色”“天然”“有机”背后则是百姓谑称的注水“水牛”、阳澄湖“洗澡蟹”“下乡返城”鸡……所有这些渲染性“产品介绍”都近乎相声演员的逗哏,模棱两可、华而不实,最终还是落进了满腹狐疑消费者的购物车。
毫无疑问,传统食品与传统饮食文化不足以抗衡产业化食物。为什么?因为传统食品与传统饮食文化是人们主要为了吃饱的目的习惯成自然地不经意沉淀下来的,对于进食者大众来说基本是满足于吃时嘴巴舒服、吃后身体舒服,更高境界的追求与理解只是微乎其微的美食享受者或研究者的事——他们基本与大众饮食无多关涉。正如人们习常所说的,各种文化或每个民族的传统饮食都是“妈妈味”,是一家一户独自完成的,是“整体文化欠缺”或基本是“习俗文化”群体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文化创造”。但是,产业化食物则不同,它是社会或政府集中知识精英为着引导消费、推广大众而精心设计的。这种设计依仗知识、科学、技术、文化优势,利用营养学家身份,以不容置疑的研究数据与权威口吻宣传消费者并且是集合了企业、研究机构、媒体、政府等多元力量,依仗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推行的。饮食者,无从选择,他们甚至都无暇思考就要匆匆随波逐流做出购买选择。事实上,在无处无时不在的铺天盖地的媒体传播中,营养学家的各种说法不能不左右着面对越来越多困窘而无所适从的饮食者,那就“姑且听营养学家说的吧”,于是,大众都被绑架裹挟了。即便人们知道了食品企业资助营养研究的结果总是更有利于该行业的产品[2](P156),他们也只能是不明就里、无可奈何。
人类工业化开始以来,科学刷新了人的自然观,机器的作用重构了人索取地球的关系。机器论曾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人是机器”[注][法]J.O.拉美特里:《人是机器》(L’homme-Machine),1747年匿名发表,是18世纪法国第一部系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著作。作者根据大量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科学材料,证明人的心灵状况决定于人的机体状况,特别着重证明思维是大脑的机能和道德源于机体的自我保存的要求。《人是机器》假定一切生物都具有所谓“运动的始基”,它是生物的运动,感觉以至思维和良知产生的根据。《人是机器》在自然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和伦理学等许多方面还提出一系列后来为其他法国唯物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的思想。经典的机械理解,就是将人类本质应当是娱乐养生的进食行为解读成也完全如同内燃机烧煤、汽油燃烧驱车的燃料供给。于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结果的食物,民族文化烹饪结晶的食物,就最终异化成了在科技支配下的产业化可食之物。而事实上,近代科学才让人类刚刚开始认识自熟食以来漫长历史上逐渐积淀形成的烹饪文化,它还在逐渐认识食物之间以及人与食物之间的极其复杂关系的初级阶段。
人类伊始就在自然状态下经验主义地不停体验食材的作用与探索食物的成分。近代科学对食材与食物化学成分的揭示无疑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营造更美好餐桌的巨大进步。也许人类过于急切了,结果让许多尚不确定认识严重扰乱自己本来很和谐健康的饮食生活。“当普罗特和李比希确定了微量营养素时,科学家们便认为他们已经懂得了食物的本质以及身体对于食物有哪些需求。几十年后,当维生素被分离出来时,科学家们又想,好啊,我们现在真的了解了食物,也知道了为健康的身体应当从食物中获取什么了;而到了今天,多酚和胡萝卜素似乎又成了任务的最后终结者。但是,谁知道在胡萝卜深深的灵魂里还游荡着些什么呢?”[2](P78)全世界的营养学家们都是课堂里或实验室里的学生,营养学还在热烈地讨论中,没有人能给我们最可信赖的科学指导,迄今为止的事实就是如此。比起将食物分解成化学成分,消化过程本身有更多值得关注的东西,对于今天的营养学家们来说,他们还在继续摸索中。
纽约大学营养学家玛丽恩·内斯特尔指出:“从营养素到营养素的营养学研究”,“说到底就是将营养素从事物的内在关系中割裂开来,再将食物从饮食结构的内在关系中割裂开来,最后将饮食结构从生活方式中割裂开来。”[2](P73―74)这种研究方式是实验室的,就方法来说无疑很科学,也事实上取得了许许多多成功。但是,迄今为止,全世界的营养学界尚无力提供科学指导民众健康饮食的系统方案。
“产业化食物链病”自然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因此人们习惯性称之为“美国式西方饮食病”。美国人是率先染病的族群,继之成为蔓延世界的“美国式西方饮食病”,而美国的这种病症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加速沉重起来的。面对20世纪70年代粮价暴涨的压力,美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鼓励玉米、大豆、小麦生产的农业政策和低价食品政策,导致1980年以后美国农户为美国人均多生产了600单位热量。这些热量将近1/4来自添加的糖(绝大部分是果葡糖浆)、近1/4来自添加脂肪(多为豆油)、46%的热量来自谷类粮食(大多经过加工)、8%来自水果和蔬菜。[2](P145)结果是:自1985年以来美国人一直为饮食添加额外热量,其中93%都是糖、脂肪以及占比最大的加工粮食,而它们除了能提供大量的热量外几乎没有其他。美国农业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对43种农作物进行跟踪检测,数据表明:这些农作物的营养成分都大幅度减少了,2007年美国的一份题为《依然没有免费的午餐》分析报告显示:[2](P142)维生素C减少了20%,铁减少了15%,核黄素减少了38%,钙减少了16%。至少有30%的当代美国人的饮食中缺少维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A和镁。大量的数据信息综合和分析研究指出,“美国农业部门一门心思要增加产量的做法制造了一个盲点”:等量营养所需摄入的实物量虚高,而这种天下昭昭的“我们食物的营养品质一直渐进受损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逃过了科学家、政府和消费者的眼睛。” 英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粮食作物中的铁、锌、钙和硒的含量都减少了10%以上。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生活在21世纪今天的我们,要吃3个苹果才能获得几十年前(后工业化地区20世纪40年代或中国50年前)1个苹果的铁含量;同样,欧美人要多吃好几片面包才能获得身体所需锌含量。产业化食物链病涵盖了营养失调、肥胖、维生素缺乏、维生素过多、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某些肿瘤等。“糖尿病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全球性传染病,但也是最不寻常的一种传染病,因为它不涉及病毒或细菌,也不涉及任何微生物,只是与吃的方式有关。”[2](P159)人类健康离不开食品健康以及整体观念的健康,食物链中的所有环节都环环相扣,土壤健康保证我们所食用的植物和动物的健康;而植物和动物的健康又保证我们食用的饮食的健康。其中的法则不仅涉及吃什么,也涉及如何吃以及那些食物是如何生长出来的。食物不单单是化学成分的堆砌,它也包括各种社会的和生态的关系,不仅与大地相关,也和其他人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注意到:ω-3脂肪酸由植物叶子产生,ω-6脂肪酸则由植物种子制造,两者皆为人体必需,而且两者的比例极为重要。若ω-6脂肪酸比ω-3脂肪酸高出太多则易导致心脏病,前者有助于血液凝结(会促进炎症反应),后者有助于血液流动(会抑制炎症反应)。如果人类的饮食(以及所食动物的饮食)由绿色植物为主转变成以谷物为主(从吃草转变为吃玉米),那么ω-6脂肪酸与ω-3脂肪酸的比例就会从1∶1转变为10∶1(油脂氢化的过程也会使若ω-3脂肪酸减少)。采猎者的饮食就是1∶1状态,吃草的牛,肉中ω-6脂肪酸与ω-3脂肪酸比例为2∶1,若吃谷物则是10∶1以上,人吃了这种牛肉后果可想而知,食物链工业化正驱使人们向毁灭性深渊越走越近。
一方面是食物的扩大量摄取,另一方面则是营养素的缺乏,造成如此看似矛盾背离的现象,原因就在于:粮食生产方式与粮食品种的巨大变化。大量的数据与无争议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肥种植的作物营养水平低于有机土壤中种植的同类作物。效率与效益决定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必然采取单一栽培(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随着规模扩大,多样性有所下降;而随着多样性的下降,健康状况也就下降;而随着健康状况下降,人们对于药物和化学品的依赖必然会增加。”[2](P187)“在饮食工业浩劫下,我们吃的是会走的玉米?喝的都是石油?你每日不自觉吃下的食物,真相可能令人战栗”!“我们所依赖的工业社会,正是让人类生病的饮食源头”!这就是美国人正在痛中思痛的产业化食物链病现实。
这种正在影响世界的“以数量而不是质量为基础的”美国式饮食,正在改变地球史上最强势的物种——人类自身。正在被改变的人类,或产业食物链正在造就的新人类,其特征就是过量饱食而营养不良的人。当然,这里要特别强调:当今时代“美国式”或“西方式”的营养不良,绝非传统食物严重缺乏导致的营养不良,那是健康食物缺乏导致的营养不良,或曰是传统的、“良性的”营养不良,可以通过健康食物正常供给以改善之恢复正常。笔者作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居民,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处于长期的饥饿状态,食物匮乏一直到80年代以后才逐渐改变。而当今时代“美国式”或“西方式”的营养不良。
20世纪末,我们提出了“食品安全是基本人权”,继之我们又让“食品安全食是时代人权保障的底线”的口号响彻中国媒体并得到国际食学界的高度认同。[3]的确,民主和民权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成为越来越多民众的基本意识。但是,到了今天,几乎是全体人类都正在被拖入基本人权遭受毁灭的泥潭之中,“食色性也”,自有人类以来,最美好的餐桌竟然变成了死亡陷阱,何等残酷又何其荒唐滑稽!
二、健康食品论的呼唤
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因其一系列震撼性著作:《杂食者的两难》(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2006)、《为食物辩护》(In Defense of Food,2008)、《吃的法则》(Food Rules: An Eater’s Manual,2009)以及大量的调研、论证性文章在美国——进而整个世界掀起了健康饮食思想的风暴。获选美国《新闻周刊》“10年来10大思想领袖”,2010年《时代杂志》“全球百大影响人物”等等,他也因此有了“美国饮食界的良心与革命者”,“美国首屈一指的饮食作家,食物类研究权威,也是无数人的饮食导师”,“美国饮食界的引领者”等诸多赞誉,他的著作被评论为“划时代饮食意识觉醒之书——是写实、深入的关键报告。”“饮食写作的最高典范。”他的书名《In Defense of Food》汉译成“为食物辩护”或“保卫食物”,而该书的序则径直称为“一个食者的宣言”,通览全书,可谓充满了战斗性和挑战性。我们的时代真的进步了吗?我们真的变得更加文明了吗?面对餐桌,我们真的缺乏自信。我们竟然到了要“为食物辩护”的窘境,到了逼迫“一个食者”为了免受产业化食物之害不得不呐喊“宣言”的地步!不得不承认,我们活得的确真够悲哀的了。
为了深刻揭示和生动说明美国产业化食物链的迷失,迈克尔·波伦别出心裁地周密设计并严格执行了一项极具启示意义的实验,即模拟自然生态下亲自完成采猎全部食材后在伯克利独自完成了一次名为“杂食者的感恩节”晚餐。预定菜单规则:1.所有食材都是本人亲自狩猎、采集或是种植得来的。2.餐点必须各有一种以上的食材去凸显三大可食生物界的特色,包括动物界、植物界、真菌界,此外还有可食矿物(盐)。3.必须使用当季的新鲜食材,这一餐不但要反映这些食材生长的地点,也要反映出特定的时节。4.在必要时可以使用储存室里现成的食材,除此之外,不再另外花钱采购。5.除妻儿外,宾客限于曾经帮助其采集食物的人及其伴侣,共计10人。6.本人下厨。菜单:蚕豆土司与索诺马野猪肝酱、大火羊肚菌佐意大利宽蛋面、索诺马野猪炖腿肉与烤里脊肉、湾区东部野生菌酵母菌面包、纯本地田园色拉、富尔顿街法式红樱桃派、克莱尔蒙特峡谷甘菊茶、安杰洛(共同采猎者)2003年份西拉红酒。野猪亲手射杀,菌、鲍鱼、盐等均亲自采集。樱桃系某户人家平氏品种樱桃树所结,该品种1875年取名中国籍农场工人阿平。晚餐设计的寓意是“位于森林食物链的末端”,逆转人类饮食的历史轨迹,让森林再度喂养人类。整个宴程中的交流都围绕着特殊的植物、动物和真菌,以及这些生物生长的地区。这些食物采集者诉说的故事,让大家的思绪离开了餐桌,重温了采猎过程。他们说的故事以及吃的食物,把这些地区以及生活、死亡在其中的生物都联系了起来,最后汇集到餐盘中,给了大家一种仪式感。这一餐如同感恩节与逾越节晚餐,因为餐盘中的每道食物都如同圣餐一样有其含义,诉说着一则则关于自然、社群甚至是神圣事物的小故事,主题通常是神秘。这些充满故事的食物能够滋养进餐者身体与心灵,对话让大家彼此相连,变成一个整体,也让这个整体与更广大的世界相连。而他对一头编号534小牛变成超市分割食材饲养全过程的跟踪观察,也使现时代人均年消费200磅肉食的美国社会感受到了牛排的生物与生命意义。迈克尔·波伦在布莱尔牧场(Blair Ranch)以598美元购得一头8月龄小牛,然后送到800公里以外的波克饲养场,并以每天1.6美元作为该牛的住宿、伙食(能吃多少就给多少)和医疗费用支出,开始了他的跟踪观察。他的目的是要想清楚准确知道“产业化食物链机制是如何将1千克玉米转变成牛排的。牛是食草动物,要如何让这种不相干的生物去消化美国的过剩玉米?目前美国的每1千克原材料玉米中,大部分(约60%,也就是2160颗玉米粒)是拿来喂养牲畜,其中有许多是喂给美国的1亿头肉牛。在过去,这些母牛、公牛和小牛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在户外的草原上低头吃草。”[1](P64―65)
迈克尔·波伦还精确计算了一次快餐体验,他在马林区麦当劳为自己、妻、子一家三口人解决的快餐,只花费了14美元晚餐,在时速90公里的私家车上10分钟完成。位于加油站旁麦当劳现代产业快餐食物与“森林食物链末端”慢餐的比较研究之旅很有启示性。有研究发现,在18~50岁的美国人中,大约有五分之一人的饮食行为是在汽车里进行的。而其在伯克利筹备的“杂食者的感恩节”晚餐则耗时、耗资、耗力巨大。他的结论是:“在准备与吃下如此耗费体力、精力与情感的一餐时,我们不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的产业化饮食对于大自然的亏欠有多么深。也就是在工业化时代,我们只是吃,而不会去想自己在做什么。”作者指出:位于人类进食光谱上两个终端的这两餐,一餐的乐趣来自几近全然知情,另一餐则截然相反。前者的多样性反映出自然的多样性,后者的各种选择反映的则是工业创造力,尤其工业界那种在同样土地上种出玉米,再以玉米这一单一物种去仿造出多样性的能力。相较之下后者似乎更廉价,但却涵盖真正成本,因为这些成本已经转嫁到自然、大众的健康与荷包以及人类的未来上。
在时下产业化食物链下,工厂摆满超市食品货架的“可食产品”,与和谐自然传统食物链的精神、功用截然相反,是它让“肥胖儿童患上营养不良症”——如佝偻病——成时代食相特征。孩子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快餐而不是传统的食物与新鲜果蔬来填饱肚子,更多地引用工业饮料,“旧时代的营养缺乏症”就会卷土重来,人群中的胖、瘦子一概不能幸免。这一灾难性后果犹如恐怖整个欧洲的黑死病瘟疫,甚至更严重,因为它不因人死而病去,活下来的也都是病体,产业化食物链上的所有人已经成为一个集体携带病因的种群。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推动美国式饮食中无休止的变化呢?其中之一便是规模达320亿美元之巨的食品营销机构,而其本身就是要靠不断花样翻新才能茁壮成长。另一个因素就是营养科学的理论依据一直在变化,而这种理论依据要么是在稳步地将我们关于饮食和健康的知识推向最前沿,要么就是反复无常,因为作为一种有缺陷的科学,他实际上所了解的东西远比他乐于承认的要少得多,得出以上这两种看法完全因人而异。祖父辈的饮食文化现在已经从美国人的餐桌上消失殆尽,官方的科学观点恐怕难辞其咎。这种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观点,主要认为动物脂肪是一种致命的物质。同样脱不了干系的还有那些食品生产商,他们原本很难从我祖母下厨当中赚到什么钱,因为她做饭从来都是自给自足,就连烧菜的油也是自己炼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推广‘最新科技’,他们往往想方设法地向祖母的女儿兜售氢化植物油的种种好处,而我们今天已经了解,这些油也许才是真正致命的物质。”[2](P9)得到联邦财政资助的美国妇女健康行动组织(Women’s Health Initiative)2006年结论说:没有发现低脂肪食物与罹患冠心病之间有什么联系,即人们一直以来坚信的低脂肪食物能防癌事实并非如此,营养学关于食用脂肪的正统观点似乎正在彻底瓦解。[2](P10)
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人们尽可能“避开印有健康声明的食物产品”,甚至“除非万不得已,无论何时都尽量别进超市”。“逃避西方饮食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远离受其影响的那些地方:超市、便利店和快餐店。”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大型食品公司才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确保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其产品的健康声明,然后再跑到全世界大肆吹嘘。”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大型食品公司普遍地缺乏基本的人道责任,“就大部分情况而言”,他们产品的“健康声明所依据的却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常常错误百出的科学——营养主义令人怀疑的成果。不要忘记,作为最早的工业化食品之一的富含反式脂肪酸的人造黄油,就曾声称它比它所取代的传统奶油更健康,结果却让人们心脏病发作。”[2](P182)同时,产业化肉类生产行业不仅野蛮地对待动物,而且还大肆挥霍浪费资源:水、粮食、抗生素,同时是水、空气最大的污染者之一。2006年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牲畜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要多于整个交通行业。[2](P197)没有或较少受到环境污染与工业破坏的食材与食物。在外婆时代本来是最普通、最正常、最便宜的,而在产业化食物垄断大众餐桌的当代,它们竟然成了真正绿色、营养、安全因而令人愉快放心的“高质量食物”,当然它们同时是高价的,普通消费者难以企及。“同样的情景今天正在中国发生着,中国食物系统的快速产业化使得食品安全性和完整性遭受了令人震惊的破坏。监管是担当和信任的一个不完善的替代品,并植入这个市场之中,而在这个市场里食品生产商总是会面对食者质疑的目光,反之亦然。”[2](P188)
三、动物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意义
迈克尔·波伦的《杂食者的两难》2006出版,旋即被《纽约时报》列入当年最好的5本非小说类书籍;被吉姆斯·彼尔德基金会(James Beard Foundation)命名为2007年度最好饮食书籍。迈克尔·波伦谈到自己的写作目的:“主要是从生态和伦理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的饮食选择。”著者是杂食主义者和杂食论者,他不认同纯素食主义的理论,因此他与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观点相左,后者是世界著名的动物伦理学者。1975年,澳籍学者彼得·辛格出版了他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 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一书,此后1990第二版,2002第三版,2009第四版,2015发行40周年纪念版(NY: Random House1975,second edition 1990, third edition 2002, fourth edition 2009,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15)。1999年,该书有了大陆中文版(光明日报出版社)。这部被誉为“动物保护运动的圣经”“素食主义的宣言”“生命伦理学的经典之作”,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英文版的重版近30次。彼得·辛格说:“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4](P1)因为,在“肉食虐待动物”的伦理之上,它关涉到任何文化都不容回避的此种生活方式不利健康、浪费资源、毁坏环境的明显事实,它最终导致了整体人类与地球的健康与生存。
以笔者的阅览与信息所及,可以说彼得·辛格与迈克尔·波伦是近40多年来对人类食事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伟人,一位是看到被煎至五成熟的牛排就流涎水的杂食者,另一位是满怀悲悯连鱼都拒绝食用的素食主义者(但他声明说自己“总的说来,我并不反对吃自由农场所生产的鸡蛋”),理念、理论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也确实直接讨论过彼此的分歧,正如笔者也曾与彼得·辛格有过对话一样。但分歧是属于迈克尔·波伦和彼得·辛格两人之间的,而就社会意义来说,他们又是一致的,那就是生命与生态伦理的认同与有力坚持。而在实践上,重要的就是实践,辛格的动物伦理学与波伦的健康食品论都是对产业化食物链的彻底否定,可以说它们是“产业化食物链病”的真正克星,是最终可能斩断美国式西方饮食产业化食物链的两柄利剑。
毫无疑问,动物伦理学的意义远远超越对动物宠爱行为本身,它“关怀的是防止(因为人类的原因而致使)动物所遭受的痛苦与不幸”。[4](P6)动物伦理学的深入人心,无疑会激发人类慈悲与爱的本性,道德善化人类心灵与情感,使人更成其为人。但时下更重要的还是彻底改变当今世界每过3.9秒就饿死一个人悲惨现状的可行途径。因为为着肉食材料的生产,仅仅是美国,每年饲养和屠杀的牛、猪、羊就超过一亿头,禽类则高达53亿只。它们基本都是工业化“科学”高效速成的。“肉鸡”7个星期就被宰杀(鸡的自然寿龄是7年),而快速育肥的牛则仅有6个月寿龄(自然寿龄是30年)。毫无疑问,按照营养级理论,哪怕只是减少1/3的食草动物饲养也足以生产免除任何一个人饥馁的谷物,同时极大地改善生态环境。这因此成为辛格的一句经典的口号:“少养肉品动物——拯救地球”。因为“人为了吃1磅动物蛋白质,必须给动物吃21磅蛋白质。我们所得补给供应的5%。……每1英亩可以产生的植物食物是动物性食物的10倍”,甚至高达20倍。肉类生产水的消耗亦极大,1磅牛肉所需水比1磅小麦高50倍,因此有“1000磅的肉牛身上所用过的水足以浮起一艘驱逐舰。”而在环境污染方面,“在美国,农场动物每年产生的粪便20亿吨——是人类粪便的10倍——其中一半来自工厂化农场,而这种农产的粪便是不能回归自然的。”[4](P197―202)
早些年的田野调查让笔者知道,20世纪上半叶,鄂伦春族猎手用快枪改变了中国黑龙江地区的原始生态,最佳猎手竟然一天能够射杀一百几十只鹿科动物(狍子为主),而且这还不是刻意追求的极限数据。显然,“鄂伦春式”的食生产与食生活模式过去了,不能也不应当恢复了。问题是,我们落入了另一个极端的陷阱。辛格深怀忧虑地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西方人开始意识到食用过多的肉、蛋和乳制品是一个错误的时候,中国却在这方面开始增加其消费,而如麦当劳之类的美国快餐店也在中国城市纷纷开张。(1997——引者注),在一次世界肉类会议上,中国国内贸易部一位高级官员为‘把肉事业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竟呼吁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而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目前已经有一千多个肉类加工的合资项目。中国肉类消费已占世界生产和消费总量的1/4,而且还在迅速增长。”“如果中国为了追求生产更多的肉和蛋而仍在模仿西方,……为了生产足够的饲料,又将对农业造成更大的压力,使更多的山野失去天然植被而被砍伐,更多的草原放牧过度,从而出现更多的沙漠。所有这些都将消耗更多的能源,往大气中排放出更多的甲烷和二氧化碳,从而引起温室效应、干旱、飓风和海平面上升。而中国人的心脏病、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病率也将很快超过西方。”[4](P3―4)作为警告,中国人置若罔闻;作为预言,中国则早已实现并大大超越。
四、人类有希望走出产业化食物链的陷阱
鉴于越来越多的病人深受“对健康饮食的不健康忧虑”,美国一些心理学家已经发出将“饮食紊乱症”列为临床“精神障碍”的建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健康饮食的不健康忧虑”致患很多美国人,那么对于那些塞进嘴里的每一份食物都是有问题、有危害的无助者又怎样呢?既然蛇充斥赖以生存的土地、水源、空气及不得不吃的一切,他们当然不会怕井绳的。“既然营养主义根植于以科学手段处理食物,因此就十分有必要牢记这一点,即营养主义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食品行业、新闻界和政府都要对营养主义征服我们的思想和饮食负有同样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国在内,所有产业化食物链陷阱中的人们都在寻求挣扎出来的途径。诞生于1969年4月20日的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人民公园”,可以视为尝试先例。当时一个自称“罗宾汉委员会”(Robin Hood Commission)的团体占据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块空地开始铺草皮、种树、开辟菜园,他们自称“农业改革者”,自己种植“无污染”食物,声明要在这块地上建立新型互助社会。这标志着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绿化”,导致了乡村的公社运动、食物消费合作社与“游击式资本主义”(guerilla capitalism)的产生,最终带来有机农业的崛起。
兴起于美国的“小区支持性农业”,又名“盒装计划”(box schemes),就是“农业改革者”“无污染”食物理念与行动的延伸。小区支持农业或译为共同购买,一种小区支持当地有机农业的推进组织,由消费者与生产者(农民)共同组成,是有机农产品常见的销售模式。消费者在产季开始时先支付农场一笔金额,然后每周会收到一箱农产品。通过这种做法,消费者与生产者可以共同承担风险与享受潜在的产品报酬。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为,那么美国政府做了什么呢?美国政府迫于压力出台的“有机食品与生产法案”规定乳牛必须“接触到草地”,有些动物必须“走到户外”,于是工业化生产厂家就弄出了可以“接触一下”的草地、能够“走出”的户外。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丹麦超市试验在肉品包装上增加第二道条形码,收银台刷了条形码之后,屏幕上会出现该肉品的农场以及这只动物的遗传特性、所喂的食物与药品、宰杀日期等详细信息。批评者尖锐指出:当代“美国大部分超市根本经不起这种信息透明化。”
英国植物学家、有机耕作先驱,艾伯特·霍华德爵士(Sir Albert Howard),被称为“现代有机农业之父”。美国科学家和生态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其著作《野生动物经营管理》《大地伦理》《沙郡年记》等发展了环保主义理念,被奉为生态中心主义权威之作。源自意大利的“慢食”运动很有代表性,慢食运动发起人卡罗·佩屈尼(Carlo Petrini)认为:消费者成为“共同生产者”,因为他们的饮食行为对于保留地貌、物种与传统食物有所贡献。法国羊奶奶农琼斯·博维(Jose Bove)开着拖拉机穿过麦当劳的落地玻璃窗以抗议全球化。目前最强烈反对全球化的抗议活动都围绕着食物进行,如抵制基因改良作物运动、在印度对于WTO专利种子的抗议活动(40万印度人民上街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法规)。工业制造食物美国率先世界且祸害全球,而受过之重则美国人为最。正因为美国人受害最重,因此美国社会的自救也就走在世界前列。如美国女厨师、餐厅经营者、美食作家艾丽斯·沃特斯(Alice Waters),这位有机食品运动最著名支持者之一,奉行有机食品40年不辍。她所开设的潘尼斯之家以善用当地生产的有机食材而著名,在加利福尼亚饮食界居于领导地位。更早,20世纪30年代,美国牙医普赖斯创立了“普赖斯基金会”(Weston Price Foundation),他在世界各地旅行研究那些活得最健康、最长寿的族群,他发现那些“原始”部落牙齿保护得比工业化国家的人更好,活得更健康。他们的饮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量来自野生或放牧动物的肉品、未经高温消毒的乳制品、未经加工的全谷物、用发酵方式保存的食品。美国波利弗斯农场(Polyface Farm)无疑是个典范,“在农场中,数种动物以和谐共生的韵律,密集上演轮番饲养(牛、鸡、兔等——引者注)的舞蹈;萨拉丁是编舞者,而草就是碧绿的舞台。这出舞蹈,让波利弗斯农场成为全美最有生产力,也最具影响力的农场。”[1](P134)场主乔尔·萨拉丁(Joel Salatin)的经营理念、原则、方法应当是健康食物现代化生产的模式。
人类学家估计,典型的采猎者,一周只要工作17个小时就足以喂饱自己,而且比农民更长寿、更健康。崇尚自然并唾弃文明的环境哲学家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认为:“人类无需回到旧石器时代,因为我们的身体从未离开过那个时代。”“吃什么,这本是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但如今却被变得十分复杂,而这一由简变繁的过程充分显示了食品工业、营养科学,还有新闻界所共同形成的所谓体制性强制力。其实人们用不着专家指点就知道自己该吃什么——人类自打从树上下来之后就一直做得挺成功,不过如此一来,对于食品公司来说便是无利可图,对于营养学家来说就是绝对的失败,而对于报纸编辑和记者来说那就实在是索然寡味。……于是,庞大而复杂的所谓科学性的阴谋就如同一大团乌云,将最简单的营养问题团团围住,以便有关各方都能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唯一被撇开的,反倒是所有营养建议在理论上的受益者,也就是我们大家,以及我们作为食者的健康和幸福。关于将饮食建议变得更加专业化的运动,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家都应该知道,那就是这种专业化运动并没有使我们更健康。”[2](P11)
波伦说:“西方饮食所造成的最后一个变化,严格说来,并不在生态方面,至少不在这个词的狭义之内。但是,我们食物的工业化,也即我们所说的西方饮食的工业化,正在系统地、蓄意地破坏着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这对我们健康的破坏,恐怕不亚于任何营养不足。”[2](P155)我要说的是,我不是一个只有昨天可以依赖的守旧者,事实上,无论我们拥有多少传统,如中国俗谚“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人物两非”所说,我们以及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每天都在缓慢地变化中。人一天天地在老去,一切生物与非生物也都在这样的变化中,时间在验证一切。我们不是因为眷恋而拒绝变化,重要的是“西方饮食的工业化”带给了我们什么?
一份涵盖了2012年全球84个国家(地区)的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显示,中国人均食品消费额排76位,不足600美元,用于食品的开支额占消费总额的26.9%,排在全球第28位。但中国人因吃饭而承担的消费成本并不低。巴基斯坦虽然高达47.7%,但人均年食品支出额却只有415美元,是美国的1/4,总消费额仅871美元,是美国的2.5%。在所有国家中,食物最便宜的当属印度,每年该国人在食品上的消费额仅220美元。而中国人的食物消费比值在金砖国家中,仅好于俄罗斯(31.6%),从全球来看,尽管富裕国家的公民需为食物支付更多钞票,但这对于总消费的占比却基本低于15%。在买吃的这件事上,亚洲人民掏腰包比例高于拉美人民。美国人的占收入9.9%,意大利人的支出为14.9%,法国人为14.9%,西班牙人为14.7%。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尽管美国人均食品支出额高于世界均值,达到2273美元,但该国人均食物消费占据总消费额的比例却是全球最低,仅占全部消费额的6.6%。这里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美国人人均消耗肉200磅。因此,有理由期待,美国作为“产业化食物链”最发达和“产业化食物链病”最严重的国度,也可能是率先脱离产业化食物陷阱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的能力与国民实力不难做到这一点。人类总要延续下去,负面的示范之后,正面的表率将会更有力度,我们应当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