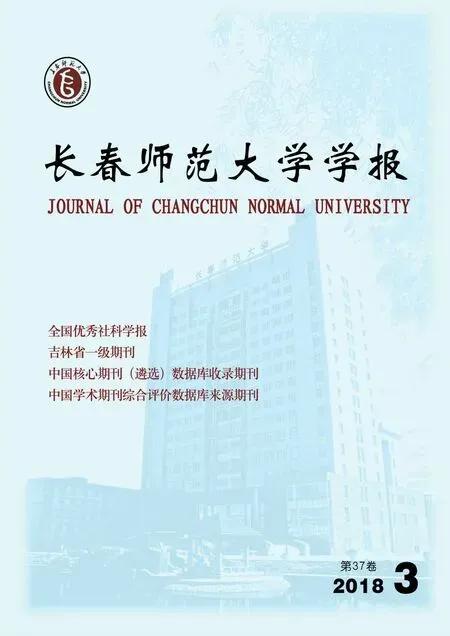市民社会的张力:清末议会政治产生根源研究
尚润泽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立宪派是晚清立宪运动的主力推动者,其主要由官、商、学界及普通民众组成,但立宪派最大的动力乃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阶层。官员中的立宪派由于所处的权位关系,能对立宪要求表达或明或暗的同情就已难能可贵,唯有以商人、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阶层在官员和学者的帮助之下,为立宪奔走呐喊,不遗余力。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江浙地区最为兴盛,因而该地区立宪派的组织和运动势头也最为庞大,而且立宪运动不是“各自为战”、盲目混乱的,而是主要以商会为纽带所进行的有组织的作为。江苏预备立宪公会、广东粤商自治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等的建立,意味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阶层为主要构成部分的立宪派由分散的个体变成了有组织的团体。这一切的背后,便是市民社会的萌芽在清末之际生发的作用。
一、市民社会概念的回溯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到近代的黑格尔、马克思以及更近时期的葛兰西和哈贝马斯,其含义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经历过数次变化。亚里士多德将市民社会与法治的、自由的、不同于传统野蛮社会和村落社会的城邦国家相联系,同时提出了公民的权利和政治参与的必要性,认为“一个人只要参与了某一政体,他就是一位公民了。”[1]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交融的。“市民社会”一词传承到西塞罗手中时变得愈加明确,他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2]西塞罗还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文明的一种,其与法律息息相关,提出公民的平等权之类的法权要求。“那么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市民起码应该在权利方面是相互平等的。就这样,市民社会若不是市民的法权联盟,又是什么呢?”[3]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离状态越来越明显,导致学者对市民社会的定义也发生变化。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理论是继往开来的,他使市民社会从国家的藩篱中解脱出来,明确地分离了两者的界限。与此同时,黑格尔注意到了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人格。“个别的人,作为这种国家的市民来说就是私人,他们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但黑尔格仍然认为市民社会是依附于政治国家的。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思想,他认同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其中的个体部分,而私人利益关系构成了市民社会。这个私人利益关系中包括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尤其是经济领域,他强调生产力和市民社会相互作用。论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时,他则认为是阶级分化带来的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分化所导致的,所以当阶级消失的时候,市民社会将会连同国家一起湮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是批判性继承的,他并不认同黑氏对市民社会依附性的思想,肯定了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安东尼奥·葛兰西则从文化角度给出了市民社会的概念,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为了宣传意识形态的各种非政府组织(教会、学校、报纸等)的总和。在葛兰西眼中,“教会努力代表整个市民社会,虽然教会是这个社会的不很重要的成分。”[5]哈贝马斯则将市民社会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认为市民社会具有相对独立性。[6]这体现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公共领域的促进作用。束缚在个人身上的封建性随着市场的扩张逐步被剥离,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个体性得到张扬,政治国家之于公民社会的力量被毫不留情地削弱了。
综观市民社会概念的变化,笔者发现理论的变化更多的是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分离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在当前市民社会的运行中,应当考虑的不是国家是否应当介入,而是国家以何种形式介入以及介入多少的问题。保障和满足市民社会中个体法权需求的多少,应该作为上述问题的首要价值标准,毕竟市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个人权利的不断扩大,市民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史,而议会便是为个人权利的行使应运而生的。市民社会进步虽然不能够成为个人权利保障的全部条件,但一定是一个必要条件。中国市民社会的羸弱,正是个人权利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现实的滥觞,而市民社会的羸弱又是法治和个人权利保障进程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二、权利意识的生发:清末地方议会的社会基础
在列强的炮火中,中国的商品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促进了中国民众特别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权利意识上的觉醒。他们开始从注重实物方面的平等,如“均贫富”的想法,转向追求权利平等的目标。而要求权利平等的第一步,便是推动地方议会的建立。
(一)晚近时期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历史进程角度看,市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事务领域、社会事务领域以及个人事务领域的不断分离,而商品经济的成长是推动这种分离的经济动力。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平等交换,核心是契约精神,基础是双方自愿,法律则是其制度保障。每一笔交易都建立在买卖双方内心认同的前提下,相互不认同的地方主要靠“商量”来解决,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自主的环境,并在这个环境里关注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他们不希望其他人尤其是公权力过多插手自己的事务。商人们总是倾向选择交易费用较少的政治体制,希望减少由政治体制造成的交易费用的增加。[7]272商人的诉求何尝不是小市民阶级的诉求呢?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明确化,每个人都需要跟其他人进行交换,以此取得生活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在此意义上,生存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被视作“商人”,这是不同于小农经济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全民皆商”程度的逐步扩大,使得商人和普通民众的法权要求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为市民社会提供了立足之本,也印证了商品经济对公民权利观念的巨大影响。
中国市民社会的起源应该从晚近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伴随着列强的数次侵略,中国的社会结构悄然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变化是诱发中国市民社会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你们(西方殖民者)让你们的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奴役和殖民的危险时,客观上也为中国带来了工业社会的文明,中国的市民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铺展开来,这也是殖民者的双重“使命”之一。在自然经济环境下,中国社会更多以身份关系为纽带;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使中国一步步走向以契约为主导的市民社会,原本自给自足为主、商品交易为辅的经济运行路径慢慢被“反过来”了。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的工坊工作并转为产业工人,而社会分工也变得愈发明确,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从事相似专业的人们在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为了保障共同利益不受侵犯,自发形成了一个个团体,而这些团体的产生和发育正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团体逐步成长起来,主要表现在数量不断增加、经济力量不断壮大。当时的商人们以各个级别的商会为轴心,构建了一个从沿海沿江大城市到内陆地区较为发达中等城市进而到乡镇的大型网络,他们将各自的力量汇聚起来。商会领导人基本都是通过一张张选票产生的,对于商会各项事物的决定也大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7]261在这个过程中,商人们的独立性、民主意识和驾驭民主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他们要求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扫除阻碍商品交换的社会制度,扩大自己的权利。
(二)市民社会的发展对民权观念嬗变的影响
西方市民社会的权利概念,具有表征个人在法律之上的利益、资格与要求的功能,而自然经济下的中国社会民众的权利概念首先着眼于获取实物的机会(通过政治的、权力的方式)和议价能力。[8]中国人在传统意识层面没有过多的权利概念,比如其更重视财产而非财产权。长期以来,在儒家思想影响下鲜有个人诉求之想法,更多的是“克己”与“治国平天下”之理念,这恰恰与近代西方的个人诉求——建立国家——以国家保障个人诉求的权利思维逻辑大相径庭。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及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振臂高呼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都和近代意义上的“权利”有相当大的差别。在古代中国,实际存在的程序法则主要是为君主专制体制服务的,民权思想因此只能是不完整的,这是古代民权思想与近代民权思想的区别所在。[9]
中国人的权利观念滥觞于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之时,时维京师同文馆翻译《万国公法》,将“right”译为“权利”,意为“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此后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官吏逐渐接受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权利观念。梁启超曾云,“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10]严复认为,仁政之关键在民权,而非统治者中的仁人。“国之所以长处于安,民之所以长免于暴者,亦恃制而已,非恃其人之仁也。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即亦可以吾不仁,权在彼者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11]
正如柏克所言,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马克思曾说,商品交换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12]商品天生无脚,不可能自己走进市场,所以需要“监护人”带入市场,“监护人”当然要求对手与己是地位平等的。在此论断上可以推知,当商人力量增大之后,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利益保障和扩展的诉求,必然会要求国家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平等权利。观清末以“立宪”为中心的各项活动可以看出,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利益团体要求确立一种新的制度去限制过于庞大的公共领域的权力,从而保护公民的交易自由、财产权人身权不受国家机器的侵犯。清末时期,商之视官,政猛于虎[13],当时的法律对自由企业制度和私有财产都没有进行很好的保障,各级政府层层卡要的“厘金”制度更是限制了商人的交易活动。商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利,被放置在社会的底端,这使得商民感受到争取自身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的重要性。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有参与政府工作的权利,更有监督政府的责任。
三、市民与议会:清末立宪运动的动力
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自然伴随着一种新的精神的成长。封建等级制度严重阻碍了个体权利的张扬,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员,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必然要摆脱这种束缚,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观念体现在现实活动上就是敦促国家制定新的、满足商品经济发展进而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权力运作模式。诚如约翰·密尔所言,人民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由于人民并不亲自主事,所以要求有一套制约方法,以防止仆人滥用权力变为主人。[14]
清末立宪运动正是在上述基础之上产生的。它的发生反映了历史的潮流和国内矛盾的激化,立宪与其说是清王朝的统治者所作的最后挣扎,毋宁说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运行路径变革的“倒逼”。当时的改良派代表张骞在1901年慈禧宣布变法后不久,就在《变法平议》一文中提出设立“议政院”的建议,海外的康梁等人皆著文呼应。康有为在1902年发表《辩革命书》,倡导君主立宪;梁启超也于同年发表《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直接批评传统的君主专制。这一时期地方上敦促中央政府设立议院的大员亦颇多。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认为国会乃立宪之根本,“窃以今日创行宪政,急起直追,已患不遑,但若漫无次第,则前后倒置,似亦非政体所宜,……,论者多骤设国会势有难,几不知若无国会以通舆论而参政权,则宪政精髓不存,新机之萌芽安望。”[15]署理广西提学使李翰芬在奏折中请求加快颁布宪法和设立议院的速度,“明降谕旨,于光绪三十七年颁布宪法,开上下议院,有五年为之绸缪预备,则各省之议局,各州府县之议事会,渐多合格之议员,而两院制不难成立,即宪法亦编纂完善行之有效矣。”[16]由于立宪派的共同努力,资政院和咨议局的设立为公民与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博弈的“角斗场”。在商人的强势引导下,旧有的法律制度和权利分配模式遭到有力冲击。资政院在设立之初就通过了几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法案,如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等都体现出市民社会的力量对国家权力进行的抗争。
各省咨议局在1909年末至1910年末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组织进行了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声势一次高过一次。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次请愿策划中,请愿代表们要求各省府厅州县都有代表参加,签名人数在百万以上,且打破之前请愿签名仅有咨议局议员和乡绅士民的局限,要求普及到农工商各界。从规模、行动方式、成员等方面观之,其已初具西方民主之式。请愿运动表面上看是在争论召开国会时间早晚的问题,实际上却是立宪权之博弈。《钦定宪法大纲》只规定了宪法颁布时间,却未明确国会召开时间。若国会于宪法公布之前召开,便意味着立宪派有机会参与到制定宪法之中,掌握立宪的主动权。根据史料,虽然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通过之议案大部分未被施行,但仍有为数不少的议案被施行或不完全施行[17]。因此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晚清社会来说,得到这些成果已经非常不易。资政院和咨议局的设立使得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期间的活动也培育了人民的权利意识。清末议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家权力的运行发生了转型,使得民权在法律上从无到有。《钦定宪法大纲》后附臣民权利义务的九个条款,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人身自由,财产、居住受保护,有诉讼、依法担任官吏及议员等权利。权利虽然有限,又缺乏相应的程序和物质保障,但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形式承认了人民的权利,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预备立宪公会里,商人身份的有68人,占公布总人数的29%。但必须值得注意的是,官员及拥有官衔的会员还有122人,占公布总人数的52%。[18]除此之外,由于当时“轻商”思想以及权位的缘故,部分官员在登记时往往不提及自己身份。照此推断,商人在预备立宪公会里的比例已然占据半壁江山。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中,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主要参加的人员,其中商人6543人,达到总人数的26%。[19]
清末无论是地方议会(咨议局)还是中央议会(资政院),事实上就是由以商人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群体共同推动的成果。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创设,是清末筹备立宪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历史上崭新的政治景观。商人和知识分子作为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其觉醒使得议会这一现代政治组织在近世之中国得以产生。虽然昙花一现,但对后世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来说具有极大的开拓意义。
四、余论
中国近代的国情决定了重大的国家活动与群众斗争,无不与自强御侮、救亡图存这条近代历史的主线相联系。清末议会之路从结果上看是失败的,但从其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权利意识的树立以及为后世提供的经验借鉴上来看又是成功的。当前,我们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机遇期,而民主化、法治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点。综观中外现代化历史,在一个落后的社会结构中很难孕育出现代文明,而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便是市民社会的成长。议会的建立是为了使个人权利得以最大化,推动清末议会萌芽和发展的根本动因与市民社会中公民对自身权利诉求的提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清末议会的失败实际上也是市民社会在当时中国根基不稳所致。中国的民主化和市民社会的成长在改革开放后得以重新开启,虽然经历了数年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推动中国民主与法治发展,应该立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一深广视野[20],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沟通、制约、合作的运行模式,培育我国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形成现代化的土壤和根基。只有这样,以权利制约权力、以个人制约国家而又不失公权力之威信的多元平衡社会以及以保障个人权利为价值标准的民主法治体系才能得到确立。
[1]颜一.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7.
[2]马拥军.“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还是“城市社会”?——生活哲学视野中的“城市社会”理论[J].东岳论丛,2010(11):7.
[3]王焕生.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35.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1.
[5]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3.
[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M].上海:三联书店,1998:272,261.
[8]于文豪.“五四宪法”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J].环球法律评论,2015(2):33.
[9]夏勇.民本与民权——中国权利话语的历史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4(5):10.
[10]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99.
[11]严复.孟德斯鸠法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8.
[12]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4.
[1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52.
[14]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M].上海:三联书店,1998:37.
[15]韦庆远.清末宪政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21.
[1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署理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条陈五年预备立宪及建立内阁事宜折[A].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301.
[17]张晋藩,朱勇.中国法制通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30-131.
[18]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210-222.
[19]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6.
[20]马长山.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