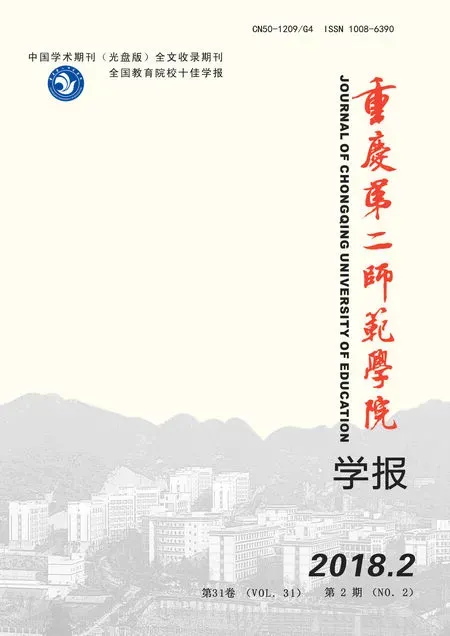李道纯中和思想及其道德实践研究
王 瑜
(新疆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7)
李道纯,字元素,号清庵,别号莹蟾子,都梁人,生活于宋末元初,是将南宗融入北宗全真教的一代高道。作为那个时代道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著述颇丰,存《中和集》《全真集玄秘要》《道德会元》《三天易髓》《清庵莹蟾子语录》等。他的内丹学说,以“中”融合三教,把内丹修炼视为道德实践的过程,对后世道教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中”
(一)引儒入道
《中和集》是李道纯最重要的著作,其中和思想深受三教的影响,在他的道德实践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在对儒家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他融通了 “致中和”的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里的这段话以人的情绪为立足点诠释出“中”与“和”各自的关键之处,并区分出“中”为“本”“和”为事物最普遍的规律,然后将“致中和”的思想推广至天地万物。宋儒伊川将“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引入“中和”思想,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1]。并通过“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这两个层面使“中和”思想与心性的体与用相联系。陈来在其《朱子哲学研究》里也指出,从杨时到李侗的道南一派特别注重《中庸》“未发已发说”的伦理哲学,通过杨时强调以“心”去体“未发”的途径,来体证“中”之意。陈来认为,这就把《中庸》的未发伦理哲学转向了具体的修养实践“体验未发”[2]。这也是宋儒将“中和”作为其道德修养的方法,而李道纯的感应于未萌到“寂然而通”“无为而成”再到“不见而知”,也体现了上述“中和”之“通”的过程。另外,李道纯的“应变”观中还提到如果可“致中和”则可以达到“虚而灵,静而觉,动而正”从而“应无穷之变”[3]483,认为“致中和”是人以之适应世界最好的方式。
李道纯进一步引“易”入道,融通了《易传》的中和思想。如《中和集》中发扬《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提出“三易”观点:“观天易贵在穷理,理穷则知天。观心易贵在行道,道行则尽心”。明“天易”在“读圣人之易”,明“心易”在于知“天易”,一旦懂得了“心易”也就足以“通变”[4]486。这里肯定了人可以通过“易”提高 “穷理”水平,辅助实践“行道”,进一步实现“尽心”和“知天”。李道纯认为这“三易”是可以通过感应之道来使它们相互渗透与作用的,而这感应之道也就是中和之道。另外,李道纯还对“易”进行剖析,提出“常易”不易之易和对应的“可易”,认为二者在认识上是“常者易之体,变者易之用”[4]484的体用关系,而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知其用,全其体,则能利其用”[4]484的相互作用。“易”包含寂然不动的体和瞬息万变的用,若持“动静不失其常”的中和思想则可以明了“易”之体用[4]485。可见,其用关键还是回到“致中和”上,“致中和”则可在实践上“体极利用”,以“屈伸相感之道”[4]485尽天下无穷之利,以“中”连接“常易”与“变易”。历代道教也重视“易”的研究,如东汉时期的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引“易”入“丹”,开创了将炼丹理论本于《周易》的先例。
李道纯的《中和图》明显受到《太极图》的影响,他以儒家立场返“太极未判前”,从太虚到受气到形体未分最后生而立性立命,从而“穷理尽性至于命,原始返终,知周万物”[4]493。从中不难发现,其对宋儒道德伦理上的接纳与借鉴(按思想史的进程,《太极图》的产生过程应当是陈抟《太极图》——周敦颐《太极图》——朱熹《太极图》——白玉蟾《无极大道图》——李道纯《太极图》[4])。在对人的道德标准上,他提出:“人之极也,中天地而立命,禀虚灵以成性”[4]484。认为人存在天地间需要立足于自己的性与命。之后,李道纯用了动静、实虚二理来进行具体论述:“动而主静,实以抱虚”,它们是相互依存与作用的,“二理相须,神与道俱”[4]484。 显然,这是发扬了周敦颐“立人极”的道德标准,并为其达中和的道德境界提出了“主静”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李道纯的“主静”与“抱虚”实际上是为“立性立命”,从而为全真性命双修的丹道道德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李道纯将儒家思想融入其思想,借鉴与发展了“中和”“易”“性命”等内容,并融入他的丹道体系里,使其丹道的理论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
(二)融佛进道
印度龙树发展般若思想创中观学派,提出“非有”亦“非无”的“中道观”。其思想有四句非八不中道以及“诸行生灭不住,无自性,故空”(《中论·观行品》)为标志的缘起性空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三是偈),则集中体现了中观派的“空”观。天台宗的“三谛圆融”完成“即空即假即中”的中国化中道思想[5],提出了“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两个层面的思想内容。“三千”即宇宙万物,都在一念心中,本质是圆融三谛,即空、假、中存于一念。天台宗圆通则无障无碍的认识,发展了佛教的心性论。李道纯的中和思想明显受到佛教心性说的影响,并且融汇了佛教的中道思想。他有一句对佛教总结性的话:“二身一体、三心则一、消碍悟空、显微无间、不立有无、戒定慧、无有定法、虚彻灵通、真如觉性、常乐我静、朝阳补破衲、对月了残经、金刚经塔。”[4]526其解释“二身”实为“法身”与“化身”“法身清浄本无形,有象何名圆满身。假使化身千百亿,不能合一不全真”[4]526。实际是把佛教的“二身”服务于其全真性命说。“不立有无”则有缘起性空观的中道观痕迹。当然李道纯在吸纳他说的同时也有所创新,他既认识到《心经》“自起初一句,至末后一句,都不出一个空字”[4]526,又在诠释“真如觉性”时提到“真性元来本自圆,如如不动照中天。光明莹徹无遮障,照破鸿蒙未判前”[4]526。这样的宇宙观明显与佛教有区别,此处“真如觉性”的解释并非阐述佛家的空性心性,而更多的是融合了道家的宇宙生成论。
李道纯在他的著作里常采用佛家教学教化的“禅机”方式,他与弟子的对话也常使用三教对比与意境融彻的教导方式,如弟子疑问儒道释都各有文字性经典时,李道纯用“是入道之径路,超升的阶梯”[4]496、“过河之筏”来启示弟子们不着于文字,于文字语句外悟真的观念,在《金刚经》里亦有“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的说法。再如弟子问三教一理,李道纯则回答,涅槃与脱胎是一个道理:“脱去凡胎也,岂非涅槃乎?”[4]496类似的案例说明李道纯在融佛入道的过程中,以佛教为用阐述自己的中和思想时也深受佛家义理与实践方式的影响。
(三)三教一理
《中和集》开篇即云:“释为圆觉,道曰金丹,儒谓太极。”佛教讲“如如不动,了了常知”,儒家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道教言“身心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这三者都是“言太极之妙本也”[4]482。在《三天易髓》里也有相似的描述,认为“玄珠”“太极”“金丹”是“名三体一”[4]526。李道纯对三教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认为其三者名殊理不殊,统一于“一”,认为致极处就是这个“一”。“这一字法门,深不可测”[4]518,力主三教本于一源。
李道纯认为三教是异名同实的,他用“○”表示三教之本,也是最终的归宿。佛教视“○”为“真如”,儒家视“○”为“太极”,道教视“○”为“金丹”,体同而名异[4]497。而关于三教对“○”的切入点,他认为道家从“虚”与“静”入手,以体认“玄关”的内丹为方法顺应万物;儒家立足于“诚”字,尽“易”的深奥精微;佛教落脚于“空”,常惺惺识“真空”。他认为“○”是“真性”,其内丹就是取“真性”的过程,而佛在于见性,道在于存性,儒在于尽性。李道纯解释引儒释之理阐述道的目的是使学者明了三教本一,从而不生出二见[4]526。他以儒释来融合道,其实也是以“道教”贯通两教,证明作为最高目的的“道”,是可以通过三教来体现的,只是三教各自的方式路径不同而已。
李道纯特别提出,“中”为“儒宗”“道本”“禅机”[4]516。他认为三教都是以“中”为捷径,同时也都是“抱本还原”的。“中”贯穿了这个过程,儒有“致中和”贯穿“原始返终”太极未判前,道有“中为玄关”的内丹以回归道体,佛有“中道观”以观心性。三教以各自对“中”的不同见解作为基础,最终通往“○”这个归宿。
二、道德实践的方法路径:“中派内丹”
内丹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命活动,表现了人对生命的积极反思。早期的全真教并不过于看重修炼的工夫,而更注重宗教的社会实践,所以导致了讲性较多,而炼神气及火候法度较少。李道纯则把注意力转到了人的内修内炼,实现了从宗教社会实践向个人精神提升实践的转变。
首先,李道纯区分且对比了“外药”与“内药”:“外药”为用,可治病而长生久视,为“交感精,呼吸气,思居神”[4]488三元,其于外有为而实无;“内药”为体,作为内在超越的本质,泯灭有无差异,为“先天至精,虚无空气,不坏元神”[4]488三元,其于内无为而实有。他的方法路径为:“一、炼精化气:初关有为,取坎填离;二、炼气化神:中关有无交入,乾坤阖辟;三、炼神还虚:上关无为。”[4]489前两个阶段皆用“外药”从炼命到炼性命,第三阶段则是以“内药”炼性的过程。这是李道纯所构想的从“外药”到“内药”的修炼过程。而他亦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并把整个认识过程的主体人分为三种“根器”人:圣人生而知之,已得自然无为之道;夙有根器之人虽也为生而知之,但仍需“了性”与“了命”;而根器浅薄者,也可“自教而入”、学而知之。他认为人的天赋虽有不同,但人身上都存“道心”与“人心”,无论哪种根器之人皆能“了性”“了命”,皆具有认识与实践体验的能力。
其次,李道纯对“性”与“命”有独到的认识:“性”为“先天至神,一灵之谓”,而“命”为“先天至精,一气之谓”[4]503。只有对性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才能在具体实践体验方法上有自己的创见。此前的南北两宗都主张性命双修,只不过南宗侧重“先命后性”,而北宗主张“先性后命”。从李道纯的修炼顺序可以看到,他虽是依循南宗的,但却认为人要“性命兼达”,应“先持戒定慧”以“虚心”,后才是通过炼精气神的过程来“保身”[4]503。他以“性”作为修炼起点,也是其融合南北宗内丹学说的体现,同时他还提出炼丹之要就是“性”与“命”。若是不讲“性”“命”,或者有所偏颇,便是旁门,他称之为“偏枯”[4]502。不偏枯于一边的性命兼达,是他引中和理法入丹道的贡献。因为在李道纯那里,性与命都统一于一“理”,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性”造化于心,“命”造化于身,而身心为性命之本,是统一的。面对身心,李道纯提出的实践路径是“虚其心”和“保其身”,心因为有“见解智识”和“思虑念想”的向内存思反倒让“性”受役使,身因有了“举动应酬”和“语默视听”向外的接触外在环境的能力反而使得生命劳累[4]503。在此基础上,人是一种有生也有死,有往也有来的存在。相对于“有”的存在,为达“无为”的终极目标,必须立足于炼身心,先虚其心“持戒定慧”,后保其身炼精气神。
李道纯将“玄关”与中和思想紧密联系,首先继承了北宋张伯端《悟真篇》中关于“玄关”的认识:“一孔玄关最幽深,非心非肾非脐轮。膀胱谷道空劳力,脾肾泥丸莫搜寻”[6]204。又有“超然而出者,乃玄关一窍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有形之中也,○无形之中也。先就有形之中,寻无形之中,乃因命而见性也。就无形之中,寻有形之中,乃因性见命也。”[7]243在张伯端这里,对“玄关”的认识已经是不限于静态身内可寻的了,而是要对它进行整体和动态的把握。“○”作为超越有无的终极,与玄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李道纯称为“关捩”,可见他认为“玄关”的存在决定了能否到达终极目标。李道纯在阐述自己的“玄关”观时,有其独创之处,认为“玄关”不可离了赖以修炼的身,亦不可执于身的任何一个实在之处,为此他举了傀儡的例子,操控傀儡的线如“玄关”,它牵动身却也是由人来控制[4]490。而对于如何把握“玄关”之要,他以“中”字引入丹道:“中”即“玄关”。所谓中者,不在中之内也不在中之外,也非空间上的中[4]498。他认为不可执着于身体从“顶门”到“脚跟”的一处,但亦不可离了此身,向外找这个“中”,所以圣人只以一“中”字示人,只这个“中”即“玄关”[4]490。随后,他又用三教理论来解释:如佛家的不思善恶时的本来面目,如儒家中庸情绪未发之中,如道家念头不起之中。最后,把它归结为“四正中真,发无不中”[4]498。这时的“中”带中和思想的哲理性,所以他也提出,修行之人即以“中为玄关”“择一而守之不易,常执其中,自然危者安而微者著矣”[4]495。这是他将中和思想融入全真丹法的关键,“若身心静定,方寸湛然,真机妙应处,自然见之也”。儒家描述的“寂然不动”为“玄关”之体,“感而遂通”为“玄关”之用。“自见得玄关,一得永得。”[4]495唯有理解了“中和”境界,才能在修炼中把握“玄关”作为立性立命的根基。正是李道纯独特的以“中”字理解“玄关”的方式,使其成为中派丹法的创始人。
三、道德实践的终极目标:“与道合真”
李道纯在《中和集》里提出对生死的见解:“性命之大事,死生为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则自然知死也。”[4]504他认为,进行道德实践 “了性”与“了命”,最终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而切入点则在于先认识“生”,在于认识身是怎么来的。他借用儒家“穷理尽性至于命”的说法,认为原始返终就可知万物、明生死,并进一步提出他对“复”的解释:复卦中,一阳爻位于五阴爻之下,阴静阳动,静极生动之处,便是“玄关”[4]498。他对于“复”的理解是与“中”所贴合的,“复”的过程即“中为玄关”的体现。他也明确表达了“观复”可通晓事物变化之理,进而可“不化”,最终“复归其根”[4]505。由此,他对“生”的探究过程也是以“玄关”为关键的内丹修炼过程。
对于生死的认识,李道纯在《道德会元》中提到,若人不“厚生”,生死的观念又怎么能够束缚住人呢: “及吾无身,忘形无累。吾有何患,忘贵无患”[7]653。他认为,人之所以有生死,是因为人们滞于身、形以及外在得失,人们对生死的认识让自己执着于外在物质上,这种认识与庄子对于生死的观念十分相似。庄子说:“若死生为徒,吾有何患?”(《庄子·天下》)“道”与“天”给予人“貌”与“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庄子·德充符》)。人们外其神,劳其神,外逐生死得失与穷通贵贱,实际上是与道相违背的,所以庄子以“坐忘”作为其对于个人精神超脱的路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庄子·人间世》)。在庄子的精神世界里,个人只有泯灭了对立,随物而化,才可以在大化里“逍遥游”,获得真正的自由。李道纯把庄子“忘”的根本态度运用到他对生死的超越认识上,认为如有人可以将自己的境界提升到不为物眩和不被缘牵,则外在世界也不会束缚其一丝[4]504,“物我两忘,尽性至命定矣”[4]523。人通过生命的内在修炼而后不被外物所牵,实现精神的解放而到达彼岸,这也是李道纯中和思想的归宿。
李道纯主张通过内丹的实践过程,以精神解脱带动形体解脱,有了对道的体认,性命双全而回归于道体。他认为内丹实践的最上乘,即无上至真之妙道:以“太虚”“太极”“清静”“无为”“性命”“定慧”为基础,以“窒欲惩忿”“性情合一”“洗心涤虑”“存诚定意”为实践方法,以“戒定慧”“中为玄关”“明心”“见性”为实践要点,最终“三元混一”,性命相即“脱胎”从而“打破虚空”[4]492。在此,李道纯将三教“一以贯之”,认为最上层的内丹实践是精神层面而非可守持外功可致的,正如三教的最终归宿皆为“与道合真”,即通过综合丹道与对宇宙整体的认识而把有限的个体生命投向无限的道之中,也是“复归其根”。李道纯认为,性命相即人的真实存在,实现自我超越,最终实现真正的自由,实现个体存在的意义,进而也把内丹的上层推到了理论的极致,于是他说:“性命双全,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这个时候无生死可超越,无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观念,没有因果的联系,可以“无知得大轻快,得大自在”[4]504。在李道纯的道德实践进程中,把性命相视为人的生命的本质,立“中和”为基础理论,从“玄关”体证入手。换句话说,在李道纯这里,道德上升纯化的过程不仅是精神境界提升的修养,而且也包括形体肉身变易的修炼。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319.
[2]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83.
[3]道藏:第四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4]岑孝清.李道纯中和思想及其丹道阐真[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83.
[5]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80.
[6]王沐.悟真篇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道藏:第十二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