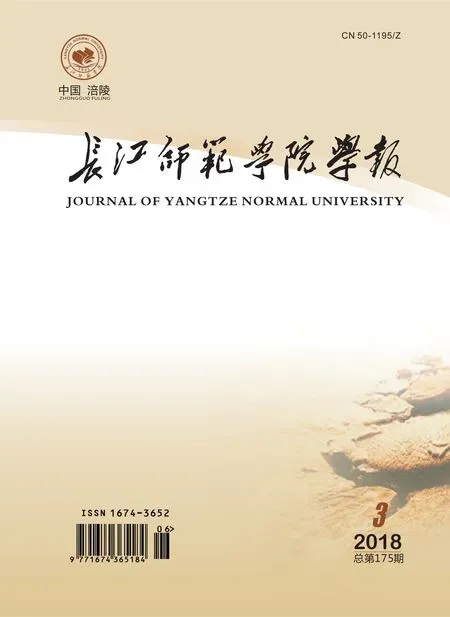新旧《五代史》关于吴越钱氏家族记载的异同
苗梦颖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吴越国,一在春秋战国,一在晚唐五代北宋初。这里所研究的是后者,因其开创者和后来的即位国主分别是钱镠及其子孙,故在“吴越国”前加“钱氏”二字。史书对于钱氏吴越国均有记载,这里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新旧《五代史》关于吴越钱氏家族记载的异同。
一、钱氏吴越国
吴越是五代时十国之一,钱镠作为吴越国的建立者,发迹史颇具传奇色彩。唐末追随石镜镇将董昌,为其副将,击败黄巢起义军的进攻。乾宁三年击败董昌,尽有两浙十三州之地。后梁开平元年封吴越王。历经三代传至钱俶,立国80多年。
吴越钱氏政权在江浙地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政治上,宋太宗称誉钱俶:“卿能保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1]苏轼同样盛赞钱氏给吴越居民带来的福祉,云:“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2]在经济上,钱俶纳土使百姓免于战火,更使江浙得以发展。入宋后,江浙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为全国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在文化上,钱氏奉行“向学重文、礼贤下士”,文人学士聚集于此,如皮光业、林鼎、沈菘、罗隐等。钱氏广建佛寺、佛塔等佛教建筑,弘扬佛教文化,佛教的信仰使处于动荡社会中的人们有了精神寄托和心理慰藉,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些贡献都被宋朝统治者所认可,同时也为钱氏在宋朝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新五代史》(以下简称《新》)的编撰者欧阳修与钱氏后人钱惟演关系密切。欧阳修在中进士后,便在钱惟演的幕府中工作,与钱惟演、谢希深等人终日饮酒赋诗。欧阳修在其《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中明确地记录了这段快乐的时光:“(钱惟演)公,王家子,特以文学仕至贵显,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属,适皆当时贤材知名士,故其幕府号为天下之盛。”[3]386
钱惟演也将欧阳修视为英才,优待有加,如《渑水燕谈录》就记载:“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国学补试国学解,礼部奏登甲科。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待公优异。”[4]40在欧阳修离开钱惟演幕府后,仍念念不忘恩公,甚至在钱去世后,还努力为他请得美谥,记载于《邵氏闻见录》,以反映钱惟演礼贤、爱贤的品质[5]。
二、新旧《五代史》记载的异同
《旧五代史》(以下简称《旧》),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新》原名《五代史记》,为北宋欧阳修私撰。始撰时间大约在宋仁宗宋景祐三年,至宋仁宗皇祐五年成书为止,历时18年,比薛氏《旧》晚出近80年。后人依薛史、欧史问世之序,以“新”“旧”相别,故薛氏《旧》、欧阳氏《新》为后世沿称。
北宋时期,两书并行于世。在南宋,兴行《新》而废止《旧》,后人据《永乐大典》及众多史料,重新恢复《旧》大致原貌。同处一时代,共记一时期,两书的命运却大相径庭,至于原因,前人多有研究,这里主要探讨作为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在新旧《五代史》中的记载,寻其异同之迹。究其缘由,亦希有所发现,以求正于方家。从整体来看,新旧《五代史》关于吴越国钱氏记载有异有同,然是异多同少。
第一,相同之处。《旧》将中原政权以外的地方割据政权,分为《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对于五代,《新》《旧》均持肯定态度。然十国就另当别论了,《旧》视其为独立之国,《新》则认为十国是“并起争雄的鲸先盗贩”。可见,在对待十国的态度上,《新》《旧》大体相同,均视其为正统。对待五代和十国两者之间截然不同的态度,究其原因,是因为宋朝承袭后周政权,尊“五代”也是为了维护北宋政权的正统地位。“实际上,十国与五代在当时并立于世,不分正伪,何况,五代立国都非常短促,加起来不过53年,而十国政权立国皆比五代时长,最短的北汉也有28年,而且它们都是自建国号制度,有的表面服从中原王朝,实际完全独立。”[6]作为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当然亦不能免俗,相对于五代,新旧《五代史》记载内容较少,但记载内容大体相同,这是因为两书皆是来自于《五代史录》。钱镠作为吴越国的第一任君主,两书都花费大量笔墨进行描写,其发家史大致如下:跟随董昌(讨黄巢、灭刘汉宏)→割据两浙(占浙西、讨伐董昌、平定徐许之乱)→建国吴越(封越王、吴王、吴越王)。经历三代四传,至于其他各君主,记载较少,大多几笔带过。这与新旧《五代史》的编纂者们的态度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材料之不同。《旧》共150卷,《新》共74卷,然后者的史料相较于前者,有增无减。欧史增补了薛史所无的史事,如王鸣盛所言:“僭伪诸国,皆欧详薛略,盖薛据实录,实录所无,不复搜求增补,欧则旁采小说以益之。”[7]709不可否认,欧史对薛史的增补确是事实,特别是对十国政权的记载,《新》比《旧》更加详细完备。具体原因有三:1.欧阳修修撰《新》时,十国政权消失数十年,各国的史籍尤其是南唐和后蜀史籍汇集京城;2.在此期间,《九国志》等已经问世,欧阳修曾参加过《十国志》的撰写;3.欧阳修比薛居正等修史晚80年,这期间又出现许多薛史所未能见到的新材料。据学者考证,欧史所据文献材料大约有60种之多,除文献材料外,欧阳修还注意从金石及社会调查中获取材料。
在两书中,有些关于吴越国钱氏家族的记载也是不尽相同,取其一例:《旧》记:“镠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镠大庀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8]1771《新》载:“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9]843
由此可见,《旧》侧重于描写钱镠的穷奢极欲,而《新》不仅描写了钱氏的淫奢,还描写了苛政严法。此外《五国史补》中也提到钱氏的奢侈之风。曾在雍熙年间任苏州长洲县令的王禹偁对吴越的情况较为熟悉,说:“钱氏据十三郡,垂百余年,以深赐为名而肆烦苛之政,邀勤王之誉而残民自奉者久矣。属中原多事,稳小利而忘大义,故吊伐之不行也。洎圣人有作,钱氏不得己而纳其土焉。均定以来,无名之租息,比诸江北,其弊犹多。”[10]钱氏吴越国在水深火热的五代十国时期,再加上钱镠出身贫苦家庭,发迹之后免不了兴起爱奢之风。不单单是吴越国,五代十国君主没有一个可以避免。这从侧面反映了吴越国经济的繁荣,地区的富庶。然而《吴越备史》称钱镠“自奉节俭,衣服裘被,皆用绸布”[9]。这与《新》《旧》两书记载截然不同,究竟哪个更为接近历史,就如司马光所说那样:“按钱镠起于贫贱,知民疾苦,必不至穷极侈靡,其奢汰暴敛之事盖其子孙所为也。”[11]这种说法无疑得到更多的认同。关于吴越的赋敛苛政现象,宋人内部多存在争议。对此,司马光也说:“吴越虽重税敛以事供贡,然椒多宽民之政,下令租赋多所通滞,岁杪必命镯荡。又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于是境无弃田。或请纠遗丁以增赋,椒杖之国门。故终于邦域之内悦而爱之。”[12]其实无论真实与否,都不会影响世人对吴越的正面评价。
史书之所以备受后人重视,其重要原因在于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这也是衡量其文学价值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唐宋这些悠久且重要的朝代,对五代十国的记载就相对略少。新旧《五代史》作为研究五代十国的重要史书,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相对于薛史,欧史增加了不少材料,然欧史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一味地追求言简意骇,删除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旧》150卷,直接引用了许多皇帝的诏书、敕令和大臣的奏疏。这些材料源出五代历朝实录,弥足珍贵。所谓“奏疏”,即奏与疏,“奏”意谓臣子向君主进言或上书;“疏”意谓官员向朝廷的建议。据统计,《旧》直接引用官员“奏”原文有87条之多,直接引用官员“疏”原文6条。如新旧“五代史”均提及由于乌昭通的关系,钱镠被贬,其子钱元瓘为父上书陈情的事情。《旧》摘录了钱元瓘奏章的具体内容:“窃念臣父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国王臣镠,爰自乾符之岁,便立功劳;至于天复之初,已封茅土……谨遣急脚,间道奉绢表陈乞奏谢以闻。”[8]1769-1770
而《新》以“元瓘等遣人以绢表间道自陈”一句话概括之。此外,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称:“欧史喜采小说,薛本多本实录。”[7]677
欧史记载其事,较薛史详尽,因为欧史利用小说、笔记等材料,补充了不少传记中的史事或者细节,但却删除了较多宝贵的原始材料,因此就史料价值而言,《旧》高于《新》。
第三,作者思想的差异体现。其一,10世纪的中国,南北纷争、五代更迭、十国割据,而偏安东南一隅、国狭势弱的吴越国却休兵息民,社会安定,国富民强,以及后来入宋后的隐忍态度,这与其实行崇尚佛教的政策都是有一定联系的。如广建寺院,其中有著名的灵隐寺扩修,修建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功臣塔等。钱氏吴越国历经三代五王,钱谬、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徐和钱弘俶皆崇释礼佛,大力提倡佛教,王室成员更是带头礼佛、供佛,从而在全社会蔚成习佛风气,且在历代帝王之中,鲜有出其右者。因此新旧两书在记述钱氏家族时必然要提及,然《新》并未提及此事,令人不免生疑。《旧》在文后摘录《五代史补》,云:“僧昭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塘钱珝所礼,谓之国师。”“僧契盈,闽中人。通内外学,性尤敏速。”[8]1775《旧》记述了君王与僧人的往来,由此看出其皇族崇释礼佛。撰者薛居正所处的宋代初年,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及价值体系领域还都处于过渡阶段,重武轻文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士大夫们不受重视,对于国家民族命运淡漠,因此其编纂过程中自己的思想流露较少。《新》对于此事却只字未提。细究原因可发现,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复兴儒学、排斥佛教的有力倡导者。欧阳修反对天命、佛、道及各种迷信的思想在一些史著和史学论文中也早有论及,如《原弊》一文中指出,佛教势力的发展与“农本”追求背道而驰,已成为危害社会的一大弊端,“今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图之民”[3]870。且“为僧者,养子弟而自丰食,是一僧常食五农之食也”[3]872。庆历三年,欧阳修完成了《本论》3篇,其中《本论》中、下两篇集中论述佛教的危害,阐发欧阳修的排佛理论。因此他在史料取舍时,对相关记载弃而不用,很好地表现了欧阳修的反对迷信思想。
其二,《新》云:“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镠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9]835此言钱镠自小骨法非常,有贵人之才,不免有重天人之嫌。又云:“元瓘字明宝,少为质于田頵。頵叛于吴,杨行密会越兵攻之,頵每战败归,即欲杀元瓘,頵母尝蔽护之。后頵将出,语左右曰:‘今日不胜,必斩钱郎。’是日頵战死,元瓘得归。”[9]841此关于钱元瓘的记载也不免增加了神秘色彩。《新》撰者为欧阳修,他主张树立儒家传统,反对天命和各种迷信思想,对于此等史料,作者都是弃而不用,为何作者却一反传统描述了关于天命的事情。探而观之,则不难发现,这就是欧阳修修史所采用的春秋笔法。北宋中期的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欧阳修等人积极倡导政治变革,其意识形态在《新》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因此欧阳修选择用“春秋笔法”来宣传王道大一统的思想,用春秋义法来结构史书。《春秋》宗旨和笔法是欧阳修史学实践的基础,他通过对钱镠及钱元瓘的谶应占卜之言的记载来对这种迷信思想加以深刻批判。王辟之则在叙事之末评价欧史曰:“文约而事简,褒贬去取,得《春秋》之法,(司马)迁(班)固之流。”[4]70
相比之下,《旧》史料基本来源于历代实录,五代实录由五代、北宋初年人撰写,于政权建立者的神化、溢美之词不言而喻,然对于吴越国,薛史却一反传统,只字未提,相比于欧史借史书来宣传自己的思想,《旧》作者更是客观陈述,个人思想融入较少。其实关于这些灵异传说,《通纪》《吴越备史》《太平广记》等书均已提到,如八百里退兵、钱镠射潮等,更多地表现出百姓们对钱氏功绩的褒扬。
第四,史论之不同。史论列为一文之末端,较能反映编撰者的观点思想。对于吴越钱氏家族,两书有不同的评论。《旧》云:“史臣曰:自唐末乱离,海内分割,荆、湖、江、浙,各据一方,翼子诒孙,多历年所。夫如是者何也?盖值诸夏多艰,王风不竞故也。洎皇宋之抚运也,因朗、陵之肇乱,命王师以遄征,一矢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瑶琨筱簜,咸遵作贡之文;江、汉、雎、章,尽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盖属大统有归,人寰允洽故也。惟钱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盖事大勤王之节,与荆楚、湖湘不侔矣。”[8]1775-1776
薛的观点显而易见,认为钱氏不是节俭之人,但对其功绩还是表示认可的,赞赏的是钱氏历代君主与众不同的“盖事大勤王之节”,奉中原为天子,称臣纳贡。然《新》称:“呜呼!天人之际,为难言也。非徒自古术者好奇而幸中,至于英豪草窃亦多自托于妖祥,岂其欺惑愚众,有以用之欤?盖其兴也,非有功德渐积之勤,而黥髡盗贩,倔起于王侯,而人亦乐为之传欤?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是时四海分裂,不胜其暴,又岂皆然欤?是皆无所得而推欤?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9]844
由此可看出,欧阳修在前面引用大量谶应占卜之言,是为了更加有力地进行批判,这与他反对符谶灾异迷信也是相吻合的。此外欧阳修对钱氏大加苛责,认为其苛政严法,没有造福于一方百姓。对此,我们不甚赞同。钱氏在位84年,保境安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最后一代君主钱俶更是纳土归宋,使万千百姓免于战火。怎么能说其无德泽施其一方呢?表明欧阳修此种偏见的,还有《新》卷61《世家序》中的一句话:“驳剿弗堪,吴越其尤。”[9]747
钱氏家族至今在两浙地区都深受百姓的爱戴,这与钱氏“纳土归朝”是密不可分的。《十国春秋》论曰:“钱氏据有两浙,几百年。武肃以来善事中国,保障偏方,厥功巨矣。”[13]由此可见,对于钱氏家族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
总之,新旧“五代史”对吴越国的记载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可以看出其鲜明的不同态度,以及新旧《五代史》编纂的异同。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904.
[2]苏轼.苏轼文集编年笺注[M].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587.
[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吕友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5]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3.
[6]姜海军.新旧《五代史》编纂异同之比较[J].史学史研究,2013(3):27-36.
[7]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钱俨.吴越备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成都:巴蜀书社,1989:349.
[1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8880.
[12]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宋元浙江方志集成[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1113.
[13]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1184.
——雷峰塔与吴越国佛教艺术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