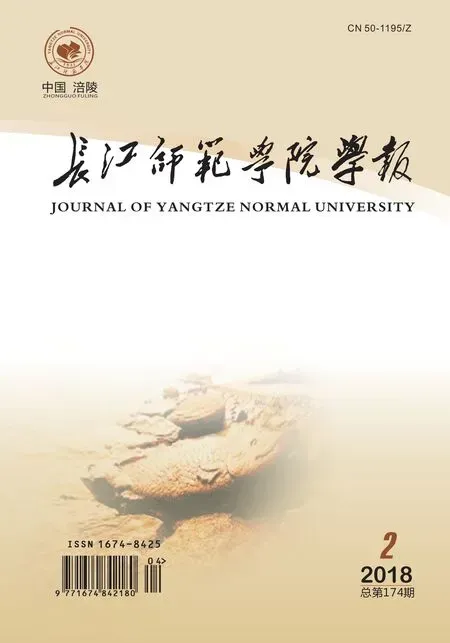梦通大道
——试论《庄子》之梦与《聊斋志异》之梦
梁锦丽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一
自两千多年前成书以来,《庄子》以其丰富深邃的思想观念和汪洋恣肆的美学风格,成了我国古代乃至今天众多文学创作者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美感源泉。可以说,自庄周之后,历代体裁各异的文学作品当中多多少少都烙有《庄子》思想的印记。成书于清代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部一流的文言小说作品集,其作者蒲松龄的思想渊源一直颇受学界重视。身为一介寒儒,蒲松龄思想中的儒家成分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聊斋》中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无须赘述。但在儒学之外,蒲松龄也深受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思想的熏陶。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聊斋》与《庄子》行文中对于“梦”这一题材的一致偏爱,以及《庄子》中“庄周梦蝶”这一故事对《聊斋》创作的巨大影响。
翻开《庄子》这本书不难发现,关于“梦”的描写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庄子》中“梦”字出现多达30次(姑且将内篇、外篇、杂篇都包含在内),其中《齐物论》《大宗师》《人间世》《至乐》等篇中尤为集中和明显。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创作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庄子借以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那么,庄子为何对“梦”这一主题格外关注呢?这与梦这一现象的特点有关。何谓“梦”?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梦是人类一种正常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凡是睡觉时留下印象的经历,醒来时还能够回忆的、讲述当下生活情感状况的、刺激认知和感情发生各种联系的,以及促使发生变化的经历的都是梦”[1]23。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们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只能夸大其所体现出的神秘主义色彩。当我们翻阅古籍时,会见到很多关于梦的记载。殷墟卜辞中已经开始出现梦兆的记录;《诗经·小雅·无羊》云:“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2]表明了梦与占卜之间的关系;《左传》中也有多处关于梦境的描写,主要起预言作用。总而言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梦或者被认为是一种现实的征兆,或者被看作是人神沟通的手段,迷信色彩十分浓重,尚不具备真正的文学审美价值。
当庄周开始进行创作时,“梦”这种理性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引起了其浓厚的兴趣。他运用强大的创作灵感和文学天赋,借助寓言的手段,使梦这一现象一扫原始粗糙的面貌,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崭新姿态。在《庄子》构建的梦幻世界中,现实世界的有限性被颠覆了,心灵可以追求无限的自由。梦既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人与鬼之间,甚至可以存在于植物和人之间、动物与人之间。无独有偶,当我们翻开《聊斋》时就会发现,尽管与《庄子》相隔了几千年的时空,蒲松龄所构建的梦幻世界与庄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庄子》到《聊斋》,这些恢诡谲怪的梦幻世界以虚幻经验的形式宣泄着创作者的情绪,表达着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及在现实中难以满足的愿望。
二
从结构层面上来说,《聊斋》对《庄子》梦幻思想的继承,首先体现在故事模式的借鉴上。在现实世界中,人与鬼、人与动物、人与植物是不可能沟通和交流的。然而在《庄子》构建的梦幻世界中,人类可以突破一切束缚,跨越生死,甚至跨越种族与天地万物直接对话,这就使作品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例如,在《至乐》篇中:“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3]接下来便是庄子与骷髅之间关于生死的一大段对话。显然,在这个故事里,骷髅作为“死”的代表进入了庄子的梦境之中,梦成了沟通“生”与“死”阴阳两界的一个精神通道。这种打破生死界限的想象模式,对后世志怪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除了生死之外,《庄子》构建的梦境还常常打破人与物之间的界限,使人与植物、动物皆可以进行直接的交流,从而使《庄子》一书呈现出强烈的梦幻色彩。在《人间世》中,庄子创建了一个匠石与栎社“神木”交流的梦境。“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匠石归,栎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匠石觉而诊其梦。”在这个故事中,庄子借助梦的虚幻性,使栎社树摆脱了身为“物”的局限,进入匠石的梦中直接表明其对于“大用”的观点。与人类短暂的生命相比,某些植物往往生存的时间更为长久,因此,以植物的视角来观照人类,往往会获得奇特的审美感受和思想突破。同样是人与物之间以梦为媒介进行交流,在《外物》篇中神龟入梦宋元君的故事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予自宰路之渊,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余且得予。’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明日,余且朝。君曰:‘渔何得?’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君曰:‘献若之龟。’龟至,君再欲杀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杀龟以卜吉。’乃刳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相对栎社树的智者之风,这则故事里的神龟则完全是一个可笑的负面形象。在落入打渔人的网罟之后,它凭借自己的神性夜半给宋元君托梦,诉说自己的遭遇。原以为可以摆脱网罟之苦,殊不知这种“神”性不仅没有使自己摆脱不幸的遭遇,反而给自己招致刳肠之患。同样是以异物的身份入梦,同样是与人类进行跨种族的交流,树和龟却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之所以以梦为媒介来创作这些故事,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加文章的趣味性,更主要的是借此阐述自己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刻哲学思想。也就是说,庄周之梦,并不仅仅只是“梦”,而是用来通向“大道”的一种表述方式。但无可否认,这种充满幻想、饶有趣味的故事模式,对后世志怪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先秦至清代几千年来,梦这一主题在志怪小说中不断得以发展壮大,创作技巧也不断成熟。作为清代最杰出的志怪作品,《聊斋》在这一方面格外突出。在《聊斋》将近500篇作品中,以梦为主题的故事时有出现,除了继承《庄子》异类入梦以说理的传统之外,蒲松龄以其横飞天外的想象能力扩大了梦的表达范畴,创造了更为瑰丽多彩的梦幻世界。
《聊斋》开篇之作《考城隍》,便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庄子》“梦入生死”的故事模式。文章的主人公宋公在病中入梦,借助梦境到达了阴间,在与阴间诸神进行一番对话之后,又顺利回到了阳间。“及抵里,豁若梦寤。时卒已三日。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语。”[4]在这一故事里,主人公可以说是“以梦入死”,同时又“以梦回生”,梦承担了沟通阴阳两界的作用,实现了人与鬼魂之间的奇妙交流。《珠儿》中的詹氏,其自幼被妖僧迷杀,“驱使如伥鬼,冤闭穷泉,不得脱化”,显然是一个可怜的鬼魂形象。后妖僧因迷杀珠儿被官府所毙,詹氏为报恩附魂于珠儿,使珠儿得以“起死回生”。此时詹氏作为一个有肉体可以依附的鬼魂,其形象更加奇幻迷离。“夜间僵卧,毫无气息,冥然若死……天将明始若梦醒。”詹氏以梦为媒介,在阴司与阳间自由穿梭,甚至可以为父母打探家中已故之人的去向。更为绝妙的是,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死去多年的珠儿之姐——小惠同样以梦为媒介,附身东邻赵氏女肉身之上,得以回到阳间与父母短暂共聚天伦。这种用梦境来沟通阴阳的故事模式在《聊斋》中还有很多,显然都离不开《庄子》的深刻影响。进一步来看,《聊斋》中还经常将“梦—醒”与“死—生”进行类比,例如在《娇娜》中孔生复活时“恍如梦寤”;《画皮》中王生复苏之后曰:“恍惚若梦,但觉心隐痛耳。”显然,在面对“生死”这一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时,蒲松龄与庄周一样,喜欢用“梦”作为媒介来进行阐释。
在异类与人类的交流上,蒲松龄也借鉴了《庄子》的故事模式。作为一部志怪小说,《聊斋》中的异类可谓种类繁多:有面目各异的鬼魂,多姿多彩的花妖,当然最多的还是形形色色的狐魅。无论这些异类以何种面目出现,他们身上多少都带有《庄子》中那些骷髅、大树、神龟的影子,只是在蒲松龄的生花妙笔之下,他们的形象被塑造得更为饱满,梦幻的色彩更为浓厚。《庄子》中的骷髅、大树入梦,是为了和人类探讨“生死”“大用”等神秘话题,显示其远高于人类的智慧水平。《聊斋》中也有着类似的故事模式。《柳秀才》记述明季沂县将受蝗灾,沂令无计可施之际,梦到一个“峨冠绿衣”的秀才前来为其谋划,指点其于西南道上祭祀蝗神。沂令依计而行,沂县的庄稼得以保全,只是境内柳叶全被蝗虫啮尽。由此才知梦中所见秀才乃当地柳神,因泄露机密被蝗神报复。显然,在这个故事里,柳神是以沂县救世主的身份出现的,他不但在智慧上高于人类,而且能够指点迷津化解苦难,并且极具自我牺牲精神。在同一故事模式下,柳神对栎社树的形象既有所继承,同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梦幻的艺术外壳下,蒲松龄展开艺术想象力,突破生死界限,超越时空,自由驰骋于幽冥、人间、仙境三界,将万物种种随意纳入梦幻,建构了一个个深远的意境”[5],可以说是对《聊斋》梦幻艺术的精确评价。
三
以上仅仅是从梦这一主题的故事模式方面阐释了《聊斋》对于《庄子》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一部杰出的志怪小说作品,《聊斋》的魅力绝不仅仅在于故事的精彩绝伦和形象塑造的丰富多彩;自然,其从《庄子》那里继承的也绝不仅仅是异类入梦的故事模式,而是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正如前文所说,庄周借助“梦”来通向他心目中的“大道”,而他的这种“大道”也在《聊斋》的“梦”中得到了继承。
历来谈到《庄子》之梦,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一故事虽然在篇幅上远远不如前文所述骷髅、大树、神龟之梦,但在思想层面上却体现了《庄子》论梦的最高水准。同样,它也成了对后世影响最深的一个梦,在文学、思想、文化多个层面上都无可取代。故事所蕴含的“人生如梦”这一重要思想最先作用于道家,而后随着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碰撞与杂糅,其逐渐超越了学理的范围,渗透到了文化的血脉里,成为文人身体里的一条隐性基因。蒲松龄自然也不例外,在其进行《聊斋》的创作时,这种基因在“梦”的主题下时隐时现,与几千年前的《庄子》遥相呼应。
从最浅显的表层意义来看,在“庄周梦蝶”这个小小的故事之中,庄周作为一个具有感性生命存在的个人,在梦中与蝴蝶进行了混化,并且完全忘记了自己。这种借助梦境实现物我转化的概念对《聊斋》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聊斋》中有着不少变形之梦,最典型的莫过于《促织》《阿宝》《竹青》等几篇。《促织》中成名之子梦中化身为蟋蟀,轻捷善斗,“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从而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阿宝》中的孙子楚因爱慕富家千金阿宝,居然梦中离魂,化身为鹦鹉依偎于阿宝身边,最终获得了美满的爱情;《竹青》中鱼容落第回家途中在吴王庙中休息,梦见自己化身为乌鸦,并与雌鸦竹青相配。由于梦境本身具有的虚幻性,这些人物在梦中可以完全摆脱现实的束缚,如同庄周所化之蝶一般怡然自得,栩栩然也。这种浅层意义上的物我转化虽不是“庄周梦蝶”这一故事的思想核心,但其中隐含着的物我合一观念对《聊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聊斋》中创作了大量的花妖狐魅,对人类来说,它们皆为异类,但读者在进行阅读时却并没有太强烈的异类感。虽“偶见鹘突,知复非人”[6],但更多时候还是感觉“和易可亲,忘为异类”[4]167,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庄子》所带来的万物一体的思想。
进一步来看“庄周梦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故事中,《庄子》提出了“梦”与“醒”这一重大命题。庄周在梦中化为蝴蝶,醒来后发现自己仍是庄周。然而,这到底是庄周真正地清醒了,还是庄周仍在蝴蝶的梦中呢?按照一般观点,“梦”的对立面为“醒”,梦为虚幻,醒即为现实。然而梦与醒之间,真的能做到如此界限分明吗?庄子在《齐物论》中假借长梧子之口说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现实之中梦、醒似乎分明,比如梦中饮酒与醒后哭泣、梦中哭泣与醒后田猎,从“醒”的角度看是确定的。但问题是,这种“醒”本身又是难以确定的,会随着人的感觉而变化。看上去与梦相对的醒,其实也不过是梦之一种而已。这样一来,梦与醒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人生就是一场虚幻迷离的梦境,而梦境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别样的人生。这样,在“庄周梦蝶”这个故事中,庄周与蝴蝶、梦与醒的区别被消解了,庄周与蝴蝶、梦与醒合二为一,精神上进入了一种体认大道、超越现实的理想状态。这种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的观点,正是“庄周梦蝶”这一故事最为精彩的核心思想,也是其对后世文化影响最大的一部分。通过后世道教学者的注解和演绎,这一思想不但构成了道教的基础理论,而且被广大文人士子所接受,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尤其是在他们身世零落、遭逢坎坷或精神孤寂之时,这种感觉便格外突出。《聊斋》的作者蒲松龄恰好就是这样一位文人,因此其必然会对这一命题进行更多思考。
《聊斋》中有不少故事打破了梦和醒的界限,梦境与现实相互交融,难以区分。如在《白于玉》一篇中,吴青庵与仙人白于玉交好,思念之下“设席即寝”,果然于梦中得以相见,并被带入天宫巡游。在与一紫衣女子一夕欢好之后,吴青庵发现自己在家中醒了过来,且窗外“昭暾已红”,显然昨夜种种皆是梦境。然而接下来他却于枕席间发现了紫衣女子于梦中赠给自己的金腕钏,表明梦境已脱离了虚幻而进入了现实。几个月过后,当他入睡时再次于梦中见到了紫衣女子,并看到了自己的亲生骨肉。醒来时果然婴儿在侧,于是取名为“梦仙”。在这个故事里,梦与现实之间的门槛被彻底打破了,人物可以随意穿梭于梦境与现实之间,由现实的源头进入梦境,而梦境则是虚化了的现实。这与《庄子》消解梦与醒之间差异的思想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最能体现蒲松龄对“庄周梦蝶”思想继承性的,莫过于《成仙》这篇作品。这是一个道家度人成仙的梦幻故事,文章的主人公周生与成生为莫逆之交,周生因与人争执无辜下狱,性命危在旦夕。成生为之多方奔走,终于将其营救出狱。经此事之后,成生“世情皆灰”,遂舍弃红尘而去。得道之后,成生致力于点化周生,其方法就是借助梦中之梦,让周生在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的情况下自行悟道。周生与成生饮酒后昏昏睡去,梦中发现妻子不贞于自己,于是怒而杀妻。忽然醒来,则身在床榻之上,于是认为杀妻只是梦中虚幻之事。而成生笑曰:“梦者,兄以为真;真者,乃以为梦。”显然预示着周生尚未能分清梦境与现实。周生返家之后,发现妻子被杀,方知此前自己以为梦者,其实为真实发生之事;而自己自以为已经醒来,但其实仍在“梦中之梦”中。此刻“周如梦醒”,这才真正彻底地从这一场大梦中醒了过来。但明伦在此批语云:“一生痴梦,到此才是真醒。”[7]可以说是对周生这场大梦的最好注解。在这个故事里,梦不但在结构上承担了推进情节发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制造了似梦非梦、梦中有梦的迷离情境,与“庄周梦蝶”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内核。
四
在对梦这一题材的创作上,《聊斋》继承了《庄子》迷离奇幻的作品形式和物我合一的精神内核。当然,由于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距离庄周已相隔几千年,因此他对于庄周之梦除了借鉴之外,必然还要加以改造。蒲松龄在创作中结合了自己的思想和经验,运用深厚的文学功力,使《聊斋》中的记梦作品内容更加广阔,内涵更加深厚,既有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又有对美好感情的歌颂。相比《庄子》之梦的轻灵飘渺不食人间烟火,《聊斋》之梦显然已经带有浓烈的生活气息,世俗化特征非常明显。
《聊斋》中涉及到梦的作品大约有70多篇,这些作品篇幅不一、形式多变,但仔细观察这些梦就会发现,无论是梦的主体,还是梦中人物所处的环境都与其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反映的大多是人物本身的愿望和追求。例如《狐梦》一篇中虽有大量的梦境描写,但梦里并没有发生离奇的上天遁地的幻想,有的只是和凡尘俗世一般的闺阁谈笑。“将闺阁细事写入梦境,《狐梦》堪称首创。”[8]62-66这个梦境生活化气息浓厚,读之令人难辨真幻,几欲迷失。又如《公孙夏》中的某生,其在现实中打算入京买官,结果在梦中得偿所愿,花钱做了阴间太守,大摆官威之余,头等大事居然是将小妾接来。人物在梦境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与现实竟无一丝一毫差别,充满了浓烈的市侩气息。
《聊斋》之梦世俗化特征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续黄梁》这部作品。从篇名上来看,《续黄梁》是对以往“焦湖庙祝”、《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故事的延续。黄粱梦故事是道家传教的重要载体,其思想源头直接来自于《庄子》中的“人生如梦”。《续黄梁》的故事在结构上与前人之梦并无太大的差别,一样是写书生入梦,在梦中经历种种富贵,梦醒之后看透一切,“入山不知所终”。但在进行阅读时,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蒲松龄强加在这个故事上的劝诫之意。诚如朱光潜所言:“材料尽管相同,每个作家有他不同的选择与安排,这就是说,有他的独特的艺术手腕,所以仍可以有他的特殊的艺术成就。”[9]以往黄粱故事中的主人公多为正面形象,他们以自己的能力在梦中获得了功名富贵,但转瞬之间又化为泡影。当他们醒来之后,不免慨叹世事虚幻,人生无常,因而得以真正悟道。《续黄梁》中的曾孝廉则颠覆了这一形象设定,其在梦中放纵欲望,无恶不作,并因自己的恶行受到了两世报应。梦中报应之惨烈,使其醒后仍心有余悸,出于惧怕放弃了“台阁之想”。这一故事虽披有黄粱梦的外衣,但其内在旨趣已基本脱离了道家,呈现出强烈的世俗色彩。这与道教在明清两代的衰落有关。道教在明代被卷入了整个社会欲望的横流之中,先秦原始道家那种仙气几乎消失殆尽。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聊斋》之梦沾染上世俗气息自然无可避免。
《庄子》与《聊斋》皆为我国文学史上极具研究价值的一流作品,对其进行比对研究,进而找出行文和思想上的关联,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部作品。与《庄子》的轻灵飘渺,不食人间烟火相比,《聊斋》之梦虽在形式上更加奇幻迷离,但明显已经开始向现实靠近,这恰好是先秦到清代几千年来思想、文化乃至文明变迁的证明。
参考文献:
[1]维蕾娜·卡斯特.梦:潜意识的神秘语言[M].王燕青,俞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23.
[2] 阮元.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438.
[3]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4]蒲松龄.聊斋志异[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王聿发,刘艳玲.管窥《聊斋志异》梦创作的艺术功效[J].安康学院学报,2009(5):62-64.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2004:167.
[7]蒲松龄.但明伦批评聊斋志异[M].袁健,弦声,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97:345.
[8]詹颂.浅谈《聊斋志异》中的梦境(续)[J].蒲松龄研究,2000(1):62-66.
[9]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