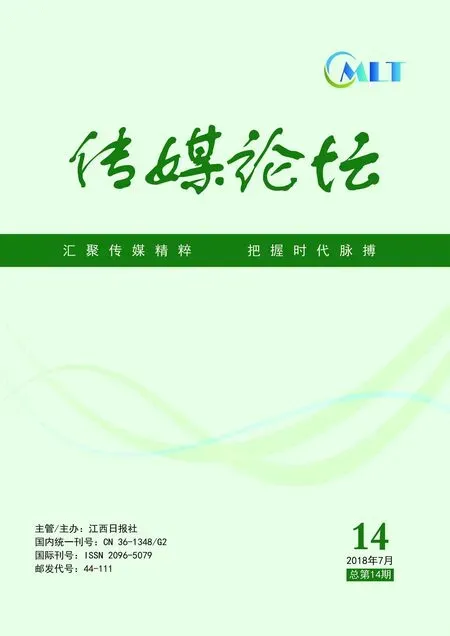探析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仙侠剧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 南京 211106)
一、引言
自2010年起,传统武侠剧逐渐没落,在这之后武侠剧屈指可数,仙侠剧当道,其中也出现了一些现象级的作品,如《古剑奇谭》《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然而,仙侠剧中隐现的“粗鄙化”现象也受到许多诟病,可以说是“黯淡了刀光剑影,渐行渐远渐无侠”。
伊格尔顿在评析后现代主义时,认为它是一种文化风格,反映了这个时代变化的一些方面。后现代主义具有无深度、无中心、游戏、模拟等特征,而这些特征正影响着仙侠剧的创作。本文从仙侠剧的内容生产出发,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研究当前仙侠剧所存在问题的具体呈现,并探讨造成仙侠剧困境的成因。
二、仙侠剧的内容生产
(一)神话母题的援引与重构
仙侠剧的题材往往援引自古老的东方神话或者遥远的传说,以此作为母题来重新建构故事。譬如女娲补天,这一神话被许多仙侠剧吸收,较早的如《仙剑奇侠传》,其女主角的身份设定即为女娲后人,较晚的如《轩辕剑》《花千骨》。此外,上古传说中的名剑、名器、神兽等神话元素也在剧中频频显现,这样的神话援引使得故事具有东方神秘感,也令受众有一种熟悉且陌生的审美观感。
此外,仙侠剧虽然在题材选择上会援引神话或传说,但并非是该神话故事的单纯视觉呈现,它只是以其为背景,进行更为轻松与世俗的叙事。剧中的神仙与妖魔皆如人一般具有七情六欲,故事内容也往往描写神话背景之下小人物的成长、反叛以及爱恨情仇,表达我命由我不由天、邪不胜正、众生平等的主题思想,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二)武侠与游戏的互文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由此,她提出了互文性。仙侠剧即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武侠文学与新兴网络游戏所进行的叙事。
传统武侠剧走向了没落,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却在仙侠剧中获得了传承。仙侠剧中的“侠”,同样遵循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是原始侠客的沿袭,它基本沿用了武侠世界的架构,只是将其拓宽到更广阔的“三界”之中。在武侠的沿袭之外,仙侠剧吸取了新兴网络游戏中“关卡”的形式来进行情节推进,在“闯关”的过程中制造悬念。
仙侠剧将武侠与网游进行结合,搭建出有别于现实生活的玄幻情境,使得受众在观看之时有一种忘却烦忧、尽情游乐的快感。
(三)东方美学的回归
在各类型电视剧中,最能直观呈现东方美学意蕴的莫过于古装剧。仙侠剧也一直试图靠近中国传统美学的表达与风骨,意图打造出史诗般的“东方神话”,具体则表现在视觉呈现与音乐创造上。
在视觉呈现上,仙侠剧的场景建构、服饰造型等均具有东方美学的意味。仙侠剧的场景不是在九天之上,就是在层峦叠嶂中,颇有一份“仙风道骨”的气韵。诸多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道具设计则在细节上诠释了古典意象的升华,人物使用的神器皆有对古典物品造型的借鉴,在人物的服饰造型上则会攫取中国历代服饰中的部分元素进行组合,形成“仙侠风”的味道。在音乐的制作上,仙侠剧往往使用民乐,使之契合东方美学的风格,描摹出东方古典格调的影像。
三、仙侠剧的“粗鄙化”现象
(一)主题的浅薄化
仙侠剧描绘的是东方玄幻,然而较之于西方玄幻剧,在主题表达上显得较为单一与浅显。西方玄幻剧大多也延续和重构着西方神话与传说,主题大多为英雄、拯救、成长、友谊、爱情等,在剧中被交织阐述,在内容呈现上显得宏大而深邃。在西方玄幻剧试图传递出命运、民族、国家、英雄等多种复杂的原型命题之时,仙侠剧却只将爱情单一凸显了,传递的内容只剩下虐恋情深。
仙侠剧所借鉴的神话母题同样有着深刻的内涵,其中不乏人定胜天、知其不可而为之、行侠仗义等复杂的精神意蕴。然而,在仙侠剧的呈现中,这些精神意蕴被“表面化”了,它们都成为了爱情的附加品,是狭隘情感的衍生品。所有的成长、侠义、反叛、济世均与单纯的爱恋紧密挂钩,“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再无其他的养料了。
(二)人物的扁平化
仙侠剧中的主人公形象普遍较为单一,他们往往集所有的美好特质于一身,在成长过程中不是缺乏明显的成长变化就是变化地过于生硬。
随着近年来IP剧大热,在仙侠领域中大女主剧频现,呈现出明显的玛丽苏倾向。她们代表着正义与善良,在初期往往平凡而普通,在剧情的推进中却被揭示出不平凡的身世,此外,她们还具有出色的容貌、强大的法力,遇难皆能逢凶化吉,困境必受高人指点,既收获爱情又拥有事业,是剧情发展的关键,可谓所向披靡。即使这类“大女主”拥有多样的身份,打着“女性成长史”的名号,却仍然无法走出情节雷同、内容相似的困境。在另一种意义上,玛丽苏的设定使得主人公在性格上“平淡而无趣”。
(三)叙事的同质化
单线叙事与多线叙事是电视剧主要的叙事结构。以美剧《权力的游戏》为例,它是多线叙事的典型,该剧的家族、人物间各自的故事均是平行却不同的叙事线索,这些线索相互呼应、错落有致,建构出宏大的史诗气质。而仙侠剧大多采取单线叙事,以主人公的成长与感情故事为线索,略显单薄。
由于仙侠剧的叙事模式无外乎成长与爱情,导致了它们的叙事形成了模式化的套路。在成长模式上,主人公往往是年幼之时突降奇难、父母双亡,在陷入痛苦与孤独之时遇到高人或恩人,之后历经磨难,最终成为三界中不可忽视的人物。在爱情模式上,男女主人公往往一见钟情,在双方相互爱慕的过程中困境跌起、误会重重,虽九死犹未悔。这两种叙事模式几乎可以套用到现下所有的仙侠剧之中,所谓“殊途同归”,不过是“虐”的略有不同罢了。
(四)视听的媚俗化
虽然仙侠剧在视听呈现上表现出了东方美学,但随着仙侠题材的流行,其制作愈显“媚俗”,陷入同质化的泥沼。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仙侠剧在构建美轮美奂的视觉景观上更进一步,为受众呈现了虚拟的真实以及视觉上的猎奇。鉴于仙侠剧人物间的打斗都以神力、法力为主,使用特效来辅助完成打斗场面也成为仙侠剧的常态。然而,在营造视觉奇观之时,仙侠剧的色调与妆造却饱受诟病。当阿宝色成为固定调色盘,“韩式大平眉”成为女性人物统一配置,不同的剧之间无甚差别,这份鲜艳亮丽已经脱离东方审美中的内敛含蓄了。
在音乐创造上,古风古韵的音乐虽是仙侠剧的一大特色,可这“古风古韵”却逐渐沦为浅薄、空洞,沦为华丽辞藻的堆砌,经不起细究。以去年大火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片尾曲《凉凉》为例,曲调虽动听,其填词却毫无逻辑,譬如“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此类的歌词无法推敲,这也成为仙侠剧的通病。
四、多重因素推动下的仙侠剧困境
(一)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催生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已经融入到当下文化产品的生产之中。大众创造着大众文化,也不自觉地被它卷入了后现代现象之中。
伊格尔顿在评析后现代主义时,认为它是一种文化风格,具有无深度、无中心、游戏、模拟等特征。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仙侠剧丧失了深度也不再刻意追求,在文本内容的世俗化与游戏化中渐趋于空洞和浅薄。在深度的丧失中,仙侠剧转而采取泛言情化的内容来填补空虚,用颜值、特效等美轮美奂的形象来刺激受众的感官。
仙侠剧的发展已有多年,其自身却并无较大的成长,从题材内容上而言,近两年更有走下坡的趋势。而今的仙侠剧,处在时代语境下的多种文化形态之中,其创作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目前的问题与短板亦是后现代文化语境催生的结果。
(二)粉丝文化的推动
在当下的仙侠剧制作中,重金聘请流量明星担当主角已是主流。粉丝文化已不再是过去简单的偶像崇拜,它已经演变为促使文化工业发展的生产力。仙侠剧追逐流量明星的现状,即是资本、偶像与粉丝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既然明星自带流量,制作方自然愿意启用高人气的偶像明星来吸引粉丝的注意力,甚至,有制作者过度迎合受众消费偶像的心理,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聘请流量明星的身上,忽视了文本的创作。
在粉丝文化的推动下,仙侠剧已陷入依赖与追逐流量明星的怪圈,致力于营造“视觉奇观”。在无法走出怪圈的情况下,仙侠剧终将沦为快感文化的产物。
(三)创作主体观念的转变
在后现代文化、粉丝文化、消费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的交织影响下,浮躁、逐利等心态跃然纸上。电视剧的创作主体同样身处于消费社会之中,他们意识到仙侠剧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只有在满足受众心理需求的情况下,才能获取商业利益。
然而,假如创作主体过度关注仙侠剧的消费价值,仙侠剧本可以拥有的文本价值也就消解了。艺术审美毕竟不是商业与资本可以取代的,用户体验也绝不可能决定主旨传递。从当下过度的、快餐式的IP开发之中,也可以看到创作主体之中缺少一些“坐冷板凳的人”。雕琢与打磨已成为一件奢侈的事,仙侠剧自然也跳脱不出快消品的行列。
五、结语
仙侠剧广受追捧与其自身的内容生产不无关系,比之于现实生活的高压状态,仙侠世界的天马行空、自由快意更令观众心向往之。
然而,其凸显出的“粗鄙化”现象不容忽视。粗鄙化作为一种“俗”文化,毕竟是由世俗化而来,虽显低俗,却仍然显示出了对于自然人性本身的正视、对生命原始冲动的认可,其戏仿、拼贴的形式也值得借鉴,也为受众带来了感官愉悦与心理快感。但无论如何,“粗鄙化”作为一种文化病,不应当肆意生长。世俗与粗鄙之间应当有度的把握,仙侠剧如果持续“粗鄙化”,它终将沦为明日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