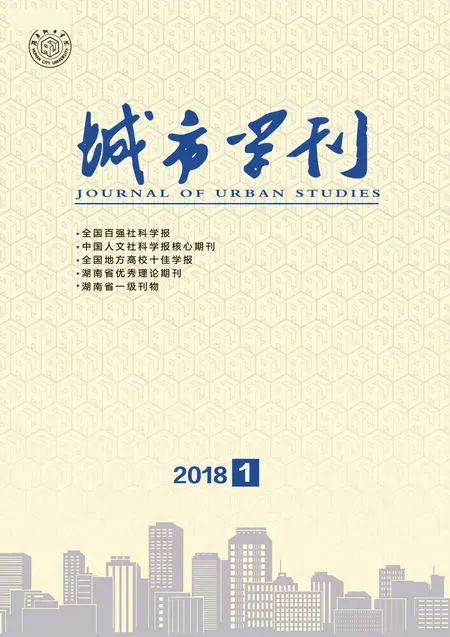环保电影还是生态电影
——《可可西里》和《狼图腾》的文本性质辨析
童业富
(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长沙 410205;2.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提到中国生态电影,《可可西里》和《狼图腾》(以下简称《可》片和《狼》片)是两个绕不开的文本。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可》片和《狼》片甚至被视为中国生态电影的标志性影片,其文本性质似已成定论,无庸置疑。但从学者们现有的论文来看,两部影片的文本性质似乎又不那么确凿,反而变得有些模糊、含混,值得认真辨析。
一
环保电影与生态电影是两个关系密切却又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但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在使用上似乎有些紊乱。陈力君在《中国生态电影意识的觉醒与匮乏》中这样评价《可》片:“将超凡脱俗的可可西里的生命奇观和护山队的传奇经历缝合在大量强大冲击力的视觉镜头中,使影片既具有充满瑰丽的浪漫色彩又具有震慑人心的现实批判力量,成为生态电影成功的典范。”[1]徐兆寿在《生态电影的崛起》一文中称,“从今天的生态艺术观来看,《可可西里》是中国最成功的生态电影”。[2]两位学者言之凿凿,《可》片是“最成功的生态电影”,是典范。而到了另外几位学者那里,情形就颇为不同。李玫认为,“陆川原本颇具希望的拍摄之旅,却在最接近生态意识的地方止步、转向、然后擦肩而过。”[3]李玫的观点表明,《可》片的生态面目非常迷惑人,因为它似是而非。而另外两位学者则直接给《可》片贴上了环保电影的标签。韩浩月指出,“《可可西里》开拓了环保电影拍摄路线,但这类电影不太容易赚钱以及太不容易出彩,才是让创作者望而生畏的缘由。”[4]王瑞红指出,“在我国,影片《可可西里》也是环保电影的代表之作。”[5]也有的学者为了保险起见,干脆把生态电影、环保电影两者合二为一称为“生态环保电影”,比如王莉丽“从《可可西里》看生态环保电影的待挖掘空间”。[6]而导演陆川本人则对这些论点似乎都不太认可,他在接受大江网记者的采访时曾说,“《南方周末》上整版的有关藏羚羊、野牦牛被残酷猎杀的报道,促使我有了这个想法。我开始想传达一种思想,但是拍了一周后改变了初衷,因为我最关注的是那里人们挣扎的生存状态。”这个想法我们推测,应该是拍一部关于生态的电影,但他最终放弃了,转向了关注人的存在。《狼图腾》一片也遭遇了大致相同的境遇:在《环保电影不能这样玩》一文里,韩浩月以《狼图腾》为例进行了阐释,认定其较好地演绎了环保主题;而邵榕榕的《浅析生态电影〈狼图腾〉》、高芳艳的《狼图腾:生态电影的一次华丽转身》、郭志清的《电影〈狼图腾〉的生态主义视域》、包丽娜《谈电影〈狼图腾〉中的生态意识》等论文则明确地将该片指认为生态电影。①其实除了这两部影片外,还有一些影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电影艺术》2010年第4期发表的《我国首部反映水危机环保电影〈河长〉在京首映》就明确将电影《河长》指认为环保电影;而刘文良在《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发表的《拯救失衡的天平——生态电影〈河长〉演绎环保人生》则毫不犹豫地将其界定为生态电影。在学者们的论文里,大多数论者并没有对生态或环保电影进行严格的定义,也没有对它们各自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或许在有的学者那里,生态和环保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没有必要区划得太清,于是就有了“生态环保电影”合并之举。这里,我们不禁心生疑惑:生态电影和环保电影存在分野吗?另外,在学者们的论文中,大多都是先入为主地将两片指认为生态电影或环保电影,然后再做其他论述,至于其为什么属于生态电影或环保电影,则大多只有指认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文本分析或语焉不详。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反问,《可》片和《狼》片究竟是环保电影还是生态电影?其归属的理由又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生态电影和环保电影是否存在分野的问题。严格说来,生态、环保都是人类遭遇到严峻的生存危机后反躬自省而提出来的。环保也好,生态也罢,表面上看都是人类慑于当前生存环境恶化,亟需要改善周边环境以求自保。但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环保与生态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分野。
福柯曾说:“人性中的自然开始死去时,环境便诞生了。”[7]福柯的意思是说当人类将自己视为万物的尺度、万物的灵长这一异自然存在时,万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必须以人为指归,人类成了中心;万物簇拥在人的周围,成了环境。环境就是人的环境。英国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认为:“‘环境’意味着‘环绕’。环境主义者是关心环绕我们的世界的人。说这个世界环绕着我们,就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就意味着坚持自然的价值终归是人赋予的,坚持自然的作用仅仅是供给。”[8]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保护,只是人类觉察到自身的供给来源出现了问题而设法采取的暂时措施,一旦危机过去,人类就会故态复萌。前段时间新闻报道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正式宣布将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将藏羚羊受威胁程度由“濒危”直降为“近危”就是明证。②http: //news.sohu.com/20160905/n467629117.shtml这种分级是否意味着当大熊猫、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种群达到一定数量时,人类又可以肆无忌惮地猎杀了?所以环境保护的出发点是为人的,人类并没有从根本上反省到正是人类自身观念的错置才造成了众多的环境问题。生态批评创始人之一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尖锐地指出:“‘环境’是一个人类中心的和二元论的术语。它意味着我们人类在中心,周围由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那就是环境。与之相对,‘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8]17彻丽尔的观点表明,当我们在说环保的时候,人与自然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关系,人游离于自然;而当我们在说生态的时候,人处生于自然之中,与其他物种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平等相待,和谐共生。
如果以这样一种观念来审视电影,当我们看到一部影片秉持以人为中心,视自然为人类的供给物时,即使这部电影以保护野生动植物为题材内容,我们仍然只能认定其为环保电影。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对环保电影定义如下:环保电影是基于人类中心来看待自然环境恶化、野生动植物生存危机的电影。它以影像的方式对这类现象加以呈现,旨在引起社会关注从而获得某种治理,从而为人类赢得更好的生存空间。而生态电影,美籍华裔学者鲁晓鹏先生进行了如下定义:“生态电影是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电影。它探讨人类与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包括土地、自然和动物,是从一种生命中心的观点出发来看待世界的电影。”[9]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都关注自然环境的恶化、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危机,但是在环保电影中,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主客体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主客是二分的;而在生态电影中,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不存在谁主谁客,人与自然是一种平等相依的关系。
基于环保电影与生态电影这一分野,我们尝试从冲突各方的设置、片中主要动物的地位、草原天葬场景的表现等几个问题入手对两个文本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对《可》片和《狼》片的文本性质做一客观判断。
二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这是戏剧创作中的一句套话。电影不是戏剧,但是冲突依然是故事片中情节的有效助推器。冲突的设置可以让我们管窥创作者的基本意图,体察他们的用心所在。
在《可》片中,冲突双方主要是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他们围绕保护与猎杀藏羚羊展开斗争。影片的叙事动力正是来源于此。藏羚羊成批被杀,高原上随意弃置的藏羚羊尸骸触目惊心。藏汉牧民自发组织巡山队,保护藏羚羊。片头以一组简洁的画面将盗猎分子的穷凶极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抓获了巡山队员巴强,当着他的面宰杀藏羚羊,最后又将其残忍杀害。这一血腥事件直接将巡山队与盗猎分子置于对立的两极,冲突一触即发。事件曝光后,记者苶玉与巡山队一起深入可可西里。一路上,巡山队抓获了两批盗猎分子,收缴了他们猎获的藏羚羊皮毛。后因天气恶劣、车辆抛锚、食物短缺又不得不将他们放走。故事结尾,追寻盗猎头目的队长日泰反倒在了盗猎分子枪下。影片以悲剧性事件始,以悲剧性事件终。
此外,影片也设置了一些相对次要但不乏深刻的矛盾冲突,比如巡山队与自然环境、家庭、朋友、社会体制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不过,在这诸多冲突中,却没有直接发生在人羊之间的冲突。“主人公的原型之一扎巴多杰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个细节,巡山队断粮后几天没有吃的了。雪山高原之上,只有藏羚羊是唯一可以让他们避免饿死的食物,而他们正是为了保护它们才来到这里。绝望之后,扎巴多杰决定猎一只藏羚羊,而且,必须是他亲自操枪。因为他的枪法准。在选择了一只老年的藏羚羊后,他扣动了扳机。他一直忘不了那一瞬间,在诉说的时候,无奈与绝望仍然刻在脸上。”[10]但是影片并没有借用这一原型事件,而是对其进行了改写,将藏羚羊替换成了一只野兔。这一改写将人与羊难得的一次冲突消解了。这一细节也让我们看到《可》片并非没有机会来表现人羊的冲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这一冲突设置清楚表明,主创关注的只是人的生存状态,藏羚羊遭盗猎这一事件只不过是借以表现人的挣扎与生存的一个道具而已。在对这一冲突设置的剖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影片虽然以保护藏羚羊为题材,但秉持的依然还是人类中心主义。“我最关注的是那里人们挣扎的生存状态”,陆川的话并非虚言。
与《可》片着重表现盗猎分子与巡山队员的冲突与碰撞不同,《狼》片虽然也不乏表现土生土长的蒙古族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冲突,场部主任包顺贵与牧民之间的冲突、狼与羊之间的冲突等,但更多的是在着力表现人与狼之间的冲突。
影片中人狼间的冲突肇始于人的贪婪。虽然蒙族人“按规矩”只取走了狼的一小部分猎获物,但外来户却毫不客气地拿走了全部。夜色中,狼立在山巅,无助地看着人掏空了它们的粮仓。在狼的主观视点镜头中,人比狼显得更加贪婪。
人不仅狼口夺食,还要让狼断子绝孙。一匹匹幼小的狼崽被摔向空中,“魂归腾格里”。场部主任包顺贵自作聪明,以为这样就能减少狼对牧场的威胁。与《可》片中藏羚羊只是一再被人猎杀的被动形象不同,狼对人进行了狠狠的报复。在草原最恶劣的一个风雪之夜,狼群攻击了牧场最珍贵的军马。狼将军马赶进冰湖,冻成冰马,就连经验丰富、骁勇无比的马倌巴图也为此丢了命。狼警告了人,在人狼冲突中,狼的主体性开始彰显。
随着人狼冲突的加剧,狼的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场部主任包顺贵组织了一支打狼队,在吉普车和狙击步枪的配合下,狼一匹匹地倒下。有两匹老狼窜上山崖,打狼队放出猎狗追击。狼走投无路,一匹跳下悬崖,一匹掘塌山洞将自己活埋。狼的烈性让人眼界大开。一匹大狼从草丛里窜出来,泅水走了。打狼队驾着吉普车一路狂追几十公里,大狼的体力渐渐耗散,最后在一片乱石间停了下来,它掉转身注视着追赶它的人。画面有些像海南三亚的那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鹿回头。不过,这个现代版的“狼回头”却失去了传说的那份优美,绝望的狼并没有像凄美的梅花鹿那样幻化成一个美丽的姑娘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而是摇晃着身子,倒在了草原上。《狼》片这一核心冲突设置表明,人、狼是平等的,狼并非是为了突显人而被纳入影片的一个符号,人、狼都是主体性的存在。
在对两片冲突各方设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可》片明显侧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羊的冲突只不过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带出来的冲突,人才是影片真正的主体;而在《狼》片中,明显侧重人与狼之间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退居次要位置,狼才是影片真正的主体。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两片中主要动物所处的地位。
三
《可》片中,藏羚羊始终只是一个客体的存在。在盗猎分子那里,藏羚羊是被猎杀的对象,是他们获取生存资源乃至发家致富的所在。在他们看来,藏羚羊是大自然赐予的,是野生的。“野”则意味着无主,意味着谁都可以占有。正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当盗猎分子被巡山队抓住后,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我犯了什么罪?”在他们心中,人类生存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为人而存在的。当“我”要生存这一问题摆出来时,其他任何问题都得退居其次。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其实也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而已。他们甚至从来不会想到藏羚羊也是大自然创造的生命,它们也和人一样理应受到保护和尊重。
在巡山队那里,藏羚羊是一个被拯救者的角色,也是一个从属于人的存在。大卫·波德维尔在《电影诗学》中曾说:“细节总是值得我们去关注,而且它们也常常被批评家们指出来以证明对一部电影的欣赏与阐释的正当性。”[11]还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细节,巡山队抓获盗猎分子后,盗猎分子质问巡山队:“我犯了什么罪?”队长日泰的回答是:“你打了我的羊子。”这是脱口而出、不加思索的言语,但它折射出的更有可能是一个人潜意识中的真实想法。当然,这个“我”并非就一定是指日泰自己,他也有可能是指可可西里人民,放大一点是指整个藏区人民,再放大一点也有可能是全中国人,再放大一点就有可能是全人类。但是总而言之,它是属于人的。人为什么要保护他?为了人类能活得更好,活得更久。因为其他物种如果一个个灭绝,人类最终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下一个灭绝的就是人类自身。所以,不管是猎杀藏羚羊还是保护藏羚羊,人类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只不过一个是只顾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一个着眼于长远,但终究都脱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
从具体影像呈现来看,《可》片中藏羚羊大多数时候是以森森白骨、被砍下的头颅、被剥下的皮毛呈现的。这样表现显然是服从于影片主旨的需要,它能有力地表现盗猎分子的残忍、藏羚羊处在灭绝的边缘。我们发现全片中正面展示活着的藏羚羊的镜头非常有限,更不用说有藏羚羊的视点镜头。也就是说影片中藏羚羊几乎不占有视点,它们没有被赋予看的权力,只是被看的对象。这样在影像表现上,藏羚羊也被始终设定为一个客体。
《狼》片中,狼基本上被作为一个与人相对平等的主体来加以表现。影片中狼的团结、忍耐、富于组织纪律、听从指挥、善于等待时机都很好地融进了故事的叙事肌理中并在狼羊大战这场戏中得到了集中呈现。面对夺其食,杀其子的“人”,狼也并非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狼肯吃苦,敢于选择在最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对人发动进攻,哪怕是面对能踢穿肚子的马蹄、能砸开天灵盖的打狼棒、能勒断脖子的套狼杆,狼都没有丝毫畏缩。即使面对吉普车和狙击步枪,狼也没有丧失自己的“狼气”。它们或掘塌洞穴将自己活埋,或舍身跳崖,或一路狂奔气绝而亡,狼把自己的“狼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影像上,狼也取得了与人的对等地位:电影中不仅是人占有视点镜头,狼同样占有视点镜头,即使与人对阵的戏中,也是人与狼各占一半视点。狼的正式出场始于陈阵的一次错误。在将羊群交给杨克后,为了快速返回场部,陈阵没有听从毕利格阿爸的忠告,肆意走近道,结果与狼遭遇。在这场将近4分钟的戏中,影片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狼的出场。陈阵骑着马进入山谷,马开始预警,陈阵不懂,强行进入。一匹圆睁双眼,眦着牙,掉着红舌头的狼出现在画面中。在特写镜头中,狼瞪着陈阵。陈阵掉过头,分别是两匹狼、三匹狼的两个近景镜头,接下来是狼的两只眼睛的特写镜头。狼全都瞪着陈阵。在一个俯拍的全景镜头中,陈阵陷入了狼群的包围之中。狼锥刺般的目光让陈阵不敢与之对视。导演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镜头,一个马眼的大特写。马眼像一面镜子,映出了狼视眈眈,也衬出了人、马的孤寂,渺小与无比的恐惧。在这或特写或近景或全景的镜语下,狼粉墨登场。但是狼的出场并不全是在人的视点镜头中,相反,在这一场戏中,人却始终处在狼的视点之下。在狼围猎黄羊、外来户夜挖黄羊等段落中,也都一再使用了狼的视点镜头。狼对黄羊的观察、审视,狼对外来户偷走它们猎获物的怒视,都将狼自然而然地放置在一个主体的地位。即使狼被打死,在影像呈现上也不同于《可》片中对藏羚羊被杀的呈现。剥下来的狼皮筒被悬挂在高高的木竿上,在风中飘扬,成为了一种桀骜不驯的狼族精神的象征。打狼行动结束后,陈阵喂养的小狼被嘎斯迈放归了大草原。恼怒的陈阵质问她,“那是我的狼。”嘎斯迈回答:“那是腾格里的狼。”在汉族青年陈阵心中可能依然隐隐约约地认为他是小狼的主人,但在蒙族人嘎斯迈那里,狼和人一样都属于造物主腾格里。当毕利格老人魂归腾格里后,陈阵再次看到了小狼。影片并没有演绎一出人们期待视野中的小狼冲过来与它昔日的“主人”亲密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眼中的是小狼在与陈阵远远对视后,旋即转身离去。陈阵目送着小狼远去,消失在天的尽头。特写镜头中,陈阵目视前方,这时天空中腾起了一朵狼的祥云,镜头定格在它的上面,这就是狼图腾,不灭的狼的精魂。至此,狼的主体性得到了一次完整的叙写。
四
不刻意保存人类的尸体,将人还给自然,可以说草原天葬是最富生态意味的人类行为。两片不约而同都选择了这一习俗,并且一再予以表现。不过在对这一场景的表现和处理上,两片却不尽相同。《可》片中第一次天葬场景是影片开始部分巴强的葬礼,第二次则是影片结尾部分队长日泰的葬礼。两场葬礼上,巡山队员围成一圈站着,中间是牺牲者的遗体,全身赤裸,洁白干净,有着很强的仪式感,象征着牺牲者灵魂的圣洁,渲染了死亡的悲壮和崇高。导演陆川本人坦言,“我觉得可可西里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队员他们的生存,和他们在另外一块土地上的那种挣扎,最能折射出一部分或者绝大多数中国人现在内心的那种挣扎。”[12]因此,即使天葬本身有将人还给自然的意味,但对两场葬礼的处理,基本上还是着重突显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彰显人的崇高。
而在《狼》片中,因为主题更多的是强调万物平等、生生相息、因因相连的观点,所以对两场天葬场景的处理就与《可》片不太一样。第一个天葬场景是毕利格老人的儿子巴图的葬礼。巴图为保护场部军马牺牲了,马车拉着巴图的尸体去安葬。在乱石嶙峋的山路上,尸体在一堆乱石前掉了下来。毕利格老人说他选择在这里下车,就在这里下葬。这就是天葬。在哪里下车就在哪里安葬,一切都依循自然。毕利格老人的解释是:草原人一辈子吃肉,为此,杀了那么多生命,等他们死了,他们将以这样的方式将肉还给草原。人生时吃了那么多肉,只有死了之后将自己的尸骨喂养其他动物,人才能回归草原。这是一种何其通达的情怀,真正将人自身置于与草原其他各物种平等的地位。第二场是毕利格老人自己的葬礼,画面上紫色天幕低垂,以暗示死亡的沉重和死者灵魂的圣洁。但依然是马车拉着尸体,依然是在颠簸的山坡上尸体自然下车,就在那里下葬。风吹开白色裹尸布,露出了毕利格老人安祥的脸,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这两场戏中并没有煽情的音乐,没有隐喻蒙太奇式的镜头语言加以渲染,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胞物与”的生态思想却已然溢于画表。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主题意蕴上两部影片还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客观上,《可》片更倾向于环保,所以在影片冲突方的设置上,杀戮与保护构成了影片的主要冲突。藏羚羊是遭杀戮、被保护的对象,处在客体的地位,而天葬习俗也成为了彰显人物牺牲的伟大而设的仪式化场景。其实影片开始部分,编导就借队长日泰的口暗示了影片的主旨:这可可西里不就是叫你们记者保护着。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这一环保主题成为了影片的旨归所在。在《可》片中,剧中人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藏羚羊作为生命现象与人之间其实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因此人要保护它,并非出于对藏羚羊这一生命现象的尊重,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自身生存的需要。其思想根源在于“环境主义”,即,“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8]13其实,从字面意义上看,“保护自然”一词就已然清晰地昭示着“人不在自然之中”。因此,这种对自然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对自然的主宰,它终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
而在《狼》片中,人狼冲突作为主要冲突贯穿全片,狼性得到了很好的彰显,狼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很好的张扬。狼以它自己的行动让人意识到它并非一个客体的存在,即使像场部主任包顺贵之流其实最终也认可了狼的行为。他听从陈阵的建议让狼王的尸体留在草原,并非陈阵的话语具有多少权威,而是一路狂奔气绝而亡的狼王赢得了他的尊重。在表现草原天葬这一人类习俗上,影片也并非完全从人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角度进行了诠释。影片暗示了人也不过是自然生态中的一员,并不享有特殊地位,即“我是自然”。而这恰是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所在,即,“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8]13正是站在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上,影片含蓄地批评了包顺贵等外来户只顾人类自身利益而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对毕利格老人、陈阵等知青尊重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等行为给予了褒扬。影片改编自姜戎的同名小说,尽管小说结尾部分提到了草原沙漠化,但影片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来扩展其环保主题。因为,“生态主义者坚信,仅仅为了人类而保护环境是不会成功的。生态主义者指出,人类社会半个多世纪的环境保护,从总体上看是成效不大的,严格地说是失败的,环保的进展远远赶不上生态危机的恶化。”[8]17-18
通过比较,我们清晰地看到《可》片距离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电影尚有一段距离,其“保护自然”的旨趣让其只能归属环保电影;而《狼》片则已然走出了这一“保护自然”的环境主义旨趣,迈向了“我是自然”的生态主义。
参考文献:
[1] 陈力君. 中国生态电影意识的觉醒与匮乏[J].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6(1): 130-134.
[2] 徐兆寿. 生态电影的崛起[J]. 文艺争鸣, 2010(3): 18-21.
[3] 李玫. 从动物的角色功能看当代电影的生态意识[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6(5): 95-98.
[4] 韩浩月. 环保电影不能这样玩[J]. 新产经, 2015(7): 75-76.
[5] 王瑞红. 环保电影传递绿色发展新理念[J]. 环境教育,2016(4): 51-53.
[6] 王莉丽.《可可西里》彰显“生态电影”传播空间[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1): 72-75.
[7] 福柯. 古典时代的疯狂史[M]. 林志明,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527.
[8] 刘青汉. 生态文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7.
[9] 鲁晓鹏. 唐宏峰. 中国生态电影批评之可能[J]. 文艺研究,2010(7): 92-98.
[10] 金田. 国产生态电影创作的困惑与追求[J]. 电影文学,2014(24): 20-21.
[11] 大卫·波德维尔. 电影诗学[M]. 张锦,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36.
[12] 陆川. 体验可可西里[EB/OL]. 央视网东方时空之东方之子,2005-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