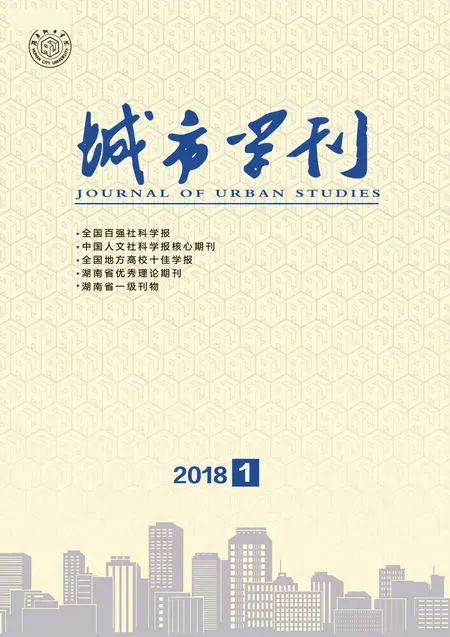人格与审美:孔子美学和庄子美学之比较
颜翔林,傅融睿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15)
孔子美学和庄子美学分别代表着中国古典美学的两个重要派别和不同的思想策略与方法路径。孔子的儒家美学和庄子的道家美学,两者之间既有显著的理论分野也有潜在的逻辑关联。海内外学术界对孔子美学和庄子美学及其关联已有连篇累牍之阐释,依然存有“意义之空白”处。如果说孔子美学是以道德本体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美学,那么,庄子则是以自然本体为基石的怀疑主义美学。两者分别以“君子”与“至人”、“仁者”与“真人”作为审美理想的象征品和道德人格的偶像,而共同的价值标准都是建立“可信”与“可爱”相契合的主体和生活世界,使现实人生和审美创造得以统一并成为可能。因此,构造理想主义的人格是孔子和庄子的共同精神目标,这既是人生哲学的诉求,也是伦理学的崇高期望,更是美学的最终归宿。
一、“至人”与“君子”
孔子是华夏的伦理主义美学奠基人,他强调人格是审美活动的最高目的,理想的主体形式必须符合伦理原则。只有建立完善的道德人格,才使审美活动得以可能。换言之,审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的道德人格。康德提出一个重要命题:“美是道德的象征。”[1]他将美和道德进行密切的逻辑关联。“只有作为道德的存在者的人才是我们承认为世界的目的的。”[2]康德把道德主体作为世界的最后目的和最高目的。“最后的目的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从属于道德律的人。”[2]113显然,康德在道德人格和审美活动之间划了等号。应该说,康德不仅是西方形式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西方伦理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因此,在美学上,孔子和康德有着思想和逻辑的同一性。
庄子和孔子的相同之处,都强调完善的人格在生活世界的美学意义,均认为理想的存在者是构成世界的最高、最终的价值和目的。两位先哲的思想差异在于,庄子仰慕“自然”的人格,认为先验的本性才是最可信和最可爱的人格。因此,庄子推崇“至人”、“神人”、“真人”的人格,认为这些人格才是所有存在者的典范,是生活世界的主体所仿效的对象和标准。庄子更深刻的运思在于:每一个存在者都蕴藏着自然人格,不需要后天的修炼和实践意志的具体躬行,只要自然无为、无所雕饰地敞开本性,就是最理想的和最完善的人格状态,也是最高的美学境界。庄子云: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
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3]
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4]
真实而完善的人格并非来源于后天的教化和实践,而是自然敞开的本性,如果刻意地进行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社会意识形态的雕琢和教育,反而造成自然人格的损毁。显然,在此庄子对于儒家的“仁义”进行了有意识地误读和曲解,持有反讽和批判的态度。但是,从庄子对于“仁义”的存疑和否定的态度中,可以窥到他对于自然本性的深切守护和崇尚,庄子认为如果以“仁义”等道德规范进行后天的教育,反而招致人性被遮蔽,损害人性的本真和本来就完善的人格。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5]
庄子认为,在文明的起始之处,“混芒”状态中的人格是最纯粹美好的,随着历史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格中美好的自然本性却呈现反比例的衰减。显然,庄子对文明和历史进行辩证理性的反思,认为历史的进步并不一定同步地带来精神境界的提升和人格的不断完善。因此,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自然无为的先验人性,而这种先验人性体现在“至人”、“神人”等理想人格的身上。后来的荀子认为:“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6]荀子肯定性情的先验性,但是否定了先验性情的绝对完善和合理:“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7]又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7]显然,荀子持有对自然性情的否定观,他提出的命题是“性本恶”,因此,需要对人的先验本性进行伦理教化。
如果说庄子思想深邃处潜隐着一种伦理主义的美学意识,其伦理主义的内涵,只能称之为自然伦理主义,而非社会实践的伦理主义。然而,庄子对于唯美的和完善的人格追求是其崇高的精神目标之一,它显然蕴藏着伦理主义美学的应有之义。
孔子建立古典主义的“审美伦理学”,或者说是一种“伦理美学”。它们共同的核心和具体内涵之一,就是理想和完美的人格建构。与此相关,理想和完美的人格建构既是美学的最高目标,也是审美活动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它们之间存在着本体与方法、目的与手段的必然逻辑关联。孔子的伦理主义美学的人格规范体现在一些重要的命题之上,其中最集中和最典型的一个命题关涉于“君子”。在《论语》中涉及“君子”共计108处,比“仁”的109处仅少一处。可见“君子”在孔子心目的重要地位。
命题: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8]梁启超:“孔子有个理想的人格,能合这种理想的人,起个名叫做‘君子’。”[9]君子是最高和最根本的人格要求,也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标准。第一,他必须做到文与质的和谐统一,既避免朴实超越文采,也不能文采涵盖朴实,如此则不会沉落于粗俗和轻浮的格调,而获得形式与内容、表象与本体、物质与精神的高度融合。第二,规定君子的人格必须超越功利而追求“义”的道德目标。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第三,要求君子放弃言语上的夸夸其谈而着重于实践行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0]85第四,具体地规定君子之人格的“四项基本原则”。孔子对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1]一是态度谦恭,二是对待君上必须认真负责,三是教养民众应该有恩惠,而役使民众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第五,孔子要求君子博学文化典籍,以礼节约束自己的内心、言语与行为,不要违背基本的伦理原则。“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8]130第六,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关注于精神上的追求,忧患道德问题而不计较贫穷的境况。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12]第七,君子必须保持坦荡光明的人格。“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3]第八,君子应该体现成人之美的善心。“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14]第九,孔子认为君子必须严格地要求自我,而小人则处处苛求别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2]342第十,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有“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2]343的品德。矜持而不狭隘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第十一,孔子认为,在总体上,君子应该体现为“学道”和“爱人”相互依存的道德人格。只有学道才能保证爱人,而爱人是君子内在的心灵诉求,是行为的指针和最高的实践目的。所以,君子是人格上的最高美学境界。
二、“真人”与“仁者”
与“君子”形成密切的逻辑关联,孔子另一重要的人学命题或人格命题是:仁者爱人。而在庄子的审美理想中,完善的人格主要由“真人”等对象担当。“真人”成为庄子美学境界中的人格偶像。因此,“真人”与“仁者”构成庄子和孔子的人格美的对应性概念。庄子多处言及“真人”,表示出极大的敬慕和赞赏: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鼽。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15]
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尚志,圣人贵精。”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16]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也,崔崔乎其不得已也,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广乎其似世也,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17]
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于蚁弃知,于鱼得计,于羊弃意。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若然者,其平也绳,其变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18]
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虽未至于极 ,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19]
“真人”禀赋的人格显然丰富多姿:其一,守望精神和行动的自由。能够“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其二,保持思想的独立和合乎自然法则。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都达到顺应客观规律:“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其三,力求人格上的自然无伪,不假雕饰,不矫情做作,守护“纯素”的心性。其四,表现在具体内容方面:能够神态自若而不受损,似乎不足却不受之于外物,超然不群但不固执,心胸开阔而不浮华。心胸畅快显得欢喜自如,行动好象出于不得不如此,表情如水而心灵充实和谐,德性宽厚令人亲近。精神宽阔如世界博大,境界高远无可宰制,内心沉默而遗忘语言。其五,放弃过分的亲近和疏远,守护内心的德性和谐,节制情绪以适应自然,甚至抛弃如蚂蚁的知觉,如游鱼般地自得其乐,就连羊一般的意念也没有。因此达到以直觉感知自我和世界,超越生死得失的界限。其六,“真人”能够“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如关尹、老聃这样,他们就是古代的博大的“真人”象征。总而言之,“真人”禀赋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自然合律、本真从容等近乎完美的高尚人格。
孔子的伦理主义美学对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是以“仁学”为基本内涵的,而“仁”的范畴在一般形态可以归纳为“仁”、“义”、“礼”三个核心。“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0]显然,“仁”在具体形态又可表现为“恭、宽、信、敏、惠”这些实践性的规范,也可以包括“温、良、恭、俭、让”和“文、行、忠、信”等态度、行为。历史地考察,因为后来孟子补充了“智”的概念,汉代董仲舒增加了“信”要求,最终构成华夏伦理的所谓“五常”。其实,“五常”在《论语》中都经由孔子反复论述和提倡,都属于孔子伦理观念的逻辑范围,上升为理想化的人格建构的核心范畴。孔子将“仁”作为完美人格的核心范畴,作为道德伦理准则的基础性概念。在总体论上,孔子将“仁”界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4]278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伦理美学命题。但是,在具体环节上,孔子对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阐释,援引生活世界的具体现象进行论证。其一,“仁”体现在对于父母的孝道和敬爱兄长。“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1]“孝”为儒家重要的伦理准则,理想的人格应孝敬父母和关爱兄长,这是人生实践意志中具体奉行的道德理念,它须贯彻于生活世界的日常行动。其二,“仁者”应热爱大自然,从中体悟人生的道德伦理意义,保持心灵的宁静以求生命的长久。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8]127其三,达到“仁”的境界,必须自己希望有作为也使别人有作为,自己力图有成就而使别人也有成就。如果能够依照眼前的情况去躬行实践,可以说是获得了实践仁道的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8]134其四,“仁”应该作为内心的责任和目标,必须持以恒久的意志。“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2]其五,“仁者”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注意克服忧虑惆怅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23]其六,孔子认为,“仁者”必须克制自我的语言、意志、欲望和行为,使之符合于礼的规范,一旦达到克己复礼的境地,则天下称许你是仁者。实践仁只能依赖于自身而不能借助于别人。具体的纲领是:不合乎礼的不窥视,不合乎礼的不听闻,不合乎礼的不言说,不合乎礼的不作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14]262其七,仁者外出行事应该如恭敬地对待尊贵宾客,役使民众如承当庄严的祭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强加于别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4]263其八,仁者应该保持语言上的节制和低调而躬行实践,力戒夸夸其谈而行为迟缓。“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所以孔子提倡“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格。其九,仁者必须态度仪容端庄,忠于职守,待人忠诚。“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24]其十,仁者应该具备意志上的勇敢品质。所以孔子认为“仁志,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25]孔子以“仁”的规范建立理想的人格概念,从而培养出生活世界符合美的标准的精神主体。
三、“可信”与“可爱”
一方面,孔子和庄子分别倡导自然与仁爱的人格,建立生存论美学。另一方面,孔子强调主体存在的道德自由,庄子推出主体生存的审美自由,他们共同创建了古典时期的自由主义美学。在目的论意义上,他们都将自由视为生命的最高的善与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阐释目的论,认为:“这个目的就是世上通过自由而成为可能的最高的善”。[2]119如果从目的论意义出发,孔子美学和庄子美学值得关注的另一个内在目的,就是对于人的主体存在的美学规范。假设寻找这种规范的特性和差异的话,那么,借用王国维的“可信”与“可爱”的范畴,可以将庄子美学对于主体的理想人格界定为“可爱”,而把孔子美学对于主体的理想人格表述为“可信”。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其二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26]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写下内心对哲学的困惑,他徘徊于理论的可信与可爱之间,犹如徜徉于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宗教徒,流露出两难的选择和矛盾心态。显然,可信与可爱在逻辑上构成王国维难以消解的精神悖论。其实,王国维的矛盾蕴藏着哲学与美学、理论与实践的普遍性。
如果说在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境域,没有必要让“可信”压倒“可爱”,换言之,可以允许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可信”走向“可爱”。然而,在实践理性的范畴,在人生境界,对于“可信”的坚守就是一个不可放弃的道德律令,也是生命中必须承受的美学准则。唯有可信,才能可爱。前者构成后者必要的逻辑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孔子坚持“信”的伦理原则,将之作为人格最根本的美学标准之一。
《论语》记载,孔子和弟子们讨论了“信”的命题,将其视为人生境界的最重要的德性之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21]5-13显然,“可信”作为儒家的实践理性中极其重要的价值核心之一,它成为君子安身立命的日课和不可缺少的操守。“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27]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倘若没有诚信,不知道如何可能。犹如大车没安装横木的輗,小车没安装横木的軏,是无法行走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3]147“信”作为孔子教育弟子的四项重要内容之一。孔子指出“信”的功效:“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12]334他还认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12]342显然,“信”是作为君子成就自我与事业的人格保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的必要精神条件。
因此,在孔子看来,“可信”是构成主体之人格美的关键因素之一。唯有守护着“可信”的逻辑前提,才使生命的“可爱”价值得以可能。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四卷中讨论“具体的德性”,推崇可信和诚实的道德意义。“有适度品质的人则是诚实的,对于自己,他在语言上、行为上都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虚伪是可谴责的,诚实则是高尚(高贵)的和可称赞的。所以,具有这种适度品质的诚实的人是可称赞的;虚伪的人,尤其是自夸的人,则是可谴责的。”[28]亚里士多德将“诚实”引申为德性的内容之一,将“可信”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准则之一,而贬斥“虚伪”和“自夸”的行为。东西方伦理学的价值准则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而对于主体的“可信”诉求是这种普世性伦理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在生活世界,主体存在除了禀赋纯粹理性的认识能力,还需要实践理性的道德律令,诚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所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于我心中的道德法则。”[29]显然,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主体,必须追求“可信”的德性和品格。
和孔子相同,庄子推崇可信的人格。但和孔子不同的是,庄子认为可信的人格不是后天的教化和实践意志的结果,而来源于先验的自然本性。因此,庄子更心仪建构“可爱”的人格境界。
从生命境界考量,主体只有守护着“可信”的实践理性,才能保证自己的“可爱”得以可能。然而,“可信”作为“可爱”的必要性逻辑前提,却不能担保自己成为“可爱”的全部条件。换言之,主体在具备“可信”的逻辑基础上,还必须经过精神的其它努力,才能获得的“可爱”的美学结果。就生命境界而论,如果说“可信”是一种伦理学的尺度,那么,“可爱”就是一种美学的标准和要求。而可爱的标准和要求,最重要的内涵就是“诗性主体”的存在。诗性主体是以审美活动为中心而将理性主体和实践主体进行综合的主体形式,它是对于本能主体、感性主体、知识主体、消费主体等予以超越与否定的主体形式,它以想象和直觉为感性工具、追求超越性的精神结构。从这个理论意义上,只有达到诗性主体的规定性,才使主体具有“可爱”的内涵,才符合于审美的标准和达到美学的境界。如果说“可信”趋向于一种伦理学意义的内容规定,而“可爱”除了具备伦理学意义的德性内容的要求之外,还需要审美的形式作为保证。换言之,“可爱”必须达到精神内容和美感形式的和谐统一。可爱既需要实践理性的逻辑前提,更需要具有审美能力的诗性主体的生成。
庄子渴望建立建立一种“可爱”的人格境界,依据庄子文本,我们予以这几方面归纳和综合:
其一,逍遥独立的精神气质。它在表层上,是对时间空间的超越,而实质上是寻求自我的独立思想。《逍遥游》、《德充符》、《大宗师》、《养生主》、《秋水》、《达生》等篇目,构想诸多形象或意象,它们作为诗意化符号,洋溢着可爱有趣的气韵,充满浪漫情怀。其二,超越功利欲望和流俗的意识形态,在精神层面上获得以心向道的品质和“超人”的技能。“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庖丁“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30]其三,不渴求名望和爵位,厌倦政治和权力,隐居山林和保全自我。《秋水》篇“钓于濮水”和“惠子相梁”生动地表现脱离政治权力和隐居山水的心态。其四,“可爱”之人,应该酷爱大自然和永葆“童心”。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感受游鱼的快乐,争辩心灵与现象的差异、人与鱼、人与人的心灵沟通。“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30]18生动传神表现一个“可爱”的主体所禀赋的沉醉自然、“相忘江湖”的本真童心。其五,“可爱”的人格应闪烁生命的智慧,能够具有打破日常经验的奇崛的想象力。《庄子》文本弥散着“神话思维”的色彩,和孔子不提倡的“怪、力、乱、神”的思维方式有所差异。啮缺、王倪、瞿鹊子、长梧子、南郭子綦、匠石、支离疏、接舆、王骀、申徒嘉、女偊等人物,他们都具备“可爱”的人格。其六,“可爱”之人可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谐。以“心斋”、“坐忘”的方式获得精神超脱。“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苔焉似丧其耦。”[30]6“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31]“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32]达到这一境界的人显然持有“可爱”的要素。其七,放弃矫情和夸饰表演的主体才可能是可爱的主体。“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33]其八,“可爱”的人格不以知识累心,追求内在的心灵自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34]其九,能够超越死亡恐惧的主体是“可爱”的人格。只有少数人可以“不知说生,不知恶死。”[32]38“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35]其十,无论人生境遇如何,保持常乐之心,这是可爱人格的自然显现。“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36]显然,在庄子心目中,孔子是一个可爱的人格形象。
庄子和孔子从哲学、伦理学和美学意义上,从存在论的立场,倡导主体的人格需要可信与可爱的价值肯定。从理想状态上,达到可信和可爱的高度融合和统一,才是最完善的人生境界和美学境界。显然,这需要任何历史语境的主体给予守护,坚持着可信与可爱的情感信仰或信念。这是先哲们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之一。
参考文献:
[1] 康德. 判断力批判: 上卷[M]. 宗白华, 译. 商务印书, 1964:201.
[2] 康德. 判断力批判: 下卷[M]. 韦卓民, 译. 商务印书馆, 1964:111.
[3] 王先谦. 庄子集解·骈拇[M]// 诸子集成: 第3卷. 中华书局,1954: 54-56.
[4] 王先谦. 庄子集解·马蹄[M]// 诸子集成: 第3卷. 中华书局,1954: 57-58.
[5] 王先谦. 庄子集解·缮性[M]// 诸子集成: 第3卷. 中华书局,1954: 98.
[6] 王先谦. 荀子集解·正名[M]// 诸子集成: 第2卷. 中华书局,1954: 284.
[7] 王先谦. 荀子集解·性恶[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290.
[8] 刘宝楠. 论语正义·雍也[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125.
[9] 梁启超. 儒家哲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39.
[10] 刘宝楠. 论语正义·里仁[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82.
[11] 刘宝楠. 论语正义·公治长[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101.
[8] 刘宝楠. 论语正义·雍也[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130.
[12] 刘宝楠. 论语正义·卫灵公[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346.
[13] 刘宝楠. 论语正义·述而[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153.
[14] 刘宝楠. 论语正义·颜渊[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274.
[15] 王先谦. 荀子集解·大宗师[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38.
[16] 王先谦. 荀子集解·刻意[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97.
[17] 王先谦. 荀子集解·大宗师[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38-39.
[18] 王先谦. 荀子集解·徐无鬼[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164.
[19] 王先谦. 荀子集解·天下[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221.
[20] 刘宝楠. 论语正义·阳货[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371.
[21] 刘宝楠. 论语正义·学而[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4.
[22] 刘宝楠. 论语正义·泰伯[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160.
[23] 刘宝楠. 论语正义·子罕[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193.
[24] 刘宝楠. 论语正义·子路[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292.
[25] 刘宝楠. 论语正义·宪问[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301.
[26] 王国维. 自叙二[M]// 王国维论学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496.
[27] 刘宝楠. 论语正义·学而[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5-13.
[28] 刘宝楠. 论语正义·为政[M]// 诸子集成: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37.
[29]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商务印书馆, 2003: 119.
[30]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韩水法, 译. 商务印书馆, 1999:177.
[31] 王先谦. 荀子集解·齐物论[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15-16.
[32] 王先谦. 荀子集解·养生主[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20.
[33] 王先谦. 荀子集解·大宗师[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47.
[34] 王先谦. 荀子集解·德充符[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54: 36.
[35] 王先谦. 荀子集解·至乐[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110.
[36] 王先谦. 荀子集解·秋水[M]// 诸子集成: 第2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