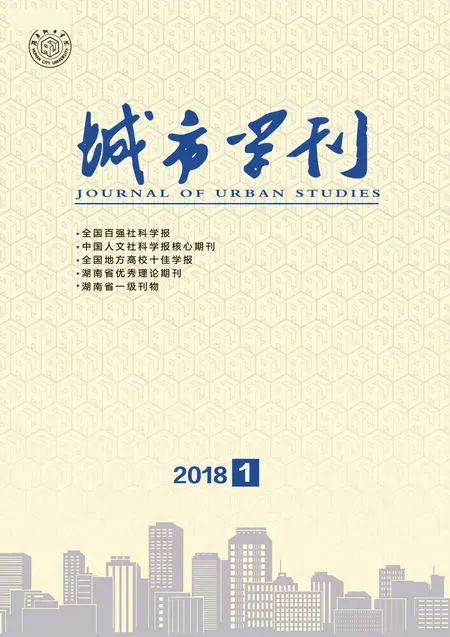共享单车的多维度伦理审视
屈振辉,李秋艳
(1. 湖南女子学院 教育与法学系,长沙 410004;2.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长沙 410132)
近年来共享单车在我国很多城市大量出现,五颜六色的各式共享单车成为城市靓丽风景;有些共享单车品牌还走出国门、被推广到国外,甚至被国外青年评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1]然而事物皆有两面,它给人们带来便利同时也引发不少问题,最常见的就是共享单车乱停或被人为破坏。这种现象固然反映了伦理问题即公众道德问题,有些情节严重者已构成违法甚至达到犯罪程度,但共享单车涉及的伦理问题绝不仅是这一方面,还包括了法律伦理、经济伦理、工程设计伦理以及公共管理伦理、交通伦理等非常多的方面。目前共享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继共享单车以后各种各样的共享产品层出不穷,共享经济的大潮已嘎然而至。共享单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共享产品,我们以它为缩影研究其中存在的各种伦理问题,也是为共享经济未来发展而见微知著、未雨绸缪。
一、公众道德问题与法律伦理问题
共享单车将扫码开锁、GPS定位等互联网科技运用于单车这种传统交通工具以实现分时租赁,解决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创新科技产品。它以便捷、环保、健身等优点吸引了很多用户,也使很多投资者觉得有利可图纷纷投资该领域,因此各种品牌的共享单车大量出现在城市街头。投放量大是不少共享单车品牌制胜的法宝之一,为方便使用者使用它又采取“无桩”管理模式,量大且疏于管理是它被乱停或人为破坏的根源。有学者将上述现象归因于某些人道德素质不高。“一些人为了将单车占为已用甚至已有,将二维码破坏,甚至将单车私藏某处,擅自上锁,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暴露出人性中的道德污点,令人齿寒……共享单车的舒畅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公民个人道德规范的约束。”[2]共享单车在我国陷入道德困境的首要原因在于,“今天一部分中国公民公共道德意识缺乏。”[3]
从辩证角度看,这些观点过于片面。不能将乱停现象全部都归咎于公众道德,共享单车运营商的“道德疏忽”也是成因之一。任何新事物都须与周围环境适应才能发展。人们制造各种产品的最终目的都是供自己使用,因此任何产品都要适应特定的人文或社会环境,而人文或社会环境就包括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平,共享单车运营商显然是高估了国人的道德水平。如前所述,共享单车为方便使用采取“无桩”模式。但当下国人的公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性仍不很高,为图自己方便而乱停共享单车的现象在所难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先出现的公共自行车,因采用有桩管理模式几乎没有乱停现象。“道德习惯的养成,是需要更加长期和反复实践磨炼才能完成的。”[4]但这种养成仅靠人们的“慎独”往往难以实现,有时还需要外力的介入。对共享单车而言“有桩”管理也许是解决之道,即应先实施“有桩”管理规范人们的停放行为,待规范停放的习惯养成后再改为“无桩”管理。但共享单车在出现伊始其运营商就忽略了这点,没有在产品设计和运营管理上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是目前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加剧更深层的原因。
共享单车与公共自行车相比凸显的是乱停现象,然而它与私人单车相比凸显的则是被破坏现象,后一现象严重到一定程度便构成违法甚至犯罪。现在城市地铁口等地方经常可看到这样的景象:不少共享单车被破坏而私人单车则安然无恙。这似乎可从公德与私德及相关问题中获得解释。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仅是我国宪法的规定,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内化为国人的一种公德;后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也被写入到我国宪法中,并随民事权利观的深入人心而内化为一种私德。公共财产由公德维护而私有财产则由私德维护,界线清晰、功能分明。近两年来我国共享单车等共享产品大量出现,人们对它是公共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却认识不清——它实质是私有动产却在公共场所任由公众使用。正是如此某些人公、私道德的底线全都放松了,以致做出了破坏共享单车的不端行为。道德规范“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这就决定了道德规范相对于社会具有滞后性。”[5]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在我国已然兴起,但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却仍然处于真空的状态,共享单车被破坏现象的频发自然也就不稀奇了。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破坏共享单车恶行积累终将构成违法甚至犯罪。目前由共享单车引发的民、刑事案件快速增长,甚至因其特殊性引发民、刑事司法中的疑难。这些疑难主要因道德与法律界线不清所致。如不付费使用已被他人卸掉车锁的共享单车,或将车隐匿在他人难找到的旮旯仅供自己使用等。这些行为最多是不道德,却很难被归入违法范畴,更达不到触及刑律程度。法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与法学交叉、融合的产物,“以法律关系和道德关系的相互交叉、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为基础,研究法现象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一般规律。”[6]道德与法律间的模糊性问题自然是其重要论域。明晰共享单车使用中失德与违法行为间的界线,有助于人们规范自身行为和司法机关正确处理这些行为。
二、经济伦理问题与工程设计伦理问题
共享单车涉及的上述公众道德与法律伦理问题,其主要指向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和其它社会公众,当然其中也包括共享单车运营商。其实共享单车涉及的伦理问题远不止上述这些,它还涉及到经济伦理问题与工程设计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仅指向共享单车运营商。经济伦理研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决策、经济行为的伦理合理性”,[7]论证和评价经济活动的合理与否是其重要功能。共享单车的经济合理性首先表现在商业模式上。它基于互联网技术将需求者与所有者联系起来,以付费方式对社会上的闲置资源进行精确匹配,既实现了生产要素的社会化,又提高了存量资产使用效率,并降低了使用者支出的成本;还节约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
共享单车的经济合理性还表现在其激励措施上。如前所述,有人经常有意将车停在犄角旮旯仅供自己使用,其他人就找不到车使用因而使运营商无法收益,于是“红包车”出现了。细心的人会发现“红包车”都出现在犄角旮旯;有人甚至纳闷骑到它不仅不付费还能获得红包,运营商岂不是亏了?恰好相反,这正是他们的精明之处。共享单车是其运营商用来获取收益的主要资本,它不断被使用者骑行运营商就能不断获得收益;但它如果被置于犄角旮旯而别人无法找到骑行,就等于资本被闲置起来而无法周转更无法收益。因此运营商就将这些共享单车标为“红包车”,用红包让有心人将其骑出来再进入周转并收益。减少闲置资本、加速资本周转可获得更多收益,“红包车”正体现了这条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目前各大共享单车品牌之间的竞争已呈白热化,但有些品牌采用的竞争策略却很难称得上道德。早期的小黄车只要记住了机械密码车锁的密码,就可凭密码不付费地反复打开车锁使用这辆车。很多人认为这是早期小黄车设计中存在的漏洞,但“在谈及机械锁等漏洞时,报道中OFO的一位投资人竟然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它在哪里有问题、有漏洞,但有些漏洞可能是有意设计的。’在解释原因的时候,这位投资人一语道破天机:‘你觉得一个项目的早期传播与挣钱相比,哪个更重要?’”[8]小黄车存在漏洞竟是它抢占市场的竞争策略!然而这种策略显然有悖于公平竞争的道德准则。有人甚至指出,运营商用技术完全可避免共享单车乱停现象,但他们为赢得竞争却对此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共享单车运营商主观上具有放松监管的意图和意愿。如果监管规则更严,则用户极有可能会选择其他品牌的共享单车。”[9]
我国共享单车品牌虽多但在设计构造上仅两类,分别以早期的小黄车和摩拜单车为其典型代表。早期的小黄车采用空心车胎骑行舒服但易爆胎,车锁只要一次获得密码后可反复开锁免费使用;摩拜单车采用实心车胎不易爆胎但骑行不舒服,车锁必须每次都扫码付费后才能自动开锁使用。“设计过程并不单纯是追求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实现技术的功能效率,人类的价值理念通过设计过程内化于技术设计成果之中。”[10]两类不同的设计构造背后蕴藏不同的人性假设:前者将使用者视为爱惜单车且诚信的“好人”,后者将使用者视为不友善、不诚信的“坏人”。换而言之,前者是以性善论为其设计构造的人性假设基础,后者则以性恶论为其设计构造的人性假设基础。现实中早期的小黄车坏损数量远多于摩拜单车,现在小黄车则完全采取了摩拜单车的设计构造,可能是其运营商认为“坏人”设计更适合国情,真是“西风压倒东风”!此外,“坏人”设计构造成本高于“好人”设计构造,也证明道德水准下降致使经济成本提高的铁律。
三、公共管理伦理
共享单车还涉及公共管理伦理与交通伦理问题,它们主要指向市政、交通等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共享单车刚出现时曾经被视为城市文明的象征,它体现了便捷、环保、健康、时尚等城市理念;然而现在共享单车似乎成为了城市文明的疮疤,乱停、被破坏等现象都暴露出人性丑陋的一面。对此社会公众、共享单车运营商都必须负责任,但是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状况的成因有:第一,提供共享单车租赁服务的企业全部是私人厂商,城市的市政部门就错将其视为纯粹的私人产品,而没有意识到共享单车其实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它虽然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等私人产品的属性,但它能满足公众交通需求而具有公共性的一面;它还大量占用作为公共资源的道路和城市空间,但却并没有因此而支付任何其应当支付的费用。共享单车这类由私人厂商所提供的准公共物品,本应由公共管理部门管理然而它们却放权弃责。第二,共享单车确实能为城市带来很多好处,如低碳环保、解决交通拥堵甚至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很多城市政府对其采取“放水养鱼”态度,以致在市政管理上对其种种乱象睁只眼闭只眼,并没有督促其运营商改善产品设计和运营管理。这是公共管理伦理弱化和失范的典型表现之一,它“主要表现在对于自身权力委托者权益的漠视,组织的权力运作不以委托者的权益为依据,对自己应当履行的职责敷衍塞责、玩忽职守,权力的滥用和乱用,情不为民所系、权不为民所用、利不为民所谋。”[11]
共享单车是由私人厂商提供的准公共物品,市政等公共管理部门不能采用传统的方式管理。事实证明,市政等公共部门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是失效的,因此必须引入公共治理。公共治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发展的趋势,它“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共同作用,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协同与合作……强调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主张通过谈判与协商、互助与合作、分权与授权、自律与自治等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12]这就要求“政府、公司和个体等多方力量理应‘共享单车’管理,政府在加强与企业沟通与对话的同时,还应引导市民依法、文明、有序使用,共促新模式、新业态,实现出行结构调整的共赢。”[13]各方各司其职就能治理好共享单车现存的问题。
四、共享伦理
共享单车作为先锋引爆了共享经济汹涌的大潮,在共享单车之后共享雨伞等共享产品纷至沓来,使人应接不暇,大有“乱花欲溅迷人眼”之势。但这些共享产品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道德尴尬,如共享雨伞登陆长沙几天就被某些人据为己有。[15]这不免引发人们关于共享经济与道德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社会经济关系决定道德,但“道德的发展变化,在总体上,往往落后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16]因此共享经济大潮虽然已经来临,但人们的道德水准并未立即跟上,这与伦理学的上述原理并不相悖;与此同时,该理论也认为道德对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反作用,“某种道德一经形成,就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作用于产生它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整个过程。”[16]70因此面对已经到来的共享经济大潮,必须尽快构建与之相应的道德。
深入思考共享单车所遭遇的问题,可以凝练出共享伦理的基本要旨。其一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共享”的反义词就是“私享”,两者分别是使用和所有的代名词。面对共享产品,使用者应克制“所有”它的私欲,以付费为前提有偿地使“用”它。其二是“尊重私产,共享共用”。共享产品虽然可以为公众所共享,但公众心中须明确其私产的性质;对其要像对自己的财产般爱护它,它才能够为“你用我用大家用”。其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想用共享产品时碰上无法使用的,每个使用者都不想遇到这种状况。要想避免这种状况就要人人爱惜,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共享伦理的要旨当然还不仅于此。
我国的共享单车现在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例如摩拜单车。据网媒报道摩拜单车在英国,同样遇到被扔进河里、破坏车锁、私藏家中等现象。还有报道称在法国,连本土的公共自行车都不能幸免。“最初在巴黎投放的1万辆公共自行车Velib(巴黎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中,80%被毁坏或偷窃,它们中的许多被丢弃到塞纳河中,甚至被走私至海外。”[17]有人将共享单车戏称为是“国民素质照妖镜”;而在我们看来,不如说是“外星人对地球人的道德试验”贴切——“外国的月亮也并不比中国圆”。不过它确实折射出了我国很多现实的伦理问题。
参考文献:
[1] 范荣.“新四大发明”标注中国创新窗口[N]. 北京日报,2017-05-12(03).
[2] 成言. 让公德成就善行——关于共享单车的道德思考[J]. 环境, 2017(2): 3.
[3] 李芸. 共享单车陷入道德困境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J]. 科技经济导刊, 2017(11): 266.
[4] 宋惠昌.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第二版[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225.
[5] 李建华. 道德的社会心理维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 109.
[6] 李建华, 曹刚. 法律伦理学[M].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2-3.
[7] 周中之, 高惠珠. 经济伦理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
[8] 肖罗. 共享单车要有一把无法“占便宜”的锁[N]. 光明日报,2017-02-27(02).
[9] 谭袁. 共享单车“底线竞争”问题探究及防治[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7(3): 36-40.
[10] 王以梁, 秦雷雷. 技术设计伦理实践的内在路径探析[J]. 道德与文明, 2016(4): 133-137.
[11] 周晓红. 公共管理学概论: 第2版[M].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9: 309.
[12] 党秀云. 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4: 47.
[13] 黄凤娟. 共享单车便利性背后的道德危机[J]. 人民公交,2016(12): 74.
[14] 陆礼. 现代交通的伦理追问[J]. 哲学动态, 2007(3): 42-46.
[15] 董怀国. 共享雨伞趔趄了一下,但不会跌倒[N]. 长沙晚报,2017-06-21(11).
[16] 罗国杰, 马博宣, 余进. 伦理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66.
[17] 何家康. 共享单车在国外[N]. 文汇报, 2017-09-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