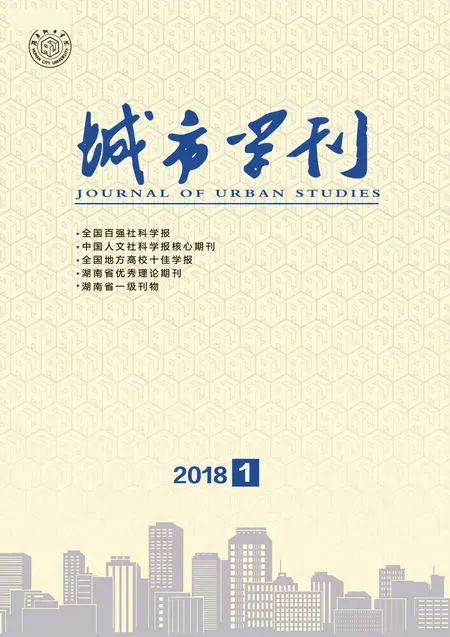关于骊靬历史的动态考察
唐相龙,曹 雪
(兰州交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兰州 730070)
一、骊靬缘起
骊靬隶属于甘肃省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中段,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小镇,早在《汉书·地理传》中记载张掖郡下有骊靬县,且在《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张骞传》等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历朝变迁、古往今来,骊靬随岁月侵蚀,逐渐失去昔日繁华的景象。
关注骊靬历史缘起,兰州大学葛艳玲、刘继华认为,1943年,德效骞发表的《罗马人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中提到“骊靬县是为罗马战俘而设”,并“首次提出罗马战俘被安置在永昌的时间”“应该是在1943年而不是1957年”。[1]刘继华先生针对德效骞在1940年至1957年发表的文章一一进行了解说,同时将其研究得出的场景与《汉书》表现出的场景进行对比。[2]
德效骞引出这个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之后,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将其推向高潮。他与兰州大学的陈正义先生、苏联专家瓦谢尼金先生、西北民族大学的关意权先生经过考察研究,最终得出结论:“罗马犁眩人到中国,至多是几个,罗马人之以数千的群体归化于中国,则始于西汉王朝元成之间”。[3]
随后国内外的媒体争相报道了此事,新闻铺天盖地而来。同时学术界的争论和异议也越来越多。不同专业、方向的学者试图找到更多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至此,骊靬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寨变成各界争相报道的争论焦点。
二、县名由来及设置年代检论
(一)县名由来
德效骞对自己观点的解释中称:“古代中国把这座城命名为骊靬,这个名字是中国人表示罗马和罗马帝国的”,[4]并认为这是作为论据证明骊靬是安置罗马战俘的地方,引起很多学者的讨论。
刘光华曾就“骊”的得名罗列出了学术界存在的7种观点:1)华丽之皮说;2)深黑色之皮说;3)地理形势说;4)骊山之异译说;5)祁连之异译说;6)向往与犁交往说;7)安置犁国人(如随使团及商人来华者、犁幻人和罗马降卒等三方面的人)说。总结出这七点,对其一一否认后又提出了匈奴犁汗部之说,认为“司马光笔下的黎轩与大秦无关,骊靬设县也与大秦攀不上亲,所谓骊靬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云云,显然是无根据的”,并提出了骊靬命名的原因是“与匈奴犁汗部有关”。[5]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中,汪受宽是其中之一。他对已有的观点做了简要列举,并最终认同刘光华先生的观点,称“骊靬县名来源于匈奴犁汗王说当为确论”。[6]莫任南为此却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犁眩人来华献计,取朝廷‘威德遍于四海’”。[7]在探究过程中张绪山也认同了莫任南的观点,认为“汉朝廷在张掖郡置骊县,很有可能是以此炫耀于来往于商道的西方商人,传达与该国交往的愿望,以造成汉廷‘威德遍于四海’的印象,取得西域各国‘重九译,致殊俗’的效果”。[8]郗百施认为“公元前30年以前大秦国不能称之为犁靬,……所以永昌境内汗县骊靬,与‘大秦国一号犁靬’的犁靬无关,也不是什么安置罗马战俘城”。[9]更有尖锐的观点,指出“士兵被俘之时,罗马还不能‘号’称犁靬”。[10]
在批判骊靬的命名与罗马战俘有关的同时,认同声也络绎不绝。代表人物有赵向东、姜青青。他们分别在自己文章中提到“‘骊’就是罗马军团的意思,它是一个带有军事色彩的词语,或者说,它作为中国一个县名,证明中国在西汉时期确确实实与罗马帝国发生了军事冲突”。[11]赵向东不但认同骊靬命名与罗马战俘有关,还认为“骊靬”是由“亚历山大”音译过来,而“亚历山大”是指以罗马为都城的整个罗马帝国。[12]张维华对各个古籍和相关文献进行分解分析,最终虽未得出自己结论,但“兹采众说,重加考核,大抵仍以服虔、师古之说,似为近于事实,虽其间亦有若干不可解决之问题,然终较他说为长”。[13]
(二)地域划分
相对骊靬的命名,大多学者对于骊靬的地域划分关注甚少,仅在少量文献中提到。
李并成在对古籍阅读和实地调勘之后,认为骊靬在“焦家庄乡杏树村南的南故城”,拿实地调研的信息和古籍中描述的项比对,最终得出了结论。[14]在王君的《骊靬钩沉》中,他对《辞海》《汉书》研究得出:“西汉在永昌县西置番和县,在今永昌县南设置骊靬县”,也同样认为骊靬城旧址大概方位应在永昌南侧。[15]同样认为骊靬旧址在永昌城南的还有曹家骧。[16]
谢继忠的《西汉张掖郡治(角乐)得考辨》中虽在说其他论据,但是在其中也透露出张掖在唐代和汉代的设县范围不同,发生过变化。也可从侧面证实,骊靬设县范围不是如今我们看到的者来寨,可能设置初期在永昌故城南侧。[17]而师永刚在《古罗马战俘消失之谜》中首先大胆猜测“骊靳城废弃以后,历代又在此废墟上重建城池,因此骊轩古城有可能深藏地下,成为城下之城”,而后因为考古发现,又确认遗址在永昌县杏树庄和河滩村。[18]
(三)设置年代
1957年德效骞在《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中提到,陈汤一共虏获罗马兵145名,汉朝廷在河西设县安置这批人,时间确定在公元前79年至公元5年之间,这也是他在论文中提到的重要论据。之后哈里斯来华与国内学者研究,关意权和宋政厚都认同德效骞的观点,“骊靬城最早在中国西汉版图上出现是公元前20年”。[3]
湖南师范大学莫任南列举了大量文献古籍,对德效骞、徐松、王先谦等人的观点做了逐一比较,认为:“按张掖置郡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王莽废西汉,建立国号叫新的王氏王朝,在初始元年即公元8年。骊靬县的设置应在公元前111年和公元8年之间的某一年,具体年代则无法确指”。[7]
刘光华则认为骊靬的设立时间约在元凤三年即公元前78年至甘露元年即公元前53年之间,不会晚于陈汤败于单于的公元前36年,在张掖郡下设立骊靬县聊以安置俘获的犁汉人。[10]刘光华根据出土于金关的简书上的记载,认为“骊靬建县的下限是在公元前54年以前,它即早于建昭三年,也早于卡莱尔战役”。[5]据汉简的出土总结提及“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出现骊靬的地名”,说明至少在公元前60年,骊靬就已设县。[19]而宋国荣则认为:汉简所说是骊靬苑而并非骊靬县,认为这两者是不同事物,认为骊靬县设置应迟于骊靬苑,也就是说晚于公元前60年。[20]张绪山在反驳部分新闻报道过程中,指出“骊靬城的建立不可能推前到公元前9世纪”,同时将时间间隔缩短到十年。“许慎《说文解字》下曰:‘武威有丽县’。‘丽’同‘骊’,如此,则骊靬置县应比新发现的汉简所能证明的年代更早,当在元狩二年(前121年)之后的十年中”。[8]王萌鲜对其他学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得出骊靬的建立时间在“公元前48年和公元前40年之间,或者说在公元前45年左右”。[21]
如我们所知,河西从西到东先设有酒泉和武威二郡,而后设有敦煌和张掖两郡,骊靬先隶属于武威郡之后又归张掖郡管辖,大概确定设县时间应在张掖郡之前。2000年,兰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汪受宽根据骊靬设置年代指出:“骊靬县当设于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河西设武威郡后不久,县之得名乃因其地原为匈奴犁汗王牧地,后讹写为骊靬”。[6]
各家众说纷纭,对于设县时间都提出自己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抛开是否与罗马战俘有无关系,设置骊靬的时间应在陈汤战败郅支单于(公元前36年)之前。
三、学术界的争议
(一)骊靬即是安置罗马战俘之城
早期德效骞提出观点之后,国际上先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骊靬和消失的罗马军团有直接关系这样的研究成果影响力慢慢扩大,有不少学者赞同了他的观点。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吸收了德效骞的观点,认为这些罗马士兵作为纽带,使汉王朝和古罗马的文化得到零星的交流。[14]冯卓慧对骊靬与罗马战俘的关系做出分析,确定骊靬就是为安置罗马战俘而建,同时认为“中国与罗马两大文明古国的交往史应该提前了两百年以上”。[22]王宗维提出“骊靬人定居于河西……说明西汉时汉代已经和罗马东部辖境的骊靬人有着往来”。[23]常征对骊靬设县原因进行的阐述中提出:罗马人归化者甚多,故汉王朝专设骊靬县来领护之。……与陈汤之灭郅支是不相干的。骊靬县的确是为罗马人而设置,但并不认同德效骞的观点,郅支城降服的罗马人其实很少,并不能形成稳定的民族群体,不久便会同化于诸国居民中。[24]
王萌鲜和宋国荣认为:“河西走廊曾经有过一座罗马城,这座罗马城是为降人而设;因远征安息而流亡的古罗马军人确实参与了公元前36年匈奴保卫郅支城的战斗”。[25]王伟也认同了骊靬是为安置罗马战俘而设,同时大胆推测:“这座城池和其他西域古城一样,由于自然条件的变迁而逐渐没落消失,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也就随之分散消失了”。[26]倪方六认为“当年这支罗马军队并没有消失,而是流落在了中国,在河西走廊上、今甘肃金昌市辖的永昌县境内定居下来,具体说就是永昌县者来寨一带”。[27]
以上观点均认为骊靬设县是为了安置罗马战俘,但是对于罗马战俘的来源有些许分歧:常征认为罗马战俘不是郅支城降服的战俘,而很多学者如王萌鲜等人则认为是郅支城降服的战俘。[19]
(二)骊靬与罗马战俘无关
在众多学者赞同的同时,质疑声渐渐响起。1958年何四维(A.F.P.Hulsewé,1910-1993)认为这一结论想象力太丰富,需要更多史实证明;1962年,美国人类学家肯曼(Schuyler Cammann,1912-1991)也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臆想,没有证据支撑。在华人界较早提出质疑声的代表人物是余英时,1967年曾发表书评《评德效骞〈早期中国的罗马城〉》,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同样认为这样论断还需要考古发掘来进一步证实。[28]
在中国较早发声表示异议的,还有台湾学者杨希枚,他不赞成骊靬县因罗马军团而设立的说法,认为《汉书》旧注中关于骊靬县的需要重新考证。[29]
刘光华和谢玉杰也都对德效骞提出的诸多论据提出自己的意见,在对考古发掘事实一一列举后,陈述出有矛盾或者疑问的地方。例如军事防御上的鱼鳞阵,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已有类似队形,并比罗马更早,正式名称为“鱼丽阵”。文章观点鲜明地指出:“汉武帝时的骊靬与大秦无关”、“即使证明了‘夹门鱼鳞阵’的百余名士兵是罗马籍,也证明不了骊靬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之城”、“新发现的‘部分珍贵文物’什么也证明不了”、“河西居民不乏印欧人种”等,都认为罗马战俘是骊靬置县原因之说有待考证。[10]
较早提出批判的还有湖南师范大学莫任南教授,1991年在对德效骞的论据进行一一论述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大汉之所以取骊靬为县名是“因犁靬眩人来华献技,取朝廷‘威德遍于四海’”。[7]刘光华认为“犁靬人寄居河西说、安置拉起幻人说等,则属推论,可备一说;而安置罗马降卒说,却有待商榷”。[5]
汪受宽发表了多篇文章,明确表明自己观点:“突围罗马军团之事是张冠李戴”、“郅支战法和城建状况不必罗马军人参与”、“骊靬和揭掳之名不能证明县为罗马降人所设”,同时尖锐地指出:从学术假说到伪史的过程,应该尽早结束。[30-32]
郭晔昊也从史料、DNA等方面不认同骊靬与罗马战俘的关系。[33]1997年,刑义田根据金关、悬泉置汉简上的资料,认为“罗马人建骊靬城是一段古今中外学者共同制造的历史”。何立波则立足于国内外古籍,有别于之前只是对比、查找国内史料,提出骊靬人并不是罗马人,而是匈奴人的观点。[34]
在支持和反对的争议声中,也有很多观点保持中立态度。顾柄枢在对支持和反对的观点一一列举之后,最终希望“罗马军团与骊靬城这一千古谜案早日被解开”。[35]原本承认自己是罗马人的当地居民宋国荣也认为应该称自己为骊靬人,骊靬与罗马人的关系需要继续考究,同时认为如若没有联系,当地出现很多像他这样外貌的人是因为“可能和当时县志记载存在的、后来消失的民族——‘黄毛番子’有关”。[36]曾江也认为骊靬研究需要继续探索和发现。[37]
四、科学的实证
(一)生物遗传学视角
对骊靬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面研究逐渐深入的同时,由于各种观念的束缚和学者们主观意向的偏颇,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观点都是无法得到直接客观证据证实。人们需要更多的客观直接的论据来支撑各自的观点。所以很多生物学家将目光转向另一个肉眼就能看见的差异上,那就是当地人的体貌特征。这显而易见的证据,通过科学进一步解释,希望能在人体基因上找到历史遗存下来的线索。
曾任永昌县委书记的贾笑天认为:“骊靬人在基因上与西亚人关系紧密。这一基因上的同质性可以解释为:要么两种人来自同一起源,要么是两群体间大规模的基因流动,也有可能是上述的两种现象都有”。他还提到“罗马军团的主要力量是由亚洲人组成,所以罗马人和骊靬人可能没有共同的祖先,但是两者却有紧密的联系。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商业和文化的不断相互渗透,之间基因也会随之交流”。[38]
马国荣对骊靬人的血液样本进行抽取检验,选取了87位具有特异体貌特征的样本进行实验,得出结论:“在整个骊靬个体中出现了个起源于中亚人群中并且在欧洲人中也广泛分布的单倍型……整个骊靬人中总共有约3.4%的个体的单倍型频率是来源于欧洲或者中亚人所特有的单倍型。尽管在骊靬人中有的单倍型是属于欧洲人的,但是从主成分分析图上可以明显的看出骊靬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很远的,而与中国汉族的亲缘关系比较近。尽管从地域上来看,回族、东乡族和撒拉族之间很近。但是主成分分析显示,他们与中亚人的单倍型类型更加接近,而不是中国汉族”。[39]而这个分析结果与历史记载和其它的报道是相一致的,这也说明我们对骊靬人起源的分析方法是科学、公正和可靠的。总之,以上结果分析也倾向于支持“骊靬人是中国汉族人种的一个亚种而不是古罗马军团的后裔的论断”。
2004年兰州大学周瑞霞从父系遗传的角度层层分析、步步推进,也是通过对87个样本进行科学分析对比,实验结果表明骊靬人和中国汉民族人群有较近的遗传关系,但和中亚、西欧亚人对比遗传关系较远。文中还利用假设法,列举出有可能是骊靬人的祖先的人群,包括蒙古族和汉族。但研究表明,还是汉民族对其基因库的影响较大,高达70%,蒙古族对其影响较小。最终,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骊靬父系遗传变异的研究结果,不支持罗马军团起源说。当前的骊靬人更具一个汉民族亚人群的特征”。[40]
郭晔昊结合周瑞霞和马国荣的实验数据认为“基因特征不需要舍近求远牵强附会到罗马人身上”,认为河西走廊周边有很多欧洲人血统,不一定是罗马人的血统,更不应拿这一论据证明子虚乌有的结论。[33]
虽然现代科学实证证明骊靬人与罗马人在DNA上没有直接联系,但贾笑天在《关于骊靬人起源的DNA鉴定》中也很明确表示,“其中有可能是试验人员或者是样本采集过程中出现差错所致”,同时他认为“就如多维度分析中所反映,骊靬人在基因上与西亚人关系密切”,同时“长时间的地理分离也削弱了基因同源的影响”。[38]
(二)体质人类学视角
视角转向当地人,他们的体貌特征异于汉人,他们身体强壮、毛发较汉民族人群较浅,肤白,有较少一部分人眼珠呈灰蓝色。建国之后,从各方迁入了不少居民,现存特异体貌特征的人已经不多,但是他们的后代还是可以一眼识别。除此之外,其他生活习俗等都与当地人没有差别。
多篇文章中都提及对当地人外貌的描述,例如闫晓冬的《骊靬城的再现—现代异域文化旅游中的戏剧效应》、宋政厚的《走访河西走廊罗马人遗址》、刘继华的《骊靬文化内涵刍议》、师永刚的《古罗马战俘消失之谜》、杜琛的《中国的古罗马军团后裔疑似者》等都有关于当地人异于其他人外貌特征的描述,认为这与骊靬人有关。
但是经过时间的冲刷,体貌特征在当地人脸上逐渐淡化,有些学者认为河西走廊少数民族众多,这些外貌体征已经不能说明骊靬人与罗马人有直接关系。
(三)考古学视角
从考古学角度分析,丁永琴总结发现“70年代,由于土地贫瘠,当地农民从两米多高的城墙上取土,用炸药炸开后,发现很多钱币,但由于缺乏保护意识,这些钱币都成为孩子们的玩具或是变卖,无从考证。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发掘到了数十件文物,并发现一处西汉墓地,发现不同于汉族骨骼的遗骸。2003年,考古专家在永昌县西水泉堡焉支山附近发现西汉古墓群,共清理出99座,出土文物300余件,骸骨上百具,这些遗骸有一特点是身长较汉族人普遍较长。[38]
对此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汪受宽总结出了“遗址遗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者来寨的古城遗址;二是该寨出土的铁锅、铁铲、铁鼎、瓷壶等;三是临近杏花村的村名挖出一根一丈多长的圆木……没有证明城墙建筑年代的证据,又怎么证明这是西汉骊靬城呢?”[33]同时,刘光华也明确提出“新发现的‘部分珍贵文物’什么也证明不了”。[10]
五、骊靬文化及其保护开发
(一)骊靬文化的包容性
骊靬文化地处丝绸之路,在各位学者不断争议过程中,它的内涵也不断升华。刘继华根据赵向东在《骊靬文化之历史钩沉及再认识》中的观点,总结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骊靬文化体现了文明多样性融合,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河西走廊的活化石,也是中欧文明交汇的活化石”。第二种观点认为:“骊靬文化是连接紧密的亚欧板块的历史激荡出来的,反映古代东西方两种高度文明之间的军事交流与碰撞,反映出古代中国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宽仁,说明历史事件所造成的东西方之间的血缘融合与印证”。[41]
这两种观点都体现了骊靬文化的包容性,但两者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种观点更多强调了文化多样性融合。赵向东对血缘产生、文化包容、军事碰撞等各方面进行了阐述,总结道:“它代表着一种中华文明极大的包容性和同化性,跨越广阔地域的‘融合’之美”。[12]
也有其他学者提出:骊靬文化不止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还与佛教文化、地域文化相融合。认为“骊靬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古罗马文明形成了‘中华文化、古罗马文化、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地方文化”。[23]东方文化与罗马文化相融合、佛教文化增添异彩、地域文化助力发展。这些学者对骊靬文化的包容性都表示了肯定。
(二)骊靬文化艺术化
相对于史学界的严谨和苛求真相的态度,文艺界则更多的充满了浪漫气息,产生出的作品也就更加轻松愉悦。这些作品包罗万象,利用骊靬文化的背景,创作出涵盖了影视、舞台剧、音乐、纪录片、诗歌、小说等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
其中影视、舞台剧、纪录片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消失的罗马军团:千年的历史回响》《罗西、莫妮卡之骊靬情》《天将雄师》《丝绸古道城池之神秘骊靬》等。例如《天将雄师》就是李仁港编剧并执导的一部古装动作电影,主要故事情节以骊靬产生为时代背景,讲述保护丝绸之路和平的故事,由成龙、约翰·库萨克、阿德里安·布洛迪等人主演,影片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讲述了保护丝绸之路和平的故事。
文学类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骊靬探丛》、《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骊靬文化”国际旅游研讨会论文集》等。其中不乏有优秀名人创作的作品,他们以骊靬文化为主脉,贯穿于各类艺术作品中,将这段传奇历史艺术化、感性化,体现出其诱人的一面,以吸引人们的目光。以此也可以看出神秘的骊靬文化确实是很多人向往和追随的艺术方向。
(三)骊靬旅游开发
金昌市基于骊靬文化,大力发展了主题旅游产业,先后修建骊靬怀古和骊靬亭。在2011年开建骊靬古城,这一举措也引起城市规划、遗产保护、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学者研究和探讨。[38]
骊靬古城原址遗存很少,只有两米余高的土城墙,复建古城在黄毛寺的原址上建造,全面打造全国第一个异域风情的佛教圣地,希望可以给游客一种身临罗马城的景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在骊靬古城建设多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主要建筑屹立其中,只有建筑细部采用了罗马建筑样式。
这样的骊靬古城复建遭到相关学者的批判,尹卫国认为:复建古城应该算清楚“土地账”和“经济账”;“复建的古城再宏伟、漂亮,充其量是一个人造景观,没有多少文化含量,许多地方人造景观因无游人关门打烊早有前车之鉴”;“古城复建有无必要,不能由地方自说自话,各行其是,这样的复建古城应该及时刹车”。[42]
从旅游业发展角度,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徐兆寿经过对金昌现有旅游资源和发展情况详细分析之后,分别从定位和推广入手,将骊靬作为旅游拳头产业,分析逐步需要完善的工作。[43]西北师大的把多勋从一二三产业入手,分析如何利用骊靬文化做好旅游产业。[44]赵玉琴则根据现实情况认为金昌旅游资源不足,只靠骊靬为拳头产业动力不足,提出与阿拉善右旗协同发展的必要性。[45]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去骊靬古城的大部分游客都会怀着好奇的心理,去寻求一种异于其他景区的体验,同时借着学术界的争论满足内心的求知欲。而只有极少数的游客是抱着学术研究和探讨骊靬古城由来的目的到此,所以这样的旅游项目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同时在永昌县,也已经有了很多其他景点,例如圣容寺、亥母寺、北海子等旅游景点,这样金山寺作为本体有佛教发扬的作用、对外还有骊靬异域风情的传说支撑。这样内外融合,作为能带动周边小范围发展的经济引擎,也是有可行之处的。[46]
从骊靬话题的缘起开始,分别从历史学、地理学、学术争议、考古学、科学论证、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综合论述了骊靬历史的研究进展,各部分的考察研究全面综合了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和可靠论据,发现关于骊靬历史研究仍处于不断的完善和深化之中,其众多神秘面纱也将被逐渐揭开。总之,对于骊靬的研究无论是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生物学、考古学,还是其他学科,都应像胡适先生说的那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立足历史、严谨求实、有理有据、避免孤证,要对骊靬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分析,不断充实关于骊靬相关研究的历史信息,不断提升关于骊靬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 葛艳玲, 刘继华. 汉学家德效骞与早期中罗关系研究[J]. 甘肃社会科学, 2012(3): 99-102.
[2] 刘继华. 汉学家德效骞的罗马军团来华研究[M]//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4: 53.
[3] 宋政厚. 走访河西走廊罗马人遗址[J]. 新闻爱好者, 1999:8-10.
[4] 德效骞. 古代中国一座罗马人的城市[J]. 屈直敏, 译. 敦煌学辑刊, 2001(2): 102-107.
[5] 刘光华. 西汉骊靬县与犁靬国无关[J]. 丝绸之路, 1994(5):21-23.
[6] 汪受宽. 骊靬县名由来与设置年代检论[J]. 敦煌学辑刊,2000(1): 114-120.
[7] 莫任南. 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M]// 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论丛: 第3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231-238.
[8] 张绪山.“中国境内罗马战俘城”问题检评[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2(3): 10-16.
[9] 郗百施. 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0(4): 158-160.
[10] 刘光华, 谢玉杰. 骊靬是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商榷[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 1999(2): 3-17 .
[11] 姜青青.“骊靬”意为罗马军团[J]. 丝绸之路, 1998(6): 52.
[12] 赵向东. 骊靬文化之历史钩沉及再认识[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4): 89-94.
[13] 张维华. 汉张掖郡骊靬县得名之由来及犁轩眩人来华之经过[M]// 汉史论集.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8-10.
[14] 李并成. 汉张掖郡昭武、骊靬二县城址考[J]. 丝绸之路,1993(1): 63-65.
[15] 王君. 骊靬钩沉[J]. 档案, 1999(4): 47-48.
[16] 曹家骧. 何处骊靬城?[J]. 中国经贸, 1997(11): 74-75.
[17] 谢继忠, 党养性, 门晓琴. 西汉张掖郡治(角乐)得考辨[J].河西学院学报, 1990(2): 26-28.
[18] 师永刚.“古罗马战俘”消失之谜[J]. 民族大家庭, 1994(C1):80-81.
[19] 刑义田. 从金关、悬泉置汉简和罗马史料再探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M]// 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49-72.
[20] 宋国荣, 徐蓉蓉. 汉代骊靬故县是否为骊靬降人而置[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4): 95-98.
[21] 王萌鲜. 王萌鲜说骊靬[M]//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研究,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4: 27-41.
[22] 冯卓慧. 我国甘肃永昌县发现古罗马人后裔[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4: 102-104.
[23] 王宗维. 汉朝西域路的开辟和骊靬人来华[J]. 西北历史资料, 1985(1): 1-11.
[24] 常征. 中西关系史上失记的一桩大事数千罗马兵归化中国[J]. 北京社会科学, 1992(1): 39-51.
[25] 王萌鲜, 宋国荣. 古罗马人在中国河西的来龙去脉[N]. 金昌日报, 2005-11-22(04).
[26] 王伟. 揭开千古之谜——“骊靬”城的来历[J]. 历史学习,1990(3): 32-33.
[27] 倪方六. 古罗马军团在中国?[J]. 中国青年, 2011(20): 44-45.
[28] 余英时. 汉代贸易与扩张[M]. 何俊, 邬文玲, 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5: 25-26.
[29] 杨希枚, 评德效赛. 古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M]// 先秦文化史论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870-902.
[30] 汪受宽. 骊靬梦断——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辨识[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 56-60.
[31] 汪受宽. 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案的终结[J]. 西北民族研究,2013(1): 16-24.
[32] 汪受宽. 驳古罗马军团安置骊靬城说[J]. 甘肃社会科学,1999(6): 34-38.
[33] 郭晔昊. 东西两段传奇生硬拼接“罗马兵团在中国”子虚乌有[J]. 国家人文历史, 2015: 32-35.
[34] 何立波. 中国骊靬古城真与“罗马战俘”有关吗?[J]. 河北学刊, 2004(6): 89-94.
[35] 顾柄枢. 失踪的古罗马军团与找不见的骊靬城[J]. 文史杂志, 1995(1): 16-18.
[36]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宋国荣否认自己是罗马人后裔[J]. 世界史: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1999(9): 125.
[37] 曾江. 骊靬仍然神秘并充满魅力[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30(04).
[38] 丁永琴.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4: 83-96.
[39] 马国荣. 中国西北骊靬人起源的线粒体遗传多态性研究[D].兰州: 兰州大学, 2009: 4-5.
[40] 周瑞霞. 中国甘肃永昌骊靬人的父系遗传多态性研究[D].兰州: 兰州大学, 2007: 47.
[41] 刘继华. 骊靬文化内涵刍议[J]. 丝绸之路, 2013(24):21-22.
[42] 尹卫国. 复建古城该刹车[N]. 中国文化报, 2011-6-10(10)
[43] 徐兆寿. 金昌市旅游资源分析、定位与推广[M]//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研究,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4: 126-130.
[44] 把多勋. 金昌市区域旅游协作区的运行特征和战略定位[M]//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研究,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4:118-125.
[45] 赵玉琴. 金昌市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旅游业协作发展研究[M]// 骊靬文化与丝绸之研究,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4:131-138.
[46] 闫晓冬. 骊靬城的再现—现代异域文化旅游中的戏剧效应[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