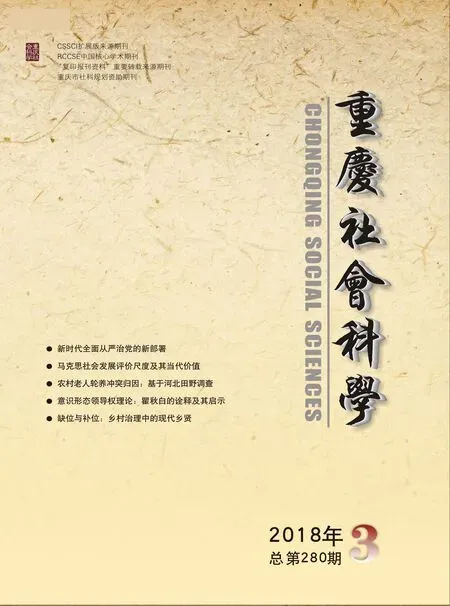《五服年月敕》与天圣《丧葬令》所附《丧服年月》关系考
张崇依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五服年月敕》颁布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是北宋关于五服制度最为重要的敕令,其影响延及南宋初年。《宋史·艺文志》题撰者为刘筠,实际编纂者应为孙奭。其书久佚,条目散见于《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司马光《书仪》、杨杰《无为集》《朱子语类》中。1999年明抄本宋代《天圣令》的公布引发学界广泛讨论。其中关于《丧葬令》的研讨使得《五服年月敕》重新进入学者视野。吴丽娱首先将《天圣令·丧葬令》所附《丧服年月》复原为唐令的《服纪》。[1]皮庆生随后反驳其说,他指出,《丧服年月》附于《丧葬令》之后是天圣修令者的创举,而非照搬唐令的旧制。而《丧服年月》正是《五服年月敕》的节略版。[2]皮氏论证五服入令的过程极为精到,殆无可疑。然而,有关《五服年月敕》与《丧葬令》所附《丧服年月》的关系,似仍有阐发余地。这里试图厘清两者关系,重新定义《丧服年月》的性质,探讨其写作目的及定名缘由,以期促进宋代五服制度、令敕关系的研究。
前揭皮庆生《唐宋时期五服制度入令过程试探》中认为,《丧服年月》为《五服年月敕》的节略版。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否真是如此?我们应当从内容的删减、形式的简省、文字的改动三方面进行考察。
一、内容的删减
在探讨本问题前,请先看两段关键性史料:
《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一四:
天圣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读学士孙奭言:“伏见礼院及刑法司、外州各执守一本《丧服制度》,编附入《假宁令》者,颠倒服纪,鄙俚言词,外祖卑于舅姨,大功加于嫂叔,其余谬妄,难可遽言。臣于《开宝正礼》录出五服年月,并见行丧服制度,编附《假宁令》,伏乞详择,雕印颁行。又礼文作齐衰期,唐避明皇讳,改周,圣朝不可仍避。伏请改周为期,用合经礼。”诏送两制、太常礼院详定闻奏。[3]
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人详定孙奭所奏的五服制度后,进奏仁宗:
“奭所上五服年月,别无误错,皆合经礼。其‘齐衰期’字却合改周为期,以从经典。又节取《假宁令》合用条件各附五服之后,以便有司检讨,并以修正。望下崇文院雕印,颁下中外,所有旧本更不得行用,其印板仍付国子监印造出卖。”
如此看来,刘筠等人是在孙奭编修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更正了个别误字,二是节取了《假宁令》的相关内容各附五服之后,由此撰成《五服年月敕》。从这种意义上讲,《宋史》将刘筠视为《五服年月》的修编者,亦非无据。换言之,《五服年月敕》中是有《假宁令》的内容的。
所谓“《假宁令》合用条件”即是指《假宁令》根据五服制度所规定的相应的官员解官守丧时间以及官员举哀发丧地点。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能找到两则史料证明之:
其一,景祐二年,郭稹是否应当为出嫁母行服。这一问题引发极大的礼学讨论。两制官、礼院官员皆参与其议。太常博士、同知礼院宋祁认为不当行服。翰林侍讲学士冯元引《五服年月敕》驳其说:
参详宋祁所奏疑《五服年月敕》内为父后者为嫁母无解官之文。……况天圣中《五服年月敕》“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降服杖期”,则天宝六年出母并终服三年之制已经行改,不可行用。又《五服年月敕》但言解官。……如非为父后者,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衰服缞杖期,亦解官申其心丧。
按:明钞本《假宁令》载:
诸丧,斩哀(衰)三年、齐衰三年者,并解官。齐哀(衰)杖期及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若庶人(子)为后为其母,亦解官,申其心丧。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
其文意与《宋会要》引文相吻合。
其二,司马光《书仪》卷六《丧仪》二:
盖以《五服年月敕》不得于州县公厅内举哀。
按:明钞本《天圣令》之《假宁令》载:
诸外官及使人闻丧者,听于所在馆舍安置,不得于州县公厅内举哀。
司马光系转述《五服年月敕》,故原文已不可得知,但应与《假宁令》令文大体相同。
是可知《五服年月敕》确有《假宁令》的内容。这与刘筠所说“节取《假宁令》合用条件附于五服之后”是相吻合的。反观《丧服年月》,它由于附在《丧葬令》之后,且《丧葬令》前两卷即是《假宁令》,为紧扣主题,也为了不涉重复,所以删除了《假宁令》的相关内容。因此,《丧服年月》才会在篇首小注中写道:“其解官给假,并准《假令[宁]令》文。 ”
那么,《丧服年月》的内容是否相当于删去《假宁令》后的《五服年月敕》?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五服年月敕》中含有变服、除服的仪程,《丧服年月》则无。
如《宋会要辑稿·礼》二九:
二十二日,太常礼院言:“近依国朝故事,详定仁宗大祥变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以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从吉,已蒙诏可。臣等谨按礼学王肃以二十五月为毕丧,而郑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而二十九月始吉,盖失之也。祖宗时,据《通典》为正,而未经讲求,故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断以二十七月。”
按:此规定不见于《假宁令》。英宗自旁枝继承大统,为仁宗后。因此,自当遵循“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斩衰三年”的制度,为仁宗服丧三年。通过本条史料,即可发现《五服年月敕》规定了“斩衰三年”的除服日期,并可以见得《五服年月敕》对宋初混乱服制的“更定”之用。
又如《宋会要辑稿·礼》三六:
景祐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审刑院言:开封府民单如璧母于姑禫服内争家财。……准 《五服年月敕》:“十三月小祥,除首经。二十五月大祥,除灵座、除衰裳,去经杖。二十七月禫祭,逾月复平常。”
按:此规定不见于《假宁令》。妇为夫之母,齐衰三年。此条史料即是齐衰三年变服、除服的具体程序。
由上述两条史料似乎可以推论,《五服年月敕》中应有根据五服之分制定的变服、除服的程序。
其次,《五服年月敕》有关于官员葬礼仪程的规定,《丧服年月》则无。
司马光《书仪》卷七《丧仪三》:
然礼文多云“三月而葬”,盖举其中制而言之。今《五服年月敕》“王公已下皆三月而葬”。
同书卷八《丧仪四》:
今《五服年月敕》“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三虞而卒哭。”
按:此规定不见于《假宁令》。
要之,根据现有史料辑出的《五服年月敕》,我们可以得知:《丧服年月》除却删去《五服年月敕》中《假宁令》合用条件之外,还删去了变服除服、官员葬礼仪程的规定。
二、形式的简省
《丧服年月》是按五服等级与丧期为标准分作“斩衰三年”“齐衰三年”“齐衰杖期”等九大类服叙。每一类服叙下列相应的亲属关系。如“斩衰三年”条下有“子为父;嫡孙为祖后者,为祖”等。部分亲属关系后有注文。
结合现存史料来看,《五服年月敕》的分类更为细密。如《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五:
熙宁八年闰四月,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李清臣言:“检会《五服年月敕》‘斩衰三年加服’条‘嫡孙为祖’注:‘谓承重者,为曾祖高祖亦如之。’又‘祖为嫡孙正服’条注云:‘有嫡子则无嫡孙’。”
是知《五服年月敕》有“加服”“正服”之分类。
又《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十二:
如非为父后者,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衰服缞杖期,亦解官申其心丧。
伏见《五服制度敕》“齐衰杖期降服”之条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服。”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作“如诸子非为父后者,为出母依《五服年月敕》降服齐衰杖期,亦解官申心丧。”[4]是可证《五服年月敕》中“降服”类。
根据《五服年月敕》现存内容,结合《大唐开元礼》之《五服制度》,《政和五礼新仪》之《五服制度》的体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五服年月敕》每一大类下又按“正服”“加服”“降服”“义服”“殇服”区分排列,但其内部顺序为何已不可知。
三、文字的改动
《丧服年月》对《五服年月敕》文字上的改动主要是注文的改动。《五服年月敕》现存注文五条。通过比勘《丧服年月》与《五服年月敕》之注文,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五服年月敕》注文详于《丧服年月》
(1)《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五:“熙宁八年闰四月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李清臣言:检会《五服年月敕》‘斩衰三年加服’条嫡孙为祖。注:‘谓承重者,为曾祖、高祖后者亦如之。’”
《丧服年月》“斩衰三年”嫡孙为祖后者,为祖。注:“为曾、高后者亦同。”
按:《丧服年月》无“谓承重者”四字,对“嫡孙”一词并无解释。
(2)《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六:“礼官言:《五服年月敕》‘齐衰三年’为祖后者,祖卒则为祖母。……又曰‘齐衰不杖期’为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唯为祖后者乃不服’。”
《丧服年月》“齐衰不杖期”为祖父母。注云:“父所生庶母同。”
按:《五服年月敕》多“唯为祖后者乃不服”一句,可见其规定更为细密。
2.《五服年月敕》注文与《丧服年月》文字全异
《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十:“伏见《五服制度敕》‘齐衰杖期’之条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服。’注曰:‘谓不为父后者。若为[父后者,为出母]、嫁母无服。’”
《丧服年月》“齐衰杖期”父卒,母嫁出及(及出)妻之子为母。注:报服亦同。
按:“为父后者,为出母”此六字据《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十一、《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十二补。《宋会要辑稿·礼》三六:“《礼记正义》、《开宝通理(礼)》、《五服年月敕》皆言为父后者,为出、嫁母无服。”“如非为父后者,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齐服衰杖期,亦解官。”
3.《五服年月敕》《丧服年月》文意全同,文字微异
《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四:“礼官言:《五服年月敕》‘齐衰三年’为祖后者,祖卒则为祖母。注云:‘为曾高祖母亦如之。’”
《丧服年月》:“齐衰三年”为祖后者,祖卒为祖母。注云:为曾、高后者亦同。
按:相比之下,《丧服年月》意义更为显豁。《五服年月敕》的注文很容易令人误解成祖父死后,承重孙为祖母、曾祖母、高祖母皆服齐衰三年。
4.《五服年月敕》有注,而《丧服年月》无
(1)《宋会要辑稿·礼》三六之六:“又(《五服年月敕》)‘祖为嫡孙正服’条注云:‘有嫡子则无嫡孙。 ’”
《丧服年月》“为嫡孙”条下无注。
(2)朱熹与门人议礼之时,曾有人问:“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题主当何称?”朱熹遂道:“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谓所生己者’,则但谓之母矣。”[5]
按:据此可知,《五服年月敕》曾于“母”字下有注。但具体注于何处则不可得知。《丧服年月》无此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天圣《假宁令》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假宁令》:“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小注云:“皆为生已(己)者。”如此看来,朱熹提及的“母”字下注似乎当属于《丧服年月》所删去的《假宁令》中的内容。但囿于史料有限,今暂附于此,俟后再考。
如前所述,《丧服年月》的注文并不是单纯地删减,而明显是修令者根据实际需要出发重新写定的(说详后)。
但也有例外。《丧服年月》与《五服年月敕》正文偶见不同。如北宋杨杰《无为集》卷八《皇族服制图序》:
《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兄弟之长殇小功三月;为其兄弟之中殇、下殇,缌麻三月。《开宝通礼》、《丧葬令》文皆同。 ”
按:《丧葬令》文即《丧服年月》作“为人后者,为其兄弟之长殇小功五月”,与杨杰所引《五服年月敕》并不相同。
考诸《仪礼·丧服》《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之五服制度并作“小功五月”。关于为人后者为其兄弟之长殇的持服,宋人从未提出异议。因此,《五服年月敕》似也应作“小功五月”。
《无为集》作者杨杰是北宋神宗、哲宗间著名的礼学家,“曾官太常数任,一时礼乐之事,皆预讨论。”[6]他自号“无为子”,故而南宋赵士粲收其遗作,题之为《无为集》。具有如此深厚的礼学修养的杨杰在为《皇族服制图》作序时,应该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这样看来,“小功三月”或是传抄之讹。但因史料不足,姑且存疑,俟后再考。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丧服年月》是在《五服年月敕》的基础上经过重新编排、删削、改写而成的改编本,并不能单纯地视之为节略版。
至于将《五服年月敕》改编为《丧服年月》的目的,恐怕要回到前引孙奭与刘筠的奏文中探讨。天圣五年,孙奭奏言:“伏见礼院及刑法司、外州各执守一本《丧服制度》,编附入《假宁令》者,颠倒服纪,鄙俚言词,外祖卑于舅姨,大功加于嫂叔,其余谬妄,难可遽言。”意在指出宋初服纪制度混乱,中央礼法机构和地方政府各执一词,给司法、礼仪事务处理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刘筠在修订孙奭编撰的五服制度后,也特别强调,“以便有司检讨,并以修正”。其最终的旨归都在于出台统一的五服制度,以便有司随时检讨。于是,当年仁宗便颁布《五服年月敕》以规范五服制度。天圣十年以令文形式发布的《丧服年月》自然也有着相同的目的。[7]《玉海》卷第六百六十六《诏令》:“(天圣)七年六月,上之赐器币,进勋阶。九月,诏下诸路阅视,听言未便者书目。《天圣令文》三十卷,时令文尚依唐制,夷简等据唐旧文,斟酌众条,益以新制。天圣十年行之。”本条史料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一,吕夷简等人于天圣七年进《天圣令文》,实际上经过了长达三年的试用期,直至天圣十年才正式行用的。二,吕夷简等人在编撰《天圣令文》时,“斟酌众条,益以新制”,也间接可证明皮氏观点,即《丧葬年月》附于《丧葬令》后是天圣令编修者的创举。此段史料前贤似未发见,今特此揭出。
除却这一共同目的外,《丧服年月》的编撰者显然还有别的考量,即令《丧服年月》成为官员处理丧服问题的简明工作手册。
第一,《丧服年月》仅保留了与丧服、服丧年月有关的内容。此处值得探讨的是,《丧服年月》的定名缘由。曾有学者认为,《丧服年月》之得名是编撰者为紧扣《丧葬令》“丧葬”这一主题。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丧服年月》之所以名为“丧服年月”,而不名为“五服年月”,事实上是因为“丧服”与“五服”的概念有微妙不同。早在宋代以前,这种差异便已存在。《仪礼正义》卷二十一《丧服经传》引唐代贾公彦疏云:“郑《目录》云:‘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 ’”[8]换言之,丧服包含服丧穿的衣服、服丧年月、因亲疏有别而隆杀不同的礼节。我们可以发现,“丧服”最后仍被归结于礼仪,故而它仅适用于与丧葬礼制有关的文献。而“五服”虽然许多时候与“丧服”混用无别,都可用来表达五等丧服,但它更多地则是强调亲疏等级,即由五等丧服衍生出来的亲属之间的亲疏等级。《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韦绦传》:“自高祖至玄孙并身谓之九族,由近及远,差其轻重,遂为五服”,可证。自魏晋“准五服入罪”以来,“五服”成为司法量刑、官员给假的准则。所以,“五服”的涵盖范围远比“丧服”广泛。至宋代,宋人语境中的“五服”与“丧服”也继承了这种细微的区隔。很明显的一例便是孙奭的奏言“臣于《开宝正礼》录出五服年月,并见行丧服制度,编附《假宁令》。”显然地,在他的概念里“五服”、“丧服”的概念是不相混淆的。天圣《假宁令》亦将五服轻重作为解官给假的依据,如“诸齐哀(衰)期给假三十日,闻哀二十日,葬五日,除服三日。”综上所述,《五服年月敕》在仅仅保留与丧服有关的内容后,“五服”二字自然也就不再适用。可以说,《丧服年月》之得名是取决于其实际内容的。
第二,《丧服年月》删除《五服年月敕》每一大类下“正服”“加服”“降服”等分类。加、降、正、义服由东汉郑玄提出,后代礼学家莫衷一是,迄今亦无定论。也就是说,加、降、正、义服是礼学范畴的概念。这些分类的删除令《丧服年月》的编排更为简明,也显示出编撰者力求简明扼要的撰作意图。
第三,《丧服年月》改写了《五服年月敕》原有注文,或是删减原注。关于改注尤为显著的一例应是“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服”条下,《五服年月敕》注云:“谓不为父后者。若为[父后者,为出母]、嫁母无服。”《丧服年月》小注仅云“报服相同”。可见,《五服年月敕》强调的是诸子是否为父后这一点,而忽略了出母、嫁母是否为子持服。《丧服年月》则重在指出,出母、嫁母与子之间报服相同。因此,《丧服年月》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涵盖各类亲属关系种类,使得有司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就能立即找到法理依据。至于删减注文,其目的应与删除分类相同,正是为了全文能够清晰明白,一目了然。
在实际行用中,《五服年月敕》与《丧服年月》并行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宋代令、敕之别。一则令、敕的法律适用性、优先性不同。略论之,敕令优先于律,敕又优先于令。[9]《宋会要辑稿·刑法》载《政和重修敕令格式》之《名例敕》云:“诸律、《刑统疏议》及建隆以来赦降,与敕、令、格、式兼行。文意相妨者,从敕、令、格、式。”是其证。二则令、敕功能分野不同。宋神宗曾言:“禁于未然谓之令,治其已然谓之敕。”《丧服年月》与《五服年月敕》的关系也是如此。前者篇题下小注言:“言礼定刑,即与《五服年月敕》兼息(行)。”宝元二年,史馆检校、同知太常礼院王洙的奏言也说得相当明确,“今以《令》、《敕》之条不载,六经之文不出,辄引以为据,废格制书,臣所以不敢雷同具奏。臣非好立异议,唯知谨守敕文,不可临事改易。且礼法之局,所共执行,于法则议刑,于礼则制服。”由此可见,归属于令文的《丧服年月》其功能在于“言礼”,也就是根据礼法规定丧服制度。《五服年月敕》之功能则在于“定刑”。但凡是违背了《令》文所规定的条目,便会根据敕文将会受到惩罚。这也是唐代以来“失礼入刑”,礼法结合日益紧密的又一次体现。
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五服年月敕》与《丧服年月》内容可以相互补充,也是两者并行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两者内容彼此有异同,可以相互补充。二是宋代令敕有别。首先敕的法律优先性大于令。其次,令敕功能分野不同。令为禁于未然,敕则治其已然。至于《五服年月敕》与《丧服年月》之区别亦是在于“言礼定刑”。丧服制度,若未曾触犯,则有《丧服年月》,若已触犯,则有《五服年月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北宋时期严密的丧服制度。
[1]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359-367.
[2]皮庆生.唐宋时期五服制度入令过程试探——以《丧葬令》所附《丧服年月》为中心[J].唐研究,2008(14):381-411.
[3]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审稿.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38-1548.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宋)王应麟.玉海[M].扬州:广陵书社,2007.
[8](清)胡培翚.仪礼正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9]魏殿金.宋代刑罚制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9: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