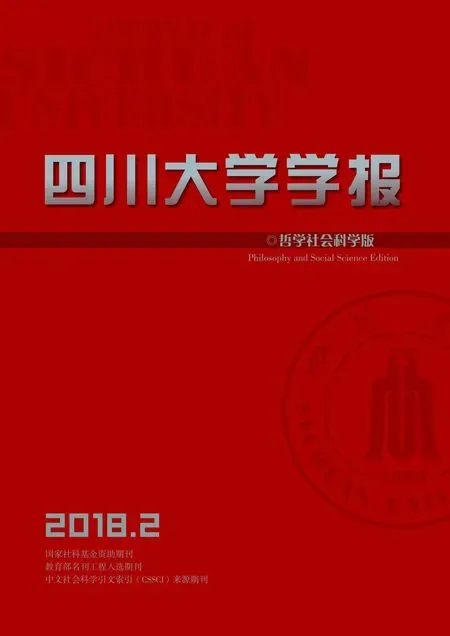军社之祀与《诗经》军征之诗的生成语境
《礼记·王制》言:“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371页。商周军事活动如田猎、出征、凯旋、战败等中,皆有祀军社之礼。*郭旭东:《殷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礼》,《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47-69页;刘桓:《卜辞所见商王田猎的过程、礼俗及方法》,《考古学报》2009年第3期,第321-348页。从考古资料来看,良渚文化祭坛用三色土封筑而成,是为早期社祀之所。*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32页。铜山丘湾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一号遗址、殷墟内社祀遗址以及清江社祀陶文,则显示商朝已经具有完善的社祀制度。*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9-106页。甲骨卜辞也表明殷商时期已建立成体系的祀社制度,并随时随地向社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址的推定》,《考古》1973年第5期,第296-298页;王宇信、陈绍棣:《关于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文物》1973年第12期,第55-58页;王震中:《东山嘴原始祭坛与中国古代的社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第82-91页;具隆会:《甲骨文与殷商时代神灵崇拜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126页;常玉芝:《商汤时的祖先崇拜与社神崇拜》,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2-92页。从文献资料来看,周代的军社之祀主要有出征告社、凯旋报社、战败祓社、田猎祭社与祊等仪式。《诗经》的邦风及“小雅”有诸多诗篇与军社之祀有关,考察这些作品对军社之祀的描写,既有助于考证军社之祀的原始礼义,又有益于辨析此类诗歌形成的文化语境。若结合有关史料来辨析这些诗歌产生及其使用的机制,还能立体地观察出相关诗篇的制度背景,深化对《诗经》所载礼乐制度的解读。本文试论之。
一、宜社与征伐之辞

《墨子·迎敌祠》具体记载了军事行动时对社、庙的祭祀:
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先于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庙,……既誓,公乃退食。舍于中太庙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门,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练名。射参发,告胜,五兵咸备。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马射自门右,蓬矢射之,茅参发,弓弩继之,校自门左,先以挥,木石继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77-578页。
假如有敌攻城,由祝、史依照祭祀仪式报告给四方之神、山川之神与社稷之神,然后国君与将士在太庙举行誓师仪式。《礼记·祭义》言:“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344页。国君驻扎在太庙之右,实际是在庙与社之间坐镇指挥,祝官、史官则守在社中进行祈祷,以求得先祖和土地之主的护佑。在交战过程中,祝官、史官及宗人随时向社神报告作战进展,以求社神庇护。
《孔丛子·儒服》更为详细地描述了战前宜社的方式:
子高适魏,会秦兵将至,信陵君惧,造子高之馆而问祈胜之礼焉。子高曰:“命勇谋之将以御敌,先使之迎于敌所从来之方为坛,祈克乎五帝,衣服随其方色,执事人数从其方之数。牲则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庙、邦域之内名山大川。君亲素服,誓众于太庙,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国,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将帅稽手,再拜受命。既誓,将帅勒士卒,陈于庙之右,君立太庙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庙门。诏将帅命卒,习射三发,击刺三行,告庙,用兵于敌也。五兵备效,乃鼓而出以即敌,此古诸侯应敌之礼也。”
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问子高曰:“古者军旅赏人必于祖,戮人必于社,其义何也?”答曰:“赏功于祖,告分之均,示弗敢专也;戮罪于社,告中于土,示听之当也。”*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8页。
信陵君为魏之贤臣,向子高询问应敌之法。可知春秋时常用的宜社之制,战国时已不常使用,故信陵君不明。子高所言,为我们补充了宜社的若干细节:一是面向迎敌的方向设坛,进行祊祀,以求某方之神护佑;二是同时祈告社稷之神及境内的山川土地之神,以求神灵保佑领土不失;三是国君告祖,以祈有功;祝、史守社,以求无过,是为战前告庙宜社之礼。
《史记·秦本纪》曾记载秦襄公拥立平王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史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9页。其所祀之西畤,是为祊祀,即祭祀秦所在的西方神灵。根据对礼县西山遗址的发掘,可知秦之西畤采用封土为台,折地为堑,祭祀采用瘗埋的方式进行,*王志友、刘春华、赵丛苍:《西畤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秦俑博物馆,2009年,第236-249页。符合西周祀地之法。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只能祀社稷而不郊天。秦襄公初封,西畤作为秦之地望,为秦祀地之所。周桓王之后,政由方伯出,诸侯方才称王而祭天。按照毛传说法,《秦风·终南》乃写襄公“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24-425页。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亡。
据《礼记·玉藻》所载:“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故诗中提到的“黻衣绣裳”,是为诸侯祭服。《礼记·祭义》亦言:“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分别参见《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900、1330页。诗中写秦襄公着诸侯之礼服至终南山,然后换上祭服以祭。故此诗乃写秦襄公以诸侯身份祀境内名山,与前文所言的诸侯祀“邦域之内名山大川”相合。其中所言的“有纪有堂”,王引之《经义述闻》释之为“有杞有棠”,言其写景物;*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7-138页。《小雅·南山有台》亦有“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之言,杞有本字,不必另行假借。故“有纪”一词,当言秦以诸侯称而有号纪年;有堂,乃赞美秦国立社以望祀山川。结句所言的“寿考不亡”,乃祈社时的祝辞。《墨子·明鬼下》中引祀社古辞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岁于社者考,以延年寿。”与之相应。*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八《明鬼下》,第242-243页。由此来看,此诗收入《秦风》,是为秦初望祀终南之歌。
战前宜社,常采用衅社的方式进行,即“杀生以血浇落于社”。*见《管子·小问》“桓公践位,令衅社塞祷”尹注。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67页。《公羊传》解释鲁僖公十九年(前641)“邾娄人执鄫子用之”:“恶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盖叩其鼻以血社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40页。战前举行衅社之礼,以求社神保佑军事行动。祭社之肉分赐给出征将士,是为受脤。《国语·晋语五》中载郤献子之言:“受命于庙,受脤于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0页。《左传·闵公二年》载晋国梁余子养之言:“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15页。言在出征仪式上受赐祭社之肉,接受社稷重托。鲁成公十三年(前579)晋侯伐秦,成子行受脤之礼时不敬,还引起了刘子的批评。既然受脤于社,意昧着承诺保卫国土,其不能全力以赴者,收兵后即惩处于社。
《秦风·无衣》乃写秦誓师出征之礼。《左传·定公四年》载楚臣申包胥入秦求援,秦初不为所动,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558页。秦哀公之赋《无衣》而出兵,正在于《无衣》本为秦誓师之辞。其中所言的“同袍”“同泽”“同裳”,以及修“戈矛”“矛戟”“甲兵”等词,是对秦地百姓由农时转向战时状态的描述。从《睡虎地秦竹简》中的《金布律》来看,秦实行授衣、禀衣制度,秦之官吏、隶臣以及囚犯可以免费领取衣服。*于洪涛:《试析睡虎地秦简中的“禀衣”制度》,《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第38-43页。《无衣》中所言无衣而能同袍,一如《小雅·出车》所言的“既成我服”“共武之服”、《邶风·击鼓》中的“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是写将士换上戎装,配备武器盔甲,出师应敌。
如果国君亲自出征,需要载社主而行。*军事活动只载社主出行而不载稷神,在于军旅不涉农事,见《后汉书·祭祀下》:“古者师行平有载社主,不载稷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00页。《左传·定公四年》载祝鮀拒绝卫灵公令其随从会同的说辞:“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社稷不动,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师从,卿行旅从,臣无事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544页。祝官乃选取“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八,第236页。以守社祀。若社主动则祝官遂行,社不动则祝不行。卫灵公参加会同而非出战,依礼社主并不随行,故祝鮀拒绝随军同行。
从《孔丛子·问军礼》所言细节来看,战时所载社主,乃便于祃祭:
以斋车载迁庙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马职奉之。……主车止于中门之外、外门之内。庙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经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将士战,全已克敌。史择吉日,复祃于所征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顿兵伤士也。战不克,则不告也。凡类、祃,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刚日,有司简功行赏。……其奔北犯令者,则加刑罚,戮于社主之前。然后鸣金振旅,有司遍告捷于时所有事之山川。*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六《问军礼》,第421页。以下所引此篇文字皆见420-422页,不一一标注页码。
《大雅·皇矣》曾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034-1035页。便是战时祭祀天地。应劭曰:“礼,将征伐,告天而祭谓之类,告以事类也。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谓之祃。”*《汉书》卷一百《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269页。据《问军礼》,祃祭祀地,若国君亲征社主随行,则祀于军社。若只是命将出征,不设军社,只是“告太社冢宰执蜃,宜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将”,军队便不祭天祀地,“其出不类,其克不祃,战之所在有大山川,则祈焉,祷克于五帝,捷则报之”,只是祭祀所经过的山川之神与五方之神而已。
国君出征载社主而行,一出于社稷之祀,二在于警戒将士。《尚书·甘誓》载夏启作战前的动员令:“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传注:“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天子亲征,又载社主,谓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亲祖严社之义。”*《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73页。是篇或伪托,然所言之制不虚。《周礼·秋官司寇·大司寇》言:“大军旅,莅戮于社。”*《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910页。战时在社中惩处不用命者,是为常制。《墨子·明鬼下》的解释是:“圣王其赏也必于祖,其僇必于社。赏于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听之中也。”*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八,第235页。国君受命于天,其赏赐部属,在宗庙中命爵命,是赋予天命;既有授命而不能保卫土地者,则于社中惩处。故《孔丛子·问军礼》进一步解释说:“其用命者则加爵受赐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则加刑罚戮于社主之前,然后鸣金振旅。”一因作战在于保卫土地,社是为土地之主,不用力者便是对不起社主;二在于天主阳而地主阴,阳赏阴罚,故出兵授命于庙,而刑罚则于社中。
宜社之祭,是两周重大军事行动中进行的祭祀活动,社主为一方土地之主,对其进行祭祀,乃求其保佑疆域不变、领土不失。将领既受脤于社,意味着接受国君及社稷的重托,万死不辞以卫国,故不用命者戮于社而报之,是为惩戒。
二、战后告社与凯乐、祓社的使用
战前宜社,意在祈求鬼神的保佑;战后告社,意在报知社神之结果。上博简《鬼神之明》言:“此以桀折于鬲山,而受首于岐社,身不没为天下笑。”*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言武王伐纣成功之后,曾将殷纣之首献于岐社。*《史记·周本纪》言周武王“以黄钺斩纣头”,《逸周书·世俘解》载周武王在周庙举行献俘之礼,所载意思不同,则纣之头被载入周则无疑。参见《史记》卷四,第124页;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39-442页。《礼记·大传》追述武王克商之后: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998页。
柴于上帝,是以禋祀郊天;祈于社,是以瘗埋祭地;设奠于牧室,是为享祖。凯旋之礼有盛大的祀社仪式。《周礼·夏官司马》言大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王吊劳士庶子,则相。”*《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782-783页。无论胜、败都要举行告社仪式,胜用凯乐,败则祓社。
凯乐,是为战胜之乐。《周礼·春官·大司乐》亦言:“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郑玄认为“大献,献捷于祖”,*《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92页。乃将献凯乐于社与献凯乐于祖相混淆。《孔丛子·问军礼》明确言战胜之后,“反社主如初迎之礼,舍奠于帝学,以讯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备乐,飨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焉,谓之饮至”。此以君王亲征之礼为例,言战胜之后要返社主于社,先献乐于社,再献乐于庙。如果是将帅出征,得胜之后,则“振旅复命,简异功勤,亲告庙告社而后适朝”,国君不亲征凯旋仪式,是先告庙而后告社。告庙、告社都有大司乐奏乐作为凯歌。
《周礼》记述了凯乐的演奏机制,大司乐于“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由大司乐主持凯乐演奏。乐师教歌演唱,“凡军大献,教恺歌,遂倡之”。视瞭,“凡乐事,相瞽;大丧,廞乐器;大旅,亦如之。宾射,皆奏其钟鼓。鼜,恺、献,亦如之。”*《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601、618页。乐师、视瞭参与凯乐演奏。《吕氏春秋·古乐》记武王伐商胜利之后,即位于商之太社,“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7页。上博简《鬼神之明》言“受首于岐社”,是为周曾献纣王之首于岐社。《大雅》中的《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等本为《大武》歌辞,*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48-50页。为周人在宗、社举行盛大献俘礼时所用的凯乐之歌。
如若战败,则要送社主归于社时,并举行祓社仪式。《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郑国攻入陈国,郑、陈两国君臣举行仪式:
陈侯免,拥社,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子展执絷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美入,数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019页。
陈哀公免冠,抱着社主之牌位,其亲族部属皆捆绑列队,以表示听命于郑国将士。陈之社主为陈国土地之主,是陈国国君拥有陈地的象征。抱着社主向郑国投降,意味着奉土地而听命,向郑国承认失败,郑军统帅子展、子产接受了陈君的投降。然后,郑国随军的祝官在陈之国社举行祓社仪式,既表示战争已经结束,也宣示陈之社主听命于郑。
鲁僖公六年,许国城破时,许僖公也按照周礼,“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向楚王受降,没想到楚王不明白该如何对待这一仪式。逢伯言:“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衬,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48页。逢伯认为应该按照当初微子启向武王投降的仪式,接受他的进献,并焚毁其自带的象征用于受死而敛的棺木,命令其继续出任国君,楚王遂依礼而行。其中的“受璧而祓之”,即接受其象征权力的玉璧,并令祝官在许社举行祓社仪式,表明国家灾难已经过去,许国从此听命于楚。在上述事件中,陈国、许国战败而未亡国,事后由史祝祓社,两国国君继续统管所辖土地。
倘若战败者亡国,胜者则封亡国之社。周灭商,以商之亳社为亡国之社。宋为殷之后,遂以亳社为国社。《左传》载鲁襄公三十年(前544)鸟鸣于亳社、鲁哀公四年(前492)亳社灾,皆意味着宋有变故。鲁昭公十八年(前525),子产在亳社举行盛大的社祀仪式,祓禳四方,振除火灾。伯禽率殷民六族以封鲁,鲁以亳社作为殷人之社,名为亳社。鲁昭公十年季平子取郠,便献俘于亳社;鲁哀公七年,鲁攻邾,俘邾隐公益,亦将之献于亳社。由此可见,宋、鲁之亳社作为殷民之社,仍然承担着护佑一方百姓的职能,但形制有所变更。《吕氏春秋·贵直》载狐援曾说齐湣王:“殷之鼎陈于周之廷,其社盖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国之音不得至于庙;亡国之社不得见于天;亡国之器陈于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无使齐音充人之游。”*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621-622页。言战败之国的社,不再具有祭一方土地的功能,原本用于祀社告庙的音乐,只能作为地方乐歌而不再用于告社。狐援以此提醒好乐的齐湣王要努力工作,不要令齐国亡国,使得齐音不能用于祀社。
战胜用凯乐,战败祓社也依乐歌哭。《孔丛子·问军礼》载:“若不幸君败,则驿骑赴告,不载櫜韔。天子素服,哭于库门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将失城,则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军,命将帅无请罪,然后将帅结草自缚,袒右肩而入。盖丧礼也。”是言战败需要在社中举行歌哭仪式。《左传·闵公二年》载许穆夫人赋《载驰》,杜预注:“许穆夫人痛卫之亡,思归唁之,不可,故作诗以言志。”*《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12页。毛传言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於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10-211页。吊失国曰唁,此诗当乃许穆夫人吊卫之亡国的哀辞:“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几可听闻哀哭之音。
此外,《左传·闵公二年》又载:“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13页。毛传据此认为此诗意在“刺文公也”,为郑人战败之歌;又言《王风·兔爰》亦出于“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所作,*《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86页。当为战败之歌,作者在诗中感慨自己“逢此百罹,尚寐无吪”“逢此百忧,尚寐无觉”“逢此百凶,尚寐无聪”,便是对失败的无可奈何之辞。《唐风·采苓》亦写战败之事:
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 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阳之下。人之为言,苟亦无与。 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阳之东。人之为言,苟亦无从。 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理解此诗的关键是“舍旃”,郑玄认为“旃”是“之焉”的合声,*《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03页。乃依毛传刺晋献公好听谗的理解注释。从礼制来看,“旃”之实义,乃为七命诸侯所用的旗帜。周制,诸侯之旗用釆,其中通帛为旃,析羽为旌,为战时招致将士的标志。《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400页。齐之先君为七命之侯,以旃为旗帜,用于号令五命之大夫。由于齐侯不按照礼制招致部下,因而虞人拒绝其征召。《释名·释兵》言:“通帛为旃。旃,战也。战,战恭己而已也。三孤所建,象无事也。”*刘熙:《释名·释兵》,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14页。旃是诸侯赐命的象征,晋之旃为晋国君权的象征。舍旃,是言晋君之失其君权。从史料来看,晋之君权转移,常由仇杀而起,穆侯太子仇率袭殇叔而立;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曲沃庄伯弑孝侯,周平王使虢公伐之而立哀侯;曲沃武公杀晋哀侯而即位。晋献公之前,君权屡失,是为舍旃。晋君以仇杀更立,使得礼义崩坏,军队无所适从,原先的约定承诺皆不可信,诗写人言难信之叹。
由此可见,战前告社、战后报社,是军事行动的基本礼仪,告社意在鼓舞将士保卫社稷;国君亲征,社主遂行,战前战后要迎社主、还社主于社,随即以社乐演奏。国君不亲征,则只举行告社、报社仪式,胜则凯乐、败则歌哭。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誓师、凯乐、歌哭之辞,成为《诗经》相关诗篇的生成机制。
三、献禽祭社与田猎之诗的形成
《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载田猎之制,为春献禽以祭社,夏献禽以享禴,秋献禽以祀祊,冬献禽以享烝。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目的,乃“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93页。利用农闲训练军队。从甲骨卜辞来看,“禽”乃“擒”之初文,*孟世凯:《商和西周时期献禽制初探》,《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第7-11页。甲骨文亦有献获、献禽之说,“献禽”即“以所获禽祀四方之神也”。*《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36页。《周礼·春官宗伯·小宗伯》所谓“若大甸,则帅有司而馌兽于郊,遂颁禽”,*《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95页。即言田猎后军队以所获之物献于神灵。
《秦风·驷驖》是为田猎献禽之礼所用辞,毛传认为其乃美襄公“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诗写冬狩,着重强调田猎所献猎物之大:“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毛传言其按时献禽:“辰,时也。牡,兽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鹿豕群兽。”*《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11、412页。乃赞美秦公下令以后按时田猎为制,取所获野兽以献。与之类似的《齐风·还》,亦赞美田猎时武夫的合作狩猎,如“并驱从两肩兮”“并驱从两牡兮”“并驱从两狼兮”,双方相互称赞对方勇武,其中的驱狼校猎,乃写冬猎场景。
毛传将《郑风》之《叔于田》《大叔于田》释为言共叔段“多才而好勇”,并认为共叔曾田猎于京,诗写田猎意在“刺庄公”。*《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82、283页。其中《叔于田》按照叔于田、叔于狩、叔适野为次,赋田猎出行之场景。《大叔于田》紧随其后,写冬猎的场面,其中的“火烈具举”“火烈具扬”“火烈具阜”,是为冬猎时的火田仪式。*《尔雅注疏·释天》言:“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宵田为獠,火田为狩。”《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83页。此二诗乃赋郑国冬猎之壮阔场面,其中的“襢裼暴虎,献于公所”,乃言共叔肉袒搏虎而擒之,献于庄公。公所,国君所居之所。《礼记·玉藻》:“将适公所,宿齐戒,居外寝,沐浴。”*《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884页。
《卫风·芄兰》,毛传言之为“刺惠公也,骄而无礼,大夫刺之”,*《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37页。徐绍桢则认为:“当是惠公初即位,以童子而佩成人之觽,行国君之礼,其大夫作诗美之,欲勉其进德耳。”*徐绍桢:《学寿堂诗说》卷三,引自张树波:《国风集说·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4页。从诗中所涉名物来看,实写秋季田猎之事:“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虽则佩觿,能不我知。……虽则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带悸兮。”其中的芄兰,乃种植于田猎之所的边界,汉代称艾兰。*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有:“艾而张罗,行成之。四时和,山出黄雀亦有罗,雀以高飞奈雀何?为此倚欲,谁肯礞室。”亦是写田猎时的情形。沈约:《宋书》卷二十二《乐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40页。《谷梁传·昭公十二年》:
秋,搜于红,正也。因搜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以葛覆货以为槷。……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84-285页。
其中的“防”,范宁注:“防,为田之大限。”秋猎以射为主,未成年的童子佩觿、佩韘随父母射猎。《礼记·内则》:“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829页。刘向解释觽、韘的象征意义为:“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烦决乱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军者搢笏;衣必荷规而承矩,负绳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五貌而行能有所定矣。”*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2页。童子佩觽、韘,乃列席秋季田猎,一个个如同大人一样威严。
夏猎、冬猎之后献禽,用于祭祀先祖。《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60页。《小雅·天保》亦言:“禴祀烝尝,于公先王。”《小雅·车攻》先写夏季田猎活捉猎物:“建旐设旄,搏兽于敖”;尔后写献祭:“徒御不惊,大庖不盈”。朱熹注:“大庖,君庖也。”*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8页。《周礼·庖人》载庖人“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鲜羽,膳膏羶;岁终则会。”*《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89页。由庖厨烹饪所获猎物,先献祭先王先公,然后周王与将士一起饮酒。《小雅·吉日》所言“兽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从,天子之所”,是将所获的野兽汇聚到天子之所,将士们“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与天子一起举行宴饮;“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656-658页。则是描述田猎之后举行的饮至之礼。*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6-197页。
周制,春猎祀社,秋猎祀四方。《周南·兔罝》亦写田猎之事,诗以设置“兔罝”的过程为兴词,依次写打木桩固定罟罝、将之放在路口、林中,以捕获野兔,进而写公侯率领赳赳武夫捕猎。《墨子·尚贤上》认为此诗中所谓的“武夫”,是言闳夭、泰颠:“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毕沅注云:“事未详。或以诗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诗而为说,恐此诗即赋闳夭泰颠事。古者书传未湮,翟必有据。”*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二,第47-48页。认为可能墨翟时有相关的传说,后世不闻,可知此诗或为周初言田猎之歌。
与夏、冬享先王用熟食不同,祀社采用血食,即当场宰杀活牲,以其血衅地,以其骨掩埋,为祀社之礼。《周礼·春官宗伯》中载“肆师”负责血牲:“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则为位。”郑玄注:“师甸,谓起大众以田也。”*《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685页。在大规模田猎之后的祀社仪式,肆师辅佐宗伯设置几筵,宰杀用于祀社、祀四方神之牲。
由此进一步观察《周南·麟之趾》,其当为春秋献兽之辞。郑笺:“麟信而应礼。”*《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60页。《春秋》载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皆将麟视为秋猎时捕获的祥兽。《左传》解释为:“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钅且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673、1676页。若春秋时仍有麟存在,则《召南》之麟,绝非空想之说,亦有可能为田猎献麟之辞,以此祝愿周王室能够绵延不绝:“公子、公姓、公族,皆指后嗣而言,犹《螽斯》之言宜尔子孙也。”*王引之:《经义述闻》,第120页。麒麟象德,《周南》以之作结,用以赞美周公之德化。
这样来看,《召南》以《驺虞》作结,亦出于类似的意味。《召南·驺虞》,戴震认为是写春猎:“见春蒐之礼也,除田豕也。”*戴震:《毛诗补传》,《戴震全书》卷二,黄山:黄山书社,1994年,第一册,第178页。其中的“彼茁者葭”,是为季春物候。而“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则赞美射猎者:驺乃养马之官,虞为林泽之官,二者连用乃言春蒐将士射术精湛。《周礼·天官冢宰》言:“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时田,则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00-101页。既言四时献不同的猎物供田猎所用,又言其在田猎时与甸祝等官吏一起将猎物置于猎场之中,并守护网罟而猎获之。《墨子·三辩》:“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一,第41页。故《邹虞》作于周初,当为成王时的春猎之歌。春秋以驺虞为祥兽,郑笺:“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06页。驺虞象信,以之为《召南》之卒篇,用以昭示召公的信义。
《周南》《召南》分别以《麟趾》《驺虞》结束,实乃写田猎献祭之礼。毛传解释二南以《关雎》《鹊巢》为始,而以《麟趾》《驺虞》为终的原因:“《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9页。认为《周南》为王者之风,《召南》为诸侯之风,二者为礼乐而治的典范,故列之于众风之首。若就礼制而言,二南开篇分别以《关雎》《鹊巢》写夫妇婚嫁之事,出于衽席;《麟趾》《驺虞》乃写田猎、献祭之礼,出于治道。家齐而后国治,二南为周之燕乐,其有着严格的排序,正体现着从衽席到王道、从文治到武功的用意。